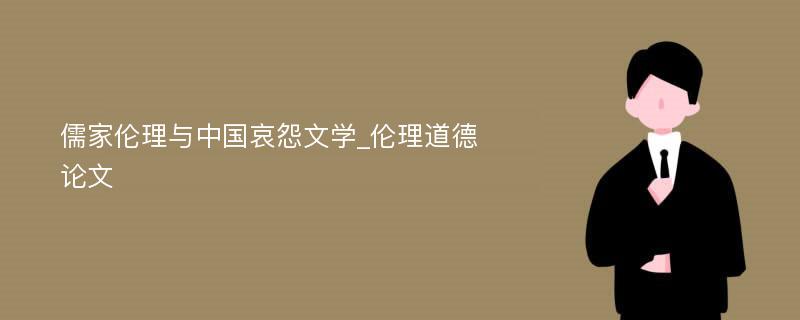
儒学伦理道德与中国悲怨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伦理道德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伦理道德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有着生命一样的意义。文学作为生命的外化形式,它的发展节奏与道德之生命节奏存在着特殊的合拍关系:既促进又阻碍。这一点无论对于思想史还是文学史皆有其独到的认识价值,故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中的悲怨角度对这方面问题作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探讨。
一
毫无疑问,伦理道德生命的社会群体特点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根据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我国先秦时期还只是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孕育阶段。此时期充斥着自然神学(祖先—神教)和民体思潮。社会义务和个体发展呈现着杂乱无章的混合态。统治阶级的思想还没有真正形成统治社会的思想,宗法伦理制度还没有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心理规则。正因为如此,伦理道德社会义务和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还不足以形成严重的心理冲突。无论在《诗经》还是在《楚辞》中,伦理道德还属于外在的东西,它和个体生命发展的努力之间基本上还是各不相扰的关系。就《诗经》而言,这典型地表现在风、雅、颂三部分的并立上。作为最能体现宗法伦理制度的颂诗和一部分雅诗,虽然代表着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但始终缺乏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生命活力。如前所析,真正充满生命活力的“风”和“小雅”中很少有伦理道德义务有力量因素。即使是充满爱国忧民情绪的屈赋,也很少基于伦理道德的力量。汉代史学家班固即曾据此加以贬责:“今若屈原,露己扬才,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悉神若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狂狷之士也。”(《楚辞序》见洪兴祖《楚辞补注》)。的确,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屈原的爱国主义并非基于一家一姓的愚忠,而是出于国家和万民的大义,这就难怪生于独尊儒术的汉代且又满腹经义的班固对此不满并加以责难了。其实又何止屈原,即使其后的宋玉、景差之流,虽然不及屈原的高洁远志,慑于权威,“终莫敢直谏”,但在作品中所表露的还是个体生命遭受压抑的悲怨,其中仍较少伦理道德的生命力量。当然,也不能说先秦时代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还没有形成,我们称之为“孕育”,实际上即意味着它们已经形成,只不过还没有脱离母体,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以及还没有在社会实际上即为伦理道德观念生命化的开始。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创举,它为后来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宋明理学(心学)奠定了始基。除此而外,老、庄、墨、荀诸家均为这种道德生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注入了生长的因子,只是因为此时期还正处于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兴起阶段,这种道德生命还未能迅速地系统化并构成社会思想文化的权威部分,因而在人的本体生命中还未能形成它的主导地位。如此状况直到秦亡汉兴仍旧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被目为“一代良史之材”的司马迁,他的史学名著《史记》亦并非本于伦理道德,时人已称之为“谤书”,班固则直接指斥其书“是非颇悖于圣人”。可见此时这种道德生命还没有建立起来。
真正把伦理道德观念融进人的生命本体是从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开始的。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并且他还在理论上使得孔孟开创的仁义道德纲常伦理进一步系统化和逻辑化。从此以后,中国古人的道德生命便逐渐建立起来,而且经过历代思想家和统治者的修补充实和宣传提倡,特别是经过唐代道学和宋明理学的修整补充,这种伦理道德与生命本体便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至潜入了人们的生命本能即集体无意识之中。然而,道德生命并不因为统治者的提倡而发展道路顺利通畅。由于抽象的伦理道德观念落实到了充满生命意识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这就连同这种伦理道德也变为具有实在内容的社会评价了。同时,由于社会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结构层次,这种道德追求和社会评价的标准也会各不相同,而追求的失败和标准的异化也会导致人生悲剧的产生,从而滋生痛苦的情愫,由此也在文学形式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道德生命同样会喷发出情绪的岩浆,从而凝铸成悲怨文学。
二
文学史上最早具有道德生命悲剧性质的是汉末三分时的诸葛亮。历史上,诸葛亮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智慧和忠贞的典型。他早在隐居隆中务农时,即已对天下事了如指掌,为刘备制订了联吴攻曹、统一全国的宏伟战略,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智慧以至生命。当汉末动乱、群雄并起的时候,诸葛亮不去投靠势力更为强大的曹操和更有根基的孙吴,而甘愿和势力虽小却代表汉家正统的皇权刘备同甘共甘。他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克尽臣节,忠心辅佐刘备,使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终于在西蜀立下根基。刘备死后他又忠心辅佐刘禅,可谓废寝忘食,殚心竭虑,直到呕心沥血病逝于五丈原伐魏的军中,他的一生在中国古代可以称得上是以道德伦理自勉的贤相良臣的楷模和典范。诸葛亮的传世作品不多,今存两篇《出师表》却是他道德生命和心血凝铸而成的: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前出师表》)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伐魏,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后出师表》)
仅此数语,即可看出诸葛亮基于君臣大义,知遇之恩,“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人格。这种人格感动了后世无数读者。伟大诗人杜甫即对此悲慨万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动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第五》)。杜甫不仅推崇诸葛亮,他本身也是一位以古道德自勉的忠臣贤士。他的最高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因为如此,他对皇帝也是拳拳孤忠,以大义和名节自许,表白自己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尽管在社会事务中他未能起到像诸葛亮那样叱咤风云的作用,但却将这种道德融合的生命凝聚成文学上的不朽成就。杜甫的时代,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大破坏,自身和家庭也随着社会的动荡而经受着悲欢离合。生命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伦理道德大义又刺激着诗人去感知国家和人民的苦难。前人说杜甫的五律都可以作奏疏看,的确如此。
忠君大节和道德情操与中国古代一批爱国主义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前面我们论及情感生命和道德生命时提到并分析的多数人身上,二者是融为一体的,只不过各自所占的比重不同罢了。我们知道,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注定他们的情感爆发也同道德情操以至忠君大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刘琨《答卢堪书》)
刘琨所处的时代,虽经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至经学大兴,但终究尚未像宋以后伦理道德无孔不入地渗入社会人生各个角落,其基本气氛和诸葛亮所处的时代相差不多,以忠君爱国情绪凝铸为生命意识的现象并不普遍,道德感和天性同时并存。至宋以后,情形就很不相同了: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阕。(岳飞《满江红·写怀》)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扬子江》)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份内事。(夏完淳《狱中上母书》)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类似的情形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这种忠君道德与爱国情感互相有机交合的状况实为古代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情操在这里实际上已融成了人们生命本体的一部分,它为中国人民族正气的形成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些正在从事救国救亡的志士仁人身上,这种道德生命力便会愈加强烈地发挥作用,并凝铸成了他们文学抒情的灵魂和风格。
三
道德生命在悲怨文学中的凝铸除了体现在作家的主观抒情方面外,还更多也更复杂地体现在宋以后兴起的叙事文体戏曲小说之中。这里,作家的创作主体和作品的形象主体之间存在着既相一致又相区别的错综交叉的局面,但并不妨碍我们从文学总体角度去讨论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提出和分析的是关汉卿的《窦娥冤》杂剧。这个被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作“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宋元戏曲考》)的戏曲名作,历来人们对其主要人物窦娥的形象说了千言万语,普遍认为在她身上体现了对黑暗社会勇敢反抗死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但在今天看来,这个人物悲剧性格的完成,除了自身的生命自主发展要求遭压抑所致外,也并不排除道德生命的作用。我们从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和拒绝张驴儿逼婚的曲辞中可以体会出来:
旧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湿,架儿上又换新衣。哪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哪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哪里有上山来便化顽石?可悲可耻!……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第二折[梁州第七]、[隔尾])
封建伦理倡导的“从一而终”的妇道竟成了女主人公抗暴的思想武器,显然不仅仅是借用。除此而外,促成窦娥悲剧的有着对婆婆的孝道:“本一点孝顺的胚胎”(《第四折[梅花酒]》),在这方面许多论者均已涉及。无疑,传统的伦理道德在作品的创作主体和形象主体中都有体现,说得明白一点,这也是作家和作品形象道德生命本体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类似这种状况我们在南戏传奇《荆钗记》、《白兔记》和《拜月亭》等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当然,和屈死刑场的窦娥不同,这些剧中女主人公的抗暴举动都是以胜利皆大欢喜收场的。
除了下层妇女形象外,文学的道德生命还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题材之中。
产生于明中叶的传奇《鸣凤记》,即为表现统治集团内部忠奸斗争的悲剧。为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首辅夏言、御使杨继盛先后揭露权奸严嵩对内招权纳贿、对外屈辱妥协的罪行,然终于失败,先后喋血刑场:
[四边静]太山颓陷梁木折,凭谁挽倾辙?忧国更思臣,衷肠大刀折。伤心事切,泪珠难彻,万里接天江,长流怨臣血。(第九出:二臣哭夏)
[北混江龙]丹书飞电,只为那忠言逆耳怒龙颜,三章定典,一剑横天。看怨气撒成千里雪,愁云卷起万家烟。(第十六出:夫妇死节)
这里爆发的悲愤抑怨情绪不可谓不强烈,然皆为纲常伦理节义道德所致。就中体现的道德生命最显者首推夏言、杨继盛两位忠君爱国的贤相良臣,还应加上杨继盛夫人这位“节义全”的贤妻,抽象的纲常伦理只有在古代中国的文人士大夫身上才能爆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这种道德生命恰与剧作家自身的生命本体有着相通之处,进一步说,正是如此道德生命感动了作者,因而凝铸成这种悲怨动人的文字。
与此类似的尚有清初李玉的《清忠谱》。该剧表现明末周顺昌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反对以魏忠贤为首的权宦误国集团的正义斗争,其中包括著名的苏州五义士死难经过,也是一部以忠义道德为主体的整治悲剧。
在这个剧作里,恪守纲常伦理的忠臣周顺昌和敢于“犯上作乱”的颜佩韦等苏州五义士竟在反对权宦误国集团的斗争中产生了共同的要求,可见这和以上所列举诸家作品一样,道德生命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戏曲而外,小说领域也有着同样的表现。《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小说描写这位“孝义黑三郎”身在梁山心在朝廷,终于使得敢于造反的梁山好汉重新成为皇家鹰犬,并且即使此后被奸臣害死亦不反悔。且听他自我表白:
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第八十五回)
显然,和在这方面多少表现出一点积极意义的诸葛亮形象不同,道德生命凝铸在宋江形象之中更多地体现为消极的和反面的意义。
这一点在钱彩、金丰小说《说岳全传》中的岳飞身上同样有所体现。诚然,爱国忠君的伦理道德促使着岳飞把抗金收复失地作为毕业的事业而至死不悔,这无疑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当他连续击败金兵,最后胜利即将在望的时候,伦理道德却使他无力抗拒奸臣秦桧发下来的十二道退兵金牌(只因后者是借皇帝的名义),从而功败垂成,葬送了事业,也葬送了自己。甚至他还阻挠部下惩治奸贼,致使岳云、张宪、余化龙、何元庆、施全这些曾在战场上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勇将屈死非命,由此保住了他一生的“忠名”。凡此种种,都只能显示出道德伦理在这位民族英雄生命中的消极意义。
道德生命凝铸在悲怨文学中的消极意义在戏曲中同样有所体现,除了我们已经列举并分析过的窦娥等形象而外,元杂剧中类似作品还很多。例如无名氏的《梗直张千替杀妻》,描写主人公张千为了报答结义兄长的知遇之恩,拿刀杀了向自己求爱的嫂嫂;杨梓《豫让吞炭》一剧,表现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出于贪欲侵暴他人被赵襄子等人攻灭之后,竟不惜漆身为癞,吞炭致哑,三次乔扮行刺赵襄子,最后自杀,以一死报之。
像这种不分是非曲直,一味讲究“恩义”而不惜戕害他人和自己生命的道德悲剧的元杂剧中还比较多见。如果说伦理道德体现在岳飞、窦娥等形象身上还在一定程度上让人理解和同情的话,那么,张千、豫让之辈的所作所为只能让人感到悲哀以至厌恶。这方面最使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无名氏的《小张屠焚儿救母》杂剧,主人公张屠夫妇为了祈祷母亲病愈以显示“孝道”,竟将亲生幼子送上神庙祭坛焚死以还神愿,无疑更是一幕道德生命凝铸的悲剧。
四
总起来说,道德生命的凝铸在我国古代悲怨文学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其表层多出于对纲常伦理秩序横遭破坏的强烈忧思,有时近乎愚忠。“臣子恨,何时灭?”在今天看来显然有它的消极性和保守性。但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却是他们社会性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抑或可以说即为中国古人特别是文人生命的精神支柱。从以上的列举和分析来看,传统的伦理道德因素由于中国古人固有的特点同样在生命深层激起波澜,就中形成的悲怨和情绪力量有它的确定性和复杂性。即以今天的目光衡量,有相当一部分道德悲剧力量仍没有完全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不容侵侮的正气。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因恪守传统伦理道德而铸成的悲怨,其思想和认识之价值取向今天看来已不可取,但应当承认,在当时它们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生命凝铸。这种凝铸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在当时的确感染了相当一部分人,促使他们创作出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掉存在价值的文学作品,当然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难以消失的遗憾。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生命样态,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审视文学史的发展演变及其价值定位,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