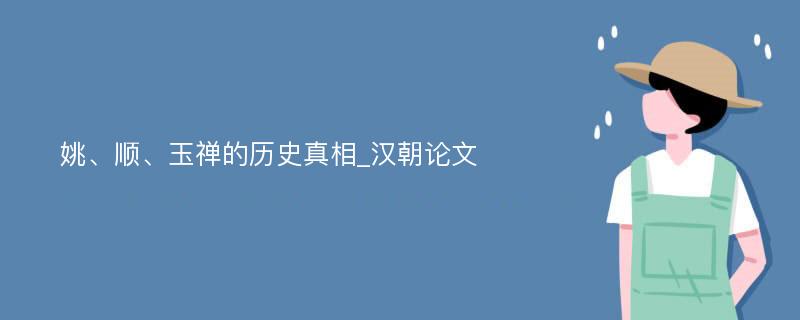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相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尧、舜、禹禅让,是古代史上一件特别受到重视的大事,与历代父子兄弟相传的惯例截然相反,因而产生各种不同的说法。议论最盛的时期有两次:其一为诸子争鸣的战国时期,其二则为近现代着重于追求历史真相的时期。追求历史真相是研究古代史的根本目的,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到正当的解决,而解决问题须有可靠的证据。禅让一事,既无当时的文字记录可供分析,也无法从考古发现中寻求踪迹,惟有依据古人的传说,结合古代历史的发展实际,以期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
在以氏族为基础成立的国家,规模不会很大,所以形成万邦林立的状态。《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反映着这种情况。这些小国之君被称为诸侯,其特别强大者,逐渐有了较高的地位,势力所及的范围较小者可以称伯,如“昆吾为夏伯矣,大彭、室韦为商伯矣”(注:《国语·郑语》。)。周文王也曾称西伯,见《尚书·西伯戡黎》。在较大的范围内者,则可以称王、称帝、称天子。其性质都是众小邦的共主,和后世中央集权强化的统治者相比,形同而实异。诸侯为一国之主,伯或王或帝也是一国之主,其主权以其本国的土地人民为限,对于所从属的诸侯,并不干预其内政,而为保持一定的特殊关系,即可以受到诸侯的朝觐,调解其间的争执,保证其安全。诸侯参加战争,也是自成一军,不作混合编制。春秋时列国对于霸主的关系,还略具这种形态。所以共主的地位,是从实际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地位虽高,实权并不大。所谓禅位,不过是把共主的名义让给别人,并不影响其原为本国之君。他们实有双重的身份,为一国之主是根本的,共主之位是兼任的,所以不必由一族一国长期占有,到后世为一家长期占有时,便成为朝代了。形成朝代以前,称王称帝的不止于一家,在绵长的历史时期中,特别有作为的帝王,他们的事迹,由于未有历史记录,逐渐消失了,其名号往往能流传下来。战国时人对于这个最远的历史时期,称之为“五帝”(注:参见拙作:《五帝释义》,《文史》第45辑。)。古代数字原有虚用之法,此言“五帝”,其义即为“诸帝”,因先已有“诸侯”之词,不便更以“诸帝”相称,于是称为“五帝”。荀子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注:《荀子·非相篇》。)正说明“五帝”的本义是表示最早的历史时期的。战国时人写的《五帝德》,实际上写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六人之事,可知“五帝”一词并非限定为五个帝王。后因金木水火土五德之说流行起来,于是有了五方神帝的说法,附会到历史上,五帝便被说成为前后相承的五个帝王,而且都是属于黄帝一个系统。“五帝”一词从此有分歧的释义,而坐实为五个帝王之说且有后来居上之势,其本义反被埋没起来了。
《韩非子》称:“虞夏二千余岁。”(注:《韩非子·显学篇》。)夏代只有几百年,相比之下,虞代应在千年以上,而后世的传说中,虞只有舜一代五十年,差距太大。结合其他传说来看,虞代原有很长的历史。《国语·郑语》史伯云:“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国语·鲁语上》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说明幕是有虞氏的始祖或其族中最早而有特殊地位的人。《左传·昭公八年》史赵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可见有虞氏不止于舜一世,其前原有很长的世系。自幕以下到瞽瞍,都是有一定地位的,其时代都在五帝时期,所以未有传政可言,甚至地位重要的幕,在后世也很少有人提到,瞽瞍则被说得顽固不化,都是后世传说发展变化的结果。尧的事迹,在传说中特别强调其举舜一事,至于尧的帝位从何而来,则不明确,《五帝德》谓受之于其父帝喾,《史记·五帝本纪》谓受之于其兄帝挚,都未足取信。按《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可见陶唐氏有一个很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就是尧在位的时候,不过好景不长,后来内部自乱,以致灭亡了。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尧是在陶唐氏兴盛的时候,从他族方面取得了共主之位,后来又转让给舜。有虞氏在舜以前为共主的机会可能较多,与《五帝德》同时写成的《帝系姓》,在瞽瞍以上,有穷蝉、敬康、句芒、蟜牛等四个名号,都是仅有名号而无事迹者。这样看来,五帝时期,共主之位在各族之间互相转让,原为行之自然者,尧、舜、禹之间的禅让,不过为其最后的两次。这两次何以能够流传下来?因为那时似已有了“瞽史”的官职(注:参见拙作:《瞽史》,《中国史学史纲要》附录(一)。),瞽史保存了这项重要史实的梗概,到战国时候,由于诸子结合其本派的思想理论,将禅让之事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是高不可及的,以致成为古史上一件难以捉摸的异常之事。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从各项传说中,分析出可以信从的实际情况,以恢复古代史实的真实面目。
世人关于禅让一事,解说纷纭而皆有所失,主要原因即在说者多就后世中央集权强化后的国家组织看待其事,同时又为其主观思想所制约。在百家争鸣的战国诸子,儒、墨、道、法都以助成其本派的理论为主而论述其事,其中影响最大者为儒家之说。儒家强调仁德,在其经典《尚书》中,有《尧典》专篇叙述其事。孟子更以“天与之,人与之”的说法,作细致的叙述。《论语》在最后有一段话:“尧曰:‘咨尔舜,无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魏晋时人作的伪《尚书·大禹谟》,特别宣扬“执中”的重要性;宋朝的理学家,便说这是三圣传授的心法,以致世人无敢对之稍作疑虑者,主观的意识完全代替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墨家以尧时生活简陋并能传贤为其节用、尚贤等主张作证,实际上因为尧时生活水平低下,从后世的生活水平来看,便以为是简朴了。道家以许由等不受尧之禅位为高,以满足其清高自赏的心理。法家持否定态度,或以年远事湮,不可详知,或直以为是相逼夺,实因其事与用法的主张难以协调。按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也称为相逼夺,是此说亦有一定的影响。
在战国时,更有以禅让为手段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者,见于记载有两次。马陵之战,魏为齐国所败,魏惠王为挽回失去的威信,对其相惠施说:“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施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愿先生以此听寡人也。”惠施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之心愈甚也。”(注:《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篇》。)魏国君臣,一得让国之名,一得辞国之名,二人作了一场不费本钱的政治交易。后来燕国的王哙和其相子之,也演了一场政治游戏,结果竟成了悲剧。子之怀有野心,盛言尧禅位之仁德,王哙真的传位给子之了,王哙的太子一派不服,引起了燕国大乱,齐乘机来侵,燕国几乎灭亡,由于燕国人民极力反抗,并有列国干涉,齐兵才被迫撤回。到后世,从王莽到赵匡胤,权臣武将要夺天子位者,多是采取了禅让的形式。曹丕迫使汉献帝禅位后,得意忘形的说了一句实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注:《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禅让一事变成这样,其本义殆已无法寻究了。
在先秦诸子的说法中,荀子的说法较为复杂,他在《正论》篇中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而在《成相》篇中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尧不德,舜不辞,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二说似相矛盾。原来荀子所反对的是“世俗之为说者”,即战国时流行的假尧舜禅让之名以达到某种特殊目的者,并非否定古代原有的史实,且言“尧不德,舜不辞”,以示其为行之自然者。孟子在回答其弟子万章提问时,曾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而提出了“天与之,人与之”的说法。这样强调“天”的作用,隐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他曾明确的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注:《孟子·公孙丑下》。)他很希望梁惠王、齐宣王之流能够作尧,由他来作舜。梁惠王已经和惠施表演了一次,他似乎幻想可以再来一次,结果落空了。荀子正是针对了这些脱离实际的说法加以驳斥的。
到近现代,各种学术空前发展,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各有自成系统的理论,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禅让问题者,多为套用这些理论加以说明。虽不再有战国时人的政治目的,因各种学术之异,更难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有怀疑是否果有其人与其事的意见。殆如治丝而愈棼,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杨希枚先生在二十年前写了一篇《再论尧舜禅让传说》(注:杨希枚:《再论尧舜禅让传说》,《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将战国诸子和近现代人的说法都罗列出来,其中近现代人的说法,计达十余种,除国人外,还有日本和法国学者提出的看法,今摘录其要点于下:
(甲)持怀疑态度者。康有为以为:“禅让传说是战国儒家者流为了托古改制而伪造的。”(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顾颉刚以为是“出于主张尚贤说的墨家之手”(注: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下编。)。日人白鸟库吉认为“尧、舜、禹均系神话人物”。高桑驹吉则认为“所谓禅让者乃是一种理想的事情”。苏雪林著《天问正简》,以为“中国古史上是否有尧、舜二人,事不可考”,她认为禅让传说“该和当时(战国中期)域外传入的(西亚或印度)文化大有关系”。
(乙)解史派者。郭沫若在所著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以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之《古代社会》为基础,谓当时为亚血族群婚的母系氏族社会,“尧、舜、禹的传说都是二头政长”。翦伯赞在《中国史论集》中所说者,基本上同于郭氏,而不取亚血族群婚的母系氏族社会之说,直称之为“母系氏族”。缪凤林在《中国通史要略》中说:“唐、虞间虽号禅让,而其关键,与禹之传子,同在得失诸侯也。”此不过推衍了古人说的,“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未有新义。徐炳昶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他说:“某族有特殊的酋长,讼狱讴歌可以暂时归到他那里,他就可以为一定时的宗主(原注:尊称之为帝)。……身没以后,他的宗主权也随着消失,更若千年而有他氏族的他帝出。”这也是一种主观的推测。黎东方著《先秦史》,根据人类学的理论,改编了五帝传说,以为五帝是担任大同盟的盟长,“尧禅位给舜,就是把中原大同盟的盟长地位让给他。”姜蕴刚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说“尧、舜禅让,为争豪之方式”,言争豪则非“举贤”之意了。法国葛兰奈氏(Marcel granet )著《中国文明》一书,对于禅让传说提出了变相二头酋长制的解释。
杨先生归结各家之说,加一总评:“近代学者对于禅让传说的解释均失其实,尤其是治学方法有欠正确。或失之于疏忽,未能详考史料,而以偏概全;或失之于套用其他学科理论,任意比附,而致主观的臆测多于本位史料的证明。”因此,他最后说:“中国古代史,尤其社会组织史的研究,亟待发展,尤其在研究方法上似有改弦易张的必要。”这个原则是对的,但如何“改弦易张”,未见提出具体意见。文中一再强调要重视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在研究有史时代的史事或考古学上的问题,这都是起码的要求。在只有传说的时代,别无其他资料可用,而杨先生对于传说提出这样的意见:“传说,纵然原是史实,或确含有若干史实成分,或竟纯属子虚乌有之说,但由于缺乏传说时代的直接或间接的其他史料可资参证,则其可信性或非可信性乃均属相对的,便无由论其是非了。”具体到禅让说本题,杨先生以为:“既是源远流长的古老传说,纵非全系史实,也至少该有若干史实背景。”虽侧重实有其事,而说法比较含糊,未能作出明确的结论。对于传说不能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坐待“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来参证,对于传说时代的历史将永远无从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甚至已有的近于情实之说也不见接受。如所列举的近代各家之说,徐氏之说原为分析了各项传说之后作出的推论,故能略得实情,而杨先生谓其“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缪氏谓“得失诸侯”为一重要条件,也是合乎实情的,杨先生则称其“未有新义”,都是明显的视而不见、失之交臂之例。
对于古代的传说,我们应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传说所保存的史实,因出现的时代不同而有或多或少之异。远古之事,最容易流传下来的是一些名号,至于各名号之间的关系及事迹,后起的传说便随时代不同而增减不定了。如商的祖先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注:《诗经·商颂·玄鸟》。)。周的祖先稷,“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歆……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注:《诗经·大雅·生民》。)。在较早的传说中,他们各有自己的来历,虽都具有神话的性质,但表明商、周氏族都自以为是天神之后,有殊于一般氏族。后来商、周二族都融入华夏集体之中,于是后起的传说谓,商契和周稷之母简狄与姜嫄同为帝喾之妃,这样二人就成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了。又如《五帝德》和《帝系姓》是战国时人编写的,当时“定于一”的思想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于是将古帝王都说成为黄帝的子孙,以成一系统。这个系统显然不合于古代的实际情况,在一般人不求甚解的情况下,倒广泛地传布开了。对于这样的传说,全盘接受明显是错误的,一概否定也是不可取的,要实事求是,作认真细致的分析,周密的考订,不存在主观成见,消除其所受的时代影响,便不难得到符合古代实际的资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