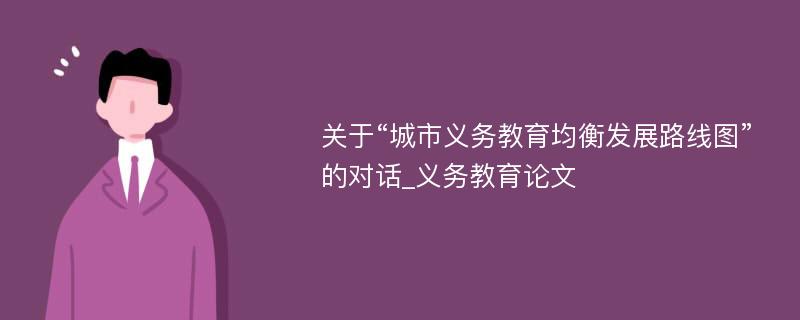
关于“A城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路线图”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线图论文,义务教育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场虚拟对话,但并非空穴来风。在生活快节奏的今天,如果空嚼舌头,恐怕不合时宜。希望这场对话能给人以有益启迪,有助于落实新《义务教育法》,也有助于义务教育以至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最终有利于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儿童、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我们把对话的双方称为甲和乙,以示区别;至于他们的身份,似乎无关紧要——都是教育工作者吧。其言论各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无须对号入座,更不一定让别人苟同。放松一点来阅读为好,既不是“红头文件”,更不是“金科玉律”,充其量是“敲敲边鼓”,引起思考,如此而已。
一、“重点校”会不会“名亡实存”?
甲:你真的相信中小学校可以“均衡”吗?
乙:当然相信。事在人为嘛!
甲:我看够呛!你随便到哪所“重点”中小学校走走,再到一所“薄弱学校”或者“普通学校”看看,无论是校舍、教学设施还是上课的情景——也就是从“硬件”到“软件”,都简直差“老鼻子”去了!假如你再从城市走到农村,你就更不会那么乐观了。当然农村也有条件好的学校,其“硬件”几近豪华水平,但那一定是“重点校”无疑!从1977年到今天,将近30个年头,“重点校”体制不断扩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哪儿那么好“扯平”呀?你太理想化了吧!
乙:正因为有差距,而且差距在拉大,所以尤其需要强调“均衡”。
甲:依我之见,中小学校“重点”发展没有什么不好,你把它都“弄平”了,家长想把孩子送个好学校都没有了,有什么好处?
乙:义务教育应该面向全体公民,一视同仁,不能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来分类施教。我们的目标是办好每一所学校,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上首先是合格、然后是优质的学校。“重点校”体制是使一部分孩子上条件好的学校,其他的孩子上“普通学校”或不得不上“薄弱学校”;而且由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向“重点校”倾斜,使保证“重点校”的“优势”以牺牲“普通校”和“薄弱校”的发展为前提。这样既影响了教育公平,也背离了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甲:可是,事物的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而均衡只能是相对的呀!
乙:恕我直言,你的话貌似有理,但只对了一半。我们承认“差别”,但不应躺在“差别”的现状上不动,更不应以此为理由继续扩大“差别”。我们的观点是,从“不均衡”出发,经过我们的努力,达到“均衡”;当“相对的均衡”被打破时,我们力求达到“新的均衡”。这个从“不均衡”到“均衡”,又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过程,就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发展过程。
甲:我们过去不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吗?“穷国办大教育”,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与其把钱撒了“芝麻盐”,还不如“集中优势兵力”办好一两所学校呢。
乙:当我们追求发展速度时,在一个短时间内,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可以理解的;但从中国社会的整体和长远持续发展来看,还是要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将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而不是继续加大,是我们当前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举个例子吧,有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村老奶奶说,过去家里穷,孩子多——老大、老二、老三、小四儿,最后一个叫“截住儿”。过节时她炒一锅豆儿“款待”这些宝贝儿子。这锅豆儿怎么分呢?一人一把,再一人一把,最后还剩点儿——就数个儿了。老太太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可是十个指头咬咬哪个都疼!”看来,老太太面对孩子分配“有限资源”时是持“均衡观”而非“重点观”的;她没有在把老大喂胖的同时,却亏待了老二、老三……她不忍心这么做。
甲:现在一些地区宣布了取消“重点校”、“重点班”,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不知你是否见到媒体报道,在某市某部门工作的李女士说:“我家附近的那所学校因为招不到学生都快被取消掉了,现在却要求我们就近入学,上这样的学校,孩子怎么能够受到好的教育?小学阶段就比别的孩子起点低,将来何谈竞争?”一位记者在该市采访时了解到,许多家长因为户口所在的地区没有好学校,早已迁了户口,有的甚至不惜花几十万元在“好学校”附近买了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A市的某些著名中学,仍然保留了以往按照成绩对新入学的初中生进行分班的惯例,实际上还存在着“实验班”、“重点班”。
乙:看来,已经形成的“重点校”的优势地位,使教育差距客观存在,要想取消重点与非重点的差别并非一日之功。一些地方由于利益驱动,仍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向“重点校”倾斜,进一步拉大校际差距。只要存在明显的教育差距,“择校”现象就不会消失。也有一些学校把“重点班”摇身一变,以“实验班”、“电教班”、“特长班”等形式出现。还有的总是舍不得这些“重点校”、“名校”的牌子,观念上扭不过来。一出手就是老思路。这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但也是必然要消亡的现象。
甲: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重点校”,到1966年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而后,在“文革”期间中断了10年。从1978年A市恢复“重点校”算起,到现在也快20年了。有这么长历史的“重点校”体制也不尽都是弊病吧?“终结”不是一件易事呀!
乙: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教育。国家对于全体公民负有提供比较公平的义务教育的责任。义务教育有两个原则,一个是“强迫性”,一个是“免费性”。新《义务教育法》用两个“必须”表达了这两个原则:“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现在,社会对于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义务教育不仅要普及,而且要优质。这种要求是合理的。但是,不应该只是一部分学校是“优质”的,而另一部分则是“薄弱校”。这种不均衡的教育,必然引发人们为了孩子上个“好学校”的“竞争”。于是就出现了“择校”风,派生出“高收费”和“乱收费”,滋生“寻租”和腐败。这种现象引起群众对于义务教育的不满,进而是对国家举办义务教育提供的机会不均等的不满。由于为数众多的学生要进“好学校”,“好学校”也为了收一些“好学生”,这种供大于求的“供”“求”关系导致在“小学升初中”(简称“小升初”)时,“好学校”就会对于选择进它的大门的学生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比如,要连续3年“三好”,要“奥数”考试优胜,要“英语等级考试”达到若干等级,要文体特长多少级的“证书”,等等。有的中学还给小学毕业年级的学生在“双休日”办什么“综合班”,让学生提前进入“中学”上课。一方面收费不菲——加重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剥夺了学生“双休日”休息的权利,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为了“好”生源,有的地区还展开了“生源大战”。而达不到这些“苛刻条件”的孩子的家长,有钱的拿出高额的“赞助费”,有权的写“条子”(或者找有权的写“条子”),与学校之间实现一种“钱权交易”。凡此种种,把义务教育搞得乌烟瘴气!有人说,我们在不断扩大“优质校”的覆盖率,今年50%,明年60%,后年70%。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供求矛盾。就是“优质校”覆盖率达到90%,让谁家的孩子去上那10%的“薄弱校”?对你来说是10%,对家长来说,他只有一个孩子——就是100%!
在这种“秩序”下,自然形成了一条“利益链”。君不见,“奥校”、“奥数”、“成人英语等级考试”等等都是暴利——十分了得的呢!有多少人发了学生“增负”、到处办班的“小升初”的大财,苦了孩子、苦了家长,违背教育规律、违背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规律,为了一己之私利,中饱私囊,干得乐此不疲!
这样看来,“重点校”体制的终结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甲:你如此乐观?
乙:你得知道,这是“法”,已经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新法第二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这是新法中非常重要的“革命性”变化。
甲:或许是因为此法刚刚出台,很多人对“重点校”能不能真的被“终结”持怀疑态度。一部《义务教育法》,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乙:我们是“依法治国”。我们谈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国家大法。《义务教育法》是2006年6月30日公布,于当年9月1日起施行。2006年10月19日,又公布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优先发展”,就要加大投入,同时还要推动公共教育协调发展,要缩小投入差距,在城乡、区域以及校际之间缩小差距,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就基础教育而言,就是使每一所学校都是“合格校”进而是“优质校”,使每一个孩子而不是一部分孩子享受“良好的教育机会”。
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第四部分“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中提到:“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请注意,是均等化!其中强调:“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义务教育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属于“基本实现均等化”的重要领域。
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有“路线图”吗?
甲:那么,义务教育怎么才能均衡发展呢?你能做个描述吗?比如,画一个蓝图什么的。
乙: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落实上,要从实际出发,从多个方面一步一步做好工作。
甲:我还是认为,有几十年历史的“重点校”,“终结”不易呀!
乙:是的。但我们首先要把目标定下来。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这是新《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的。为实现这个目标,新《义务教育法》规定了“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当然,学校均衡发展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曾有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希望我“出出主意”。我认真想了想,学校均衡的目标要分解成三个“子目标”,即“硬件的均衡”、“软件的均衡”和“生源的均衡”。
甲:很感兴趣,愿闻其详。
乙:先说“硬件的均衡”。“硬件”指的是校舍条件和教学设施。现在许多省市都制定了本地区“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我们的目标是共同达标。过去的“重点校”要达标,过去的“薄弱校”也要达标。在义务教育阶段,这主要是一个经费投入问题。第一,要加大投入;第二,要向“薄弱校”倾斜。过去,“重点校”享受经费投入的优先权,现在要拧一个个儿,使“薄弱校”达标,追上“重点校”的水平。过去,一些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往往是“锦上添花”,现在我们重在“雪中送炭”。许多国家的公立学校,比如日本,硬件条件都是一样的,因为是国家按照同样的学校标准建设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每一个儿童、少年应该享受均等的义务教育资源。
硬件问题应该说不是最难的。现在我们许多省市还没有真正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还远达不到GDP的4%。如果达到了,硬件的均衡就有了经济基础。另外还有一个投入方向的问题。这是一个地区及其地方官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素质问题和执政能力问题。
甲:有人说,在一定程度上,孩子的命运取决于他遇上什么样的教师。因此,家长未必追求优越的校舍条件,而首先是学校的名气——因为“名校”多“名师”,“名师”标志着“升学率”。
乙:这就涉及学校的“软件”——校长和教师了;也有人持“生源决定论”,与其说“孩子的命运取决于他遇上什么样的教师”,还不如说“升学率取决于生源”呢!在“重点校”的教师就是“名师”,在“普通校”的教师就不是“名师”,这种说法恐怕并不合乎实际。义务教育的公平不仅是学生享受教育资源的均衡,也是教师享受教育资源的均衡。
甲:那么,教师资源怎么均衡呢?
乙:这就是教师的“轮岗”与流动。在新《义务教育法》第四章第三十二条中明确提出:“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师资力量,组织校长、教师的培训和流动,加强对薄弱学校的建设。”新《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后,有些地方已经有了动作。辽宁省沈阳市在2006年9月新学年开学之际,就有1977位教师到新学校报到执教。可以说是揭开了教师流动的序幕。2006年11月,在河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上,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在“十一五”期间,要“软”“硬”兼施,促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生源质量等的均衡发展。在“软件”上,新增教师要优先满足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需求,同时加快县域内教师合理流动。校长在一所学校任期不得超过8年,50岁以下男教师和45岁以下女教师在一所学校任教不超过6年至8年。
甲:教师从“差学校”流动到“好学校”容易,反过来就不好办了吧?况且学校之间不仅工作条件差异大、生源质量不一,而且“结构工资”差别也很大——我听说有的差好几倍呢。这恐怕不是一纸调令就行得通吧?
乙:所以,在教师流动之前先要有一些运作。首先要从理念上明确,公立学校的教师不是某学校所有,而至少是一个“区域所有”(比如某一区县所有),因此,在一个区域里流动应该视为正常安排。一个教师不能一辈子只呆在一所学校,定期的“轮岗”是一种常规。校长则应该实行“任期制”,在一所学校一个任期三年或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其次,要创造教师流动的“平台”,就要实行教师工资和收入的均等。这个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结构工资”是A市的一个创造,后来推向全国众多省市。它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推出的。那时因教师待遇普遍比较低,国家给的工资(“国拨工资”)难以保障教师队伍的稳定,于是中小学校就以“校办企业”、“出租校舍”、“收费办班”等形式“创收”,后来又有了学生“择校”的“赞助费”、“择校费”等收入,统称为“自筹资金”,用来增加学校收入。此后,学校就有了教师“国拨工资”以外的“结构工资”。当时曾有个说法:“自筹、自筹,校长白了头。”可见“自筹”也不是一件容易事。“结构工资”在一定时期内,对改善教师待遇起了一定作用,但其弊端也很明显。一是分散了校长办学的精力。“校长姓‘钱’还是姓‘教’”成了一个问题。二是渐渐异化,失去控制,不合理地拉大了不同学校之间教师收入的差距,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产生了相当大的副作用。
甲: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填平补齐”,把高收入拉下来、低收入涨上去?
乙:这里有两种策略。一种是低收入涨上去,中等收入基本稳定住,然后“限高”——不允许有的学校发放那么高的“结构工资”和各种名堂的“福利待遇”。有人问:“发得这么多,钱哪来的?”有人回答“都是非正当‘渠道’弄来的”。这种做法,就多少带点“填平补齐”的意思。当然,作为“公立学校”,政府有调节其收入的权力和职责。
甲:我看,收入提高容易,要是把已经成为现实的“高工资”压下来,恐非易事。
乙:是的,人们的普遍心理是收入只能“涨”不能“落”。但是,“结构工资”是怎么来的?它天然合理吗?在公立学校中,教师工资和收入在同级之间差异这么大,合理吗?严格说来,公立学校的“创收”,都应是国有而非一所学校可以视为己有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在同等情况下收入存在较大差异是不合理的。就是在公务员工资的调整规范时,也有一些部门和一些人员的收入下降的情况,而不是都涨了钱。
甲:那么,你所说的第二种策略是什么呢?
乙:第二种策略是,在A市公务员工资调整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新《义务教育法》,教师工资也应该调整,以实现“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在教师工资调整时,实行教师待遇的“重新洗牌”。这样做,看来比较麻烦,但是一劳永逸,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规范教师工资,既符合法律规定,又提高了教师待遇,特别是农村教师和“薄弱校”教师的待遇。目前,是到了“结构工资”完成历史使命、“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试想,当学校和学校之间教师的收入相差好几倍时,如果说它是学生“择校”的深层次原因,你是否觉得有一定道理?有人说:“中小学教师收入的均衡就是义务教育的均衡”,这种说法是不是很精辟?
甲:这件事做起来难度不小,这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政能力可是一个考验!
乙:创造了这样一个教师待遇均衡的平台,教师在一个区域内的流动或说“转岗”就容易了。校长实行任期制,在一所学校任期不得超过两届。这样两项措施保证了学校“软件”(教师和校长)的均衡。
甲:学校“硬件”和“软件”均衡之后,如果“生源”不均衡,可能也不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其实,过去“重点校”享受了许多优惠,无论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占据了优势地位,而“重点校”得到的最大优惠,有人说是“生源”的优惠——“重点校体制”保证了它们捞到了“最好的”学生;甚至有人说,所谓“升学率”其实是生源决定的——持“生源决定论”。
乙:当中小学校在“硬件”、“软件”,特别是师资、学校管理等诸方面都均衡以后,家长和学生的“择校风”自然会煞住;当所有学校软、硬件条件都大体相当时,“舍近求远”、“劳民伤财”去“择校”就没有必要了嘛!我们带孩子去麦当劳,就不必非挑什么地方的麦当劳——因为所有的麦当劳店家都是标准化建设,服务也是统一规范的。当中小学校实现了软、硬件均衡之时,就是我们实现“免试就近入学”之日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学校都是合格校进而是优质校,百分之百的孩子都进合格校进而是优质校。天下大同,其乐融融,教育均衡,和谐公平!
甲:如果你的这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线图”不是“乌托邦”的话,那真是学生和家长的福音,也是校长和教师大展身手的新平台,也是教育公平和谐的幸事啦!
乙:但愿如此!我想,对此我们还是应该有信心的。教育公平是全党全民构建和谐社会大合唱主旋律中的一个声部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