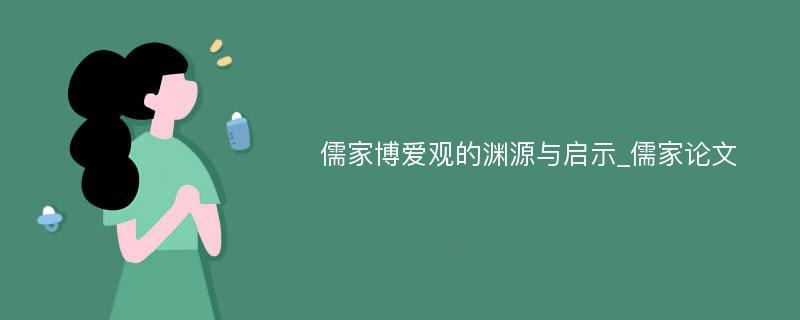
儒家博爱观念的起源及其蕴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博爱论文,起源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5-0035-09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概括康有为哲学的特色时,将其以“仁”字为唯一宗旨的哲学概括为“博爱派哲学”①。的确,康有为以为,“仁者,在天为生生之理,在人为博爱之德”②,故阐发了他自己“博爱之谓仁”和“仁莫大于博爱”③的博爱论说。康有为论仁和博爱,虽然有西学平等博爱的背景,但他以生之理、爱之德言仁,走的明显是宋明理学的理路;而“博爱之谓仁”的哲学,更是承接传统儒学的博爱论而来。尽管今天的人们更为熟悉的,是源自西方的博爱观念,事实却是博爱的观念本来孕育生长于中国文化的土壤④。“博爱”的观念和境界,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浸润在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中,并使中国社会在根本上保持了和谐的凝聚力,“和”为一个中华的群体且绵延不衰。 一、博爱观念的萌发 儒家文化的博爱情怀,渊源于商周时期形成的仁的观念。仁是博爱的母体,但在文本的层面,此时之仁尚未与爱关联起来⑤。作为一种厚重的情感,爱的生发有“类”或血缘的生理基础:“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⑥落实于人身,爱引出的是人内在的高级心理需要⑦。需要本身基于生理的驱力,属于“类”的行为,进入到价值领域,是与仁德的直接联系。到春秋时期,仁与爱开始互为训解,并从根本上呼应了普遍的人道关爱与和谐群体的中国社会发展需要。 春秋后期,晋公子孙周(后为悼公)在周侍奉周王卿士单襄公,其时他“言仁必及人”,而单襄公评价他亦是“爱人能仁”,并预言孙周以其近乎完美的品行必然成为晋的新君⑧。这一在孔子出生前二十多年的史实,披露了仁爱的规范在其孕育的雏形中,就是以一般性的爱人即博爱为特质而昭显于世的。后来,韦昭注《国语》的解释便是:“博爱于人为仁”,“言爱人乃为仁也”⑨。以博爱释仁,以爱人为仁,将博爱与仁德相关联,说明爱在满足心理需要的同时,也在根本上滋润着人的德性培育。《国语》及《注》的这些说法,表明孔子创建自己具有普遍意义的仁爱思想体系,是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 与博爱观念的产生相呼应,“博爱”语词可能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汉刘向《说苑》记载说: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⑩师旷答晋平公之问,使用了“务在博爱”的表述。倘若刘向的记载属实,则“博爱”一词在春秋后期便已产生。当然,在历史上,《说苑》的史料价值并不那么确定。从这一整段话的语气和词汇表达来说,有可能受到了汉初语言环境的影响,譬如“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这一类话,放在儒、道、墨各家交融的汉初,不会感到很唐突。然而,刘向作为西汉中后期最有盛名的学者,他之捡拾陈说、“录遗闻佚事”,的确保存了不少散佚的史料,况且,此条记载作为《说苑》全书之开篇,说明刘向对此十分重视,不应当是虚构无据之言。“虽间有传闻异词,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11),《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同时,清净无为虽是汉初政治的特点,但其思想本身在孔、老已经提倡,孔子便以“无为而治”去概括舜的政绩,舜所以能“恭己正南面而已”(12),乃是因他孝顺和博爱的德行影响和感染了天下的臣民。因此,舜之治天下如果可用“无为”来评价的话,师旷所答的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屡省考绩、以临臣下等对策,又都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参考本文随后的分析,如果立足于普遍地爱人和对仁的价值的集中揭示来说,认同博爱的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是可以成立的。同时,博爱观念的萌发,虽然源自对特定人士品行的评价和对善的治道的真诚期待,但它的出现和被提倡本身,却无疑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意义。在此基础上,儒家博爱论在其孕育和成形的过程中,生成了适应中国社会特点的丰富蕴含并在社会国家管理及人与人关系的调节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从而需要进一步来予以探讨。 二、爱的先人后己 博爱观念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实施即爱人的实践。在实践中首先会碰到的问题,就是同作为爱的对象,己身与他人之间应当如何去选择,即其中谁处于优先的地位。这在情感、动机和道德选择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并由此披露了后来儒家博爱观的基本走向。 《国语》记载,晋公子重耳谋臣赵衰劝重耳娶怀赢,并引《礼志》之言曰: 将有请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人,罪也。(13)《周语》所引《礼志》乃已逸古礼书,礼学文献由于孔子对礼的重视——“不学礼,无以立”(14),后来都收归于儒学并成为其基本典籍,加之前述的“爱人”又的确是与仁德相关联,所以儒家博爱论的起源与整个中国传统博爱论的起源在义涵上是等值的。《礼志》所言之“有请于人,必先有入”,可以说是中华最初形态的推己及人观。在这里,人与己虽然同样需要爱,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先后之分——“爱人”先于“爱己”。《礼志》所考虑的人己先后,是作为一般性的原则和礼的要求而呈现的,应当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赵衰也才能以此来劝导重耳。固然,爱己在这里可以说是目的,爱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手段一经使用,也会产生脱离具体目的的一般性意义,并成为社会评价人的德行的一个基本标准。 那么,博爱观念出现于中国社会,首要的标志就是爱人先于爱己的先人后己说。在如此的博爱观念浸润和影响之下,中华文化系统中更为普遍的“先人后己”意识也随之孕育和诞生。《礼记·坊记》便引孔子之言曰:“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从上层社会到普通民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都是认同“先人后己”的美德并给予了普遍性的赞扬。即先人后己之爱在君子的示范作用下,开始具有了“心之所同然”的意义,“爱己”的目的性考量实际上已经淡化。 相较于中华的情况,西方基督教的博爱论同样也在人己关系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但在那里,不是讲先后,而是说同一,即强调“爱人如己”(15)。“爱人如己”在中国社会,首见于墨子的学说,所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16)。后来的儒家则吸取了墨子的这一思想。《毛诗》有论“大王居豳”之义,郑玄注《礼记·哀公问》时发挥其爱民说,以为“是言百姓之身犹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犹吾妻、子也”。由此,“爱人如己”可以在中西得到共同的呼应。当然不应忽视其中的差异。儒家在传统上更为推崇“先人后己”之爱,注重“人”对于“己”的优先性;基督教则更为看重人与己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体现了中国文化更重“人”、西方文化更重“己(我)”的区别。 回到文献的层面,在战国诸子出现和孟子游说诸侯的时代,应当还保存有不少春秋时期传下的典籍,从而影响到《郭店楚墓竹简》作者和孟子等思想家博爱观念的形成。譬如,前述《礼志》的思想便在郭店竹简中得到继续,其曰: □反诸己而可以知人。是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17)“爱人”先于“爱己”是《礼志》博爱观念非常有特色的表述,但郭店简所述显然又有扩展,它将自我反省而知人作为了爱人敬人的前提,即“知己”而能“知人”,“知人”则能“爱人”,博爱的情感已处于理性认知的指导之下,是意识自觉的产物。而就“敬人”来说,不论是《国语》还是《论语》,甚至包括《墨子》,都只有具体的敬君上、敬父母、敬鬼神以及敬事等,到郭店简则从“爱人”推进到一般性的“敬人”,并在随后的《孟子》中得到呼应,博爱带上了更多的德性的色彩。 在理论上,爱己必先爱人的成立,依赖于将心比心的推度和自我心态的调适(18),属于内在性的范畴;但“先人后己”之爱落实于实践,却是需要由外在的客观尺度来确认的,故也带有外在性的意义。博爱的主体或施予者,在这里亦不限于上层社会的贤达或君子,而是已下移到普通的百姓,其所期待的,是我爱人、人爱我的善的社会效果的呼应。 三、爱的互惠性 爱己必先爱人和我爱人、人爱我的社会良性互动,实际引出的是儒家博爱的第二层蕴含,即爱的互惠性,它在博爱的实践中,表现为利他性、目的性与自觉性的统合。 郑声公五年(前496),郑相子产过世,“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19)。所以如此,司马迁的说法,是因子产“仁爱人”和“侍君忠厚”的缘故。按他的记载,孔子先前路过郑国时,曾与子产相交“如兄弟云”;闻知子产去世,孔子哭之曰:“古之遗爱也!”(20)孔子与子产相交的“如兄弟”,可以用后来郑玄注《礼记·中庸》“仁者人也”的“以人意相存问”来解释。至于“遗爱”,裴骃《史记集解》引贾奎语曰:“爱,惠也”;杜预《左传正义》则解释为:“子产见爱,有古人遗风也”(21)。显然,在孔子与子产二人心中,仁爱或博爱的观念实际上已扎下根来。“爱人”在这里,已经转化为目的本身。子产被郑人所爱戴,乃是他之治国能够施惠于郑国民众,博爱表现为惠民的实践。 “惠”之一词,孔子曾数次使用,在《论语》中多指在物质利益上施惠于民之意。“惠则足以使人”(22)是仁人五种德行的归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3)可谓其最高境界。孔子多次称赞子产,在于子产正是“养民也惠”的“惠人”。所以,《说文》释“爱”为惠,释“惠”为仁。同时,爱惠在孔子,并不只是单方面的惠人养民,而应当是互惠的(24)。弟子宰予因为幼时享有父母的慈爱,成年后就当孝敬和感恩于父母,为逝去的父母服丧三年作为回报。但他不愿如此,故被孔子斥之为“不仁”。 “仁”与“人”之际,弟子“樊迟问仁”,孔子答之曰“爱人”;又自述“泛爱众而亲仁”(25),等等。在孔子,凡涉及“人”的概念,事实上都是泛指,即所有的人,否则,便是如“成人”“小人”“善人”“乡人”一样的有具体的限定。那么,“爱人”自应当是泛爱众人,亦即博爱:“博爱,泛爱众也。”(26)《论语》中另外还有两处“爱人”——“节用而爱人”和“(君子)学道则爱人”(27),也都是在这一意义上立言的。子夏所“闻之”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28),将孔子与子产相交“如兄弟”的君子间的个别实践扩展到全天下之人。这样的推广所以可能,只能是在博爱的普遍情怀已经建立的情景之下。(29) 进入到词汇的分解,孔子“泛爱众而亲仁”这句话实际涉及爱、亲、仁三个语词,但孔子并未解释这三个语词的具体含义。战国初中期,郭店竹简中的儒家文献第一次对它们有了具体的解说,并联系人性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在郭店简,对爱与亲的细致分辨是一大特点。所谓“爱生于性,亲生于爱”(30),排出了性—爱—亲的前后序列:爱由性生,性内含而爱外现,亲近的情感则生成于爱的实践。至于仁,则首先与人的本性相关:“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唯性爱为近仁。”(31)仁揭示了性之方所(32),即性朝向爱(这一方向处所)的自然展开,所谓性生爱也。在此意义上,性生成的爱自然最靠近仁,仁所要发明的,正是由本性生发的爱。 从而,仁、爱、亲这些概念实际是互为训释的。但结合对象,可以对它们进行区分,譬如“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等等(33)。在这里,亲近笃实的情感标示出爱的品性,而由爱父而推广到普遍的爱人就是仁。爱作为亲与仁的中介,体现出兼备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重角色,特殊性以爱父为标识,普遍性则通过爱人来体现,这既包容了仁者爱人的思想意识,也将爱之普遍性视作了仁的根本特色,故可泛言之曰:“爱,仁也。”(34)。 不过,爱父与爱人作为仁,其实是有善的道德预设在其中的,即所谓“爱善之谓仁”(35)也。性善的基调在这里已经发生作用,换句话说,仁者爱人,乃是性善的结果。事实上,正是郭店简提出了中国最早的性善观念,所谓“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36)。当然,其思想较稍后的孟子性善说简单。孟子认为民情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此基础上,“然后驱而之善”以“治礼义”(37)。由于这一工夫实际上也就是教化的过程,故与郭店简“恒”在“教”之先的思想可以相吻合,民因恒有善德,故而有爱。 在孟子,关于亲、爱、仁的关系,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说法,即:“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8)孟子将仁爱的实施按对象的亲疏远近进行了划分:一是爱物。相对于“泛爱众”而言,爱之对象已更为扩大,爱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天地万物无所不爱,这扩展了孔子仁爱的范围。二是仁民。与“物”相对的“民”,实际就是“人”或孔子所说的“众”,对他们应当普遍地关爱,施以恩惠,但却不必亲近。三是亲亲。亲亲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实践,相对于亲之“近”来说,仁与爱在对象的层面可以说都是“远”,突出了人与人之间普遍性的爱或互惠。 孟子又说: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39)从《礼志》到郭店简,“爱人”与“爱己”可以解释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带有一定利益考量的色彩,故爱人是应当;到孟子则转型为前提与结果的关系,爱的互惠性品格,已成为确定的心理预期,从此出发,爱人就是必然。他的这段话,对儒家仁爱—博爱的基本面及其实现机制做了较为恰当的揭示,实际上将仁、爱人、敬人、自反和互惠整合了起来:仁表现为爱人的落实;礼则表现为敬人的实践;仁礼施与人,人必以仁礼回报之,如果不然,只能是自己的爱敬不够诚恳笃实。从郭店简的“反诸己”到孟子的“自反”,为爱人的行为是否普遍真切地实施,提供了内在的自省和自纠机制。 四、爱的两大内涵与儒墨之合 孟子无疑反对墨家互惠性的兼爱主张,但是,孟子反躬自省的德性权衡与墨家的主张又不是不可以调和(40)。作为仁爱的发生学基点,它们可以在孔子答仲弓问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处找到源头,即自己不想要他人不爱我,就不能不爱他人;或者,自己想要他人爱我,就要把自己的爱施与他人。当然,从孔子“泛爱众而亲仁”到孟子的“仁者爱人”,其间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孔子较为单纯地倡导人与人之间的泛爱或博爱,孟子则除了弘扬博爱之外,更多注意到亲与民之间的爱的差别。所以如此,在于孟子的时代,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更大的紧迫性,所谓“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42)。 孟子此说,实际已将仁爱的两大内涵和盘托出。一是普遍之爱的一般原则在具体落实时,需要考量时政的急需,因而需要以亲亲尊贤为先,这与《礼记·中庸》中孔子所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先)”(43)的宗旨是相呼应的。二是“仁者无不爱”——或者说仁者博爱,毕竟是大前提,所以《礼记·哀公问》中孔子答哀公问政,所提出的便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先)”的治国原则。事实上,孟子对时政和君王的批评正是从此原则出发。他指责梁惠王说:“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44)“所爱”与“所不爱”按其文意是指子弟与民众,“仁者”由爱亲到爱民,亦即前面郭店简所说的“爱父,其攸爱人,仁也”;“不仁者”却相反,由不爱民走向不爱亲。这说明,爱人与爱亲、“爱人为大”与“亲亲为大”看似冲突,但又不是不可以调和。博爱与差等双方,本来是同一个仁爱在普遍原则和具体实践的不同层面的表现。实际上,“亲亲为大”往往只通行于有限的人际关系,且要受相应法律条文的制约。对于统治者来说,社会国家的安稳是第一位的,而这便与和谐民众、疏通民心的“爱人为大”关联了起来。相应地,儒家博爱论的重点,亦由博爱初起时关注的人己先后,转向亲亲与爱人的适当折中和一定条件下的侧重。 同时,还需要考虑的,是亲亲、爱父还是爱人,并不是当然如此,而是教化的结果。大致成于战国晚期的《孝经》,明确宣扬了博爱教化的理念。其称:“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45)儒家先王立教化民,首先践行博爱,民众就不会遗弃自己的双亲。这说明在儒家先王眼中,父子之间虽有血缘维系,但子女并不必然产生对父母的爱敬,换句话说,爱有差等亦不是当然如此。爱敬孝顺之心是在先王博爱德行的感召下彰显出来的。那么,由教化而生起仁爱之心,与孟子立足仁义内在和善心弘扬的模式讲爱人便存在着矛盾,但这可以在荀子“化性起伪”的框架下予以化解。《孝经》的这一理路,在郭店简中已有迹可寻,《唐虞之道》便称“孝之方,爱天下之民”(46),以爱天下之民来阐扬孝道,说明孝是可以在普遍之爱的层面上被理解的。 《孝经》提出和阐发的“博爱”观,无疑是孔子“泛爱众”观念的恰当引申和发展,但同时也与对墨家兼爱、尚同等思想的吸取有关。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墨家的思想说:“(墨家)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以孝视(示)天下,是以上同。”墨家的这两大“所长”主张,不但被儒家的后来人所继承,更被汉以后的国家所采纳。那么,孟子声称兼爱则无父(不孝)的论断,在作为东汉儒家正统代表的班固这里,事实上已经被否定。 融合儒墨的典型文本是《礼记·礼运》(47)。在文中,其所提出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倡导普遍之爱的“大同”之道,与随后所提及的“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未有不谨于礼”的维护等差的“小康”礼制社会,在形式上表现为退化和替补的关系,博爱与差等之爱也相应成为划分大同与小康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参照。然而,这一划分在《礼运》本身便是受限定的:“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天下为公在礼制社会同样是遵循的准则;而“养生送死”的“人之大端”既是礼制社会、也是博爱“大道”的基本内涵。所以,匡正“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48)的社会弊病而推行礼义,与博爱的大道之行在质上是同一的。后来历代儒家思想代表的博爱情怀,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49)。 更重要的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在历代的先进分子那里是一直都在发出的呼声。《礼运》所描述的“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50)的礼制社会,实际上预告了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社会现实。张岱年先生说:“‘以天下为一家’,即兼爱全人类;‘以中国为一人’,可谓即通国一体之说。此通国一体之思想,可谓较墨家兼爱说为进一步。由兼爱说而发展,可得到一群一体,或通国一体之观念。”(51)“通国一体”固然离不开有强制力的国家政权,但同样也离不开由于兼爱或博爱思想浸润而积淀起来的华夏心理认同。就思想资源来说,到西汉董仲舒时,孔子的“泛爱众”、“博施济众”与墨子的“尚同”、“兼爱”已经被整合起来。孔子之道就是圣人之道,就是先王之道,“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52)。“尚(上)同”在董仲舒就是“大一统”。如果能行“博爱”而“尚同”,则一统可至,太平可达。 五、结语:“博爱之谓仁”的命题与实践 汉末三国时,韦昭注《国语》以“博爱于人为仁”释“仁”,将“仁”之要义落实到博爱的践行上,恰当地揭示了仁爱的普遍之爱内涵。在此之后,儒家仁爱的理论概括,大都不离这一特点和轴心。东晋袁宏撰《后汉纪》,他对两汉之际名士李业不愿在公孙述治下为官而甘愿饮毒酒自尽的事迹,做出了中肯的评论,并概括出了“博爱之谓仁”的典型命题,认为“博爱之谓仁,辨惑之谓智,犯难之谓勇,因实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53)。 袁宏概括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54)。在这里,“辨惑之谓智”“犯难之谓勇”直接继承了孔子;但“博爱之谓仁”与“仁者不忧”在形式上则有距离,二者如何关联需要斟酌。汉孔安国和苞咸于“仁者不忧”分别有“无忧患也”和“不惑乱也”之解(55),参考孔子由“季氏之忧”引出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56)的言说,可以联系到物质上的贫乏与救济的观念。博爱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慰藉,它包括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蕴含。从孔子的“泛爱众”可以推出给人民以恩惠,达致在邦、在家无怨。事实上,当子张向孔子问仁时,孔子明确以“惠则足以使人”(57)为“天下为仁”的内涵之一,因为它直接体现着“爱人”的物质层面的关怀,而“博施济众”便是典型的表现。博施济众不是高于仁,而是仁在“王”的层面的实现,亦可说是孟子所称颂的饱食、暖衣、逸居的王道仁政。 可能正是基于如此的考虑,梁皇侃疏解“仁者不忧”为:“仁人常救济为务,不尝侵物,故不忧物之见侵患也。”他处又说:“仁者,周穷济急之谓也。”(58)在皇侃,忧患、惑乱都与“物”相关,因为有救济作为常务,以爱物为己任,所以就不担心人物有灾患。那么,当物质的救济和关爱成为“仁人”的基本考量之时,仁德的博爱内涵就得到了突出的彰显。所以,皇侃以“广爱一切”释“泛爱众”,以“人有博爱之德谓之仁”释仁(59),从正统儒家经学的立场推进了袁宏的典型概括。 到唐代,唐玄宗注《孝经·天子章》“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为:“博爱也。”唐玄宗将爱亲与博爱统一起来,以倡导人人相爱的“泛爱众”思想,接续了经学的博爱理路,是抓住了传统博爱观的脉络和孔子思想的实质的。在这一时期,随着佛道众生平等和慈悲等观念的渗入,博爱为三教所共同倡导和推行。欣赏佛教的柳宗元,在为其叔父柳氏所作的墓版文中,称赞他是“用柔和博爱之道以视遇孤弱,仁著于内焉,此公修己之大经也”(60)。柔和博爱之道就是内在的仁德和大经,能否躬行博爱,其时已成为社会评价人的修身水准的基本标识。反抗佛教而坚守儒家道统的韩愈,在博爱观上与佛教的融通儒墨却保持了一致性。韩愈进一步确认了“博爱之谓仁”的命题,以为大爱体现的正是儒家的仁德,这在后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并直接以“泛爱亲仁”和“博施济众”释“兼爱”,肯定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而不应当强化二者的差别。这不是说差别不需要考虑,但那是次一位的——“行而宜之之谓义”,义可以在行仁而适宜上去体现,它不应妨碍普遍之爱这一最高的准则(61)。 而从国家政治和统治者的层面说,推行博爱也是一个基本的考量。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并颁行、后被誉为中国古代法典楷模和中华法系代表作的《唐律疏义》,便有“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爱”的条款,按其《疏义》的解释,此条“言国家制刑,惩一而诫百,使之畏于未犯之先。不幸而丽于法,则宽平其徽纆,而心则主于博爱之仁也”。(62)在唐代的立法者这里,制定刑法固然是为了惩戒犯罪,但最后的目的并不在惩戒本身,而是在未犯之先的预防和已犯之后的宽宥,其中贯穿的是博爱仁德的精神指导。 可以说,从汉到唐,倡导普遍性的仁和博爱,已成为包括统治者和思想家在内君臣上下的共识,并形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情怀。这当然不是说汉唐时期没有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冲突的情势,而是表明要成功维护大一统的中华国家,不可能只从差等的观念来强化等级和职分。董仲舒之“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63)的观点,便是对此做出的深刻阐发。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内在的凝聚力,博爱观念的灌输和相应政策的施行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民心的疏通的。博爱从情感的层面抚慰人心,和谐国家,也最终与诸多因素一起,合力造就了至今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汉唐盛世。当然,从先秦到汉唐的博爱论在理论水准上还主要限于经验的层面,将博爱论与宇宙观结合起来,从形而上的角度阐释和论证博爱的精神和价值,是后来宋明理学才承担起的任务。 收稿日期:2014-06-20 注释: ①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②康有为:《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 ③康有为:《颜渊》《宪问》,《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7、213页。 ④其实,人们所以能用中文“博爱”概括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和翻译西语普遍的“兄弟”之爱(universal fraternity/fraternité)——“民胞物与”便是其例,正说明博爱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中华仁爱精神的沃土,张载之“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所谓‘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者也”(《正蒙·中正》,《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页)的对儒家仁爱的界定便是一例。 ⑤譬如,《尚书》诸篇已有仁的观念,但主要在人性和德政的意义上使用,尚未与“爱人”的情感相关联。 ⑥《礼记·三年问第三十八》,陈澔:《礼记集说》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314页。 ⑦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爱是人的基本需要且属于高级需要。见《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参见该书第2章和第5章的论述。 ⑧《国语》卷三《周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6页。 ⑨《国语》卷三《周语下》,第95、97页。陈荣捷先生认为:“‘博爱’一词首见于《国语·周语下注》,《注》云:‘博爱于人为仁。’《孝经》亦用之。”(《仁的概念之展开与欧美之诠释》,《王阳明与禅》,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0页)陈先生虽未明言《国语注》的作者和时间,但所引“博爱于人为仁”正是今存最早的《国语注》——韦昭《注》之语。即便韦昭《注》可能保留了汉以前先贤的旧说,但却陷于无法验证的境地。据此,“《孝经》亦用之”意味《孝经》成书在“首见”博爱的韦昭之后,与学术界主流观点不同,故本文不取。《孝经》的成书,本文采较为通行的战国后期之说。 ⑩刘向:《君道》,《说苑》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696册,第4页。 (11)纪昀等:《子部一·儒家类一·说苑二十卷》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1页。 (12)《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杨伯峻:《论语译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页。 (13)《国语》卷十《晋语四》,第358页。 (14)《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178页。 (15)《马太福音·最大的诫命》(22.34—40)记载:当法利赛人问耶稣“在摩西法律当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时,耶稣回答说:“‘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条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摩西全部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的。”(参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6年印行《圣经(双语并排版)》)在“爱上帝”这一条上中西没有可比性;其“一样重要”的第二条就是集中体现基督教博爱精神的“爱人如己”说。就此而论,与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爱之“先人后己”说有相似也有不同。 (16)《墨子·兼爱中第十五》,孙诒让:《墨子间诂》本,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3页。 (17)荆门市博物馆:《成之闻之》,《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其中首字因不能辨认暂缺。 (18)“将心比心”,亦即《礼记·大学》所说的“絜矩之道”,参见《朱子语类》中的相关讨论,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2—363页。 (19)《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 (20)《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 (21)《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并参《左传·昭公二十年》。 (22)《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183页。 (23)《论语·雍也篇第六》,第65页。 (24)互惠(Reciprocity)是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W.Gouldner)认为:“互惠规范,就其普遍的形式来说,有两种相互关联的最低要求:(1)人们应该帮助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而且(2)人们不应该伤害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一般来说,互惠的规范可以被视作一种可以在所有价值体系中找到的尺度,而且,特别是作为普遍地出现在道德标准中的多种‘首要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之一。”见《互惠规范:一个初步的陈述》,冯钢编选:《社会学基础文献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5页。 (25)《论语·学而篇第一》,第4—5页。 (26)孔安国:《古文孝经孔氏传》云:“博爱,泛爱众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第182册,第11页。 (27)《论语·学而篇第一》,第4页;《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181页。 (28)《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第125页。 (29)本段及以上二段文字,笔者先前已有过简约的表述。参见:《仁爱与博爱》,《哲学动态》2013年第9期。 (30)荆门市博物馆:《语丛二》,《郭店楚墓竹简》,第203页。 (31)荆门市博物馆:《性自命出》,《郭店楚墓竹简》,第180页。 (32)在郭店简如《性自命出》中,有不少“……之方”的表达句式,这里解作“方所”,系参考《周易正义·系辞下》“井以辩义”句,孔颖达疏韩康伯“施而无私,义之方也”为:“井能施而无私,则是义之方所,故辨明于义也。” (33)荆门市博物馆:《五行》,《郭店楚墓竹简》,第150页。其中的“攸”字,按整理者意见当读为“迪(进)”或“继”。 (34)荆门市博物馆:《语丛三》,《郭店楚墓竹简》,第211页。 (35)荆门市博物馆:《语丛一》,《郭店楚墓竹简》,第198页。 (36)荆门市博物馆:《性自命出》,《郭店楚墓竹简》,第181页。 (37)《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杨伯峻:《孟子译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页。 (38)《孟子·尽心章句上》,第322页。 (39)《孟子·离娄章句下》,第197页。 (40)譬如墨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第十五》,第104页)便与孟子之言颇相似。况且,利的概念,孔子并非不谈,孔子言仁惠亦讲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篇第二十》,第210页)。 (41)《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第123页。 (42)《孟子·尽心章句上》,第322页。 (43)孔颖达疏解《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之意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者,仁谓仁爱,相亲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己亲,然后比亲及疏,故云‘亲亲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者,五服之节,降杀不同,是亲亲之衰杀。……礼者所以辨明此上诸事,故云‘礼所生也’。”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1629页。孔氏要说明的,是仁爱在实施中表现出来由近及远的先后次序,或者丧服、丧期在礼制上由亲及疏的依次递减问题。简言之,“亲亲为大”即亲亲为先;“亲亲之杀”即由亲及疏,服丧渐轻。 (44)《孟子·尽心章句下》,第324页。 (45)《孝经·三才章第七》,胡平生:《孝经译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页。 (46)荆门市博物馆:《唐虞之道》,《郭店楚墓竹简》,第157页。 (47)《礼记·礼运》是儒墨融合的作品。肯定儒家吸收了墨家思想,在前辈学者已有充分的论述。如伍非百:《礼运》“大同”之说“实则墨子之说,而子游弟子援之以入儒耳”;“‘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则兼爱也”(见蔡尚思主编:《十家论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蒙文通:“究之《礼运》一书,取之墨而义又有进于墨者”,“夫儒墨同为鲁人之学,诵《诗》《书》,道仁义,则《六经》固儒墨之所共也”(见《先秦诸子与理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2、94页);张岱年:“所谓大同,实即以兼爱为原则之社会”,“大同实乃儒家吸取墨家思想后创立之社会理想”(见《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280页)。 (48)《礼记·乐记第十九》,第206页。 (49)整合博爱、仁义和礼乐来治理国家,在儒家官吏那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唐朱敬则在总结秦以来的国家政治所著的《五等论》中便认为:“盖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爱,本之以仁义,张四维,尊五美,悬礼乐于庭宇,置轨范于中衢。然后……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见《旧唐书》卷94《朱敬则传》。 (50)《礼记·礼运第九》,第126页。 (5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280页。 (52)参见《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53)参见《后汉纪》卷三《光武皇帝纪》。 (54)《论语·子罕篇第九》,第95页。 (55)参见何晏《论语集解》,孙钦善校点,《儒藏精华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册,第143页。 (56)《论语·季氏第十六》,第172页。 (57)《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183页。 (58)皇侃:《论语义疏》之《子罕》、《卫灵公》,陈苏镇等校点:《儒藏精华辨》第104册,第372、496页。 (59)参见皇侃《论语义疏》之《学而》、《为政》的相关注疏,《儒藏精华辨》第104册,第221、243页。 (60)柳宗元:《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柳河东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133页。 (61)参见韩愈:《原道》、《读墨子》,《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影印)版,第172、184页。 (62)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义》卷一《名例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2册,第21—22页。 (63)董仲舒:《为人者天》《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