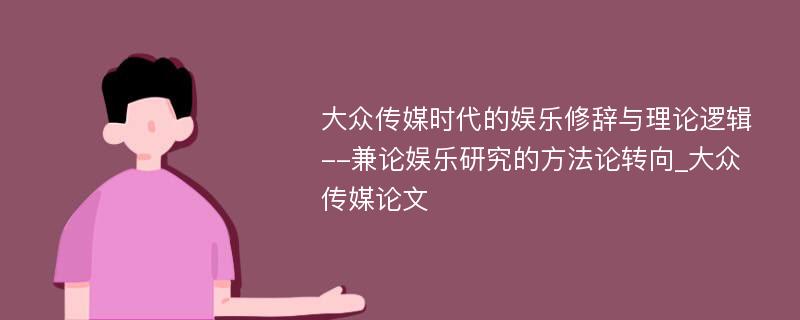
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修辞及理论逻辑——兼论娱乐研究的方法论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修辞论文,逻辑论文,大众传媒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初露端倪,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的表征形式。“娱乐的代码渗透到新闻、信息、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①。现代传媒技术使得数字娱乐超越传统娱乐方式。大众传媒不仅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还制造娱乐需求,引导娱乐需求,娱乐似乎成为当今生活的刚性需求,并实现了娱乐与传媒的高度一体化,使当下的世界真正进入了娱乐时代。娱乐如此受到热捧,“并不仅仅是一种内容或者形式,其实它在本质上是人与世界沟通畅达时所产生的快感,是人性自由所追求的一种境界”②。尽管娱乐常常被理解为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以放松、消遣为目的,以游戏方式进行的休闲活动,但其实娱乐绝非只具有单纯的消遣属性,它的内在层面与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当下的大众传媒时代,权力、资本的实现都离不开娱乐。在娱乐表现出“超”意识形态时,涉及意识形态内涵的诸如政治、伦理、道德等“严肃”内容其实则更为隐蔽地内嵌其中。 本文将分析娱乐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的重要修辞手段,其概念、构成要素及理论思路是怎样的?它又以怎样的作用机制作用于大众传媒?并反思当下大众传媒娱乐化研究的缺失与出路。 一、娱乐的内在肌理:心理学基础与神话学范畴 这样一个问题始终困扰我们:为什么娱乐会在当代社会广为流行,会被奉为大众传媒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状况?回到最简单的日常经验,不难发现,其实娱乐具有深厚的民间根基,广为民众所欢迎。 一般来说,娱乐符合人“趋乐避苦”的人性,这一心理学观察深入揭示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和原动力。娱乐带给人以“快乐”,满足人的感性刺激和生理欲望。娱乐能够有效地避开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原则”而进入“快乐原则”。娱乐与游戏旨趣相同,游戏被描述为“过剩的生命能量的转换”、某种“模拟本能”的释放、放松的需要等③,而娱乐能够将人从常轨故辙的生存模式中解放出来,使其置身于游戏、刺激、消遣之中,解除日常的不适和压力。可见,娱乐具有一种自然而然地将我们引到“应当如此”生活的功能。就像鲍德里亚分析的与娱乐密切相关的享受在消费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质那样,享受不再是消费社会的“权利或乐趣的约束机制”,而是变成一种“义务约束机制”,“消费者把自己看作处于娱乐之前的人,看作一种享受和满足的事业。他认为自己处于幸福、爱情、赞颂/被赞颂、诱惑/被诱惑、参与、欣快及活力之前。其原则便是通过联络、关系的增加,通过对符号、物品的着重使用,通过对一切潜在的享受进行系统开发来实现存在之最大化……这便是‘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我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满意的一切可能性”④。这种充满“娱乐道德”的“事业”实际上暗含某种更为值得探究的意蕴,这是一种深入规训后的享受,而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娱乐的意识形态性。 为什么娱乐不可避免地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普遍性。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以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为对象,考察该城市的娱乐化现象,发现娱乐之潮不可阻挡,因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⑤。阿尔都塞也提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是无所不在的⑥。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客观的遍及人心的无意识,既为娱乐产品提供结构性框架,也为娱乐本身制造深度和潜能。关于娱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约翰·费斯克有过精彩的论述:“作为一个概念,娱乐是意识形态化的,因为它被用来证明这样一种话语实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⑦娱乐从来不只是“娱乐而已”。在考察一系列娱乐产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后,马尔库塞反问道:“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传媒区别开来吗?”⑧答案是否定的。大众传媒本身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其播散模式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形态,比如技术化媒介中时空拼贴方式,将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和意义联系的讯息配置在一起,制造媒介权力的幻觉。我们还可以从娱乐生产流程来看作为娱乐产品的制作者——过滤者和“把关人”,他们直接决定娱乐的内容与形式。显然,“把关人”既受商业逻辑又受政治观念的影响,表现为对广告商的迎合,对审查制度的适应。这样一来,大众传媒制造和呈现了种种娱乐符号的内爆,界限被抹平、消弭,传统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主客之分倒塌,严肃的媒介产品转而追求娱乐效果,用娱乐的方式构建它们的叙事,政治、商业和娱乐高度融为一体。 更进一步说,娱乐与操纵、灌输的权力关系密切,它也是一种合理化的策略手段,甚至还具有“法西斯性质”⑨。大众传媒的特殊符号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强迫性。娱乐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表征,其修辞机制完全可能充当大众文化“法西斯性质”的卫道士。以美国影视为例。劳拉斯·蒙福德在《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中讨论了电视剧文化意识形态问题,认为美国肥皂剧所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愉悦,还推波助澜地宣传与维护父权制意识形态。美国好莱坞电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加显而易见。在《世界大战》、《阿甘正传》、《独立日》、《拯救大兵瑞恩》等大量影片中,随处可见美国意识形态的宣扬。显性层面上,白宫、自由女神、美国国旗等美国符号反复出现;隐性层面上,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美国梦、美国制度、美国中心论等意识形态不断向全球播散。 那么,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化是如何实践意识形态功能的呢?这可以通过神话学范畴来具体观察。何谓神话?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谈”,一种传播体系、一个讯息等,神话的定义“来自神话吐露这一讯息的方式”⑩。从这些概念界定可以看到,神话旨在突破索绪尔构建的“能指/所指”静态区隔的言说模式,动态地揭示其更为深层的意义、动机、作用机制。尽管意识形态内涵复杂多样,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对相对稳定的价值信息的追求。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对“价值信息”的播散或诉求,而神话是意识形态价值信息的最有效的承载方式和传递话语方式。 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由神话进入娱乐,娱乐的神话意义不再是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上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而指向第二层能指与所指关系,即遍及某种文化的一系列广为接受的概念。正如他在《玩具》中所分析的,玩具第一层表意是给孩子们提供一种游戏方式,不过,巴特所看到的玩玩具已经不再是小孩子嬉戏这么简单,而是一种价值观念如何通过轻松娱乐的方式被赋予主体,即第二层意指里成人世界的规则通过提供娱乐的方式自然而然地生成一种“幻觉”。这便是神话运作的秘密所在。因此,神话通过游戏化而实现自然化,隐蔽地将意识形态完美地编织进符号系统,以达到其合法化的目的。因此,娱乐意义的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娱乐的神话化过程,也即神话植入娱乐符号的意指实践的过程。这可以称之为一种娱乐的修辞化。娱乐修辞便是借助这种特定的言说方式将隐秘的意义融入娱乐的生产与消费。 二、娱乐修辞的运作机制:符号形式与文化编码 对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定位,约翰·费斯克一语中的:“娱乐属于20世纪比较成功的修辞策略之一。它似乎将普遍接受的、源于印刷报刊与生动的电子媒介,包括视觉与听觉、叙事与表演等类型的主流产品轻而易举地归结为一种饮食起居制度。”(11)我们身边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已经在资本运作、商业营销中被高度修辞化,娱乐本身也属于大众传媒的修辞。实际上,娱乐作为一种修辞,已经成为21世纪大众传媒的主色调。 修辞是指一种为了适应特定语境和意义表达的需要,求得某种言说的效果,运用语言表达的方法、技巧或规律的着意构建的话语方式。回顾修辞学发展史,修辞主要以语言为媒介,即语言修辞。随着修辞研究领域的扩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不断融合,修辞呈现出一种涵盖所有人类符号交际或传播模式的趋势。比如图像越来越成为影响人类符号交流或传播类型的重要因素,“视觉修辞”得到广泛研究(12),而视觉修辞“是一种以语言、图像以及音像综合符号为媒介,以取得最佳的视觉效果为目的的人类传播行为”(13)。所谓的娱乐修辞,是一种基于语言、图像、音频等大众传媒符号,实现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方法。娱乐修辞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是就修辞所依托的对象和所追求的效果而言的。娱乐修辞是一种综合性修辞概念,以契合某种意识形态为目的,这是娱乐修辞最基本的命义。 进一步思考,娱乐修辞由哪些元素构成自身的自足系统?它如何让观众在毫无察觉、快乐的氛围中“领略”意识形态意涵? 在修辞理论中,传达信息分为表层修辞与深层修辞。表层修辞是指辞面(辞表)和辞里(辞内)完全一致,所运用的辞语能直接表达概念、判断、推理,读者可以直接理解其含义,不存在歧义性。深层修辞是指辞面(辞表)和辞里(辞内)不一致,即借用传统表层信息的话语编码形式传递可能暗含的信息,具有某种歧义性(14)。都兰德在《广告图像中的修辞手段》中依据结构主义符号学原理将修辞手段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修辞性操作,指将某陈述的一些成分进行转化的过程,由“偏离”行为的生产、识别和评估组成(一般认为修辞便是对“常规”的偏离)。操作可分为两个类型:“附加”,即为该陈述添加一个或多个成分;“压制”,即删除该陈述部分成分。同时,又可衍生两级次生性操作:“替代”,即用另一些成分替代被“压制”的陈述;“互换”,即将某陈述的两个成分相互交换位置。二是成分的修辞性关系。这种修辞性关系划分为“同一”、“类似”、“差异”和“对立”四种(15)。这样的修辞分析极大地拓展了传统修辞的空间,使得修辞研究具有了与娱乐宣泄、意识形态播散相结合的可信基础。 关于娱乐的基本精神,学界的很多研究值得借鉴。比如皮特·沃德尔等将娱乐的内核界定为“快乐”,尼尔·波兹曼提出了娱乐需要遵循几个原则(16),它们可用低门槛、线性、轻松等词汇加以概括,也就是说,不需要很深的知识储备,不需要复杂的镜头闪回,避免涉及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等。法国休闲学专家罗歇·苏则认为:“娱乐活动摆脱了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达到一个确切结果的约束。娱乐时,人们只服从于自己毫无拘束地选择的规则,以达到自己预定的结果,没有任何强制或外界的义务来干扰个人的选择。”(17)这一主张强调了娱乐的个体的自由选择精神。巴赫金的狂欢节研究也可以纳入娱乐意义一并思考。通过节日气氛、广场意味的揭示和制造,巴赫金试图引领全民进入狂欢之中。他所描述的狂欢节具有四大特征:一是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各种形态的不平等如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都被消除,人们在狂欢的广场上发生了随便而亲昵的接触。二是插科打诨,在狂欢节中,人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制约中解放出来。三是俯就,狂欢仪式使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贱、伟大与渺小、明智与愚蠢等界线模糊。四是粗鄙,比如狂欢式的亵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世俗中和人体生殖相关的不洁秽语,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模仿等(18)。由此可知,巴赫金从文化学角度提出的狂欢概念,注重的是全民性、仪式性、消除等级性等特征,这些也正暗合了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特质。 通过对学界有关修辞和娱乐特质论述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推断,娱乐修辞既是修辞手段,也是修辞策略。修辞有优劣之分,使用不当,言说或传播内容易于呈现直接、粗暴、赤裸裸等的宣教形式。尽管娱乐修辞与修辞原理相同,但是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表现形态更为复杂,呈现目的更加隐蔽,有其独特的运作机制。 一般而言,娱乐修辞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娱乐符号”层,可说是表层修辞,注重诸如故事性、视觉性、欲望性、狂欢性等,更倾向于直接的身心快乐因素的选择,比如搞笑、噱头等。二是“神话符号”层,可说是深层修辞,是指现代文化如何编织到娱乐之中。娱乐符号是一个庞杂的系统,不是所有的符号都能够通往“神话符号”层,比如在传播旨趣与传播噪音的影响下,有一部分娱乐符号被压制或替代,无法在娱乐符号层表现出来。应该说,这些神话符号的存在以及它们可能的能量,构成了娱乐修辞最核心、最隐秘的内容,因为它们本身表达了最深入的意识形态内涵,也是需要运用更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主体视野才能认知的符号。 其实,娱乐修辞真正的核心策略在于,娱乐符号所制造、所招募的文化编码与背后的意识形态的连接状况。表面看,为了避免因枯燥教化而被拒绝解码,为了契合观众的认知心理,对大众传媒所推崇的娱乐修辞往往以与意识形态无关的身份出场,以故事化、感官化、视觉化等为基本形式,从而让产品至少在外在形式上看已经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使社会权力、等级、价值变得像自然秩序那样天经地义,或者像启蒙理性那样处处散发自由、平等、博爱的光辉。这正是我们需要格外关注的经过转换、伪装的意识形态化的“神话符号”。 意识形态内容庞杂,特征各异。不同的文化传统、利益诉求导致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意识形态赋值方式花样翻新,意识形态参与社会生活更具策略性。娱乐修辞作用下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收编异质意识形态的人才、创意以及平台,剥夺或扰乱其他意识形态的符号生产活动,实现自身符号的最优传播和效益最大化。二是召唤,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主体的召唤。在《信息批判》中,拉什分析了主体的时间体验是“非线性”、“拉长”、“加速”,空间体验是“压缩”、“被拔起”(19),大众传媒给技术化的生命带来一系列改变。比如当代身体崇拜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身体涉及生产性目标、经济效益,它将主体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控制紧紧渗透于生产目的之中(20)。三是对话,即在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格局中,开放性和包容性显得尤为重要,大众已经不完全是被动的、被规训的对象,相反他们常常采取规避与游戏策略,与意识形态周旋。大众传媒为对话的展开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尤其基于Web 2.0的自媒体兴起,从理论上每个人都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马克·波斯特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是从双向而去中心化的,为新型互动性提供了可能,其主体建构是通过互动性这一机制发生的。显然,娱乐修辞下的对话机制是多元的,通过视觉化、感性化等途径进入大众传媒,实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互动、交融和耦合。 大众传媒全方位地干预社会生活,深度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意识形态实践的重要渠道。修辞化的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方式成为“创造世界、整合社会的力量”,同时获得统治者、被统治者的普遍认可。这样的语境,使得意识形态的精神、价值在娱乐形式中隐秘而有效地传达给大众,并以一定的(神话)符号形式与大众的生命记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勾连起来,内化为主体的记忆。 三、方法论转向:大众传媒时代娱乐研究的进路 尽管在西方历史传统中,娱乐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谴责和限制的,比如基督教极端主义就认为欢愉是有罪的,但是也有16世纪的哲学家蒙田指出过娱乐的积极效果,它能够消除紧张、厌烦等心理情绪。而本世纪的弗洛伊德更认为,快乐体验一直被压制,娱乐把人们从压制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归快乐的生活方式(21)。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推崇,也使得娱乐具有了更多的话语空间(22)。 当代对于娱乐的理解,众说纷纭,除思想差异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对大众媒体认知上的差异。随着权力化、资本化的大众传媒对娱乐的改造,娱乐的大众传媒化的负面效果日益显现,围绕大众媒介泛娱乐化的批判广泛展开。整体来看,有关大众传媒娱乐化的批判研究大多指出娱乐自身道德意识消亡、美学品格滑坡的严酷现实,也就是说,娱乐从根本上削弱了大众的社会批判精神、独立思考能力、高雅的审美品位等等。 在我看来,尽管这些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它们或许过于集中于娱乐的社会评价方面,从而陷入单纯的伦理学泥淖,使得方法论层面的娱乐研究难以被学界所关注。从思维范式看,这些研究基本属于启蒙范畴。启蒙运动是现代性最重要的思想运动,是一场发生在17到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运动,背景是反对封建和宗教思想的束缚,提倡思想自由、个性发展等,它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性成为整个自然、社会、历史以及人自身的通约物,成为世间万事万物的“中介”,成为一种思想交换的“货币”。也可以说,启蒙运动是一场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世俗化过程。启蒙精神值得倡导,是整个现代社会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涵养。但是,从理性主义的切入点对现代社会进行一刀切的研究方法不能不让我们反思:长期被推崇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蜕变成新的极权力量,我们又该如何认知这一严酷的历史现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详细讨论了理性如何转向其反面,生产出新的理性化的社会统治形式。他们具体分析了社会理性如何变成了非理性,启蒙如何转变成了欺骗,自由和进步模式作为现代性之特征,如何转变成了统治与倒退(23)。理性在摧毁神话、打碎偶像、颠覆权力之后,又成为新的神话、偶像与权力。 既然在大众传媒时代理性已经捉襟见肘,那么是否有其他形式引向“启蒙”?当然,尽管我们说启蒙运动出现某种历史偏差,但是确立“人的价值”这一启蒙精神的内核不应改变。只不过,“启蒙”作为一种价值坐标和精神高地,其诉求可有多种道路选择。 当代文化,尤其大众传媒时代的娱乐文化,日益注重感官体验以及感觉经验对知识、信息与认知的形塑。因此,从感觉引向反思启蒙之径是否可能实现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价值?所谓的感觉,既包括视、听、触等身体感觉,也包含对外界事物或对象的直觉式察觉,还包括快乐、痛苦、欲望和恐惧等心理情绪。那么,以感觉为主导的娱乐是否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通向人的存在和价值? 首先,娱乐的生命力本于天然,适于个性自由,也适于个体生存,甚至娱乐精神还能构建出一种社会生活的自由审美状态。席勒认为,游戏所包含的审美维度对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人性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24)。大众传媒时代所形成的娱乐化或泛娱乐化现象,使得快感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大规模地进入、改造和构建人们的感官与生存体验,这些无不说明娱乐作为当下生产与解放体验和审美维度的独一无二的影响力。 其次,感觉是认知的重要途径。在传统认识论框架下,认识不可能来自感觉经验,感觉阻碍真理性认识的形成(25)。人的感觉说到底被视为与颜色、形状、质量等物理属性相关而不具有认知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能力。其实,感觉的自主价值与逻辑法则并未淡出学界的视野。马克思把视觉、听觉、触觉、直观、感情、愿望、爱等个体官能的感悟看作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并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属人的感觉都将彻底解放(26)。把感觉看作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在于把感觉作为携带知识、理念的中介,感觉是认识实体的过渡性桥梁,虽然感觉不能够直接洞察理念世界的实体,不过它却能够追求理念世界,其背后存在着完满的世界和实体的知识(27)。此外,感觉不仅是中介,它本身还蕴含很多理智的认识。正如法国孔狄亚克在《人类知识起源论》中指出:“当我们在感觉着某些感觉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我们的知觉更为清楚、更为明白的了。”(28)甚至“我们所提取出来的知识是从感官中所含有的那些清楚、明白的观念里得来的”(29)。毋庸置疑,作为认识中介的感觉,在认知领域的贡献是无法被忽略的。 再次,从媒体技术的发展趋势看,现代科技主导下的大众传媒已经与现代主体无缝衔接。麦克卢汉提出“冷媒介”与“热媒介”概念,其标准在于:一是媒介提供信息的多寡以及清晰度的高低,二是媒介的使用者参与程度的高低。当代流行的电脑、移动终端、携带终端、Google眼镜等都属于“热媒介”,它们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更擅长延伸人的感觉,“并使之具有高晰度”(30)。“热媒介”系统某种程度上排斥理性,高度抽象的数字化神奇地把抽象的概念逻辑转化为生动的感性图像,变成吸引感官的娱乐话语,大众传播进入感性传播,也正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只有借助于发达的工业,“人的情欲的本体论的本质才能充分完满地、合乎人的本性地得到实现”(31)。未来的媒体终端对感觉的注重,使感觉叙事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引入社会生活。 大众传媒开启了娱乐狂欢的新时代。从这一意义出发,娱乐研究应该走出合法性的争论,走向方法论的探索。如今的大众传媒时代,娱乐表征作为当代社会的一种集中修辞,为更具人性化的价值立场的播散提供了启发和路径,这正是我这里强调的方法论转向,其中至少应该包括:其一娱乐作为方法是如何更有效地传播人的生存状况的;其二娱乐话语是如何传递人的价值关注和立场的有效性的;其三深入发掘和反思娱乐逻辑与人性逻辑、社会逻辑的纷争与融合,也由此实现娱乐研究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方法论的真正转化。 ①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②张小争:《娱乐财富密码——引爆传媒心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③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多人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④(20)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3页,第129页。 ⑤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⑥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201页。 ⑦(11)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96页,第96页。 ⑧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⑨罗兰·巴特认为,大众文化的语言也具有“法西斯性质”。语言无所谓革命或反革命,因为它原本就是法西斯的。套用此表述,娱乐无所谓革命或反革命,因为它不可避免就是意识形态的,是法西斯式的。 ⑩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12)罗兰·巴特的《图像的修辞》、都兰德的《修辞与广告图像》是较早的视觉修辞研究成果。 (13)陈汝东:《论视觉修辞研究》,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4)骆小所:《修辞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328页。 (15)转引自冯丙奇《视觉修辞理论的开创》,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16)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不需要动脑筋,目的就是情感上的满足;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参见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73—77页)。 (17)罗歇·苏:《休闲》,姜依群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18)《巴赫金全集》第6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9)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杨德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21)布莱思特·汤普森:《传媒效果概论》,陆剑南等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22)以威廉斯、托尼·本尼特、约翰·菲斯克等人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持较为开放的态度,这为主要寄生于大众文化形式的娱乐创造了更好的生存平台。 (23)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84页。 (24)Richard Shusterman,Pragmatist Aesthetics:Living Beauty,Rethingking Art,2nd Ed.,New York:Rowr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pp.211-212. (25)《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2004年版,第664页。 (26)(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3页,第103页。 (27)代海强:《感觉在柏拉图知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8)(29)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牛张力译,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第15页。 (30)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