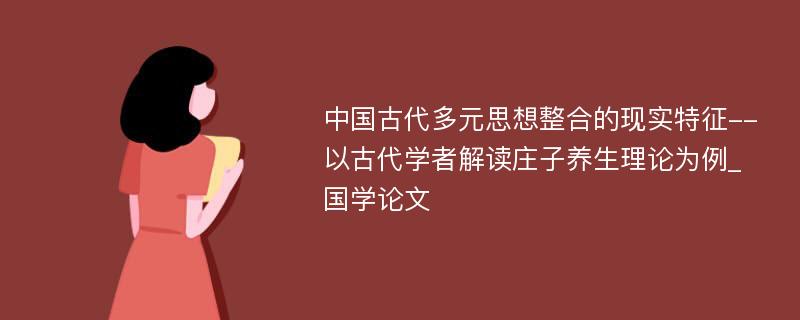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多元思想整合的现实风貌——以古代士人对庄子养生论的诠释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为例论文,庄子论文,风貌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3.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710(2008)06-0107-06
《庄子》一书,因其义理的高度思辨、思想的博大深奥、表述的模糊空灵等特点,给后人的解读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故而自汉至今,陆续产生了许多有关《庄子》的不同注本。现在留存下来的,据严灵峰《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续编收录的情况,约有100多种。就这些注本而言,后人对《庄子》意旨的理解极其繁复庞杂:“道家援之以入道,儒家挈之以合儒,释家引之以证释。千歧百出,淆乱是非,豪夺巧取,莫知所可”[1]。这些似《庄》而非《庄》的解读,在使《庄子》真实涵义变得淆乱不清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古代多元思想整合的现实风貌。就此,本文拟以庄子养生论为例,做一尝试性探讨。关于庄子养生论之主旨,《庄子·养生主》篇是这样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2]115。从这段文字的表述来看,庄子是以“自然”论养生的。他认为,“知”、“名”、“刑”等皆是残害人之自然本性的外物,人只有顺应本真、原初的自然本性,做到无知无欲,对外物无所追求,才可以实现养生的目的。庄子之后的士人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多种诠释,这一理论也因之变得丰富起来。
一、玄学思想诠释下的养性说
郭象生活于玄风大畅的西晋时期,是当时新义玄学的代表,在其理论体系当中,万物存在的个性价值受到极大重视与肯定,他在庄子养生论的注解中说:万物之存在,乃“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2]128;“生以养存,则养生者理之极也。若乃养过其极,以养伤生,非养生之主也”[2]115。事实上,郭象的解读并不符合庄子原义。主要有两点分歧:(1)对物“性”的表现形式是“一”还是“多”的看法不同。庄子认为万物之性皆以自然为本,不存在个体差别;而郭象认为万物之性虽受之于天(天即自然),但个体之间优劣高低不同的性分差异则是先天就有的,是本然存在而不容抹煞的。由此可见,庄子是在抹煞个体差异,而郭象是在凸显个体差异。(2)也正是鉴于庄、郭二人对物性是否存有个体差异理解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他们对物性达成自足的具体方式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庄子不仅认为物性禀于自然天成,甚至连成就物性的方式亦是自然的,物性的自足是凭借“无为”的方式来实现的;而郭象由于肯定了物性差异的存在,所以为了维护这种差异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达成万有性分满足的方式必然会有所区别。尽管郭象也把万有达成性分满足的方式名为“自然”,但究其真实内涵,确实与庄子“自然”之真实涵义不尽相同。
在庄子看来,“自然”即本来如此之意,亦即无人工介入之本真、原初状态:“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2]294。自然是拒斥人为的,人为是伪,伪即有造作模拟,有了造作模拟,便有假的成份,就是“杂”而“不纯”,就是自然本真的丧失。在庄子看来,人为的介入,强作妄为,乃是对本真的破坏,将会残害自然本性,有违天道,最终会导致事物天性之异化。庄子所谓的“本真”就是放弃人为,一切顺乎万有自然之性,一切皆要做到“无益损乎其真”。由此可见,庄子将万物之性达成的手段归结于无为。所以说,庄子所谓的养生,说到底就是以不养为养。而郭象认为,万物自生之后,便具有了一种先天的内在质素,表现为万物皆自尔,亦即所谓“自性”。这种本性是一种天然的性分,而这种性分就是最合理的存在:“物各任性,乃正正也”[2]317。万物只要按照这个天赋的性分存在,即是合理的。而这个天赋性分之满足又如何实现呢?郭象认为,万有性分虽有不同,但只要根据这种个体差异,施与不同的方法,以“独化”为手段即可实现万物“适性”的生存状态,正所谓“养生者理之极也”。养的最终目的就是养至性分规定的极限,“达到所要达到的一切”[3]205。他认为,“适性”而自然是存在的最高追求,是物性完善之最终结果。为了达成“适性”而存,人可以有为,只要“适性而为”,一切都是可行的。所以说,郭象所说的这种“自性”的达成方式,既包含有庄子自然无为之义:“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2]1,又容摄了人为,甚至把人为因素也说成是物之天性达成的手段。他在《秋水》注中说:“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2]591。郭象认为,牛马被人穿落服乘,虽是人为,但这一切又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符合自然之理的,牛马自然本性的达成恰是需要借助人的穿落服乘才能实现的。由此可见,郭象所谓万有达成自然性分的手段,实际上包含了无为与有为两方面的因素。
就实在情形而言,郭象对万物存在个性价值的肯定,正是对其时任情纵欲世风的回护之说。郭象生活的西晋时期,任情而行成为风尚。这个时段的士人,既重物欲之满足,又重心灵之超越。此时,老、庄思想被广泛用来解释现实生活的种种行为。在任自然这一点上,老、庄思想无疑给当时任情而行的风尚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老、庄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在实质上与任情纵欲是不同的。庄子的任自然,是重心轻物,贵心贱身,越弃肉体,超越情欲,所以它不可能完全满足魏晋士人的现实需要。为此,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魏晋玄学家对老、庄思想加以改造,给予新的阐释[3]59-60,郭象的《庄子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郭象的养性说对后世的注《庄》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原因是《庄子》在流传过程中,“自唐、宋以后,诸家之本尽亡”,“惟有郭象注本”[4]。士人读《庄》不得不读郭本,在潜移默化中必然要受到郭象注解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郭注对《庄子》所做出的世俗化改造:庄子无物无我的人生境界,只存在于理想的精神世界当中,是超越现实的,在世俗中是无法实现的,而郭象对之做出的这种诠释,使得庄子哲学下降到世俗层面,成为论证现实士人存在状态的人生哲学,所以郭注受到后人重视,其思想得到了后人延承,这一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郭象对庄子养生论做出的这一诠释,在后人陈景元、王元泽、沈一贯等的《庄子》注解中均留有明显痕迹。
宋人陈景元的《南华章句音义》对庄子的养生论作了极为简单明确的解释,只用了短短三个字“养性分”[5]。如果深究他所说的“性分”之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去养,他与庄子、郭象的解说究竟有哪些异同,人们不得而知,因为他的解释实在是太简短了。但仅从字面来看,陈景元对庄子养生的解释显然是因袭郭象养性说而来的。
较之陈景元,王元泽的解释则丰满得多:“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于人,素定其分而不过其极,故曰吾生也有涯,役于富贵,悦于荣宠,思虑交萌而妄情无限,故曰智也无涯”;“天者,命也。命之所受于人,不可逃遁而已,逃其命则累其生,适自致于忧患矣,故曰遁天之刑也”[6]。在王氏看来,人之性分源于天地之委和,是不可逃遁、不可违逆的。任何役于富贵、悦于荣宠的追求,都是超越人生自然性分的遁天之举。王氏此论显然是承袭郭象养性说而来的,他也承认万物受命于天,所禀之性各有限分,要恪守之,顺应自然之天命,就可达到养生之目的。不过细究起来,二者对“性分”之具体内涵又确实存在很大差异:郭象对性分的规限是含有情欲的,他认为在自身性分的规定之内,积极主动地借助“独化”手段,任情也好,纵欲也罢,只要能使个体性分得到满足都是可以的,都是符合天命自然的。可以说,郭象所谓的“适性”而存,旨在极力追求个体外在肉身的享受而已,而王元泽的天命“性分”,则是排斥对情欲的追求,希望通过节欲的方式来实现对天命的绝对顺从,用以实现儒家人性的道德完善,此种解读明显折射出宋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观念。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看到,王元泽的这种解读也是有违庄子无为自然之本义的,刻意对人欲强行节制的做法,其实是把庄子的“无为”养生改装成了“有为”养性了。由此可见,王元泽尽管接受了庄子和郭象的思想,但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根据需要对之做了取舍与改造。事实上,王元泽对庄子养生论做出的这种解读,恰是借助了玄学的性分理论阐说了他的理学观念。
对郭象的性分理论既做继承又做改造的注《庄》者,除了王元泽之外,明人沈一贯亦如之:“人各有志,性各有极。吾犹鹪鹩,不过一枝;偃鼠之饮,不过满腹。箕山之阴已了,吾荣愿自足,无待外求,君其休矣。吾何用天下为哉!譬之庖人尸祝,各有司存,纵废宰割之功,亦庖人责尔。尸祝不宜越局而代事。子虽倦勤而禅让,吾肯去山林而代子乎?不愿有天下也”[7]。沈一贯此论显然是承袭了郭象“天性所受,各有本分”、“所禀之分各有极也”的思想,只是二者思想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不同罢了:郭象的“性分”理论追求的是个人欲望的最大满足,而沈一贯不过是想要表达一种不为物累、遗世独立、怡然自足、悠闲淡然的人生理想而已,这与庄子超越世俗的逍遥游境界多有暗合。沈一贯对郭象思想所做的改造,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明季党争中士人内心疲惫与不安的愁苦情状与渴望回归宁静生活的一种自保心态。
通过如上对郭象、王元泽、沈一贯等人对庄子养性说疏解的分析得知,不同注家在接受、改造庄子养生论的时候,往往会从各自所处时代环境出发,打着庄子的幌子,摄入一己观念,以图为时人的生存状态做出思想上的论证。反过来说,也正是从前人对《庄子》所做的这些不同改装,折射出了不同注家所处时代特异的思想风貌与时人各自的人生境遇。
二、佛教理论诠释下的守空论
成玄英为初唐道教重玄派的重要人物,其思想极为复杂,从成氏的《庄子》注疏来看,文中杂糅了郭象玄学与道家、道教和儒家的多种思想。此一现象之产生,与唐初朝廷推行三教并用的政策有着密切关系。在成氏的《庄子·养生主》疏解中,“服道日久,智照渐明,所见尘境,无非虚幻”[2]120,“养生运知,妙体真空,细惑不染心,麄尘岂能累德”[2]122,“况体道之人,虽复达彼虚幻,至于境智交涉,必须戒慎艰难,不得轻染根尘,动伤于寂者也”[2]123之类以佛理论养生的内容比比皆是,从总体上看,成氏主要是以佛教理论来对庄子养生思想进行疏解的。
对于庄子养生论的理解,成玄英疏:“夫善恶两忘,刑名双遣,故能顺一中之道,处真常之德,虚夷任物,与世推迁。养生之妙,在乎兹矣”[2]117。成氏此论讲了养生的三个方面:(1)“善恶两忘,刑名双遣”,谈养生之法。他认为,养生须借助“双遣”为手段,最终在意识上实现对“有”与“无”、“非有非无”的依次否定,进而达成对“空”的体认。庄子“物我两忘”对“道”的体认是建立在无为自然基础之上的,弃绝外在一切的人为,养生就是以无为的方式来达成万有的自然之性,而成氏以“双遣”为实现体道先在的修持手段,显然是背离庄子自然之旨。至于“双遣”一词,早在郭象《齐物论》注中就已使用:“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2]79。不仅不存在无是非之心,连这种不存在无是非之心的想法也不存在。郭象做如是解说,其目的在于消弭世俗中之是非,为生命个体价值的极度张扬寻求理论依据,所以其理论之最终归宿仍然是“有”,而非成氏所说的“空”。综观成氏疏《庄》的整个思想,他以“双遣”解释庄子养生论,其思想来源似与佛教空观及思维方式有关。僧肇论“性空”:“性莫之易,故虽无而有;物莫之逆,故虽有而无。虽有而无,所谓非有;虽无而有,所谓非无”。僧肇是以有、无、非有、非无双重否定的形式来论证“诸法亦相非相,亦非无相”的[8]。(2)“顺一中之道”,讲养生之内容。这里所谓的“一中之道”,实指大乘空宗中道观的中道:“诸法无非因缘所生,而此因缘,有不定有(空),空不定空(假有),空有不二,名为中道”[9]。所以成氏所谓的养生应该以“顺中道”,即“顺空”来解。由此可见,庄子尽管也讲“道”,但实际上庄子所谓的“道”与成氏之“中道”的最终旨向又的确不同:成氏借助“双遣”的修持方式,最终在意识上实现对“空”的主观体认;庄子以不养为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道冥一,无为而自然的物性。成氏的“中道”指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不具有庄子之“道”的本体论意义。当然,成玄英顺“空”的思想与郭象的“生以养存”,即养“有”,养个体之性的理论差别就更大了。(3)“虚夷任物,与世推迁”,明得道之体验。成玄英在《庄》疏多处对此做出描述:“与世相宜。虽复代历古今,时经夷险,参杂尘俗,千殊万异,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怀,抱一精纯,而常居妙极也”[2]102;“养生之士,体道之人,运至忘之妙智,游虚空之物境”[2]123。这就是说,一旦修得正道,便可体道任化:心既虚寂,万境皆空;于是天上地下,悉皆非存,物我为一,无物无我;进而出生入死,随变化而遨游,莫往莫来,履玄道而自得。
除成玄英之外,明人陆长庚亦是一位以佛教理论阐述庄子养生论的典型代表,陆氏对《庄子》养生论是这样做解的:
学道者,只宜虚静恬淡、寂寞无为,常使一念不起,万缘皆空,如是安养主人许有进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恶时是汝本来面目,善恶尚不许思,况复为之而至于近名,犯之而至于近刑,不亦远之又远乎?且善必近名,恶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种则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则无因可知。故此二句当如此看,即不思善恶,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性也,学人当守此中极以为常经。[10]
学道之人要保持一种虚静空灵的心境,如若如此,方能消除一切妄念。妄念既已无存,善恶又如何分别?此时本心清净,便可达到对“空”的体认。如此以往,也就达到养生之目的了。故陆氏所谓的养生即为守“空”之义。需要指出的是,陆西星此处所谓的“空”,是指禅宗真空不空,空为妙有,而非成玄英般若空观中空空之义的“空”。
从上述陆氏对庄子养生论的诠释来看,庄、陆二人的养生思想主要有两点不同:(1)对“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理解不同。庄子所谓的“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与道冥一”的心境,是对“吾丧我”体道状态的一种表述,这种心境是自然得之,并不存在一个预先的修持过程。而陆氏在此处却把庄子“恬淡虚静、寂寞无为”的心境化为达道先在的修持过程,试图借此来克除尘世欲念的产生,达成灭“缘”的效果,进而使得主体达成对“空”的体认。二者的此一差异如果用“无为”、“有为”两个范畴描述,陆氏对庄子做出的改造,则是将庄子的“无为”养生化为“有为”养生。由此可见,陆西星对庄子养生论作出的这一改造与成玄英是完全相同的,都强调了达道之前这个不可或缺的修持过程。(2)实现的目标不同。庄子养生的最终结果是顺应自然达成物性之自然状态,而陆氏养生之最终结果则是对“汝本来面目”(即禅宗清净佛性)的体认,就此而言,他与成玄英基本是一致的。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描述,庄子以不养为养可描述为以“无”(无为)养“有”(自然);郭象养性追求个体价值的最大满足可描述为以“有”(人为)养“有”(个体性分);成、陆借助虚静的心境克除“妄念”最终实现对“空”的体认可描述为以“有”(人为)养“空”(非无非有)。如果用“一”与“多”对他们所养的对象再做分辨,庄子所养的“自然”与佛家所守的“空”都可以“一”来统之,而郭象所养的个体“性分”则可归于“多”。
成玄英与陆长庚均非僧人,而他们运用佛教理论来阐释庄子的养生论,实为不同历史时期多元思想走向全面整合的一种具体表现,只不过促成多元思想合流的机缘不同罢了。成玄英以佛解《庄》,是在唐王朝推行三教并用政策的背景下完成的;陆西星以佛释《庄》,则是明代后期士人思想自觉走向多元化发展的结果。
三、理学思想诠释下的顺理观
林希逸是南宋时期的理学传人,对庄子养生论的理解,较之上述诸家,表现出很大不同:“世事之难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顺而行之,无所撄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伤其生,此所以为养生之法也”[11]132;“人之处事,岂得皆为顺境,亦有逆境,当前之时,又当委曲顺以处之”[11]133;“人世有余、不足,皆是造物,虽是人做得的也是造物为之。盖欲人处患难之中亦当顺受之也”[11]137。在林氏看来,人生处世无非顺逆二境,人世的这些余与不足虽是人做,但又皆是造物(自然)所为,都是“生生之理”(天理)的具体体现。人不论处境如何,皆要“自能顺以应之,不动其心,事过而化其身安于无为之中,一似全无事时也”[11]135。如若如此,也就达到了养生的目的。由此可见,林希逸所谓的养生即为“顺理”之义。林氏这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对“天理”绝对遵从的态度,与庄子是趋同的。
较之庄子养生观的原义,林希逸对之做了两点改造:首先,就“天理”之义而言,林希逸解释说:“命得于天者,子之事亲,与生俱生,此心岂得一日去……义,人世之当为者也。臣之事君,世间第一件当为之事……盖事有难易或有祸福,既出君命,则是自家合做得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顺之……能如此,则为至德之士。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难,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实而已”[11]135-136;“嗜欲者,人欲也。天机者,天理也。曰深浅者,前辈所谓天理人欲随分数消长也”[11]183。此论显然是与朱熹的表述相一致的:“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是退”;“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12]。可见,林氏所谓的“天理”实为一个理学范畴,其中包涵着浓厚的儒家伦理教义,这一点也是违背庄子自然本真之旨的,是庄子极力反对的。其次,正是基于二者对“天理”赋予了不同内涵,所以“顺应”的最终归宿有着明显的不同:林氏顺应的天理是指理学教义,以人为制定的规制约束世人,说到底,林氏所说的“顺应”并非庄子真正的顺“无为”之自然,而是顺“有为”之人事。
除此之外,林氏思想与上述诸家的不同还表现在:林希逸的养生论是为了论证俗世人生的生存状态的,而庄子与成玄英的理论则恰好与之相反,是超越世俗、纯精神上的,所以他们的理论不具有实践的品格。此一差异之产生正是基于他们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所致。林氏认为,人活着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既有此身,而处此世,岂能尽绝人事,但要人处得好!”[11]143人生状态,无非是顺、逆二境,不存在除此之外的第三种状态,人是不能对此做出超越的,只能顺应,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由此可见,林希逸完全斩断了人世当中除顺、逆二境之外的任何退路,所以,类似于庄子与成玄英超越世俗的第三途(即“中”)也就被林氏彻底否定了,或许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林氏思想的基本精神只能是人世的,不能走向类似于庄子和成玄英的空无境地。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不同的人由于诠释的差异,最终也可导致其理论产生的人生指向并不相同。郭象同样把儒家的仁义规范纳入了他的物性体系当中:“夫仁义者,人之性也”。鉴于他对人之个性价值的重视与肯定,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个性得以张扬的依据;而林希逸对儒家思想做出的上述诠释泯灭了人的个性,成为了严厉压制人性的思想教条。
林氏以对“天理”绝对顺从的理论来解读庄子的养生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是从正面肯定了儒家教义的绝对权威。这一做法对此后以儒解《庄》的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郭良翰的《南华经荟解》,其“内注多主林希逸”[13];而韩敬的《庄子狐白》,则是全文照抄林氏的注解。除此之外,明人朱得之的《庄子通义》亦多承袭林氏之说,如他对《庄子·养生主》篇中对“缘督以为经”一句疏解:“此一句乃养生修德之纲领,曰养生而不言修德,正逃名之意也。保身不犯世纲,全生完其天性,养亲尽其当为,尽年不取夭折,皆不尽刑名之实也,……以解牛之技拟养生,言应世当审几顺势而不以强力制割也”[14]124-125。从上述的阐释来看,朱得之将庄子的养生说成是修德,把对儒家世纲的恪守和养亲尽孝看作是人生当为之事,人生应世当以此为行为准则,“审几顺势而不以强力制割也”。由此可见,庄子顺应自然的养生论经过朱得之的诠释,完全变成了儒家世俗人生的处世哲学。这一点与林希逸是俨然一致的。其实,对庄子养生论做如此解释的,也并非仅林希逸和朱得之二人,附于朱氏注文之后的宋人褚伯秀的《义海篡微》,也做了类似的解读。如褚伯秀对《庄子·养生主》的开头部分疏解:“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恶而恶之,虽为非为也,又何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为善恶而近名刑,不为善恶而无近名刑,皆理之当然。今则为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视之以为善恶,而圣贤之心常顺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归也”[14]125。褚氏对顺应“天理”的疏解似乎是绕了一个弯子,他说:天下人所共同认可的善即为善,天下人所共同认可的恶即为恶,人之行为只要符合这一约定俗成之标准,亦即“天理”,即使是做了也不会被别人觉察,做了也等于“没做”,“没做”也就是所谓的顺应了“天理”。若以此方式去应世,自然也就不会因违反处世规则而有刑名之累了。在褚氏看来,“为”与“不为”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判定“为”与“不为”的标准,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参照物来判定这些行为,即这些行为所达成的效果是否被世人所认可。如果这些行为被世人认可,那么“为”也是“不为”,反之,如果这些行为不被世人认可,“不为”也是“为”。其实,褚氏对“为”与“不为”做出的这一界定,与上述玄学家和儒家把庄子的“无为而自然”化为“有为而自然”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清人吴世尚《庄子解》也是用顺应儒家天理来解释庄子养生论的。他说:
程子曰心如谷种,仁则其生之性也。庄子所谓生主,正指此而言。养谓顺而不害也。心不可放操之,则存性不可逆,循之为是。身之主,心也;生之主,性也。庄子言性非言心也,故通篇总是个顺而不言之意。[15]73
天命之谓性。性者,生之主也。率而循之,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胥在于此。世之人乃不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以其无涯之知。忧其知之所不及,强其力之所不能,舍安就危,去顺即逆而不知其岁月之间忽已销亡矣。……圣贤行其所无事其道固如此耳,是可知性以利为本,天下之养性者,亦惟不凿其私智,则处顺处逆,我有以善其天为生为死,帝不能县乎我。……我不能养之天下事,皆我累也。……我能养之天下事,成我顺也。[15]77-78
吴世尚借用程子“心”、“性”等范畴来阐述庄子的养生论。他认为“天命之谓性”,“存性不可逆”。人须要顺性而存,依天理而行,正所谓如若能“率而循之,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换言之,“我能养天下事,咸我顺也”。所以说,在吴氏看来,庄子的养生就是顺性、顺天理之义。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与郭象、林希逸、朱得之、褚伯秀等人一样,吴氏的“天理”所附有的儒家伦理教义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其所言:“仁则其生之性也。庄子所谓生主,正指此而言”。
通过对林希逸、朱得之、褚伯秀与吴世尚等人对庄子养生论的解读分析,可以看出,儒家积极入世之态度及其对俗世人生的普遍关切,决定了它的理论只能是落归于实在的“有”,即现实的俗世人生。所以,儒家的理论不可能脱离现实,像佛、道一样走向精神世界里的空无。
概而言之,玄学思想诠释下的养性说、佛教理论诠释下的守空论以及儒家思想诠释下的顺理观,在《庄子》诠释史上只是较有代表性的三种观点,并不能涵盖古代士人对庄子养生论的所有理解,如明人陈治安的《南华真经本义》、清人方潜的《南华经解》等,即是用道教的内丹养生理论来诠释的,限于篇幅,恕在此不予展开论述。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一种思想被传承、丰富的过程,也是这种思想被不断与其他思想整合的过程,其整合的形式与结果也会随现实机缘的变化而呈现出多种风貌。在庄子养生论的诠释史上,养性说是郭象在西晋玄风大畅时期融玄学于庄子为时人生存状态做出的思想论证,守空论是成玄英、陆长庚等人在唐初、晚明思想多元化的情境之下对庄子思想做出的具体理解,顺理观则是林希逸等人在宋明理学兴盛之际为推行朝廷主流意识形态对庄子思想做出的积极改造。
[收稿日期]2008-0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