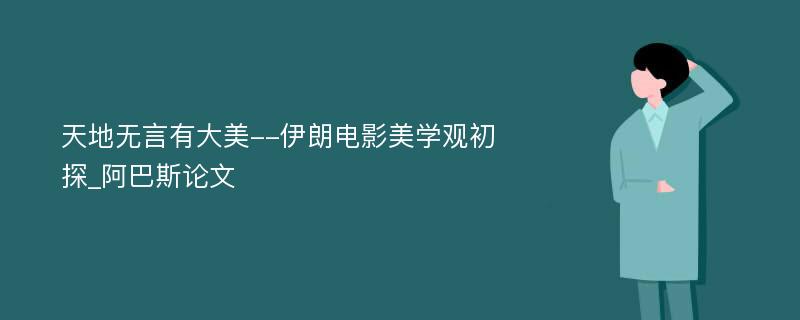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伊朗电影美学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朗论文,美学论文,不言论文,天地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你家中破旧的门,遮住的贫穷很美 ——海子
或许是对电影司空见惯,使得我们对于它的语言有了一种世故的漠然,我们的感性能力在越来越多的电影面前越来越衰竭,是伊朗电影让我直觉到了这种能力的苏醒。正如劳拉.穆尔维在谈到初次观看《橄榄树下》的感受时说:“我感到一种突然的、直觉上的震动,当时我觉得电影仍然可以是令人惊奇的、美妙的或者触动理智的。”这种惊奇是如此柔软细密,布满高度感知的神秘力量,让人失去思想的能力,人类的情感在面对这惊奇时突然变得异样粗糙和不可言说。在这惊奇的朴素的美面前,我们只有错愕,没有亢奋,没有憧憬,没有悲伤,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一、实践理性的抒情艺术
德国著名的古代美术史研究者维克尔曼认为希腊艺术之美,在于其“高贵的单纯性,及平易的伟大。”我想这样描述伊朗电影:深刻的单纯性,及平易的伟大。陆绍阳在《从简单出发》中,认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文化是他们的文化根源……法律很有效地凸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风格、精神气质,电影作为一种现代传媒无疑是一个国家民族气质的一面镜子,一种保守、排他的宗教根源决定了伊朗电影中朴素、简单的风格。”[1]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认识,这不是伊朗电影形成“深刻的单纯性,及平易的伟大”的美学风格的全部。伊朗电影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风韵,深情、执着、温柔含蓄的情怀,安详凝练的静态姿势和内在精神,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无一不呈现着东方美学的精髓。讲述伊朗本土的故事,熔铸具有强烈东方色彩的美学精神和哲学思考,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本相,构成了伊朗电影在文化的限定和保全中的美学范式:风格取向上的本相化,文化取向上的民族化。
文化的差异制造了伊朗电影的神秘和隔膜,当神秘和隔膜与伊朗无可阻挡的本土文化力量相结合时,成为了美。神秘和隔膜不仅来自宗教,也来自战争、苦难、贫穷、悲惨。然而用感伤和悲悯的态度永远无法理解伊朗电影,认为伊朗电影讲述的是战争、贫穷、悲惨,就更加远离了它。伊朗电影的实质用海子的诗可以基本诠释:你家中破旧的门,遮住的贫穷很美。是的,伊朗电影寻找的是贫穷中的诗意,灾难里的生命力,破败中的力量,逃难里的美。绝望中的自由。阿巴斯说过:“我总是寻找简单的现实,这种现实往往隐藏在表面现实背后。”[2]简单背后,隐藏的现实有着巨大的迷惑力。无论是探寻生命本质的阿巴斯,迷恋情感表达的马吉德.马吉迪,还是在残酷的现实中顽强地寻求诗意的玛哈玛尔巴夫父女,甚至对茫茫人世充满宿命感的贾法.帕纳西,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整体的感性气质,我把它叫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华夏庄子美学的精髓。庄子学派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美存在于“天地”——大自然之中,为“天地”所具有。人要使自己“备于天地之美”,就要“观于天地”,“原天地之美”,“判天地之美”。即要人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去了解美,寻求美,而不是到某种超自然的神秘的精神世界或天国中去找美。阿巴斯《随风而去》里的老医生早已悟此真谛:“观察自然比做西洋双乐棋戏和不做什么更好。观察自然使我获得大部分生活。”“天地之美”的本质在于“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一切纯任自然,而至“素朴”的大美之境。达到了素朴,也就达到了天下不能与之相比的美,即纯审美的境界。“所谓纯审美,是与无限自然同一的积淀感性。这种积淀感性以及其对象——无限的美,便正是那不可言说的本体存在。”[3]所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虽呈现为外在的客观形态,实质却指向那最高的‘至人’人格。”[4]这正是在伊朗电影里自然地包含着的生动地呈现着的那种文化与美学的感性里深刻停留的理性力量。我们恐怕永远也难以忘记《随风而去》里茫茫的淹没尘世的金黄的稻田,和飘荡在稻田的风中的老医生的话:“死亡是最可怕的疾病,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这种风景,自然的奇妙,上帝的慷慨,意味着你永远回不来了……他们告诉我说她和天堂女神一样美丽,然而我说葡萄汁更好。”《樱桃的滋味》里的老人表达了同样的生死观:“路很长,但一路风景不错……生命是永不休止的,也是有始有终的,死等于终止。”人作为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依据何在,在这里有了空前的突出。伊朗导演以个体的现实存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来询问真理。因此,“这真理便不再是观念式的普遍性概念,也不是某种实用性的生活道路,而是‘此在’本身”。[5]完美的全景镜头,一览无余的金黄,神喻般乍然焕发的绿,如此平凡、写实、自然,但它传达出来的意味却是永恒的静,本体的静。来自生命深处的声音回荡在天地的大美之中,生命的本体存在、主体的人格理想以大写的形象顿然隐现于天地之间。这是东方式的具有深刻感性力量的实践理性的抒情艺术。
伊朗电影不是以追求某种外在美为目的,而是以追求人生的解放、探求生命的本质为目的。这种艺术性的精神,在其影像表述中,自会流露出某种性格的美,从而形成一种自然天成的气质,即是“天地之大美”的那种平淡天真的纯素之美。为了逼近自然,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原生态,伊朗电影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法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拍摄故事片。阿巴斯说过:“电影是为了记录事物的。画面具有比现实自身更加强烈的资料性”,[6]无论是莎米拉视线里逃难的人群,视儿子为唯一生命的女人,背着黑板求生的教师,战争,死亡;穆森视线里茫然的失学的女童,固执地要达到目的的女人、男孩,向着飘然降落的假腿奔跑的断腿的男人;马吉迪视线里艰难承担生活的意外来回奔跑的充满人间情性的儿童;还是阿巴斯视线里琐碎静止的日常生活,安详的妇女、老人,绿树、稻穗、红土、环行的尘土飞扬的路,走不出的又舍弃不了的生命的圆圈,这种种或悲惨或温暖或静穆的形象中,保有着一种真实的稚气,使这些毫不掩饰的天真拙扑近乎原始的人间图像荡漾着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人类童年气派的美丽。这美丽是在若即若离又无比纤细的属于感受的描述中获得的。伊朗导演不是用摄影机去抚摸事物,而是用目光和内心的颤动去抚摸。
“在路上”一直是伊朗电影的一个大写的中心意象,这一意象在伊朗导演的作品里得到惊人的反复的整体性表达,这除了与伊朗的本土文化和动荡的社会现实相关外,恐怕更与伊朗导演的生命体验、美学情怀相关。无论是开车行驶在路上一直想自杀的出租车司机,不断请求路人告诉他们有关两个孩子的消息的导演父子,坚定不移寻找妹妹的女记者,一心寻找朋友的家的小男孩,反复开车到高岗上的工程师,追寻音乐之声的瞎男孩,还是莎米拉目光里逃难的流浪的人群,马吉迪的凝视里为了换鞋来回奔跑的孩子,“在路上”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生活。“在路上”表达了伊朗人朴素的生命观,以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体验。生命永远在行程中,充满寻找、失望和痛苦,也充满美,起点和终点只是一个停顿。“在路上”真实地观察自然,记录生活,体现了东方美学中美与真互为统一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那就是“法天贵真”,崇尚不事人工雕琢的天然的美。“在路上”那么多的空间形象包括自然、人和日常生活,无不渗透了时间的深情和人文的依恋。“在路上”不仅是伊朗电影的表意策略,同时也是它的修辞策略、美学策略。“在路上”将无数的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从本质上展示和流露出时间进程的流动美。
伊朗电影叙述中柔软凝视的目光一方面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在积淀感性的本体沉思中扩大了这样的距离。这正是伊朗电影朴素简单背后难以让人真正读懂的原因。也正是在此体现出东方美学中实践理性抒情艺术的精髓。在外在的客观形态的美身后,在安详凝练的内在精神里,在贫穷、死亡、阴影的耳语里,是生活的真谛、生命的顿悟,是人间的情味和人际的温暖,是残酷破败中的诗意,是“不道破一句”的“天地大美”。它平凡而凝练,冲淡而真挚,表现出来的不是顿时的感情,而是稳定的人格。阿巴斯在《樱桃的滋味》里不着痕迹地让一心求死的主人公聆听机器铲土的阴影的耳语,在假借的生与死的对话里,以安详的静态姿势表达出主人公内心的惊心动魄,暗示出生与死的真相。穆森在《坎大哈》中以极其优美的影像和天籁般的音乐描绘了一群瘸着腿奔向空降的假腿的男人,在高速摄影的充满静态感的运动中,伊朗人谋求生活的顽强生命力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随风而去》里遭受人为灾难的乌龟几经努力后又翻转了身体,阿巴斯以极大的耐心和温情再一次目睹了生命在继续。每一个感性的影像里都蕴涵着深刻的实践理性精神。伊朗电影里呈现的“大美”,不同于西方美学所谓的“崇高”,也不同于“壮美”,它不是主体受到无限力量压迫又在压迫中意识到自身力量的结果,它是与自然的同体同在,是主体等同于无限的结果。它的痛感不是来自恐怖的力量,而是来自安详与静穆的滋味中的失魂落魄,那是对自由生命透彻领悟的力量。伊朗电影始终隐藏着一种昂扬的美,你只要有足够的真诚去倾听贫穷和苦难中的生命,就会找到那种明朗的满怀祝愿的肯定着人的自由和伟大的美。
伊朗电影大都保有开放式的结尾,阿巴斯说过:“所有影片都应该是开放性的和提出问题的,应该给每一位观众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如果忽视这种自由就回到教训观众的老路子上去了”[7] 开放式的结尾既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自由生命与自由意志的尊重,正如《樱桃的滋味》里的老人所说:“这事只能由你决定,别人谁也无法阻止。”即使导演也无法干预生命的自由选择。在伊朗导演简洁凝练的叙述里,其实弥漫着理性的茫然,无法确定的开放式结局是理性茫然的结果,然而他们热衷于这样的茫然,因此当他们不断地靠近真相时,又在不断地隐藏。被隐藏的总是更加令人着迷,也更加失去确定性,它使观看走向不可接近的状态。因此,才会有《樱桃的滋味》在黑暗里体验了生与死的交错的主人公未曾揭示的理由未曾确定的选择,才会有《坎大哈》寻找妹妹的主人公未果的寻找,才会有《黑板》里幸存下来的逃难的人群不可知晓的命运,才会有《随风而去》中反复开车到高岗上通过电话一次次暗示行程的工程师未曾道出的悬疑,才会有《天堂的孩子》在历经重重努力后仍旧茫然的目光仍旧无言的哀愁。然而,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又绝不是单向的温情脉脉,而是充满了现实人生的复杂性。理性的茫然使他们获得了现实的宽广,也获得了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伊朗导演在展示人间深情、人际温暖,在展示美的同时,绝不回避现实的残酷,生活的真实,理性的茫然支配着感性的温情,在柔软的感性深处,是无法回避现实的理性目光。因此,《天堂的孩子》在命运的阴差阳错中最终也没能实现心愿《哪里是我朋友的家》在历经重重的寻找后仍旧没有找到朋友的家;《坎大哈》女主人公在战乱中也绝不可能轻易找到妹妹;《万籁俱寂》中的瞎小孩在通灵了音乐的神性后同样不能替母亲挣到付房租的钱;《黑板》里那些返乡的流浪的人群在战争和死亡的路途上能够平安返乡吗?在伊朗导演充满人道主义的悲悯目光中,是同样充满人道主义的实践理性的抒情精神。
二、电影有没有护照
单万里在《大器晚成大盈若缺——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素描》中沿用切西尔的观点,认为阿巴斯和黑泽明、雷伊、张艺谋一样,是一个跨文化的导演,认为“他的电影以东方的异国情调和西方的本土文化的适度融合护卫着一种不知名的影片进入西方艺术殿堂。”单从上文即可知晓,这实际上是对阿巴斯的误读,也是对伊朗电影和伊朗文化的误读。阿巴斯说过:“我生活在伊朗,但我不想让我的影片也有伊朗护照。我是为人类拍电影的,我的影片没有精确的地理界限,它是关于整个人类的。电影没有护照,就像树木一样。”[8] 他还说:“我认为梦想是没有边界的,音乐也无须护照才能旅行。虽然这些音乐是西方人创作的,但它所表达的是全人类的情感。”[9]阿巴斯并非要在西方文化与伊朗文化之间寻到一种平衡点,而仅仅是,他在宏观上的表意是人类性的。正如他所说:当人们将脑袋伸出窗外,发现天空到处是一样的。不仅阿巴斯,其他伊朗导演在主题上的取舍也都如此。伊朗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其民族性有着深厚的宗教文化烙印,然而伊朗电影整体渲染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的生活意绪,将天地的大美与对人的本体存在的深刻感受和探询连在一起,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在充满战争、动乱、贫穷和无处不在的死亡的伊朗,伊朗电影的深刻性在于:超越了情绪宣泄的简单内容,而以对人生苍凉的感喟,来表达出某种本体的探询。由对人生——生死——存在的探询,达到哲理的高度。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在这里,一切情感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有限的人生感伤总富有无垠宇宙的含义。它变成了一种本体的感受,即本体不只是在思辨中,而且还在审美中。不仅对死亡,而且对人事、对风景、对自然,也都可以兴发起这种探询和感受,使世事情怀变得非常美丽。”[10]
这种探询显然是人类性的,但是这种探询的方式,探询的气质,探询的细部叙述以及对这种探询的深情迷恋和重复表达,又是为伊朗民族乃至东方民族所独有的。现代原型研究认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特征会在文化发展中以不同的变形表现出来。比较文学专家叶维廉也说:“文化极其产生的美感感受并不因外来的‘模子’而消失,许多时候,作者们在表面上接受了外来的形式、题材、思想,但下意识中传统的美感范畴仍然左右着他对外来‘模子’的取舍。”[11]伊朗电影同样如此。在人类性主题的宏观表达背后,是繁复的伊朗本土文化的细密痕迹。关于这一点,上文已就伊朗电影的东方美学气质作过相关论述,在此拟从几个细部探讨伊朗电影里流露出来的本土民族文化的印痕。
众所周知,阿巴斯的电影风格,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循环往复的特征,循环往复不仅包括情节的反复、对话的反复、影片与影片之间的循环关联,也包括结构上单向线性叙事带来的重复。在其他的伊朗导演中,同样表现出这样的特征。伊朗电影给人以简单朴素的表象,很大程度上是由结构上的单向线性叙事带来的。伊朗电影是电影里横断面理论的有力证明,没有哪一个国度的电影能够像伊朗电影这样固执地守持着这种横断面的表述,但又有着远远超越横断面的经度和纬度。我们惊讶地看到,《樱桃的滋味》、《生命在继续》、《坎大哈》、《哪里是我朋友的家》、《随风而去》、《天堂的孩子》、《万籁俱寂》,采用的都是中心聚焦的方式,顽强地单向地跟随主人公向下讲述,目光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主人公。《黑板》似乎是个例外,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方式,这反映了年轻一代伊朗导演在文化的限定和保全中所做出的新的努力。伊朗电影呈现出来的这种横断面结构的整体景观,决非人类性的,而是为伊朗民族所独有,它表达了伊朗民族顽强的近乎固执的民族性。
这种民族性的固执、坚韧的气质在伊朗电影里无处不在。情节的重复、细节的重复、对话的重复、人物行为的重复无不在表达这种固执。无论是《天堂的孩子》那个蒙受着巨大委屈固执地请求老师要参加比赛的男孩,《坎大哈》里不停行走一定要找到妹妹的女记者,《哪里是我朋友的家》中艰难地固执地寻找朋友的家的小学生,还是《樱桃的滋味》里行驶在路上一心求死的出租车司机,甚至《黑板》里自比为火车将儿子视为唯一乘客的逃难的女人,《橄榄树下》不断重复表达爱情固执得无以复加的男演员,《万籁俱寂》里执着追寻音乐之声的瞎小孩,这些人物是如此固执地保有着一种信念以致任何障碍都不能改变他们的既定动机和行为。同时,伊朗电影里意象的重复也有着巨大的象征意味,尤其“路”是不断反复堆积的意象,《樱桃的滋味》里那条循环往复尘土飞扬的环形车路实在让人惊讶阿巴斯那种固执得近乎自负的凝视方式,这种方式除了表达伊朗人对生命的理性体验和哲学沉思外,更表达了伊朗人独特的感性经验的固执和坚持。
不仅如此,这种固执的民族性更深刻更富于哲理地体现在人物的对话上。伊朗导演大都善于反复推敲人物对话,这除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外,恐怕更在于民族性的无意识。在伊朗电影里,人物对话的方式是极为奇特的,几乎看不到常规的正反打镜头,要么是单向对话,前景里只有主体的一方,对话的另一方被置于背景或远景或干脆不出现而只闻其声,主体似乎在自言自语;要么双方都不出现,只有声音在画面上回荡;要么双方都在画面中,看着对方各自说话,就像在对自己自由表达。这同样是伊朗人固执、保守的民族性使然。执着于自由意志的表达,不为任何外来力量所干预阻挠。这同时也反映了伊朗导演在美学上的固执追求,剔除一切枝蔓,甚至语言的枝蔓,展示伊朗人的生存本相。因此,当我们看到《哪里是我朋友的家》中的小男孩在母亲的责备中执意地重复着要还同学的作业本,画面上,没有母亲的形象,只有母亲模糊的责备的声音,和男孩固执的不断重复的话;《随风而去》中工程师无论和同事,还是和邻居妇女对话,工程师总是被凸现于前景,说话对象要么被隐藏要么处于背景或远景中;《坎大哈》中追逐着女记者嚷着要卖戒指的带路的男孩;《黑板》里执意要教会视儿子为唯一生命的女人“我爱你”的乡村男教师,以及帮助老人读信的男教师和失去儿子的老人之间那场各自表述的奇特的对话,我们就不会为这种表达感到惊讶。这是文化的差异造就的别样气质。
在伊朗电影简单朴素的影像背后,无论是其人类性主题的宏观表达,还是其细部叙述的民族化立场,还是其深情、执着、温柔含蓄的本相化东方审美情怀,都是异常丰富复杂的。伊朗电影并不是“不是欲望,更不是关于欲望的欲望”,而是多种欲望的表述,多重欲望的呈现。欲望隐匿在纯粹的深处,你只要能足够领悟伊朗电影里那些执着于自由意志表达的声音,就会明白这个民族在安贫乐道里的信仰和欲望是何等炽烈。犹如蒙着面纱的伊斯兰妇女,伊朗电影的单纯是深刻的单纯,平易是伟大的平易,美是不可企及的美。
标签:阿巴斯论文; 伊朗电影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天堂的孩子论文; 黑板论文; 坎大哈论文; 万籁俱寂论文; 剧情片论文; 战争片论文; 儿童电影论文; 家庭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