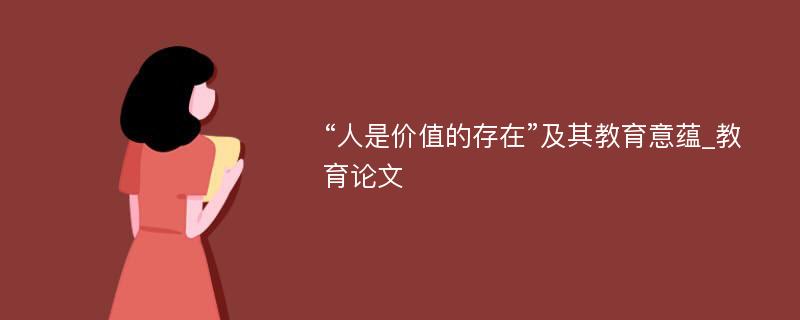
“人是价值的存在”及其教育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人是论文,教育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 (2001)05—0007—05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成人”,教育学乃“成人之学”。这种问题的特殊性使得对教育的探索更适于采用价值研究的理路。换言之,价值关涉是教育学作为“成人之学”的合法性、有效性的灵根所在。在此意义上,任何丧失了价值关涉的教育研究都背离了教育的“成人”宗旨,使得教育沦为一种教授之术或操作技术。然而,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价值论研究主流的“关系说”却无力担负起我们重新理解教育的重任。因为从根本上说,“关系说”仍然是以“物”的方式来理解“价值”、理解“人”,由此导致了人在教育中的放逐。为了在教育领域中实现人的回归,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一、人:价值的存在
“关系说”认为:“价值”这个概念所肯定的内容,是指客体的存在、作用以及它们的变化对于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1 ]简言之,价值反映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即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关系说”一方面没有否定客体的意义,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主体之于价值的作用并在主客体之间显然更强调主体,所以它具有较强的解释性。
但“关系说”也有着极大的缺陷:第一,以“需要”来定义价值,无法凸现价值的实质。因为价值“不只是体现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而且还表现着人的主动追求……而人之为人恰恰在于,他有需要却不束缚于需要,也从不以满足需要为满足,总是在那里不断提出新的更高的追求。应该说正是这点才使人和动物分道扬镳。”[2]由此可见, 价值并不主要指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和被满足的关系,而是指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
第二,由于“关系说”把“价值”仅仅看作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相结合的产物,因而把二者结合最重要的焊接点——自由选择——丢失了,所以它在价值问题上根本无法凸现人的自主性[3]。为此, 我们必须深化一步:在承认以上二者的前提下,是人之自由选择把价值引入、带入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自由、自由选择是价值的根基和灵魂。不以自由为基础、不经自由选择的东西没有价值。这一点正如康德所指出的:一个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不仅在于它是合乎道德的,更在于它是出于道德的。“出于”就是自由选择。所以,在价值问题上必须立“自由选择”这一项,否则,价值问题就只是事实问题。可以说,自由、自由选择使得价值世界充满了意义。可见,价值是客体属性、主体需要和自由选择三者的结合,而不仅是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的被动的一致、适应、结合。
综合上述,“关系说”没有看到价值与选择、追求之间的本质关系,因而充其量只能部分反映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中诸如追求、超越、创造等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部分却无法得到反映。这不能不说是“关系说”的深层缺憾。
这种不足已经体现在近年来的主体性教育研究之中。应该肯定的是,提供主体性教育切中了中国教育的“无人”时弊。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研究者已经走出了近代以来所倡导的狭隘的个人占有性主体性误区,开始自觉地向价值主体性教育思想转化。这既是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流,也是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方向。但也应该看到,价值主体性教育的立论基础仍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知识论模式。这种模式从严格意义上讲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它最初是一种认识“物”的范式,逐渐扩大并用于认识“人”自己。由此,这种范式的潜在弊端是:(1)把认识“物”的模式套用到“人”身上;(2)获得的对“人”的认识是残缺的——这种模式的认识论立场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主要是一个“认识者”,因此,这里的“人”实际上是不完整的。以之为立论基础的主体性教育也不可避免的染上了以上双重症状:(1 )明明我们讨论的是“主体性教育”,但由于这种主体性是立足于“物性”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在教育中获得的很可能是一种“物化”的主体性、“工具化”的主体性,“人”仍然是不见的——这恰恰违反了我们研究的初衷;(2)退开一步说,即使主体性教育关注了“人”, 但其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立场又把受教育者牢牢定位于一个“认识者”,这必然使“人”发生断裂和畸变,换言之,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仍然是不见的——这恰恰背离了教育的真谛。
可见,以这种“物”的模式来研究价值,必然导致人的目的的地位失落,进而使人“手段化”、“非人化”。因为不管它多么强调人的价值性、能动性,人还是摆脱不了被“物化”、“工具化”的命运。在这种思路支配下的教育价值观,也必然以“物”的眼光来看待活生生的学生,尽管它也强调尊重学生,也强调学生的能动性,但这充其量只不过是“活的物”、“活的工具”而已。所以,仅仅呼唤人的回归、仅仅倡导培养主体性还不够,还要看是在“成人”还是“成物”的立场上呼唤人的回归、培养人的主体性。
以上表明,只要我们还局限在认识论、知识论的视野上探讨价值,我们充其量获得的只是关于价值的认识论、关于人生的认识论,而不是真正的价值论即人生哲学。从极端意义上说认识论告诉我们“知其不可为必不为”,即所谓明哲保身;而价值论则要阐发“知其不可为而必为”。所以,基于认识论立场上的价值论研究具有先天的不足,这种价值论以“物化”的方式来看待“人”,因此,它看不到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这是价值的根基所在,看不到“法由己立”,看不到人的目的的地位,看不到人的生活。因而这种价值论也就根本无力承担我们对教育的崭新理解。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一条能够找回人的尊严、尊重人的生命的“价值”之路。人学的观点恰恰在这一点上对我们有重大启发。
人学倡导以“人”的方式来把握人、理解人。由此,在人学的视野中,人是价值的存在。它以“人是目的”为最高原则和出发点,它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它看到了人的选择性、超越性和创造性。以上思想在作为人学源头的康德那里就已得到彰显。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足的。因为“人是目的”,而且是最后的目的,亦即他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以任何其他目的为条件的。这是人和物的根本不同。自然界的任何事物,由于其本身并不是目的,所以它的价值是相对的,是使用价值,即它只有被人使用作为工具时才具有价值;但人不同,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一切其他事物作为手段都是为人服务的,因而人也就成了价值的源泉,康德称之为绝对价值。由于康德是从本体论高度阐明价值的,所以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而且是自足的价值(这缘于他有人格)。所有价值都根源、发生于自足价值。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就是人的自身本质。”[4]一言以蔽之, 本体意义上的价值,“既不是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所构成的实体,也不是客体对象与主体需要之间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因为它是绝对的,所以是自足的。又因为它是自足的,所以是超越的。由于是超越的,价值又表现出应然性、理想性、目的性和批判性特征。”[5]“追求”、 “超越”等等充分凸现了人之自由选择的重要性。
这样,我们就确立了人在价值上的本体地位——人是价值的存在。它表明,从最高意义上讲,只有人,才是一种“无价”的价值。换言之,“人”是价值的真正源泉。所有其他的价值都是从这一根本价值、绝对价值、自足价值中派生、衍生出来的。
上述立场的确立,必然使教育呈现出新的情形。在以往的教育理论中,尽管也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或主体地位,但却从来没有为此而找到“立法”的根据,以致于我们总是羞羞答答而不能理直气壮。教育理论的不彻底性导致了教育实践中学生事实上的被改造地位:所谓的学生主体性不过是一种“活动的物性”罢了,即在“物”的被改造范式中给你一点灵活性,从来没有上升到“人”的高度上来把握。由此,“教育”的丰富意义都被遮蔽了。现在我们知道,以上问题的症结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没有意识到“人是价值的存在”,没有意识到“人是目的”。而它们恰恰是确立学生之主体地位的立法依据所在。一旦脱离这一根据,人也就必然沦为“物”的存在、“工具”的存在,而教育也只能沦为一种“成物”的手段而已。
二、“人是价值的存在”的教育学意蕴
“人是价值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考察“教育”的基本线索,它内在地要求把人性化、个性化和创造性放在教育的首位,由此也就生发出一种新的教育学语境。
第一,人性化。
人性化首先意味着教育对人的尊重,它包括教育理念的人性化和教育环境的人性化。前者指教育者要在头脑中真正树立起受教育者之主体地位的意识,敬重受教育者的人格。所谓“教育爱”正是源于对“人是价值的存在”的深刻体悟。也就是说,不能再把受教育者当作“工具”,进而像对待“物”、“动物”那样对受教育者进行改造、加工和训练。后者则指整个教育环境都要以对“人”的方式来设计。无论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还是师生关系,都应该自觉地渗透一种关怀意识,亦即以关怀意识为底蕴。这种关怀意识对于“教育”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教育事实的属人性,亦即一种价值关涉。从根本上说,没有这种价值关涉,教育就根本不成其为教育。只有在人性充盈的地方,才能生长出健康的人性和自尊的人格;而在人性的沙漠中,我们收获到的只能是病态孱弱的人性和冷漠的人格。
人性化还意味着自觉培养具有完满人性的人,也就是把价值主体的培养放在根本位置。强调价值主体,并不是要排斥知识,而是把知识统合于价值的意义关照之中。由此,对受教育者情感、意志等品质的培养也就必然得到关注——它们并不比知识低贱。这样,我们才能突出“教育”的完整内涵,也才有可能培养出相对完整意义上的人性丰满的人。杜威对此的认识是深刻的。针对教育的惟知识化倾向,杜威提出了“道德即教育”的著名命题:“道德意味着行为意义的增长,至少它意味着这样一种意义的扩展;……在道德这个词的最宽泛的意义上说,道德即教育。”[6]这一点实际上已为世界教育所认同。 《学会生存》确定了一个指导教育发展方向的基本思想:“人类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创造性的理想家,来承担不同的责任。”[7]《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则又进一步指出:“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使每个人的潜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这既符合教育的从根本上来说的人道主义的使命,又符合应成为任何教育政策指导原则的公正的需要,也符合既尊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又尊重传统和文化多样化的内涵发展的真正需要。”[8]
以上论述实际上表明人性化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内在关系。“人文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在培养人文精神这一点上,人性化教育与人文教育是一致的。所谓“人文精神”,就是反对把人作为一个死的“东西”来研究,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它要求尊重人的需要、情感,并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它提倡每个人在自由生活的同时承担必不可少的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的责任;它要求关怀人的终极意义,弘扬道德价值和审美意蕴,培养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时代风尚。质言之,人文精神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内蕴类意识的个体主体的提升为最高目的。
顺着这样的思路,反映在当代教育的培养目标上,人文教育不仅强调人性的培养和理性的养成,而且趋向于培养完美的人,也就是集“真善美”于一体的人。这诚然带有“理想”的成分,但这也正是人文教育的卓越之处——它深刻的看到了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均在于理想的人的形象,因为如果没有某种关于受过教育的人的理想,就无法从事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教育是对本真教育的一种自觉捕捉和把握。从历史上看,近代人文教育主要以维护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为特征,现代人文教育则以批判、反思现代教育的惟科学主义倾向、功利化倾向为特征。目前,它又有所深化,即特别强调道德在个体完美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中又着重强调理解与和平、人的尊严、自由和责任、敬重自然等伦理价值等。为此,它要求把价值教育置于整个教育的首要地位,把人性化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和因素之中,使整个教育环境人性化。这集中体现在“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等新时代的教育思想之中。
第二,个性化。
如果说人性化侧重于对人的完整性的强调,那么个性化则侧重于对人的独特性的强调。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站在价值论的高度,教育对人之个性的尊重就是对人之价值的尊重。但我们的教育却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实质上是对人之价值的伤害。正如《学会生存》所指出的,传统教育有两个根本弱点,“第一个弱点是它忽视了(不是简单地否认)个人所具有的微妙而复杂的作用,忽视了个人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的表达形式和手段。第二个弱点是它不考虑各种不同的个性、气质、期望和才能。”[9 ]这种工厂“流水线式”的工业操作模式生产出的只能是划一的“样品”,是“制器”而非“育人(杨叔子语)。由此,这种“产品”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区别,完全可以互相替代和忽视。这不能不说是对个体存在权利的侵犯,因为此在的亲证是通过个性来体现的。更严重的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只能造就一个毫无生机的沉闷的社会,这个道理就像“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一样简单。
而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来说,关注个性、发展个性对于中华民族的腾飞意义重大。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对人的个性重视不够,也可以说是抹杀个性。而没有了个性的内在支撑,这种“人”其实也就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人”。所以,处在转型期并以人的转型为重大使命的中国教育能否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取决于我们对人之个性的发展和解放程度。价值论正是从价值本位的高度上捍卫人之个性的不可侵犯性。因此,认识到“人是价值的存在”对于我们发展人的个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因为,发展个性就是对人的尊重。一言以蔽之,价值论就是把人的因循于人的存在本身而具有的差异性,以价值立法的形式来加以保证,从而使得本身就丰富多彩的个性变得更加绚丽多姿。
第三,创造性。
创造性实际上是对以上两点的延伸,这种延伸具有实质意义。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10]人的自由本质必然要落实为人的创造性。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不同。自然存在物只能消极被动地服从物种的规定而不能自由超越自身去选择另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而人不同。人是实物与应然的统一。其中“实然”归根到底是作为一个被否定的环节而内在于“应然”的。这其实也就是辩证法所说的:肯定是为了否定。换言之,正是人的自由本质使人永不满足于已有的实然状态,不断向着一种更高层次的应然、未然状态迈进。这种迈进本身就是创造。这种创造的意义就在于人可以凭籍其创造性的活动打破肉体自身的束缚,使自己生命的存在获得开放的、应然的性质,从而不断展现、充实自己的自由本质。由此,人也就彻底摆脱了自然存在物的那种封闭、既成、宿命的存在方式而获得了人的创造内涵。可见,正是创造性使人具有不可还原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创造性成为人之价值的源泉。价值论就是把这一点明确化,指出创造性之于人的价值本体意义。换言之,创造性在完整人性中占据核心位置,它揭示了“人的存在是怎样使存在本身成为有意义的”[11]。而一旦放弃了对人具有本体意义的创造性,也就意味着把自己沦落为“物”而自动放弃了“人”的资格和身份。
传统教育对创造性的认识根本达不到上述高度,它充其量只是从一种工具层面去理解创造性,因而它所推行的那一套“复制型”模式无助于从根本上激发、培养人的创造性。尽管它的创造性,无非是在“物性”的范围内给你一点灵活性罢了。因此,只要还局限于这种立场,我们就永远无法从价值本体的高度去理解创造性之于人的实质意义。
巴西学者弗莱雷对此有深刻认识。他认为传统教育类似于“银行储蓄”,也就是说,教育成了一种储蓄行动,而不是一种创造活动——学生是储蓄所,教师则是储蓄者。教师在学生那里储蓄越多,就越是个好教师;学生接受储蓄的能力越大,就越是个好学生。在传统教育中,学生是完全被动的一个受体。他可能是一个性能优越的“录音机”,一个一丝不苟的重复者,但却决不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物化”状态,一种地道的技术——生产取向。在这种状态中处久了,人的心灵也就麻木了,缺乏一种出自生命的创造敏感,当然也就不会自己思考、自己选择、自己走路了。当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时,在所谓的“思”首先是指“怀疑”精神,有怀疑才有创造,有怀疑、有创造才能确证“我”的存在。可见,创造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相关着人的存在与否。“人是价值的存在”就是以价值立法的形式确证、捍卫人之创造性的不可或缺性。
所以,我们不能把创造性仅仅理解为一种强国富民的手段,亦即仅仅理解为一种能动的生产力因素。创造性的确包括上述内涵,但仅仅局限于此,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工业模式,把人蜕变为“人力”。毋宁说,价值本体意义上的创造性是对人之存在的价值确证,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也深远得多。而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对自己丰满人性的创造,对自己独特个性的创造,对可能生活的创造。一言以蔽之,我们应当立足于价值本体的高度去把握人之创造性。
在创造性问题上另一个容易引起争端的焦点是对道德规范的理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道德”理解为一种对规范的服从和适应。笔者无意反对规范,相反,有些规范是极有必要的。但这些并不是“道德”的核心所在。道德的领域是自由的领域,创造的领域,选择的领域。一旦将这些核心内涵排除,道德也就只能处于一种外在的他律层面。而丧失了自律层面的内在支撑,道德也就必然走向虚无和毁灭。因为这种道德里已经不再有自主和创造。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否认规范,而在于如何完整地理解道德。完整的道德不仅指服从和适应特定社会所认可的习俗或规范的行为,而且更指在面临各种不同规范和行为时所做出的选择行动和创造行动。由此,单纯讲规范是没有道德意义的,它能够造就出“规范人”,却培养不出生活者和创造者。康德之所以以“自由”为基石建构其道德学说,正是深刻地看到了“法由己出”的创造内涵。没有这一点,道德大厦必然崩溃。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自主、创造的层面上来把握道德、把握道德教育。也只有这样,道德才能成为人对自己主体地位的一种确证和践履,才能成为一种自我尊重。在此意义上,教育或道德教育决不是告诉人们去过哪一种标准的生活,而是向人们揭示了人们本来可以拥有哪一些美好的生活,从而有可能在将来不完全一样地重复过去、模仿过去,而是成为一种新生活的开拓者、创造者。
我们以为,从价值的角度对人之创造性加以立法保障,有助于我们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痼疾:对创造性的忽视。传统文化在漠视个性的同时也在泯灭着创造性。所以我们更多的是重复行为、从众行为,鲜有极具个性色彩的创造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局面的一个根本原因。
以上我们对“人性化”、“个性化”和“创造性”三个方面的强调,其实也反映了人们对一种民主教育的渴求,因为,“如果学习者被引导上自我教育的途径,简言之,如果学习者从学习对象变成了学习主体,教育的民主化才是可能的。当教育采取了自由探索、征服环境和创造事物的方式时,它就更加民主化了;而不是像往常一样是一种给予或灌输、一项礼物或一种强制的东西了。”[12]这当然也是“人是价值的存在”所具有的内涵之一。
收稿日期:2001—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