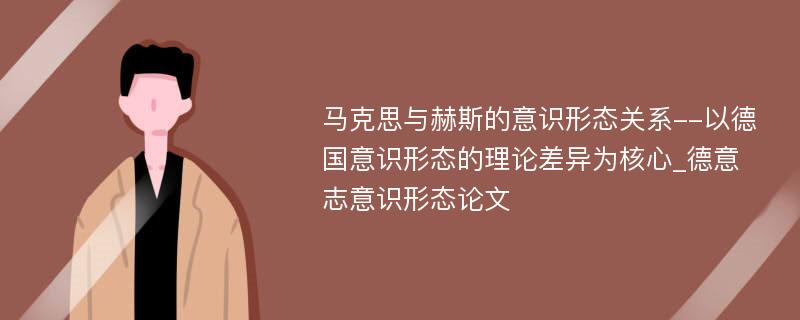
马克思和赫斯的思想关系——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分歧为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斯论文,德意志论文,马克思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分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40年代初,莫泽斯·赫斯的一些著作对马克思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把赫斯的《行动的哲学》等三篇论文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看作“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就这些方面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赫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引路人的意义。1845年11月以前,赫斯与马克思在很多事情上形成了伙伴关系;但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赫斯从“合作伙伴”变为“批判对象”,这种关系的改观微妙且复杂。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 作为“引路人”的赫斯 国内外对于赫斯思想的研究已经很多,绝大多数学者用“引路人”、“大前辈”、“先锋”等称谓来肯定赫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影响,这里有必要简单加以回顾。赫斯1812年生于波恩,比马克思大6岁,他自学了卢梭、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斯宾诺莎的哲学,并称自己为“斯宾诺莎的弟子”。赫斯较早登上德国哲学的理论舞台,他至少在四个方面影响甚至引领了马克思:一是走向共产主义;二是接受并运用费尔巴哈的哲学;三是超越费尔巴哈;四是运用古典经济学。 在1837年发表的处女作《人类的圣史》中,赫斯表达了自己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初步思考、对现代社会症结的本质透视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展望。他认为,人类最初是“原始公有”的状态,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不平等是“私有制”与“继承权”出现的结果,社会的不平等在现代社会中达到了顶峰。革命必然发生,但这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革命将通过废除私有制和继承权,铲除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恢复平等与和谐”①。可以说,赫斯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最早走向共产主义的哲学家。他第一次将黑格尔哲学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也是赫斯引领马克思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的哲学论证走向共产主义。 1841年,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不久,赫斯写了《德国哲学的现代危机》一文,发表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机关报《雅典神殿》上,其中就显露了费尔巴哈对他的影响。1842年2月,费尔巴哈发表了《论对〈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评判》一文,澄清了鲍威尔等人的误解,同时也阐明了自己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这两篇文章使马克思转变了对费尔巴哈的态度,并及时与鲍威尔决裂,终止了写作《末日的宣告》第二部的计划。赫斯在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赫斯于1842年5月在《莱茵报》上发表的《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集权问题》一文,表明了赫斯开始接纳费尔巴哈的哲学并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的生活”②;发表在《二十一印张》上的文章表明,赫斯在积极推进费尔巴哈的哲学,他又将人的“类本质”理解为“自由活动”;赫斯还进一步区分了“理论的类本质”和“实践的类本质”,前者是“自我意识”,后者是“自我行动”;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通过交换、交往和协作表现出来,因此也就是人的“现实本质”。赫斯的这些观点使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引导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马克思这时同样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 但是,赫斯的认识水平在1844年不断提高。他认为,包括卢格、费尔巴哈和鲍威尔在内的哲学家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们没有处理好哲学思辨与德国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马克思写道:“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③。这里的“几篇文章”指是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三篇文章。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中,赫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质规定为自由和平等的统一。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已经开始借助费尔巴哈的哲学展开对社会生活的经济分析,他曾感叹“费尔巴哈是德国的蒲鲁东”。赫斯同时认为,费尔巴哈未能介入实际生活过程,因此要求“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赫斯认为,“自我意识”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青年黑格尔派则是“今日的实践哲学”,正在向“行动哲学”过渡,精神哲学的任务在于成为行动的哲学,这个观点也影响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可以说,无论是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还是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羁绊,都是赫斯在前,马克思在后。 赫斯的理论创造在1844年《论货币的本质》中达到一个高峰,从中可以看出赫斯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它对马克思的启发也是最大的。与恩格斯一样,赫斯的这部著作为马克思提供了经济学的背景支援,是马克思将异化论用于分析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直接诱因或中介。在赫斯看来,货币在当时不是“贵金属”,因为在现实中人们使用的纸币、债券、银行券已经远远多于贵金属。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凡是不能交换、不能出卖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货币使人可以买卖,也使人有了价值,自由的人比奴隶更有价值,所以货币成了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是彼此异化的人的产物。《论货币的本质》是赫斯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是1843年末或者1844年初赫斯为《德法年鉴》而写的。赫斯写好后就将手稿交给了《德法年鉴》编辑部,但由于《德法年鉴》停刊,直到一年以后这篇文章才在《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中发表出来。马克思应该知道并阅读了赫斯的这篇文章,马克思本人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赫斯的这篇文章虽然在表述形式上有所区别,但核心观点惊人地相似。麦克莱伦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在写自己的文章以前谅必读过赫斯的大部分文章”,马克思“估计赫斯的论文不会发表因而作了大量抄录”,“毫无疑义,马克思在他的思想发展上开始把经济领域作为直接对象这个转变关头,从赫斯那里吸取了所有重要的论点”④。姑且不论赫斯对《论犹太人问题》的影响,他通过“货币”引申出的经济学背景的确是被马克思采纳了。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关头充满了困惑,他不得不求助黑格尔哲学去重新理解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从而开拓了与赫斯不同的理论路径。 在1845年1月《最后的哲学家》一文中,赫斯终于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并将费尔巴哈的“类”称为“哲学的妄想”,他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把只是作为类本质才属于人的东西,即自主的或绝对自由的生活活动归于作为单个个体的人,“人们陷入的分离状态,在实践上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即人们紧密团结,在共同体中生活,在其中劳动,并通过扬弃私人所得,才能够得到扬弃”⑤。因此,赫斯在1845年达到的思想高度有资格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这一合作的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 作为“合作伙伴”的赫斯 赫斯与马克思的合作并非一朝一夕。实际上,1841年在《雅典神殿》上发表了《德国哲学的现代危机》一文以后,赫斯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并结识了马克思,并给予马克思很高的评价。马克思与赫斯的合作是从《莱茵报》时期开始的。1842-1843年间,赫斯作为《莱茵报》的创立者之一和通讯员为该报撰写了近百篇政论文章。马克思针对赫斯的《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集权问题》写作了《集权问题》,但未能最终完稿。同马克思批判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样,赫斯也尖锐地批判了这个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制度。马克思和赫斯都在《莱茵报》时期的文章中批判了鲍威尔为首的柏林“自由人”组织。赫斯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援引马克思在《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中的论述,与马克思在理论上遥相呼应。 《莱茵报》被查封以后,1843年5月,卢格、赫斯与马克思商定创办《德法年鉴》。赫斯致力于研究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论货币的本质》就是赫斯给《德法年鉴》的投稿。马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不但高度赞扬了赫斯,还在手稿中写下“关于拥有这个范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⑥。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再到巴黎时期,马克思与赫斯的合作是实质性的。也可以说,二人的思想是相互影响的。如果说赫斯通过“共同体”思想引领马克思接受并超越费尔巴哈的“类”哲学,那么,赫斯也从马克思那里学习并提高了经济学的研究水平。1846年夏,赫斯给马克思写信,并表示自己在经济学方面是马克思的“弟子”。 1845年1月17日,赫斯给马克思写信,向马克思介绍了《最后的哲学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新见解,说明二人能够就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毫无保留地展开讨论。从恩格斯1845年2月22日至3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与赫斯的接触较为密切,二人协力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争。赫斯对宣传共产主义不遗余力,功不可没;恩格斯完全同意并支持赫斯的看法,即英国将率先爆发社会革命,他还以自己和赫斯的名义请求马克思给《莱茵社会改革年鉴》投稿。但这也不意味着三人之间毫无理论分歧。恩格斯认为,“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看来他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荒唐思想”,恩格斯指的是,赫斯将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归结为范畴,他不能理解“现实的个人”作为理论出发点和基础的重要性。恩格斯还说,等赫斯到达布鲁塞尔后,“你可以亲自同他谈谈这个问题”⑦。1845年下半年,赫斯也住在布鲁塞尔,与恩格斯一样,赫斯同样对马克思有着重要的影响。按照他们的研究习惯,赫斯应该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谈到自己的文章及观点,并和马克思、恩格斯交换意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与赫斯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1845年10月底在莱比锡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鲍威尔和施蒂纳分别撰文批评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用“莱比锡宗教会议”讽喻“两位圣者”的“控诉”,并与赫斯处于同一理论阵线上⑧。赫斯在自己的论著中不时提到和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并把二人的著作联系起来。马克思对此也表示认可。在批判施蒂纳的“圣麦克斯”章中,马克思援引赫斯在《晚近的哲学家》中的观点,强调思辨和现实的关系,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⑨。马克思还为赫斯在《晚近的哲学家》中对施蒂纳的批判进行了直接的辩护,回击了施蒂纳对赫斯的诘难⑩。 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合作也是实质性的,他们共同制定了最初的写作大纲,赫斯也执笔写作部分章节。赫斯的很多思想融入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题,除思辨和现实的关系以及共同体思想之外,通过货币对生产力概念的创造性理解也影响了马克思。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写道:“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货币应该是一般的交换手段,因而是生活的中介物,是人的能力,是现实的生产力,是人类的现实的财富。如果这种外化的财富在现实上同内在的财富相适应,那么每个人的价值就恰好等于他所拥有的现金或占有的货币价值——正如彻底的神学只能根据人的信奉正教的程度来评价人,彻底的经济学只能根据人的钱袋的重量来评价人。但是,实际上,经济学同神学一样,关心的根本不是人。”(11)赫斯进一步指出,货币被称为人的生产力。很明显,赫斯所理解的生产力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含义是一致的,即生产出财富数量的多少。赫斯认为,个人的真正本质在于他们的产品交换、贸易和协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强大;如果交往范围狭小,他们的生产力也就低下。赫斯明确指出:“只有这种共同活动才能实现生产力(Productionskrafe)”(12),因为单个的和孤立的人还没有联合起来,联合起来的共同生活才是人的生活,才是共产主义。将生产力规定为“共同活动”是赫斯的创见,这一理解甚至被马克思沿用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界定生产力概念的哲学内涵,而且马克思在恩格斯笔迹上特意加写了一句话:“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3)。可见,赫斯的观点与马克思有着相当的一致性,那么,问题也随即产生,他后来是如何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对象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译第1版第3卷有这样的注释:“第2卷第5章是魏德迈手抄的,在最后标有莫·赫斯的记号。”所以,考释者并不确定地说:“大概这一章是赫斯起草的,魏德迈抄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校订的”(14)。这一事实表明,不能将赫斯简单地归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第1卷第2章“圣布鲁诺”的第4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拟定的标题是“与‘莫·赫斯’的诀别”,并在提到赫斯时加的一个括号中写道:“对于他的著述,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不负任何责任”(1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格律恩时指出,格律恩的观点几乎都是从赫斯那里抄来的:“格律恩先生总是以最冠冕堂皇的手法来转述赫斯”,并“十分忠实地抄录了赫斯明显的错误”(16)。鉴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有关论述,有学者指出赫斯参加一本对他自己进行激烈批判的著作的写作是自相矛盾和不可想象的;还有学者认为,赫斯当时参与了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工作,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已让他参与了部分章节的写作。但是马克思与赫斯真正的理论分歧是什么?从合作伙伴忽然变为批判对象的关键是什么呢?截至目前,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第2版第1部分第4、5卷还没有出版,国内外学者对此尚无一致的观点,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发展过程还没有最后澄清。这个思想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其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都没有最终确定,因此,没能成功地建构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有机整体。 三 作为“批判对象”的赫斯 赫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生动写照,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却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对象,因此马克思和赫斯的理论分歧从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行文中可见一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文本表明,马克思与赫斯的“实践”哲学,与所谓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与他本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范式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在此,笔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为依据说明一点:即放弃人的本质和异化学说,转向生产力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格律恩先生装备有对德国哲学如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些结果的坚定信念,即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宗教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和万物的尺度;格律恩先生还装备有德国社会主义(见上文)的其他真理,如货币、雇佣劳动等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德国社会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实现,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真理等等。格律恩先生既装备有这一切,于是就带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自满情绪到布鲁塞尔和巴黎去了”(17)。 广松涉认为,这里的命题都曾经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那两篇论文中的思想,而现在却已经成为马克思“嘲笑的对象”(18)。从马克思行文的逻辑上看,这里所说的格律恩所装备的“德国社会主义”指的是赫斯,这段话也是马克思对人本主义哲学范式的批判性反思。所谓赫斯的“明显的错误”是高估了“实践哲学”的解释力。在赫斯看来,理论体系构成实践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似乎只要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与“实践”结合起来,将费尔巴哈的学说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批判,因此,赫斯要做的“只是到处寻找‘人’和‘人的’这个词”(19),并把个人之间的关系看作“人”的关系。同时,海尔曼·泽米希曾肯定地说,费尔巴哈“消灭了宗教的幻想”,赫斯“摧毁了政治的幻想”(20),这或许是赫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重要推进,使宗教批判扩展到政治和社会批判。但是,赫斯的政治和社会批判更具道德规范化的色彩。赫斯主张哲学必须从思辨的高处下降到现实生活中,并朝向实践行为发展。然而费解的是:赫斯没有将实践行为推进到物质生活领域并深入挖掘,而是将这种对象性的活动引向自身的精神生活回归,从而与费希特的“自我”形成了共鸣关系,最终回归到德国思辨哲学的框架内。赫斯回到费希特,没能认真地清理黑格尔的辩证法,没能理解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及其价值,因而也就无法认清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他在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全盘否定了黑格尔,从而走向马克思的反面。赫斯认为,黑格尔以观念中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为基础,演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这未能实质性解决思辨和现实的关系。赫斯看重的是费希特思辨的历史观以及费尔巴哈式的直观把握,并认为真正的统一在于行动或实践,他积极地用行动哲学补充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但如马克思所说,赫斯将“人”和“人的本质”当作万物的尺度、当作历史的最终目的,这是典型的人本主义哲学范式,不可能真正揭示历史的奥秘。 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关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必须吸收隐藏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对劳动的辩证批判,而且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上,将劳动的异化和私有财产的形成与扬弃放在历史的辩证运动中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一点赫斯是做不到的。那么,通过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并发现历史冲突的根源是马克思的理论创见,赫斯则不能具体地解开历史的生成和演进之谜,不能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力,也不能洞察经济生活的神秘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古典经济学中脱胎换骨的“生产力”才是唯物史观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概念,它是“现实的个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缩影。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冲突的根源表述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就意味着与人本主义哲学范式挥手道别。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不再是理解历史的出发点,相反,它需要通过生产力得到合理的说明,因而,马克思将解析历史的逻辑起点置换为考察现实的个人在各个历史时代的生产力状况。换句话说,不能依据人的概念或人的本质来推论历史发展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而应该去解析“现实的个人”改变自己现实生活的过程亦即生产力生成的过程。历史最终由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来阐明。反之,在赫斯那里,生产力和交往的对应关系,虽然接近唯物史观的核心表述,但赫斯不是作为根本性的和物质性的要素来把握。赫斯几乎洞察到交往和协作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系,但他没有将生产力概念运用到对现实和历史的分析之中,也没有将具体样态的分工理解为生产力,更无法把握基于分工并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改造。赫斯还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理解为消除货币得以存在的社会关系的条件。 可以说,马克思和赫斯都致力于解决德国哲学抽象思辨和脱离现实的弊病。马克思通过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生产力切入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分析发现了历史的根本动力,进而建构了唯物史观,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论证了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赫斯则停留在道德控诉的情境中,他最终坚持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于是和马克思分道扬镳,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47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赫斯“不再有往日的严肃”,表现得“惊人的谦虚”,以及“一度震撼世界的、不可一世的赫斯的那副遭强暴的神情,几乎使我怒气顿消”(21)。可见,马克思与赫斯的理论分歧以赫斯的失败收场。赫斯的后半生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渐行渐远。 恩格斯以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径奠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是通过重新发挥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来重构马克思的哲学。利用“青年黑格尔派”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研究框架,它使我们得以微观地透视唯物史观的成立过程。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依次经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三种批判潮流:一是以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宗教批判;二是以卢格为代表的法哲学批判;三是以切什考夫斯基、赫斯为代表的行动哲学批判。因而,赫斯的思想较鲍威尔、费尔巴哈和卢格更接近唯物史观,马克思超越赫斯的思想历程十分紧密地与新世界观诞生的历程“重合”在一起。 注释: ①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刘丕坤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255页。 ②⑤(11)(12)《赫斯精粹》,邓习议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8页;第184页;第146页;第139页。 ③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12页;第190页。 ④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陈启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63-16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5页。 ⑧⑨⑩(14)(15)(16)(17)(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90页;第261-262页;第293、486页;第716页;第113页;第580页;第576页;第581页;第552页。 (13)(18)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6页;第37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53页。标签: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德国生活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论犹太人问题论文; 基督教共产主义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