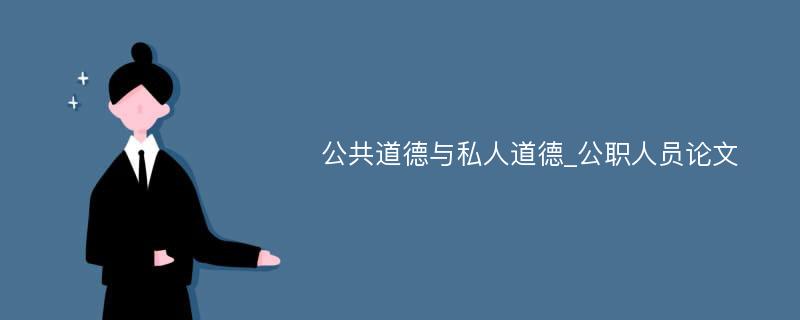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私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常识:同一个人或两个不同的人,在他(们)承担某种公职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与其以私人身份行事时应当履行的伦理规则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特定时空内甚至是相互冲突或相互悖反的;但也并非完全不同,二者在一些普遍性和深层次的内容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其最质朴的一种表达是“公职人员也是人”。这是一个不容辩驳的直觉,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道德观点。作为一种直觉,除了诉诸神灵启示、常识或内心的感觉以外,我们能说的不多;但作为一种“道德的观点”,它则“必须用道德论据来进行批判或维护”。(注: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以下我们先就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殊分历史作简要的梳理,然后再切入当下话题。
一、一般历史的追溯
在古希腊、英雄时代和传统中国,人也具有多种社会角色,但是各种角色规范之间不存在不可通约的矛盾,因为存在着某种总体性生活秩序、礼仪秩序。这种秩序的一般表达式是:个人从属于集体、私人伦理从属于公共伦理、低级规范从属于高级规范。在古代中国,家法从属于宗法、宗法从属于国法(国法从属于天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一脉相成。在古代西方,个人在社会整体或城邦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了他的生活全部规范,社会道德和社会结构事实上是同一回事情。与社会结构性质不同的道德是不存在的,评价问题就是社会事实问题。每个人都既对自身的角色地位规范有明确的认识,知道处于自己所在位置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与此角色有关联的人应承担什么责任。这种责任既是固定的、明确无误的,又是特定的:正是为了特定的关联对象,我必须做我应当做的。处于特定社会节点上的个体自我并不希望把自己普遍化。当然,处于某一角色的个体除了知道自己对他人负责有的责任或义务之外,也清楚他人是否对自己有义务以及有什么义务。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如果不能履行这些义务,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人,应受到何种对待与处置(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十章。)。尽管这些描述摘自麦金太尔对英雄时代德性状况的描述。但它们同样也适用于古希腊城邦乃至中世纪的情况(注:可参见《德性之后》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那么,人的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分裂与冲突始于何时何事呢?基于传统与现代在观念上的习惯性对立,人们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开启现代化之门的启蒙运动(精神上)和产业革命(物质上)。因此,正是由于启蒙运动催产了“现代人”,使他们从诸如出身、身份和等级等种种封建的社会桎梏和中世纪的神学统治的压迫中得以解放出来,使个体理性与个体道德得以高扬;正是产业革命使人类劳动生产力飞速增进,迅速摆脱“必然王国”的奴役,因此,连马克思也不得不肯定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贡献。从进化论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时代的必然。但是,在麦金太尔看来,正是由于这一双重解脱,使现代人成了没有任何社会规定性的自我。在理论上,它导致了情感主义的盛行和道德争论的“没完没了”、“无终止性”,道德理论的“无公度性”。最终的结局是相对主义的甚嚣尘上;在实践上,则酿成了当代社会严重的道德失范与道德危机。(注:《德性之后》,第二章。)因此,这种不具有任何必然社会内容和必然社会身份的民主化的自我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像欧文·戈夫曼所说的,自我不过是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一个“衣架”;(注: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见《德性之后》,第253页。)要么是三、四十年代的萨特所倡言的那种与其可能扮演的任何社会角色都截然不同的“自我设计”的自我,或者是自由主义者的“原子式的”(atomic)个体模式。在前一种观念中,自我只是一个毫无实质性意义与内容的心理衣架,是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一个纯功能性部件,是现代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可以被复制、被取代的不具任何个体特殊性的一道程序而已。因此,当在角色扮演之上或之外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自我时,就会出现个体价值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与此相反,在后一派观点看来,错误正好源自前一种立场本身,即将自我等同于他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这两类观点表面看起来正好相反,但是,实质上二者有着某种深层的一致性:如同前者认为社会就是一切、自我什么都不是一样,后者实际上也认为自我无论占据何种社会地位,都是偶然为之。因此,他们都看不到自我的任何实在性;(注:《德性之后》,第43页。)真正的自我永远处于与他我社会的对立面,互为客体、互为工具。相对于私人领域的从业者而言,这种对立在公共职业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辩明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关系,分析公共职业人所面临的种种价值困境并试图为之提供某种理论性的指导和证明,就成了公共伦理学研究的一项核心内容。
尽管把现代个体与社会冲突之源归结于启蒙以降的现代化(性)算不上错,但是,首先使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分离的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瓦解理性与道德、理性与信仰、教会与国家之间在观念上的一致性的也是这场改革。路德和加尔文等人几乎完全抛弃了托马斯·阿奎那关于自然与超自然、理性与道德合而为一的思想,认为人的理性与意志已经过于堕落,因此无法相信它们能识别或遵守自然法。他们一方面相信在基督教社会里,信奉圣灵的启示与指导的个体是有道德的;另一方面,他们相信在公共的、社会的环境(如国家)中,必须用法律、威胁、惩罚的约束力来抑制人的罪恶。由于这些观点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逐渐形成了两套道德体系:教会以内的道德(基督徒的道德观)与教会以外的道德(公共道德观)。就这样,“在新教社会思想之上牢固地树立起了一种二元论,这种二元论随着其含义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掏空了宗教的社会内容,掏空了社会的灵魂。”(注: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纽约:哈考特,1972年版,第90页。)依据这种二元道德论,一个人攻击另外一个人也许是错误的,但同样的戒律不能适用于国家为保卫其领土或法律而采取的行动。在道德领域里,应该将一个公职担任者的公职行为与其作为私人个体的活动区分开来。譬如一个统治者,必须因其谋害妻子而受到上帝的严厉惩罚;但他绞死某个盗窃犯则被认为合乎公共道德的需要。因此,R.T.诺兰认为“宗教改革家的道德假设所造成的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后果,也许是他们区分了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注:R.T.诺兰:《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姚新中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这种区分模式一直沿用到现在。
然而,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将政治与道德、更准确地说是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截然分离,并试图彻底剔除国家生活中的道德考虑从而将政治处事逻辑建立在以成败论英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恶人”,不是宗教改革者,而是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巨人之一的尼科诺·马基雅维利。他认为一个优良的统治者“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注:尼科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3页。)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显然,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公共生活中没什么事(包括一切德行与恶行、仁政与暴政)必为或必不为,一切都应视情势而定,为与不为的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增长,是否有利于避免“大恶”。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脏手”论。
二、公私道德的分殊
在对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关系历史理论与实践进行上述梳理之后,让我们在当下语境中,就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关系以及公职人员的价值选择问题作进一步的阐释。
相对于社会权利而言,公职所赋予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公共权力(譬如一名普通警察、征税员的权力),也是硕大无比的。这无论是从公共权力的适用规模,还是从它的强制性,以及由此对公民权益造成的可能侵害的深度与广度来说,都是如此。按照常理,某行为能力(注:按照关于权利和权力的标准定义,二者都可以视为某种行为能力。)对他人权益的威胁性越大,它所受到的各种约束也应该越大。就是说,公共权力所受的约束应该远远大于对个体私人权利的约束。撇开其他形式的约束不谈,这里仅讨论道德约束。
理虽如此,现实却不尽然。留意当今社会,我们发现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一方面经常借公共职业道德规避私人道德的约束,使自己处于一种“道德屏障状态”;另一方面,又常常借私人道德规避公共道德,徇私舞弊。所谓道德屏障状态指的是,公职人员将自己视为政府的代表、某组织机构的职员、某异于私人活动的公共职责的履行者,其行为只是履行公事、执行命令而已,因此,作为个体,他们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受“任何人都应对其行为负责”这个一般规则的约束。假如其公职行为确实构成了公务犯罪,他们既不应承担法律责任,也不应当受到道德谴责。比如许多纳粹战犯就是这样规避良心和道德谴责的。更为奇怪的是,不仅官员或公务员们自己认为如此,很多旁观者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尽管有1972年的圣诞轰炸以及此前的凡此种种,基辛格还是一位享誉全球的人物;也无人去追究埃利奥特·理查森任尼克松政府的国防部长时,在越南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对柬埔塞进行完全非法轰炸所犯下的罪行,人们记住的是他后来任司法部长时,在水门事件中表现出的刚正不阿。至于公职人员有意无意地混淆私人道德与职业伦理,以私代公、情凌驾于法之类的事情,可谓司空见惯、无处不有,已经成了常态的反常现象。难怪麦金太尔说当代社会是一个道德权威陨落、情感主义盛行、充满道德危机的社会。
由上引发的疑问是,私人道德是否适用于公职人员?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一致性?是否可以由私人道德直接引出公共道德?如果说二者之间存在差异性,那么,二者有什么不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只要公职没有占据其承担者生活的全部,那么他就受到公私两种不同道德伦理约束,尤其是当这二者相互冲突时,他该当如何取舍呢?
内格尔不无深刻地指出:“权力的行使,不论在什么职位上,都是个体自我表现的最个人化的形式之一,是纯粹个人快感的一个丰富源泉。……不管是否有意识地喜欢,行使权力都是一种基本的个体表现形式,作为它基础的机构或公职不是消除而是增强了这种表现。”因此,“在执行公务时犯下的公务罪的人可能和私人犯罪一样有罪。”(注:《人的问题》,第84、98页。)就是说,即使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以及不道德的行为是履行其职责或职务的结果,也不能以公职为理由,否认道德约束在公共生活中的适用性;即使国家法律不追究公职人员的过错,他们也不能规避道德良心的谴责。当然,这并不是说,私人道德可以直接适用于公共生活。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确实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我们大致可以将道德观的内容都归为两项:对行为本身的关注和对行为结果的关注。以行为为中心的道德观的特点是,重视行为程序,禁止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对待他人,即禁止侵犯他人的权利和每个人的私生活空间,要求行为本身的诸方面能经得起合理性论证。相反,以结果为中心的道德观的核心关注点是行为的效果,总是从促成最好的结果的角度去规定人们为此能做的一切。众所周知,道德观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冲突的,在特定的时空中达成某种比例性的适恰。在现代的私人生活领域,我们奉行的是约翰·密尔的自由规则,即每个人在不侵害他人的权利范围的条件下,他的任何活动都是自由的、自主的,其他人无权干涉,即使是出于某种善良的目的。
但是,当我们转而关注公共机构及其公职人员的活动时,肯定不会坚持同样的规则。原因很简单,公共机构也好,公职人员也好,他们行动的正当性权利和目标都是外在性的、异己的,追求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另外,完整的公共行为是通过各部门、各人员分工协作达成的,其行为道德正当性的充分实现也需各方面各有侧重地分工配合。因此,对于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来说,公共道德的上述两个方面的比例结构,表现出非个人化的特征,而且,对于不同的部门及其公职人员也会有所不同。
就对行为本身的关注而言,首先,公共行为往往受到严格的法制程序的约束,以确保公共机构与公职人员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公民,防止公职人员的“寻租”。同时,这也使得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一定程度上的“冷酷无情”和刻板表现,具有某种道德上的必要性:公共官员或机构与他们所要对待的私人个体相比,没有类似的自我放纵或偏袒的权利。其次,在手段上,公职的履行者被允许依法使用强制性的办法。这些办法是不允许个体使用的。譬如,税务人员有权依法(强制性)征税,但若某私人个体也行此举,则犯了抢劫或敲诈勒索罪。第三,公共事务虽然也遵循个体生活的“密尔原则”,不过它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在它们与其国民的关系上:国家在外部争端中可以保持中立,并且可以合理地偏袒自己的人民,虽然不能以世界其他地方的无论多大的牺牲为代价。
行为效果在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的价值谱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现代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主要支柱是其政绩。对于某特定的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来说,也无不如此。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功绩主义”在世界各国的普遍盛行之中。依照现行的职位分类制度,任何机构、任何职位以及据此安排的任何一个人员,其合理性依据都在于它(他)所履行的职责或工作任务。因此,努力推进这些结果的实现、达成其职能目标,既是其法律责任,也是其职业道德的要求。于是,在适度的范围内,公共决策可能有理由比私人决策更加注重效果。当然,效果论者的价值观未必就是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要求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除了要尊重个体的生命、健康、财产和私人生活的正当权益以外,还必须确保其制度、活动以及决策的公正、平等。因而,在对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的道德评估和合理性论证中,效果论的考虑以及公正无私有着特殊的意义。根据效果论的理由,公共机构在其法定权限内,有权就某些事情相对自主地做出决策,而无须事事征得选民或纳税人的同意,尤其是那些出于整体利益的需要必须予以强制执行的事情。譬如征兵和纳税就是如此。当然,为了防止这种相对自主权的行使成为决策者的主观武断,或成为某些人牟取个人利益的道德幌子,必须通过其他途径来确保其道德正当性。譬如,听证程序、定期回答选民的质询、司法救济等办法。
如果公共机构在遵守必要的程序规定、对行为本身给予必要的关注的条件下,总体上表现为倾向于关注结果,那么,要减少这种价值取向的道德风险,就必须存在一些“异类”的部门:它们的职责分工主要是关注行为本身,他们的公共道德是以行为为中心的。司法部门就是这类部门的典型。对此,恕不赘言。
三、分殊与关联的辩驳
关于公共道德的独特性的论证,我们现在最常用、最熟悉的理由是“义务论”。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谁,只要他担任某特定公职,就必须履行某特定职能和常常是为某特定组织与利益集团服务的义务。因此,有些行为,譬如撒谎、偷窃、欺骗和杀戮等,在私人道德领域视为罪恶的行为,当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为时,譬如战争、执行法律等,会被(某政治共同体)认为是一种义务、荣誉甚至被奉为英雄。(注:Dwight Waldo:"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Ethics:A Prologue to aPreface".In Richard J.Stillman Ⅱ Public Administration:concept and cases,p502-511.Boston,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由本文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出,这种论证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但是,这种论证有一个前提假设,即存在“正当的”具体处境。许多义务都是有其道德背景的;离开这一条件,对某项义务的履行就可能是不道德的。从道德上讲,下属成员没有义务履行上级领导或组织的病态的或反人道主义的命令。进一步讲,任何公职人员在执行命令、履行职责时,都必须接受其道德良心的监督,都不能也不应该放弃其道德自主性能力的行使。所以,我们并不认为,公共道德与人类普遍的道德伦理是相悖的。而且,义务论也不为这种观点提供支持:在公共生活中,目的可以使手段合理化,或者说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破坏性的手段必然会改变目的的性质”。(注:E·弗洛姆:《人性的追求》,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现实中,常常有人过分强调目的而不充分探讨手段的作用。这会导致一种变态的目的—手段关系:使目的抽象化,脱离其具体的处境,最终成为一种空想,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于现场之外;使手段与目的脱离,手段篡夺目的的作用。
汉普希尔对于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讨论。(注:Stuart Hampshire."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In Stuart Hampshire.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他是从道德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解说这一难题的。公德—私德问题源自传统的道德—政治问题。如前所述,这一问题被马基雅维利永久地标题化了。汉普希尔赞成马基雅维利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加以区分,但是很不赞成马基雅维利将私人道德从公共生活中祛除出去。于是,他实际上提出了同上所述的一种主张,我们姑且称此为公德与私德的有限分离论。汉普希尔的视角是新鲜的。他将人的道德思维分为两类:明示推理(explicit reasoning)和隐晦推理(implicit reasoning)。前者也叫解析推理(illuminat reasoning),其典型是逻辑推理或数学推理。其实质是理性的逻辑化和可公认性表达。这不仅要求从前提到结论要经过一系列逻辑适恰的步骤,而且这种逻辑模式及其前提都必须是他人能够理解和承认的。正是由于明示推理的这种“公共性”,所以它被要求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一种通行的推理方式,显然,这种推理方式不能被强加给私人道德,除非道德主体有意说服他人或有义务向他人明示。典型地体现私人道德观的个体性或隐私性的是隐晦推理。这种推理由直觉支配并瞬间完成,其过程不能展开为一系列清晰的或逻辑计算的步骤,因此又被称为简约推理(condensed reasoning)。在隐晦推理中,人的背景知识起着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潜意识的作用;其中包括一个人在其生活经历中所形成的不计其数的欲望、情感、信念——个体在为其道德选择辩护时往往只能就近列举其中少数几条,好比冰山之一角。尽管汉普希尔为了批判功利主义的“理性计算道德”(rational computational morality)或“抽象计算道德”(abstract computational morality),为了给隐晦推理在现代社会中争取一席之地,而将这种直觉思维看作与逻辑思维具有同等理性思维的做法,有些牵强,并已受到质疑,(注:陈晓平:《评汉普希尔的公德私德观》,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陈先生主张将隐晦推理归类为非理性,从而把公德与私德区别为理性成分与非理性成分所占比例的不同。我认为,这种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倒退——这种修正反而没有了汉普希尔那种划分的灵气。)但是,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公共道德推理的实质性要求: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共生活有时为什么会“不顾”私人生活的道德标准——汉普希尔就是因此而抱怨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注: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p.51)尽管汉普希尔发现了公德与明示推理、私德与隐晦推理之间的联系,但是,他并没有将这种联系绝对化,从而将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两相分立与对立。相反,他认为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在私德中不能完全排除明示推理。私德并不等于任性、我行我素,它也必须具有可感受、可领会性。个体如要说服或使其他人理解他的话,则必须诉诸明示推理。或者如汉普希尔所说的,当一个人面对私人生活的道德时,“尽管他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推理弄得明显化,但他也许出于与公共机构无关的个人原因这样做。他也许想要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出于某种观念上的偏好而‘跳至结论’,即查实一下自己并非主要由于自己相信某一个结论而相信这个结论。”(注:Public and Private Morality.p.35)另一方面,公共道德生活有时也需要隐晦推理。这是因为公职人员往往会遇到多重价值困境,使其道德生活呈现出一定的“悲剧性与悖论性”。这种价值选择往往不是在明显的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之间的选择,恐怕也不是在多种可以序列化的价值之间的“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简单数学活动——像功利主义建议的那样,而首先是指在相互冲突的一个(些)善与另一个(些)善、一种(些)价值与另一种(些)价值之间的选择,譬如对祖国的爱与对近邻的爱,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和民族利益的需要,个体人格的保持与政治理想的实现,对人民的忠诚与对组织甚至是整个政府的忠诚,对法律的服从与对上级领导的服从等等之间就经常发生冲突。汉普希尔称此为“终极冲突”(ultimate conflict)和“终极选择”(ultimate choice)。显然,在当今道德理论多元化的时代,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程式化的话语逻辑是无效的;此时,必须诉诸我们的道德良知和内心信仰,即进行隐晦推理。总之,现时中的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既相区别又有联系。
那么,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历时性关系又加何呢?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很难作出这样的推断,即:公共道德可以由私人道德中推演出来;也很难说公共道德是私人道德适用于公共生活的产物。因为仅当道德约束必须首先用于形成支配个体行为的原则,而不能直接用于公共事务时,公共道德才可能是从私人道德中引申出来的。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有力的论据来支持这一伦理逻辑结构:普遍的道德约束→私人的道德原则→公共道德原则。在当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包含的家国德性同构的观点,已经历史性地失去了其存在环境,公共与私人之间的道德鸿沟更是无法逾越。因此,我个人倾向于赞同内格尔的观点: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都不是终极性的,不是由一方推出另一方;而是享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当它用于生成迥然不同的私人和公共生活环境的行动原则时,便产生各不相同的结果。”(注:《人的问题》,第86页。)首先,公共道德受到一种更具普遍性的伦理规范(注:有些学者譬如德怀特·沃尔多,称此为“高级法”(higher law),它超越于政府与个体之上。Public Administration:concept and cases.p.502-511.)的约束;后者是前者的上位规范。这些普遍性的道德规范源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些基本需要,它们往往表现为人类的本能、情感、欲望、睿智,或以传统习俗的形式表达出来,或出自圣贤之口。“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其次,这种普遍的伦理规范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环境中的具体表达形式,某些方面除了规范对象上的不同以外,其实质内容是一致的。譬如,待人要忠诚老实、工作要勤恳努力、不得损害他人等等,既是对私人个体行为的约束,又同样适用于公共生活。因此,公职义务不能成为免除这些看似私人道德约束的理由。
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的上述辨证关系突出表现在公职人员个体身上,因此,公职人员尤为需要发挥其道德判断能力进行一些比较困难的价值选择。正是通过这种理性自主的道德选择,他才能成为伦理主体,才会对其行为持负责的态度。我们相信每个正常的人都具有这种潜能,所以才要求人们对其行为承担“主观”责任,企图以此促进人们尤其是公职人员的道德理性的发展。
现实中,公职人员经常会遇到一些悲剧性的道德选择情景,这种选择往往是残忍的。譬如,当私人道德伦理与公共职业道德伦理相冲突时,公职人员往往面临诸如“忠孝两难全”之类的选择困境。英国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曾不无感慨地说,“我恨事业这个观念,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作选择的话,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祖国。”尽管福斯特不是一个公职人员,他的选择意向也不符合公共道德,但他却表达了做这种选择时的内心真实感受。尽管笼统地就两种道德观的地位而言,选择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算错,但对于一个公职人员来说,由于义务论的理由——如果某一个体自愿担任了某一公职,就意味着他承认了某些义务、某些限制,以及他所能做的事情的某些限度——他只能选择遵循职业伦理的要求。
公职人员面临的第二类选择困境是,按照职业道德应当执行的命令与人类的普遍伦理规范相违背,譬如,他被命令去进行一起合法的谋杀,或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如遇到这种情形,内格尔提醒公职人员注意,“此时公共道德本身划定的界线正在被逾越。……在这种时候,除了拒绝别无选择,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阻止它。”(注:《人的问题》,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