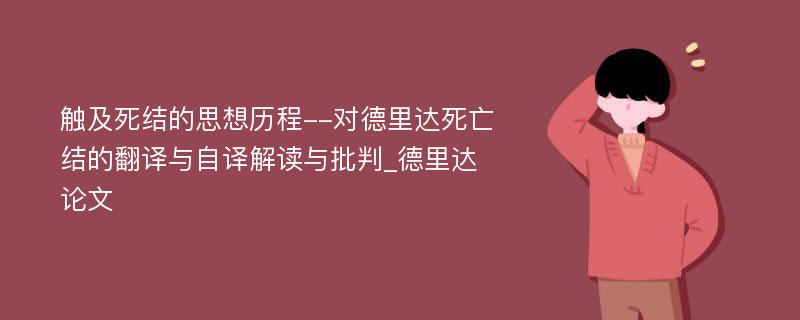
触动死结的思想之旅——《翻译与自我—德里达〈死结〉的翻译学解读与批判》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结论文,之旅论文,自我论文,思想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2-0148-4
从囿于语言层面的研究扩展到文化层面的研究,翻译学研究历经变迁,研究范围不断拓展。但是,和这广阔的天地相对的,是人们仍然有些狭隘的研究思想。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仍脱离不了二元对立的窠臼,非此即彼、不对即错是普遍的观念。从语言层面的研究到文化层面的研究,貌似拓展的研究领域仍摆脱不了狭隘思路的限制。原文—译文是人们永远的归依,忠实对等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在这样的局面下,翻译学研究的创新是很难谈得上的。引入源头活水,让思想的清流为翻译学研究带来生机与活力也就成了迫切的要求。只有引入源头活水,让思想的清流为我们带来生机与活力,翻译学研究才会“清如许”,才会散发出它应有的光彩,才会显现出它应有的活力。蔡新乐的近作《翻译与自我—德里达〈死结〉的翻译学解读与批判》就是这样的尝试。
该书是对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死结》的翻译学研究,是作者把德里达哲学中的某些元素和翻译学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众所周知,德里达这位法国的思想精灵是很“难懂”的。之所以难懂,正如作者所言,原因之一在于他与众不同的理路:既要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又不能不依照逻辑的范式,或“类逻辑”的方式去思考。这种理路无异于戴着脚镣跳舞,是对大多数人的神经的挑战与刺激。而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去解读这位哲学大家的思想,并使之和翻译学研究结合起来更显示出了作者的创新之处。而且,作者对德里达的这部著作的标题“Aporias”的翻译与解读正是对德里达思想精髓的体现。
作者没有把“Aporias”译为通常所见的“难题”或“困境”,而是译为“死结”。对“死结”的翻译与解读,不仅体现了德里达基本的思想走向,而且为读者带来了思想冲击,带来了启迪。因为正如作者所言,“Aporias”不是“境”,也不是“题”,而是“结”,是既定的、不能不予以正视的现象,是不能“结果”的“结”,是无法摆脱因而人人都要为之焦虑的“情结”:既然最终都要走向它,所以,该怎样加以面对,的确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作者在其著作中通过对德里达的解读提出了这个问题,把这个人人无法摆脱、都要面对的“结”摆在了我们面前。另一方面,作者指出,德里达在文章中使用的是复数形式的“Aporiass”。他对单数的拒绝,也一样别有深意。因为,只有复数形式才能体现出,人们趋向“结”(有“劫难来临”或“大难临头”的意味)的方式各自有别甚至迥然不同。德里达对“死亡”的认识别具匠心。因为,就“死亡”来看,在这样的“真理的界线”上,人的趋向互不相同。这正能体现出与形而上学所描述的不同的情形。或许,只有在这里,人才是拥有“自我”的,因为她/他的“自由”绝不是“统一性”的。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看,这样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翻译的必要性。因为,在形而上学所要求的“一体化”及“同一”中,语言之间仅存表面上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异质、对立以及碰撞的可能性已从根本上被取消。这样,翻译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
所以,通过作者对德里达著作的题目的翻译与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深谙德里达著作的精髓,而且他本身的论述也正是对德里达思想的体现,和德里达的思想指向一致。透过作者的文字,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要求思想解放的力量,是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追求思想自由的精神。从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用意:翻译研究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就不能唯“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尊,就应该承认别的思维方式的存在,就应该承认,“逻辑”之外还应该存在别的“逻辑”。否则,思维方式的一致,即使按照一般的见解,也会造成人的思想指向上的趋同。而在这样的“一体化”之中,是很难找得到翻译的容身之所、存身之处的。
另一方面,解读德里达这样一位“饱学之士”的著作,自然需要厘清有关知识背景,追本溯源。因为,他虽然是就某一个哲学家某一方面的概念展开讨论,但每每触及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探讨,认识清楚,的确会觉得他的著作艰涩难懂,类乎“天书”。于是,作者在其解读中展开了这样的思想之旅,带着我们逆流而上,去探求那遥远的源头,去捡拾那里熠熠生辉的思想宝石。
作者提出,就思想渊源上讲,德里达尽管在很多著作中对海德格尔展开批判、颠覆,但是,海德格尔始终是他某种意义上的“导师”。后者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方面,德里达都重新探讨研究过。而由海德格尔上溯到尼采,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思想的延续性:尼采提出的“价值重估”始终是德里达“解构主义”中暗含的一个核心问题。
海德格尔的思想仍然是形而上学某种程度或意义上的延续,说明他的哲学思路的确还存在着一定的合理因素。所以,作者又带领我们上溯到了苏格拉底这个源头,并指出,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一种“灵知”活动。所谓“灵知”,作者在文中提出了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3)所作的解释:“它的字面含义是‘知识’,具体地指秘密的、启示的、拯救的知识。也就是说,它是关于奥秘的知识,它不是以自然的方式达到的,这种知识的拥有会决定性地改变知道者的状态。”同时,作者通过约纳斯所分的四种“灵知”指出,约纳斯定义的这四类“灵知”实质上象征着苏格拉底一生的哲学道路。而第三类“灵知”适应于苏格拉底的“出神”所含有的那种意向或“预示”的描述:走向智慧、逻各斯以及美德的内在要求。
将苏格拉底同“灵知”联系起来,原因何在?作者指出,诚如约纳斯所说,西方很长时间以来已经形成了“人神分离”的思想格局。在苏格拉底那里还可以见到的神秘、奥秘的智慧诉求早已丧失。西方文化已经形成了“断裂性”的主导文化取向;所以,几乎在人存在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断裂”、“差异”、“距离”以及“不同”。那么,与此相反动的,可能就是另一种取向。不过,尽管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探讨中逐渐失落,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灵知”的激情。这或许可以说明,西方古代的“灵知”一定还会找到它的某种现代形态,否则人对自身的异化便是不可遏止的。而作者在对德里达的著作的解读中就感受到了,他的无意识之中一定也有一种“灵知”精神在发挥作用。所以,作者指出,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灵知”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几乎还在潜在地左右着人的基本思路。这说明了中西思维的一致之处,说明了德里达和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天人合一”、“天通地通”才能促成真正意义上的翻译。
作者指出,不管是在古希腊,在远古的中东,还是在上古的中美洲,以及古代的中国,还有德里达所可能代表的这一时期,人们都看到了那种“灵知”:期望着人与动物、与“神”以及“灵魂”世界以某种方式达到“趋同”与“合一”。这都指向了一个现象:人们跨过了人类语言的边界与界限,努力追求着中国先秦时诸子百家“天人合一”的理想。所以,在语言与另一种交流渠道面前,在一种神秘到了几乎不可知的存在面前,人类早已找到了一种对话、交流、交接的对象,一个伙伴,一个可以伴随人走过一生的那种伴侣。因此,人的交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从人与那个十分亲密但又极其神秘的他者那里开始的。既然交流的起源是在“这里”,而不是在语言、理性、逻各斯或者说逻辑等等人类的思想以及思想建树中,那么,人的外求、精神的外向发展,也应成为翻译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也就是说,对翻译的研究既然要从起源入手,就不能不重视起源的来历本身。而起源不在我们这里,不在我们的语言之中,而是在远古,在原始的神秘之中,在萨满教巫师狂躁的舞蹈中。翻译因此的确是“语际”的。因为它表示了人要向他自身极限挑战的那种决心和勇气。只有突破这样的极限,“原始社会中的人”才可能变幻出“莫须有”的神灵来,使人有所依靠、有所顾忌,也与自身有所不同,进而找到提升自身的台阶。在跨越语言障碍的同时,翻译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要改变人自身的面貌。这也就意味着,人是通过幻想来转化自身的。这样的转化,就是“语际翻译”,即那种对语言的超越,导致人幡然醒悟、促成人对人间的一切都要由“精神”来解决的境界所必经的那种渠道、桥梁以及途径。
因此,作者提出,翻译研究一定不是仅仅对语言的研究,即它不应该仅仅是对民族语言、地区性语言与其之外的另一种语言的研究,也不是对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而应该首先是对人类跨出自身的可能性的研究,也就是德里达所不断强调的那种“死结”之外可能维系着事物的东西的研究。也就是说,翻译研究就其起源而论,是对原始交流情势的探讨;就其功能来说,是对维系世界的生命力的探索;就其目的来看,是在延续诸多物种的那种关联的可能性的研究。
由此可见,翻译的确已经不再可能保持它“语言”指向上的定位,而应该扩展其概念化的覆盖面。作者在其著作中所要论述的,正是如何通过对德里达的研读,接合上“原始”可能传来的声音,带来的启示。而作者在对德里达的解读中对庄子寓言的引入,更是大大拓宽了我们的翻译研究思路。
作者指出,在有关“灵知(主义)”论述的启发下,可以得知,“庄周梦蝶”之所以成为可能,那是异类转化的另一种说法,也就是人与世界合一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样的转化可以被视为“语际翻译”,因为它并不关乎人的语言、理性以及逻辑思维,甚至要跨出语言的边际;它完全依赖梦境、幻想或想象,依赖非理性的“奇思妙想”。而想象力的减弱,造成了现代人对这样的现象的“神奇感受”或“不可思议的感慨”。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转化中,我们才能看到古今同一、中外一律。因为,这样的莫名其妙的转化,在古今中外都被视为人生的根本、文化的象征力量或历史性的指向。那么,将翻译的起源置于这样的转化之中,不仅可以明白苏格拉底的“出神”的哲学沉思的意义,而且也自然能够解释庄子的现代意义;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透过历史的迷雾将本来隔膜甚深的两种文化结合起来,以说明在人类的“原始”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闪烁到了今天的那种曙光:相互了解,要超出人类本身,“知遇”的实现要依赖人的自我放弃。因此,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走出理性主义的现代意识,可能是我们了解翻译的历史变化与趋向的一条途径。这条途径告诉我们的是,只有在保持多种思维的前提下,人类本身的交流与来往才是正常的、健康的、合理的。那种以逻辑思维为导向甚至将它视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的观念,已经背离了时代要求,因而需要认真加以矫正。
可以说,蔡新乐的这部著作就是一次贯通古今中外的“逍遥游”。他对德里达的解读,对其思想渊源的探寻,对中西思想的融会贯通,对翻译学未来发展道路的定位,都告诉我们:只有解开我们思想上的“结”,只有破除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只有超越“自我”,在多种思维方式存在的情况下,翻译研究领域才真的会是“海阔天空”,才会显示出它那古老的、永久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