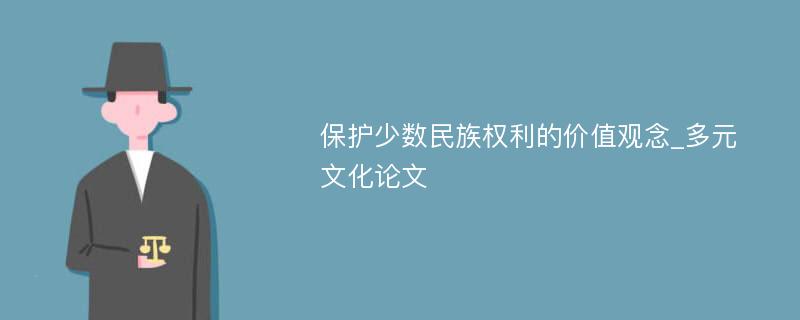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权利论文,理念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理念问题是少数民族① 权利保护的深层次问题。不同的价值理念产生不同的政策和立法,继而产生不同的实践效果,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政策和立法文本相同,但由于贯穿其中的价值理念不同,其实践效果也迥然不同。受自由主义的学术传统和民族国家“民主政治”均质化理念的影响,西方学界主流长期对少数民族的权利要求采取“应对”策略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的研究成果多散见于各种政治学派尤其是自由主义学派的对策性研究中。从另一个向度来看,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制度、机制、政策、立法的设计层面,缺乏对制度、机制、政策、立法背后价值理念的系统考察。这种现象使得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多限于操作层面,缺少对所涉问题价值层面的深层次追问,如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以及如何协调它与现代(多)民族国家公民政治过程的关系等。
在国内,虽然一些学者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做了不少分析和建构,但如何在理论上认识这些建构性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在实践中,不仅一般的民众甚至一些政府官员对我国运行了数十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共识,而且学者中亦分歧明显(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解构性分析的不乏其人),这在“3·14”和“7·5”事件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上述情况表明,研究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理论、制度和政策文本的分析,梳理归纳出五种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即:出于多数民族的利害或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的价值理念、权利正义的价值理念、保存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的各民族政治族格② 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这些理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或者在某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单独或共同作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一、出于多数民族的利害或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的价值理念
多数民族的利害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关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是“价值动机”)。从最初的无情的杀戮、俘虏和奴役,到后来的歧视、排斥甚至种族灭绝,再到后来的平等保护甚至特殊优惠,无不贯彻着多数民族对利害的权衡。16世纪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欧洲的多数民族在反封建(教会)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种适合保障自身群体利益的重要形式——民族国家。从此,多数民族的利害话语就逐步转化为一种更为宏大、更为抽象的话语——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与统一的利益。
被视为最早③ 保护宗教上的少数民族之权利的两个和约《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和《威斯特伐里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同时也是最早保障“国家”安全与统一的国际性和约。《奥格斯堡和约》结束了欧洲准民族国家——天主教和新教各邦诸侯——之间的战争,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教随国定”原则承认各邦诸侯有权自由选定其辖区内的宗教信仰,有权决定诸侯自身及其臣民信仰天主教或路德新教。这里,和约贯彻的不是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而是国家(诸侯)决定宗教信仰的自由。也就是说,保护宗教上的少数民族之权利的选择直接受制于国家(诸侯)利益。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和约规定不接受所在诸侯国宗教信仰的臣民可以出卖其产业后离境。《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确认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合法地位,确认新教诸侯和天主教诸侯在帝国内的平等地位,规定各诸侯邦国可自行确立官方宗教,享有外交自主权,正式承认荷兰和瑞士为独立国家等。《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被认为开创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其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及国家独立等原则,不仅成为近代以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且它所创立的宗教上的少数民族之权利保护受制于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的价值理念,为近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制度和实践定下了基调。
一战后,由于欧洲版图的重新划分,一些多数民族的成员被划分在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民族国家内。为保护那些离开族源国的少数民族群体,防范各国因少数民族问题发生冲突,从而危及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主要的协约国和参战国坚持同那些存在着少数民族的新兴国家缔结保护少数民族的特别条约。这方面的条约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以主要的协约国和参战国为一方,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等国家为另一方缔结的条约;第二类是在与匈牙利、奥地利、保加利亚以及土耳其缔结的和约中加入保护少数民族(义务)的特别章节;第三类是在有关默麦尔地区和上西里西亚的专约中,加入保护少数民族的条款。“在这些条约中,凡适用少数民族制度的国家都承担对受保护的少数民族的成员不加歧视的义务,并承担为保护他们种族的、语言的和宗教的完整性而赋予其所必需的特别权利的义务”,一些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伊拉克等以单方面声明的方式承担了类似义务。④
为切实保障上述条约和单方面声明中所规定(确认)的保护少数民族的义务的实现,切实保障欧洲民族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统一,国际联盟还建立了一套专门的申诉制度,并在必要时提请国际常设法院就急迫的少数民族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应该说,国际联盟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体来说,二战前保护少数民族的价值理念多出于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安全的需要(尽管有关条约不乏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目的和动机)。这种情形加上国联时期的条约只规定某些欧洲国家有保护少数民族的义务,且这些义务只适用于其管辖下的某些少数民族,⑤ 条约所追求的目标即通过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以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与统一的利益未能实现。
二战后,鉴于一些少数民族的悲惨命运严重地影响了世界和平,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安全与统一,也影响了多数民族的命数,从《联合国宪章》始,在联合国的努力下,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公约、宣言和其他国际文件。这些公约、宣言和国际文件,从一般的和特殊的角度规定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及其实现途径或机制。与此同时,一些地区性的保护少数民族的公约和条约也陆续制定并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性或地区性的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具有国际法地位或意义的国际文件,仍然表现出很强的保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的价值倾向。这种价值倾向不仅表现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没有一条关于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规定,⑥ 而且那些包含有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文件,无论是在制定过程中,还是在文本表述、条文解释和权利救济中,都明显表现出了浓重的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价值理念。关于后者,笔者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27条为例进行阐述。
在制定该公约第27条的过程中,困扰《世界人权宣言》的分歧继续存在。新世界的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和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印度等),为了国家安全和统一,都力主融合和同化少数民族(政策);而由领土变更而导致各种少数民族问题的欧洲各国,则多主张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以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来讲,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问题)。从各自价值取向出发,在受保护的主体范围方面,苏联坚持将受保护的主体限制为“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y),但多数国家坚持使用“人种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少数人”的界定形式。关于土著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以下简称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代表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不属于“种族、语言或宗教上的少数人”,其中,澳大利亚代表声称“土著人太原始了,以致不能被看作是少数人的群体”;智利建议在“人种的、宗教的和语言的少数人”前面加上“长期存在的、稳定和明确的”,以确保移民不被视为“少数人”。⑦ 与此相类似,在少数人权利的属性上,多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公民权利与人权、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类分成为争论的焦点。苏联的“少数民族”方案,被认为除了“使27条的适用范围变得更为狭窄”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有“一种主观因素:共同的意识和要求独立的政治意愿”,使得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受到威胁;而明确对移民的保护则“会刺激新的少数群体的形成并因此威胁国家统一”。“在联合国大会社会、人道及文化委员会上,人们所强调也是防止第27条被滥用来威胁国家统一。”⑧ 可以说,当时在“少数人”权利属性方面,“人权”、“群体权利”、“积极权利”的取向被认为不利于国家的安全与统一。
因此,公约第27条最终被表述为“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⑨ 这一表述充分表明了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上存在的顾虑,即:少数民族的权利威胁国家的团结与安全,过于积极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容易导致外部干涉。⑩
在公约第27条的理解和解释方面,人权委员会及相关国家多倾向于将少数民族权利解释为个人权利,而非威胁国家安全的集体权利。在权利救济方面,人权委员会有时以来文“没有穷尽国内的救济手段”为由拒绝受理;(11) 有时将自称是“人民”的土著人的申诉降格为“少数人”的申诉,(12) 以最大限度地回避对有关国家的国家安全和统一造成影响。
总之,最早的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理念源于多数民族的利害权衡。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多数民族的利害理念逐渐转化为国家安全与统一的理念。进入近代以后,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逐步成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层面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少数民族权利立法和实践的基本走向和实际效果。当然,在“国家安全和统一”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对应关系。在一些情况下,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需要对过分宽松和放任的保护政策加以调整;在另一些情况下,自由和包容的少数民族政策可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一剂良药。其动态的平衡关系取决于每个国家不同的少数民族国情。
二、权利正义的价值理念
“权利正义”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回应诸如“为什么要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这类诘问上,权利正义的价值理念最具论辩性。所谓“权利正义”,简单地说,是指权利作为一种利益与机会,在分配上应该遵循正义的原则。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3) 正义地或公平正义地分配利益和机会是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重要环节,也是处理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关系的主要方面。
权利正义或公平正义地分配利益与机会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民主权利的制衡问题,另一个是权利补偿问题。
1.民主权利的制衡问题。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制度和机制,而民主权利则是参与这种利益分配制度和机制的资格。民主权利是以公民身份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早在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就存在公民参与决定公共事务的传统,只不过那时的公民仅限于一部分男性成年自由民,妇女、奴隶和外来人是被排除在外的。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民权利逐渐扩至全体国民。在民主政体下,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无差别的”民主权利。
“无差别的”民主权利建构在现代公民—国家的基本理论之上,该理论假设社会上的公民都是无族群文化差异的“无性状的人”。(14) (公民)民主权利没有质的差别,只有量的不同。一定量的达致(如过半数或2/3)构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基础。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多数人的意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设置,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领导人的任免,决定国家和地区层面的主要政策、法律,决定民意,决定合法性,等等。在一些历史场合,民主(权利)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决定谁是异端并继而决定这些异端的去留和命运。(15)
在民主国家,民主多数的原则天然契合了多数民族的各项利益。在这样的国家里,多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经过多数原则顺理成章地成了“国语”和“国家传统文化”,多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利益成了“国家利益”,多数民族主导制定的法律成了“国法”,甚至多数民族的成员都成了典型意义上的“国人”,表面中立的国家常常具有十足的“民族性”。(16) 这种情形使民主(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多数民族实现国家控制权或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工具或手段。
在一个存在着少数民族的多元化社会,简单的民主多数原则实际上意味着用选票箱将少数民族挡在政治参与之外。少数民族在数量上的劣势地位,决定着其民主权利(选举权)即使是有所放大,也难以在多数民族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选举市场中起到作用。人们普遍认为的通过民主制处理公共事务,以实现每个人的影响力、政治地位的平等的正义原则,(17) 在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问题上难以体现。
现代民主制国家形式是多数民族选择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最理想的工具。在这种国家形式下,多数民族的权利和利益总是以一种抽象的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多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利益、宗教利益(包括无神论)和政治经济利益都非常巧妙地结构化于一种普遍的、平等的治理构架中。民主制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多数人(民族)的国家。在这种国家形式下,少数民族(族群)受到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多数民族的系统的、强有力的统治。
民主(权利)的实质是平等,德沃金曾区分了两种平等的权利:一是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treating people equally),如每个公民在民主选举中都有平等的选举权,并且都只有一个同权的投票权,此为民主权利原则;二是作为平等的个体而受到对待的权利(treating people as equals)。第一种权利强调平等地分配某些机会或义务,如投票权的平等。第二种权利强调公民(人)自身的平等即每个人都能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18) 此为正义原则。民主权利原则需要受到正义原则的制衡。
为实现“每个人都能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的正义原则,抑制民主的“过度庞大的权利”,(19) 学者和政治家、法学家们设计出了种种制度和机制,如权力分立、公民社会(结社自由)、少数民族的权力自治和权利优惠等。在这些制度和机制中,以司法制度和少数民族的自治制度最为凸显。
司法制度平衡民主权利的基本理念来源于反对大多数的权利不能交给大多数人去决定的理论、“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正义原则。民主权利(立法)的运行过程贯彻的是民主原则,而司法过程贯穿的是正义原则。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过程中,正义原则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美国,正是由于司法判断的正义之手率先打破了种族隔离的立法。美国人深信,司法判断是限制立法、制衡民主、保护社会上的少数派免遭“严重破坏”的重要平衡器。(20) 20世纪以来,美国的违宪审查司法实践对纠正立法的偏颇、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21)
少数民族的自治制度是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系统性、根本性制度。这一制度设立的基本理念是交换的正义,即国家由事实上的多数民族统治,作为对其统治合法性承认的交换,少数民族应该享有“超越”一般民主权利的少数民族权利。这一交换的正义模式也被概括为“多数人的统治”(majority rule)和“少数人的权利”(minority right)。
2.权利补偿的问题。权利补偿是权利正义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民主权利的制衡是为了解决现实权利分配中的不公正,那么权利补偿则主要是为了解决历史上的权利分配不公问题。相对于通过民主权利的制衡来实现权利公正,用权利补偿来实现权利公正得到了更多的共识。不仅社会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理论支持对历史上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少数民族给予公正的补偿,就连把已有的权利视为“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的、铁杆的“右派”自由主义学者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也认为,应当偿还那些被非法手段剥夺的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财产。(22)
在权利补偿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是列宁,他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1922年12月)中指出:“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对少数民族要“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23)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也发表了类似观点。在西方自由主义的阵营里,罗尔斯和德沃金也都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关切。他们认为少数民族作为“最少受惠者”应该得到优待和补偿。德沃金还从资源平等理论出发,提出政府应当补偿给少数民族应该有而没有拥有的那部分资源。对于由于补偿所造成的“不平等”,德沃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将很多人置于不利地位的政策,因为它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境况变好,所以它是合理的”。(24) 在权利补偿问题上,金里卡的观点最为犀利,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主流社会的发达就离不开对土著人的驱逐”。(25) 通过揭示权利的剥夺与权力的强制之间的关系,金里卡提出了一种可以说是近乎道德“强迫性”的补偿观点。总之,随着托马斯·海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开始关注平等问题以来,自由主义的主流已逐步接受优待或补偿少数人包括少数民族的观点。(26)
在实践层面,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出采取积极措施(包括补偿)保障少数民族平等享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为了体现权利补偿的公正性,相关国际公约(宣言)还严格区分了作为种族或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人和土著人的权利。在国内法层面,一些国家如美国和加拿大先后采取立法的、行政的或司法的手段来保障少数民族获得补偿的权利。在美国,针对历史上因种族或族裔身份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政府在一些社会福利,如就业、入学、获得政府合同、享受政府津贴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照顾。有鉴于印第安人的历史遭遇和美国主流社会的繁荣存在着几乎对应性的因果关系,美国政府(包括立法、司法机关)给予了印第安人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族群)的特殊补偿,如地域性自治、免税等。
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价值理念中,权利正义尤其是权利补偿的正义理念最具合法性抗辩力。它表明,目前世界各国坚持的有关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种种政策、立法及实践,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来自多数民族的慷慨或无条件的优惠,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恢复性正义。
三、保存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
多元文化是人类生活式样多样性的表现。保存多元文化是理解人类自身完整性的一个必要方面。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多元文化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少数民族作为多元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其权利保护也相应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具体而言,保存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主要有三个不同的出发点:一是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视为一种对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文明的挽留。这种权利保护的理念往往伴随着浓厚的文化欣赏动机,或怀古幽情——多数民族对与自己有关的逝去的岁月的追忆。当然有时也纯粹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典型的例证是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将那些濒危的少数民族(文化)相对隔离加以保护,防止其被多数民族文化彻底同化,以留下“活的”文化标本。这一活的文化标本,连同存在于博物馆的已经被浓缩为一个文化符号的死的标本,一同成为保存多元文化的一个体征。这方面典型的例证是北美世界的印第安文化。二是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视为与人类社会利益攸关的文化参照措施。这种观点认为,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是整个人类社会可资借鉴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土著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协调、和谐关系,对于西方工业社会的那种非持续性的、自我毁灭的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27) 建议采取措施积极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人类社会利益攸关的多元文化的探寻,还潜含着反对全球范围内经济、社会、政治单一化(西方化)趋势的努力。这种努力为了使全球化具有人性(to humanize globalization),也希望借助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去平衡可能危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单一化或西方化趋势。在此情况下,保存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还蕴含着反西化的意识形态。三是把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视为完整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强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就是保护人类文化本身。这一出发点建构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即认为每种文化“都具有尊严和价值,必须予以尊重和保存”,“所有文化都是属于全体人类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应尊重每一文化的特殊性质”。(28)
为了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合理性和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l条中指出:“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文化是人类行动最深层次的动机。联合国框架下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建立在所有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基础之上。它强调文化上的民族尊严和平等对于民族国家、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在其序言中发人深省地指出:“因为战争是在人的心中开始的,所以,保护和平必须建于人的心中。”(29)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民族的身份证和尊严的符号。文化上的平等性既决定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性,又反过来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博登海默在揭示人的平等的心理根源时指出,人之所以追求平等,“原因之一乃是人希望得到尊重的欲望……原因之二在于人不愿受他人统治的欲望”。(30) 民族文化的平等性体现的正是这两种“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上的平等是所有平等的前提。
保存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对于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正当性具有重要的支持意义。但仅从“保存多元文化”的视角辩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正当性似乎缺乏一定的要素构成(尤其是当这种受保存的多元文化被客体化时)。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正当性,需要从人权的视角加以系统的论证。
四、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
以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保护少数民族权利意味着,(多数民族)从同为平等的人类、享有平等的人类尊严和权利出发,以“待彼如待己”的价值理念对待和处理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问题。与上述三种价值理念的关系是,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超越了狭隘的主权安全(多数民族)的利害价值观(但并不绝对排斥这种价值理念),包含和反映了权利正义以及“保存多元文化”的价值理念(但在总体上形成超越)。与上述三种价值理念相比较,“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具有相对的全面性、完善性、自洽性和综合正义性。
尊重人权价值理念的核心是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一样,平等地享有一切基本权利和自由。“平等地享有权利”与享有平等的权利或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诸如此类的权利原则相比较,前者具有实质性平等或无限接近实质性平等的价值意味。可以把这种意义上的平等概括为“人权意义上的平等(权)”。
平等(权)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最早对平等(权)在技术上进行了比较完善论述的是亚里士多德。亚氏认为平等就是“正义”,他将平等分为两类:一类是“数量相等”,即“你所得的相同事务在数目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的相等”;另一类是“比值相等”即“根据个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务”,(31) 这一平等观也被概括为“类似的事物应该得到类似的对待”和“不同的事物应根据其不同而予以不同的对待”(treat the equal equally,treat the unequal unequally)。(32) 值得注意的是,亚氏的平等(权)理论并不是一个具有特定道德内容的价值原则,它既可以被用来解释现代民主社会的一些合理的区别对待现象,也可以被用来论证等级社会的合理性,甚至还可以被用来解释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平等权是否同时受到其他权利的支持或限制。
“人权意义上的平等(权)”在强调“类似的事物应该得到类似的对待”和“不同的事物应根据其不同而予以不同的对待”的同时,强调人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的普遍平等性,强调人的人格尊严的平等性和良心自由、免于强迫等权利和自由。通过赋予平等以人权的价值,人权意义上的平等(权)成功地解决了平等(权)的“空瓶子”(33) 的问题。
以人权意义上的平等(权)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意味着少数民族应该真正平等地享有和多数民族一样的普遍的人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非歧视和特殊保护两个方面着手。这里的逻辑公式大致是: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非歧视+特殊保护。以下简述之。
平等是国际人权法的首要原则,所谓“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即是这一原则的写照。平等也是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普遍原则。少数民族权利有普遍权利和特殊权利之分,保障前者需要反对歧视,保障后者需要对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做出规定。因此,在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方面,有两个嵌入式的内容是非歧视和特殊保护。
(一)非歧视
联合国的《关于增进和保护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的规定》中把“歧视”定义为“基于种族、肤色、语言、宗教、民族或社会起源、出身或其他身份的差别而采取的区分、排除、限制和优惠,其目的和效果是为了消灭或削弱所有人在平等基础上对权利和自由的享有和行使”。反对歧视是为了“防止任何阻碍个人或群体享有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平等待遇的行为”。(34) 非歧视的规定出现在大量的国际公约和宣言[如《联合国宪章》(第1条和第55条)、《世界人权宣言》(第2条)等]中,非歧视的条款也包含在几乎所有的地区性人权文件(如《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欧洲公约》、《欧洲社会宪章》等)中。可以说,“非歧视”原则已经成为在各个领域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一个“王牌”原则。
(二)特殊保护
在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地享有多数民族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特殊保护与非歧视原则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当少数人能够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能够从他们自己组织的服务机构中受益、能够参加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时,他们才能取得属于多数的人理所应当享有的地位。(35) 多年来,就少数民族的特殊保护问题,国内外学者中存在着大量似是而非的观点。反对特殊保护的学者往往把特殊保护措施视为对多数人(民族)的逆向歧视,甚至视为少数人(民族)对多数人(民族)的特权。他们把亨金的“人权一词意味着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的所有人的权利”(36) 空泛化、模糊化,把人权的平等看成是所有人的无差别对待,看成是冷冰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至于完全忽略富翁和流浪者的悬殊境遇和差别。
平等地享受权利,在逻辑上首先要求补齐影响平等享有权利的差别。现代民族国家主要以公民权利的平等为特征。公民的权利的享有与否或享有的程度,与公民的实际处境和状况密切相关,如一个在经济上贫困或完全受制于人的公民,同经济上能够自立自治的公民显然享有不同的实际权利。忽视这一点,就难以建设一个公正的公民社会。也许正因为此,罗尔斯认为,在他的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之前,应该设定一个更基本、更优先的原则。这一原则首先应该保证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如起码的温饱与卫生、基础教育以及人身安全),以便保证公民们都能理解、都有能力运用自己的基本权利与自由。(37)
在人权法层面,特殊保护受到广泛的正当性支持。《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2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儿童权利公约》(第30条)、《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第5条)、《少数人权利宣言》(第5条)等均规定有对少数民族权利的特别保护。区域层面的《关于保护少数民族的框架公约》和《地区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欧洲宪章》等也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特殊保护问题。当然,这些规定也强调,特殊保护一经达成目标,“绝不得产生在不同种族团体间保持不平等或个别行使权利的后果”。(38)
五、马克思主义的各民族政治族格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的各民族政治族格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体现和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和政治家的著述及相关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突破了殖民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樊篱,提出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坚持“不承认和不坚持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反对民族同化政策,认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39)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理念建立在反对民族压迫与剥削、各民族政治族格一律平等的基础之上,其平等理念的最大特点是“政治化”即将民族关系政治化,试图从政治上、从根本上找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不平等问题。这大大超越了(多数民族的)“利害化”、(将少数民族问题)“文化化”、“优惠化”以及以保护个人利益为主要形式的“人权化”等价值理念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各民族政治族格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的全方位性:既认同主权理念,又超越狭隘主权论;既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又承认统一性(克服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弊端);既坚持权利的正义性,又注重权利的阶级性;既尊重人权价值(理念)的一般事实,又形成超越人权价值的共产主义大同视角。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各民族政治族格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并不尽如人意,但在指导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采取的原则如民族平等原则、民族团结原则、民族互助原则、民族和谐原则,采取的制度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特殊代表权制度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各民族政治族格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在中国的良好实践。
注释:
① 本文沿用我国政策和实践以及相关学术研究中惯用的“少数民族”提法。在国际法层面,这一概念大致与“种族或民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人”以及土著民或原住民相对应。
② 由法律上的“人格”一词推衍而来,指一个民族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政治和民事主体资格。“族格”在这里主要是一种借喻的提法,其意在表明:“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或在国际关系中),每个民族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相关论述可参见马俊毅、席隆乾:《论“族格”——试探民族平等与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的哲学基础》,载《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也有学者将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问题追溯到古埃及、古希腊时期,详见Kristin Henrard,Devising an Adequate System of Minority Protection:Individual Human Rights,Minority Rights,and the Right to Selt-determin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0,p.3.
④ 徐显明主编:《国际人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337—338页。
⑤ Kristin Henrard,Devising an Adequate System of Minority Protection:Individual Human Right,Minority Right,and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p.6.
⑥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以及苏联、南斯拉夫等国都提出了这方面的草案,但都没有形成结果。苏联也因此在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表决中弃权。
⑦ [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毕小青等译:《民权约法评注——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78-479页。
⑧ [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毕小青等译:《民权约法评注——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第484页。
⑨ 转引自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国际人权法教程》第二卷(文件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⑩ Michael Freeman,Human Rights: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115.
(11) 在处理针对法国不列塔尼人就学校和公共机构使用不列塔尼语问题的来文中,人权委员会以“未穷尽国内补救”为由宣布来文不可受理。人权委员会的做法与法国政府的声明密切相关,法国政府声明,根据本国宪法第2条规定(“法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公约第27条不适用于法国。[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毕小青等译:《民权约法评注——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第478—479页。
(12) 在卢比肯湖营居群案中,虽然来文者声称加拿大政府在开发资源和工业化过程中,破坏了他们的环境和经济基础,从而侵犯了他们的自决权,但人权委员会根据第27条而非第1条审理了这一来文。[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毕小青等译:《民权约法评注——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第487—488页。
(13) [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
(14) Matthias Herdegen,Equality of What,转引自李常青、冯小琴:《少数人权利及其保护的平等性》,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5期。
(15) 犹太政治家西奥多·赫兹尔(Theodor Herzl)曾明确指出,多数(民族)将决定谁是另类或异端;在民族关系中,这一问题及其他所有问题都是权力问题。详见Theodor Herzl,“A Separate Jewish State Is Necessary”,in P.Cozic Charles(ed.),Israel:Opposing Viewpoints,Greenheaven Press,Inc.,San Diego,1994,p.18.
(16) 周勇:《少数人权利的法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17) Geoffrey Cupit,“The Basis of Equality”,Philosophy,vol.75,Jan.,2000.
(18)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99—300页。
(19) [法]邦雅曼·贡斯当著、阎克文等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20) [美]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94页。
(21) 当然司法审查只是一种有限的、事后救济的措施,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数民族的权利保护问题。
(22) 刘擎:《诺齐克的思想之旅》,载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3月号。
(23)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2—353页。
(24) [美]罗纳德·德沃金著,信春鹰、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25) [加]金里卡著、刘萃译:《当代政治哲学》(上),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91页。
(26) 详见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2页。
(27) 李忠:《论少数人权利——兼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
(2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合作原则宣言》(1966年)第1、6条。
(29) Declar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UNESCO's Standard-Setting Instruments,IV.C.(1994).
(30)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
(3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4页。
(32) Manuel Velasquez,Claire Andre,S.J.Thomas Shanks,and Michael J.Meyer,“Justice and Fairness”,in Ethics,vol.3,no.2,Spring 1990.
(33) Peter Westen,“The Empty Idea of Equality”,Harvard Law Review,no.3,vol.95,Jan.1982.
(34)(35) UN Human Rights Fact Sheet No.18 on Minority Rights(1998).
(36) [美]路·亨金著、王晨光译:《人权概念的普遍性》,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37) 详见钱永祥:《罗尔斯与自由主义传统》,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2月号,总第75期。
(38)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
(39) 恩格斯:《波兰宣言》(1874年5月——1875年4月);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
标签:多元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政治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安全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