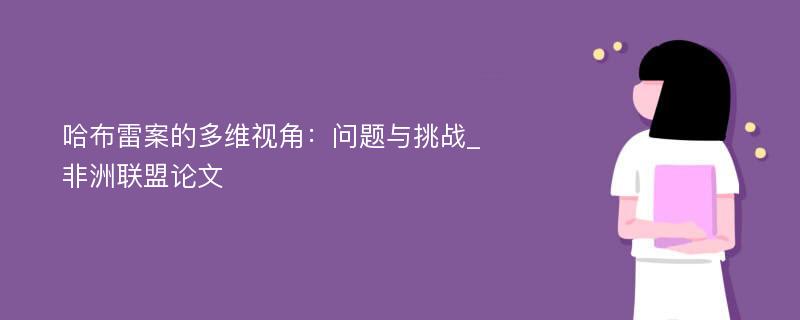
多维视野中的哈布雷案:问题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6月30日,塞内加尔宣布逮捕已在本国“避难”达23年的乍得前总统侯赛因·哈布雷(Hissène Habré)。这是自塞内加尔议会于2012年12月同意非盟建议、决定设立特设分庭以便对哈布雷在任期间所犯罪行进行审判以来,塞内加尔、乍得、比利时、非盟、欧盟、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国际法院等各方围绕哈布雷案长期“博弈”后所取得的最新进展。由于哈布雷一直被称为“非洲的皮诺切特”,对其审判所取得的此次进展,意味着塞内加尔“向正义迈进了一步”①。 尽管如此,从各方围绕本案所进行的长期“博弈”来看,由于其中既涉及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又涉及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之间的冲突;既涉及国际法的碎片化与统一适用之间的挑战,又涉及普遍的人权保障与被告的人权保障之间的挑战;既涉及人权机构与司法机构的不同立场,也涉及不同司法机构不同的价值追求。这使得哈布雷案成为近年来在国际政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领域中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将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文章将对哈布雷案进行必要的描述与梳理,为下文的展开提供基础;第二部分是文章重点,但是限于篇幅和案件所涉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出于主题集中的考虑,本部分不试图对哈布雷案进行“全貌性”研究,而将仅从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国际法的碎片化与统一适用等三个角度来对其进行剖析;最后是总结部分,将主要针对此案对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及其启示进行总结性探讨。 一 哈布雷案简介 哈布雷于1982年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就任乍得总统,1990年12月因军事政变被推翻。被推翻后,其曾在喀麦隆短暂逗留,随后向塞内加尔提出政治避难申请并被接受,此后便一直居留塞内加尔至今。在任期间,为维护统治,哈布雷对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严厉打击,涉嫌犯有酷刑、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多种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据统计,在其任期间有超过4万的反对者被杀害。② 正因为哈布雷涉嫌犯有上述罪行,2000年1月25日,7名乍得国民和一个受害者联盟一起,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提起了针对哈布雷的刑事指控程序。2000年2月3日,负责本案的调查法官确认,哈布雷涉嫌犯有反人道罪和酷刑等罪行,并将其予以监禁。2月18日,哈布雷以塞内加尔法院没有管辖权、相应刑事程序缺乏应有的法律基础、塞内加尔的行为违背了其宪法、刑法和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下称《禁止酷刑公约》)等为由上诉至达喀尔上诉法院,主张针对其的诉讼程序无效。7月4日,达喀尔上诉法院判称,由于相应犯罪发生在国外,犯罪嫌疑人系外国人,受害者也不具有本国国籍,塞内加尔对此案没有管辖权,针对哈布雷的刑事程序无效。受害者随后就此判决上诉。2001年3月20日,塞内加尔最高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诉。2001年4月7日,塞内加尔总统瓦德要求哈布雷离开本国,但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于4月23日要求塞内加尔不要让哈布雷离开塞国。同年9月27日,瓦德总统同意不让哈布雷离开本国。2000年11月30日,根据比利时1993年制定的《关于惩治严重践踏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法律》③和《禁止酷刑公约》,一名乍得裔比利时人在比利时启动了针对哈布雷的刑事指控程序,指控罪行包括反人道罪、酷刑罪和灭种罪。负责本案的调查法官于2001年和2002年分别给塞内加尔和乍得发出调查函,以征询塞内加尔针对哈布雷的相关程序进展和哈布雷作为乍得前总统是否享有管辖豁免。乍得司法部长在2002年10月7日的回函中确认,乍得已放弃了哈布雷应享有的所有豁免。④ 2005年9月19日,在经过长达4年多的调查之后,比利时签发了针对哈布雷的缺席逮捕令,并将此逮捕令转给了塞内加尔,要求塞内加尔将哈布雷引渡给比利时。基于此请求,塞内加尔当局于2005年11月15日逮捕了哈布雷。2005年11月25日,达喀尔上诉法院基于哈布雷享有管辖豁免这一理由拒绝了比利时的引渡请求并释放了哈布雷。同一天,塞内加尔将此事项提交非洲联盟大会讨论。非盟为此设立了一个名为“杰出非洲法学家委员会”(Committee of Eminent African Jurists)的机构,要求该机构考虑此案并提供解决建议,提出考虑建议时应优先考虑利用非洲机制。⑤在听取了该委员会的建议后,非盟于2006年7月作出第127(Ⅶ)号决议,决定“授权塞内加尔代表非盟起诉并确保哈布雷受到审判”,“相应审判应由一合格法庭进行,并应确保哈布雷受到公正审判”⑥。瓦德总统同意接受此决议要求。 针对达喀尔上诉法院2005年11月25日的判决,比利时先后多次发出照会以征询塞内加尔对于引渡请求的正式官方立场,但塞一直避免正面回应。2006年3月16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名为《针对非洲有罪不罚现象尤其是哈布雷案的相关决议》(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impunity in Africa and in particular the case of Hissène Habré)。决议声称,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分子,不论身份为何,均不应得到赦免或豁免,这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决议同时呼吁塞内加尔保证对哈布雷展开公平审判。如果通过非洲方式审理哈布雷不可行,就将其引渡给比利时审判。⑦ 2006年5月17日,就一些乍得人针对塞内加尔的指控,禁止酷刑委员会认定,塞内加尔违背了《禁止酷刑公约》第5条第2款的“应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⑧以及第7条第1款的“或引渡或起诉”义务。⑨关于后者,该委员会特别指出,由于比利时提出了引渡请求,塞内加尔如不履行起诉义务,就有义务将其引渡给比利时。⑩ 2006年11月2日,塞内加尔政府发言人声明,为审判哈布雷,履行基于《禁止酷刑公约》第5条和第7条所承担的义务,塞内加尔将修改本国法律。随后,塞内加尔于2007年先后修改了本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将灭种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和酷刑罪纳入其本国法律体系之中,并规定塞内加尔法院对发生在他国的上述犯罪有权管辖。(11)新法案于2007年2月12日开始生效。2008年4月,为了使本国法院有权对法案修改之前的灭种罪等罪行行使管辖权,塞内加尔修改了宪法第9条有关“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为其规定了相应例外,清除了展开对哈布雷案审理所面临的最后的法律障碍。 2008年9月16日,14位受害者在达喀尔上诉法院提起了针对哈布雷的刑事指控,指控后者在其任期内涉嫌犯有反人道罪和酷刑罪。但随后,塞内加尔以审理本案需要巨额资金为借口,一直拖延对本案的“重新”审理。(12)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为推动塞内加尔对本案的审理,欧盟、非盟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前往塞内加尔磋商资金支持的问题。塞内加尔开始要价高达6600万欧元,后压缩至2700万欧元,最后同意整个预算为860万欧元。与此同时,乍得自身也开始对哈布雷在任期间所涉嫌的犯罪行为进行“问责”。2008年8月15日,乍得恩贾梅纳的一个刑事法庭缺席判处哈布雷死刑。 2008年8月11日,一个叫米谢乐·尤戈戈巴尼亚的乍得国民在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我国国内也译作“非洲人权法院”)提起了针对塞内加尔的诉讼,要求塞内加尔暂停对哈布雷的诉讼程序,理由是:塞内加尔修改宪法的行为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违反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7(2)条,并且滥用了非盟授权其审判哈布雷案的权利。2009年12月15日,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作出了自该院成立以来的第一份判决,裁决对此案无管辖权,理由是塞内加尔没有发表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13) 2008年10月6日,哈布雷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起诉塞内加尔,称如果塞内加尔针对他的审理程序继续,将会构成对其所享人权的侵犯。2010年11月18日,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判称,塞内加尔对本国宪法和刑法等的修改表明,其对哈布雷的审理极有可能会对哈布雷的人权构成侵犯。塞内加尔应尊重自己法院已作裁决的“既判力”(res judicata),(14)并遵守“法不溯及既往”这一绝对原则。该法庭还认为,非盟2006年授权塞内加尔审理哈布雷案时,实际上是要求塞内加尔首先做好充分准备,从而确保对哈布雷的审理能在一个严格的、特设的、具有国际性的法庭框架内进行。(15) 针对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上述判决,2011年1月,非盟大会要求非盟委员会与塞内加尔就建立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特别法庭进行磋商,以便就审理哈布雷的形式问题作出最终决定。(16)2011年7月,非盟大会再次确认了授权塞内加尔审理哈布雷案的立场,并催促塞内加尔履行基于《禁止酷刑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执行禁止酷刑委员会决议和非盟授权其审理的决议;或者如果不审理,就将其引渡给愿意审理的任何其他国家。 由于引渡请求一直未获正面回应,比利时于2009年2月将塞内加尔诉至联合国国际法院,指控后者违背了《禁止酷刑公约》第5条第2款、第6条第2款和第7条第1款所载义务,并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塞内加尔应毫不迟延地将哈布雷案提交塞内加尔主管当局以便起诉;否则,应毫不迟延地将其引渡至比利时接受审理。2012年7月20日,国际法院就此案作出判决并判称:塞内加尔违背了《禁止酷刑公约》第6条第2款和第7条第1款所载义务。塞内加尔如不将哈布雷引渡,就应毫不迟延地将案件提交本国主管当局以便起诉。 2010年12月10日,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宣布:“非盟举行下届峰会时,我将明确地要求他们(非盟)将此案收回去。我知道该将哈布雷送往何处,我可以将他送回他的国家,反正我要完全摆脱这个案子。”(17)2011年7月8日,塞内加尔宣布将于7月11日将哈布雷遣返回乍得。但由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认为此举将会导致哈布雷在返回乍得后受到“虐待或死刑”,2011年7月10日,塞内加尔决定暂不遣返。基于此,7月22日,乍得要求塞将哈布雷引渡给比利时。 2011年4月,塞内加尔同意与非盟及乍得一起,合作建立一个特设分庭以便审理哈布雷案,但同年5月30日,塞内加尔又改变了主意且未作任何解释。在此背景下,非盟委员会于6月30日发表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非盟委员会敦促塞内加尔将哈布雷引渡给比利时审理。(18)受此影响,特别是受国际法院2012年7月20日判决的影响,2012年8月22日,塞内加尔终于同非盟达成了在本国法律体系内设立特别分庭的协议。12月,塞内加尔议会通过了设立特别分庭以审理哈布雷的相关法案。2013年2月,这个被称作“特别非洲分庭”(Extraordinary Africa Chambers)的塞内加尔法院内设机构在塞国首都正式宣告成立。(19)2013年5月23日到6月1日,特别非洲分庭总检察官专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比利时;随后,又于6月8日到16日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去乍得。7月2日,该分庭正式指控哈布雷在任期间涉嫌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和酷刑罪。 2013年4月23日,哈布雷再次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起诉塞内加尔,指控塞国与非盟签订的有关设立特别分庭的协议及特别分庭规约违反了法院此前所做判决,而执行此协议将构成对其人权的侵犯。2013年11月5日,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就此作出判决,认为塞内加尔出于履行其所承担国际义务的目的而缔结了该协议;无论是塞内加尔还是非盟,皆有权缔结类似协议。由于塞内加尔的行为系主权行为,法院无权对此类行为进行审查。同样,对于特别分庭对哈布雷案的审理,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指出,不同法院是平等的、没有隶属关系,自己同样无权对此进行审理。法院最后裁定自己对本案无管辖权。(20) 为了充分调查哈布雷所犯罪行,2014年10月3日,特别非洲分庭向乍得提出,希望能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去乍得,目的在于对已被乍得逮捕的哈布雷的两个前副手进行调查和讯问(特别分庭此前已经签发了针对其的逮捕令,指控罪名是反人道罪)。出乎意料的是,乍得于10月14日拒绝了此要求。尽管特别分庭最终对哈布雷定罪量刑的判决肯定会作出,但是,考虑到乍得的合作对于顺利进行哈布雷案审理的重要意义,乍得的上述立场与态度无疑将带来困扰。2015年7月20日,特别非洲分庭开始了对哈布雷案的审理。一天之后(即22日),哈布雷被法警带至分庭第一次出庭,这标志着对其的审理正式拉开了大幕。(21)因此,各方接下来围绕本案的“博弈”,值得继续关注和研究。 二 不同视域下的哈布雷案 综上所述,哈布雷案所涉及的主体及其关系是多样和复杂的,涉及不同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冲突。本部分将主要对这些价值和利益冲突进行分析和评论。 (一)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间的冲突 哈布雷案中所涉及的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比利时基于终结全球性有罪不罚现象而谋求引渡哈布雷与塞内加尔向哈布雷提供庇护之间的矛盾,欧盟与非盟围绕解决哈布雷案的方式之间的矛盾。 比利时向塞内加尔提出引渡哈布雷的请求是引发所有矛盾的源起和关键。实际上,从2005年9月签发针对哈布雷的逮捕令并于同月22日第一次向塞内加尔提出引渡请求开始,比利时和塞内加尔就一直围绕引渡与否的问题“纠结不已”。对于塞内加尔而言,无论是同意还是拒绝,都将面临尴尬局面:如果同意,于情理上难以解释自己当初同意给予哈布雷庇护的行为;如果拒绝,则将直接违背自身基于《禁止酷刑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尤其是其中第7条第1款规定的“或引渡或起诉”义务。而对于比利时而言,自其于1993年制定《关于惩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法律》,在其中确立了对相关严重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以来,比利时一直在国际社会表达着充当“世界警察”并终结“有罪不罚”现象的政治意愿。且此种意愿只有在与自身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案件上积极行使普遍管辖权,才能被清晰地展现在他国面前。因此,针对发生在他国的严重国际犯罪积极地行使普遍管辖权已经构成了其外交战略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因此而被视为积极实践普遍管辖权领域的“先驱”。这正是比利时在引渡哈布雷至本国受审的问题上一直锲而不舍的真正原因。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比利时的引渡请求,塞内加尔一直拒绝正面回应:要么不给予任何答复,要么“顾左右而言他”。例如,对于比利时2006年1月11日要求其就是否同意引渡给予最终答复的照会,塞内加尔就没有给予任何回应;对于比利时2006年5月4日的照会,塞内加尔回复称,自己2005年12月23日给比利时的照会已经就其引渡请求作出了答复。对于比利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30条,将彼此围绕哈布雷案审理的争端提交仲裁的建议,塞内加尔同样不置可否。(22)塞内加尔避免正面回应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旦正面回应且被比利时认为构成对引渡请求的拒绝,比利时即可进行接下来的法律行动——指控塞内加尔违背了基于《禁止酷刑公约》所承担的“或引渡或起诉”义务。而对于此指控的法律后果,塞内加尔当然心知肚明:自己肯定会被败诉,不仅如此,不履行公约义务和庇护严重国际犯罪者的不利形象也将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与其这样,还不如对比利时的指控“打太极”。 而从非盟和欧盟围绕本案的立场与态度来看,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获得体现。首先介入哈布雷案的是非盟。塞内加尔于2005年将本案提交给非盟大会进行讨论时,在2006年1月通过的第103号决议中,当非盟授权“杰出非洲法学家委员会”从六个方面考虑本事项,非盟特别强调应“优先采用非洲机制”来解决。(23)对于“优先采用非洲机制”的含义,在米谢乐·尤戈戈巴尼亚诉塞内加尔案中,米谢乐·尤戈戈巴尼亚认为,应该是指优先采用非洲传统哲学中的“乌班图”(Ubuntu)制度来解决。(24)按照南非大主教图图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对此制度的解释,其强调的是宽恕与和谐,以及乐与他人分享。(25)贯彻此种制度的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在宽恕基础上的赦免与和解。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对于多数犯罪分子的处理,遵循的即是此路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废弃之后的种族和解,遵循的是同样的路径,采用的是同样的方法。 对于非盟的上述意图,塞内加尔可谓心知肚明。上述第103号决议通过之后,塞内加尔外交国务部长谢赫·蒂迪亚内·加迪奥即表态称,哈布雷将不被引渡到比利时法院受审,哈布雷是非洲人,他的问题应由非洲人自己解决。(26)塞内加尔此后与比利时之间的周旋,一定程度上同样是基于上述认识的结果。在塞内加尔最初的“如意算盘”中,用“乌班图”制度来解决哈布雷案显然是非常理想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化解自身给哈布雷提供庇护所带来的尴尬。只是,一方面,哈布雷犯下的罪行是严重的国际犯罪,不仅受害者很难接受通过和解的方式来化解自身与哈布雷之间的仇恨,在强调终结“有罪不罚”现象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也同样很难接受此种处理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哈布雷案来谋求经济收益的想法同样重要:塞内加尔最初的漫天要价行为即是明证。上述两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乌班图”制度很难适用于本案。 在上述背景下,“优先采用非洲模式”在具体适用中就被赋予了新的意涵:不再强调宽恕与和谐,也不再要求赦免与和解,而是只具有了地理和方式上的“非洲”含义,即在非洲土地上、由非洲人自己来审理。这不仅与非洲传统哲学无关,相反,还不排斥接受外界,例如来自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资助。 但是,即使从单纯的地理和方式上的“非洲模式”来看,圆满地解决哈布雷案依然存在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从塞内加尔自身情况来看,就是如何克服此前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由于在塞内加尔国内法程序中,其最高法院已经于2001年3月2日裁定对本案不拥有管辖权,作出了最终的、不可上诉的判决,相应的判决具有“既判力”。因此,从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来看,本案在塞内加尔国内法框架内解决已经不具有任何可能性。成立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特别法庭来解决就成为博弈各方都能够接受的选项:特别法庭一方面能够解决塞内加尔国内法程序已经终结的难题,一方面又能够实现终结“有罪不罚”现象的目标,从而能够满足欧盟的关切。 然而,从最终设立的分庭的人员选任与构成,以及分庭所适用的法律等要素来看,如果将其与其他已经设立的国际法庭相比较,特别非洲分庭在严格意义上很难被认为是国际性的:分庭除了适用国际刑法,还适用塞内加尔刑法、刑事诉讼法;分庭庭长由塞内加尔提名;分庭预审分庭由4名塞内加尔法官和两名备选法官(同样来自于塞内加尔)组成;分庭检察官及其3位助手同样来自于塞内加尔等等。(27)因此,与其说该法庭是一个国际性法庭,还不如说其是塞内加尔国内法院的一个分庭。在此意义上,“特别非洲分庭”这一名称倒也“名副其实”。 而从欧盟的视角来看,非洲模式天然地就不是首选。终结“有罪不罚”现象是欧盟的优先目标,也是欧盟致力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外交工具和手段。因此,对于比利时请求引渡哈布雷的行为,欧盟方面是大力支持的。在2006年3月16日通过的《针对非洲有罪不罚现象尤其是哈布雷案的相关决议》中,欧盟同时提到了与非洲有关的三个案件:利比里亚前总统泰勒案、埃塞俄比亚前总统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案和哈布雷案。而在这三个案件中,唯有哈布雷案进展迟缓。所以,欧盟在上述决议的标题中就特别地提及此案,除了通过此种方式向非盟传达自己对此案高度关注的信息外,欧盟主要还是敦促塞内加尔将哈布雷引渡给比利时审理(决议正文第12段)。 但在非盟执意寻求通过“非洲方式”审理的背景下,欧盟最终软化了上述立场,转而对非盟和塞内加尔的行为予以支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欧盟通过不同渠道展示自身关于问责哈布雷的立场。例如,在2008年4月28日与西非经济共同体举办的第13次部长级会谈中,欧盟即向西非经济共同体表达了自身对在塞内加尔审理哈布雷案的支持。(28)(2)在塞内加尔“答应重新审理”哈布雷案后,欧盟第一时间派出专家协助塞内加尔制定相关检诉计划,编制审理所需预算。(3)为帮助塞内加尔筹集到审理所需经费,欧盟积极参与资金筹集。 无论是支持比利时,还是支持非盟和塞内加尔,欧盟的行为逻辑从头到尾都具有一致性:支持比利时是基于纯粹普遍管辖权的实践和终结“有罪不罚”的目标。正因如此,对于非洲模式,欧盟优先支持的是建立一个国际法庭这样的机制,而不是非盟原本应优先考虑的“乌班图”制度。因为根据后者,欧盟所追求的终结“有罪不罚”现象的目标就会落空。 但是,从非洲的角度来看,由于欧洲方面在追求终结“有罪不罚”这一目标上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非洲,并且相当部分是非洲在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高级官员,从区域治理的角度,欧洲的行为在很多时候不仅不能达到终结“有罪不罚”并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反而有时会给非洲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威胁。非洲的事务只有非洲人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也只有由非洲人自己来处理,才会有更积极的效果。因此,对于欧盟及其成员国所热衷行使的普遍管辖权,非洲方面是颇为反感的。自2008年开始,非盟大会不仅每年都会将滥用普遍管辖原则的问题纳入讨论范围,并先后多次通过相关决议,(29)而且还成功要求联合国大会将此议题列入联大会议议程。(30)在上述背景下,非盟于2012年5月进一步通过了名为《非盟有关针对国际犯罪确立和行使普遍管辖权的示范国家法(草案)》。(31)该示范法的主要目的,即在于通过呼吁更多非洲国家在本国国内法中确立和行使针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来防止来自于欧洲等国家的外交干涉。就此意义而言,非盟坚持了非洲事务“非洲区域治理优先”的同样立场。 就欧洲的上述实践而言,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将其描述为欧洲视角下的全球治理和欧洲中心主义式的全球治理,可能更为适当。毕竟,对于欧盟全心全意支持比利时行使纯粹普遍管辖权的相关实践,其他区域的国家并不一定认同,(32)更遑论作为欧盟眼中实践“重灾区”的非洲了。 (二)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间的冲突 塞内加尔确立对哈布雷案管辖权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贯彻国内法治的过程;但由于违背了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此过程不符合国际法治的要求。当哈布雷案最初在塞内加尔启动的时候,塞内加尔法院即裁定,自己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这一裁定完全符合塞内加尔国内法:无论是根据其宪法,还是根据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塞内加尔都没有确立普遍管辖权。因此,对于发生在乍得的相关犯罪,即使其属于严重国际犯罪的范畴,塞内加尔也无法行使相应管辖权。也正因如此,塞内加尔最高法院于2001年3月20日作出驳回上诉的终审裁定,符合其国内法治要求。但是,从塞内加尔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的角度来看,这一裁定却有违国际法治的要求。塞内加尔所承担并违反的国际义务,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1.由于塞内加尔是《禁止酷刑公约》当事国,而哈布雷涉嫌犯下的罪行中,酷刑正是其中之一,从其基于公约承担的义务尤其是“或引渡或起诉”义务和初步调查义务来看,塞内加尔如果不针对此案采取任何行动,就会违背自身所承担的公约义务。根据其最高法院2001年的终审裁定,在塞内加尔缺乏针对此案管辖权的背景下,无论是“起诉义务”还是“引渡义务”,显然都不可能履行。(33) 2.塞内加尔1999年2月2日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因而承担了规约所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对规约所规定的罪行优先确立并行使管辖权的义务。哈布雷所犯罪行如反人道罪,正是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罪行。尽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不具有溯及力,国际刑事法院对此案无管辖权,但塞内加尔作为规约缔约国,对于哈布雷所犯的国际罪行,却有义务在国内法层面履行规约规定义务、对哈布雷案确立管辖权并展开审理。塞内加尔裁决自身对哈布雷所犯罪行包括反人道罪行无管辖权,就明显地违背了其基于规约所承担的义务。欧盟之所以在2006年3月16日通过的决议序言第(A)段和(H)段中特意提及国际刑事法院及国家基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承担的在国内法中赋予规约规定以法律效果的义务这一内容,含义即在于此。 然而,当塞内加尔基于履行国际义务的目的而修改了本国的国内法,以便确立对哈布雷的管辖权并准备行使管辖权时,虽然从国际法治的角度来看,塞内加尔的行为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反过来,从国内法治的角度来看,却同样面临着挑战。为了确立对哈布雷的管辖权,塞内加尔首先修改了本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通过修改,塞内加尔就拥有了对发生在他国的灭种罪、反人道罪和酷刑罪等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但由于哈布雷所犯罪行发生在法案修改之前,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塞内加尔还是无法确立自身对哈布雷所犯罪行的管辖权。在此背景下,塞内加尔最后又修改了本国宪法,为“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规定了有限的例外。从塞内加尔对本国多部法律的修改,尤其是对本国宪法的修改可以看出,塞内加尔在履行自身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上付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其履行国际义务的诚意也是异常明显的。然而,从国内法治的角度来看,塞内加尔上述修改法律的行为至少存在以下两处“硬伤”: 1.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其含义是:国家不能用当前制定的法律指导人们过去的行为,更不能用当前的法律处罚人们过去从事的当时是合法而当前是违法的行为。该原则是各国法律中通行的一项基本原则。例如,美国1787年《宪法》规定,追溯既往的法律不得通过。《法国民法典》同样规定,法律仅仅适用于法律通过之后,没有溯及力。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具有绝对性,一般不得减损。仅有的例外是:只有在适用当前的法律对当事人有利时,才可以有条件地针对过去的行为而适用当前颁布的法律,即所谓的“有利追溯”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有利追溯”表现为“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但如果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较轻的,就适用新法。(34) 很显然,由于哈布雷的犯罪行为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而塞内加尔对法律的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发生在2007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新修改的法律只能适用于发生在2007年后的相关犯罪行为,而不能溯及既往地适用于哈布雷所犯罪行。在完成了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后,塞内加尔也意识到存在的问题,于是就发生了2008年对本国宪法的修改行为。但即使如此,考虑到“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重要性和绝对性,并且,国际法也没有一般性地规定该原则不适用于国际犯罪,(35)毫无疑问,塞内加尔为确立自身对哈布雷管辖权的修法行为违背了该原则。这也是米谢乐·尤戈戈巴尼亚在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哈布雷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诉塞内加尔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原因,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在其判决中也曾经支持了哈布雷的诉求。 2.违背了生效终审裁决的“既判力”原则。所谓生效终审裁决的“既判力”原则是指法院所作出的具有终审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具有约束力,不得再上诉,也不得被改判。就哈布雷案而言,当塞内加尔最高上诉法院于2001年3月20日裁决驳回受害者的上诉,确认本国对此案无管辖权之时,该裁决由于系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当然就具有“既判力”。这也意味着,再通过塞内加尔国内法院系统重启对哈布雷案的审理将有违国内法治的要求,不具有可能性。因此,当塞内加尔后来于2007年、2008年完成对本国相关法律的修改,准备行使针对哈布雷案的管辖权之时,其相应行为就构成了对2001年最高上诉法院终审裁决“既判力”的违背。在哈布雷向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起诉塞内加尔案中,哈布雷所指控塞内加尔违背终审裁决“既判力”的诉求同样获得法院的支持,原因正在于此。 塞内加尔在“既判力”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一开始就为非盟所关注。在2006年通过的第127(Ⅶ)号决议中,非盟在授权塞内加尔审理哈布雷案的同时,还强调“相应审判应由一合格法庭进行”。所谓的合格法庭,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在哈布雷诉塞内加尔案中作出了非常正确的解释:即应在一个严格的、特设的、具有国际性的法庭框架内进行。因为只有通过国际法庭的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塞内加尔最高上诉法院裁决的“既判力”效力所带来的困境。虽然最终成立的国际法庭更像是塞内加尔国内法院的一个分庭,但无论如何,至少在形式上,该法庭的设立有效地解决了塞内加尔最高上诉法院终审裁定的“既判力”所带来的困境。 因此,从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冲突的视角来看,一方面,在国际法治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塞内加尔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不仅修改了本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而且,还修改了本国的宪法,突破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限制。但即便如此,其在履行国际法律义务方面依然备受“苛责”:这其中既包括来自于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敦促,也包括自来于联合国国际法院判决败诉和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败诉判决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国内法治方面,塞内加尔自始至终秉承着“一贯性”的立场:维持自身最高终审法院裁决的“既判力”效力。虽然其中有波折,例如,试图通过修改本国法律来达到重新审理的目的,但最终还是寻求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解决途径:通过自身能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控制的国际法庭来审理。从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的平衡角度来看,国际法庭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一个适当机制。 (三)国际法的碎片化与统一适用间的矛盾 国际法的碎片化是国际社会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其含义主要有三个:不同国际法部门在适用中存在冲突,不同国际法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以及不同国际法庭在适用同样的国际法规则、裁决同一个案件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解释与适用实践,从而导致结果的不统一。(36)从不同国际法庭的角度来看:由于国际法所适用的国际社会是平行结构,不同于国内法所适用的国内社会的垂直结构,不同国际法庭彼此间都是独立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因此,不同国际法庭在适用同样规则的时候,由于彼此之间不存在着协调的关系,需要根据自身对国际法的理解来适用,在不同法庭有着不同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解释和适用结果出现差异就是必然的。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法院之间,在“塔迪奇案”、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波黑诉塞尔维亚“《灭种罪公约》适用案”中,就曾经发生过围绕“处于国家控制和支配关系”问题的不同裁决实践。(37) 在哈布雷案中,不同机构,包括国际司法机构和人权机构,在面对同一个案件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实践;即使是同一机构,如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也在不同情势下作出不同反应。因此,本案所引发出的国际法碎片化问题无疑值得特别关注。总体来看,国际法的碎片化在本案中主要表现在: 1.人权机构的不同反应。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之间。禁止酷刑委员会对本案的介入主要表现在:(1)塞内加尔总统于2001年要求哈布雷离开本国之时。2001年4月18日,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22条的规定,苏拉马尼等多名受害者向禁止酷刑委员会递交“来文”,指控塞内加尔有关哈布雷的行为构成了对《禁止酷刑公约》第5(2)条和第7条义务的违背,并因此而给他们带来了伤害。接到此来文后,根据自身程序规则,禁止酷刑委员会给予了介入,指示了临时措施,要求塞内加尔不要将哈布雷驱逐出本国,也不要让哈布雷自己离开本国,除非有国家提出了引渡要求。(38)显然,禁止酷刑委员会此时的介入是出于确保相关程序的继续进行,以及基本的程序正义的目的。(2)根据上述来文,禁止酷刑委员会于2006年5月16日作出结论性意见,认定塞内加尔的行为构成了对公约第5(2)条和第7条所承担义务的违背。 人权高专的介入则是在塞内加尔准备将哈布雷遣返回乍得前后。在塞内加尔作出相关决定而尚未执行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即警告称,考虑到哈布雷被引渡回乍得可能遭受的酷刑等风险,塞内加尔作为《禁止酷刑公约》当事国,有必要重新评估自身所作出的决定。(39)在塞内加尔决定暂停之后,相关决定受到了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言人的肯定和欢迎,认为这对于保证哈布雷受到公平审理很重要。与此同时,其还强调,塞内加尔应尽快启动针对哈布雷的检诉程序,或将其引渡给愿意对其进行公平审理的国家。(40) 禁止酷刑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基于公约所应履行的义务,而人权高专优先关注的是作为被告的哈布雷的个人人权保护。无论是国家履行义务还是作为被告的哈布雷的人权保护,二者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一方面,国家要履行自身义务以实现国际正义;另一方面,正义的实现也应该是建立在公开、公平和透明的基础之上的。正义不应该以绝对牺牲被告个人人权的方式来实现。 2.不同司法机构的不同裁决。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国际法院、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之间。除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基于技术原因(即缺乏管辖权)而没有作出相应裁决外,其他两个司法机构都作出了实体性裁决。 国际法院2012年的裁决不仅对哈布雷案的发展影响明显,还对其他国际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哈布雷案对国内影响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塞内加尔最终同意设立特别非洲分庭;从对其他国际机构的影响来看,主要指国际法院有关《禁止酷刑公约》的解释所产生的影响。国际法院在判决中明确裁决塞内加尔违背了其基于《禁止酷刑公约》第6(2)条和第7(1)条所承担的义务。其中,国际法院有关《禁止酷刑公约》第6(2)条即“应立即对事实进行初步调查”的相关解释,以及有关塞内加尔违背了此义务的裁决,相对于人权机构(包括禁止酷刑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法庭而言,极为重要并具有创新性,会对这些机构尤其是禁止酷刑委员会今后相关实践产生影响。 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的两次介入均是建立在哈布雷本人启动诉讼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哈布雷个人人权的关注自然就成为其重点审查的内容。无论是有关塞内加尔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裁决,还是有关塞内加尔违背自身终审裁决“既判力”原则的裁决,都是由此法院作出的。由于塞内加尔对上述两原则的违背确实是哈布雷案整体进展中的重大问题与缺陷,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的上述裁决无疑特别重要。 3.同一法院前后不同“基点”的裁决,这主要体现在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前后所作的两份不同判决上。在第一份判决中,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支持了哈布雷的诉求,裁决塞内加尔的相关行为构成了对哈布雷个人人权的侵犯,本判决的“基点”显然是维护和尊重哈布雷所享有的人权;但在第二份判决中,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转而支持了塞内加尔和非盟为终结“有罪不罚”现象所作出的努力,以不同国际法庭彼此之间是平等的、不存在隶属关系为由,裁定自身对本案无管辖权。本案的裁决理由虽然具有技术性,但显而易见,法院以一种默契的方式选择了与塞内加尔和非盟站在一起,事实上起到了“站台”的效果。因此,其“基点”是终结“有罪不罚”现象。 上述三个方面尽管均体现了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由于不同机构在作出相关决定时的“基点”不同,致力于维护的利益不同,有的强调的是国际法治,保护的是普遍的人权,如国际法院和禁止酷刑委员会;有的则强调的是国内法治,保护的是作为被告的哈布雷的个人人权。而无论是普遍性的人权还是被告的人权,都需要在国内法和国际法这两个不同层面得到保护。因此,尽管国际法的统一适用有其必要性,但在国际法所适用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水平”而非“垂直”的状态下,每个不同的国际机构,保护人权机构和司法机构,都有各自独立的管辖范围,都必须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国际法在适用的过程中的碎片化也并非完全是不好的现象,其既有利于不同机构充分发挥各自作用,也有利于在不同的价值冲突间维持适度平衡。而当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不同机构之间也会有适度协调。例如,在本案中,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的第二份判决即考虑到了其他国际机构已有的裁决。 三 结论 通过前述介绍和评论可以看出,哈布雷案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方面,还是在国际法的发展与挑战方面,都带来了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哈布雷案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国际社会对终结“有罪不罚”立场的变化,尤其是非洲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启示。在冷战期间,囿于意识形态对抗等原因,犯有国际法上的罪行而未被有效惩治即“有罪不罚”的现象,一再出现。冷战结束之后,为终结此种现象、保护人权,确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尤其是基于犯有严重国际犯罪者应确保获得审判的理念,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设立之后,特别是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建立起来之后,终结“有罪不罚”的口号被提出并一再强调,迄今已获得了充分的国际共识。(41)而要真正实现终结“有罪不罚”,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各国不仅要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在国际层面追诉国际犯罪分子,而且也要在国家层面积极合作。而就国家层面的合作而言,就需要在管辖权的确立和行使上持积极的立场,实现各国在管辖权上“无缝对接”,只有这样,才能让犯罪分子无处可逃。在此共识的基础上,传统上作为补充性的普遍管辖权(包括普遍刑事管辖权和普遍民事管辖权)获得了快速发展。(42) 在哈布雷案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欧盟还是非盟,都在普遍管辖权问题上采取了较积极的立场,尤其是非盟。为了防止欧洲等国家借助于普遍管辖权来“肆意”地干涉非洲事务,确保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自己主导和处理,更是通过了《非盟有关针对国际犯罪确立和行使普遍管辖权的示范国家法(草案)》,鼓励所有非洲国家确立并积极行使针对四种严重国际犯罪的管辖权。哈布雷作为一位曾经的国家元首,因其所犯罪行,在逃避追责长达20余年之后被成功追责,这本身便凸显了非洲国家在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给国际追责带来的积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可以反映出,国际社会正越来越致力于国际法治的强化和监督机制的建设。 由于“有罪不罚”的重要对象往往是在任或曾任的国家高官,甚至是在任或曾任的国家元首,而针对他们罪责的清算,往往既会给国家间关系带来困扰,也会给国际法中既存的国家豁免制度等方面带来挑战。因此,很多时候,追究高官的罪责并不容易。但从哈布雷案中,至少可以得出两个重要启示:(1)只有相关国家愿意放弃本国所享有的豁免,如像乍得那样,那么,通过国家层面追究罪责就会变得容易和方便,只要其他相关国家愿意积极行使普遍管辖权——如像比利时那样,通过积极地行使普遍管辖权,反复不断地给塞内加尔施加国际压力,最终促使各方寻找到了对哈布雷进行追责的适当方案——那么,终结“有罪不罚”现象才有成功的可能。(2)建立针对特定个案的国际法庭,如像塞内加尔和非盟设立特别非洲分庭那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际法院在刚果诉比利时“逮捕令案”中的相关论述,国家豁免是不能对抗国际法庭的。因此,通过设立特定的国际法庭来追责,可以有效地解决因国家层面追责所面临的豁免法律难题。 从国际法的发展与挑战的角度来看,哈布雷案所带来的启示在于:(1)国家应善意并及时履行自身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塞内加尔之所以在国际法院败诉,以及遭受到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批评,主要原因在于其作为《禁止酷刑公约》当事国,没有履行“及时启动调查程序”义务,以及履行“或引渡或起诉”义务。而无论是履行“及时启动调查程序”义务还是履行“或引渡或起诉”义务,都要求其首先完善本国的相关国内立法。没有根据公约规定及时完善本国的相关国内法,就无法履行上述义务中的任何一项。(2)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适当平衡问题。在国际社会通过多种途径向塞内加尔施压,意图实现国际法治的过程中,塞内加尔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还是来源于本国国内法治所“制造”的两个难题:“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终审裁决的既判力”问题。如果无法在二者之间找到适当平衡,或者试图减损任何一方面,最终结果要么将损害塞内加尔的国内法治,要么将减损国际社会终结“有罪不罚”的努力。就此意义而言,在尊重国内法治的基础上追求和实现国际法治,应该是国际社会急需从本案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不顾及一国国内法治的实际而拼命向一国施加压力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也是应该避免的。 前南刑庭副庭长刘大群法官和国际法院薛捍勤法官曾对本文初稿提出过若干修改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文章错误由作者本人承担。 ①非洲保护人权大会主席阿利翁·梯纳(Alioune Tine)语,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hS0I7GSJth31VN0ELsuM2TOfMICA?docId=CNG.4fe0cb53fa3afbb412c2a959ae285e36.8f1&hl=en,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2月8日。 ②《乍得前总统于塞内加尔被捕被指曾杀4万政治犯》,http://news.qq.com/a/20130701/000522.htm,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0日。 ③根据该法案,比利时拥有对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灭种罪的普遍管辖权。 ④本部分有关哈布雷案的相关信息主要来自联合国国际法院2012年7月20日就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或引渡或起诉义务问题案”判决,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2010年11月18日和2013年11月5日的判决,禁止酷刑委员会2006年的有关决议,非盟2006年的决议,以及世界人权运动联盟等有关哈布雷案的资料等。关于国际法院相关判决,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4/17064.pdf,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0日;西非经济共同体判决,http://www.courtecowas.org/site2012/index.php?option=com-content&view=article&id=219:hisseinhabrevrepublicofsenegal2013&catid=26:judgments-2013&Itemid=90,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1日;禁止酷刑委员会决议,http://www.unhchr.ch/tbs/doc.nsf/0/aafdd8e81a424894c125718c004490f6?Opendocument,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1日;非盟决议,http://www.au.int/en/sites/default/files/ASSEMBLY_FR_01_JULY_03_JULY_2006_AUC_SEVENTH_ORDINARY_SESSION_DECISIONS_DECLARATIONS.pdf,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7日;世界人权运动联盟的相关资料,FIDH:Chronology of the Hissène Habré Case,网络链接:http:/www.fidh.org/en/africa/Chad/Hissene-Habre-Case/chronology-of-the-hissene-habre-case-9776,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7日。 ⑤See Assembly/AU/Dec.103(Ⅵ),http://au.int/en/sites/default/files/ASSEMBLY_EN_23_24_JANUARY_2006_AUC_%20SIXTH%20_ORDINARY_SESSION_DECISIONS_DECLARATIONS.pdf(last visited Oct.25,2014). ⑥See Doc.Assembly/AU/3(Ⅶ),August 2,2006. ⑦See the case of Hissène Habré,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impunity in Africa adopted on 16 March 2006,paras.2,12. ⑧该款规定:“每一缔约国也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在下列情况下,该国对此种罪行有管辖权:被控罪犯在该国管辖的任何领土内,而该国不按第8条规定将其引渡至本条第1款所述的任何国家。” ⑨该款规定:“缔约国如在其管辖领土内发现有被控犯有第4条所述任何罪行的人,在第5条所指的情况下,如不进行引渡,则应将该案提交主管当局以便起诉。” ⑩See CAT/C/36/D/181/2001,19 May 2006,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Download.aspx?symbolno=CAT%2fC%2f36%2fD%2f181%2f2001&Lang=en(last visited Dec.15,2015). (11)通过对本国法律的这一修改,塞内加尔确立了对这些罪行的普遍管辖权。 (12)“重新”审理的含义是:由于塞内加尔最高上诉法院已于2001年判决驳回了受害者的上诉,在法律上,哈布雷案已经审理完结,成为了“定案”,在法理上不存在“重新”审理之说。 (13)See Michelot Yogogombaye v.Senegal,Judgmnent(15 Dec.2009),Appl.No 1/2008,ACTHPR,http://www.worldcourtscom/acthpr/eng/decisions/2009.12.15_Yogogombaye_v_Senegal.htm(last visited Dec.15,2015). (14)裁决的“既判力”是指已经生效的具有终审性质的裁决的效力是确定的,不应再被推翻。 (15)See http://www.courtecowas.org/site2012/pdf_files/decisions/judgements/2010/HISSEIN_HABRE_v_REPUBLIQUE_DU_SENEGAL.pdf(last visited Nov.2,2014). (16)参见非盟大会2011年1月31日决议:Decision Assembly/AU/Dec.340(ⅩⅥ)。 (17)参见新华网相关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12/c_12870356.htm,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1月20日。 (18)此部分的内容参见维基百科有关哈布雷的相关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s%C3%A8ne_Habr%C3%A9,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6日。 (19)之所以称为“特别非洲分庭”,是因为尽管该法庭具有国际性,却设立在塞内加尔本国法院内,法官由塞内加尔司法部长提名,法庭预审分庭的法官由塞内加尔法官组成,检诉分庭的法官同样来自于塞内加尔。关于分庭特点的介绍,http://www.trial-ch-org/en/resources/tribunals/hybrid-tribunals/extraordinary-african-chambers/main-features-of-the-extraordinary-chamber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0月24日。 (20)See Hissein Habre c.Republic of Senegal,Judgment,ECW/CCJ/APP/11/13,http://www.courtecowas.org/site2012/pdf_files/decisions/judgements/2013/HISSEIN%20HABRE_c-REPUBLIC_OF_SENEGAL2013.pdf(last visited Dec 15,2015). (21)See Chad Refuses Cooperation in Habre Case,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410211636.html(last visited Dec.15,2015). (22)See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Obligation to Prosecute or Extradite(Belgium v.Senegal),ICJ Judgment of 20 July 2012,paras.25-32. (23)See Assembly/AU/Dec.103(Ⅵ),http://www.au.int/en/sites/default/files/ASSEMBLY_EN_23_24_JANUARY_2006_AUC_%20SIXTH%20_ORDINARY_SESSION_DECISIONS_DECLARATIONS.pdf(last visited Dec.18,2014). (24)See Michelot Yogogombaye v.Senegal,Appl.No.1/2008,ACtHPR,Judgment(15 Dec.2009),para 22.http://www.worldcourts.com/acthpr/eng/decisions/2009.12.15_Yogogombaye_v_Senegal.htm(last visited Dec.15,2015). (25)参见德斯蒙德·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江红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6)参见新华网相关报道:http://news.qq.com/a/20060127/001209.htm,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2月19日。 (27)See Anne Bodley & Sousena Kebede Tefera,"The Extraordinary Role of the Extraordinary African Chambers Convened to Try former Chadian Leader Hissène Habré",https://www.academia.edu/5410029/THE_EXTRAORDINARY_ROLE_OF_THE_EXTRAORDINARY_AFRICAN_CHAMBERS_CONVENED_TOTRY_FORMER_CHADIAN_LEADER_HISS%C3%88NE_HABR%C3%89(last visited Feb.10,2015). (28)See Final Communique,13[th] ECOWAS-EU Ministerial Troika Meeting,Luxembourg,28 April 2008,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r/100203.pdf(last visited Feb.11,2015). (29)See Assembly/AU/Dec.199(Ⅺ),Assembly/AU/Dec.213(Ⅻ),Assembly/AU/Dec.233(ⅩⅢ),and Assembly/AU/Dec.292(ⅩⅤ),Assembly AU/Dec.335(ⅩⅤⅠ). (30)参见联合国大会文件:A/63/237。 (31)See African Union(Draft)Model National Law on Universal Jurisdiction over International Crimes,EXP/MIN/Legal/VI,http://legal.au.int/en/sites/default/files/MODEL%20LAW%20FINAL-EN_0.pdf(last visited Dec.15,2015). (32)其他国家不认同的证据主要体现在:对于积极主张并践行纯粹普遍管辖权的两个国家即西班牙和比利时,后来都迫于国际压力而先修改了本国相关立法,对自身行为进行了“自我约束”。关于此方面的更多分析,参见宋杰:《国际法中普遍性法律利益的保护问题研究——基于国际法庭和国家相关实践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175页。 (33)引渡义务也不能履行的原因是:在没有确立管辖权的背景下,针对比利时的引渡请求,塞内加尔缺乏采取相应行动的国内管辖权基础,因而无权以比利时所指控的犯罪为名来临时逮捕哈布雷并将其引渡给比利时接受审理。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35)国际法仅规定,国际犯罪不适用任何有关法定时效的规定。除部分条约、部分国际性法庭和部分国家规定或认可了部分国际刑法公约具有溯及力外,多数公约都强调其不具有溯及力。更有学者主张,不溯及既往原则已经成为了习惯国际法规则。《世界人权宣言》第11(2)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1)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2(7)条等都规定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部分相关材料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etroactive_law,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3月24日。 (36)Se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Reports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Finilized by Martti Koskenniemi,A/CN.4/L 682,pp.10-20. (37)See Militarv and Pu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Nicaragu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erits,Judgment,I.C.J.Reports 1986,paras.114-116; ICTY,Case No.:1T-94-1-A,Judgment of 15 July 1999,pp.35-75;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Bosnia and Herzegovina v.Serbia and Montenegro),Judgment,I.C.J.Reports 2007,paras.402-412. (38)See CAT/C/36/D/181/2001,paras.1.1-1.3,http://www.claiminghumanrights.org/fileadmin/redaktion/PDF/CAT_181_2001_Guengueng_et_al_vs_Senegal_en.pdf(last visited Feb.15,2015). (39)See Pillay:Senegal must review its decision to extradite Hissène Habré to Chad,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1217&LangID=E(last visited Feb.16,2015). (40)See Spokes person for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11233&LangID=E(last visited Feb.16,2015). (41)有关防治“有罪不罚”运动的相关信息,参见两个相关网站:http://endimpunity.com/和http://endimpunity.org/。《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序言也规定,“对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不能听之任之不予处罚,为有效惩治罪犯,必须通过国家一级采取措施并加强国际合作”,缔约国“决心使上述犯罪的罪犯不再逍遥法外,从而有助于预防这种犯罪”。 (42)有关普遍管辖权发展的相关描述,参见宋杰:《国际法中普遍性法律利益的保护问题研究》,第147—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