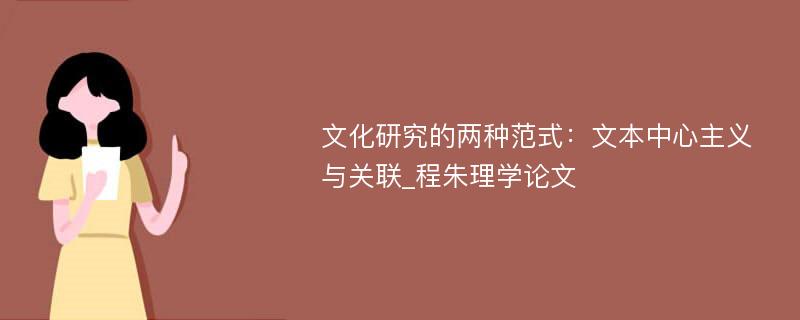
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文本中心论与相关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两种论文,相关性论文,文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本中心论: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
传统文化研究范式,可以称之为“文本中心论”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中心取向,就是研究者把作者意图和价值观放在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主张意义为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赋予。在中外历史上,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可以说由来已久。
西方思想史上的“作者权力”概念,就是“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的典型体现。据卡瓦拉罗的研究,“作者”源于拉丁文动词“augere”,意思是“使生长”(to make grow)或“生产”(to produce)。同时,它又与权威和权威行动联系在一起。因此,作者的身份,也就同时意味着自由和约束两种力量。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品被称为“经典作品”,而它们的作者则被称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等等。赫希(E.D.Hirsch)的观点就集中地体现了“作者权力”的概念。对赫希来说,作者的意义乃是由一些纯粹的、坚固的、“自我同一”的东西构成的,它们可以无可怀疑地用以维系作品。既然作者的意义是作者自己的,因而就不应该受到读者的偷袭或侵入。文本的意义不应该被社会化,不应该被变为形形色色的读者的公有财产;它们完全属于作者自己,就是作者死后也应该有支配这一财产的唯一权利。①
在西方传统中,意义往往被视为是内在于“经典作品”中的,是文本固有的特质。艾布拉姆斯说,宗教经典“由被赋予决定权的教会权威建立;由拥有宗教裁判权的权力机构去实施”,“它所指涉的书,意义是明确的;(内容)是封闭的,既不允许删减也不许添加。”②正因如此,经典作品被视为提供了指导的思想宝库、可供选择的行为典范,一个引发可能问题和可能答案的发源地。它们有待于人们怀着敬畏之心去吸取和体会,而其作者则是文化的代表、权威和监护人。正如巴尔特所说,西方文化过高地估计了作者这一角色的价值,把他们看做是“父亲”或“上帝”,有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一样,他们不仅独自负责作品的创造,而且完全掌握着作品的意义。③“这数世纪以来,我们对作者感兴趣太甚,对读者则一点儿也不注意……作者被视为其作品的永久的主人,余下我们这些人,他的读者,则纯粹被看作是只拥有用益权的人。此系统显然隐含着一个权限主题:认为作者具有某种君临读者之上的权利,他强迫读者接受作品内某种特定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真实的意义:由此产生了一种权利意义的批评伦理,人们力求确立作者所意谓者,毫不顾及读者所理解者。”④艾布拉姆斯也说,“一个作者一旦被牢固地确立为经典作家,他就会显示出强大的抵抗力,以抵御受到反面责难和变化不定的文学偏好的颠覆。”⑤他以诗人雪莱为例说明这一点。尽管新批评理论家极力攻击雪莱,但这种批评反而吸引了人们对这位诗人的注意力,从而进一步维护了他的经典地位。
欧洲中世纪的人在阅读手抄本的时候,通常都是大声地、像唱歌似地拉长声集体朗读。这不是对话,读者如同朝圣者,沿着文字走向文本中所包藏的真理。“文字是迷宫,几乎就像是画家画出来的圣像,没有标点符号,你无法同它争论,只能诠释。”⑥罗素在谈到中世纪的经典崇拜现象时说,“中世纪的怪事之一就是:人们虽有独创性而不自知。所有党派都假借好古的或拟古的议论来证明其策略的正确性。皇帝在德意志则引据查理曼时代的封建原则;在意大利则引据罗马法和古代皇帝们的权柄。伦巴底诸城更远溯到共和时代的罗马制度。教皇派则部分以伪造的君士坦丁的赠与,部分以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扫罗与撒母耳的关系,作为其权力的根据。经院哲学家不是引据圣经就是先引据柏拉图然后再引据亚里斯多德;当他们有所创造时,也试图把真相隐蔽起来。”⑦科尔巴斯(E.D.Kolbas)也指出:“经典作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模仿和再生产的源泉,任何这类作品的必然特征将是其时间上的永久保存和文化上的广泛知名度。”⑧
值得一提的是,“文本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不单存在于传统西方社会。在中国传统社会,对经典的崇奉和迷信,甚至到了唯经是从,唯经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说法,“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仔细求索之耳。”⑨圣人的言论可以说句句都是真理,经典中不可能存在谬误,所谓“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⑩因此,对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则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11)对经典的这种态度就有点近于迷信了。为了准确理解经典的“微言大义”,注解经典的“训传之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而注解经典的各种“传”、“注”也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言语理解的障碍。所以,要准确理解经典,就必须准确理解那些羽翼经典的传注;要准确理解传注,又必须对那些传注进行传注。如此不断的循环解释,不能不造成浩繁无数的注经群籍这一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文化景观。早在汉代,注经之言已经十分烦琐,“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12)甚至出现了“一经说至百万余言”(13)的经师。另一方面,为了绝对保证对经典的原样接受,背诵这种接受与阅读经典的方式,便无论如何不可缺少了。许衡在论到读经之法时说:“讲究经旨,须是将正本反复诵读,求圣人立言指意,务于经内自有得。若反复诵读,至于二三十遍,以至于五六十遍,求其意义不得,然后以古注证之。古经训释不明,未可通晓,方考诸家解义,择其当者,取一家之说以为定论,不可泛泛莫知所适从也。”(14)意义是经典所固有的,“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所以,应当怀着敬畏之心、认认真真地从文本中挖掘精奥义理。如罗钦顺所说,“有志于学者,必须熟读精思,将一个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翻来覆去,体认穷究,方寻得道理出,从上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5)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厥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16)如果解读者不懂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大义,并非圣人未说清楚,更不是圣人有意要把“义理”据为私有、秘而不宣,而是解读者没有“积诚研精”、其所见未到火候的缘故。
近代以来,传统经典文本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权威性被“启蒙”话语所消解,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消除这个着魔的世界,取缔神话,破除迷信,用知识代替幻想。然而,启蒙运动并未否定任何东西的神圣性、权威性,而仅仅以“启蒙”话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取代了传统经典话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从而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自己的产物。”(17)启蒙运动本身所提倡的知识、理性等原则本身,已经一步步地陷入神话之中。“启蒙”反对神话、迷信的过程,也是与之同流合污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深刻地揭露了“启蒙”变成“神话”的辩证法。然而,吊诡的是,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也未破除文本的神圣性,其研究范式,也仍然是一种文本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在他们那里,文本尤其是严肃、高雅文本依然受到“敬畏”。阿多诺对音乐的分析就显示了这一点。如吉安德隆(Bernard Gendron)所说,“阿多诺的立场预设了音乐文本的本质主义概念。正如我们所展现的,他似乎以为人们能客观地或历史地分析任何音乐文本的内核和外表结构。”(18)阿多诺关注音乐文本本义并试图从音乐文本固有特质上区分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比如,在贝多芬作品等严肃音乐文本中,“细节实际上包含着整体并且导致了整体的呈现,与此同时,细节也是从整体的概念中生发而出的。”而在流行音乐文本中,“关系却是偶然的。细节与整体没有关系,它显示为一种外在的结构。”(19)
二、文本意义:作者生产或读者生产
在当代,文本中心论研究范式不断地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巴尔特认为,一个文本并非释放了一个唯一“神圣的”或作者即“上帝”的意义的语词系列,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共存。文本的意义乃是读者解释的结果,而不是作者意图的产物,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大批重要的符号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释。写作的真正位置乃在于阅读,读者的诞生不得不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20)反之,“作者之死”让读者诞生,使读者能进入被作者所禁闭的文本空间,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生产具有参与权,他们也是文本的写作者。福柯也将作者身份历史化了,他强调作者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由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所限定的一个概念。(21)海德格尔则认为,主体性并非一个给定之物,而是一个不间断的生产过程。世界是我们的投射物,是我们创造了它,但我们也受这个世界支配:我们被抛入或投入存在,到了一个未经我们选择的时间和空间。“此在”(Dasein)是一种存在形式,它既无固定的性质,也非理所当然,它必须不断地被创造。而理解则是此在的构成因素之一,此在借它获得生命力,成为可能性。海德格尔从自身的基本哲学观点出发,将解释视为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自明、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22)
解释学表明,人决不会生活于真空中,在他有自我意识或反思意识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属于这个世界。因此,他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的。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和思想状况、物质条件、他所从属的民族的心理结构等等,这一切是他一旦存在于世即已具有并注定为他所有的东西,是自始至终都在影响他、形成他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不同的“视界”对应于不同的“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固然都有各自的视界,但理解并不是抛弃自己的视界而置身于异己的视界。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界就进入他要理解的那个视界,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我们的视界是同过去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地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界与传统视界不断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称之为“视界融合”。“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23)对于伽达默尔而言,所有解释都取决于具体语境,由特定文化的那些具体历史相对性标准所形成并受其制约的,并无所谓可能“如其所是”地认识文本。一切解释都是生产性的;理解总是“别有所解”(understanding otherwise),亦即去实现文本中新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意义从未被其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传递到另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中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演绎出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时代的读者预见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声称忠于经典、唯经典是从的人,事实上也不可能过滤掉他自己的“成见”,从而“如其所是”地按照所谓“原旨”来解读经典。主张对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则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的朱熹,就未能实现按“原旨”解读经典的意图。冯友兰曾一针见血地以西方君主立宪制下被架空了的“君主”与握有实权的“内阁总理”,来比喻《四书》原著与朱注《四书》之间的巨大鸿隙。他说,在朱熹注释的《四书》变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后,“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只是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24)
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即使是被确定为经典之后的程朱理学文本,也没有被后人按“原旨”解读。比如,在极力倡导“存天理,灭人欲”、“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朱熹祖籍新安(徽州),以厚利为追求目标的徽商,却以程朱理学为尊崇对象。如《茗洲吴氏家典》所说:“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若孙也。”(25)徽州“自朱子后,多明义理之学”。(26)“自宋元以来,理学阐明,道系相传,如世次可辍”。“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27)清代各地徽州会馆中“崇祀朱子”,而现存徽州族谱中都收入朱子的《家礼》。这些也是徽商尊崇朱子的明证。因此,可以说,尊崇理学是宋元以来徽州社会的普遍心理特征,理学构成了徽州特殊的人文环境。
显然,程朱理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追求实用功利的商人意识形态,并非徽商群体“如其所是”地对文本进行解读的结果,而是徽商群体和程朱理学文本之间“视界融合”或“妥协阅读”的产物。通过“视界融合”或“妥协阅读”,程朱理学文本中不利于徽商群体的内容被“忽略”,而与徽商群体的生活具有相关性的或有利于徽商的内容,则被“弘扬光大”。徽商群体与程朱理学文本的这种“视界融合”不是同一或均化,而只是部分重叠,它包含着差异和交互作用。如唐力行所说,“徽商整合理学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从其研究理学的方法来看,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大多数不是致力于理学的系统研究,而是从理学中撷取某些章句、格言,立竿见影地服务于商业”。“众多的徽商从不同的侧面,环绕着理欲之辩这个问题,以群体的力量改铸着理学,将其整合为徽商的经济利益服务,并能体现其价值观及审美情趣的徽州商人文化。”(28)因此,程朱理学文本的复杂意义不是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其文本间隙,使徽商群体得以从中产生符合自身需要的新文本。徽商文化的生产和流通,既依赖于程朱理学文本提供的意义和空白,又依赖于徽商群体积极的参与和创造。就像真正的对话一样,在徽商群体和程朱理学文本之间进行的解释学谈话包含着平等和积极的相互作用。它预先设定谈话双方都考虑同一个主题、一个共同的问题,双方正就这个问题进行谈话,因为对话总是有关某些事情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平等和积极的解释学谈话过程中,徽商群体成了把程朱理学的过去传递到当前的传递者,也就是说,徽商群体对程朱理学的理解在本质上是把程朱理学的意义置入当前的一种调解或翻译。
这就充分地表明,对经典文本纯粹客观的阅读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在最严格的“客观分析”中,似乎也不可能根除某种解释性的成分,因而也就不可能根除主观性的因素。因此,如伊格尔顿所说,截然区分“文本所意谓的”与“文本对我所意谓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对于《麦克白斯》在它的时代的文化环境中可能意义的解释仍然是我的解释,这一解释必然受到我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参考框架的影响。我绝不能用我的鞋带把自己从这一切中提起来,从而以某种绝对客观的方式来了解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心中实际所想的是什么。任何一种有关这样的绝对客观性的观念都是幻想。”(29)事实上,作者的意图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它就像任何其他文本一样,可以加以争辩、翻译并进行不同的解释。
三、文化研究的新范式:“相关性”
在传统文化研究文本中心论范式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一种以葛兰西式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新文化研究范式,即“相关性”研究范式。这种新研究范式超越了对一个文本的本义(meaning of a text)的兴趣,而转向集中关注一个文本可能产生的意义范围。“葛兰西式”文化研究,从未真正对一个文化文本的本义即作为某种本质性的、被嵌入和被保证的东西感兴趣过。文本的意义潜能只有在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才能被激活,而文本只有进入了读者的日常生活而被阅读时才能产生社会关系。“文化研究通常更多地关注文化文本的诸多意义,也就是它们的社会意义,它们如何被挪用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被使用:作为归属(ascription)的意义而不是作为刻录(inscription)的意义。”(30)在“葛兰西式”文化研究那里,意义从来就不是明确的,而通常是地方性的,取决于语境的。因此,“相关性标准”研究范式并不把作者的意图和价值观放在文本结构的中心位置,并不关注文本内部的文本特质,而是把研究重心置于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相关的切入点上。
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已经显现了葛兰西式文化研究之“相关性”范式的端倪。霍尔认为,信息的发送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照单全收。在传播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编码(信息的构成),还是解码(信息被阅读和理解),都有其特殊形态和对之施以制约的特殊条件。编码和解码之间并无给定的一致性,某一信息可以由不同读者以不同方式解码。霍尔解码理论表明,由于编码者和解码者采用的符码不一样,文本意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读者对文本的完全认同或完全不认同都不容易发生,更多的是一种在文本和具有确定社会性的观众之间的妥协阅读。在后来的“接合理论”中,霍尔进一步提出,“文本”如果与其他语境发生关联,其表明的东西就完全是不同的。如斯道雷所述,在霍尔那里,“文本”并非是发布意义的来源,“而是意义的言说——变化的意义——得以产生的场所。由于‘文本’是‘多声部’的,所以,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语境中,出于不同的政治需求,就会以不同的‘声部’言说。在这种方式下,于是意义以及更为广义的文化领域就总是调停和冲突的场所,一个霸权或许胜利或许失败的竞技场。”(31)在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不会包含或提出它们本身的、固有的、单一的和内在的意义,因此意义仅仅通过语言来转换。意义是一种社会生产、一种实践。世界必须由人们生产出来意义,语言和符号化(symbolization)是意义生产的工具。“因为意义不再依赖于‘事物如何成为’而是依赖于事物如何被表意,这会导致,如我们所提到的,同样的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意。既然表意是一种实践,而且‘实践’被定义为‘一定的原材料转换为一定的产品的过程,这种转换受到一定的人类劳动、一定的(生产)生产工具的影响’,那么,这也会导致表意与一定形式的劳动——一种具体的劳动有关,在这里,就是意义生产劳动。”(32)
既然葛兰西式文化研究关注“整体生活方式”,便不可能脱离日常社会生活而仅仅将“文本”本身作为中心研究对象。伯明翰中心第三任主任里查德·约翰生就曾指出,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要消解‘文本’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心。‘文本’不再由于自身的缘故而受到研究,也不是由于它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而是为了它实现和使其成为可能的主体或文化形式。文本在文化形式中只是一个手段;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原材料,由此形成特定的形式(如叙事、意识形态问题框架、表达方式、主体位置等)可以抽象出来。它也可能构成一个更大的话语领域的一部分,或在其他空间里有规律地出现的形式的综合。但是,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文本,而是在每一个流通时刻的主体形式的社会生活,包括它们的文本体现。”(33)斯道雷也认为,文本的意义“不能从生产因素(把意义、快感、意识形态效果、合作、抵制多方面地定位在生产目的和方式或生产本身中)被读出,这些生产因素对于作为‘使用中生产’的文化消费来说仅仅是语境方面,最终是在‘使用中生产’中,意义、快感、意识形态效果、合作或抵制问题才能被(可能性地)决定。”(34)当我们在解读一个文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女性的、酷儿的、后殖民主义的或者后马克思主义的阅读视角来阐述,从而得出不同的意义。从一个特别的、对于解读实践的批判视角出发,我们有时含蓄有时明确地承认所讨论的文本一直是被表达的或被用来表达的。社会性别的认同也是符号具有多义性的例子。比如,男性气质有其存在的(生理的)客观条件,然而有不同的方式来表征男性气质并使其具有不同的意义。赋予男性气质以意义的不同方式并不是语义学的简单游戏,而是争夺可以被视为“正常”的东西的权力斗争的重要部分,把某种东西看做是“正常的”本身就是意义政治学的一个例证,即企图把具备多种含义的东西制造成似乎只有一种解释的东西。这就证明了“批判性的分析所关注的并不是‘文本’的意义,即作为‘单一的’、‘本质的’和确保无疑的意义。探寻某事的真正意义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应该把批判的眼光集中在特殊的意义是怎样获得它们的权威和权力的。”(35)
“葛兰西式”文化研究的“相关性”范式,在费斯克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费斯克认为,从文本结构中,人们看不出它们在社会情景中会如何被使用,也因此无法由文本的分析中得知。同样地,文本中的某些意义也不会从文本的分析里显露出来。“因为它们是在文本阅读者的社会情景交集的刹那所产生,而在这样的交集中,读者可能为意义的生产过程带进了无法预期的、与文本无关的因素。”(36)如果文本的意义仅仅是语境中的、暂存的,那么,事物的意义就绝不会是固定的、最终的或真理性的、本质性的。这样,文本就既不是解释的中心,也不是解释的开端。恰恰相反,“认识物质条件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阐明解释对象的前提,而且也是解释过程本身的开端。”(37)
一些传统美学家认为,一件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主要在于它是否具有一种高品级的艺术特质或审美特质。而一种经验之所以是审美的,就是因为经验的对象具有一种客观的审美特质,没有这种客观特质,也就无所谓审美经验。传统美学的评价范式,就是典型的文本中心论的评价范式。因此,传统美学需要的是批评家—牧师,去控制意义以及对文本的反应,它要求的是正式的教育程序,以教导人们如何欣赏“伟大的”艺术。而实际上,传统美学仅仅是一套规训系统,是资产阶级控制文化经济的企图,就像它控制金融经济一样。“美学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权,而大众的辨识力正是对这种霸权的拒绝。”(38)
事实上,文本意义的生产和流通总是在权力结构中进行的,被这种结构认可并判定为“高雅”的文本往往隶属于权力结构的上层,而被判定为“低俗”、“粗俗”的文本则处于权力结构的下层。费斯克声称自己不是文学本质论的主张者,他所关注的只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文学被教导和流通的方式。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差异之处,在于它们在社会中的运作方式的不同,而不在于文本本身的差别。费斯克说,“解读文本是件复杂的工作,而大众文本的复杂性既在于它的使用方式,也在于它的内在结构。文本意义所赖以存在的复杂密集的关系网,是社会的而不是文本的,是由读者而不是文本作者创造出来的。当读者的社会体验与文本的话语结构遭遇时,读者的创造行为便得以发生。”(39)
有些评论家从文本的固有特质出发,认为,莎士比亚作品曾经属于大众文化,但如今不再是了。他们虽然描述了事实,但由此得出20世纪的大众趣味比17世纪的大众趣味低俗的结论,却完全是错误的。实际上,恰恰是那些评论家活动其中的文学体制,赋予了莎士比亚作品以“正确的”意义,使它们成为高雅艺术,把它们限制在昂贵的或是矫揉造作的剧院中,更有甚者,把它们变成了研究的主题,其结果是,那些对莎士比亚文本解读得好的人可以得到高分,因而被认为是比那些解读得不够“深刻”的人更聪明、更优秀的个人。当一种文本被用来辨别不同的个人,并训练人们接受一个特定阶级的思维与感受的习惯时,它怎么可能成为大众文本呢?就像布尔迪厄《区隔》(Distinction)一书的书名所呈示的,文化的功能在于区别不同阶级和阶级群体,并将这些区隔在美学或是趣味的普遍价值中加以定位,籍此伪装这些区隔的社会性质。“‘高雅’艺术的难度和复杂性首先被用来建立它相对于‘低俗’或浅白艺术的美学优越性,然后,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符合这些高雅趣味的人(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所具有的趣味(或品质)是优雅的。以此为中心的批评工业发展起来,旨在强调(如果尚不能称为创造)高雅艺术的复杂性,从而在可以欣赏和不能欣赏高雅艺术的人之间划出伪装的却是令人满意的区隔。艺术的复杂性其实是阶级差别:难度是一扇文化的单向旋转门,只接受买对了票的人,而排斥大众。”(40)
正因如此,费斯克把文化批评的评价工作定位于社会的或政治的,而不是文本的或美学的。“批评者试图探索与评价文本中相关性的社会政治效力。批评者所关心的是文本做了什么,或被用来做什么,而非文本是什么(虽然,它是什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可以被用来做什么)。”意义是在具体社会处境下文本与阅读者之间的联系中产生的。寄寓在文本中的相关性标准仅仅是一种潜力,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特质。相关性是由每一个特殊的解读时刻所决定和激发的特质,解读是通过读者将一个理解框架(如认知模型,世界观等)加诸文本而发生的,是读者通过建构文本的意义“体验”了该文本。尽管批评者可能鉴别出形成这种潜力的文本特征,也可能假设或预言这种潜力被激发的方式,但这种预言并不必然会成为现实。这首先是因为相关性不是由文本单方面生产的,它总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总是意味着一种历史性和情景性,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生,并随着大众日常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我在阅读文本的时候,不能不研究作为阅读者的我自己,因为文本只有当我以特定的方式阅读它时,只有当我真正使用它提供给我的资源时,文本才成为文本。“而此时的‘我’并非个人主义的‘我’,而是一个话语领域:‘我’是一个竞技场,在那里,我的社会生活的诸种话语贯穿并构成了‘我’,也是在那里,这些话语在阅读实践中,被带来而与文本的话语资源发生关系。这些话语资源也许会限制我可能创造出来的意义,但是,他们无法限制日常的创造性。这些话语资源正是被推送给日常的创造性,而且事实上,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些话语资源正是由日常的创造性所界定的。”(41)如果承认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承认读者的有效活跃的意识会随场景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意义就是流动不居的,文本自身的表现形式及其所激发的反应之间并无所谓固定不变的联系,今天相关的艺术,明天也许就变得无关紧要,今天不相关的艺术,将来也可能变得相关。而追求“永恒的”、“伟大的”艺术的“美学”恰恰拒绝承认大众文化的短暂性。
其次,也是因为相关性要求意义的多元性与相对性,拒绝封闭性、绝对性和普遍性,相关性意味着多样性。一个文本要成为读者的文本,就必须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语境中,对于各式各样的读者具有相关点。“相关性是被读者发现或生产出来的;相关性是文化经济中一些特定的时刻和生产过程,使得文本不再仅仅是金融经济中的商品。因此,大众的辨识力并不作用在文本之间或者文本内部的文本特质层面上,而是旨在识别和筛选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相关的切入点。”(42)阅读就是创作,它承载着个人化的词语,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时间赋予它们意义、相关性和生命。如果承认大众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是变化的,那么就要承认社会差异必然产生出文化差异,这就意味着无论读者分属于多少不同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文本可以提供或至少可以提供相应的切入点。不同的阅读者对同一文本的含义的阐释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文本的含义会由拥有不同社会体验的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腔调说出来。即使是同一个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也可能是多元的,经常是矛盾的,这是因为个体读者要么属于很多不同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要么在这些社会效忠从属关系之间来回摆动。简言之,解读就是翻译,就是根据“个人词典”来阅读文本,它意味着一种多元化、动态化和个性化的过程。
正因如此,文本要在范围广大的读者中流行,“就必须在一个极具危险性的支点上维持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它的众多对抗力量之间的平衡:误读《豪门恩怨》以发现其中对父权资本主义的批判,或误读《囚犯》以发现对机构权力的冷漠无情的暴露。”(43)无论《豪门恩怨》在金融经济中是怎样一种商品,在文化经济领域,它是一个丰富而未定的资源银行,它为全世界众多的观众提供了广大的相关性领域,既提供支持资本主义或父权制的意义,也提供反对资本主义或父权制的意义,观众可以从中选择,并且将之烹调为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意涵。费斯克还援引埃科的话说,文本能够和广告一样生产出不妥协的社会相关意义,这种意义甚至可以具有一种革命性色彩:“讯息从资源中发射出来,到达各种社会学情境中,在那里,不同的符码在不同的情境中运作。对一位米兰银行职员来说,电视播映的冰箱广告代表了一种购买的刺激力,但是,对于一个卡拉布里亚的失业农民来说,这同样的图像言说的是一个不属于他的繁荣世界,一个他必须去征服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贫困国家,电视广告的功能是传达一种革命讯息。”(44)这就充分地表明,相关性是意义的核心,读者的快感在于感受和探索文本与日常生活的相关点,以便从日常生活体验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
四、余论
与注重文本的“固有特质”、把作者意图和价值观放在文本结构中心位置的“文本中心论”传统文化研究范式不同,以葛兰西式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新文化研究提出了“相关性”新范式,主张意义不是文本的固有特质而是被读者发现并生产出来的,读者所关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一个文本只有进入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其意义潜能才能被激活,无论读者分属于多少不同的社会效忠从属关系,文本可以提供或至少有潜力提供相应的切入点。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标志着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以往过于注重文本分析转向注重阅读者的文化实践。
但另一方面,“相关性”文化研究范式,也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或贬低了文本本身的意义,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麦克盖根所说,由于仅仅关注在我们的社会中文本被教导和流通的方式,过分重视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并否认文本自身属性,“相关性”这种研究范式,已经制造了一场“质量判断危机”,它意味着“好”和“坏”的绝对主义判断标准已经丧失。比如,在“相关性”研究范式中,先锋文本、“高雅”艺术常常被简单地视为一种承载区隔功能的东西而弃置一旁,“‘高雅’艺术的难度和复杂性首先被用来建立它相对于‘低俗’或浅白艺术的美学优越性……艺术的复杂性其实是阶级差别:难度是一扇文化的单向旋转门,只接受买对了票的人,而排斥大众。”(45)先锋艺术与大众艺术的差异,仅仅被归结为它们的社会运作方式不同,而不在于文本本身的差别。对先锋文本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多少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如凯尔纳所说,其结果是“牺牲了对于所有文化形式的可能洞见,并复制了对于文化领域的二元划分——‘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它只是倒转了比较陈旧的高/低区分的积极/消极的价值评价而已)。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文化研究脱离了发展与‘历史先锋派’相联系的对抗性文化形式的尝试,像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等先锋派运动,意欲发展出能够改革社会,提供不同于文化霸权形式的另类选择的艺术。”(46)
注释:
①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②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影印本)2004年版,p.29.
③(21)[英]参见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④[法]罗兰·巴尔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⑤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影印本)2004年版,p.30.
⑥[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⑦[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23页。
⑧E.D.Kolbas,“The Contemporary Canon Debate”.载王晓路等编著《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⑨⑩(11)朱熹:《朱子语类》卷11、19、19。
(12)桓谭:《新论·正经》。
(13)《汉书·儒林传》。
(14)许衡:《鲁斋遗书》卷1。
(15)罗钦顺:《困知记》卷3。
(16)晁说之:《晁氏客语》。
(17)[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18)[美]伯尔纳·吉安德隆:《阿多诺遭遇凯迪拉克》,陈祥勤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4页。
(19)Theodor W.Adorno,"On Popular Music",in John Storey,(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2nd edn,Hemel Hempstead:Prentice Hall,1998,p.200.
(20)See L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the author',in Image,Music,Text,Glasgow:Fontana,1977.
(21)[英]参见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2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4页。
(23)[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页。
(2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25)转引自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26)乾隆《绩溪县志》,卷三,《学校》。
(27)万历《休宁县志·重修休宁县志序》。
(28)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29)[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30)(34)[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和磊译,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91页。
(31)约翰·斯道雷:《英国的文化研究》,王晓路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2)[英]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媒介研究中被压抑者的回归》,[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8页。
(33)[英]里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陈永国译,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35)[英]约翰·斯道雷:《霸权和大众媒体的象征权力》,关涛译,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36)[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等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版,第209页。已将原译文中不符合大陆习惯的“产制”一词,改为“生产”。
(37)John Fiske,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A Study of the Culture of Homelessness,in Eungjun Min,(ed.) Reading the Homeless Culture:The Media's Image of Homeless Culture,Westport:Greenwood Pub Group,1999,p.1.
(38)(39)(40)(41)(42)(45)[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148、147、72、156、147页。
(43)John Fiske,Television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pp.321-322.
(44)[美]转引自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See U.Eco,Travels in Hyperreality,London:Picador,1986,p.141.
(46)[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接合》,陶东风译,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