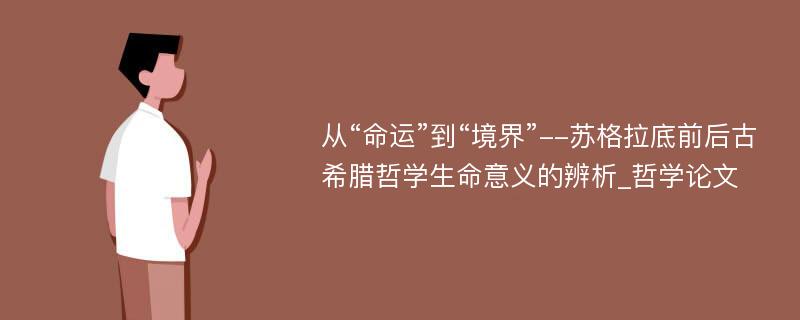
从“命运”到“境界”——苏格拉底前后古希腊哲学命意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格拉底论文,命意论文,古希腊论文,境界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命运:悲剧时代希腊哲学的主题
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哥拉以至德谟克利特,所谓古希腊哲学的前苏格拉底时期,正是希腊悲剧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那里达到鼎盛的时期。称这一时期为希腊的悲剧时代是贴切的,然而悲剧时代的哲学是否也曾有过足够动人心魂的悲剧情怀呢?尼采写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书,但他所作的与正统的哲学史家意致略异的探索,也许对高卓的智慧的诉求更多些,而问题却在于沉重得多的生命的寻问。
泰勒斯是第一个断言万物有其“始基”的人,他认为这始基是“水”。一切从“水”生出,一切又复归于“水”,“始基”在这里获得的是万物之起始同时即是万物之归宿的意趣。“水”对“始基”说来显然并不那么配称:“水”带着智慧的瞩望从泰勒斯那里流出来,“水”又会随着泰勒斯的感性的生命流过去,但“始基”的观念却长久得多地留存了下来。这里重要得多的不在于“水”或另一种什么东西对于万物的“宗”、“元”(“始基”)地位的提撕,而在于“始基”观念本身所意味的一种致思向度的开抉。泰勒斯是无愧于“哲学之父”的殊誉的,“始基”表征着一种可堪以“哲学”相称的运思从此真正开始。
然而,“始基”在一个未必预期过的时代所由生发的契机会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 页)这个在此后一直被学人奉为圭臬的论断当然可以用来阐释“始基”观念的发生,但所谓“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不也可以用来解说种种科学概念的萌发么?可见“惊异”即使可作为哲学致思的某种必要情境,却也不必是哲学之思所以为哲学之思的真正契机。正像黑格尔从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命题中体味出“以‘一’为真实,乃是哲学的看法”(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 187页)一样,尼采窥破了同一命题的“一切是一”的底蕴。不过,在 黑格尔那里,吸引他的全部问题只在于“说水是原则的这种哲学究竟到了甚么样的思辨程度”(同上书,第182页); 尼采虽然说了“一切是一”作为“一个形而上学信念,其根源深藏在某种神秘直觉之中”之类的话(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8页),但人们并不能从中捕捉到任何关于“始基”之思的缘起的更明确的消息,而且他似乎也轻忽了这一点,即泰勒斯作为第一个参透“一切是一”的理致的人,也是“第一个肯定灵魂不死的人”(《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页)。
一个确信“灵魂不死”的人,终于酝酿出了“一切是一”的“始基”观念,那隐帅或驱动着古希腊第一位哲人的心灵的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也许正是那早在荷马时代就已经相当典型而在后来又不断催发了希腊悲剧作家的灵感的“命运”。“命运”是默无声息的,它在“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断制中的寓托只在于默默而势所必至地从“水”中流出,又默默而势所必至地流归于“水”。诚然,从幸存的记述泰勒斯思想的片断文字中,寻取“命运”感对哲人的追逼的线索是件困难的事,但没有疑问的是,从泰勒斯那里接过了哲学圣火的阿那克西曼德曾明确地把“始基”关联于“命运”。他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同上书,第7页。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有趣的是,这段话的意味差不多与整个希腊悲剧所内蕴的精神相契:淹贯于剧情的“命运”,固然是所有希腊悲剧赖以为悲剧的终极依凭,而发于“始基”之思的所谓“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则恰合着使悲剧得以错综铺陈的又一深不可拔的信念——“报应”。
把“水”作为万物的“始基”,这可能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只是一种智慧的错觉,但由命运感带出的“始基”观念依然寓托着他的得自整个希腊民族的命运感。在他那里同在泰勒斯那里一样,对自然宇宙之谜的探究同时即是对人的命运之谜的索解,或者更确切地说,无论是他的老师泰勒斯,还是他,都只是因着对人的命运的发问才在哲学而非科学的意义上——尽管这在引出哲学后果的同时也会引出科学后果——引发了对自然宇宙的究竟的发问。他用不再能诉诸直观的“无限(者)”取代了“水”,于是新的哲学命题便成了这样:“‘无限’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和原素”(同上书,第7页)。但“无限”毕竟太飘忽了些, 它确乎与人的命运或宇宙大化示于人的那种神秘相称应,然而哲学的品格却在于从神秘中走出时同神秘保持足够的张力。于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同道或学生阿那克西美尼再一次匡正了始基的设定,他说:“万物的始基是无限的空气”(同上书,第11页)。“无限”的属性被保留下来了,“空气”的可感而无形的品质使它被确定为“始基”时比“水”虚灵而又比“无限(者)”可凭,这至少更能满足那有着深重的命运感的希腊人崇实而不滞濡的心理。同相期于“命运”的揭秘一致,哲学在它的滥觞期是负着浓重得多的宗教情愫的,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都不否认神的存在,他们或者认为被肯定为始基的“无限”或“空气”就是神灵,或者认为遍在的神灵总不外于始基而为始基所笼罩。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他们都是古希腊伊奥尼亚的米利都人,因此这一最初的哲学流派又被称为米利都学派——对于“始基”的设定,一开始就隐含着某种富于诗意的内在纠葛:“始基”的被指谓在于它的恒久而确定,其本身不增不减因而无所谓生灭;“始基”的被指谓又在于它的流转而变化,它只是由于这一点才可能化生万物创造世界。在后来的希腊哲人那里,这隐含其中的两种勉可称做规定性的东西以深刻而不无偏执的方式强化了,以巴门尼德学说为中核的所谓爱利亚学派独钟于前者,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则更看重后者。但无论是巴门尼德,还是赫拉克利特,其学思的命意无不牵系着世界而人生的命运。
据说古希腊人的家或家族中总要设一火的祭台,柴薪相续的长燃圣火关系着一家一族的生机和运会。(参看古朗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版,第12页)赫拉克利特以“火”为万物的“始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古人崇火意识的启示不得而知,但“火”在他那里对有着一定节奏的“流转”、“变化”的承担,本身也表达着一种无从规避的命运。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火产生了一切,一切都复归于火。一切都服从命运。”“神就是永恒的流转着的火,命运就是那循着相反的途程创生万物的‘逻各斯’。”(《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17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所谓“逻各斯”,诚然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被动创生中的世界的某种秩序、规律或必然性,但这如此轻蔑人的意愿、好恶、欣求的秩序、规律或必然性,对人说来不就是那未可抗拒的命运么?赫拉克利特断言:“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同上书,第21页)其实,这“火”的“燃烧”或“熄灭”的“分寸”感,也正是哲人所真切把握到的那份世界和人生的“命运”感。同阿那克西曼德一样,他甚至也从“命运”说到了“报应”,不过他用的是另一种表述:“一切变成火,火烧上来执行审判和处罚。”(同上书,第25页)
在赫拉克利特的“活火”赋予可感世界以灵魂却又使这瞬息都在流转的世界变得几乎无法认识之后,巴门尼德以他的决绝的“存在”差不多宣布了这可感世界不再有认识的必要。同古希腊早期的许多哲学家一样,巴门尼德的主要话题仍在于“论自然”,但“自然”在他那里终究被他的“存在”逻辑排斥在所谓唯一真实存在的“存在”之外。唯有“存在”存在着,“非存在”不可能存在。“存在”是不生育的“一”,它并不生出“一切”来,它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显示一种信念或逻辑上的绝对真实,以映衬那可感的世俗世界的虚假。也许从价值意味上,“存在”的被设定更好理解些;黑格尔曾写下如下的一段话,但他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它:在苏格拉底的学生克贝斯的有关记述中,“‘一个巴门尼德式的生活’在习惯语里已被用来表示一种道德的生活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63页)但即使在价值意味上领会“存在”,“存在”也决不带有能够为人启示某种自律原则的性质,它始终为“命运”所拴缚。巴门尼德指出,“存在永远是同一的,居留在自身之内,并且永远固定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强大的必然性把它局限在这个锁链之内”。同时他又说:“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把它固定在那不可分割而且不动的实体上。”(《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3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毋庸赘释,这里所说的“必然性”的“锁链”即是“命运”,而“命运”亦即是“必然性”的“锁链”,正像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一样,它们是同义语。
巴门尼德的“存在”没有经验世界的依托,但当这“存在”在想象中被描述为“从中心到每一方面距离都相等”的“一个滚圆的球体”(同上书,第53页)时,人们会极自然地想到它同数学世界的关联和它所由产生的毕达哥拉斯学说背景。毕达哥拉斯是比米利都哲学家略晚却比巴门尼德大约早出一代之久的哲人,他和他的学派以认可“数学的始基就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同上书,第37页),在古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独树一帜。这个学派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他们对“数”的神秘关注,其实调动他们全副心力的是远不如“数”的演推那么清晰的“命运”。亚非洛第西亚的亚历山大在他的《哲学家的师承》中说,他在那些关于毕达哥拉斯的回忆录中发现了如下思想:“万物的始基是‘一元’。从‘一元’产生出‘二元’,‘二元’是从属于‘一元’的不定的质料,‘一元’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元’与不定的‘二元’中产生出各种数目……”(同上书,第34页)对于作为万物始基的“一元”,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派都不曾有更具体的诠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确认:“一切都服从命运,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同上书,第35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在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之后,哲学一度从“活火”的永恒燃烧与“存在”的寂然不动的对峙中觅求新的出路,这期间,最可推许的哲学家是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哲学的“命运”主题依然在延续,并且依然凭借着所谓自然宇宙论的理论外观。
从恩培多克勒开始,世界的构成被认为因着两种不同的因素:质料的因素和形式的因素。恩培多克勒认可的质料因素是火、气、水、土,形式因素则是所谓“爱”和“恨”。“爱”和“恨”似乎已经涉及价值抉择,——文德尔班以为“它表明‘价值’的规定开始引进了自然界的理论”(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1页),——实际上,它们在这里还仅仅意味着倾向不同的两种原始力量:前者是结合的力量,后者是分离的力量。论主显然没有在“元素”(不变的火、气、水、土)和“力量”(引起变化的“爱”和“恨”)间倚轻倚重,古希腊人脱不去的命运感把他引向隐在元素和力量后面的更根本的东西。在他看来,“必然性是一,四种元素是它的质料,恨和爱是形式”(《古希腊罗马哲学》,第74页)。这里的对宇宙自然说来的“一”或所谓“必然性”,也正是对人说来的命运。
与恩培多克勒同时,阿那克萨戈拉沿着几乎相同的路径在命运感的敦促下探向宇宙自然。不过,在“质料”——姑且借用只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才真正被确定的这一范畴——方面,他不像恩培多克勒那样局限于四种元素,而是诉诸形、色、味各不相同的诸多“种子”;在“形式”方面,他所认可的大致相当于恩培多克勒的“爱”和“恨”的因素是“心灵”(“奴斯”,一种意向中的宇宙神经)。据记载,他的著作的开篇写得极富于诗意和涵盖力:“万物都在混沌中,然后有心灵出,对万物加以安排。”(同上书,第65页)这在宇宙论中有着统摄地位的“心灵”似乎很可以理解为自然万物的灵魂的,但阿那克萨戈拉并未让它作价值或意义的承诺。它毋宁只是宇宙自然的“植物神经”,它使宇宙动起来,却绝然不会在如何动的意味上提供任何好恶迎拒之类的价值决断。“心灵”仅仅是必然而无目的的命运的代称,它对因它而有的人像对因它而有的金、石、土、水、植物、动物一样,除开“安排”一个无须追问的秩序外,没有更多的担待。
然而,无论如何,这冰冷、缄默的宇宙“心灵”终是启示了苏格拉底的祈向“美”、“善”、“大”的人的心灵。古希腊悲剧时代的“命运”哲学应该说是由这“心灵”宣告终结的,尽管几乎与此同时,德谟克利特的博大雄浑的原子论体系仍然伴着命运之问的余响。
二、境界:苏格拉底的哲学方向
“一切是一”的运思方式无疑为经由简择、提纯而达到普遍性或抽象性的自然科学方法启迪了决定性的范例,但悲剧时代的古希腊哲学毕竟是哲学而不是科学。这当然不能从泰勒斯以至阿那克萨哥拉对宇宙自然的解释还过分粗糙去理解,因为科学自有科学粗陋的源头,再粗陋的科学依然是科学。把哲学视为一种前科学或科学的准备形态,是科学一元论或所谓科学主义在精神世界的僭妄。问题甚至也不在于那些睿智的米利都人、萨摩斯人、爱非斯人或爱利亚人对自然大化的关注多着眼于宇宙整全,因为纯粹的自然科学并不把宇宙的总体秩序及其生成排除在自己的研索对象之外。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分辨,只是这一分辨才把所谓古希腊的自然宇宙论同种种粗疏的或精细的科学宇宙观察区别开来:在古希腊人的自然宇宙论中渗透着一种科学所没有的“命运”关怀,单是这一份“命运”关怀——人文关怀的一个维度——即可辨出它的确凿的哲学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史家所谓早期古希腊哲学面向“自然”的惯常提法,则未始不可以勘正如下:那些以“自然”为着思话题的哲人所真正经心的是苦苦纠缠着他们的灵思的人的命运。因此,他们的生命情态也未必像后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潇洒,否则德谟克利特便无由弄瞎自己的双眼,而煞似浪漫飘逸的赫拉克利特也不至于被人称为“流泪的哲人”了。
一般说来,古希腊哲学的悲剧时代的结束同普罗泰戈拉的一个著名命题不无关联,这位“智者”派中最负盛名的人物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他用人本身驱走了令人惴惴的“命运 ”,但哲学并没有因此被赋予一种足以与“命运”关怀相比勘的新的使命。
真正的转机开始于苏格拉底。只是因着他,希腊哲学的主题命意才从“命运”转向“境界”。同是起于对人的生命存在的关怀,智慧在“命运”上的投射是外扑的,在“境界”上的觅求则属于心灵之光的反观自照。与哲学在深层意味上的微妙转向相应,希腊悲剧在它的最后一位伟大作家那里出现了把“命运”归结于人物性格的创作趣向。俄国史学家塞尔格叶夫曾品评三位悲剧大师不同的“命运”观念说:“照埃斯库罗斯的看法,命运接近于神性,照索福克勒斯的看法,命运是存在于人类之外的抽象概念;然而,照这第三位雅典伟大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看法,命运就在人自己的身上。欧里庇得斯把命运与人底睥睨一切的激情看成一个东西。”(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325页)这个中肯的评说, 或可用来印证产生于欧里庇得斯创作高峰期的苏格拉底哲学的一般时代背景。
苏格拉底不能满意他的哲学前辈只是把天体描绘成一个环绕大地的漩涡,或把大地设想为一个由空气支持着的广阔的槽,在他看来,探询世界的原因本身即意味着发见世界的目的,不涵寓目的原因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举例说,他之所以坐在雅典的牢房里接受一场凶多吉少的诉讼而不是伺机逃到麦加拉或波奥提亚,不是由于他的肌肉骨胳保证了他现在的坐姿,而是因为他认为“留在这里承受对我的判决是比较好,比较正当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4页)。 他“坐在这里”的原因,不在于他的能弯曲自如的四肢,而是在于他的“比较好”或“比较正当”的价值决断。他相信世界的最后原因里一定有类似的断制,对这“好”或“正当”的选取才是世界的活的灵魂。他曾为阿那克萨哥拉的“心灵”(“奴斯”)所激动,然而他终于失望了,——因为它并不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有着对它支配的世界的“涡旋运动”作“好”或“正当”的导向的使命。苏格拉底的这一重心思或祈想当然是非科学的,它只是表明了在他那里,燃烧着的价值热情如何由自觉到善恶、美丑分辨的人扑向整个世界。
在苏格拉底看来,向着真正的存在寻找最高的“善”也许是把握这个世界的原委的最好方式,但他承认,这“最好的方式的本性我既不能自己发见,又不能从任何旁人学到”。不得已,他选择了“次好的研究原因的方式”。所谓“次好的”方式,犹如人们在日蚀时只是从水或其他同类媒介物中观看日影而不是直视太阳(以免弄瞎眼睛)那样,它不是一往地向外逐求,而是“求援于心灵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寻求存在的真理”。这经由心灵的体认曲折地达致目标的方法在于:“首先假定某种我认为最强有力的原则,然后我肯定,不论是关于原因或关于别的东西的,凡是显得和这原则相合的就是真的;而那和这原则不合的我就看作不是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5 页)苏格拉底正是这样着手界说“美”、“善”是什么的;他的“假定”和“我认为”显然为他的方法平添了几分独断的姿态,但在那观测日蚀的比喻中所涵的索解本然之太阳的衷曲,则提醒我们有理由对这位另辟蹊径的哲人作更大程度的同情理解。
当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所做的是“用心于为事物觅取定义”的工作时,他是对的;但当他同时说“苏格拉底正忙着谈论伦理问题,他遗忘了作一整体的自然世界,却想在伦理问题中求得普遍真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6页)时,至少,他是有欠公允的。苏格拉底并没有“遗忘了作一整体的自然世界”,他只是把自然世界纳入了带着价值意向的人文视野。不过,苏格拉底的运思重心的确是在价值问题——它与“伦理问题”相关却不与“伦理问题”等质或等值——上,他把人的“心灵的最大程度的改善”始终视为他和他的学说的本份。他劝勉人们“留心美德”并不是要人们淡漠“命运”,在他对雅典人所作的“马虻”式的提醒中显然暗含着这样一层理致:人的“命运”并不在人之外,而只在于人能否通过性灵的修养自己措置好自己,自己成全住自己。黑格尔指出这一点是深刻的,他说:“苏格拉底以前的雅典人,是伦理的人,而不是道德的人”,“道德学的意义,就是主体由自己自由地建立起善、伦理、公正等规定”。因此他称“苏格拉底的学说是道地的道德学说”。(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 版,第43、42页)这种不同于一般伦理信条的道德学说是属于“境界”形态的,它指示人们从自身方面而不是脱开人性素养的提升从自己的无可如何处去索解或寻味“命运”。
“伦理”意味着一种秩序,一种有别于法律秩序的秩序。秩序总是客观化在人际关系中的,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维系不像法律关系那样重在对个人的当有“权利”的护持和限制,而是在于对约定俗成的种种行为规范的默然认取。但无论是法制制度,还是伦理规范,都不能替代人的心灵在反观自照中所达到的那种道德、人格的自觉。法律的和伦理的秩序,是人在追求所谓“幸福”——身心需要的相当的满足和由这满足带来的愉悦——价值时所不能或缺的,然而法律和伦理秩序的健全或完善并不能保证每个处在这种秩序下的人的人格的“高尚”。“高尚”是人生的不同于“幸福”价值的另一种基本价值,它的酝酿或求取在于自觉的道德修养。悲剧时代的希腊哲学由“命运”思考所偏重的是人生价值的“幸福”取向,这同当时整个希腊社会的人文精神情态是可以相互说明的。诚然那时也不乏人格高尚的人,但道德意识的真正自觉,亦即把人生的“高尚”价值作为独立的、乃至比“幸福”价值更高的价值从哲学上作一种提撕,则不能不说是肇端于苏格拉底。
人生“幸福”价值的实现,多会伴有功利的创发或致取,心灵的“高尚”却往往是超功利的。苏格拉底确曾说过“德性不出于钱财,钱财以及其他一切公与私的利益都出于德性”(《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页)这样的话,似乎他在强调“德性”重于“利益”的同时也顾及到“德性”可能带来的“利益”效果,其实他不过是借这种措词方式对过分看重钱财、利益的世俗的雅典人作一种德性价值高于一切的提醒。当德性的高尚作为一种独立而根本的价值向度被提出后,它的极纯粹的自律原则可能会使某些相当确定的伦理规范变得无足轻重。这一点,常常因为被误解而为苏格拉底招来种种责难。“说谎”、“欺骗”、“抢劫”、“偷窃”,在通常情形下是不言而喻的非正义或非正当行为,但苏格拉底说,当这些行为发生在敌我对峙的背景下时,它便不再是非正义、非正当的了。而且,即使是在友人之间,苏格拉底认为“说谎”、“欺骗”与“偷窃”等也未必就一定该当受谴责。他举例说:当一位将军处在战役的非常时刻为鼓舞士气而谎称援军即将到来,这“说谎”便是完全可理解的正当行为;当一位父亲瞒着自己生了病而又不肯吃药的孩子,把药放进食物中让孩子吃了,这种“欺骗”也便不能被责备为恶行;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朋友因失望而选择了自杀时,他偷走或是抢走了这位朋友赖以自杀的器具,这类“偷窃”或“抢劫”又何尝不是一种善举?苏格拉底的这些说法很可以被看作是诡谲的机辩的。黑格尔敏锐地发现正是这样的机辩“把一向固定的观念弄得动摇起来”,因此他甚至说,在这里,那一向被普遍认同的东西成了依环境移易的特殊原则,“环境是偶然的——客观的——,换句话说,这里加入了我的兴趣的偶然性。”(《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74、75页)然而, 对理解的入路作如下的变换也许更切近于苏格拉底发论的本怀:重要的不在于行为在通常伦理的意义上被怎样指称,而在于行为主体在采取某一行为时的真实心曲。对于苏格拉底说来,主体向“善”的德性是重要的,从这里看出去,那看似被“弄得动摇起来”的人文而自然的世界自有一个稳固而不无辐射力的重心在。
认可“勇敢”、“节制”、“虔敬”、“正义”……这一切德性属于“灵魂的善”,这在苏格拉底那里同在常人那里并没有两样,苏格拉底的无与伦比的原创性洞见只在于他在常人不再成为问题的地方作了深进一层的追问。使“虔敬”成其为“虔敬”的是什么?使“勇敢”成其为“勇敢”的是什么?使“虔敬”、“勇敢”、“节制”、“正义”这些德性成其为值得称许的德性的完整意义上的“善”是什么?苏格拉底在寻问中试图予以贞定的是“虔敬”、“勇敢”、“节制”、“正义”的标准及作着这些标准的理由的“善”的标准,这期间,他从未离开过亲切的日常经验,也从未执著或牵累于这些经验。他不厌其烦地枚举生动可感的实例,仿佛是在做一种实证性的归纳,但他为“勇敢”、“虔敬”、“节制”、“正义”乃至“善”所作的未尽于言的界说——所谓“定义”——却总是超出经验而同可感的事相保持着离而不断、即之弥远的距离的。他开出了“境界”趋于“高尚”的价值向度,他又因此必须为这境界中人所自觉祈向的“善”、“美”、“大”定出一个有着极致意味的标准。对于这一被提到至高地位的新的价值向度的体认,及对这一向度上的某些价值的标准的把握,有赖于发自生命深处的智慧。理解了这一点,或可说,也才可能理解所谓“美德即知识”的真实命意,也才可能理解堪以“轴心时代”的伟大哲人相称的苏格拉底。
三、两种原子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
古希腊哲学的底蕴在苏格拉底前后从“命运”到“境界”的嬗演,最具典型意趣的例据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差异。同是从“原子”说起的,德谟克利特由原子“旋风式的旋转”所表达的“必然性”原则与整个悲剧时代的“命运”观念相通,伊壁鸠鲁以原子偏斜所喻说的理致却在于“境界”形态的自由意识对命运束缚的冲决。
自称“阿那克萨哥拉年迈时,我不年轻”的德谟克利特是苏格拉底的同代人,但正像他虽然到过雅典却始终在苏格拉底的视野之外那样,苏格拉底的迥异于前贤的哲学取向对于他的自成格局的学说不曾有过任何影响。他的“原子”是万物的“始基”,也是世界得以建构的“元素”;“始基”的观念是一脉相承于泰勒斯以降的诸多哲学家的,“元素”的涵谓可能受启于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因此,把他的原子论视为悲剧时代希腊哲学的顺理成章的殿后者,——因而视为“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可能更妥当些,尽管他已经对伦理学领域有了相当规模的开拓。
不像德谟克利特那样师承于留基波,伊壁鸠鲁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哲人。他早年听过德谟克利特的追随者的讲演,但从德谟克利特学说那里他只是借用了原子论的表述方式。他在后世的许多人那里留下的是一个被委屈了的形象,除开无端的“享乐主义”的名声外,不少哲学家甚至认为他是哲学史上最大的剽窃者:斯多葛派的人们断言,被伊壁鸠鲁当作自己的学说加以宣扬的不过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居勒尼学派的伦理学;西塞罗认定,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大部分是属于德谟克利特的,凡是被他着意修改了的地方,恰好就是他损害和败坏了德谟克利特的地方;乃至近代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也曾这样说:“我们关于这个伟大人物(德谟克利特)所知道的东西,几乎只是伊壁鸠鲁从他那里抄袭来的,而伊壁鸠鲁又往往不能从他那里抄袭到最好的东西。”(《莱布尼茨致德梅佐的信》,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 卷, 第197页)然而,真正说来,伊壁鸠鲁也许是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之后最具卓识的哲学家,他的富有独创性的原子论的主题,是德谟克利特在自己的时代还完全无从理解的人生“境界”意义上的“自由”。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和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哲人马克思是伊壁鸠鲁的真正知音,他们分别在他们不朽的著作《物性论》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对前后两位原子论者的旨趣悬异的思致作了精到而恰切的分辨。
在德谟克利特那里,作为万物始基的“原子”是数目无限、不生不灭、坚实独立而彼此不存在质的差异的物质微粒,它以涡旋的方式永恒运动于“虚空”。万物在这涡旋运动中生成,万物也在这涡旋运动中消散。同巴门尼德的学说相比,原子的不生不灭、不可分割正同所谓“存在”的属性相通,但德谟克利特在肯定原子存在的同时也肯定了在巴门尼德看来的“非存在”的“虚空”,而这则使原子得以运动而不至于像排斥“非存在”的“存在”那样默然静处。然而,无论如何,“必然性”的不容抗拒对于恒动的“原子”和恒静的“存在”并无二致,它为“原子”论和“存在”论涂上的是同样深重的“命运”的底色。
在“质料”的意义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比恩培多克勒的火、气、水、土等四元素和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更富有阐释世界万物生成、变迁的功能;在“形式”的意义上,“原子”则既无须凭借恩培多克勒那种“爱”与“恨”的力量,也无须依托于阿那克萨哥拉那样的“心灵”(“奴斯”),它自己即是自己运动的原因。就“原子”的运动、聚散在于“自因”而言,原子论也可看作是向着米利都学说或爱非斯学说的回复,但“原子”一元论显然是“水”一元论、“无限(者)”一元论、“气”一元论乃至“火”一元论在嬗替中矫治其内在缺陷所可能达到的那种“一切是一”的思致的极限。不过,这里的“自因”还仅仅是非价值自觉的“自然”,在恩培多克勒的“爱”与“恨”和阿那克萨哥拉的“心灵”(“奴斯”)那里多少透露却还不曾酝酿出胚芽的价值自觉的要求,被深深淹埋在“原子”的绝对盲目的“必然”运动中。苏格拉底是离开阿那克萨哥拉的“心灵”(“奴斯”)而诉诸人的价值自觉的心灵的,德谟克利特则离开阿那克萨哥拉的“心灵”(“奴斯”)而以虽然精细却终是茫然无抉择性状的“原子”解释人的心灵(或灵魂)的构成。以“自因”而非“自由”(在价值自觉意义上自作主宰)的“原子”为人的心灵的最后理由,只能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在“必然性”的命定中,人的心灵不“自由”。这个逻辑必至的结论是伦理学中的德谟克利特所不能接受的;他诚然确认“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97页),但他的原子论同他的伦理信念的抵牾却终于搅扰着他的无法安宁的灵魂。
不像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学说那样为沉重的“命运”枷锁所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不过是他所企慕和追求的个体“自由”境界的理由化。“原子”依然被界说为不生不灭、不可分割、坚实、独立而自己运动的物质微粒,但原子除开因重量——这是伊壁鸠鲁而不是德谟克利特赋予原子的规定性——而作直线下落运动外,它也在某一不定的地点和不定的时刻脱离直线而偏斜,并且因此,原子间也便有了排斥或碰撞。这三种运动的关系在于:直线下落是原子的物质性的体现,它以对象化或客观化的方式表达了原子的“质料”规定;脱离直线而偏斜是原子的独立性和坚实性的体现,——如果仅仅是直线下落,原子便毋宁只是被扬弃在直线中的一个没有独立性、也无所谓坚实性的点,——它以对象化或客观化的方式表达了原子的“形式”规定;排斥则是原子两重规定的矛盾和整合的体现,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原子的排斥中,表现在直线下坠中的原子的物质性和表现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7 页)依伊壁鸠鲁的原子视界相衡,德谟克利特把由原子的相互排斥或冲撞所产生的涡旋运动看作是必然性的实现,最要害的失误就在于他在这排斥中只看到了原子的物质性规定,忽视了原子概念中的单一、独立、坚实等“形式”因素。原子运动的自因性原在于每个原子自己使自己运动,而且正因为这样,每个原子在运动中自己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个性,——而这自己运动中的自我肯定即意味着自由(自己是自己的理由)。德谟克利特把原子的个性泯没在必然性的旋风中,这恰恰背离了原子成其为原子的概念,乖违了原子论的本然逻辑。
“偏斜”是原子对德谟克利特那里的命定了的运行轨道的出离,这出离隐含了因原子而生灭的事物得以创造和更新的全部秘密。理解这一点似乎并不困难,但它需要理解者以亲切的生命契入。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道破了那看似诡谲的“偏斜”的真趣,他写道:“若非它们(原子)惯于这样稍为偏斜,它们就会像雨点一样地经过无底的虚空各自往下落,那时候,在原初的物体之间就永不能有冲突,也不会有撞击;这样自然就永远不会创造出什么东西。”(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5页)不过,对于伊壁鸠鲁说来,原子偏斜概念的提出与其说是为了更精当地解释某种宇宙秩序,不如说是在自然的探询之外别有寄意。对于这一点,卢克莱修显然也是深有所悟的,他提示人们说:“如果一切的运动永远是互相联系着的,并且新的运动总是从旧的运动中按一定不变的秩序产生出来,而始基也不以它们的偏离产生出某种运动的新的开端来割断命运的约束,以便使原因不致永远跟着原因而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大地上的生物将从何处得到这自由的意志?”(同上书,第76—77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从“命运”中挣脱出“自由意志”来,是伊壁鸠鲁的近乎寓言式的原子论的慧命所系,它使这位一再被误解因而总是被归置在德谟克利特的巨大身影下的原子论者的自然哲学和伦理哲学得以浑然一体。
的确,因着原子的概念——“质料”规定与“形式”规定非同一地统合——真正成熟于伊壁鸠鲁,这“后苏格拉底”的原子论即使在用于解释自然方面也已经比先前的原子论更具理致的魅力。例如,在关于天体的说明中,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的诠释功能几可谓达到了由德谟克利特所开辟的这一诠释向度的极致。然而有趣的是,伊壁鸠鲁不仅没有为着由此可能赢来的殊誉而陶醉,反而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古希腊哲学的“命运”意识的典型表达是哲学家们对天体的崇拜,这崇拜在伊壁鸠鲁看来正足以破坏人的心灵的宁静,而他的自然哲学的方法在天体学说中的贯彻却只会为传统的天体崇拜提供更令人信服的论证。为了个体自由意识的祈向,他宁肯起而反对这富有喜剧性的逻辑结果。于是,在他那里便有了这样的推论:因为天体的命定的永恒性会扰乱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宁静,一个理所当然的信念便应该是——它们并非是被命定了的永恒。马克思透过伊壁鸠鲁学说的这一深刻矛盾,别具慧心地发见“在天体现象学说里表现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灵魂。”他断定:“他(伊壁鸠鲁)的解释方法的目的在于求自我意识的宁静,而不在于自然知识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41、207页)
“自我意识的宁静”属于一种不假外求的“境界”。德谟克利特并非不希求心灵的宁静,但宛如一个处在“旋风式的旋转”中的原子,他从未脱开过“命运”的引力场。他的学说和他的人生也许正应了他的一句箴言:“大胆是行动的开始,但决定结果的则是命运。”(《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22 页)他一生都在“命运”背景下为破译宇宙之谜而东奔西走;他漫游过许多地方,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但最终,却因着对孜孜以求的知解之途的绝望而自己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鸠鲁的“境界”向往则是彻底的,他完全像是一个他所描绘的那种自作主宰、个性自由的原子;他相信感性是真理的报导者,却终生都在他的雅典的花园过着恬淡的书斋生活。当死神向他呼唤时,他坐进铜盆洗了一个温水澡,喝了一杯醇酒,然后平静地叮嘱他的朋友:要忠实于哲学。
四、结语:哲学的承诺
在古希腊第一批使哲学成其为哲学的人们那里,对宇宙万物的究竟的寻问曾引发过天趣盈盈的动人智慧。这智慧滋养过科学的胚芽,但它并不因此只是作为真正的科学史的史前时期才被回味。科学未始不向着自然追根觅底,但科学却不必像哲学那样带着人的“命运”的困惑以生命投入。古希腊的悲剧所以有万古不灭的魅力,就在于它表达了对于人说来永远亲切却也永远令人肃然的“命运”主题。与此相应,沉潜于希腊悲剧时代哲学的“始基”说、宇宙论的运思神经,乃是一种远非所谓“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所能涵盖的“命运”关切。
悲剧时代的希腊哲学家看似不曾明确提出“人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当泰勒斯说万物产生于“水”而又复归于“水”,或当德谟克利特说万物产生于“原子”而又复归于“原子”时,那作为“始基”的“水”或“原子”中已经包藏了这一问题的预设和解答。赫拉克利特宣称“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其实,对于他说来,那作为万物“命运”的“逻各斯”也正是他沉甸甸地揣在自己心灵深处的人的“命运”。阿那克西曼德在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时可能并不轻松,而从毕达哥拉斯的“一切都服从命运,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一类话中,会心的读者当然听得出人的命运喟叹的弦外之音。诚然在实用的意义上,哲学确实如亚里士多德以至海德格尔所说是“无用”的,但哲学的慧眼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人的“命运”。
苏格拉底为哲学之思开出了另一个向度,他把人对“命运”的执著引向心灵在反观中的“境界”追求。在“境界”中,哲学的提问方式从“人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转换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的价值或意义何在”。对“境界”的看重在苏格拉底以降的古希腊哲人那里显然并不意味着对“命运”的轻觑,但比起悲剧时代的哲学来,问题已经复杂得多。柏拉图甚至也要借第缪求斯(δημiουργοs,造物主)之手创构出一个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宇宙来,但这与悲剧时代全然异趣的宇宙创生是依“理念”而行的,而“理念”则以一种极致的方式为它所对应的宇宙万物贞定其价值或意义。(参看拙文《柏拉图“理念论”辨正》,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5 期)亚里士多德对宇宙的生成不再有太大的兴趣,但他在解释既得世界的秩序或构成时以并不更少于柏拉图的热情申说了把一切事物安排得尽可能完美的所谓宇宙目的。苏格拉底之后的希腊哲学,即使是讲述宇宙论或自然哲学,也都无不最终辐辏于人生价值或意义的认取,“境界”对哲学运思的笼罩必致哲学家们为自然确立某种神秘而又亲和于人的“目的”,——这“目的”看似从自然一以贯之于人,其閟机却总在于由人的价值取向而逆溯至被用来印证于人的自然。
一般说来,东方园地上的哲学果实并不比西方收获得晚,但哲学的自觉——哲学以它独具的价值赢得命名——却是在古希腊人那里着了先鞭。古希腊哲学作为整个西方哲学的源头活水,确然为此后的哲学之思在西方的演历或嬗替厘定了一个独异的方向和格局,但更重要的是,它也为哲学所以为哲学提供了一种非可限止于西方的界说:它当然不至于冷落所谓认识论、方法论或语言分析,但它的终局关切或最后承诺,乃在于人的“命运”与“境界”,在于人的自觉归置中的心灵祈向和生命存在。
标签:哲学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泰勒斯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古希腊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史讲演录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