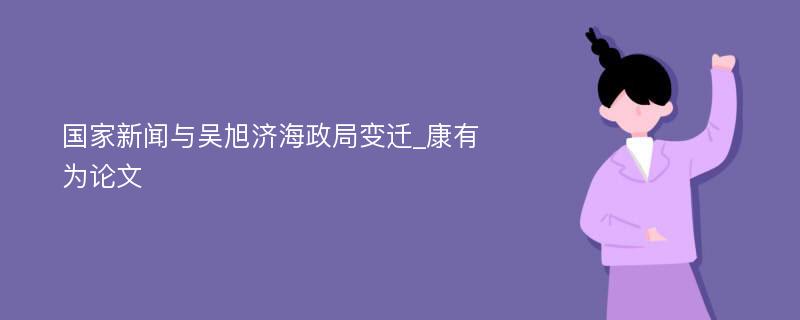
《国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局论文,变动论文,国闻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闻报》是由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初一日在天津创办的维新报刊。该报以宣传变法为职志,意在“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①,自创刊之日起即发表了大量开通明智、呼吁变法的文章,对戊戌变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六日,在清政府和俄国人的双重压力下,《国闻报》为了“保全自主”,被迫“借助外援”②,转让给日本人。《国闻报》的此次转让仅是名义上的,主笔阵容依旧,报道内容受日本人影响较小。戊戌政变后,在清廷的高压之下,《国闻报》再次受到冲击,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二十日彻底卖于日本人,严复、王修植等人离开了报馆③,其报道宗旨和内容也与此前大相径庭。 但从政变发生到彻底卖于日本期间,《国闻报》对当时复杂的时局进行了及时、深入的报道,深刻反映了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面对政变后扑朔迷离的时局,《国闻报》自身的报道策略也几经调整,而每一次调整的背后,都折射出其与清廷关系的疏附离合。目前,学界对《国闻报》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对其在戊戌政变后的报道内容虽有所涉及,但却失之简略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期间《国闻报》的报道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观察戊戌—己亥政局的走向,进而探讨戊戌政变后清廷与趋新士人关系的离合。 一、与“康党”划界靠拢清廷 曾经为戊戌变法大声疾呼的《国闻报》在政变后并没有改变呼吁变法的宗旨,但面对政变之初云谲波诡的复杂时局,《国闻报》并非像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退缩”,“仍然是以显明的态度,对改革派表示同情与支持”,而是适时调整策略,及时表态,与“康党”划清界限,拥护政变后的慈禧太后,将继续变法的希望寄托于清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日政变发生,慈禧太后训政,拿问康有为。随后几天,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徐致靖、张荫桓等人被捕。《国闻报》很快得到消息,并于八月初九日报道了天津政变后的情形。八月初十日,《国闻报》便刊出《恭纪太后训政事》,表达了对时局的态度。该文一反维新变法中紧随康梁、积极报道“康党”变法活动的做法⑤,不点名地批评了“康党”的“结党营私”,指出,当胶州、旅顺、大连“相继沦胥”,皇上力图变法,挽救危局时,“草莽新进之士,闻风而起,众啄雷鸣,一人攘臂,百夫拾决”。然而,这众多附议变法之人,“迹其论事之心”,约分三种。其一“则思以危言悚论劫持朝局,使将来新建之策,新进之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牢笼宙合,志在非常,此一流也”。其二“则流涕上书,苟图富贵,谏书朝上,恩命夕颁,自以为非常之宠遇,夸耀朋侪,光辉门族,升官发财之外,别无他求,此一流也”。其三“则始本愿谨,亦深知瓦缶争鸣,必非久局。而若则以数纸之书,位跻卿贰。若则以一命之士,职掌多财,鸣吠相闻,触喉技痒,遂变初志,希附末光。此又一流也”。显然此中所说的“其一”即指康梁,“其二”、“其三”即为附和康梁者,合三为一即是“康党”。接着文章对上述“三流”提出批评:“嗟乎!若此之流,其为苟便身图,无补国计,深识之士,必辨其微。然而其始也,枢臣侧目,莫敢先言,疆吏咨嗟,但闻咋舌,亦谓苟全名位,遑恤其他。乃未几而礼部六堂一朝去位,枢廷四弼相率登朝。在旧臣则骎骎乎有我躬不阅之忧,而新进则汲汲乎有党羽将成之势。甚者乘机煽乱,离间宫闱,遂使皇上孝治天下之心与皇太后慈爱臣民之念,一家之事,判若两途。植党营私,诡为得失,狗彘之肉,其足食哉!”这里所说的“礼部六堂一朝去位”、“枢廷四弼相率登朝”、“新进”“有党羽将成之势”、“乘机煽乱,离间宫闱”,都是在批评“康党”,且可谓严厉。随后,文章明确表达了对慈禧太后训政的支持:“所幸皇上圣明,于危疑震撼之交,吁请训政。而皇太后垂念时艰,俯如所请。盖致是而谣诼之风得□稍息,皇太后、皇上以孝慈治天下之心,亦庶几大白于天下矣”⑥。从文章的内容可见,《国闻报》的消息非常灵通,在八月初十日已经得到“康党”获罪是因为“乘机煽乱,离间宫闱”的消息。因此,《国闻报》迅速表态,批评“康党”、拥护太后。只要联系维新变法中,《国闻报》曾对康梁的变法活动及时报道、大力支持,并因此被人指为“真康党”⑦,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闻报》政变前后的态度转变。 八月十一日,《国闻报》又以《汪进士呈文》为题,刊登了政变前汪康年关于“康党”奏劾其抗旨不交《时务报》的申明,后附“本馆谨案”。在“本馆谨案”中,《国闻报》明确将戊戌变法中的“康党”与“新党”区别开来,称:“新党议论之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人心之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自汪、梁之狱起,识者已知维新党之厄运将临。咨嗟太息,欲为保全者,颇不乏人。而康党不悟也,怙而不改,遂有今日。独惜新党中多有并非康党中人,而亦横罹其祸者。故先箸录此文,以见新党中又自分党,不能以康党一概相量也。”⑧这里,《国闻报》之所以于政变后亟亟刊登这一呈文,突出汪康年与“康党”政变前的矛盾,意在将包括自身在内的“新党”与“康党”区别开来,“以见新党中又自分党”,从而保护“新党”免受牵连。同一天,在得知荣禄奉旨进京的消息后,《国闻报》再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中堂此行,其庶几与父言慈,与子言孝,使中国臣民外人观听,晓然于皇太后之训政与廷旨之密拿康有为,不过罪康有为一人,而于皇上数月以来维新变法之事,三五新近之臣,均无所妨碍,则中国之幸,即支那皇太后、皇上万寿无疆之福。是所望于社稷之臣矣,此外臣之愿也”⑨。《国闻报》的态度非常明确,既然“康党”获罪已无可挽回,只能与“康党”划清界限,以求自保,并保护其他参与变法之人,继续呼吁推行“维新变法之事”。 八月十三日,《国闻报》刊出《圣躬欠安》消息,称:“日来皇上圣躬殊觉不适,其病症大约是食不消化,因而成痢。皇太后怒御前太监服事(侍)不周,责毙数人,并另派太后处熟悉当差之内监八人,在皇上左右留心伺候。传说如此,未知确否。”⑩其实,皇太后责毙太监并非因为服侍不周。当时流传的说法是,太后杖毙了皇上身边的亲信太监,换上自己的耳目。而《国闻报》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有利于太后的说法,无疑说明政变之初的《国闻报》,并没有与太后为敌,而是在报道中尽量维护训政后的慈禧太后。 然而,清廷并没有像《国闻报》期盼的那样,只罪康有为一人,而是于八月十三日对戊戌“六君子”不审而诛。八月十四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了“康党”罪状:“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并说明朝廷政策,即“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谋逆,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即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11)。清廷除了说明“康党”的罪状外,还有两个重要表态:一是表示余党“概不深究株连”,二是表示新政将“次第推广”。“不深究株连”余党、继续新政,这是政变后无数趋新之士的期盼,清廷的这一表态对于惶恐不安的人心,无疑是一种安抚。 在得到了清廷继续新政的承诺后,《国闻报》遂刊发论说,呼吁变法。《国闻报》连续刊载了《论变法有自然之势》一文,对中国自甲午之后的变法大势进行了总结,指出变法乃甲午战后中国之大势所趋,非某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推动,因此也非某一人力量所能阻遏: 夫天地之运,风气之开,至为奇绝。其一事之将行也,必同时有数人或数十百人不必相谋,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群然以为此事之当行;数十人创之,千万人应之,至于千万人之议论,群以为然,则此事之行大约即在于旦夕。虽阻以绝大之势力,可以暂息,而仍必推行。不见夫大江河之流乎,既有百千万之小水同一方向,并为一流,欲向何处而去,人即欲以筑隄防、造关闸之事,竭力经营,止其流向而必不能阻。其甚者,敌之愈甚,其势愈横,转盛于未阻以前焉。人心之向,初无异是,盖事之或行或止,均积久而形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天也,非人也。支那皇太后、皇帝深知此故,因时制宜,与民更始……不意八月间偶因停止数事之故,中外之人翕然谓支那惟(维)新之机将自此绝。为此言者,可谓不知世变者矣。夫日月往来,一寒一暑,草木荣落,动植蕃变,机缄一发,万不能止,此上帝所定之公理,岂支那而能违哉。吾愿支那之政事家深见此意也。(12) 这里,《国闻报》苦心孤诣,借着清廷继续新政的承诺,大谈变法乃“上帝所定之公理”,势不可遏,“敌之愈甚,其势愈横”,意在讽谏清廷履行诺言,顺应历史潮流,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 二、指责朝政呼吁变法 然而,遗憾的是,清廷随后并没有兑现其八月十四日做出的“概不株连”、继续新政的承诺。继“六君子”被杀之后,不但株连“新党”,而且停废新政。清廷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趋新之士的极大不满。《国闻报》也没有沉默,但其态度的转变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酝酿过程。最初,《国闻报》对新政的停废虽表惋惜,但并没有公然指责朝廷,而是将批评的矛头指向那些巧取奉迎、“揣测希荣”的言官,借此为朝廷开脱,对清廷继续新政仍有所期待。之后,在看到清廷推行新政已无希望的情势下,《国闻报》才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清廷。 就在“六君子”被杀的次日,湖南学政徐仁铸被革职,永不叙用。八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李端棻被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同一天王照被革职,严拿务获。八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下发懿旨,罢免了陈宝箴、陈三立、江标、熊希龄等人的职务,永不叙用(13)。八月二十三日,清廷连下几道谕旨,罢免了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刑部主事张元济,张百熙也因保举康有为使才一事,交吏部严加议处(14)。刘坤一奉旨秘密看管黄遵宪(15)。十月二十一日,翁同龢被革职,永不叙用。 同时,清廷还陆续发布上谕,停罢百日维新中推行的诸多新政。早在八月十一日的上谕中,清廷就宣布复冗官、裁撤《时务官报》、禁止士民上书等。对此,《国闻报》认为这尚不足以阻遏变法之大势,但接下来的上谕却不能不令其沮丧:恢复八股取士、停止经济特科,裁撤农工商总局;禁止各处报馆,严拿抓捕报馆主笔;严禁结会,拿获入会人等,分别治罪(16)。这正是康有为所说的“复八股,禁报馆,捕会社及主笔人,罢经济特科、农工商局,复冗官停漕折,务反其旧。凡昔所经营者,尽皆罢废”(17)。 面对清廷的大肆株连与复旧,《国闻报》及时做出反应。八月二十九日,《国闻报》刊出《经济厄运》,对清廷取消经济特科表示惋惜,认为“支那人向以不得科第为文章厄运,自今而后,又添出一重经济厄运矣”(18)。九月五日,《国闻报》刊出《是何言也》,对八月二十四日恢复八股考试进行评说:“旅京东西各国人于政府办理此事颇为震动,咸思考求其主议之人。嗣探悉规复八股试帖、停止经济科之议,系倡于新简奉天府府丞何乃莹。何府丞于是日呈递封章,力言八股试帖之好处,于三纲五常相关,故政府特从其请。或云此事系中国从八股出身之各大官授意,令何府丞上之。故此折既上,不待详议,即刻奉旨。”(19)《国闻报》委婉地表达了其对废除经济特科、恢复八股的惋惜之情。而对于禁止报馆、捕拿主笔的上谕,《国闻报》并没有表态。而且,在谈及新政停废的责任时,《国闻报》也没有归罪于清廷,而是将之归咎于言官。九月四日,《国闻报》刊出消息,称:“北京访事人来信云,中国政府自杀四卿之后,本无钩稽株连、穷治新党之意,亦并无将皇上数月以来开创百度之事全行反复之意。而都察院各道御史,以为趁此机会,不分青黄皂白,凡有关涉皇上所创行之新政,皆指为康有为之邪说,太后无不力予平反;凡有曾经皇上所赏识之小臣,皆指为康有为之徒党,太后无不严加惩治。我辈从此升官,从此放缺,即可从此发财,利莫大焉。于是今日单衔递一折,明日联名上一章,凡半月以来或革职,或放废,或永不叙用,皆言官之功也;复六衙门,复八股,禁学会,禁报馆,撤农工商局,亦皆言官之功也。然各言官将来之升官发财,其得失未可逆料,而初一日太后之慈训,则已大加申斥。此则所谓求荣反辱,弄巧成拙,北京各言官,其亦可以结舌矣。”(20)九月初五日,《国闻报》再谈言官与株连、复旧的关系:“杨御史(杨崇伊)亦复封章叠上,至再至三,然其立言之宗旨,则大要不外乎诛新党、复旧制,欲尽翻五月以来皇上之所为而已。上月二十八日因呈递封奏得蒙召见……嗣经探悉,杨御史此次封章乃系揭参多人,其所参之人,有京官,有外官,大抵均系平日讲求西学,主议变法之人,其人数多至数十名。政府之意亦不欲与新党人全然为难,惧授外人以口实,故其召见之敕语略谓:‘概不株连之谕,朝廷已再三言之,中外共知,势不能将新党之人,全行诛戮罢斥。若如该御史所奏,欲将讲求西学、主议变法之人一律治罪,则不特国家无此政体,即办理亦有许多为难之处。自今以后,该御史勿复多言。进退黜陟,朝廷自有权衡,毋须再三之渎也’”(21)。诚然,政变后清廷的株连、复旧之举,与言官们的奏劾密切相关。但若将此责任完全归咎于言官,则未免忽视了慈禧太后的决定作用,言官们的言论也只有迎合了慈禧太后的旨意才能奏效。对此,《国闻报》主笔们并非不知,之所以要归咎于言官而为慈禧太后开脱,正是《国闻报》的报道策略。这说明,此时的《国闻报》尚不想与清廷决然对立,仍然对清廷的继续新政有所期待。而此中的关键与《国闻报》上文所提到的“初一日太后之慈训”颇有关系。 所谓的“初一日太后之慈训”,是指九月初一日慈禧太后发布的一道懿旨。该懿旨对言官们的“揣测希荣”进行了批评,并重申了继续新政的旨意: 国家制治保邦,纲常名教,亘古为昭。至于条理损益,随时变通尽利,本无一成之法。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当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应次第推行,不能因噎废食。叠经明降谕旨,剀切宣示,大小臣工当能仰体此意。惟言事诸臣,往往胸无定识,即如谋乱方张之日,内外章奏能灼见先几、防微杜渐者并不多见。迨至事后,或且仰窥意旨,揣测希荣。岂知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执两用中,不偏不倚。用特再为申谕,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精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凡所建白,但期有裨时局,不得妄意揣摩,甚或挟私攻讦,是非所在,亦自难逃洞鉴也。(22) 正当“新党”被株、新政被废的关头,慈禧太后突然发布一道重申继续新政的懿旨,“无论新旧,仍应次第推行,不能因噎废食”,这无疑会让那些期盼新政的趋新之士为之动心。从内容可见,《国闻报》九月初四日对于言官与复旧、株连的报道,正与这道懿旨颇多关联。或许,正是在九月初一日懿旨的鼓舞之下,才有了《国闻报》九月初四日的报道。既然慈禧太后再度表达继续新政的意愿,那么依靠慈禧推行新政无疑是最理想的结果,也是政变后包括《国闻报》在内的多数趋新之士的愿望。因此,《国闻报》有意强调株连、复旧之责在于言官,为慈禧太后开脱,显然是一种策略。九月九日,《国闻报》再申此意:“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清国八月初六日以后,一切反改守旧政策,在皇太后亦尚无成见,皆因各言官陈之于下,而军机大臣刚毅一人主持于上,虽以荣中堂之见信于太后,亦不能与刚毅争执”(23)。如果慈禧太后真无成见,真能按照九月初一日的懿旨推行新政,那么《国闻报》就可以如愿以偿,继续为其开脱到底了。 但此后清廷的作为非但没有继续新政的迹象,而且在言官们的弹劾下,《国闻报》竟成了清政府的眼中钉,清廷甚至命令直隶总督裕禄“设法严禁”《国闻报》。九月十四日,署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准良奏劾《国闻报》,称:“窃以报馆自奉旨停止,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其诽谤时政,诋斥廷臣,较诸往日有加无已,然未有肆逆不法如九月初七日之甚者也。述康逆问答之词,以肆其指斥之意,吠声吠影,丧心病狂,稍具天良,不忍闻述。此即设馆实系洋款,秉笔出自洋人,犹宜念和好邦交,共懍犯上亡等之训。况以中国之人,居中国之地,食中国之食,乃敢以首逆无父无君之言,广为传布乎?应请密饬直隶总督设法严禁。若能出之该管地方官本意作为,一见《国闻》此报即行查办,不敢上渎圣聪,似尤得国体之正。”(24)改归知县庶吉士缪润绂也上奏说:“报馆已有旨令督抚查禁,访拿主笔人,从重惩治……天津之《国闻报》依然邪说横行,假外人为名,实皆华人主笔,康有为在香港问答语一篇,即载于九月初七八两日《国闻报》,有往英求援使皇上出险云云……报馆梗令若此,朝廷尚有何令之可行?无怪谄附洋人者纷纷日众也。”在他看来,“近出之《国闻报》,语言狂谬,诋斥朝政,摇惑人心者,以《劝善歌》跋、康有为问答语二篇为最”,并摘录部分内容,进呈慈禧太后(25)。 这里所说的《劝善歌》跋、康有为问答,分别刊载于《国闻报》九月初六日与初七、初八日。前者是对政变后端方撰写的为清朝歌功颂德之《劝善歌》的批判,称:“《劝善歌》一篇,中国政府以此颁示其国中臣民者也……然吾闻清国家法,其著为律令者,当不止此数端,今果能一一遵守之否?……若乃劝士之法,则曰切莫结党;劝农之法,则曰歉岁有赈;又曰外国税重中国轻,外国物贵中国贱。兹数说者,若不考情实,猝然闻之,亦似切近情理,洞见利害。然于政治得失之故,其道相左,其效相反。守一先生之说,固不足以定天下之是非也。盖士而无党,则导民以散,国必不强……”(26)该文对于端方的巧取奉迎之不满,跃然纸上。但与《国闻报》后来对清廷的责难相比,这一批评并不尖刻,却已令言官们感到不快。后者系《国闻报》照录八月二十三号香港《华字日报》的“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其实,自政变以来,在华的西文报刊及上海《新闻报》等对“康党”言论的刊载可谓连篇累牍,但因《国闻报》对清廷继续新政尚有期待,不愿与清廷决裂,因此对待“康党”的言论也颇为谨慎。该问答是《国闻报》转载的首篇相关言论,且是一篇康有为与记者的谈话。但由于其中对慈禧太后多有微词,因此言官以此弹劾《国闻报》,可谓一发即中。就在准良的弹章奏上的当天,清廷便发布上谕:“内阁学士准良奏,报馆挟洋自重,刊布邪说,丧心指斥,据实密陈一折。据称:报馆奉旨停止,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其诽谤诋斥较诸往日有加无已。九月初七日,述康逆问答之词,尤为肆逆不法等语,自系指天津《国闻报》馆而言。该报馆名为设自洋人,必有内地匪徒,挟洋为重,敢于肆行指斥。著裕禄拣派妥员,密查明确,设法严禁。此等败类,必应拿获惩办,毋得轻纵,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27)。随后,裕禄便开始谋划停办《国闻报》。当《国闻报》的生存成了问题之时,其对清廷继续新政的期待显然已是白日做梦,随后《国闻报》的报道锋芒便直指清廷。 九月二十、二十一日,《国闻报》连续刊出了《论中国禁止报馆事》,对清廷禁止报馆的上谕进行严厉的批评。该文层层推进,深入分析了清廷禁报之因、报馆当存之理以及清廷禁报之恶果,指出:“揆今日中国朝廷禁报之宗旨,其命意所在亦不过恶闻恶言而已。今试问,此恶言也,胡为乎来哉?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明乎庶人之有议,乃由于天下之无道。而孰使天下之无道,则朝廷固不能辞其咎焉。”既然天下之无道,朝廷负有责任,那么报刊作为庶人议政之地,就不能封禁,“吾闻今日东西各国之有报章,犹古者列国之有风诗”(28)。“若中国犹以孔孟为圣贤,则吾报馆固亦犹行风诗创惩之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而为孔孟之所许”。不仅如此,《国闻报》进一步指出,此前的报道往往委婉讽谏,隐讳其词,“自今而后,亦不复隐讳其词,曲为解免,固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盖不如是,则是非之公,终不足以大白于天下”。随后,对清廷禁报之举大加抨击,指出,各通商口岸之西文报纸讥讪中国不留余地,但因为政府诸公不识西文,“固虽熟视而若无睹,倾听而若闻”。作者进一步分析说,华文报纸之所以不像西文报纸那样批评朝政不留余地,原因有二:一是华文报纸,主笔多系华人,国家虽无道,作为臣子,直斥其君父之过,发其隐私,“虽甚愤激不平,其心犹有所不忍”;二是中国政府之权力“御外人虽不足,而欲自贱其民,则瘠牛偾豚,其畏不死,以文字之故,取快一时,而甘自蹈于法网,虽强项骨鲠之夫,其心终有所不敢”。最后,文章指出了清廷禁止报刊的不智之举,必将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的恶果,“揆之中国圣贤立教垂世之义,报馆之不当禁也如此,按之今日中外错处,国权有限,报馆之不能禁也又如彼,若中国朝廷明知其不可而必欲为之,则亦不过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使海内豪杰有志之士,后先疏附于强邻敌国。而强邻敌国亦乐用之,以为指臂之助,独留此昏庸守旧之人,收拾山河,供献他族而已。呜呼!凡吾同洲之人,言念及此,岂不痛哉!”(29) 该文的刊出标志着《国闻报》彻底改变了政变以来靠拢清廷、维护慈禧太后、希冀依靠清廷继续新政的态度,开始与朝廷公然对立。《国闻报》批评的矛头之所以会转向清廷,正是因为清廷“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的结果。清廷禁止报馆的上谕是八月二十四日下发的,《国闻报》在近一个月后才做出回应,这说明《国闻报》的主笔在报道方向的调整上,是经过充分斟酌与考量的。而九月初一日懿旨所透露出的变法意愿,无疑让《国闻报》对清廷的变法再寄希望,但在看到清廷继续新政并无诚意之后,《国闻报》便改变态度,公然与之对立。 之后,《国闻报》又刊发《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30)一文,与清廷禁报馆、抑学堂之举针锋相对,大声疾呼“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在《论中国阅报之风必将大开》一文中,《国闻报》再度批评清廷的“禁报”之举,“号称有教化之国,怎能行野蛮之事”,并指出,自朝廷于八月二十四日颁布禁报之谕后,中国之报纸,印如故,售如故,根本不必担心报纸会因此滞销。而且,西文报刊各通商口岸到处皆是,即使禁止华文报刊,西人议论照样可看可传,“欲掩饰而不能掩饰也”。文中还对清廷屡次言变而不变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今中国朝廷既朝言变法图强,夕言变法图强矣,未有欲变法图强而犹使朝野之人不明内外之势,不同上下之气,以愚民为得计,始终谓报馆不当设,报纸不可阅也”。因此,预言“报馆必将盛,阅报之风必将大开也,是不待智者而后知也”(31)。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二十日,《国闻报》又刊出《论日报本春秋之义》,通过引申春秋之义,说明开报馆的合法性与重要性,指出:“日报之设大足为国家之用也……日报者邦家之光方富,旌赏之不暇,何可目为斯文败类,而概行禁绝也哉?今外国之兴衰强弱,无不视报馆之多寡以为定程,盖凡为国民,既气盛而言宜则为之,国家必迩安而远服。若民既敢怒而不敢言,则其国将由危而即于丧。”(32) 清廷的“禁报”之举令《国闻报》愤怒不已。这种愤怒并不只是出于对自身生存的考虑,更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责任。事实上,此时的《国闻报》已在名义上属于日本。正是借助于日本的保护,严复、夏曾佑等人才能够公然与清廷对抗。也正因如此,清廷的很多复旧之举都成了《国闻报》指责的对象。 《国闻报》刊登《论求治必自广言路始》,对清廷政变后的禁止士民言事上谕提出批评。文章指出:“言路通则治,言路塞则乱……泰西议院之设,中国固不能行,而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之法,洵可复也。国有大事,令公卿以下皆得上书,以广陈言之路……执两用中,惟善是择,如是以言之权,授于下,而用言之权仍操诸上。太阿不致倒持,而上下不忧否塞矣。”(33)该文并以秦史为鉴,指出:“秦之法至暴,不足道,然其并天下也,以能用人言,而其失天下也,以不闻其过,秦固如此,后之有国家者,其可知所鉴矣,亦可知所求矣。” 之后,《国闻报》再度刊发《拟请复开言路书》,进一步呼吁清廷重开言路。这是一封写给朝廷的奏折,名为“奏为时局艰难,群情摇动,请复开言路,以达民隐而固人心”折。作者有鉴于“言路一闭则民隐不能上达,人心不可复收,事关国家大计”,遂“敢昧死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言路开则得人心,言路闭则失人心,这是该奏折反复强调的主旨: 为今日之计,惟有特降纶音,复开言路……若犹不然,臣恐惧罪者联络愈固,抑郁者从逆愈多,冠贼蜂兴,蔓延难灭。语曰:‘涓涓不绝,终成江河,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此民隐不达之可忧者也……立国之本在得乎众,得众之要在结其心。昔大雅有询于刍荛之言,洪范陈谋及庶人之义……盖以人之有心不能无欲,人之有口不能无言。阳以采其言,实阴以结其心也。况夫国家多事之秋,群下危疑之际,人心所向则固,人心所背则倾。是则固结众心,诚为当今急务。今我皇太后皇上以议论纷淆,遂塞言路,以致君民隔膜,上下相疑,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箝天下之口,因以失众庶之心,开塞之间关系甚巨。昔唐臣陆贽曰:欲理天下而不□得人心,则天下固不可理矣;欲得人心而不诚于接下,则人心固不可得矣。此人心不固之可危者也……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广求言之路,宏纳谏之怀……是乃顺天下之好恶,以固邦基。(34) 与上述批评报禁的文章相比,该奏折语气委婉,语重心长,但却一针见血,道出了政变后清廷“欲箝天下之口”却“因以失众庶之心”的恶果;并告诫清廷,要挽救危局,必须拿出“诚”意,否则“惧罪者联络愈固,抑郁者从逆愈多”,后果不堪设想。可见,《国闻报》已深切地感受到政变后清廷的复旧、株连所造成的人心流失,因此一再呼吁清廷悬崖勒马,收拾人心,挽救危局。 与批评清廷的复旧之政相配合的是,《国闻报》从多个角度疾呼变法。概言之: 一是强调变法乃今日中国急切之图,这显然是针对清廷的停罢新政而言。十月十四日,《国闻报》借助西人之口论中国时局,称:“上海西商议论中国时局,谓最上之计,由政府开诚布公,向英美日德四国政府申言,本国兵力不足以御强敌,如贵国能保此后无割地受欺之事,则中国政府当力图自强,且举行维新各政。”(35)十二月十八、十九日刊发的《论中国必将变法》一文指出:“时至今日,于中国变法一节,谁复狐疑莫决哉?要惟糊涂之人,泾渭不分,以寻常小民与当轴大员,双目已瞽,旧章是利者,两相紊淆者耳。此处既如是,他处亦何独不然。”(36)此外,《国闻报》刊发的《论黄人不宜视变法为无裨因循自误》、《庆变》等论说,也都是呼吁清廷继续变法以图自强。 二是强调“变法不宜操切”,这正是反思“康党”激进变法的结果。十月初二日,《国闻报》刊登《论变法不宜操切》一文,强调“处今日中国之势”,“变法为急不可缓矣”,但又“不宜操切”:“积弊则断非旦夕之功耳,今夫变法即所以去积弊也。积弊不可不去,是法亦不可不变……今中国内有蔽,外有侮,因陋就简,日就暗弱。嗣自厥后,惟有变法,庶可以挽回富强之机……变哉变哉!诚不可以因循而懈怠矣”。但变法必不能一蹴而就,急切图之,“必因时制宜,从容不迫,循序而进,以次推及……不然有不召意外之虞、贻事后之悔者几希,而何可以操切图之耶?” 而在《国闻报》持续不断呼吁变法的一系列文章中,一篇来自日本人内田甲的《兴清策》引人注目。《国闻报》从十二月十三日起,连续四日刊载此文,其中对政变后“新政之士”的自处之道、改革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所讨论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和平改革的范畴,不惜借助革命的手段推进改革。文章对清朝统治者极尽批评之能事,甚至直呼其为“胡人满客”,称:“夫胡人满客之寄食于中国既久矣,以蛮夷之资,而居三公之贵者有焉;利禄□身、玉帛养亲者有焉;出将入相、门客满堂者有焉。而皆取给于中国之民租,无一事于社稷,而其荣其福业已极,无所复遗憾于人间也。是以心气腐朽,进取之力,发愤之慨,无足见者。妄自曲辩,强斥泰西之美技,必欲舍短取长,因循固陋,混混晏如矣。中国勤勉之民,欲与之共日新之计,不亦难乎?”基于此,作者提出迁都之策:“有策于此,选大帝于江南,以武昌为新都,爰建宫阙,布令于各省,以帝□万世之基,则一代之人心,豁然有所发,乃乘其机,新敷教化为文明之础,兴产练兵,以图富强之本”。在批评清廷的同时,作者对康有为等新政之士的变法也提出批评,并强调“改革之事,以期渐为序”,认为处今日之势,新政之士必须韬晦养德,收拾民心,而后再图变法。而变法再起之时,新政之士必须掌控兵权、财权,“欲行天下之权者,必先拥天下之兵;欲拥天下之兵者,必先握天下之财;欲握天下之财者,必先收天下之心”(37)。而且,提出不排除以革命推进改革的可能性,“若国家依然太平而成改革之事,此固亿兆之所共望,而国家之庆福无过此也。虽然,改革之事,决非可必取于太平之时会也,不得已则流血成渠亦不可辞。此非好兵战残害百姓之比,救社稷于将亡,护宗庙于将倾,是国之重大事也。为全其重大事,行小不仁,仁者不咎之。夫改革之兵一动,天下之事定当不出数年”(38)。 《国闻报》连续四日转载该文,不仅说明对该文十分重视,也表明对其观点的认同。其中指责清廷、反思“康党”变法、主张变法不宜操切等内容,都与《国闻报》此前的报道一一暗合。即使迁都问题,也是《国闻报》一再强调的观点。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三十日、二月初一、初二日,《国闻报》连续刊发了《迁都论》,主张通过迁都达到重启新政的目的,称:“当此一大危机,如欲变危而为安,变弱而为强,则惟在赌国之命于一迁。若迁都而得有以善其后,则中国犹能保也。”(39)故而“宜速迁都于南方,下情上达,鼓举革新之气,以顺民心也……若北京厌改革者甚多,若满洲人八旗禁卫之兵,则大利害故断。行革新于北京一事,甚为难也”(40)。内田甲文所论及的掌握兵权财权再行变法、不惜借助武力推动变法等观点,虽是首次出现在《国闻报》上,却与《国闻报》一直强调的清廷复旧、株连之举必将造成民心大失、“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之恶果等观点,不无相同之处。显然,《国闻报》是在借用日本人之口表达中国有可能以革命手段重启新政的观点。 三、同情“康党”为“康党”辩护 在指责朝政、呼吁变法的同时,《国闻报》一改政变初与“康党”划清界限的做法,不但对“康党”表示同情,甚至公然为“康党”辩护。 就在《国闻报》刊出《论中国禁止报馆事》决然与清廷对抗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二日,《国闻报》转载了上海《新闻报》发表的《论康有为》,并附“本馆跋”。该文对康有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认为“成败之见,不可以论英雄也。人云亦云之说,不足以为定评也。吾于康有为之事,而不禁潸焉出涕,拊膺长叹,重为我国家惜也”。同时,也对康有为变法中之激进做法给予批评,最后对清廷的株连、复旧加以谴责,“所可惜者,谭嗣同四章京,及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株连弃市,并波及张荫桓、徐致靖、陈宝箴、江标、黄遵宪,诸君纷纷革逐遣戍,且有得罪在已奉明诏概不株累之后者。窃为保国会诸公危之。朝政反复,幻如弈棋。噫!维新之机,其止于是乎?热心甫温而使冷,爱力渐起而全弛,是谁之过欤?”上海《新闻报》此文发表于八月二十七日,而《国闻报》迟至近一个月之后才转载,正可见《国闻报》报道方向的前后转变。这种转变从《国闻报》附于该文后的“本馆跋”中,可以更清楚地见及。跋文对上海《新闻报》政变后同情康有为的报道大加赞扬,认为《新闻报》“于此次国事之变,记载最详,见闻亦最广,而犯难敢言,尤为各报之冠,一载康有为之问答,再登康有为之来书与中国皇帝之密谕,其孰是孰非,孰情孰伪,固未敢据是以为断,而援两造之词以成十载之信狱,则东西各邦来兹觇国者,皆将于此取资”。 上海《新闻报》在政变之后,对“康党”充满同情,对清廷大加批评,其九月初五日刊出“康有为之来书与中国皇帝之密谕”后,遭到了张之洞、刘坤一乃至总署的多方责难,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并被迫调整报道策略,一度减少了对“康党”的报道,同时对清廷的批评力度也有所减弱。而《国闻报》也只有在报道策略调整之后,才敢于公然转载《论康有为》,大加赞赏《新闻报》的“犯难敢言”。在《国闻报》看来,《新闻报》的敢言改写了中国自秦汉以降“凭一家私说”定是非的历史:“三代以前,列国并处,君权不甚尊,民义不甚绝,故其时毁誉是非,犹存直道。秦汉以降,中国一家,功首罪□,悉凭朝论,士苟得罪于君,则四境之内,一姓之朝,皆将无所逃命,文致罗织,何患无辞。故天下至不平,而大可伤心之事,莫甚于凭一家之私说而无两造之讼直。即如康有为一狱,自八月初六日以后,中国之懿旨上谕,始则曰辩言乱政,继则曰大逆不道”。“康有为一狱”幸有《新闻报》的报道“犯难敢言”,才不至于仅凭朝廷一家私说定是非。文章甚至对清廷为“康党”定下的“谋围颐和园”之罪提出质疑,认为缺乏真凭实据,“上谕‘谋围颐和园’五字,前不见来踪,后不见去影,冥冥几阍,茫茫终古,长留此不明不白一种疑案而已”(41)。这里,《国闻报》对“朝论”的批评与对“康党”同情溢于言表。 同一天,《国闻报》还刊登“录上海《新闻报》九月初三日译西报康有为召见奏对之词”;次日,又“录上海《新闻报》九月初四日记康有为问答之词”。尽管此前《国闻报》也曾关注过“康党”的出逃信息,并于九月初七日转录了“德臣西报访事人在香港与康有为答语”,但像这样大规模转载有关康有为的言论及评论,则是首次。显然,报道方向转变后的《国闻报》是在效仿《新闻报》的“犯难敢言”。不过,对于《新闻报》刊登过的、曾引起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极大恐慌的康有为来书及光绪密谕,《国闻报》并未转载,这说明,《国闻报》并不欣赏康有为将其来书及光绪密谕公然刊布于《新闻报》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事实上只能是恶化光绪帝的处境。 十月初六日,《国闻报》在“日本新闻”栏目中刊登了梁启超的《去国行》,文后有语:“呜呼,此非我友徐小隐去国之诗歌乎?今读此作,感激怆喟,沉痛刺骨,如闻抚膺之恸,非橐籥云月、镂刻风露者所梦想也,又岂流灵鼠兽、偷生草际者所企及哉!”(42)隐去梁启超而假名徐小隐,自然是为了减少麻烦。 如果说此时《国闻报》对“康党”的同情尚以转载他报内容为主、还有所隐讳的话,那么到了己亥年之后《国闻报》便不惜出而为“康党”辩护。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十六日《国闻报》发表《论中国党祸》一文,公然为“康党”辩护,指出“维新之徒,纵曰植党营私矣,守旧之辈,亦何尝非植党营私哉?且新党未尝以杀人为事,旧党先以杀人为功,是党祸之开,开自旧党也”,因此告诫旧党不得以“作福作威,独行独断,中国之法也”为藉口,为所欲为,应当以“三宥之说、八议之条”为律,宽宥“以素王纪年、以总统期许”之“新党”:“或曰作福作威、独行独断,中国之法也。不思三宥之说、八议之条,独非中国之法乎?康熙之世,有身为探花作忠臣不可为之论者;同治之朝,有职居御史而为今上不应立之奏者,其视以素王纪年、以总统期许者,相去几何?而当时皆不以罪也”(43)。显然,面对清廷的株连与复旧,支持变法的《国闻报》与“康党”有更多的共鸣,曾经有意界划“康党”与“新党”,不过是恐怖株连下自我保全与保全新政的策略,而今以“新党”指代“康党”正是对清廷失望后内在共识的表白。其对“以素王纪年、以总统期许”之“康党”的同情,直接源于两个月前清廷再度声讨“逆党”的一道谕旨。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六日,清廷在两广总督谭钟麟抄没康有为老家的书信后颁发上谕,称:“昨据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康有为本籍钞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称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款大,不欲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前因康有为首倡邪说,互相煽惑,不得不明揭其罪,以遏乱萌。嗣无知之徒,浮议纷纭,有谓该逆仅止意在变法者,试证以钞出函件,当知康有为大逆不道,确凿可据。凡属本朝臣子,以及食毛践土之伦,应晓然于大义之所在,毋为该逆邪说所惑,以定国是而靖人心。”(44)这里,清廷意在借此坐实“康党”“谋逆”之罪,说明“康党”罪不容赦,从而挽回人心。不料《国闻报》竟针锋相对,历数“旧党”处置“康党”的失当,并与康熙、同治朝的案例相比照,认为“以素王纪年、总统相期”的“康党”并非罪不可逭,而是应当宽赦。这里《国闻报》公然对抗上谕之举,已与政变之初积极配合清廷区分“新党”与“康党”的做法,迥然不同。 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十九日,《国闻报》刊发《刘培村别传》,该文的主旨在于说明刘光第并非“康党”。正月二十八日,《国闻报》再发《读刘培村别传书后》,对《刘培村别传》中力图洗刷刘光第与“康党”关系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在立传者之意,无非欲极力为刘培村刷冤,其心亦良苦矣。虽然,刘培村既死,明明罹变政党祸而死,则亦何妨曰刘培村之死上为其君,下为其友。如不然者,则既立朝同事知终必败,爵禄可辞也,白刃不可蹈也。恋恋胡为者?恐刘培村死而有知,必当怨曰信如是,既非新党中人,又非旧党中人,新旧两不容,将我适安归乎!故仆窃不解为之立传者视刘培村之人为如何人?”(45)显然,在作者看来,“罹政变党祸而死”并不可耻,而是上为其君,下为其友,无须洗刷。 三月初四日,在看到上海某报报道张之洞禁售《清议报》、并与日方交涉欲封禁《清议报》的消息后,《国闻报》刊发《讼冤说》,对张之洞大加讥刺,通过列举张之洞政变前对梁启超的种种推重,如张之洞饬令各学堂订阅梁启超所办之《时务报》、聘梁启超主讲其所辖之时务学堂、举荐梁启超经济特科等,说明张之洞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然后发论:张制军昔日“提倡报馆不遗余力如此,今若此,是谓反覆。反覆小人所为,张公顾忍为之哉!……今不惟没其(梁启超)学,并禁其言,前日之聘是,则今日之禁非也。今日之禁是,则前日之不禁非也。张公达人,顾为是世俗之朝杯酒暮茅戈哉!况夫当国家议开经济科,张公以湛深经术时务博通,荐○○○于朝。八月之变,○○○为公为私可不必辩,然诸臣中之稍□牵涉者,甚者杀戮,次者窜逐,又次斥革,不一而足。张公乃岿然独存,其见识阅历诚非朋僚意量、权力所能几及。祸机已息,正宜坚忍隐默,使渐相忘,明哲保身,端推此种。今乃因此毫末,遽生事端,设朝廷闻之,以前日荐牍相诘驳,张公果何辞以对乎?”(46)戊戌变法中,张之洞的确与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很多维新人士多所交往,然政变后,出于自我保全的考虑,张之洞不仅与梁启超决裂,而且面对清廷的复旧、株连,默不作声,甚至不惜指认自己的同事为“康党”。对于政变后张之洞的表现,趋新之士多有批评。孙宝瑄就曾如是说:“今日中国之反复小人、阴险巧诈者,莫如两湖总督张之洞为甚。民受其殃,君受其欺,士大夫受其愚,已非一日。自新旧党相争,其人之罪状始渐败露,向之极口推重者,皆失所望。甚矣,人之难知也。”(47)这里,《国闻报》对张之洞的公然嘲讽、为梁启超的辩护,正道出了部分趋新之士的心声。 三月十六日,《国闻报》又刊发《醒迷歌》,肯定“康党”变法之“公心”,公然为“六君子”喊冤,指出“维新之徒,学术虽偏,然以变法自强为名,救焚拯溺,犹有公心。守旧之徒,诬以莫须有之狱,力赞不讯而诛,焚艾及兰,究竟无枉否?天下后世谁其信之?”文章进一步对清廷株连新党提出批评,认为“旧党中明明有正有邪,新党中亦岂有邪而无正?……乃无论新党之邪正,概以‘不轨’二字抹煞之,固身家之窟穴,藉疑团为离间,贻慈圣以无穷之忧,置圣上于累卵之危,无病幸其有病,小病幸其大病,抄录脉案,传示京外,释疑而转以滋疑,一时之耳目迷于利而可欺,万世万国之耳目,可尽欺乎?”并警告清廷不要轻举废立,“伊霍之事,岂近世用人所可效颦,一经妄动丧乱遂至,彼号为证人者能免溃臭于万年耶?”在文后的跋语中明确指出:“去秋之衅机,触于变法而实不专在变法也。夫宜言伤时,而讽言不足以悟人。与其人人缄默,坐视意外之来,盍若姑妄言之,以冀消弭于万一。” 《国闻报》之所以会在己亥年敢于公然为“康党”辩护,可能与其已经决定彻底卖于日本有关。 《国闻报》的报道转向自然引起守旧之士的不满,虽有日本的保护,但其主笔却屡遭弹劾。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初六日,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道:“日来《国闻报》指斥朝政,略无忌惮,意在挑衅。彼必有以待之者,惟幼陵当益危耳。”(48)署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准良奏劾《国闻报》,改归知县庶吉士缪润绂也奏请停办《国闻报》,都尚在《国闻报》报道方向转变之前,虽然其对朝政的批评力度远不及后来激烈,但这已引起了如此反弹。据此可见,九月二十日之后《国闻报》的报道必将引起更激烈的奏劾。十月二十五日,文渊阁大学士昆冈上奏,弹劾《国闻报》,说其“肆口污蔑。灭绝人伦,丧心病狂,不如狗彘”(49)。十月二十九日,江西道监察御史熙麟又劾及《国闻报》(50)。在各种压力之下,王修植、严复也产生了停办报刊的念头,但由于日本人不同意而作罢。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主笔夏曾佑遂于此时离开报馆(51)。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十八日,夏曾佑致函汪康年,谈及各主笔的处境,说:“严又陵甚自危,菀生(王修植)稍可。”(52)也就在此时,严复、王修植已经在运作将《国闻报》彻底卖于日本之事,并于三月二十日正式与日方签署出售合同。此后,“尽管王修植等人还时时以该报为阵地,发布一些同情维新党与顽固派作对的文字,但是,其性质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日本所有并掌握其经营权的报纸”(53)。 从政变发生到彻底卖于日本人,《国闻报》呼吁变法的宗旨虽然一以贯之,但为了应对政变后复杂的时局,其报道策略却几经调整。政变之初,为了免遭株连,《国闻报》及时与“康党”划清界限,并寄希望于慈禧太后继续新政,而清廷几次上谕做出继续新政的承诺成为《国闻报》靠拢清廷的重要缘由。然而,随着清廷继续新政的承诺化为泡影,《国闻报》的报道方向发生转变,公然指责朝政,呼吁变法,一改政变之初与“康党”划清界限的做法,对“康党”给予同情,并公然为“康党”辩护。 而《国闻报》与清廷关系由合到离的转变正是当时趋新士人与清廷关系的一个缩影,由《时务日报》改名而来的《中外日报》与清廷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与《国闻报》相同的转变,只不过其转变的速度不像《国闻报》那样迅速,对朝政的批评也不如《国闻报》激烈而已,但其离心清廷、疾呼变法则与《国闻报》并无二致。《国闻报》与清廷的公然对抗正是清廷复旧、株连造成士人离心的结果。然而,《国闻报》一再强调的切勿“为渊驱鱼、为丛驱爵”的警告并未进入清廷的视野,清廷在复旧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朝野离心之士愈来愈众,当部分趋新之士还在耐心呼吁变法之际,另一部分却急切地转向了革命。最终,在改革与革命的夹击中,清朝走向了终结。 ①《国闻报缘起》,《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②夏曾佑:《致汪康年》,载《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0页。 ③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下),《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 ④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曾利用日本外务省有关《国闻报》的档案撰文,对《国闻报》创刊背景、《国闻报》的灵魂人物、《国闻报》在百日维新中的作用、《国闻报》与日俄两国的关系、《国闻报》的结局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对政变后《国闻报》的报道内容却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戊戌政变刚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该报馆既没有退缩,也没有改变原先之立场,仍然是以显明的态度,对改革派表示同情与支持”。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上、下),《学术研究》2008年第7、9期。 ⑤关于《国闻报》在维新变法中紧随康梁进行报道之事,从其对康梁京师保国会活动与宗旨的宣传上可以见及: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国闻报》刊出《拟保国会章程》;闰三月二十三日、三月二十四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连续刊出保国会第二次与会人员名单及入会列名之人;闰三月二十九日刊载《书保国会题名记后》,对“康党”倡开保国会给予了高度赞扬;四月初三日又刊出《论保国会》、《闻保国会事书后》;四月初十至十三日,连续刊出《保国会三月二十七日第一集演讲》(康有为)、《演说保国会开会大意闰三月初一日第二集》(梁启超);四月十五、十六日连续刊发《如有三保》;四月十六日刊出《会事续闻》;四月十九、二十日连续刊出《保教余义》(上、下);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连续刊出《保种余义》等。 ⑥《恭纪太后训政事》,《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 ⑦《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载《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87页。 ⑧《汪进士呈文》,《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⑨《中堂入京》,《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⑩《圣躬欠安》,《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11)《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431页。 (12)《论变法有自然之势》,《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二十日。 (13)《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445页。 (14)《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450页。 (15)《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9页。 (16)《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425、451~452、453、455页。 (17)楼宇烈:《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页。 (18)《经济厄运》,《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19)《是何言也》,《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20)《言官之言》,《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21)《杨御史召见述闻》,《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22)《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461页。 (23)《一人刚断》,《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 (24)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2~483页。 (25)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6页。 (26)《〈劝善歌〉跋》,《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27)《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478页。 (28)《论中国禁止报馆事》,《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 (29)《续论中国禁报馆事》,《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30)《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十二日。 (31)《论中国阅报之风必将大开》,《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六日。 (32)《论日报本春秋之义》,《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日。 (33)《论求治必自广言路始》,《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34)《拟请复开言路书》,《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35)《西人论时局》,《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36)《论中国必将变法》,《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十九日。 (37)《兴清策续前稿》,《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38)《兴清策三续前稿》,《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39)《迁都论》,《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三十日。 (40)《迁都论》,《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41)《照录八月二十七日上海〈新闻报〉〈康有为论〉》,《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42)《去国行》,《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43)《论中国党祸》,《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44)《光绪朝上谕档》第24册,第569页。 (45)《读刘培村别传书后》,《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 (46)《讼冤说》,《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4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48)《郑孝胥日记》(2),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91页。 (49)《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91页。 (50)《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94页。 (5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336页。 (5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339页。 (53)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下),《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