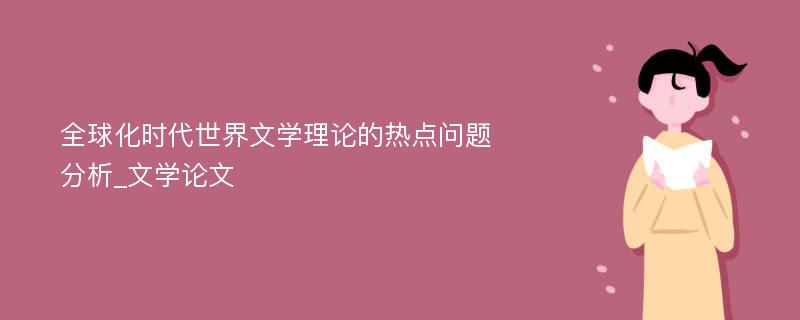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热点问题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时代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旧世纪的转换,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文学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就是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的复兴。1999年,法国学者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世界文学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出版(英文版出版于2004年);2000年,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reti)发表论文《世界文学的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3年,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出版,这些著作和论文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直接策动了新世纪世界文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其后出版的重要著作还有莫莱蒂的《曲线、地图、谱系:文学史的抽象模式》(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2005)、约翰·皮泽(John Pizer)的《世界文学的观念:历史与教学实践》(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History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2006)、麦茨·汤姆森(Mads Rosendahl Thomsen)的《图绘世界文学:国际经典化与跨国文学》(Mapping World Literature: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2008)、达姆罗什的《怎样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09)等。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2000—2012年间,在重要的国际英语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世界文学理论研究论文达200余篇,而且总体上呈现持续增加的态势。一些重要的学术杂志,如《比较文学评论》(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还分别在2006年和2010年推出世界文学研究专辑。克里斯多夫·普伦德加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主编的《世界文学论争》(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2004)、Theo D'haen等主编的《劳特里奇世界文学研究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of World Literature,2011)等书,也选收了不少世界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优秀论文。 随着理论研究热潮的出现,世界文学实践也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这集中体现在三大世界文学作品选集的出版上:诺顿公司在2003年推出7卷本的《诺顿世界文学作品选》(第7版),2004年贝尔福德公司推出《贝尔福德世界文学作品选》,同年,朗文图书公司出版了《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热,同样影响了相关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反思与重构,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2003),苏源熙(Haun Saussy)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2006)、阿普特的《翻译地带:一种新的比较文学》(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2006)都回应了世界文学理论热的兴起对比较文学产生的推动作用。 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时代”的理想,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但这一世界文学的现实并不符合人们的普遍期待,反而衍生出诸多问题,产生出许多新的可能性;同时,一些后发国家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其民族文学要求在世界文学中占据更大份额。世界文学理论研究受这些因素的推动,在新世纪呈现繁荣的局面,产生了许多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对世界文学的重新定义、世界文学体系的形成、世界文学与翻译、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关系等。本文将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评析,批判世界文学观念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探索世界文学话语助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有效路径。 重新定义世界文学 众所周知,歌德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世界文学”观念并进行系统论述的人。歌德的论述集中在1827—1830年间,归纳起来有两个要点:其一,世界文学是一个合乎世界主义的理想,能够推动各民族文学逐渐打破孤立割裂状态,影响融合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二,世界文学是一个对话、流通和展示的平台,各民族文学可以通过进入这个平台,彰显、提升自身价值,并与其他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①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文艺复兴以降欧洲人逐渐形成的世界视野和世界观念,以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内部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是歌德创制和阐发世界文学观念的历史背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应了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指出随着资本输出和世界市场开拓,不仅物质生产,而且精神生产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世界文学看成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世界各民族文学走向普遍联合的一种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扩大了对世界文学的理解范围,阐述了世界文学发展与世界市场形成之间的因果关联,是对世界文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如果说歌德的世界文学带有更多乌托邦的建构色彩,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已经开始指向一种审美现实。 整个20世纪,世界文学这个用以描述超出民族国家界限之文学整体图景、隐含着彰显民族荣耀、实现人类大同的观念,持续激起思想界、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情。莫尔顿、泰戈尔、郑振铎、韦勒克、艾田伯等都对世界文学观念做过创造性的、深刻的论述;这一观念也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研究及全球文学图景的描绘中去。在他们眼中,世界文学至少有三重含义,首先是指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其次指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品,第三是基于人性共通性和相互影响的世界各国文学的广泛联结。在具体实践中,欧洲中心主义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对世界文学范围的理解在不断扩大,世界文学多起源、多线索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 关于什么是世界文学,在21世纪有了新说。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为世界文学下了三个定义:第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第二,世界文学是因翻译而增色的作品;第三,世界文学并非一系列一成不变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从自身所处时空抽离,以超然姿态进入许多别样天地的方式。③达姆罗什继承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是一个超民族文学的有机统一体的理念,但他没有规定或描绘世界文学的理想蓝图,没有说世界文学应该是什么,而是在说世界文学实际是什么,以及世界文学是如何生成的。这标志着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从规定性向描述性的重要转变。更重要的是,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描绘成一个公共空间,最大限度地剥离了西方经验与世界文学根本原则之间的必然联系,充分考虑到世界各区域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东方国家利用世界文学话语创造了条件。 这个定义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性折射”(World literature is an elliptical refrac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s)这一描述。“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是达姆罗什借用光学术语“椭圆形反射”(elliptical reflection)自创的一个短语。所谓“椭圆形反射”,是指在一个椭圆形空间里,一个焦点上的光源会通过反射作用重新聚焦到第二焦点上,从而形成双焦点。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意在说明原语文化和宿主文化(the source and host cultures)各自提供一个焦点,从而形成一个椭圆形空间,一部作品作为世界文学存在于此,和两种文化都有关联但并不受制于任何一方。达姆罗什之所以把“椭圆形的”(elliptical)与“折射”(refraction)混搭,生造出一个没有科学根据,但却深刻揭示了世界文学本质的隐喻,意在表明民族文学在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不是简单、直接的“反射”,而类似于穿越了一些介质(例如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的“折射”;民族文学透过介质“折射”成为世界文学,与它本源的样子已经大为不同。从这一理念出发,不难理解他所指出的世界文学与其他两个要素(翻译、阅读模式)的关系。世界文学的形成实际上关乎全球范围内文学的生产、出版和流通的整个过程。从读者角度看世界文学,它并非有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跨越时空与不同世界进行交流的模式。达姆罗什的这一说法,很显然受到读者反应理论的影响。按照读者反应理论,一个文本在被读者阅读之前,只是一些装订在一起的纸张、印刷的一些文字而已;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赋予它作为“文学作品”的生命。据此,民族文学作品在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人类最古老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在1849年才被考古学家发现,到20世纪初叶才被翻译成现代语言,才得以被不同民族的读者阅读,它作为一部世界文学作品才逐渐为人们所知,也由此加入到世界文学的序列之中。同样,一部作品在其他民族中被阅读,会引起新的关注,并赋予作品新意。例如在中国文学中并不受重视的清代小说《好逑传》引起欧洲的关注;英国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在英国文学中并不重要,在中国却成为经典。这些都是跨时空、跨文化阅读和交流对与世界文学生成的意义所在。这些结论的得出,显见世界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歌德的前瞻式理想,还是一个变化着的动态概念。 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离开起源地,穿越时空,以源语言或通过翻译在世界范围流通的文学作品。这一定义,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的认可。达姆罗什还在其他各种场合补充、丰富、推广着这一全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他发表于2006年的《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见苏源熙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文,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经典的恒定性和变化规律。达姆罗什指出,自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主编的《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1995)出版以来,美国学界对世界文学的理解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善,欧洲中心主义被打破,世界文学经典的范围扩展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诺顿、朗文、贝德福特版世界文学作品选的最新版本史无前例地收入了来自全世界数十个国家的500多位作家的作品,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达姆罗什统计了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版的《现代语言学会书目》(MLA Bibliography)所收1964—2003年间研究不同作家的论文数量和比例后,发现经典的范围虽然扩大了,但旧的经典作家地位并没有动摇。达姆罗什由此提出世界文学经典的三层次说:超经典(hypercanon)、反经典(countercanon)和影子经典(shadow canon)。超经典指的是那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地位或者甚至地位越来越重的“大”作家。反经典指非主流的、有争议的作家,他们使用非主流语言创作,或者虽然使用大国的主流语言,但隶属于非主流的文学传统。影子经典指那些被超经典遮蔽的小作家,他们越来越隐身退去,消失在超经典的背影里。达姆罗什的统计表明,超经典作家,像如莎士比亚、荷马、乔伊斯等,他们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反经典作家可能在某一个时期红极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声誉下降,在经典的边缘徘徊,地位并不稳固。而影子经典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会彻底淡出读者的视线。由于课时的限制,所以世界文学课堂总是被超经典霸占着。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在其世界文学作品选集中的地位,极有可能是反经典,只是昙花一现,到最后还会淡出西方读者的视线。对超经典霸权的批评再多,也无法改变其独霸的现实。 世界文学体系的形成 从古至今发展着的世界文学实际是怎样的一幅图景?有无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体系?早在1886年,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一书就对此进行过探讨。他提出世界文学多元起源的思想,认为世界文学起源自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它们是各自独立生长的,不存在影响关系。波斯奈特又从这四个文明古国的文学中,归纳出由民族特性凝练而成的世界文学精神,他认为各民族的世界文学精神具有可通约性,但和而不同。波斯奈特还认为,文学的发展与社会进化同步,是从简单向复杂、从城邦到国别再到世界的发展过程。波斯奈特的世界文学观破除了世界文学单一起源与发展的固念,扩大了世界文学的范围,是了不起的创见。 197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兴起于美国,对世界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产生重大影响。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由结构性经济联系及各种内在制度制约的、一体化的体系,以此作为考察社会发展变迁的分析单位。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形成的经济链条,将各个国家、地区牢牢地黏结在庞大的网络中。这个体系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层级构成,各个层级的利益不是均等的,而是通过体制性剥削,以保证中心区获取最大利益,边缘区则总是处于被剥削的境地。按照沃勒斯坦的划分,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区,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区。 21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应用了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等理论,探讨了近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若干规律和结构性问题,展示了欧美学者视域中的世界文学图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弗朗哥·莫莱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在他们眼中,波斯奈特的世界文学图景是“马赛克式”的拼贴,只符合古代世界文学的事实。近代以来,世界文学的发展模式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即一体化,原先独立发展的文学逐渐被征服、同化,演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世界文学体系。 卡萨诺瓦现任职于法国巴黎艺术和语言研究中心研究院。在《世界文学共和国》一书中,她描述了世界文学所蕴含的巨大的关系性结构。在她看来,世界文学空间与现实中的国家一样,有自己的首都、外省和边疆,中心与边缘。文学资本往往高度集中在宗主国,对世界文学政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巴黎是世界文学空间的首都,也是世界文学的中心。世界文学空间首先出现在16世纪的欧洲,法国最先勾画出了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学空间,西班牙、英国及其他欧洲各国相继而起,以自身的文学财富互相竞争。18世纪至19世纪,这个空间在中欧和东欧得以巩固和扩大。20世纪它在非洲、印度次大陆及亚洲国家继续扩展,并表现为一个仍在进行的去殖民化过程。世界文学空间的主要特征是等级制和不平等,并拥有相对的自治性,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例如,尽管德国民族文学观念的兴起,起因于对当时作为欧洲文化霸权的法国的政治对抗,但18世纪后半叶德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对整个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且使其自身(德国浪漫主义)获得了独立性和自治能力。又如,拉美国家在国际政治世界中的地位,无法与其文学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的地位比拟,国际声誉的获得促使民族的文学文化脱离了民族政治的束缚。卡萨诺瓦还指出,欧洲空间最早进入跨国的文学竞争,积累了丰富的资源,拥有最大程度的自治。世界文学空间的发展与整合,既包括伴随着世界不同地区的民族独立而获得的文学空间的持续扩张,也包括面对政治(民族)权威的文学解放,即文学的自治趋势。在卡萨诺瓦看来,中国、日本、阿拉伯国家这样古老的文学空间虽然拥有长久的历史,由于他们很晚才进入国际文学空间,所以占从属地位。世界文学的统治结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并不因为多元文化主义的热情而消失或颠倒,边缘作家仍要追赶中心所确立的审美现代性。卡萨诺瓦描绘了近代以来世界文学的基本格局和走向,揭示了世界文学空间隐秘的权力运作机制。 弗朗哥·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猜想》(2000)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受进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影响,莫莱蒂把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学看成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有中心,有边缘,其权力关系是不平等的。文学的进化发展总是从中心向边缘运动,是一个不断扩散的过程。中心区域的文学样式扩散到边缘区域,将边缘区域的文学发展吸引到类似的轨道上来,这实际上干预了它们的自主发展。而反向的扩散则很少发生。这种不对等的扩散可以解释文学史上的相似性,也强化了体制中的不平等。但边缘地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会对来自中心的形式加以选择和改造,其融合方式常常表现为一个来自中心的情节和一种来自边缘的风格,也即外国形式与本土材料的结合。造成世界文学形态空间分化和聚合的分水岭是国际市场的形成。18世纪以前,人类文化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并通过不断地分化产生多样化的新的形式。18世纪国际文学市场发展到足够强大,开始征服独立的文化,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即世界文学体系,并发展出相似性。这两种世界文学的结构差异很大,需要用不同的理论去分析。莫莱蒂对世界文学的论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用“树”和“波浪”比喻世界文学运动的两个基本规律。“树”取的是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的树状结构,指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由一而多,不断衍生分岔,从而形成一个个家族系列。“波浪”的比喻取自水流运动所具有的覆盖性、吞噬性的特点。树描述了事物从统一性到多样性的发展;波浪则相反,描述了事物在发展中,由不断吞噬多样性而达致统一性。莫莱蒂认为,与语言、文化、技术的发展相同,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是树和波浪的交错运动,其产物必然是合成的。 从积极的一面看,卡萨诺瓦指出了近代以来世界文学的格局与走向,凸显了世界文学体系中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和不平等关系,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但另一方面,卡萨诺瓦的立论基本以近现代欧洲文学为基础,具有强烈的法国中心主义色彩。比较而言,莫莱蒂虽然承认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与不平等,但更多地思考了边缘地区文学在世界文学机制里的能动作用。 世界文学与翻译 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关系同样备受关注。从源头上看,翻译对于世界文学观念的构建意义重大。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与他对翻译的重视和实践密不可分。他不但亲自翻译过许多欧洲国家的文学著作,而且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歌德的许多作品在他有生之年也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这使他能深切地感受到翻译在建构世界文学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美国学者理查德·莫尔顿(Riczhard Moulton)在其影响深远的《世界文学及其在总体文化中的位置》(1911)一书中,为译本的价值进行了充分辩护。在该书的导言中,莫尔顿认为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来自原语言崇拜的偏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显而易见,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不依赖译本是不可能进行的。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即阅读翻译文学是一种权宜之计,有二手学问的味道。但这一想法本身是对文学进行分科研究的产物,这种分科研究迄今仍然流行,它不能摆脱语言和文学紧密纠缠,以致很难想象将二者分隔开来。这种想法经不住理性的检验。如果一个人,不通过希腊文,而是通过英文读荷马,他毫无疑问会失掉一些东西。但问题出来了,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文学吗?很清楚,相当大比例构成文学的东西没有丧失;古老生活的描写,史诗叙事的节奏,英雄形象的观念和事件,情节技巧,美妙的比喻——荷马史诗中的所有这些元素对与译本的读者仍然敞开着。”④一句话,文学中所反映的生活、情感并不曾失去。 德国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本雅明在其发表于1923年《翻译者的任务》中,讨论了作品的可译性,以及原作与译作之关系诸问题。莫尔顿为译本辩护的出发点,是认为译本能够忠实地复现原作的面貌,本雅明的辩护正好相反。他认为译本的价值不在于从字面和句法上忠实地复制原作,而在于忠实原作的意向,在于挖掘和传递原作的本质属性。由于译作晚于原作,同时也因为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从来不可能在其诞生之日就觅见所有选定的译者,因此它们的翻译往往标志着其延续了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译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与发展,“翻译也将迈过原作而前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1970年代以降,随着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改写理论、巴巴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雪莉·西蒙(Sherry Simon)等人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大行其道,本雅明的翻译观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引述,甚至被抬到神主的牌位。而事实上,197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翻译理论,与本雅明的翻译观一脉相承,都是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对译本之于原本的独立性及其价值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都对世界文学理论以极大的启发。 正是受到这些翻译理论的启发,达姆罗什在重新定义世界文学时,才会宣称“世界文学是因翻译而增色的作品”。达莫若什的定义之所以重要,是他把“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看待;民族文学不是天然就能成为世界文学,它要穿越诸多介质,进入这个椭圆的公共空间,才能成为世界文学;而翻译是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时必须穿越的诸多介质中最重要的一项。达姆罗什高度重视翻译对世界文学的意义,认为翻译是帮助民族文学跨越语言藩篱,在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流通并获得广大读者认可的必要途径;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一部文学作品,在其本民族当中,哪怕地位再高,再优秀,如果没有其他语言的译本,就很难为其他民族所熟知,就不能成为世界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学作品是由译本构成的,是融合了源语国文化与译语国文化的混杂、共生作品。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是美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其《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2010)⑤一文,进一步探讨了翻译在建构世界文学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是从翻译文学的这种性质出发,论述了原语国与译语国文学关系的重构问题。他指出,翻译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世界文学的流通,不纯粹是转移主流文学声望和价值,对从流文学进行渗透和改造的过程,还是一个主流文学在从流文学中被“增值”和重新创造的过程。此外,尽管主流文学与从流文学之间的翻译从来都不是对等的,主流文学作品被翻译得更多,但从流文学也往往显示出翻译的自主性:在通常情况下只有译文文化的价值观念可以接受的文本才会被选中;从流文学还可能通过翻译对主流文学传统提出质疑;而不同的从流文学之间进行翻译,从而绕开了主流文学。这些情形说明,主流文学传统与从流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单向的,而是要远为复杂。 世界文学与区域、民族文学关系 如前所述,歌德1827—1830年发表世界文学系列言论时,他一方面把世界文学看成合乎世界主义的理想,同时也将其当成彰显民族文学价值的场所。这意味着当世界文学话语进入实践层面时,既包含了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也会传达特定的民族倾向和区域立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价值观并行不悖,是世界文学观念充满张力和魅力的根源。 在世界文学与区域、民族文学关系中,最可注意的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及其批判。早期西方学者的世界文学观主要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如理查森(John William L.Richardson)和杰西·欧文(Jesse M.Owen)合编的《世界文学》(Literature of the World:An Introductory Study,1922),美国约翰·玛西(John Macy)的《文学故事》(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1925),英国学者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water)的《文学大纲》(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等著作,虽然都冠以“世界文学”之名或普遍的“文学”,但主体部分都是欧洲文学,至多扩展到美国文学;《圣经》被堂而皇之地作为西方作品,其他的非西方文学往往只占极小的篇幅,而且只是作为西方文学产生的源头之一、外援性影响因素之一而存在。这样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在洛里哀、迪马、韦斯坦因等比较学者那里多少都存在着。即便到了21世纪,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仍然有相当市场。如帕萨诺瓦在《世界文学共和国》中,就把欧洲文学看成是世界文学的中心地带,更把法国文学看成是欧洲文学的核心。 20世纪中期以后,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声音逐渐高涨起来。法国学者艾田伯在其《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1974)中,对当时西方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表达了强烈不满,他列举了多种世界文学年表、书目、作品选、研究资料,指出其徒有“世界文学”之名,却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例如严重忽视东方文学,崇拜民族文学偶像,把绝大多数国别文学描述成从属几个所谓伟大的、具有原创性的文学等。艾田伯认为西方学术界这些狭隘的世界文学观念,背离了歌德的初衷,“不过是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和基督教价值观的著作而已”。⑥艾田伯力主将世界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东方文学。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an Owen)在1990年11月19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全球影响的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引发国际汉学界的热烈讨论。安德鲁·琼斯在1994年发表《“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94年第8卷)一文,呼应宇文所安的观点。宇文所安文章借讨论北岛诗歌的可译性,反思世界文学话语中的西方霸权及其危害。他把北岛诗歌称为“世界诗歌”,指北岛为了易于被全球(主要是英美)读者理解,有意在创作时弃用有明显中国特色的韵律和词汇,而采用最容易翻译为外国语言的诗歌媒介——意象进行创作的诗歌。在宇文所安看来,这样的世界诗歌剪断了扎在特定国别和语言中的根基,从而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另一版本,是西方文化霸权借世界文学话语扩张的明证。安德鲁·琼斯的文章以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的翻译和接受为例,对世界文学话语中包含的西方文化霸权进行了反思。他直言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充满了东方主义修辞,是以帝国主义方式构造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当前中国文学在跨国文学经济中,并没有向上活动,而是处在全球村边缘的某个文化聚居区,这个聚居区四周的高墙正是世界文学话语堆砌的。而要减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阻力,应该推倒世界文学话语高墙。 更多学者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探讨在这个有机统一体形成的过程中,各个区域文学,尤其是东西方文学如何互动,以及亚非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他者,如何在形塑西方文学的同时形塑自我,从而完成从自身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印裔美国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副教授阿米尔·穆夫提(Amir R.Mufti)的论文《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机制》(文载Critical Inquiry,Spring 2010),就以这种思路,探讨了东方主义在建构世界文学机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为东方主义理论的奠基人,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的知识实践,它的出现首次使不同文明群体居于单一世界空间成为可能。他的这一认识对于反思世界文学概念自身可能存在的遮蔽性因素,即工业革命后世界文化和社会的重构及全球性的力量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穆夫提是萨义德的学生,他在论文中指出,应该将东方主义理解为全球范围内语言、文学和文化重构的一系列过程,这种重构实际上是将异质的、分散的文本进行同化的过程;而要反思世界文学观念与东方主义的关系,必须融合本土的与全球的双重视野。穆夫提以印度古典语言与现代文学为例指出,近代早期的欧洲,随着对东方古典语言的发现,东方语言作品的翻译,非西方的文学和文化早已在世界文学空间当中发挥着作用。而在现代,东方主义又翻转过来,推动了印度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构建,如对传统文学的发现、知识精英的产生、“印度文学”概念的形成、印度—乌尔都语的创制等。 还有一种观念值得特别关注,即把世界文学当成一个复数的存在。这一观念认为,并非只有一种世界文学,从不同区域、族裔、语言出发,可以发现多样的世界文学。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哈佛大学副教授唐丽园的论文《反思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台湾、东亚及文学接触星云》(2010)⑦是一篇研究东亚区域世界文学的佳作。按照西方的世界文学话语,世界文学的形成从欧洲开始,然后逐渐地扩展到其他区域。因为占据了所谓“源头”的优势,西方文学于是被安稳地放置在世界文学的中心区域,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的文学,则被置于边缘区域。唐丽园认为,这样的世界文学话语应该被打破,新的世界文学研究必须采纳对文学、文化和民族更多元的理解。这篇文章考察了东亚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现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改写、挪用、交流等现象,指出其创造出了一个相互平等、彼此混合、边缘模糊的文学接触“星云”(nebulae/nebulas),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共同体。唐丽园期许如此分析非西方文学作品在区域内的交互作用,能有助于整合与重塑“地方的”和“全球的”概念,为世界文学找到一条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并接近区域中立的途径。 纵观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世界文学观,总体上经历了一个范围不断扩大,欧洲中心主义思想逐渐弱化的过程。20世纪初期西方学者眼中的世界文学,都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名家与杰作。莫尔顿1911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及其在总体文化中的地位》(Moulton,Richard G.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选了《圣经》、古希腊史诗与悲剧、莎士比亚戏剧、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浮士德题材作品等五类作品,称其为世界文学的“圣书”。1956年出版的《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的第一版,包括73位作家的作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也都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名家杰作。随后40余年时间,《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不断扩版,选入的作品越来越多,但这种欧洲中心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直到21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才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善”。⑧以《诺顿世界文学名著选》为例,这部畅销了半个世纪的世界文学作品选本,到2004年出第七版,改名为《世界文学作品选》,把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500多位作家的作品囊括其中。而紧随其后出版的《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2004)和《贝尔福德世界文学作品选》(2006)在人选作家作品的数量、篇幅和范围上也与之相当。更可贵的是三部世界文学作品选都在相当大程度上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以年代为主线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各大区域的文学贯穿起来;且非欧美文学不再依托欧美文学存在,而有了独立发展的序列。这种真正全球视野的世界文学观,在21世纪已经成为主流,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注释: ①《歌德论世界文学》,范大灿译,见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③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 Oxfro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81. ④Richard Moulton,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New York:The Macmilan Company,1911,p.4. ⑤译文见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 ⑥艾田伯:《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见《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胡玉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00页。 ⑦译文见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 ⑧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见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标签:文学论文; 世界文学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德国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比较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歌德论文; 罗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