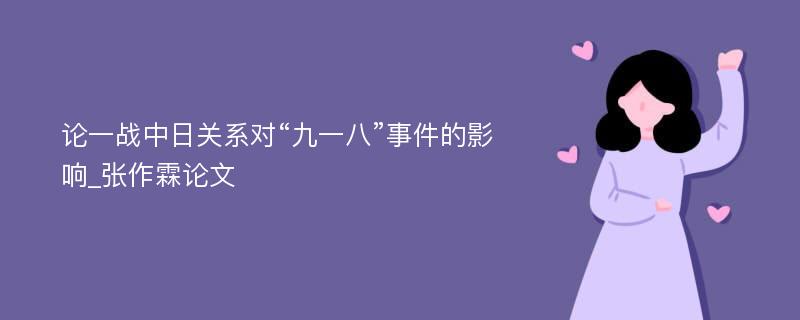
略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九#183;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事变论文,世界大战论文,一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从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段时期,曾先后出现过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举世震骇的“田中奏折”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日本政府还巧妙地利用国际形势和中国时局之变化,见缝插针地推行其“大陆政策”,并不断变换方式使其日益升级,终使“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段近20年的中日关系十分微妙且曲折复杂、变化多端,文章进而阐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
关键词:近代中日关系 “二十一条要求” “田中奏折” “大陆政策”
一
1914年4月17日,日本成立了以接受元老提出的“增加二师团议案,以满足军部积极扩充军备的野心”和“对华提出二十一条,以实现其独霸东亚大陆的政策”两项条件为前提的大隈(重信)内阁。大战爆发后不久,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特务组织“黑龙会”的头目内田良平硬向首相大隈(重信)提出一个灭亡中国的秘密备忘录,建议:日本应趁欧战之机“当机立断地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主张在支持袁世凯的同时,应该扶植其他各派势力。一旦袁世凯“抛弃日本而复与他国亲善”时,就踢开袁世凯,另换新工具。[①]大隈内阁基本上是按照“黑龙会”的方案,展开了侵略活动。它一方面,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又与英、法、德、俄四国一起借款给袁世凯2500万英磅,用以安定政权。
当时,日本的中国政策是“先经营南满洲和内蒙古,再向南推进我经济势力”。1914年9月2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并以此为借口,派兵在山东半岛登陆,占领了胶济铁路线和青岛,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夺到手。大隈内阁完成了其所谓的“蝎形政策”。然而得寸进尺的日本政府不但不撤兵,竟于1915年1月18日,派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条款,这就是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要求”其要点为:继承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将旅顺、大连租借地等的期限延长为99年;日本人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一带的自由来往和居住等等;著名的第五号,更列举着派日本人做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某些地区中日警察合并,由日本供应武器,设立中日合作的兵工厂以及华南铁路铺设权等项目。日本政府在谈判的同时,又增兵威胁,软硬兼施,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本在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中国终于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第五号外的全部要求。从此以后,这一天成为中国的“国耻日”。
“二十一条要求”,破坏了远东的均势,形成了日本独霸东亚大陆、自由宰割中国的局面。1916年7月,大隈内阁又缔结了第3次日俄协约,其中的第二条规定:“两缔约国之间一方在远东之领土权及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侵犯时,两国应即协商防护此等权益应取之手段”。[②]这样,大隈内阁利用欧战机会而巧取豪夺的地位与权利,又得到一种外交上的保障。同时又订立日俄秘密同盟条约,日俄假借“合力维持远东和平”的名义,实行其排除第三国,独立垄断东亚大陆的政策。至此,远东国际均势被打破,中国安全受控于日本。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掀起了反日高潮。全国人民讨袁行动,也日益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对袁世凯政权也愈来愈不信任。1916年3月,大隈内阁认为“为实行帝国的方针,以袁氏脱离中国势力范围为方便,任何人取代袁氏,都比他对帝国有利,乃无容置疑”。[③]决定“踢开袁世凯”而“另换新工具”。
二
1916年9月成立的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针对中国当时南北对立、军阀割据的局面,决定支持北方的段祺瑞派,以其为日本的代言人。寺内内阁鉴于大隈内阁提出“二十一条”遭到各国、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对,于是采取了一种“经济的财政的前进政策”。通过“西原借款”援助段祺瑞,实现“武力统一”计划。段祺瑞从日本取得了约5亿日元的借款和武器装备,客观上助长了内乱。而日本却获得了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口头承认,以及东北的吉长、吉会两路及“满蒙五路”的路权,吉黑矿山森林权,与在中国驻兵、训练警察和军队的特权。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说:“借予中国之款于三倍从前之数,但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④]由于段祺瑞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大大膨胀起来。1918年5月,日本又趁与英、美、法等出兵西伯利亚之际,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军队大批开入满蒙,控制了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段祺瑞政府于1918年9月,在《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以“欣然同意”字样,承认大战期间日本在山东取得的特权。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国际联盟一员,参加会议。中国全权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应该废除,希望将胶州湾租借地和山东铁路等德国的一切权益,直接交还给中国。而日本却以其获得德国在山东权益已有英、法、意等国承认,以及中日两国间曾有“欣然同意”换文为借口,拒绝向中国交还山东的各种权利,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和会满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却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线。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反日学生游行队伍,袭击了亲日派曹汝霖的住宅,要求惩办与日订立“二十一条”事宜的主要活动人物、“抵制日货”等。在上海,工人团体开始罢工,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
“巴黎和会”后,远东国际关系出现了新变化。美国曾于1917年秋,由于受欧战的牵制,与日本妥协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维持“门户开放及对工商业机会均等之主义”。但战后,美国跃居西方列强之首,对远东和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英法势力也重返东方,谋求恢复和扩大在华的权益。因此欧美列强不能容忍日本利用大战之机而独占中国的局面持续下去,千方百计寻找自己利益的代言人。因此,英美支持曹吴系军阀,于1920年7月同日本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进行了一场直皖战争。打败了皖系、摧毁了大战期间日本扶植下建立起来了“参战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给日本以沉重打击。
1921年5月,日本原敬内阁召开会议,确定先集中力量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扩张并利用张作霖充当日本在“满蒙”扩张的工具。因此,日本积极支持张作霖入关,与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权,顽强地维护其侵略利益。
三
直皖战争,美国获得了成功。但为了进一步在军事上、经济上压倒日本,于1921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由美、英、德、日、意、比、荷、葡、中等9国参加的国际性会议。经英美调停,中日双方激烈交涉和争论,于1922年2月4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和《附约》,规定日本将胶州湾退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备价赎回,以及日本由山东撤兵等项。名义上日本交还了山东,而实质上,仍据有山东的实权。
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以及“山东悬案”的解决,削弱了日本对华的独占地位。使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为两国间的交往改善了一些条件。同时,日本也调整了外交政策,主要与英美协调。但一旦涉及东北利益,日本将全力加以庇护。这也是日本在1922年四、五月之间的直奉战争中的行动方针。
退守关外的张作霖,于1922年6月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不受北京政府的节制。日本认为奉张能专心致力于“维护东三省的治安”,“也是极为符合心愿的事情”,决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予援助。[⑤]日本在援助奉系的同时,加紧对“满蒙”的侵略扩张活动。大力攫取东三省的路权,掠夺自然资源和土地。尤其是把延伸同南满铁路相衔接的“铁路网”置于首位。于1923年修通郑洮铁路,1924年10月修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吉林省天宝山至图们江的铁路。他们还对北满采取“重新开拓前进道路的方针”。首要目标是夺取具有高度经济、战略价值的洮南至齐齐哈尔之间的铁路修建权。1925年9月,南满铁路公司提出了一个更具有野心的《满蒙铁路网计划》,拟用20年为期,以5.8亿日元投资,修建35条,总长8828公里的铁路,准备把侵略势力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⑥]
四
华盛顿会议后,世界奉行“国际协调主义”。日本也调整了外交政策,主要是遵循与英美等国的协调,并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尽可能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集中力量加强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并重点扶持张作霖充当工具。1924年6月,日本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开始了“协调外交”。币原提出实行外交上的所谓“不干涉”和军事上的实际介入相结合的对华策略,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表面上,币原向国内外宣布日本对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的方针,而实际上,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为代表的军部一方,为加速实现大陆政策,却布置在华日本军人与奉军“共同合作”。推动张作霖、段祺瑞合作,共同拉拢冯玉祥发动政变,颠覆曹吴。段祺瑞在北京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实际上为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所控制。
币原“协调外交”表面上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但其能否贯彻,端视日本权益是否受到重大威胁而定。1925年冬,郭松龄与冯玉祥联合倒戈反奉。眼看张作霖统治即将崩溃。最后,张作霖得到日军的帮助反败为胜,俘杀了郭氏夫妇。郭松龄事件只是币原外交在“不干涉”旗号下,行干涉中国内政之实的开端。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1926年8月,广东国民政府发动了“以实视统一,复兴民族”[⑦]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包括东北的亲日派张作霖在内的北洋军阀。张作霖是日本推行“满蒙”独立政策的“捷径”。[⑧]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政府的眼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迅速发展的中国革命形势,日本朝野上下态度不一。以参谋本部为代表的日本军方,态度强硬、企图进行武力干涉。日本外务省则主张不要露骨地干涉中国革命,而应打着“中立”的旗号,暗中勾结能为日本侵华利益服务的实权派。但无论是参谋本部还是外务省,其最终目的都在于破坏中国革命。日本当局针对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对立,决定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采取了引诱分化为主、武力威胁为辅的政策,软硬兼施,力图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其拉拢的重点对象是蒋介石集团,勾结他背叛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分裂,中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又积极支持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依赖日本、取缔民众的革命活动等。
日本帝国主义在大力分化革命阵营的同时,并未放弃武装保卫侵华权益的强硬政策。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以实力接收了汉口、九江英租界。日本立即派十几艘军舰侵入长江,调1500名海军陆战队增援上海。[⑨]币原在1月12日通知英国:日本将与列强协调行动,必要时驻沪兵力可增至三四千人。[⑩]根据日本内阁会议批准的《汉口日本租界对等文件》,币原命令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警告国民政府领导人:如果中国方面依照收回英租界的经验,发生破坏日租界安宁的“盲动”,日方将“断然处置”。[(11)]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下妥协了,便赶紧派人密告高尾亨:“国民党绝不会对日租界发难的”。[(12)]
尽管如此,币原“协调外交”仍不能满足日本大陆政策的需要,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盛行,军部内的强硬论抬头,猛烈攻击币原外交为“软弱外交”。主张日本必须改变对华政策,变“消极雌伏”为“积极雄飞”。[(13)]在这种外交背景下,出现了为维护日本侵华权益的、比币原更强的田中外交。
1927年4月20日,黩武主义的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受命组阁,成立了震动一时的田中内阁。他对华“积极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利用中国之不统一,而独占中国东北。因此他公开主张赤裸裸的武力侵华政策。他上台伊始,即以武力遏制北伐进军,阻挠中国统一。1927年3月,北伐军攻下南京后,继续北上,进入山东省境。5月,田中内阁以保护在华日人生命财产为由,便不顾一切地派兵2000人至青岛,其目的是阻止北伐,夺取山东,为侵占中国东北铺路。由于日本的阻挠,以及中国国民党内讧,北伐军一时遭受挫折而缓进。孙传芳乘势反攻,来势汹汹。日本迫于北京、南京两政府的抗议,又见中国人民反日情绪激烈,国际舆论纷纷斥责,同时,孙传芳元气已复,日本出兵目的已达,遂于8月间宣布撤兵,但仍谓保有“将来日本为不得已而施行机宜之措置”的“权利”[(14)],随时都准备武力干涉革命。
田中内阁又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了名闻中外的东方会议。会议最后由田中宣布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规定了武力干涉中国的方针。会后,田中将东方会议决定的侵华方针密奏天皇,即举世震骇的“田中奏折”。“惟欲征服中国,必行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于亚洲大陆之第一大关键,在于把握满蒙权利”。这就是日本侵华的基本方针。田中还训令驻华公使芳泽,亦即只要国民党排除共产分子,田中内阁将援助蒋介石政府。
1928年1月,宁汉合作,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再度“北伐”。北伐军节节胜利,直逼济南。山东军阀张宗昌与日本勾结,许以青岛及胶济路一切权利,要求日军进驻济南,阻挠革命军的迅速推进。4月19日,田中内阁决定以保侨为名,再次出兵山东。25日,熊本第六师团5000名在青岛登陆,随即进驻济南城外。5月1日,占领济南的北方军阀撤退,5月2日,北伐军进入济南城。5月3日,北伐军同日军发生冲突,演成巷战,即济南事件。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反对,出兵目的从“保护侨民”发展到“显扬国军威信”的惩罚措施。5月7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对北伐军提出限期强硬要求,8日,日军对济南城发起猛烈攻击。尤其9日、10日,不分昼夜,集中炮轰济南城内,死伤数千人。日本内阁会议又决定向山东增派一个师团。名古屋第三师团与济南第六师团配合,于5月11日占领济南城,连同第二次和第三次增兵,日军总计1.5万人控制了山东。蒋介石的北伐军,只得迂回济南北上,冯玉祥部亦往北京进军,张作霖在北京的地位便日暮途穷。至此日本遂面临如何对付革命军之占领北京以及对东北的可能进攻。
1928年5月16日,田中内阁举行会议,决定如下方针:1.在革命军尚未到达津京地方以前,张作霖军如果要撤回满洲的话,将同意其回来。但要阻止革命军插足山海关以北;2.如果张作霖军与革命军交战或接触以后,才要退却满洲时,将不许武装的南北两军进入满洲。5月18日又宣布了阻止北伐军出关维持满洲全局的“和平与秩序”的政策。田中说:“满洲治安的维持为帝国所重视,假令有扰乱该地治安,或有造作扰乱该地治安之原因与事态发生,则帝国政府将极为防止,故于战乱进展之京津地方,其祸害或将及于满洲之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之治安,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有效的处置”。[(15)]由此可见,日本重视东北地区,十倍于山东。因此,日本驻华机关,根据内阁决定,一方面敦促张作霖从关内撤回东北,另一方面表示日本不阻止蒋介石北伐军进入京津地区,但绝不许进入“满洲”。同时,以军部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则阴谋乘张作霖败退之机,除掉张作霖造成东北混乱,又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动关东军武装占领东北。1928年6月4日炸死了张作霖,充分暴露了日本吞并东北的狂妄野心。饱尝国难家仇之苦的张学良继起后,不顾日本的反对、阻挠和威胁,于1928年12月29日,在东北三省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宣布东北“易帜”,使田中内阁控制“满蒙”的罪恶计划彻底破产。日本对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一切干涉,完全归于失败。1929年7月2日,田中内阁不得不在一片攻击声中引咎辞职。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并没有因为田中内阁的倒台而告终,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使近代中日关系为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所代替。
注释:
①惠勒:《中国与世界战争》,第191~196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8页。
③〔日〕臼井胜美:《近代日本外交与中国》。
④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卷下,第137页。
⑤日本外务省档案:《袁世凯帝制计划一件,满洲举事及宗社党动态》下卷,第31页。
⑥吉林省社科院编:《满铁史资料》,第2卷,第3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47~849页。
⑦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第1页。
⑧日本外务省档案:《袁世凯帝制计划一件,满洲举事及宗社党动态》。
⑨日本外务省档案:《英国对华出兵经纬》。
⑩日本外务省档案:《币原致芳泽电》。
(11)日本外务省档案:《币原致高尾电》。
(12)日本外务省档案:《高尾致币原电》。
(13)《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93~94页。
(14)〔日〕参谋本部编:《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1971年重印本,第24页。
(15)《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第116页。
标签:张作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二十一条论文; 段祺瑞论文; 田中义一论文; 甲午战争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一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