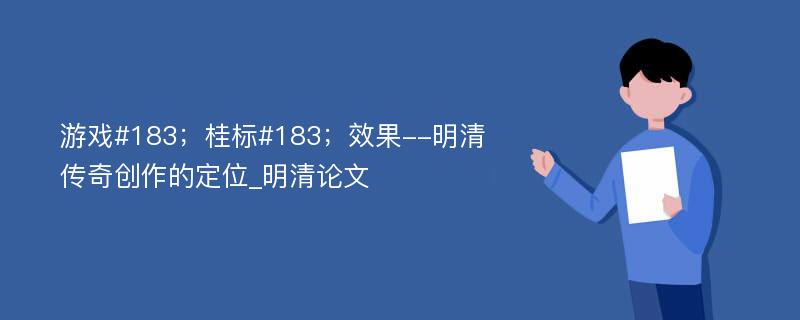
游戏#183;圭臬#183;效应——明清传奇创作取向今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取向论文,效应论文,传奇论文,圭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经·小雅·甫田》中这样写道:“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谷我士女”。这是一个上古人民以音乐(甚至还含有舞蹈)来迎祭田神、祈求甘雨,感谢赡养之恩的壮观场面。《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记载了这样一则典故:有一个叫癸的唱歌艺人,他的歌声能让盖房子的工人忘了疲劳,而他的老师射稽的歌唱得更好。在癸的歌声中,工人们筑了四板墙;在射稽的歌声中,工人们筑了八板墙。进一步测试墙的坚实程度,射稽唱歌时所筑的墙整整比癸的坚实了两倍半。
这两则记载显示了上古国人已意识到文艺具有某种力量,具有某种社会的功效,进而也懂得了这种力量还具有“正向”与“负向”的社会效应。即“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有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荀子·乐论》)。就是说传受双方有一个相对应的心理取向问题,去激活或鼓励扩展何种心理取向,有识之士决不可等闲视之。
可我国当今的少数文艺作品似乎忽略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规律,表现出“太戏”“过虚”的倾向,有背于文艺创作和社会审美的圭臬(准则或法度)。“太戏”是指作品显现出油滑庸俗、玩世不恭甚至丑陋低下的倾向;“过虚”是指凭虚而造了无生趣,无视了国人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倾向。对此类问题的认识,明清时期的许多著名的传奇剧作家、批评家就早已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给予了评判。他们所洞悉并揭示出的传奇戏曲创作规律,或许对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不无借鉴作用。
明末曲评家祁彪佳曾对明传奇戏曲创作中出现的对历史人物、历史素材进行庸俗表现、庸俗处理的现象,和津津乐道于庸俗的人生趣味之现象进行了批评。如明传奇《三桂记》所叙:退官家居的全正乘妻子外出时与侍女小桃偷情,后小桃怀孕,全正出宦,幸得全正长子全孝的保护,小桃生下双胞胎,取名大桂和小桂,两个弟弟在全孝18年的教养后,与全孝一同进京应试齐中高榜,朝廷为此对其全家进行了旌表和封官。祁彪佳评点此剧时说:“但以老夫狎一青衣,境界庸俗,无堪赏心耳”。祁在对《鸾绦记》传奇的批评中,将这一观点说得更是明白,“记王爽、韩琦自为诸生时,各狎一妓,牵缠到底。吾不知作者何所取义,而蹈袭庸腐至此也。”
祁彪佳更是不赞同有损于历史上侠烈之士形象的创作,他在评《镶环记》传奇时说:“即蔺相如怀璧一事,大有侠烈之致可传,何必增出闺阃(内室情节),反入庸俗”。究其原因,在祁彪佳看来,“词才、词学,而归之词品”(“词”指“填词”即戏曲创作),如果作者眼界狭隘,必会“手笔入俗”“气格卑下”。
明清剧作家和批评家们正视了戏曲强大的社会功用性,因此明确地提出了戏曲具有“讽谏”“教化”“主情”“史鉴”等功用的观点,也正是这种明确的文人倾向性,使得明清传奇创作成为元杂剧之后的又一座文学艺术高峰。而这座高峰的标志,无疑是作家们更多地把眼光落在了充分发挥戏曲“正向”的社会功能上。像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以微贱者的“侠义高风”直刺“台阁簪缨”显达者的卑污,简直“可补正史之缺”。孔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此剧所涉“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自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可比”。这种史迹着实,小处渲染可虚的创作方法,的确能起到“知三百年之基业,隳(毁坏)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未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起到了“史鉴”的巨大作用。
再如冯梦龙改定的《精忠旗》传奇,高度歌颂了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痛斥了卖国贼秦桧一伙。其创作目的正如冯在剧中所言,为让“贤奸今古同芳臭,愤懑心头借笔头,好教千古忠臣开笑口。”此剧惩恶扬善,在讽谏和疏导人心上令人极为称道。
明清传奇作家注重发挥戏曲“人人也深,化人也速”的功能作用,也是戏曲生存和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剧作家们并非仅片面地强调传“正声”这一社会功能,而且也注重传奇戏曲游戏娱乐之功能,并能将两者极其艺术地融合在同一部作品之中。而且这种“游于戏曲”的心理几乎成了明清剧作家们的一种价值取向。因为戏曲在萌芽之初就与“游戏”共生,人类社会少不了“游戏”,上古具有戏曲萌芽因素的蜡祭活动,就有娱人的“游戏”成分。所以苏轼说:“‘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这里化装扮角的游戏娱乐性与敬奉八方农事之神的功利性并存。汤显祖就善于“游于戏曲”,他的《牡丹亭记》是千古之绝唱。其友黄汝亨在《复汤若士》文中评曰:“得《牡丹亭记》扩之情魂俱绝。三昧游戏,遂尔千秋乎!”潘之恒也说:“叙友临川汤若士,尝作《牡丹亭还魂记》,是能生死、死生,而别通一窦于灵明之境,以游戏于翰墨之场”(《鸾明小品·情痴》)。但《牡丹亭记》的价值所在还是在于汤显祖以“游于戏曲”的方式来与当时的道学相抗衡。
李渔干脆就更为直接地说:“传奇原为消愁设”,“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皆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风筝误》)。李渔追求的是用戏曲来娱人娱己,让人在解颐之余忘却人间的烦恼,但他的“游戏”解颐又是极有分寸的。像他的《风筝误》传奇,就是借用误会手法,让人在开心一笑的同时也看到了错综复杂的人情世态,曲终而余味犹存。
再如孙钟龄的《东郭记》传奇虽取材于《孟子》,但却能加以融合发挥,其间荒唐的人物行径和荒诞的故事情节,使其能“屡出笑噱”,真个是“掀翻一部《孟子》转转入趣”(祁彪佳语),并穷形尽相地嘲讽了世态,于“庸腐”中出了“神奇”。像这类寓心志于“游戏”之中的佳构,怎能不起到“解尘网、消世虑”舒缓人心的作用呢。
可见游戏因素在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但从戏曲艺术生命力的角度来说,必须要有艺术的分寸,必须处理好游戏娱乐与“正声”功能的关系,即戏曲创作需有艺术审美的圭臬。正像明代戏曲家梁廷枏在《藤花亭曲话》中所说的,做到“庄而不腐,奇而不诡,艳而不淫,戏而不谑。”作品有了这样的艺术圭臬,才能气壮地进入戏曲艺术的堂奥。在具体的创作中要把握住这一艺术的圭臬,李贽认为重要的是平衡好“戏”与“真”的关系。他在《琵琶记·文场选士》总批中曰:“戏则戏矣,倒须似真,若真者反不妨似戏也。今戏者太戏,真者亦太真,俱不是也。”就是说,戏谑调笑的情节、奇谲的内容应当具有生活的基础,具有生活真实的一面;描写实有的情节,也可加入设计想象的内容。为追求“戏剧性”和“无奇不胜”的奇谲性,如果不惜违背生活的本质,而且这种“奇谲”性又是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已超出了人们正常的心理理解范围,根本没有生活本质精神沿展性的“过虚”编造;或者太拘泥于生活的真实性,却缺乏必要的艺术渲染,这些都是不妥当应予以否定的。所以李贽主张应将两者进行艺术的调和,将时代生活的本质精神融于奇特有趣的情节之中,才算平衡好了“戏”与“真”的关系。
在明清戏曲家对传奇戏曲的品评中,已涉及到了戏曲作品的内部结构问题,它使我们意识到,大凡能进入艺术堂奥的戏曲作品,笼统地说是具有表层和底层的结构,而处于戏曲作品表层的音乐、曲词、情节结构要素和处于底层的“意旨”“情感”要素总是对应着积极的社会心理结构(由情感、情绪、思想、需求、接受习惯、思维方式等要素构成)的。因此作家在创作时,首先就应当将积极的心理结构艺术地溶化到作品的表层特别是情节结构中去,以此再渗透到作品的底层中来,这样大众才能够对作品产生认同感,进而引发欣赏效应。从能动的方面说,作家这种更自觉的蕴蓄,可强化社会进步所需的心理状态。这其间就包含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创造消费者”的思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202)。这是明清传奇创作及其品评取向所给予我们的启迪。总之,明清传奇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经验是值得当今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