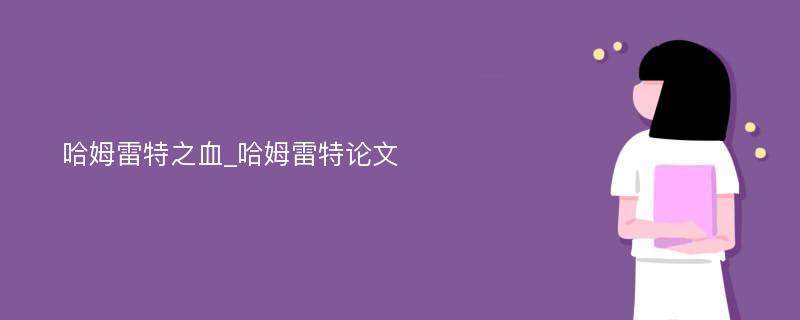
哈姆雷特的血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血气论文,哈姆雷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哈姆雷特》这部剧作中,莎士比亚展现了对血气的丰富理解。克劳狄斯弑兄篡位的恶行,激起哈姆雷特王子的强烈义愤。这种义愤促使王子寻求复仇。然而,正是在复仇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暴露了哈姆雷特的血气问题。此外,在报复不义行为时,哈姆雷特不知不觉逾越了正义的标准,走向正义的反面。尽管哈姆雷特最终杀死仇人,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莎士比亚看到了血气的极度复杂和含混,他拒绝简单地看待血气问题。通过《哈姆雷特》一剧,莎士比亚进行了一系列思考:血气的含混性何在?有没有标准界定由血气引发的行动的正义与不义?血气问题又蕴含着莎士比亚对潜在统治者的何种期待?
一、血气的含混性
对评论界来讲,哈姆雷特的性格似乎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同属一个时代的歌德与柯勒律治(S.T.Coleridge),对于哈姆雷特的勇敢,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歌德认为,哈姆雷特的灵魂过于脆弱,根本无法担起时代赋予他的重任。柯勒律治则表示,哈姆雷特“被刻画成他的时代最勇敢的人之一”。①在第一幕第三场,雷欧提斯说哈姆雷特是“血气(blood)上轻浮”的人(1.3.6)。撇开他们各自的理由,至少,他们的分歧提醒我们,在考察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时,应充分认识其复杂性。
可以说,血气问题贯穿着《哈姆雷特》始末,血气首先激起哈姆雷特的复仇心,进而导致他为寻求报复展开行动。血气在《哈姆雷特》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哈姆雷特》开篇便呈现了血气问题。埃尔西诺的守卫们在分清敌友前后的不同反应,充分体现了血气的双重性质:对敌人严酷,对自己人友善。“那边是谁?”②开篇的质问马上透露出某种咄咄逼人的敌意。令勃那多吃惊的是,对方非但没有自报家门,反将针对自己的问话回掷过来。而在确定对方的身份后,他们即刻表现出相互的友爱和关切。“站住!你是谁?”霍拉旭和马西勒斯随后的到来,再次强调了这一主题。
对敌人严酷,对自己人友善,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柏拉图《理想国》(又译《王制》)卷二中的城邦护卫者。苏格拉底将护卫者比作“狗”,认为护卫者身上存在两种相反的品质。狗的脾性恰恰是对熟人温和,对陌生人凶狠(《理想国》375e)。相应地,透过《哈姆雷特》第一幕,我们得以瞥见哈姆雷特王子血气的这种双重性。哈姆雷特由威登堡回到丹麦,面对父死母改嫁的残酷现实,沉浸在悲痛的世界里。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显然并不友善。在这位王子眼里,如今,亲族与路人毫无二致,由此便模糊了亲族关系。在对先王之死的反应上,哈姆雷特的态度显得截然不同于克劳狄斯和乔特鲁德。新王和母亲认为,先王的死是件“很普通的事”(1.2.72、98—99)。这对王室夫妇对先王之死的态度显得极不自然。他们的冷漠否定了家族的自然亲情。克劳狄斯与乔特鲁德的反自然态度,激起哈姆雷特的强烈愤慨。按照哈姆雷特的说法,“没有推理能力的野兽也会悲伤得更久”(1.2.150—51)。为此,哈姆雷特拒绝向克劳狄斯示好,也拒绝了后者的示好(1.2.66—70),并对母亲的劝慰反唇相讥。在对待父亲之死上,哈姆雷特与他们的分歧显然没有调和的余地。昔日的亲人,变成了路人。而哈姆雷特王子与霍拉旭的关系,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当霍拉旭谦卑地表示,“我永远是您卑微的仆人”时,哈姆雷特答道,“不,你是我的好朋友”(1.2.162—63)。剧本稍后表明,霍拉旭成了哈姆雷特唯一可推心置腹的朋友。在哈姆雷特得知新王用毒害先王的方式僭窃王位时,亲人就变成了最大的敌人,他指誓要为父亲报仇。在哈姆雷特看来,僭主的恶行打破了现世的正义秩序,这个时代已乾坤颠倒,他要惩治僭主,负起匡扶正义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开场一幕中,莎士比亚不动声色地引入了“敌”与“友”的含混性。虽然勃那多称霍拉旭和马西勒斯为“伙伴们”(rivals,1.1.11),但rivals一词暗含的敌意似乎打破了这种友好氛围。直到霍拉旭以“都是朋友”(friends,1.1.13)确立守卫们的关系后,场面才得以回复平静。同样,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和乔特鲁德对先王之死的不同态度,也使哈姆雷特选择不再善待这两位亲人。他甚至不愿作出友好的样子。可见,敌友关系具有含混性,并非一成不变——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视为敌人。敌友的含混对应着血气的含混。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如何辨清真正的朋友和首要的敌人,乃是哈姆雷特的当务之急。
通过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莎士比亚展现了血气含混的另一个层面。莎士比亚所呈现的血气,与柏拉图的理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看到,在《理想国》卷四中,苏格拉底起初将血气定义为人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但我们随后就发现,血气并不那么容易界定。它既与欲望有关,又与之冲突,有可能是理性的盟友(《理想国》439e—441a)。血气的含混,不仅源于自身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它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它与灵魂中其他部分紧密相关。血气与欲望的关系似乎尤为模糊——阿基琉斯的血气不就是对荣誉和胜利的欲望么?如此看来,血气不就是欲望吗?不过,我们注意到,在《理想国》里,当格劳孔首先提出这种观点时,苏格拉底接着悄悄改变了他的看法,并让他承认,血气可能是理性的盟友。苏格拉底指出,正是血气促使人责骂自己的卑下欲望,让人产生羞耻心。由于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如死尸),满足了人的低下欲望,人会变得对自己勃然大怒,进而责骂自己。血气意欲的是更高的东西。但血气本身并没有能力区分高与低。③只有在理性的劝谕或引导下,血气才能上升到这种认识。
在政治世界中,作为一种政治激情呈现出来的血气,追求的是欲望中高的部分,譬如阿基琉斯的血气。追求战场最高的荣誉,引领他所向披靡,立下累累战功。血气可谓发挥到极致。然而,当血气达到极点时,血气又变得极易失控、不辨敌友,尤其是在它对荣耀的渴望受到阻碍时。这里便暴露出血气的一个问题。由于正当追求的荣耀没有实现,阿基琉斯转而抛弃一名战士应有的原则:损敌扶友。他以拒绝的方式报复这个对他不义的世界。为此,他所处的政治世界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④单一追求荣耀的血气,会严重威胁到政治共同体的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讲,阿基琉斯的血气变成了欲望。
哈姆雷特的叔父以违反自然的方式僭窃了丹麦的王位,他不仅犯下了可怕的谋害血亲之罪,而且犯下了政治世界中最严重的罪行。杀亲和弑君可谓人性的罪大恶极。前者无疑剪断了与家族的纽带,后者则拆散了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和稳定的根基。既然叔父已不配成为亲人,哈姆雷特便反戈相向。为了展开复仇,哈姆雷特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装疯。疯狂是血气的极端表现。哈姆雷特装疯原本是为了铲除僭主,重整政治秩序(血气向上),结果却走向反面,造成一系列悲剧,并使丹麦落入他国手中(血气向下)。
由于缺乏辨认高低的能力,血气在一定意义上是盲目的。摆脱理性指引或处于愤怒状态的血气更是如此。此时的血气不仅不听从理性的劝谕,反而可能与理性对抗,因为它“不愿承认任何质疑其目标的正当性的东西”⑤。这样一来,血气就有滑向欲望的可能。在灵魂中,欲望与理性相对,血气则可能在理性的引导下上升。然而,一旦理性的劝谕失败,血气便有与欲望结合的危险。哈姆雷特的困境源于他的灵魂世界。归根结底,取决于他的血气归顺人性高的部分的统治,还是滑向人性低的部分。鉴于鬼魂一上来便激起哈姆雷特的愤怒和进行复仇的血气,如何处理好血气与复仇的关系,就成了哈姆雷特必须面对的难题。
二、道德义愤的转化
血气在本质上关乎正义。对不公正之事的不满最易激起人的血气,通常表现为愤怒。在这个意义上,由不公正所引发的愤怒就是义愤。血气的常态是道德义愤,但由于血气的含混,道德义愤也就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⑥复仇作为一种极富血气的行为,倘若缺乏正确的引导,就极易越过道德义愤所规定的范围。因此,净化和提升血气势在必行,但这依赖于在灵魂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经提升的血气,可以将人引向追求卓越和荣誉。血气也由此表现为对正义的热忱。显然,对一个身处政治共同体中的人而言,血气过强或过弱都有碍于追求正义。因为,不加限制的血气无疑会威胁到政治秩序得以稳定的根基,譬如荷马笔下的英雄阿基琉斯;血气不足则无法激起人们追求卓越、献身公共事务,并关切共同体的福祉,这对政治共同体而言并非好事。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Henry VI)就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政治血气羸弱的君王,如何给自己的统治造成混乱,并最终祸国殃民。然而,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对血气问题的思索没有停止,在很大程度上,这部戏剧是他对自己前期思索的深入和反思。
在《哈姆雷特》中,我们显然没有看到血气的净化。的确有某个东西干预了哈姆雷特的血气,并导致他的血气一步步走向狂热与混乱。这个东西就是鬼魂。对于“这东西”的来历,评论家们莫衷一是。但是,无论鬼魂来自炼狱还是地狱,这个打“从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3.1.78—79)而来的东西,显然是低下的。鬼魂是非自然的,它不属于这个世界。在开场一幕中,守卫们谈论鬼魂时,多次用“它”或“这东西”指称(1.1.20、28—29、39、41—44、49—50、54、58、125、138—147)。尽管鬼魂伪装得几乎天衣无缝,但它“冷酷无情、甚至暴躁”,完全没有哈姆雷特所描述的“风度和完美”。⑦正如霍拉旭注意到的,鬼魂一出场便满脸“怒容”(angry,1.1.61),且“哀大于怒”(230)。鬼魂血气的变化似乎预示了哈姆雷特血气的变化。哈姆雷特出场时一度萎靡不振,沉浸在悲痛与忧郁之中,但在非自然且盛怒的鬼魂的刺激下,他燃起了复仇的血气。然而,哈姆雷特的血气非但没有得到净化,反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显然,由低下的鬼魂引导,哈姆雷特的血气不可能得到净化。鬼魂要的是控制。我们看到,鬼魂一上来便诉诸哈姆雷特的义愤,使之“像惊恐万分的豪猪身上的刺毛一样森然耸立”(1.5.19—20),接着提出为其复仇的要求,最后还要他“记住我”。看来,这的确是一匹闯入哈姆雷特灵魂的特洛伊木马。⑧鬼魂违反了自己宣称的“禁令”,向“血肉的凡耳”诉说了“永恒的秘密”(1.5.13—14)。面见鬼魂的哈姆雷特,也没有为自己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感到羞耻;他不仅没有责骂自己,反将鬼魂的命令谨记于心。见过鬼魂后,哈姆雷特极度愤恨僭主克劳狄斯。鬼魂提供的真相激起哈姆雷特的强烈义愤,并让他下定复仇的决心。不过,愤怒总是以自己的立场去做出判断。这样,愤怒之大总是自以为是,容不得他人质疑自己的判断。因此,道德义愤的性质极易改变。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义愤“经常是不合理甚至不道德的血气”。⑨我们会看到,当这种愤恨冲决而出时,哈姆雷特任由无度的愤恨将自己引向狂热。
质而言之,哈姆雷特铲除僭主的行为本身,是一种政治负责的行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血气本身的含混,使道德义愤的标准显得极为模糊。有正当根据的道德义愤,很容易转化为无正当根据的道德义愤。哈姆雷特对克劳狄斯不义行为的愤恨,既激起他拾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也使他产生此世普遍存在恶行的想法。哈姆雷特不控制自己的血气,致使他对正义的热忱,不知不觉中转向愤世嫉俗。因此,他撒开一张抨击的大网,像斗士一样“拿起武器反抗人世无涯的烦恼,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3.1.58—59)。随着这张网慢慢铺开,身边的人纷纷落网,首先是哈姆雷特的母亲乔特鲁德。尽管乔特鲁德并非无可指摘,她的迅速改嫁具有一定的含混性,但哈姆雷特斥之为“乱伦”,并一再借机羞辱乔特鲁德。他对母亲的愤怒和谩骂令人惊讶。哈姆雷特无疑认为,母亲改嫁也是一种恶行,并且是一种女人的恶行。在那段关于生存还是死亡的独白中,哈姆雷特列举了七种不堪忍受的恶行。正是在这里,最直观地体现了哈姆雷特如何由有正当根据的义愤,转向无正当根据的道德义愤。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3.1.69—73)
施特劳斯注意到,实际上,哈姆雷特对中间那项恶行(被蔑视的爱情的惨痛)的控诉,并无正当根据。⑩被蔑视的爱情的惨痛,并非恶行。苦苦追求某个人,那人却不爱对方,这构不成恶行。不难发现,在哈姆雷特所列举的恶行中,他亲历的是与奥菲丽娅的爱情。他向奥菲丽娅求爱遭到拒绝,这在哈姆雷特眼里,竟成了一种不堪忍受的恶行。不仅如此,他随后辱骂并无情对待自称为心爱的人,似乎就是在正当惩罚她的“恶行”。因此,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残酷对待奥菲丽娅感到愧疚,反而变本加厉。倘若奥菲丽娅之前涉嫌充当波洛涅斯和克劳狄斯的诱饵,哈姆雷特责备她倒情有可原,但从他对奥菲丽娅的无休止谩骂中,我们看到,他的义愤矛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向了美好的事物,哈姆雷特现在相信:“美丽可以使贞洁变成淫荡,贞洁却未必能使美丽受它自己的感化;这话从前是怪诞之谈,可现在时间已将它证实”(3.1.110—14)。可以想见,哈姆雷特在说这番话时,脑海里闪现的是母亲。就这样,对母亲的愤怒一步步漾开,首先波及奥菲丽娅,“进尼姑庵去吧”;接着是婚姻(女人),“没有结婚的不准再结婚”;最后波及全人类,“我们都是些十足的坏人”(3.1.120—24)。其实,严格说来,哈姆雷特所列举的“傲慢者的冷眼”与“小人的鄙视”也算不得什么恶行。尽管遭人冷眼和鄙视会激起人的愤怒,但实际上,这些行为并不关乎正义。傲慢者和小人的行为仅仅是个人行为,不能当作恶行。
哈姆雷特在剧中的行为表明,他正是像一名斗士那样,选择与此世普遍的恶行作斗争。在他思考生与死时,哈姆雷特一开始便为自己预设了两种生活方式。他要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选择他认为的更高贵的生活方式,是“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还是“拿起武器反抗人世无涯的烦恼”?愤怒为英雄行为提供的理由并不合理,愤怒之人认为,由于此世普遍存在不义行为,有必要惩罚诸种恶行。这就是哈姆雷特为何如此残酷对待波洛涅斯的尸体的原因,也是他咒骂命运的原因所在,“啊,对了;她本来是一个娼妓”(2.2.231)。对哈姆雷特来讲,命运变幻无端,不可捉摸,“人间哀乐感动不了天庭”(2.2.454)。上天并没有看顾人类,致使邪恶压倒正义。这在哈姆雷特看来也是恶行。然而,哈姆雷特诅咒命运使他遗忘了,对一个准备充分的人来讲,命运也可以是“恩人”,譬如借助良机铲除暴政的共和国奠基人布鲁图斯。(11)命运的确给了哈姆雷特这么一个机会,遗憾的是,他却让这个绝好的机会一去不复返。
为了明确展示哈姆雷特的内心世界,莎士比亚随后精心策划了一幕戏。这幕戏发生在“戏中戏”之后,恰好处于整部戏剧的中心(3.3)。微妙的是,正当哈姆雷特的《捕鼠机》成功捕捉僭主的罪恶灵魂之时,莎士比亚又借此让我们窥见了哈姆雷特的灵魂。卡茨(Catherine Brown Tkacz)认为,祈祷一幕构成了《哈姆雷特》的道德中心。(12)的确,哈姆雷特在这里所作出的道德抉择,决定着全剧其他无辜者的死亡,更重要的是,他展露了一个身负政治共同体福祉的王子的致命弱点。哈姆雷特究竟出于何种考虑,竟抛弃了在这里实现自己一直为之努力(虽然他的努力并不成功,比如他的装疯)的复仇计划呢?
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我也算复了仇。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那么,天国的路为他敞开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3.3.73—86)
显然,哈姆雷特不愿在此世复仇,他不愿让恶人上天堂,因为,倘若他在恶人祈祷时杀死他,将使之上天堂,这是对身在地狱或炼狱中的父亲行不义。毋庸置疑,潜入哈姆雷特灵魂的那匹特洛伊木马在作怪。鬼魂描述的在地下所受的种种磨难,深深地烙在哈姆雷特的心里。为此,哈姆雷特不仅寻求此世的复仇,他还寻求永罚。唯有永罚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复仇。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人们会发怒,只有听到理智的呼声才会息怒,就像狗听到牧人的声音一样(《理想国》,440c—d)。然而,此刻给哈姆雷特发出命令的显然不是牧人,而是鬼魂临别时的“记住我”。鬼魂的声音让哈姆雷特决定收刀入鞘,以伺克劳狄斯在实施恶行时进行复仇。不过,正是哈姆雷特的这个决定,使他对弑君者的义愤失去了正当根据。就铲除僭主而言,哈姆雷特所要做的就是在此世此地寻求报复,而非逾越这个标准,去寻求永罚。正因为此,不少评论家称哈姆雷特的选择“邪恶”。其实,哈姆雷特的确不该在此时结果这名僭主的性命,原因不在于他所宣称的永罚,而在于他自始至终都没能认清的另一样东西(下文会论及)。
正如布鲁姆(Allan Bloom)所言,哈姆雷特通过另一个世界的透视镜看待此世,致使此世变形。(13)对此,哈姆雷特本人显得浑然无知,他认为自己是“代天行刑的凶器和使者”(scourge and minister,3.4.173)。为此,他展开了铲除恶行的行动。哈姆雷特没有为自己莽撞杀死波洛涅斯的行为感到羞愧或自责,反而认为这个老人家完全咎由自取。在处死两位儿时的老友上,这种含混性更加突出。克劳狄斯召见他们,起因于哈姆雷特最近变得“疯疯癫癫”,为此,这两位老友欣然前来为哈姆雷特排忧解闷;当哈姆雷特犯下谋杀罪被送往英国时,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愿意陪同他一道前往。然而,哈姆雷特对他们的草率处死方式,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尤其是哈姆雷特在信中的特别命令,要求对方将他们立即处死,“不让他们有从容忏悔的机会”(5.2.46)。哈姆雷特对不义的僭主的愤怒,使他迁怒到身边的所有人。然而,我们注意到,剧中了解真相的人,只有哈姆雷特和克劳狄斯两人。克劳狄斯并没有以公开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其他人对他的暴行一无所知。哈姆雷特对波洛涅斯和两位儿时好友的处置,并无正当根据,因为悖谬的是,在不晓得现任君王为僭主的情形下,他们执行君王的命令,只是在行使作为臣子的职责。何况,君王的命令并非毫无根据:波洛涅斯暗中监视哈姆雷特,乃因他发了疯;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斯特恩押解哈姆雷特去英格兰,是因为他鲁莽地杀死波洛涅斯。哈姆雷特鲁莽之下杀死朝臣波洛涅斯的疯狂之举,(14)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对现任君王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莎士比亚借罗森格兰兹之口,向我们道出了君主薨逝的可怕场景(3.3.15—23)。这在备战时期的丹麦,尤其值得警惕。
三、血气与政治共同体的维系
人类出于种种原因选择了群居的生活方式,并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政治共同体,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相互依存,也懂得抵御外敌,因为他们晓得,这与他们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哈姆雷特》开篇便向我们展示,丹麦受到外敌的威胁,为了应对挪威的入侵,丹麦正加紧防卫,紧张备战。显然,丹麦的局势并不妙。“生得一副未经锻炼的烈火也似的性格”(1.1.95)的挪威王子,正纠集一群无赖之徒,企图夺回挪威输给丹麦的一块土地。丹麦危在旦夕。现在,身为丹麦的王子,哈姆雷特的问题是,面对僭主和外患并存,如何处理自己的义愤?
有评论家指出,铲除暴君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首要任务,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明显的基本事实,即丹麦当时的处境并不允许哈姆雷特作出这种举动。可以预见,僭主克劳狄斯一铲除,丹麦就会落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哈姆雷特毕竟是王子,他还只是一名“王位继承者、未来的君王”。(15)他毕竟还没经过战争的洗礼。在内有僭主当政,外有敌军压境的情形下,哈姆雷特要作出何种抉择,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将血气问题置于丹麦的处境下重新审视,我们发现,血气最初所蕴含的损敌扶友的含义极为丰富。对整个丹麦民族而言,僭政和侵略这两种行为,都是对丹麦政治共同体行不义。现在作为一国之君的克劳狄斯,因其弑君篡位的恶行,侵犯了整个丹麦共同体的利益,理应成为全民的头敌,哈姆雷特完全有责任担起推翻僭政的责任。然而,对身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人来讲,战争这一非常时期危及的不仅是个人及其家族,还直接关系到整个共同体的生死存亡。因此,这一非常时期赋予他们的特殊任务是联合一致抗敌。战争时期对敌人的最大伤害.就是对朋友和国家的最大义务。(16)然而,在履行这种义务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清谁才是当前的最大敌人。《哈姆雷特》中展现的情形清楚地表明,丹麦目前的最大威胁来自挪威的侵略,而非克劳狄斯的僭政。我们看到,尽管克劳狄斯的外交手段实在算不得高明,甚至糟糕透顶——他竟让对丹麦虎视眈眈的挪威敌军取道自己的领土去攻打波兰,但僭主克劳狄斯也在尽力恢复丹麦共同体的秩序。第一幕第一场展示了丹麦民族彻夜不停备战的情形,接下来的一幕展示了他在尽力行使一名君王的职责。此外,克劳狄斯新近还取得了对英国的胜利。不同于僭政,在外族人的进攻下,丹麦民族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kairos)。
丹麦与挪威的宿怨源于一场决斗。老哈姆雷特曾以生命和领土为赌注,接受挪威老王的挑战。这场比试“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老哈姆雷特最终胜出,并由此赢得挪威的一块领土。现在,福丁布拉斯要“用武力和强迫性条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1.1.101—103)。这无疑是挑起丹麦民族与挪威之间的一场不义之战。我们期待,哈姆雷特作为丹麦未来的统治者,能够认清当前的局势,对丹麦的侵略表现出应有的义愤。然而,他对待挪威敌军的态度令人吃惊。
直到第四幕第四场,丹麦王子才亲眼目睹敌军在自己领土上经过的场景。哈姆雷特直面了登陆的军队,但遗憾的是,他并没看清真相。对于挪威的侵略,哈姆雷特显得漠不关心。当挪威军队在福丁布拉斯王子的带领下穿过丹麦国境时,哈姆雷特显然没有洞穿其中的诡计,他询问队长,“他们是要进攻波兰本土呢,还是去袭击某个边疆?”(4.4.14—15)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边疆所指何为显得含混不清,这愈加凸显了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尤其当我们联想起开场一幕中,守卫们在埃尔西诺城堡守卫边疆的情形。在地理位置上,边疆标志着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分界。它在实际上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完整和尊严,与邻国关系的好坏,最直接地体现在边疆问题上;边疆可谓两国关系的晴雨表。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显得极为脆弱,当两国交恶时,最先受到侵扰的就是一国的边疆。开场一幕展示了挪威对丹麦边疆的侵扰,考虑到挪威与丹麦的宿仇,挪威军队如今迅速地将矛头转向波兰,个中蹊跷不免令人生疑。即便福丁布拉斯的理由站得住脚,鉴于丹麦与波兰毗邻,一旦波兰的边疆受扰,丹麦的局势也危如累卵。何况,挪威要攻打波兰,必须取道丹麦。谁能保证,这个雄心勃勃的挪威王子不会借机攻打丹麦?然而,哈姆雷特显然没考虑到这些,他没有以丹麦王子的身份审视这支军队,相反,他显得超身事外。悖谬的是,哈姆雷特能够站在挪威王子的立场上评断他的雄心,却无法从自己的立场审视丹麦的处境。在他看来,这些无谓的战争,不过是劳民伤财,毫无意义,“为的是博取一个空虚的名声”。正因为如此,面对外敌威胁的哈姆雷特,并没有“为了一根稻草之微,慷慨力争”。挪威王子的雄心一定程度上激起哈姆雷特的血气,但哈姆雷特想到的依然是自己的“大仇”——“我的父亲遭人杀害,我的母亲让人玷污”(4.4.56)。显然,哈姆雷特并没有认清谁是目前最大的敌人。这致使他在面对可能的外敌入侵时置若罔闻,并依然将义愤的矛头指向僭主。
哈姆雷特为何忽略了自己身为王子,负有保障国家的职责呢?通观全剧,哈姆雷特并没有认识到何为王子,更不消说身为王子的职责,倒是雷欧提斯认识到,王子的“意志并非他自己的……因为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兴盛取决于他的决定”(1.3.17、19—20)。并且,就在他劝说奥菲丽娅警惕哈姆雷特的感情时,“血气”一词首次在剧中明确出现。通过将国家的福祉与血气集中到哈姆雷特王子身上,莎士比亚似乎意在暗示,潜在统治者的血气关乎国家安危。因此,哈姆雷特要如何把握自己的血气(义愤),就在此埋下伏笔。然而,在整部戏剧中,哈姆雷特几乎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行动。最为糟糕的是,在最后一幕公开谴责克劳狄斯犯下叛国罪的哈姆雷特,也不知不觉地犯下了同样的罪行:他竟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入侵者福丁布拉斯。其实,综观哈姆雷特对丹麦的态度,一切都不难解释。得知父亲死亡真相后,哈姆雷特王子的种种宣称,都让我们感到,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怀着强烈的不满,“全丹麦从来不曾有哪一个奸贼不是一个十足的坏人”(1.5.123—24),丹麦是全世界最坏的一所牢狱。对僭主的义愤,最终使他蔑视自己的祖国。哈姆雷特善于以超然的眼光审视丹麦的一切,结果成了一名“在丹麦的外国人。”(17)
从天性上看,哈姆雷特可谓“世界主义王子”。(18)正如罗森格兰兹所说,“丹麦是个狭小的地方,不够您发展”,哈姆雷特梦想着成为无限空间的君王,“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2.2.274—75)。因此,哈姆雷特蔑视人类的一切东西。人类的肉体可朽、可厌;人类的功业虚无缥缈,伟大的亚历山大,最终不过成为一抔黄土,凯散的尸体也终将化作烂泥(5.1.187—205)。哈姆雷特的行动从来不是为了共同体的荣誉,激起他行动的动力是对此世普遍不公的愤怒。他野心勃勃地企图荡涤这个不洁的世界。然而,政治世界中的正义是有限度的。此世无法向哈姆雷特许诺一个纯然正义的世界。政治世界的限度要求哈姆雷特必须限制自己的义愤,因为,试图超越政治共同体的人,非神即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3—4)。哈姆雷特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自己当成丹麦共同体中的一员。身为一名深受民众爱戴的王子,倘若哈姆雷特想复仇,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动民众——在第四幕第五场中,雷欧提斯向我们展示,发动一场民众暴乱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其实,要是哈姆雷特愿意,他完全可以将自己手中握有的证据交给议会,通过合法手段惩治僭主,“他没必要单枪匹马地反对克劳狄斯;议会会助他一臂之力”。(19)然而,对这个世界普遍不公的愤怒,使他选择成为“上天的凶器和使者”,而非关心共同体福祉的丹麦王子。在他眼里,君王不过是“一个虚无的东西”(4.2.28)。
哈姆雷特的血气缺失的正是政治的维度。他无度的义愤,无法与这个有限正义的政治世界达成一致。在哈姆雷特眼中,政治世界接受正义的限度,这似乎也是一种恶行。这使他不屑于采用政治手段展开报复僭主的行动。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哈姆雷特拒斥了整个政治世界,这使他始终没能看清“我们”与“他们”的差别。
四、结语
如此看来,返回丹麦并自称丹麦人的哈姆雷特,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君王,他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到敌人手中,无异于一名叛国者。尽管哈姆雷特不乏犹豫不决的一面,但他绝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剧中种种细节表明,哈姆雷特极富血气:他不顾好友阻拦,冒险面见鬼魂;为了证明他比雷欧提斯更爱奥菲丽娅,哈姆雷特跳下坟墓,并与雷欧提斯发生冲突。尽管在接下来的一幕中,他承认自己不该在众人面前失去自制,但哈姆雷特表示,之所以“动起那么大火性”,乃因雷欧提斯夸大他的悲哀。克劳狄斯的诡计之所以得逞,一定程度上因为他晓得,哈姆雷特好胜心强,他对雷欧提斯剑术的夸赞,令哈姆雷特“妒恼交加”(4.7.72)。尽管鬼魂提供的真相激起哈姆雷特的复仇血气,但酿成其悲剧的根本原因,并不能简单归咎于这一偶然事件。毕竟,在第三幕第四场,鬼魂再次出现在王后寝宫中时,提醒哈姆雷特要懂得节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平息了哈姆雷特的愤怒。显然,推动整个戏剧进展的,是哈姆雷特的血气。哈姆雷特无疑是“激情的奴隶”,使之沦为奴隶的是无节制的血气。(20)
哈姆雷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有所认识,似乎也懂得节制的重要性。在教伶人们如何演戏时,他一再强调“节制”(temperance,modesty,3.2.7、19)。哈姆雷特认为,能将血气与“判断”(judgment)调整得恰到好处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哈姆雷特的认识并不充分。而且,反讽的是,哈姆雷特在行动前都会展开宏论,这些宏论往往成为他紧接而来的行动的一面反观明镜。在面见鬼魂前,哈姆雷特那段表明人性弱点的长篇大论,恰恰预示了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根据哈姆雷特的理解,人天性上的任何一种“丑恶瘢痣”、某种过度发展的脾性和某种习惯,都足以勾销一个人的所有德性。不过,哈姆雷特区分了源于自然的缺陷与源于后天的缺陷。他认为,对于随天性而来的缺陷,我们无能为力,因为,个人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天性,因此,哈姆雷特认为,我们无需为此负责。(21)倘若循着他的思路推论下去,那么,除天生的缺陷外——过度发展的脾性和习惯都应由个人负责。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哈姆雷特似乎并没有将之归咎于个人,反而将责任转嫁给外界——“世人的非议”。这样一来,哈姆雷特实际上认为,无论天性还是外界,个人都不可控,因此,个人根本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哈姆雷特认识到,人的脾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理智的“栅栏和堡垒”,但理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旦某种脾性发展过度,它将砸碎理智的栅栏。这番话既是警示,也是预言,不仅警示并预示了哈姆雷特与鬼魂的会面,也预示着整个悲剧。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哈姆雷特所说的,“我不是赫拉克勒斯”——他没能制服灵魂中的那头“雄狮”。(22)血气失去理智的防卫,便有如“禽兽”(4.5.85—86)。哈姆雷特成了“失舵之舟”(5.2.100)。哈姆雷特的血气为何没有在理智的引导下走向节制?他对自己灵魂的认识,兴许可以为我们透露一丝线索。恰好在见鬼魂前,哈姆雷特宣称,“我的灵魂,它自身是永生不灭的,难道它会加害自己吗?”(1.4.66—67)。面对鬼魂的诱惑,哈姆雷特没有在灵魂中设下防线。难道他以为灵魂无坚不摧,没有必要防护?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哈姆雷特看来,疯狂完全是一种外物,由自己的疯狂举动导致的后果,责任并不他身上,“那样的事不是哈姆雷特做的……那么是谁做的呢?是他的疯狂”(5.2.214—15)。他甚至梦想着“把坏的一半丢掉,保留那另外一半”(3.4.155—56)。用奈特(G.Wilson Knight)的话来讲,《哈姆雷特》展示的是一颗“‘染疾的灵魂’(sick soul)被召唤去拯救、净涤并创造和谐秩序”。(22)然而,指望这样一颗灵魂去重整乾坤,后果会怎样呢?
哈姆雷特憎恶此世的普遍恶行,却惟独缺乏对政治共同体的爱。这使他不可能达到阿基琉斯的认识,从过度的义愤中重返政治世界。哈姆雷特不恰切的义愤,不仅导致他个人的毁灭,也致使整个丹麦覆灭。或许,正是通过这种惨重的代价,莎士比亚提醒我们,寻求正义不能超越自己所在的共同体。通过《哈姆雷特》,莎士比亚举起一面自然之镜,让我们看到一位未来统治者的灵魂缺陷。可惜的是,剧中人物都忙于窥探他人的灵魂,却无一人认真审视过自己的灵魂。即便有人(如一再以独白形式剖析自己灵魂的哈姆雷特,以及被迫审视灵魂的克劳狄斯与乔特鲁德)的确审视过他的灵魂,实际上也无一人为此做出任何改进或提升的努力。
血气是灵魂和城邦中最成问题的因素。《哈姆雷特》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血气失控的王子,如何给国家带来灭亡。优秀统治者的职责所在,是让自己变得更高贵,而非往下走。哈姆雷特由于没有节制自己的血气,其道德义愤逐渐失去正当根据,最后背叛了更高贵的自我,(23)陷入不义之中。
注释:
①S.T.Coleridge,"On Hamlet",Four Centuries of Shakespearian Criticism,Frank Kermode(ed.),New York:Avon Library Book,1965,p.432.
②《哈姆雷特》采用朱生豪译本,略有改动,以下引文将随文注出。英文本对照阿登版,参Ann Thompson & Neil Taylor(eds.),Hamlet,Beijing: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8.
③[美]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第五讲(丁耘译),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苏格拉底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④[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I,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⑤Allan Bloom,The Republic of Plato,Basic Books,1991,p.355.
⑥[美]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第五讲,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苏格拉底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⑦Maynard Mark Jr.,Killing the King:Three Studies in Shakespeare's Tragic Structure,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80.
⑧Zdravko Planinc,"'It Begins with Pyrrhus'(2.2.451):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amlet",Shakespearean Criticism,Michelle Lee( ed.),Vol.82,Detroit:Gale,2004,pp.35—49.
⑨Allan Bloom,The Republic of Plato,p.355.
⑩参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第五讲,第71页。
(11)John E.Alvis,"Shakespeare's Hamlet and Machiavelli:How not to Kill a Despot",p.297.
(12)Catherine Brown Tkacz,"The Wheel of Ftae,the Wheel of State and Moral Choice in 'Hamlet'",South Atlantic Review,Vol.57,Nov.4(Nov.1994),p.22.
(13)[美]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增订版),张辉选编,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
(14)注意波洛涅斯被杀时,乔特鲁德的反应。她称哈姆雷特“鲁莽而血腥”(rash and bloody)(3.4.25);事后,克劳狄斯的也认为,哈姆雷特的行为“血腥”(bloody)(4.1.16)。
(15)Julia Reinhard Lupton,"Hamlet,Prince:Tragedy,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Theology",ALT Shakespeare,(2007),p.181.
(16)[美]M.W.布伦戴尔,《扶友损敌》,包利民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68页。
(17)[美]康托尔:《哈姆雷特:世界主义的王子》,刘小枫、陈少明编《政治哲学中的莎士比亚》,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19、123页。
(18)[美]康托尔:《哈姆雷特:世界主义的王子》,刘小枫、陈少明编《政治哲学中的莎士比亚》,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17页。
(19)Zdravko Planinc,"'It Begins with Pyrrhus'(2.2.451):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amlet",pp.35—49.
(20)Lily B.Campbell,Shakespeare's Tragic Heroes:Slaves of Passion,Gloucester,Mass.:Petre Smith,1973,pp.109—147.
(21)对比《理想国》575a以下。在谈到僭主的欲望时,苏格拉底表示,“这些欲望一部分是外来的,受了坏伙伴的影响,一部分来自内心,被自身的恶习性释放出来”。
(22)赫拉克勒斯系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成为迈锡尼国王之前,他所完成的第一项艰巨任务便是屠杀涅墨亚的猛狮。
(23)G.Wilson Knight,The Wheel of Fire:Interpretations of Shakespearean Tragedy with Three New Essays,London:Methuen & Co Ltd.,1961,p.20.
(24)Eric P.Levy,"'Things Standing thus Unknown':The Epistemology of Ignorance in Hamlet",Studies in Philology(Spring 2000),p.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