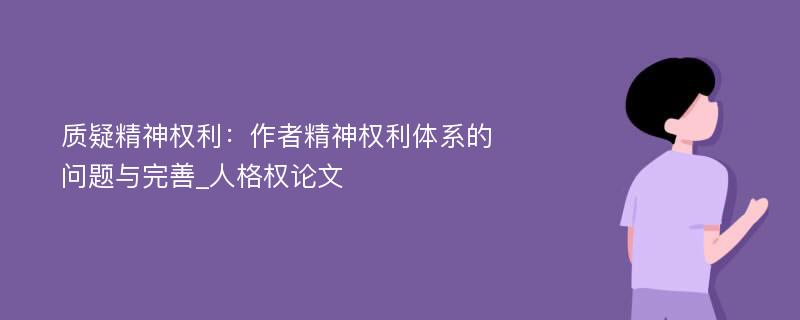
质疑精神权利——作者精神权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利论文,精神论文,制度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602(2015)05-0005-15 康德在1785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著作权属于人格权(jus personalissimum)的学说①,康德将财产权利视为财产的人格化,尤其是当财产利益涉及一个艺术创作活动。私有财产只是促进了自我表现和人的发展。自我表现和个人实现,而不是财产金钱,成为创新活动的主要激励机制。康德认为,作者的作品是通过出版者向公众发表的演说;对作为有形艺术产品的一册图书,可拥有物权,但对于只是作为作者向其读者圈所作的演说,可拥有人身权利。②后来德国学者基尔克在其所编著的《德国私法》第1卷中,将精神权利表述为:“一位作者的某个作品属于该作者人格的势力范围,著作权则保障了作者对这部分人格领域的主宰。”③他认为,著作权的对象是智力作品,智力作品则是作者人格的表露,作者通过创作活动使自己具有个性特点的思想得以反映。至此,精神权利逐渐成为著作t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 精神权利与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一样,并不随着原件所有权的转移而穷竭。这是著作权与商标权、专利权明显区别的一个特点,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物的转移会导致商标权和专利权的穷竭,而在著作权法中,原件的转移并不导致著作权的穷竭,例如美术作品原件所有权转移后,几乎全部著作权并未穷竭,著作权人依然享有几乎全部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按照精神权利理论,作品的创作者可以保留对其作品的控制,不论这一作品是否脱离其所有。购买者在购买作品之后修改作品,会受到作者完整权的对抗,这是精神权利的益处所在。”④通过这种精神权利的规定,可以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 精神权利之所以在著作权法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精神权利制度能够达成保护社会公益的目的。应当看到,精神权利提供了对国家和文化遗产等公共利益的保护机制,当出现损害国家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时,可以通过精神权利的保护来制裁这些侵权行为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因此,精神权利具有保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意义,“精神权利的保护也涉及公共利益,如果放任对作品进行歪曲,将使社会公众不知道作品的原样,将导致文化的破坏。”⑤ 然而,精神权利并不是自始即存在的。“在伯尔尼公约的早期的第一个文本中,并没有关于精神权利的规定。只是到了1928年之后,才在一些国家的推动下规定了精神权利。”⑥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1994年的Trips协议中也没有规定精神权利。由此可见,在国际公约层面上,精神权利并不统一;精神权利在世界各国也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领域,许多国家的规定都不相同,立法规定差异较大,这也反映出这一制度上的理论争议依然非常激烈。 本文对于精神权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希望通过这些质疑与反思,看到我国精神权利制度的不完善和应当修改之处,并且找到完善我国的作者精神权利制度的方法。 一、精神权利与人格权 著作权中的人格利益,与人格法中的人格利益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精神权利保护的是作者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格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不应当使用精神权利(moral rights)这个概念,德国的urheberpersnlichkeitsrecht一词应当是精神权利的最好的词源,这个词应当翻译成“作者人格权”。⑦事实上,著作权法通过禁止他人歪曲、篡改作品,保持作品的原貌的方式,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 作者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格利益,与作者本人的人格利益,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作者通过作品获得的名誉,与作者本人的名誉,也并不完全一致。例如马丁·路德·金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名誉与荣誉,与马丁·路德·金本人的名誉与荣誉并不一致。通过保护作品完整所保护的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利益,也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名誉,这种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利益,可以说是作者人格利益的一个方面。 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与人格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格权的客体是相同的,但不同的作品中包含的精神权利并不完全相同。“保护精神权利是由于一个理念,即在创作作品时,作者向作品注入了自己的精神。”⑧作者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格利益,与作者本人的人格利益,并不完全相同。作者通过作品获得的名誉,与作者本人的名誉,也并不完全一致;通过保护作品完整所保护的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利益,也并不一定是作者本人的名誉,这种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利益,可以说只是作者人格利益的一个方面。二、主观性。应当看到,是否侵害人格权中的人格利益是比较客观的,某种行为对名誉的损害通常是一般性的,名誉、荣誉和声望对于任何人来说在性质上都是相似的。但在判断是否侵害了著作权中作者人格权中的人格利益则是较为复杂的。同样的行为,有的作者会认为侵害了精神权利,而有些作者可能不会认为侵害其精神权利。同样一个对作品的修改行为,有些作者认为是破坏完整,有些作者可能不认为是破坏其完整性,社会其他人也可能会认为是补充和完善了作品。可见,在侵害作者精神权利的问题上,认定事实是比较复杂的。 因此,精神权利是保护作者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名誉和声望,精神权利是只人格权的一部分,但精神权利又与人格权有各种差异,这些差异在各种不同的精神权利与人格权的比较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下文将深入分析各种不同的精神权利与人格权的差异,从而具体研究不同精神权利与人格权的区别所在。 1.保护作品完整权与人格权 精神权利的保护也涉及公共利益,如果放任对作品进行歪曲,将使社会公众不知道作品的原样,将导致文化的破坏。精神权利制度,通过保护作品的完整,防止任意歪曲、篡改作品而保护作者在作品中的人格利益。通过行使精神权利,要求他人不得歪曲、破坏、篡改其作品而保护外在表达形式的完整。如果他人损毁该作品的原件,作者就可以通过诉诸物权法加以解决。然而,作品的原件没有被他人破坏,但其复制品受到他人的破坏、歪曲、任意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物权法将无法发挥其作用,而只能通过行使精神权利,要求他人不得歪曲、破坏、篡改其作品而保护作品的完整。在这种情况下的完整,并不是作品原件的完整,而是作品外在表达形式的完整。 对作品的歪曲性使用,完全可以在不侵害作品原件物权的情况下,损害其完整权,如雕塑品的照片的破坏性使用、美术作品的复制件的歪曲性使用。因此,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立法目的,是针对作品的歪曲、篡改性使用行为,保护作品的外在表达形式的完整。在作品上划一条线,固然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但第一位的是侵犯了作品的物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物权法追究侵权人的责任。 从保护作品完整权与人格权的关系来看,著作权试图通过保护作品的完整,来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因此实质上,保护作品完整性,只是保护作者人格权的一种方法。保护人格权的方法有很多,具体到著作权法上是通过保护作品完整权来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因此著作权法将此上升为保护作品完整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是相对的,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完整权并不是强制性的,除非毁损是严重的。法院判例也支持这个观点。作者的完整权并不是稳定的,受到不同的判例的不同影响,在不同的判例中有不同的完整权。”⑨ 伯尔尼公约中关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概念,是值得探讨的。《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规定,不受作者经济权利的影响,甚至在上述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仍保有要求其作品作者身份的权利,并有权反对对其作品的任何有损其声誉的歪曲、割裂或其他更改,或其他损害行为。应当注意的是,伯尔尼公约并未完全禁止任何对作品的更改,它要求各成员国禁止的是“有损作者声誉”的歪曲、割裂或其他更改。例如在视听作品中夹杂广告的行为,虽然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但并不构成侵害作者精神权利的行为,否则任何电视台都可能会构成侵权人。因此,伯尔尼公约所禁止的是歪曲、割裂和其他更改具有一个附带的构成要件,即必须达到“有损作者声誉”的程度。 作品的完整性,是否包括作品使用环境的完整,这本身也存在着争议。在并不破坏作品外在表达形式的完整,而是将作品用于其他场合时,也可能会损害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将作品用于歪曲和搞笑的场合,或将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悬挂于厕所。在这些情况下,通过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并不适当,而应当求诸于人格权制度加以解决。通过使用人格权制度,认定这些使用是侵害了作者的名誉权、荣誉权,而不必通过行使保护作品完整权,就可以较好地解决争议。 2.署名权与人格权 署名权与姓名权并不一致,署名权的本质意义是归属权(The right of attribution),因此它表达了作者希望将某个作品与自己关联在一起的愿望,这是一种人格利益,它与姓名权的立法宗旨不同,姓名权是保护自然人对自己姓名的设定、变更和专用的人格权,署名权则是作者在作品上署名,以标示该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联性的权利。署名权并不强调作者在作品上是否签署自己的姓名,即使并不签署自己的姓名,而是以笔名、艺名、网名等签署,也是允许的。对匿名作者、假名作者来说,只能说这是作者已经主动放弃了归属利益,不要求保护自己的归属利益,这也是署名权的一种行使方式。署名权所强调的是作品与某一作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如果引用某一作者的作品而未标示其署名,或者标示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侵害的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联关系,使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联关系被人为割裂,阻碍或限制了作者通过传播作品而宣扬自己的署名的人格利益。由此可见,在著作权精神权利中,署名权所保护的利益,是一种能够独立于一般人格权的特殊人格利益。 《伯尔尼公约》留下的问题之一是,署名权与完整权之间的权利边界并不明确,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保护作品完整权去保护署名权,因为整体作品就包含着署名部分,如果使用作品而不标示署名,就侵害了作品的完整权。笔者认为,姓名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两者保护的人格利益是不同的,姓名权强调的是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联关系,保护作品完整权则强调保护作者通过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名誉,因此,虽然在表现形式上,署名可以作为作品完整性的一部分,但在保护机制上,应当作为两种不同的权利加以保护为宜。 3.发表权与人格权 发表权是指只有作者才能决定何时作品完成,并且决定何时发表。发表权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人格权。这是因为人格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发表权则是基于作品的创作而产生的权利。任何作品创作出来之后,都保留在作者隐私范畴。只有作者有权决定何时和以何种方式发表该作品。发表作品相当于将作者的隐私进行披露;未经作者许可而披露作品,相当于侵害了作者的隐私权。 因此,在作品创作之后形成隐私权,发表权完全可以通过隐私权的行使而实现,没有必要单独规定发表权,在许多国家也没有规定发表权。如果在隐私权之外,另行规定发表权,将会导致发表权与隐私权权利发生竞合,在法律制度上叠床架屋,人为制造权利冲突与适用上的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不规定发表权的原因。 二、精神权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对精神权利的权利内容规范不全面 按照《伯尔尼公约》的规定,签字国至少要保护署名权和完整权。《伯尔尼公约》的规定可以看做是最低限度的标准,但这并不是全部精神权利,许多国家在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之外,还规定了其他精神权利。 发表权的反面权利是收回权(或撤回权),即允许作者从公开展览或销售中撤回其作品。有些国家规定,作者在原件所有权转移的任何时间,有再反悔和再取回作品的权利。允许艺术家从公开销售中撤回自己的作品,可以使作者在作品违反自己创作理念,或作品有可能损害其名誉和声誉的情况下,收回该作品,这同样是保护作者人格利益的一种精神权利。 署名权是赋予作者在作品上正确地标示自己姓名的权利,这一权利也允许作者以无名或匿名方式标示其作品。署名权的反面权利是防止错误署名的权利,即保护作品不被错误标示,从而归属给非作者的权利。在我国只有署名权,但没有禁止错误署名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托名作品,就产生了适用上的麻烦。例如一件署名某画家的赝品,该画家如果以署名权提出诉讼,但他实际并未在该作品上署名,只是其他人在该作品上故意错误署名;如果画家使用姓名权提出诉讼,也无法禁止故意使用该姓名作为艺名的其他人在作品上署名。如果禁止错误署名权没有被法律所规定,将导致画家缺少权利依据禁止这种托名行为。 法国法赋予作者反对过度批评的权利,并且使作者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销毁作品。禁止过分批评或无根据攻击,可以使作者的名誉免于因对作品的过分批评和攻击而受到损害,因此,反对过度批评的权利也被认为是一种精神权利。精神权利是否能够超越经济权利的保护期间,是一个文件和政策的问题。按照乌尔默教授的观点,在作者死后五十年或七十年之后,公共批判和讨论的价值应当超过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这应当由各个国家的法律和文化传统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国家则规定了作者享有禁止销毁权,例如在瑞士,要求艺术品的所有人在销毁艺术品之前应当通知作者,由作者决定是否回购该作品。《伯尔尼公约》只规定了禁止对作品的歪曲、毁损、修改或贬损行为,但没有规定禁止对作品进行销毁。作品的销毁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作者的名誉或荣誉,如果通过销毁作品而损害了作品的传播,则会影响到作者的名誉。为了更好地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有必要赋予作者禁止销毁权。 还有些国家规定了拒绝创作的权利,这种拒绝创作的权利,可以在采访、新闻报道等领域内,使受访作者拒绝接受访问并且拒绝作出任何创作行为,从而更好地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和独立,因此将拒绝创作权作为作者的精神权利之一。 有许多学者认为,尽管追续权具有浓厚的著作财产权属性,但同样不可否认其明显的精神人格属性。例如DuBoff认为追续权起源于精神归属权,并最终作为额外的精神权利加以保护。李明德在《著作权法》一书中虽然将追续权列在经济权体系之下,同样认为在理解追续权时应当注意的一点是,“追续权的享有者是作者或其继承人,带有鲜明的人身权利性质,从这种意义上说,追续权更接近作者的精神权利,带有不可转让的性质。”⑩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将追续权列入精神权利范畴。例如《澳门著作权法》第57条第1款规定:“追续权不可让与,也不受时效限制。”《巴西著作权法》第39条也是将追续权作为人身权加以规定。(11)艺术品与艺术家本人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即是艺术家的人格特征,艺术家能够追及艺术品的后续转售就是基于这种人格属性。因此,将追续权列入精神权利的权利内容。 在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中规定了滑稽模仿的构成要件,反过来说,作者有权针对不符合滑稽模仿构成要件的模仿行为,提出禁止的权利,这种反对任何模仿、歪曲性模仿的权利,可以保护作品不受恶意模仿的损害,从而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因此同样也应当属于精神权利之一。 由此可见,在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之外,尚存在诸多的精神权利,为什么我国著作权法无视这些精神权利,不对这些精神权利加以规定呢?精神权利是作者的人格利益的体现,它们依附于作者而需要加以认定,单纯地规定四种精神权利,并不足以全面地认定和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 (二)任意割裂与分配的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的授权,其目的是保护作品创造者的人格利益。作品创造者在创作作品之时,在作品中灌注了自己的精神和人格,因此,赋予创作者以精神权利,以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因此,只有作品的作者才存在人格利益,也只有作品的真正作者才需要保护精神权利。 然而,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特殊职务作品的规定,人为地割裂了精神权利,直接违背了著作权法赋予精神权利的立法宗旨。在特殊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规定中,实际创作者只享有署名权,其他精神权利——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都通过法律的硬性规定而转移给单位享有。这一立法规范的意图在于,考虑到特殊职务作品的投资、法律责任都由单位承担,那么何时决定作品创作完成而可以发表,以及决定作品如何修改和保护作品完整权都应当由单位来享有和行使,能使单位更好地决定作品著作权的行使。虽然这种立法意图是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但这一法律规定直接违反了精神权利的立法宗旨。我们不禁要问,精神权利可以由立法者任意切割,直接从创作者身上剥夺而分配给其他主体吗?这样规范,就等于承认精神权利可以分离于实际创作者而任意通过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变动其权利主体,这就等于承认精神权利是可以分割的、任意支配的、并不与其创作者的人格相关联的,这直接违背了精神权利的立法宗旨。精神权利与创作者具有不可分割的人身关系,立法的实用主义不能以违背权利的基本宗旨为代价,否则精神权利就成为任人割宰的一项权利。 关于职务作品的立法,世界上存在两种模式。法国《著作权法》L111-1条明确规定:对作品享有专有的、对抗所有人的无形财产权的唯一事实依据是对作品的创作。存在或者签订雇佣或服务合同,对作者享有的权利不产生任何消极影响。这意味着即使是为了完成雇主所交付的任务而创作的作品,原始著作权人仍然是创作作品的雇员。雇主能够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行使或受让著作财产权,但不能被视为作品的“作者”。英国《版权法》规定对于雇员在受雇期间创作的文字、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除有相反约定之外,其雇主为原始版权人,但这并不影响实际创作者的“作者”地位。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则对两大法系的规定进行了折衷,其第11条规定:受雇人因职务行为完成的作品,以受雇人为著作人(即作者)。但合同可以约定以雇主为著作人。 我国《著作权法》则人为割裂了精神权利,与上述两种立法模式均不相同,通过法律硬性地划分了精神权利,并且将财产权利全部归属给单位所有,并没有为当事人约定留下余地,这种立法规定显得非常武断和强硬,也是与精神权利的权利宗旨相违背的。 对精神权利的任意切割,在我国关于视听作品的立法规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危害也更加突出。在视听作品中,导演、编剧、摄影、作词、作曲者等作者只享有署名权,而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均归属给制片者享有。作为电影作品的实际创作者,导演无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导演无法决定作品何时完成而可以发表,也无法对作品的修改提出意见。“电影作品中的导演如果没有著作权,只有署名权,对于电影作品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就没有权利,就只能由制片者进行修改,这违反了导演的利益。”(12) 在电影作品需要进行修版、删节、上色等处理时,就会出现制片者与导演等主要创作者的人格利益的冲突。“美国导演们就曾经游说法院和国会,防止他们的作品出现删节、上色、低分辨率或其他处理版本。”(13)在许多情况下,制片者行使法律所赋予的精神权利,就可能会损害导演等主要创作者的人格利益。其原因在于,从立法上人为否认实际创作者的精神权利,而将精神权利赋予另一主体,就会人为形成双重的人格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将精神权利任意切割给不同的主体,人为创造了精神权利行使上的混乱。因此,“在Fairbanks一案中,美国法院认为作为导演,他有权对自己作品的进一步艺术加工在电影首映之后也享有精神权利。”(14) 美国的Fairbanks一案,还提出了演员应当享有精神权利。1922年,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提起诉讼,该诉讼涉及他的电影生涯早期的一些电影。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在其与电影公司的雇用合同中写入了一个条款,只有著名的大卫·格里菲斯才是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出演的电影的导演。当大卫·格里菲斯和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都因某些原因而离开Majestic电影公司后,后来,费尔班克斯早期的一些电影增值了。Majestic电影公司决定在这些电影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将这些电影及其附属的全部版权卖给Triangle电影公司。1922年,Triangle电影公司决定将这些电影改编成上下两集形式的电影销售给Leader公司。 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并没有寻求禁止Majestic电影公司将电影销售给Triangle电影公司。在拍摄这些电影时,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仅仅是Majestic电影公司的雇员,并且没有版权。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争辩认为,尽管他没有版权,上下两集形式的版本,损害了他的表演。纽约上诉法院将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与Majestic电影公司签订的原始合同作为判案基础。尽管该合同并没有给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任何权利,但它明确规定大卫·格里菲斯是电影的导演,并且赋予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审查电影最终剪接版的权利。该案的法院判决认为,该雇用合同永远地保护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的艺术观点,他有权利继续监视他的作品的品质质量,即使在电影首映之后。因此,“在Fairbanks一案中,美国法院认为作为导演,他有权对自己作品的进一步艺术加工,在电影首映之后也享有精神权利”。(15) 此外,我国在邻接权中的精神权利分配则更为混乱。我国《著作权法》只赋予了表演者以精神权利,而没有给录制者、广播组织者以精神权利。应当看到,录制者和广播组织者尽管并不是作品的创造者,但他们通过智力劳动,制作了各种录音录像制品和广播电视节目,但立法并没有规定其享有署名权和保护其制作成果的完整权。如果不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和广播组织者的署名权,那么破坏和遮挡台标的行为,就不能受到追究;破坏录音录像制品中的电子管理信息的行为,就失去了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源。如果不规定保护其制作成果的完整权,录制者和广播组织者就无法保护其创作的录音录像制品和广播节目的完整性。 (三)精神权利的非一致性 首先,对于不同的作者,精神权利并不完全相同。可以说,不同的作者,即使在同样类型的作品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人格利益需求。严肃作品与一般流行的网络作品,其作者的精神权利是否完全一样?严肃的文学名著,可能需要更严格的精神权利加以保护;一般流行小说作家的作品,则未必需要程度非常高的精神权利去加以保护,其作者对于作品的完整性要求也并不高。 禁书作者的精神权利,是否与其他作者完全相同?禁止违反社会道德和公共利益的书籍和电影的发表,未尽侵害其发表权;对这种书籍和电影的内容进行删节,也并不构成侵害其保护作品完整权?在这种情况下,禁书作者的精神权利都是存在限制的。因此,立法针对不同情况,都同样规定和保护这种一般意义的精神权利,是存在问题的。 其次,不同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也可能并不相同。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他人可以对该程序进行修改,以使之与自己的计算机环境更为兼容;也有许多计算机程序本身就是开源软件,即在计算机程序发表之际,作者即已放任他人对程序进行较多较重大的修改,作者已不寻求保护自己的修改权和完整权。对这种计算机程序来说,只留下署名权一种精神权利,而计算机运行和使用时,署名权根本无从体现和表现。因此可以说,对于计算机程序而言,精神权利中仅仅留有署名权需要加以规定,这就使得计算机程序作者的精神权利显得非常单薄。 “对于最近出现的计算机程序或数据库作品,更纯粹是一种商品而其中的精神权利表现较弱。精神权利更多地适用于艺术品或较少功能性的作品。”(16)计算机程序作为一种作品,其同时具有更多的功能性和工具性。作为一种计算机运行所必需的工具,虽然可以通过著作权加以保护,但其本身也无意维护其完整权。如果硬性规定精神权利,而计算机程序的作者又主动放弃了保护作品完整权,或者向他人转让计算机程序的修改权,那么就会面临精神权利是否可以放弃、转让的质疑。 第三,不同作品上的作者精神权利也并不完全相同。文字作品常常受到他人的编辑、修改,包括合作作者对作品的修改。此外,文字的完整并无法完全保护其思想的完整,常常在原文引用时歪曲了作者的思想。因此,在不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损害其精神和思想的完整,那么此时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又有何意义?如果作者的精神和思想受到歪曲,就会损害作者的人格利益,那么此时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又有何意义? 美术作品相较其他作品类型来说,更加重视其外在表达形式的完整性。因为美术作品等艺术作品,是通过其作品的外在形式进行艺术表达的,这也正是美国VARA法侧重单独为视觉艺术作品的作者设置精神权利的主要原因。 视听作品则很难损害其完整权,除非电影修版或进行其他衍生创作时才可能会损害电影作品的完整权。即使在法国,肯定和维护每个电影作品主创者的精神权利的国家,也仅仅限于署名权和财产权利认定,对精神权利中的完整权的侵害是比较少见的。 音乐作品的完整性,则非常难以保护。这主要是由于音乐作品常常被片断性使用,通常在打破其作品的完整性的情况下使用该作品片断,如果这些片断性使用行为都构成侵权,则并不现实。利用音乐作品的片断进行其他衍生创作,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演唱者对音乐作品进行表演时,唱歌跑调也并不等于侵害了音乐作品的完整性,如果这样也构成侵害音乐作品的精神权利,则保护与追究责任均不现实。 (四)作者死亡后的精神权利悖论 作者去世后,精神权利由继承人保护,这种情况下,继承人不是以保护自己利益去保护精神权利,而是以维护死者的利益为目的保护精神权利,因此就会出现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如果继承人并不实施和保护精神权利,精神权利就没有人会提供保护,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插手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精神权利没有人提供保护,就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精神权利永久存在永久保护的理念,产生矛盾。 美国著名版权学者Kwall教授反对过分延长作者精神权利,她认为,在作者死后,没有人的判断能够代替作者本人的判断,即使是他的继承人。因此,精神权利应当截止于作者死亡之时。如果在作者死后,继承人不维护作者的精神权利,放任作品的完整性或署名权被破坏,认定作者享有永久性的精神权利就毫无意义,这就产生了权利享有和权利行使的悖论。 作者去世后,精神权利的真正主体已无法行使这一权利,只能通过继承人来保护精神利益,而非由继承人行使精神权利,因为继承人并不享有作者的精神权利。继承人只是维护作品的完整性,保护作者的署名权。由于精神权利是不可以像财产权利一样进行继承的,因此,如果继承人提起诉讼来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但其并没有通过继承继受作者的精神权利,那么继承人为了保护作者精神权利所提起诉讼的权利依据,就成为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在作者死后,实际上使继承人享有了一种特殊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法定权利,是在作者去世之时所产生的赋予继承人的权利。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为了更好地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继承人应当享有这种法定权利。 这一点在发表权中,表现为发表权的行使欠缺权利依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发表权的保护期限是作者终生及作者死后五十年。在作者死后,作者已无法行使发表权。由于精神权利的不可转让性,继承人也并未继承发表权。如果作品由继承人发表,继承人的发表权的权利来源并无法律依据。继承人的发表,并不是行使了作者的发表权,因为发表权并未通过继承转让给继承人,除非作者生前立有遗嘱授权继承人发表,否则继承人的发表行为的权利就欠缺法律依据。如果继承人的发表行为欠缺法律依据,则著作权法规定发表权延续到作者死后五十年就失去了意义。 可见,死后人格权的保护问题,在人格权制度中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著作权法上就表现为作者去世后的继承人不保护精神权利,使精神权利保护落空和保护精神权利时欠缺权利依据两个问题。在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对这两个问题加以解决,否则将会导致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永久性精神权利,在法律适用上产生障碍。 三、精神权利对艺术创作的干扰与影响 (一)窒息视听作品等艺术投资的积极性 视听作品需要大量的投资,但著作权法设置过多的精神权利,会导致创作者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从而影响新作品的产生。 在目前的著作权法中,就已经存在着表演者权与制片者著作权的冲突。著作权法赋予表演者较多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表演者一方面通过与制片者签署合同,获得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精神权利的不可转让性、不可放弃性,导致表演者无法通过合同而放弃精神权利,一旦表演者行使精神权利,就将影响制片者对视听作品著作权的行使。因此,制片者的著作权无时不处于表演者精神权利的威胁之下。 一旦发生电影的重新包装、重新制作、修版等问题时,导演权、制片者权、表演者权之间的精神权利冲突就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在修版时,表演者可能会提出精神权利中的保护表演形象完整权,主张不得随意改动电影。导演则会主张自己是电影的创作者,未经其同意任意修改电影,损害了导演的精神利益,同时认为著作权法上没有给导演设置精神权利,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在美国之所以迟迟不希望赋予作者以精神权利,就是看到了精神权利可能会对于视听作品的投资带来较为严重的干扰。“美国出版商、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都可能受到精神权利的限制,因此他们极力反对精神权利。”(17)精神权利,被美国法院解释为允许当事人可以提出非版权来源的任何诉讼的理由。美国法中不规定精神权利,则可以减少作品使用中的干扰因素,更为符合将作品视为商品使用的英美法版权理念。在美国通常认为,完整性最好受到合同的保护。例如Zechariah Chafee教授说:“任何希望保护自己精神权利的版权人都可以在其与出版商、制片人的合同中插入适当条款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精神权利,例如明确禁止未经其许可的改动或删节。”但许多学者也认为,作者与出版商、制片人的谈判中并不处于优势,很难在合同中纳入这种保护完整权的合同条款。 “对于视听作品来说,赋予导演、演员的各种权利,即使精神权利,也可能会给制片者行使视听作品著作权带来影响。”(18)可见,通过精神权利而不依赖于财产权利去控制和干扰作品的使用,会形成作品使用的额外负担。对于视听作品来说,赋予导演、演员的各种权利,即使精神权利,也可能会对于制片者对视听作品的应用带来影响。Marshall Leaffer教授对于精神权利提出了如下质疑:“对于电影制作、出版和广播来说,都需要有很大的投资,如果放开精神权利,则会干扰这些领域的投资,使其投资回报和利润预期受到影响。”(19) “精神权利可能会威胁在艺术的公开传播上的商业投资。可能会窒息需要很多投资的艺术作品的创作活动。”(20)应当看到,即使在美国制订了VARA法(Visual Artist Rights Act of 1990)之后,VARA也明确地将电影、活动画面、视听作品、图书、期刊杂志、电子出版物和广告或行销材料排除于保护之外,并不赋予这些作品的作者以精神权利,从而防止精神权利的赋权对这些需要大量艺术投资的投资人带来干扰。“精神权利会威胁艺术的经济投资行为,窒息艺术创作的产生。精神权利会产生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威胁编辑自由,赋予艺术家非常宽泛的审美否决权。”(21) (二)精神权利与现代艺术创作的矛盾 不同时代的文化观点,也决定了不同的精神权利的保护需求。精神权利的认定忽视了“艺术”的本质概念。“精神权利所预设的艺术概念,恰恰是近五十年来艺术家们所极力反对的。精神权利所极力保护和认定的艺术本质与实际的艺术本质并不相同,这种艺术本质是已死去的。”(22)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艺术观和精神权利去阻碍艺术的创作活动的发展。 精神权利以保护艺术品的方式损害了艺术创作,这是因为在精神权利中的“艺术”概念已经被废弃了。对于后现代艺术创作来说,其本身具有很多独有的特性。后现代艺术具有自由性,因为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所有束缚和一切禁忌,追求返璞归真、超越自然,体现艺术创作的无限自由和不断创新。后现代艺术具有虚拟性,在后现代社会,艺术不再是现实的反映;相反,现实成了一种虚拟的、构造出来的实在。图像或影像制作,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后现代艺术的重要创作方式。后现代艺术使用令人震惊的现场效果,瓦解日常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和理性秩序。怪诞变形,为了使寻求幻象,表达主观精神和对世界再创造的艺术,艺术家往往运用把现实人物和事件变形的手法,塑造怪诞的形象。 艺术日益带有符号化倾向,更多地表现出抽象的意蕴。在后现代艺术界中,将以往出现的各种艺术联系起来的时间脉络已经失效,艺术的历史没有了时间先后。艺术不再有古今之分、内外之别,一切曾经出现过的艺术都可以成为后现代艺术家挪用和拼贴的对象,后现代艺术也因此不再要求独创性。情节的非逻辑性和虚幻性,时空任意倒置,无逻辑可依,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处于一种混乱癫狂状态。 毁灭和改变原有的作品是现代艺术的一种重要的创作方式。在当代艺术中,通过损毁和修改以前的艺术作品而创建新的艺术品,这成为一种艺术创作方式。(23)文化遗产对现代艺术创作提供着灵感。在这种情况下,精神权利将会以保护作品的名义而限制作品的创作。因此现代精神权利制度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24)例如被波普艺术重新演绎的梦露照片,将梦露的肖像一排排重复排列,色彩简单,效仿着廉价印刷品的低俗,单调的梦露,橘色的梦露,斑斓的梦露,其中有美国社会的大众趣味,也有商业社会的空虚。如果坚持照片作者的精神权利,禁止破坏其原作品的完整性,则不会产生这一新作品。同样,对于蒙娜丽莎这一世界名画的再次演绎,也必将破坏其完整性,但在对原作破坏的同时,会产生新的艺术作品。《在钢琴边的女孩》则复制了一幅连环漫画,比《在钢琴边的女孩》原作放大了五百多倍。画家不仅把原作的构图与人物形象准确复制下来,而且对原作者的笔法以及丝网印刷的网点作了精心细致的模仿,通过有意模仿印刷工艺中的网点,以表明其放大的连环漫画的通俗文化色彩。对于这种完全模仿另一幅艺术作品,使用全新的艺术表达手段进行复制,从而传达出不同的艺术思想的后现代创作,如果使用保护作品完整权禁止其创作,则会阻碍这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的出现。 虽然使用他人的作品进行创作,需要获得原作作者的许可,而原作作者即使给予许可,也通常并不允许对作品的完整性进行重大破坏。然而,在他人作品上进行艺术创作,必须修改和破坏原作的完整性,因此这里就产生了艺术创作上的尖锐矛盾。通过获得原作作者的许可,当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如果无法获得原作作者的许可,或即使获得原作作者许可,但原作作者坚持自己作品的完整性的情况下,则将导致干扰和影响新的艺术作品的产生。由此可见,使用精神权利禁止他人进行再创作,是不符合艺术发展趋势的,有必要使著作权法上的精神权利制度适应现代艺术创作的规律。 四、作者精神权利制度的完善 (一)尊重精神权利立法宗旨,完善我国精神权利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关于精神权利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英美法系狭窄的精神权利模式,二是大陆法系宽泛的精神权利模式。 英国的精神权利只适用于有限的作品之上。英国只立法保护三种精神权利:署名权、完整权和隐私权。署名权和完整权也仅适用于文学、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和电影作品。精神权利不可转让但可放弃,署名权截止于作者死后二十年,其他权利在作者去世时截止。 美国法院长期以来认为,精神权利是来自外国法制,因此认为不适用于美国。(25)对精神权利的认可,违背了美国社会的法律文化,“精神权利会威胁艺术的经济投资行为,窒息艺术创作的产生。精神权利会产生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威胁编辑自由,赋予艺术家非常宽泛的审美否决权。”(26)美国通常认为作品是一种财产保护对象,而不认为精神权利高于财产权利。(27) 在美国,精神权利并未被纳入著作权法之前,是通过合同法、隐私法、不公平竞争法、刑法中的诽谤罪来加以保护的,因此在美国不保护精神权利,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实际上美国作者受到不公平竞争、合同法、诽谤和隐私法的保护。保护作品完整权通常受到合同的保护,“任何希望保护自己精神权利的版权人都可以在其与出版商、制片人的合同中插入适当条款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精神权利,例如明确禁止未经其许可的改动或删节。”(28)但许多学者也认为,作者与出版商、制片人的谈判中并不处于优势,如果很难在合同中纳入这种保护完整权的合同条款,则将使作者权益受到限制。(29) 随着美国著作权制度的发展,美国逐渐吸收和采纳了精神权利制度。在1979年加利福尼亚等十一个州制订了保护视觉艺术家的精神权利的州法。1988年美国加入了《伯尔尼公约》,这促使了美国逐渐接受精神权利制度。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VARA修订了美国版权法。VARA赋予视觉艺术家三个精神权利,完整权、署名权和禁止彻底销毁权。但是,VARA法案中所确定的“视觉艺术作品”仅仅包括以下两类:(一)以孤本形式存在的绘画、图画、印刷品和雕塑,或其不超过200件的复制件,且由创作者签名并连续编号;(二)以孤本形式存在并由作者签名的仅出于展览的目的而制作的静止的摄影,或其不多于200件的复制件,且由作者签名并连续编号。大多数作品被排除在“视觉艺术作品”之外。因此,VATA适用于只有一个复制品或不足200个有限版本,并且由艺术家签过字的绘画、打印、照片或雕刻等作品。VARA明确将电影、活动画面、视听作品、图书、期刊杂志、电子出版物和广告或行销材料等作品排除于保护之外。在美国只提供给视觉艺术作品的作者以精神权利,并不向其他作品的作者提供这种权利。因为只有这种作品才存在原件及原件的破坏、修改和侵害完整权的问题。(30) VARA仅适用于该法生效后,即1991年6月1日之后的视觉艺术作品。在VARA中,VARA禁止作者转让这些精神权利,但允许作者放弃这些精神权利。精神权利只持续到作者生前,截止于作者去世后的当年年底。即使有了VARA,美国法院也倾向于狭窄地解释该法的适用。 在欧洲许多国家,则赋予很广泛的精神权利,通常没有依据作品类型而限制精神权利的做法,而且精神权利是不可转让和放弃的,精神权利的保护限制也是永久的。(31)即使在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中对于精神权利也没有明确列举式的规定,而是由法国法院对精神权利的保护采取自由认定的办法。目前有些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其他精神权利的存在,而积极制定关于拒绝创作的权利、撤回或销毁作品的权利、禁止过度批评的权利、禁止任何人伤害作者人格的权利等。 应当看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一定正确,许多英美学者也认为,其精神权利立法的赋权范围过于狭窄,提出应当扩张精神权利的赋权范围的观点。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我国的著作权法继承《伯尔尼公约》所建立的基本体系,因此保持大陆法系的精神权利立法模式,而不采取英美法系的模式,是妥当的。 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著作权法立法中,留下了许多缺陷与不足。不顾大陆法系精神权利的立法宗旨,任意割裂与分配精神权利的现象,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职务作品和视听作品之中。采用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但又进行实用主义的变通,不尊重精神权利的立法原则,任意割裂与分配精神权利,导致我国职务作品和视听作品上的权利冲突日益严重。因此,应当一视同仁地给所有实际创作者以精神权利,尊重精神权利的立法宗旨,改变我国目前特殊职务作品和视听作品上的著作权归属立法,真正赋予作品创作者以精神权利。 同时,也应当赋予邻接权人以精神权利,在我国邻接权制度中,只有表演者享有精神权利,而其他邻接权人并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导致其他邻接权人的权利保护不周密,广播电视台台标和录音录像制品电子管理信息的权利来源缺位,因此也应当赋予邻接权人以精神权利,促进精神权利制度的完善。 (二)计算机程序作品的精神权利问题 对于计算机程序等并不是以其外在表达形式而是以其内在的功能性为主要特征的作品来说,一旦赋予精神权利,将导致权利放弃现象的出现,作者不得不主动放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使。同时,修改权的定位不清,甚至在计算机保护条例中不得不将修改权作为财产权加以规定和保护,因此,对于计算机程序作品来说,精神权利立法对其并不适用。 计算机程序作为作品受到保护的同时,计算机程序的使用人依然能够对计算机程序进行必要的甚至较重大的修改,以使该计算机程序与自己使用的计算机系统相兼容,在这种情况下,无疑是破坏了计算机程序的完整性,但并不构成侵犯了计算机程序的精神权利。在我国计算机保护条例中,甚至都没有将修改权放置在精神权利中,而是放置在财产权中,认为通过修改权的许可使用,可以使计算机程序的开发者获得经济利益。 因此,对于计算机程序这种以功能性为其主要特征的作品来说,常常需要对作品进行大量修改,因此对这类作品来说,保护作品完整权就成为不必要的一种权利,再行设置也将导致与现实不相适用。此外,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修改权又具有财产价值,从而导致修改权日益脱离精神权利。因此,对于计算机程序作品来说,精神权利的要求本身并不强烈,设置完善的精神权利制度并无必要。因此,对于计算机程序或数据库作品来说,其更纯粹是一种商品而其中的精神权利表现较弱,精神权利更多地适用于艺术品或较少功能性的作品为宜。 (三)防止精神权利对艺术投资和艺术创作的影响 鉴于表演者精神权利与制片者著作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日益突出,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时,已经将之作为一个焦点问题。虽然按照大陆法系精神权利的立法宗旨,对精神权利进行赋权,符合精神权利制度的基本理念,但目前视听作品的精神权利设置方法,会干扰视听作品著作权的集中行使,影响视听作品的财产权利的实现,从而窒息大规模艺术投资的积极性。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赋予导演、编剧、作词、作曲、摄影、表演者等精神权利的同时,调整目前视听作品上的著作权归属制度。不应当人为硬性地赋予制片者著作权,而应当参考法国和德国著作权法的做法,建立视听作品的实际创作者与制片者之间的契约优先的理念。使具有精神权利的导演、编剧、作词、作曲、摄影、表演者与制片者之间,事先形成关于著作权归属与使用的契约,然后依据该契约行使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在该契约中,必然会将精神权利的行使考虑进来,从而防止精神权利主体,任意行使其精神权利,与制片者著作权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影响视听作品经济利益的实现,窒息大规模艺术投资的积极性。在美国,在精神权利保护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平衡采取的做法是:艺术作品的损毁通常是被允许的,即使修改是被禁止的。许多保护仅仅适用于有很高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 此外,针对现代艺术创作的特点,不应当因保护精神权利而影响和阻碍现代艺术的创新和创作。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应当禁止下游作者进行新作品的创作,应当扩大现代艺术创作的创作空间,防止原件者利用精神权利进行干扰艺术作品的创作。因此,从促进现代艺术作品的创作角度考虑,应当限制精神权利对艺术创作的过度干扰,以促进现代艺术作品的创作涌现。 (四)防止精神权利与人格权之间的权利竞合与冲突 精神权利制度与人格权制度具有共同的保护客体,两者之间会存在法律适用上的竞合与冲突。有必要在著作权法上肯定和保护精神权利,但精神权利的认定又容易与人格权发生混同,认定两种保护相同人格利益的权利,就将会导致权利适用上的竞合。在著作权法上规定了精神权利,就可能会与人格权制度产生双重授权和保护的问题。因此,在规范精神权利时,应当尤其注意防止出现权利体系上的混乱。 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竞合与冲突,应当谨慎对待精神权利的认定与赋权,有些通过人格权制度就可以加以解决的,不必要纳入精神权利制度之中,例如反对过度批评权、禁止销毁权、禁止恶意模仿权,这些权利完全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制度加以解决,就没有必要设置到精神权利制度中,以防止出现不必要的竞合与法律适用的冲突。 当出现权利竞合与法律适用冲突之时,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的法律制度,在有些情况下,应当允许作者通过人格权法解决著作权法上的精神权利纠纷。有些情况下通过人格权制度解决相关诉讼纠纷时,具有更强的保护效力。能够通过人格权加以解决的,没有必要直接上升到著作权精神权利,否则将导致精神权利对于作品的行使造成更多的干扰与混乱。相反,如果作者通过行使精神权利,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时,作者完全可以使用精神权利制度解决相关争议。因此,当出现权利竞合与法律适用冲突时,赋予作者选择权,可以更为灵活地保护作者的权益。 (五)继承人不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救济措施 没有主体的权利,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死后人格权的保护问题,在人格权制度中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著作权法上就表现为作者去世后的继承人不保护精神权利问题和保护精神权利时欠缺权利依据两个问题。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永久保护精神权利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应当对这两个加以解决,否则将会导致《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永久性精神权利,在法律适用上产生障碍。 笔者认为,如果继承人不履行其维护精神权利的义务,则可由国家有关机关负起保护的职责。在没有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情况下,由国家有关机关负担保护职责。同样,在继承人不履行其维护精神权利的义务的情况下,也应当由国家有关机关负担起保护职责,这样可以为去世作者的精神权利提供更为完善的保护。 在作者死后,继承人行使的并不是精神权利,而只是保护作者的归属权和完整权的各种行为。在作者死亡之后,继承人行使这种死去作者才享有的精神权利,其权利依据是欠缺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赋予继承人法定权利,在作者死亡之后,其精神权利自动转由继承人保护,为了使继承人更好地保护这种精神权利,继承人应当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法定权利,其并不是行使作者的精神权利,而是保护作者精神权利的法定性权利。 “康德与黑格尔将财产权利视为财产的人格化,尤其是当财产利益涉及一个艺术创作活动。他们认为,自我表现和个人实现,而不是财产金钱,成为创新活动的主要激励机制。”(32)精神权利理论并不需要废除,但需要修正和完善。为什么在在商标和专利法上,存在着权利穷竭问题,而在著作权法上,并不存在穷竭?购买者在购买之后修改作品,会受到作者的完整权的对抗,这是精神权利的益处所在。放弃精神权利制度未必会最小化社会成本和无效率,但完全放任地行使精神权利,也可能会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精神权利理论是一个“艺术尊敬与社会利益之间的权衡”的问题,立法者必须权衡“精神权利保护的价值和精神权利对于艺术家和社会的影响”(33),通过完善精神权利制度,促进艺术创作,促进作者权利保护,应当是精神权利制度的立法目标。 ①康德1785年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Von der Unrechtm igkeit des Büchernachdrucks》,其英文译名为“On the Injustice of Reprinting Books”,中译名《论假冒书籍的非正义性》。 ②G.卢夫,《Filosofia del derecho de autor》中的《Corrientes filosoficas de la epoca de la Illustracion y su influjo en el derecho de autor》,波哥大,国家著作权局,1991年,第43页、第44页。参见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1页。 ③M.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④Amy M.Adler,"Against Moral Rights",California Law Review,February,2009,97 Cal.L.Rev.263. ⑤ibid. ⑥Gerald Dworkin,"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Moral Rights and The Common Law Countries",Columbia-VLA Journal of Law & the Arts,Spring/Summer,1995. ⑦Robert C.Bird,"Moral Rights:Diagnosis and Rehabilitation",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Fall,2009,46 Am.Bus.L.J.407. ⑧Amy M.Adler,"Against Moral Rights",California Law Review,February,2009,97 Cal.L.Rev.263. ⑨Ilhyung Lee,"Toward an American Moral Rights in Copyright",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Summer,2001,58 Wash.& Lee L.Rev.795. ⑩李明德、徐超:《著作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11)邹国雄、丁丽瑛:《追续权制度研究》,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12)Peter Decherey,"Auteurism on Trial:Moral Rights and Films on Television,Symposium: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sconsin Law Review,2011,2011 Wis.L.Rev.273. (13)ibid. (14)ibid. (15)ibid. (16)Jacqueline D.Lipton,"Moral Rights and Supernatural Fiction:Authorial Dignity and The New Moral Rights Agendas,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Spring 2011,21 Fordham Intell.Prop.Media & Ent.L.J.537. (17)Ilhyung Lee,"Toward an American Moral Rights in Copyright",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Summer,2001,58 Wash.& Lee L.Rev.795. (18)Peter Decherey,"Auteurism on Trial:Moral Rights and Films on Television,Symposium: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Wisconsin Law Review,2011,2011 Wis.L.Rev.273. (19)Jacqueline D.Lipton,"Moral Rights and Supernatural Fiction:Authorial Dignity and The New Moral Rights Agendas,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Spring 2011,21 Fordham Intell.Prop.Media & Ent.L.J.537. (20)Ilhyung Lee,"Toward an American Moral Rights in Copyright",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Summer,2001,58 Wash.& Lee L.Rev.795. (21)Dane S.Ciolino,"Moral Rightsand Real Obligations:A Property-Law Frameworkfor The Protectionof Authors' Moral Rights",Tulane Law Review,March,1995. (22)Amy M.Adler,"Against Moral Rights",California Law Review,February,2009,97 Cal.L.Rev.263. (23)Robert C.Bird,"Of Geese,Ribbons,and Creative Destruction:Moral Rightsand Its Consequences",Texas Law Review,December 30,2011,90 Tex.L.Rev. (24)Amy M.Adler,"Against Moral Rights",California Law Review,February,2009,97 Cal.L.Rev.263. (25)Ilhyung Lee,"Toward an American Moral Rights in Copyright",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Summer,2001,58 Wash.& Lee L.Rev.795. (26)Dane S.Ciolino,"Moral Rights and Real Obligations:a Property-Law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Authors′ Moral Rights",Tulane Law Review,March,1995. (27)Jacqueline D.Lipton,"Moral Rights and Supernatural Fiction:Authorial Dignity and The New Moral Rights Agendas,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Spring 2011,21 Fordham Intell.Prop.Media & Ent.L.J.537. (28)Ilhyung Lee,"Toward an American Moral Rights in Copyright",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Summer,2001,58 Wash.& Lee L.Rev.795. (29)ibid. (30)Brian Angelo Lee,"Making Senseof 'Moral Righ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Temple Law Review,Fall 2011,84 Temp.L.Rev.71. (31)Ilhyung Lee,"Toward an American Moral Rights in Copyright",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Summer,2001,58 Wash.& Lee L.Rev.795. (32)Robert C.Bird,"Protecting Moral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U.K.'s New Performances Regulations",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Fall 2006. (33)Robert C.Bird,"Of Geese,Ribbons,and Creative Destruction:Moral Rights and its Consequences",Texas Law Review,December 30,2011,90 Tex.L.Rev.标签:人格权论文; 著作权法论文; 署名权论文; 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