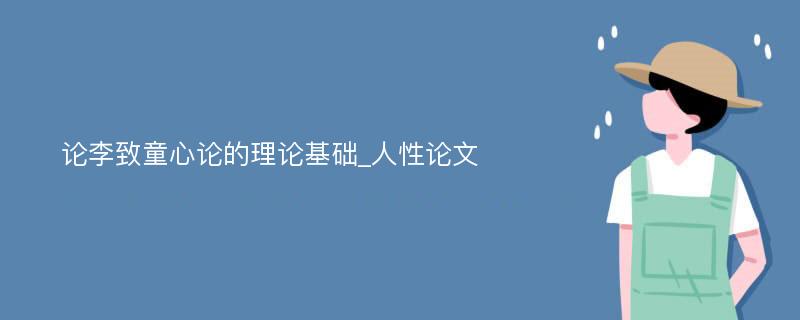
试论李贽“童心”说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童心论文,理论基础论文,试论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B24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4-0156-05
李贽的“童心”说不但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人性论的集中体现,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这种“童心”说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人们很容易把它与孟子“赤子之心”和“性善”说联系起来。孤立地从字面上看,这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若以此为李贽“童心”说的理论基础,必然会把李贽自己的理论体系弄得支离破碎。所以,本文拟对此略加探讨。
在探讨李贽“童心”说的理论基础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李贽基本的社会思想。这从他以下的言论中可以较清楚地看出来:
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答邓明府》[1](卷1)
夫唯以迩言为善,则凡非迩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故以为恶耳。——《明灯道古录》[2](卷19)
“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忧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答耿中丕》[1](卷1)
由此可知,他肯定人的“好货”、“好色”等欲望和对“富贵利达”的追求,把这些作为“迩言”和“善”,而反对以“德礼”、“刑政”来对人加以束缚。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童心”说的理论基础的,绝不可能是与此相反的理论。
李贽《童心说》把“童心”界定为“最初一念之本心”,然而,为什么对“最初一念之本心”就应该珍视、保存?为什么失掉了“最初一念之本心”就不再成为“真人”了呢?其依据何在?在《童心说》中对此全无论证。那么,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是否已有人对此作过论证,以致李贽已不必论证了呢?其实,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很难找到这样的依据,与此相反的观点却俯拾即是。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人性的问题一直是引人注目的、极为复杂的论题。作为人性论的主流的,是儒家的学说;其中又可大致分为主张“性恶”和主张“性善”的两大派别。荀子主张“性恶”,由此而提倡后天的礼义教化。所以若以他的理论为依据,“最初一念之本心”正是最要不得的。孟子主张“性善”,似乎可以作为珍视“最初一念之本心”的依据,但孟子在与告子争论人性问题时,已经对告子所主张的“食色,性也”的理论作了严厉批判,而只把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伦理观念作为人性的内涵(见《孟子·告子》);换言之,对于“食色”的要求——当然也包括与此同类的物质性的生活欲望——是不包括在“性”里边的。后来的程朱理学之所以在崇奉孟子的同时又大讲“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因为他们把“人欲”都排斥在“性”之外,而只把符合儒家伦理的那些观念作为“天理”的体现,而这原是与孟子的人性论一致的,至多只是对孟子的理论作了一些引申。也正因此,若以孟子的“性善”说作为倡导“最初一念之本心”的依据,那就只能把“最初一念之本心”限制在儒家伦理学说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因为“最初一念之本心”原是含糊的说法,它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婴儿从无知进入有知时的“最初一念之本心”,但那是迄今为止谁也说不清的,所以既可以说这种行为是符合“最初一念之本心”的,也可以说它是违反“最初一念之本心”的,其结果就是大家都随心所欲地阐释“最初一念之本心”;另一种是人在遇到每件事情时的“最初一念之本心”,例如一个饥者看到食物而当时环境又给偷窃或抢夺以充分机会时,他最初很可能萌发偷窃或抢夺的想法,后来或因考虑到道德的要求,或因害怕这种行为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改变了原先的念头,那么,这样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否都应珍视或保持呢?这就必然因不同的伦理观而回答不同。李贽若以孟子的“性善”说为依据,也就不能从原则上肯定后一种含义的“最初一念之本心”,而只能肯定前一种含义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并把“好货、好色”等欲望全都排斥在这种“最初一念之本心”之外。因为按照孟子的理论,“食色”原不属于“人性”的范畴;但李贽的肯定“童心”原是与肯定“好货、好色”等欲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此点已是当前李贽研究者的共识)。若将其“童心”说置于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就反而成为否定“好货、好色”等欲望的依据了:人们可以说:“好货、好色”等欲望是不属于“最初一念之本心”的,坚持这种欲望的人失去了“最初一念之本心”,不是“真人”了。因此,假如考虑到李贽自己的理论体系,孟子“性善”说也显然不能作为提供“童心”的依据。
倘若仔细查究,那么,李贽这种理论的依据其实是禅宗学说,比如“生知”、“空不用空,终不能空”等。以下对此略加分析。
与性善及性恶说相反,李贽强调了人性的自然认识能力。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天赋的本能。他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如耳。”(《答周西岩》[1](卷1))他所说的“生知”,意味着产生对万事万物的觉悟、产生真知;而这种真知,意味着对宇宙的透彻认识。
从表面上看来,他的这种理论与王阳明的“良知”之说相一致。但王阳明的“良知”说是说人具有天然的趋向于善的能力,也即所谓“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其根本乃是孟子的“性善”说。这样,王阳明的学说虽然废除了后天的修养,但仍以儒家的道德为准绳。而李贽在这里所说的“生知”,乃是“人”、“物”所同具的,所以,那不是王阳明说的“良知”(“良知”是只适用于人类的),而是佛家之说。佛家主张“众生平等”、“众生皆具佛性”,这才能认同“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
不仅如此,他还从“众生皆具佛性”进而引申为人性即是佛性:“且既自谓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谓此生不能成人乎?……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答周西岩》[1](卷1))这就是说:只要是人,具有人性,就可以成佛。而且,从“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等语,可知“佛性”是人在身上自然出现、自然成长的,因而只要自然地按照人的本能要求去做就行,而根本不必管这种本能要求是否符合“闻见道理”和“孝弟”等要求,也不必按照某种规范去修持。他的这种否定修持的主张,不能不使人想起禅宗史上的著名故事:南宗六祖惠能针对北宗六祖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偈语,作了另一首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本来就无处“染尘埃”,所以也就用不着拂拭。因为本来就空无一物,所以就不需要任何道德规范,也就不存在人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的问题了。只要保持了“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保持了佛性。
但是,他所说的“佛”并不是脱离了世俗事务的、出世的佛,而是入世的、能够帮助人解决各种世俗事务上的困难、也即能使人的世俗生活更为顺遂的明灯。他说:“……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则是成佛必待无事,是事有碍于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无益于事也。佛无益于事,成佛何为乎?事有碍于佛,佛亦不中用矣,岂不深可笑哉!才等待,便千万亿劫,可畏也夫!”(《答周西岩》[1](卷1))很明显,此处所谓的“事有碍于佛”、“佛无益于事”,都是他所反对的观点。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事”是包括“仕宦婚嫁”之类的俗事在内的。这也就意味着“仕宦婚嫁”等事不但不是与“佛”相对立,而且学佛还对经营“仕宦婚嫁”等事有益。由此可见,李贽宣扬的“佛”,并不是通常意义——也是确切意义——上的脱离世俗欲望的佛,而是与俗欲相得益彰的“佛”。就其本质说来,这样的“佛”与当时市民心目中的能带给人妻、财、子、禄的“佛”(是以市民不断地向“佛”求妻、求财、求子、求禄以致寺庙香火鼎盛)并无二致;当然,李贽说的学佛有益于经营“仕宦婚嫁”等事与当时一般市民认为佛能赐人妻、财、子、禄的想法在具体内容上是不同的,但在本质上却都把摒弃世俗欲望的佛转化成了有利于世俗欲望的“佛”。
因此,如果把李贽的倡导“童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和他的这些关于佛家的理论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明白:“童心”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性本是佛性(是以天下无“人外之佛”、“佛外之人”),而且是时时刻刻都在“生知”的。既然如此,自然只要时时刻刻保持人性——“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即“童心”——就够了,用不着再去学外在的“闻见道理”了;而且,“佛性”本来是与“仕宦婚嫁”等事并不冲突的。所以,在以自然的“佛性”来证明“童心”之可贵的同时,也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把“童心”与“好货好色”等欲望合二而一;而若以“良知”来阐释“童心”,就必然与这些欲望相冲突。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既然在李贽看来,外在的“闻见道理”不但不必学,而且学了反而有害,那么,他为什么又主张“学佛”呢?这不是也在主张学习外在的“闻见道理”吗?不是的。佛家以“悟空”为认识的最高境界,而李贽认为:只要一切任其自然,就是符合了佛家所谓的“空”的原则。他说:
所谓“空不用空”者,谓是太虚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则不得谓之太虚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学者专以见性为极则也邪!所谓“终不能空”者,谓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染了一点尘垢。此一点尘垢便是千劫系驴之橛,永不能出离矣。可不畏乎!——《答邓石阳》[1](卷1)
夫使空而可为,又安得谓之真空哉?纵然为得空来,亦即是掘地出土之空,如今人所共见太虚空耳,与真空总无交涉也。——《解经文》[1](卷4)
在这段话中,他清楚地说明了所谓“太虚空”、“真空”不是“人之所能空”,若有“一毫人力”,反而阻挡了达到觉悟“真空”的状态。因为“太虚”的本性就是“空”,并不是以人力来使得它空的。再说,一旦以其他人为的手段来求觉悟的话,天赋的本性就无法体现出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李贽所说的“学佛”绝不是要人们去学外在的“闻见道理”,而是要人从外在的“闻见道理”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一切任其自然的境界。
所以,李贽这段话不但是使我们明白他所谓“学佛”的真意的钥匙,更是对理学的批判。晚明当时的许多理学家,都将学道见性——通过静坐排除欲望,以见真性——奉为学道的最高境界。李贽之所以援用“空不用空”、“终不能空”等佛教的境界来反对“容得一毫人力”的修养,就是提倡一种自然的人生态度,反对以后天的道德、法律来限制人的行为。因为,在李贽看来,人的欲望与“人性”是一致的,所以,他不但主张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注:《焚书》卷一《答邓石阳》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各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而且认为“好货好色”等欲望都是善的(见前引文),而理学家则是主张克制乃至消除“人欲”,这就违背了自然,堵塞了真空,也就违反了人性。
总之,李贽倡导秉持“童心”,其实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人只要能保持人性,自然能认识真理,用不到去学习外在的“闻见道理”,受它们的束缚;否则就会失去人性。这也就意味着他所提供的乃是自然人性,也即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的欲望、要求、感情等等;所以才会与任何外在的“闻见道理”相冲突。而这种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的欲望、要求、感情等等,在人的童年时期体现得最为充分(尽管人的某些自然要求在童年时尚未成形或尚无充分自觉,但其根蒂却在童年时期就已存在,其后的强化不过是此种根蒂的滋长),这也就是李贽特别强调“童心”,在《童心说》中作出如下论述的原因:“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童心说》[1](卷3))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贽虽主要利用了佛家之说,但也有许多违背佛家理论之处。第一,佛家只是主张众生皆具佛性,而并不主张人性就是佛性。所以,李贽的“人外无佛”、“佛外无人”之说是对佛家此说的修正。第二,佛家本来是要摒弃世俗欲望的,李贽却说学佛有助于经营“仕宦婚嫁”之类的事务,从而把佛与世俗欲望调和了起来。这更是对佛家之说的篡改。第三,佛家的主张“空”,其主要内容之一是要破除“我执”,破除了“我执”,也就不会去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了。李贽却把这种关于“空”的理论改变为纯任自然,而即使就儿童来说,纯任自然也必然是个性越来越发展,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对欲望的追求越来越自觉,这就与佛家要求破“我执”背道而驰了。因此,我们固然不妨说李贽“童心”说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佛家之说,但更确切地说,“童心”说的理论基础乃是经过李贽改造了的佛家之说。而在他的这种改造工作中,其对自然的强调,则又显然与王阳明的“心自然能知”之说和道家的主张自然无为的理论存在相通之处。不过王阳明说的“心自然能知”是说心能自然地产生符合孝弟等道德规范的意识,道家(不是指道教)所说的自然无为则是要使人回到最朴素的生活,而李贽的强调自然,则是主张顺应普通人的自然要求,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愈益丰富。所以,他对释、儒、道三家之说都有所吸取,但也都有所剔除,以他自己为主,重加组合。
李贽之所以以佛家理论为主干而构造自己的哲学,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佛家思想(特别是禅宗南派的废除修持之说)易于被改造得与李贽的人性论和社会思想相一致,另一方面当也是因为佛家思想在士大夫中远不如儒家思想之家喻户晓。换言之,在李贽的时代,士大夫中真正懂得佛家真髓的很少,无论李贽把它改造、理解为怎样地远离佛家学说的本来意义,在士大夫中也未必会有人发觉这一点而加以批判。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李贽生存时和去世后都受过不少批判,但却没有见到以严格的佛家理论为依据而批判他歪曲佛家的。
收稿日期:2000-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