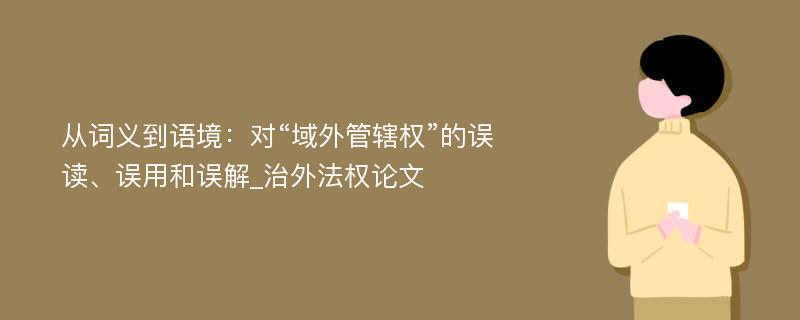
从词义到语境:“治外法权”误读、误用及误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外法权论文,词义论文,误读论文,语境论文,误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2-0152-12 “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的概念由来已久,关涉两者的论争已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无法规避也未曾规避之焦点问题。清末以来便有两概念辨析的论著问世,民国更达至顶峰。学界基本观点有二:一为主张两词判若鸿沟。民国学人吴颂皋、陈启天、陈腾骧、耿习道等皆持此论,陶广峰、郭卫东、赵晓耕、李启成等学者也多以治外法权指代外交官之豁免权、领事裁判权指代领事所拥有的司法特权为基本点,进而得出“治外法权应当以不损害国家领土主权为前提,而领事裁判权则为一国单方面优惠政策,有违于国际公法上的平等原则”①的主张;二则视两词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有交融。周鲠生由词语原意“本国领土以外的法权”而得出“领事裁判权恰是一种治外法权”②的论调为郝立舆等继受,并得到王铁崖、吴义雄、康大寿等学者的广泛认可。笔者无意于两种论调非此即彼的简单辨正,却希图于两词论争过程中学者们常易忽略的几点陈一孔己见,以祈方家指正。 一、英美还是日本: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词义混淆的省思 最初,建构于“怀柔外夷之中,仍不失天朝体制”③观念下治外法权的相让,在清廷看来“并非违背国家的主权”④之举,却恰恰是“天朝固有的观念”⑤。伴随中外条约的签署及国际法知识的引介,近代意义上的治外法权的意涵范畴渐为国人知悉。王韬称之“额外权利”⑥,郑观应亦称华洋交涉之案“此尤事之不平者”⑦,可见,对于治外法权或者领事裁判权的概念厘定,彼时并未引发争议,无论是“额外权利”还是黄遵宪依据日语转译“治外法权”一词,皆指华洋诉讼中不公审断的状态,而未将之付诸专有名词指称。此端缘由乃是早期中外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等)仅描述华洋诉讼的争端解决方式而未有专词代称之故。 (一)国人对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的认识的激变 国际法观念的逐步深入以及作为专用术语的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在条约与辞、书中的次第浮现,使得国人对于两词含义的追问逐渐显现,继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是治外法权还是领事裁判权”的讨论。 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2款中以extra-territorial rights对应“治外法权”一词⑧,使得治外法权正式作为词语首次于条约正文中出现。该词在辞书中的最早出现见于1908年颜惠庆所编《英华大辞典》,其中将extra-territorial注为beyond the limits of a territory or particular jurisdiction,解释为“疆界外的,法权之外的,治外法权的,管辖之外的”;以exterritoriality为the state of being beyond the limits of a country,as the settlements and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解释为“国境之外,治外法权,治国权所不及,免辖(犹在中国之租界及外人)”⑨,该辞书未对两词作严格划分。 consular jurisdiction的用法则直至1918年6月13日的中瑞(士)《通好条约》附件中才正式出现,约云“关于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瑞士国领事应享有现在或将来允与最惠国领事之同等利权”⑩。及至1921年中墨《暂行修改中墨1899年条约之协定》继续沿用此语(11)。不过,值得指出,早在1836年惠顿(Henry Wheaton)《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已然使用consular jurisdliction一词,业已初露依两国约定而赋予领事有权对旅居国外的侨民拥有管辖权之端倪(12),只是在经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译为《万国公法》之时仅以“因约而行于疆外者”指称,并未依照原文将其确定为“领事裁判权”(13),使得领事裁判权一词错失进入中文语境的先机。至1925年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编纂的《中英法外交词典》,consular jurisdiction一词才算在辞书中首次出现,表征其基本含义为领事裁判权;且该词典将exterritoriality、extraterritorial right的解释通称为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为治外法权(14)。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收录词条14000余条、总计400万字的《法律大辞书》可谓民国时期辞书编纂的佼佼者。该辞书将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解释为“国家对于外国代表国权者,因敬礼之表示,及职务执行上之便宜与必要,不行时其管辖权而予以免除也。享有此项权利者为外国元首外国外交官及代表或外国军队之在境内者以及国际联盟国际法庭之人员”;对领事裁判权(extraterritoriality or consular jurisdiction)则作以详析,“凡甲国人们依条约在乙国领土内不受乙国司法权管辖,而由本国驻在之领事官依本国法律加以制裁者,曰领事裁判权。此种制度起自土耳其,继行于东方各国,学者对此制度之根本性质,有谓系治外法权之一种者,有谓系权利国代行法权之说者,有谓系权利国裁判权之延长者,据余所信,以最后说为当,但亦有所谓混合或者会审之例外者,然均以条约之订立为准”(15)。可见,此辞书对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的概念解释固然无差,认为两者最宜区别,不可相混,岂料治外法权之词却作extraterritoriality解,误入两词混淆境地,显然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上述词语辨析的含混不清必然引起学界热议。光绪32年(1906)10月12日载《北洋官报》的“论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性质之区别”一文可谓最早对此阐发之作。文中就两词区别列明:公使、元首等3类享有完全治外法权,而领事则享有例外之治外法权,仅在领事兼理公使或两国定有领事条约之下享有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则为旅居他国之人,凡民刑事诉讼并不遵守他国法律,而由本国领事进行裁判(16)。在其看来,依领事条约而定之治外法权并非领事裁判权,此种结论实非可靠。其后,民国学者论争便多聚焦于此,对两词区别标准而得之论断也纷乱复杂、层出不穷(17)。 据笔者分析,对于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的认知,民国学者观点基本分若两极。梁敬錞主张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大异”(18),陈启天将之视若“有如天壤,不可混也”(19),陈腾骧认为两者“实则各为一物,不可混为一谈”(20),吴颂皋则认为二者意义“大相悬殊”(21),总之,将二者严明区别的论调俯拾皆是;不过,亦有学者认为两者并非毫无关系,并将两者综而述之,认为领事裁判权至少可称作治外法权的一种,周鲠生即指出,“治外法权与英文的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相当。这就在本国领土以外的法权的意思。……治外法权的意思,若依这个解释,领事裁判权恰是一种治外法权”(22)。该观点并非毫无市场,郝立舆在《领事裁判权问题》一书中便基本照搬周鲠生的分析,只在文字表达上略作修饰(23)。综上所述,对于两概念的论争,民国学者的观点也大致可以总结为: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不可混同以及两概念有相交点,即领事裁判权为狭义治外法权之一种形式。此两种认识基本涵盖学者诸多论调,即使是今时学者,从论点、论据到最后的结论都未能出乎其外。 两词混同局面缘何得出,此时的民国学者也作了些许分析,且在此问题上似乎达成共识。综述之,谓大陆法系包括日本学者对于两概念的区分极为严谨,而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此则往往使用治外法权代之,此种结论之后又演变为西方列强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的需要,进而有意混淆两者区别,甚至借“治外法权”之名,欲获“领事裁判权”之实(24)。具体言之,则诚如周鲠生于《领事裁判权问题》所指出的,“欧洲大陆与日本学界,把领事裁判权与这个意思的治外法权两个名词分得很严……但是英美习惯及我国倾向,却喜用治外法权的名词;常把治外法权,当作领事裁判权说”(25)。这一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附和(26),并成为他们以此证明前述混淆概念并非归罪于己的有力支撑。 (二)英美对近代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意涵两分的认定 前述学者基本认为,英美学界对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之间的关联讳忌莫深,往往通过将两者混淆,达致以治外法权之名行领事裁判权之实的目的。果如此言还是可另作他解,值得审慎考察。 笔者以exterritoriality为关键词检索“近代法律全文资料库:法学专论”(27)数据库,查得该词首见英国法学家菲力摩尔(Robert Phillimore)《国籍法释义》一书。该书对此词解释称:其基本依据乃是基于通用礼节性习惯,适用对象不仅仅包括使臣个人,还延伸至其家属及随从;此种特权有时如1745年《俄萨和约》般由条约明文规定(28)。文中提及,中世纪的领事裁判权(consular jurisdiction)机制在属地主义的影响下已经改变其情境及特色,在基督教国家失去其效能,成为仅具仲裁性质的特权。不过在伊斯兰国家则因条约明文规定得以继续保留(29)。不过,遍览全书皆未觅见extraterritoriality一词踪迹。 威斯特莱克(John Westlake)在1858年《论国际私法或冲突法》一书中开始使用extraterritoriality一词以指代通说的治外法权,并指出这一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特权并未延伸至领事,若非条约明文规定则其并不享有司法豁免权及管辖权(30)。本著虽对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在词语适用上存在差异,但其所表征之意义却如出一辙,并不含混。 对此,皮葛爵士(Sir Francis Taylor Piggott)总结道,一些学者认为exterritoriality和extraterritoriality并无不同,而另有学者则认为前者为公使及其附随的特权,后者为建立于东方的领事裁判权(consular jurisdiction)之下的条约特权。但上述特权准确地说应被描述为“域外的”(exterritorial),由此称之为“治外法权”(exterritoriality)并无不当。在理论上,使节被授予主权豁免与居于他国而豁免并无二致,两者区别在于,前者为礼节性的,而后者则依照条约;两者程度也不同,前者几乎完全豁免及统一,后者则为局限且类型各有不同;区别还在于对母国政府产生关系及通过法律影响享受权特权群体的方式不同。但就基本事实上两者是共同的,普遍结果都是在国外的旅居者,因其国君主权力的影响使得居在国对旅居者本应享有的管辖权不同程度的放弃(31)。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治外法权在作为单独术语最初使用时,其基本意涵为“域外的”(exterritorial),故常以exterritoriality、ex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形态表述,在形成为固定习惯并得到主权国家认可后演变成为礼节性的指称“外交官”等群体的司法特权,并与之形成固定搭配。17世纪以来,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缔结及属地管辖权观念的逐步兴盛,原本视若稀松的域外司法管辖权限缩为仅涵摄使臣及其家属、随从的较小范围,原本与之同享这一司法特权的领事蜕变为仅具商业性质之人员进而丧失其司法管辖权属性,在西方国家自是如此。但依然存在一种特殊范例,便是基于宗教、文明及国情等诸多因素,使得领事裁判权形式继续存续于东方国家,这也便造成了本与治外法权区分得当的领事裁判权在此领域又变得含混起来。 其次,若依前文所述领事裁判权断然得出两者泾渭分明并进而以此为据抨击英美国家以治外法权之名行领事裁判权之实的结论未免有些武断。实际上,英美对之区分已然,也未继续依照外交官所享特权之依据而主张对旅居东方之领事及侨民适用裁判权。两者区别之处便在于外交官之治外法权的享有乃是国家间基于礼节性的互相认可的消极性质的特权,所辖范围有限;而领事之治外法权则是基于国家之间的特殊条约的明文规定而获取的积极性质的特权,不仅及于领事,更是涵括侨民,而以领事裁判权称之仅仅是源于最初裁判者主要是领事而非其他。当然,此种特殊条约其性质往往以“不平等条约”指称,才使得领事裁判权自然而然蒙上一层对他国司法主权践踏的卑劣色彩。但此种价值评判其实在最初阶段并非不可或缺。 最后,领事裁判权的称谓实际上来自于consular jurisdiction,正是条约下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才导致领事裁判权这一术语的产生。可以说,consular jurisdiction正是此种意义上治外法权的实践状态(32)。关于这一点,吴颂皋也承认,领事裁判权本身固然不是一种治外法权,但至少是使旅居东方国家的外国侨民享有治外法权的唯一媒介(33)。所以贸然将二者作以严格划分的观点值得深思。 (三)日本学界对于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界分的延续 前述表明,对于两种治外法权的认识,英美学者虽在词语运用中并未作出明确区分,且用语时有混乱情形,但明确的是,对于两者所涵摄范围有着清晰的界定。既然如此,国人所主张的英美学者为享特权而有意误用或混淆两者差异以愚弄国人的结论便不能贸然作出。那么仍存在一丝疑问便是,日本学界果如学者们所认为的对两概念作出了明确的划分? 日语中“治外法权”一词多表示为chigaihoken(34),而其所指称的词则是extraterritoriality(35)。关于这一点,台湾学者林茂生有过印证,“Tī-goā hoat-koan(治外法权):照条约上的约束,外国人所享受特别的权利,毋免受在地的法律所拘束,通自由照本国的法律,对彼所在的领事来家己裁判,抑是行政。对国语的chigaihoken来,就是英语的extraterritoriality”(36)。 又查1894年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外相睦奥宗光、イギリスに治外法権の撤廃(領事裁判権の撤廃)を認めさせゐ,与之对应英文版为“The Anglo-Japanese 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1894):Foreign Minister Munemitsu Mutsu obtained an agreement from England to abolish exterritoriality(whereby consular jurisdiction was repealed)”(37)。对于此约的翻译可见,约中恰恰以exterritoriality用于指代治外法权。 通过前述对比,日本学界对于两词词义运用所致模糊不清的端倪业已初见。为进一步了解日本学界对于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的区分,笔者以“治外法权”为关键词对“近代日本史料资源库”(http://kinda.ndl.go.jp)进行搜索,查得包含治外法权章节的著述有241部之多,以“领事裁判权”为关键词检得著述50部,其中17部论著同时提及二者(38)。可见,日本学界对此作出区分的著述并不十足丰富,多数著述并未将二词作以区分进而展开论述。通过初步研读,笔者发现平冈定太郎所著《国际公法》(攻法会1898年版)、中村进午所著《新条约论》(东京专门学校1898年版)以及《平时国际公法》(中央大学1906年版)等著述在论述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之间的区别上用力颇多,遂作以简要综述。 桥本胖三郎将治外法权作出两种区分,指出此处所论及治外法权是基于特殊条约产生的权利,而非国际上通行的治外法权。对于目前欧美国家和东亚诸国之间存在所谓治外法权应尽早取消(39)。此处虽未使用领事裁判权一词,但以特指的治外法权相称。 平冈定太郎先谈及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以及关于规定罪犯引渡的事项;而后又指出,领事裁判权则基于特殊的条约产生,是国际法上的一个特例,此权利的产生需要具有重大理由,通常是所谓文明国家的人民认为未开化国家的法律不健全,以保障文明国家的人民在未开化国家的生命财产以及利益的安全为由,签订条约规定该项权利;最后说明,两者区分突出表现在性质、原因、适用主体以及目的诸方面(40)。可见,这正是主张二者泾渭分明的民国学者的理论来源。但需说明的是,此种观点与前述英美学者的论调并未有实质差别。 中村进午采取对两者分而论之的策略,对领事裁判权注重于历史沿革与内容梳理,对治外法权则着重其意义的明晰。他通过对英语exterritorial进行解释,认为ex意为除外,意味着“领域之外行使权利”,并指出治外法权经历着属人向属地的转变。此外,还对拥有治外法权的主体进行分析,指出把治外法权等同于领事裁判权的论断极为常见(41)。但其最终并没有对两概念作出详尽的区分说明。不可否认,以上著述有助于明晰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的区别,也成为国人常引以为据的主流观点,但不容忽视的是,对于两词的适用并非前述“日本学者对于两概念的区分极为严谨”般精确,学者观点并未达致统一。 现代日本学者也习惯采治外法权为广义概念,如《国际法辞典》对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便是明证(42)。可见,日本学界也并非前述民国学者所认为的二者泾渭分明,同样存在混淆两者区别的现象。有鉴于此,今井嘉幸曾指出领事裁判权之语稍欠精要,试以外国裁判权统之(43)。 二、由日语到中文:“治外法权”在词语转借中的误读及误用 近代以降,西方法律词汇先是藉由来华传教士的引入而传衍,希冀于汉语中搜寻对应词以表征类似含义,对此种语言传播现象学界一般以外来词、借词指称;而后期驻外使领臣、留学生的规模性出洋,使之成为法律词语引介的中坚,引领“跨语际实践”及法律词语的近代化。此过程中,得源于日语对西方知识的积极接受使之及早实现与西方词语接洽、重构,并基于“汉字文化圈”的天然秉性,使得日、中词语转借而来的“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等涌入法学类书籍与法政学堂,并在中国大量出现(44)。可以肯定,治外法权正是经历由日语向汉语的词语转借,但在引入及吸收过程中却经历着语际交流中不可避免的误读现象。 (一)谁之误读? 使日参赞黄遵宪所撰《日本国志·邻交志》乃是最早引入“治外法权”这一概念的著述。《邻交志》共6处提及此词,黄氏不仅将此词由日文转借为中文,还对其基本内涵及缘起予以详介,谓“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权也”(45)。 此种解释却引发学界异议。据笔者所见,前述“论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性质之区别”(1906)一文即认为黄遵宪所编《日本国志》对治外法权的解释“颇欠明晰”进而导致国人对此误读,应为“本国之民不受他国法治之权利,非谓居留他国而有能行本国法治之权利也”(46)。不过,笔者以为该文所持观点与黄氏之观点并无任何显著区别,只是话语稍作变通、换种说法罢了。真正引致异议的在于1903年由汪荣宝、叶澜编纂的《新尔雅》一书,该辞书将治外法权定义为“在甲国领土内之乙国人们,须服从甲国之法律者”(47)。这一概念与黄氏定义显然大相径庭。那么,上述几种理解究竟谁更接近词语原义呢? 首先,黄遵宪对治外法权是否存在误读呢?在《日本国志》卷首序中,黄遵宪坦陈“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48),这当然并非自谦,实际上,黄在赴任驻日参赞前并无日语基础(49)。但这并不能直接说明其不可胜任日语转译事宜,《日本国志》尤其“刑法志”堪称日文汉译的绝佳文本足以证实黄氏在中日语际交流中的突出贡献。当然,这一方面由其依照日汉文字相通法则直接将日语法典中法律新词“拿取”(50)较为便捷;另一方面也有赖日本友人相助,如曾求石川鸿斋将日文的文献译为汉文,并结交鬼谷省轩、重野安铎、宫岛诚一郎等著名法、史学家(51)。可见,在此种情境下的黄遵宪显然对于由日转中词语的把握并非毫无经验,而是在研读中发现日语结构规律,提出诸如“日本之语言其音少,其语长而助辞多,其为语皆先物而后事,先实而后虚”等真知灼见,无怪乎周作人认为黄遵宪的总结“很能说明和文的特点”(52)而对其盛赞有加。 其次,《新尔雅》是否存在误读?这应从汪荣宝、叶澜赴日经历及成书背景谈起。两位编者曾于1901年留学日本,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等研习政治、法律及历史等,回国后也皆任职于京师译学馆从事教员工作,汪荣宝更是于1922年成为驻日公使。但该辞书却绝非二人倾力之作,只可看作留日学子风潮这一特定时期下的产物。这一时期,不少学子遵从梁启超“和文汉读法”,此法便于初学者对日语的简单掌握,但无视语种界分差别、以中文之法习日文的理念设定必然导致学人对于日语的理解并不精准,也造成语言沟通出现障碍。此后,为弥补此项不足便繁衍出通过对“半懂不懂”或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的词语作出注解,以增进人们对其认知的做法。梁启超本人便多有尝试,其行文中对“群学”、“智学”、“资生学”分别注解为“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等(53)粳是明证。在此种情境之下,汪荣宝、叶澜于1903年所编《新尔雅》的初衷正在于将此种词汇辑编成册,使之趋于系统化。如其再版广告中所言,“留东同人有鉴于此,特就所学分科担任,广汇术语,确定界说”(54)。该书分14部分,对政、法、计、教育、群等专业词汇作出诠释,虽薄薄百余页,却涵摄广袤。与其时留日中国学生的译书、杂志等出版物一样,《新尔雅》可定性为一本在日本执笔、印刷之后,通过中国国内的书店借以销售的图书,是20世纪初叶由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所编纂的新词语、术语的词汇集(55),在当时也颇具影响。该辞书以简明含义解释西方法律中的特有名词,仅就此种意愿自是有其贡献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工程完美无缺,前文提及该书编者并非全才,面对这一繁杂汇编难免有失妥当,也造成该书所辑录词语的解释准确与否值得探讨。而且该书对同一词汇还存在多个解释现象,都足以说明该书编纂绝非无瑕。将“治外法权”定义为“在甲国领土内之乙国人们,须服从甲国之法律者”的这一表述显然表明编者对此不甚了了,可能依据词语的表象便望文生义的依照中文惯常语法解读将之理解成为“甲国”有治理“在甲国领土内之乙国人”的权利。依照此种解释,治外法权反倒成了“属地主义”的代表,而我们一直所讨论的治外法权恰恰是一种不正当的“属人主义”的近代延续,两种解释显然差之千里。那么,此种解读是否具有普遍性呢?其实不然。 据笔者考察,以戢翼翚为首的早期留日学生1900年于东京所创的《译书汇编》期刊,其时也颇具影响。该刊第7期刊登日人鸟谷部铣太郎《政治学提纲》一文在论及“公使”一词时曾对治外法权作以注解,言明“治外法权者,盖谓不受他国法律之制限,如有罪必使其本国自治,他国不得而治之是也”(56)。即使按照此种诠释仍应得出治外法权乃是“于甲国之乙国居民有行乙国法之权”的意涵,与前述《新尔雅》的表述绝非一致。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尽管词义解释上存在着些微差异,“治外法权”的含义终未脱离“领域之外的治权”这一基本内涵,黄遵宪的解释显然恰合词语原意,也与日本学界通说极为妥帖,而留日学生所编《新尔雅》显然在此问题上并不精当,所作解释完全背离词语的原意、造成误读。 (二)缘何误读? 笔者以为,此种误读正是由前述国人所惯用或提倡的“和文汉读法”负面效果所致。依照汉语的语法与词语结构在分析“治外法权”这一词语时确实会产生背离原意的解释,使得原本属人主义延续的词语平白无故成为属地主义的代名词。甚至在郝延平及王尔敏所撰《剑桥晚清史》第三章“国人对中西关系认识的转变”中提及治外法权还依旧采用“管理外国人之法权”的说法(57)。 对于此词的误读,语言学家胡以鲁早就特例指出,“治外法权,就吾国语章法解之,常作他动字之治字。下缀以外字者,宜为外国或外人之隐名。若欲以外为状词,其上非常用为名字者不可”(58)。国人依照汉语习惯,往往将“治”后面的“外”字理解为“外国”或者“外国人”,由此,“治外法权”也便相应解释为治理外国人的权力,前述《新尔雅》可谓个中代表。但此种解释却与原词意义相反,主要原因在于,日语中若要将“外”字作出“之外”的理解,那么其前面必须有名词相称。 就此笔者咨询关西大学沈国威先生,其回复称,“日本人造词时的理解是统治以外的法权,即‘外’是自己的权利管辖范围以外的意思。‘治’作为定语修饰‘外’”。但按照汉语规则,“治”当治理、统治之解时,乃及物动词,其后所跟名词一般作宾语理解,“外”也便被理解成“外国人”,于是治外法权也便相应演绎成为“治理、统治外人的法权”。初赴日本的汪荣宝等,正是以此惯常理解译介此词。可见,将治外法权简单理解为治理外国人的法权的解释显然不合日语构词原理,也违背了该词的原意。 由此,正因为治外法权一词的最初创造者为英美等西方列强,而其所表达的最初意愿便在于“超越其领域之外依然保有法权”。于是,对于治外法权的理解应将之放诸其词语来源处这一特定语境之下进行解释,并不能将其随意转换,更不能对其产生偏离语境的误读。笔者以为,该词主语不应限定为被施用国,而应建立在施用国语境之上,将其理解为“治域之外的法权”这一原始内涵,具化为其地域管辖之外所拥有的司法管辖权的确切含义。唯此,方可避免基于认识错误而致本为属人主义延续的“域外法权”误解为属地主义的“治理外国人的法权”。 (三)“取消”而非“收回” 误读必然导致误用。学界提及治外法权,往往将其与“收回”叠加,组成“收回治外法权”的固定搭配。此种搭配的使用较早可见1905年沈家本所呈《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指出“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59);迟至1908年张之洞以学部名义覆奏新刑律草案折中提及“盖收回治外法权,其效力有在法律中者,其实力有在法律外者”(60);更有报刊杂志文章以此为准纷纷以“收回治外法权”作题定论(61)。不唯如此,时至今日,对此搭配之沿用仍大有人在,往往以“英美放弃领事裁判权,我国收回治外法权”(62)等貌似对仗之语句存在,兹不具数。 不难发现,前述语句所及“收回”正是将治外法权视为“治理外国人之法权”认识下的误用,其意在呼吁国人摆脱无法治理外国人的窘态,重新获得治理外国人的属地管辖权。然而经过前述分析,可以发现此种运用虽符合汉语理解习惯,但显然并非词语本意。不过,应当指明,沈家本、张之洞等人误将“治外法权”意为“国家属地管辖的司法权”的“治权”(63),这在其时的认知环境下尚情有可原,但目下今人将此误读继续沿用、扩大则实不应该。 而且,此时的中外条约已然出现治外法权一词。前述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2款规定“……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64);随后的中美、中日条约基本沿用此条,未作过多变动(65);1908年中瑞(典)《通商条约》第10款也规定,“一俟各国均允弃其治外法权,瑞典国亦必照办”(66)。上述约文中英版本对照,可以发现其以extra-territorial rights对应“治外法权”,以relinquish对应“弃”。于是,在此种意味上,治外法权必然是建立在西方国家放弃的基础上,但西方国家放弃未必就意味着中国收回,在此语的运用上必然不能简单以一来一往、一失一得的形式表述,倘若如此,则曲解了词语的含义。西方国家所主张“治域之外的法权”可以由其放弃、废除、取消、收回,这是基于西方国家作为第一人称施用国可以采取的基本表述,但对于中国这一饱受压榨的被施用国基于特定语境却不可使用“收回”表述,以“取消”或者“废除”此种制度表述方属恰当。 三、利权争回:基于民族主义语境下治外法权的误会 近代语境下的“不平等条约”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文化中有着强烈的隐含、象征意义,可以说已经上升为国家与民族危亡的要害关键。作为与“不平等条约”相提并论的领事裁判权,在民族主义色彩的渲染下也已超出原本词义所涵括的简单意义,上升为政治性的术语。民众于有识学者鼓动下无不为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享有的治外法权或领事裁判权而愤慨,再加上报刊杂志等舆论媒介对此不遗余力的宣传,造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67)、“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和特权(领事裁判权)”(68)等口号式样语句大行其肆。甚至对基于法权会议而作的司法调查,民族主义者也大多采取排斥态度,谓“和平主义者……不懂得帝国主义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是何种用意;他们不问帝国主义有何权利可以干涉中国的司法行政,拿中国司法行政的改良为撤废治外法权的条件……”(69)时任“中国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张耀曾即提出,“望吾国民勿失此收回治外法权之大好机会……急宜万众一心,合群运动”(70),法学期刊与舆论等也纷纷以此为基调。此种背景下,本就含混不清的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这对概念更难辨明。彼时学者们的任务绝非仅仅在于将两者作以区分,更兼有承担“领导和训练民众”(前述耿习道语)的政治使命。于是,本也涵盖各国公认的外交豁免权含义的治外法权显然并不具备适于情感宣泄的纯粹潜质,不如领事裁判权这一更易为民众理解和领会的词语来得直白、具体,更易激发全民族的反抗热潮,与前述“不平等条约”的主旋律更为融洽。 殊不知,治外法权的提法涵盖范围更广,在争取利权的非常时期,显然更有助于保护国家司法主权。其实,早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时期,中国代表团便在题为“中国希望条件之说帖”中主张废除治外法权(71);随后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亦请求西方取消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而非领事裁判权(consular jurisdiction)(72);1926年《法权会议报告书》中,中国代表团同样是使用治外法权而非领事裁判权的字眼来主张权利(73)。王宠惠所提交的《中国委员对于在中国治外法权现在实行状况之意见书》,指出“各国委员所送达委员会关于调查治外法权之文件,仅记载各该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一节,中国委员以在中国治外法权现在之实行状况,其范围较领事裁判权为宽,实际上收治外法权之支配者,远出领事裁判权范围之外”(74),无疑是对此的最佳证明。此种努力之下,法权调查团调查“参观各省法院、监狱、高等地方审检两厅及察看中国司法制度之实行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各国领署会、租界巡捕房、洋务拘留所等与治外法权相关的外国机构,也都受到调查”(75),虽事后所作报告书并未直接引发治外法权的废除,但无疑其为之提供了可能。 废除治外法权条约的呼声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顶峰。二战期间,中国沦陷为日占区,使得西方国家在华治外法权的存在已无实质意义。1942年3月27日,美国远东事务部(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部长汉密尔顿(Maxwell M.Hamilton)在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沦为日本军管区,使得美国行使治外法权已无可能。而治外法权及其附带作为历史陈迹显然也已不合时宜”(76)。与此同时,国内舆论渲染浓郁,充斥其间的多是呼吁英美废除治外法权的言论、社论。其实早在1941年中美外长就此已经展开交涉,6月2日《新华日报》便刊载“美国务院发表郭外长与赫尔来往函件,赫尔谓美愿于将来放弃治外法权,一俟和平恢复即可进行谈判”(77)的声明,并随即登载《治外法权撤废问题》的时评性文章(78);《纽约时报》1942年4月19日刊登宋美龄的《如我是观》一文,指出“西人还建立起一种恶劣的司法制度,这便是举世皆知的治外法权,它使外国人不再受中国法庭之裁决”(79),在美国产生舆论导向作用。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作出“美英两国应向中国表示,决定放弃治外法权”(80)的回应性报道,随后又有“美舆论主张立即放弃英美在华治外法权”的呼应性主张(81);《解放日报》更是转载美国参议院汤姆斯“联合国应即放弃在华一切治外法权”的建议(82),这一建议即在美国已得到各报支持(83);《新华日报》就此问题专组一栏“社论:论英美放弃治外法权”的文章(84);1942年10月11日“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感谢美国自动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电”中,也声称“欣悉美国自动放弃在华之‘治外法权’,举国无不欢忭”(85);随后《文化杂志》刊有“英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声明”(86)以及何襄明在《新中华》发表《废止约定治外法权应循的途径》(87)一文,等等,不一而足。即便从始至终一直坚持“领事裁判权”语调的《申报》,1943年也一改往昔格调而刊发日本、丹麦、瑞士等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文章(88)。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治外法权已得到舆论认同与普遍接受。 迫于各种压力,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89)。通过上述条约及其换文,美、英在华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 rights)宣告终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还专门作出特别报告,对美国在华治外法权从初建到废除的近百年历程进行回顾性总结,并对治外法权的废除提出合法性解释,指出:“百余年前,对于条约中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并不被认为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对历史、哲学、政治体制、法律与司法体制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或政体,治外法权往往有助于彼此交流与沟通,减少法律冲突与摩擦。……但随着时间推移,情景已然大相径庭,此种背景下的中国采取废除治外法权措施恰合逻辑。”(90) 可以说,治外法权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已成为国内外通用之共识,对其与领事裁判权差异的论争已遁于无形,而开始贯彻以治外法权一词作为主线的态度。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各主要条约的签署文本上,并没有因词语产生任何争执或者争论。究其缘由,一方面是由于条约的签署其初衷正是基于取缔或终结治外法权为根本目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两词的中文表述虽然大相径庭,但体现在英文约文或讨论中,这一对象早已被限定在确定的范围内。所以,无论是治外法权还是领事裁判权,在条约签署中所指称的对象是一致和确定的。学者们聚焦于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民族主义情结体现的一种特殊方式,实际上并无实质意义。 结语:重新审视治外法权 最初意义上的治外法权实际上可以归入“域外法权”这一具有高度涵盖性的范畴,不过,民国学人基于民族主义与政治语境的双重压力,在摆脱殖民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大旗的指引下,对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二者概念所作的简单辨正未免有失客观。考察发现,英美学者对两词所作释义虽未免偶有混乱,但对两词已然作出较为清晰的界限说明,反倒是国人所信赖的日本学者在此问题上不甚明晰。离谱的是,因语言传播路径的失措使得国人对“治外法权”造成误读,进而导致该词在实践中产生误用,本应以“取消或废除外人在华治外法权”句式表述,却演变为“收回治外法权”的固定搭配。此外,近代国人尝以领事裁判权试图获取最广泛民族舆论的支持,却可能因该词所辖范围有限反而不利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利权争回,与原有初衷背道而驰。须知,若简单以领事裁判权指代列强在华司法管辖权,势必无法将领事法庭之外英、美两国所设置的驻华法院这一职业司法机构模式(91)囊括其中。于是,相较于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一词显然更具有包容性、涵盖性与确定性。 收稿日期:2014-10-30 注释: ①赵晓耕:《试析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周鲠生:《领事裁判权问题》,《东方杂志》第19卷第8期(1922),第9-10页。 ③民同廿一年十二月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三册),第51页。 ④Frank E.Hinckley,American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the Orient,Washington,D.C.:W.H.Lowdermilk and Company,1906.p.17. ⑤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97-498页。 ⑥(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90页。 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页。 ⑧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9页;John Van Antwerp Mac Murra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p.351. ⑨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08年版,第836、834页。 ⑩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374页;J0hn Van Antwerp Mac 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Vol.2,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p.1430. (11)“本国政府放弃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一事,当居修改各款之(express on one of the amendment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reaty the renouncement that will be made to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in China)”,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3页。 (12)其英文版第2部分第2章第12节标题便是consular jurisdiction。See 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London:B.Fellows,Ludgate Street,1836.pp.155-161. (13)参见[美]惠顿《万国公法》,[美]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节,第106-107页。 (14)参见外交部条约司编《中英法外交词典》(1925年刊),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74辑0740),中国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40、59页。 (15)郑兢毅编著:《法律大辞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82-783、1865页。 (16)《论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性质之区别》,《东方杂志》第3卷第13期(1906),第232-233页。 (17)参见李洋《治外法权,还是领事裁判权?——从民国以来学者论争的焦点切入》,《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6期。 (18)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19)陈启天:《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辨》,《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7期,第5-7页。 (20)陈腾骧:《领事裁判权阐说》,载东方杂志社编《领事裁判权》,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0-62页。 (21)吴颂皋:《治外法权》,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0页。 (22)周鲠生:《领事裁判权问题》,《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8期,第9-10页。 (23)参见郝立舆《领事裁判权问题》,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2-23页。 (24)赵晓耕:《试析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5)周鲠生:《领事裁判权问题(一)》,载东方杂志社编《领事裁判权》,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1-12页。 (26)参见郝立舆《领事裁判权问题》,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23-24页;《领事裁判权的撤废问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宣传部1930年印行,第6-7页;耿习道《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30期(1930年5月);等等。 (27)“近代法律全文资料库:法学专论”(The Making of Modern Law:Legal Treatises,1800-1926),主要收录了19世纪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者与思想家的著作,是目前收录时期最完整的关于传统法律的法学专论全文资料库。 (28)Robert Phillimore,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Vol.2,Philadelphia:T.& J.W.Johnson,Law Booksellers,1855.pp.97,137-138. (29)See Robert Phillimore,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Vol.2,Philadelphia:T.& J.W.Johnson,Law Booksellers,1855.pp.166-167,170. (30)See John Westlake,A Treati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or,The Conflict of Laws,with Principal Reference to Its Practice in the English and Other Cognate Systems of Jurisprudence,London:W.Maxwell,32,Bell Yard,Lincoln's Inn,1858.pp.114-121. (31)Sir Francis Taylor Piggott,Exterritoriality:the Law Relating to Consular Jurisdiction and to Residence in Oriental Countries,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s,Limited,1892.p.3. (32)Sir Francis Taylor Piggott,Exterritoriality:the Law Relating to Consular Jurisdiction and to Residence in Oriental Countries,London:William Clowes and Sons,Limited,1892.p.4,50. (33)吴颂皋:《治外法权》,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8页。 (34)See Mark Spahn and Wolfgung Hadamitzky,The Kanji Dictionary,Tuttle Publishing,1996.p.366,507,509. (35)See Hyojun Romaji Kai,All Romanized English Japanese Dictionary,Tuttle Language Library,1973.p.255; Tsuneta Takehara,A Standard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Hōbunkan,1933.p.81. (36)林茂生:《新台湾话的陈列馆》,《台湾教会公报》第593卷,第4页。“台湾白话字文献馆”,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pojbh/artical-4973.htm,访问于2014年4月26日。 (37)其后附的条款规定Her Britannic Majesty consents to renounce all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at present exercisable by British courts in Japan for the judicial hearing and determination of matters in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subjects and subjects of Her Majesty the Emperof of Japan.可见,此处也以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代之。See Treaty of Commerce and NaVigation,Japan-U.K.,July 16,1894,来源于http://www.austlii.edu.au/au/other/dfat/treaties/1901/66.html,访问于2014年4月20日。 (38)参见http://kindai.ndl.go.jp/search/searchResult? searchWord=%E6%B2%BB%E5%A4%96%E6%B3%95%E6%9D%83,以及http://kindai.ndl.go.jp/search/searchResult? searchWord=%E9%A2%86%E4%BA%8B%E8%A3%81%E5%88%A4%E6%9D%83,访问于2014年4月18日。 (39)参见[日]桥本胖三郎《治罪法讲义录》,博闻社1886年版,第153-159页。 (40)参见[日]平冈定太郎《国际公法》,攻法会1898年版,第72-73页。 (41)参见[日]中村进午《平时国际公法》,中央大学1906年版,第124-138页。 (42)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99-600、801页。 (43)参见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四卷·司法场域),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44)屈文生:《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 (45)(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七,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第21-23页。 (46)《论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性质之区别》,《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13期,第234页。 (47)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上海明权社1903年版,第29页。 (48)(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第3页。 (49)参见沈国威《黄遵宪的日语;梁启超的日语》,[日本]《或问》2006年第11号,第137页。 (50)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51)[日]伊原泽周:《〈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2)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53)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四》,载《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0-82页。 (54)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第二版),上海明权社1905年版,“再版广告”。 (55)沈国威编著:《新尔雅: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56)[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89页。 (57)See Yen-P'ing Hao and Erh-Min Wang,"Changing Chinese views of Western relations,1840-95",in John K.Fairbank & Kwang-Ching Liu,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1,Late Ch'ing,1800-1911,part 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195. (58)胡以鲁:《论译名》,载氏编《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34-135页。 (59)(清)沉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24页。 (60)张国华、李贵连编:《沈家本年谱初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61)参见《申报》1908年7月5日,第2版;1919年4月17日,第3版;1919年11月23日,第6版;曾友豪:《法权委员会与收回治外法权问题》,《东方杂志》第23卷第7号。 (62)张仁善:《半个世纪的“立法秀”——近世中国司法主权收复与法律创制》,《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63)高汉成:《晚清法律改革动因再探——以张之洞与领事裁判权问题的关系为视角》,《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 (64)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9页;"Great Britain agrees to such reform,and she will also be prepared to relinquish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when satisfied that the state of the Chinese laws,the arrangements for their administration,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warrant it in so doing",See John Van Antwerp Mac 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p.351. (65)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第15款、中日《通商行船续约》第11款,只将“中英商约”中的英国改为美国、日本国。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8、194页;John Van Antwerp Mac 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p.414,431. (6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18页;John Van Antwerp Mac 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1894-1919),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p.745. (67)《北京促成会成立大会之盛况》,《民国日报》1925年1月11日,第2版。 (68)庸公:《山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民国日报》1925年1月11日,第2版。 (69)超麟:《帝国主义又一骗局——法权会议》,载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43页。 (70)张耀曾:《法权讨论会张会长演说录要(续)》,《法律评论》1924年总第71期,第21-24页。 (71)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8页。 (72)《领事裁判权的撤废问题》,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宣传部1930年印行,第6-7页。 (73)《附录:法权会议报告书》,《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期,第119-166页。 (74)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5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页。 (75)《法权委员团在鄂参观各厅监所程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03-34/7-(1),转引自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76)See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Mar.27,194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2.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p.271-273. (77)《新华日报》1941年6月2日,第1版;当日《解放日报》也称《美对华发出空头支票,愿将来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美公布郭泰祺赫尔交换函件》,《解放日报》1941年6月2日,第2版。 (78)《新华日报》1941年6月4日,第2版。 (79)《东方第一夫人致美国》,载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2页。 (80)《新华日报》1942年8月19日,第3版。 (81)《新华日报》1942年8月31日,第2版。 (82)《解放日报》1942年8月20日,第1版。 (83)《汤姆斯提出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美各报赞助》,《解放日报》1942年9月1日,第1版。 (84)《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1日,第2版。 (8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713页。 (86)《文化杂志》1942年12月10日,第3卷第2号。 (87)何襄明:《废止约定治外法权应循的途径》,《新中华》1943年第2期。 (88)参见《日发言人谈英美撤销治外法权》,《申报》1943年1月30日,第2版;《丹麦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申报》1943年3月29日,第7版;《瑞士准备放弃治外法权》,《申报》1943年4月4日,第5版;等等。 (89)Se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r relinquishment of extraterritorial rights in China and the regulation of related matters,signed January 11,1943",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690. (90)Report of the Senate Commission on Foreign Relations,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Mar.20,1943,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pp.245-248. (91)除领事法庭外,英国曾于1865年设立“英国按察使署”,美国曾于1906年设立“美国驻华法院”。参见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