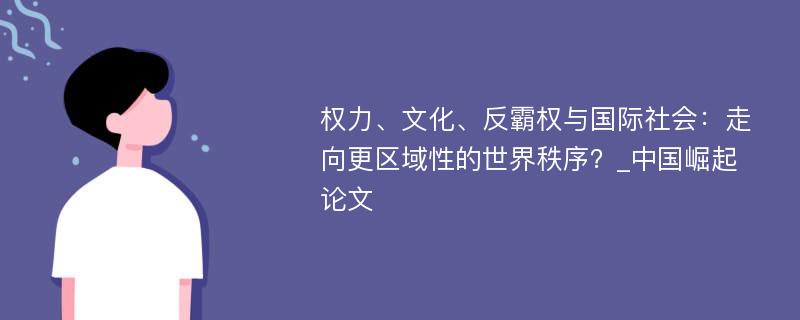
权力、文化、反霸权与国际社会:走向更为地区化的世界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国际社会论文,秩序论文,权力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11-0016-18
一、导言
冷战期间的权力分布按历史标准来看,它不但是极其不均衡的,而且是高度集中的。大约二十年前,苏联解体使一个超级大国从体系中消失,从而把两极体系变成了20世纪90年代那种更不均衡、越发集中的单极结构。尽管美国还是全球最强国,但人们认为它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会持续太久;同时,中国和欧盟也难以跃升到超级大国的行列。① 美国的全球地位不仅依赖物质要素,同样也依赖社会要素,而两者都由于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发展趋势而丧失,这包括小布什政府对自由价值观和多边主义的攻击,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以及世人对作为美国领导权理论基石的“华盛顿共识”的质疑等。美国在领导某些事务(如环保事务)上出现过失误,试图在另一些事务(如中东、世界经济、一定程度上的中国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时又不受欢迎,加之霸权在全球政治中普遍不被认可,这一切都持续弱化了美国的社会地位。俄罗斯降低到“一般大国”级别,或许勉强称得上“地区强国”,但要恢复到从前的地位几乎没有可能。此外,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正在改变国际体系中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格局。由此看来,一幅国际体系权力分布正恢复到西方崛起前均衡状态的图画便出现在我们眼前。
的确,那种认为有别于“一般大国”和“地区强国”的“超级大国”的概念范畴② 正在淡出历史舞台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超级大国”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专业的论著中非常常见,但它是在二战后才开始出现的,从近代史上追溯也绝不早于19世纪。“超级大国”属于历史现象。认为任何国家都应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权力支配地位的看法是19世纪西方特有的、权力非均衡分布的产物,而正是这种非均衡分布状态使此类失衡在短期内成为可能。此后,这种状态又借助二战的结局得以强化,导致了欧、日诸帝国的分崩离析,使世界陷于一片废墟之中,并将一对在意识形态上格格不入的对手提升为全球性大国。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传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集中的趋势迅速放缓。再加上物质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双双弱化,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没有超级大国,只有一般大国和地区强国”的世界政治局面。
这些发展趋势对国际社会的未来来说具有何种意义?笔者认为,和目前流行的单纯关注美国能否保住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或其他新兴超级大国是否会挑战美国的思路相比,地区化视角更能使人们理解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当前的这场变革。在高度紧张但却相互依赖的体系内部出现真正全球化意义上的权力分布这一前景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欧洲崛起前,我们曾有过全球性的权力分布,但当时所处的场景是一个相当薄弱且相互依赖程度非常低的国际体系。欧洲崛起后,我们也曾有过一个紧张却相互依赖的体系,但几乎所有权力却集中在西方国家和俄国手中。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局面是全新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必须习惯“自己再也不能无可厚非地稳坐头把交椅”的观点。而崛起中的大国也必须习惯“权力大责任就大”的事实。现实主义者或许会视这种局面为充满危险的权力过渡时期。英国学派也许会担心西方的衰落和非西方的崛起会削弱国际社会赖以生存的规范基础。笔者将通过本文来证明这两种担心都是多余的。与更分散的权力分布相对应的是更具地区化特征的国际社会结构,其在稳定性和功能性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景。③
要了解地区化国际社会的前景,就需要考察国际社会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下一节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随后的各节将详细考察地区化国际社会的存在逻辑、可行性及可取性的原因所在。
二、对“国际社会”的统合论解读
要了解国际社会的未来,我们有必要了解它的过去以及历史在这一进程中曾给我们提供的社会资源。笔者以前曾在不同的场合详细讨论过与国际社会扩张有关的两种理想类型解释,即“先进论”和“统合论”。④“先进论”属于较为正统的解释。按“先进论”的解释,全球国际社会的发展几乎都是西方扩张的结果。16世纪以降,欧洲列强的崛起先是迅速摧毁了美洲两大文明区域,接着通过侵略彻底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到19世纪末,整个国际体系不是按欧洲的形象重新塑造(如美洲和大洋洲),就是直接屈服于欧洲(如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再就是为避免殖民地化而极力追赶欧洲(如古典世界里的几个最具弹性的地区,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本和中国)。欧洲列强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互动水平出现了急剧持久的提高,而且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即所谓的“文明的标准”)开始以帝国形式统治整个体系。这种解释立足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可以与之媲美的是其他扩张性帝国文化,如中国化、罗马化、俄国化、伊斯兰化等,西方化进程与这些进程都很相像。它强调的是欧洲在扩张中的中心地位,表达所采用的是文化从西方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单向传播视角。该解释总体担心的是欧洲国际社会向全球扩张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的永久性弱化。因为扩张过程就是国家构成的社会与多文化世界社会的碰撞过程,而多文化世界社会无法提供支撑共同价值所必需的文化同质性,因而也就弱化了国际社会。它特别担心的是,在尚未将世界其他地区按自由价值观加以改造、使之不再威胁资本主义、人权和民主之前,西方的权力就已经衰落。因此,权力向非西方文化的扩散不仅会危及国际社会的稳定,而且会危及西方的安全。正如几个英国学派作家所指出的,尽管当代国际社会的合法性是基于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去殖民地化准则以及一定意义上的国民和民族平等原则之上的,但它还是充斥着在其先进式创建进程伊始时所遗留下来的霸权、等级尊卑等恶俗和地位不平等。⑤ 因此,“先进论”要摆脱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仍是任重而道远,其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必然会有不安全感。
相比之下,“统合论”解释则更加强调扩张进程中文明间的互动,因此,它在总体上采用了更具动感和交互感的视角来看待文化传播。尽管它承认西方从19世纪以来的确处于事实上的全球支配地位,但它在解释国际社会成因时却不怎么坚持西方中心论。“统合论”解释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文化观念在不同文明区域间的流动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因此,文化的进化不仅是对本身内部动力的反应,同时也是和其他文化(哪怕是遥远的文化)相遇的结果。很明显,“统合论”要成立就必然要求存在某种接触,而观念传播所需要的互动能力又很低,这就使得此类传播成为常态性预期。⑥ 例如,13世纪以来,去过中国的少数欧洲人带回了中国科技和政治方面的重要信息,古代与古典世界里相当薄弱的贸易系统便充当了当时各地间文化传播的纽带。⑦ 佛教从印度传到了东亚,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世界传到了非洲和亚洲。在联系更紧密、互动能力更高的地方如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或印度洋贸易系统内部,都存在许多思想观念上的互动。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曾猜测中世纪欧洲十字军东征是从伊斯兰圣战那里得到灵感的,⑧ 这一观点可以说颇具挑衅意味。
“统合论”解释对“先进论”解释所提出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巨大差异以及“西方例外论”和“优越论”提出了质疑。按“统合论”的解释,欧洲国际社会并非简单地从独特而自足的欧洲文明中孕育出来,相反,欧洲在其发展阶段中曾和欧亚大陆及北非的其他文明发生过重大互动。正如怀特所说,在12-13世纪时,十字军东征使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早先因伊斯兰占领西班牙而形成的联系更加紧密,两者都发挥了“中世纪基督教同化渠道”的功能。⑨ 几乎与此同时,蒙古对亚欧大陆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发生接触,并增加了观念的传播。13世纪后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以及1453年其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意味着崛起的欧洲要与一个敌对而强大的非欧洲文化为邻并定期接触。努里·约杜塞夫(Nuri Yurdusev)向我们展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如何与近代早期的欧洲发生互动以及如何在后来的“欧洲国际社会的威斯特伐利亚制度”(如权力均衡、外交、国际法、大国治理等⑩)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随着欧洲逐步迈入近代,它既不孤立也不强大。相比之下,它在欧亚大国系统里处于贫穷、软弱和落后的边缘地位,从其他先进文化那里吸收了许多思想观念,正是这些思想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欧洲人借着地利优势最先到达美洲,并抓住当地居民对疾病缺乏免疫力的良机,轻而易举地摧毁并替换了当地原居民及其相对落后的文明。(11) 接管美洲的政策使欧洲第一次把东西半球的贸易系统联结起来,并借此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占据了中心地位。(12) 然而,尽管其在创建全球体系方面获得了上述初期优势,但欧洲人却是以较弱和较原始的身份进入亚洲的。事实上,正如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所说,他们并非进入了真空地带,而是不得不与一系列已经非常发达的国际社会打交道,与早在他们到达之前就已经非常发达的庞大的亚洲贸易体系打交道。(13) 迈克尔·皮尔逊(Michael Pearson)告诉我们,欧洲人在进入印度洋体系后的250年间,对印度洋体系的基本进程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力。(14) 亚历山德罗维奇(C.H.Alexandrowicz)对当时的条约进行过仔细研究,劳伦·本顿(Lauren Benton)也对当时法律制度及双方相遇的情形进行过详细考察,两者都显示双方当时相遇时多半是有来有往的。(15) 例如,雨果·格老修斯(Hugo Grotius)在17世纪曾提出欧洲人应当接纳“公海属于国际领土”的准则,而印度洋正是这方面的第一个例证。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在这一阶段,“两个世界的相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随后的商业和政治交易也并非处于法律真空,而是依照各国法律并加以调整,使之符合当地的国际习俗……这并不比欧洲法律逊色”。(16)
从“统合论”的角度看,甚至“现代性”也绝非欧洲或西方的专属发明,而是一种全球性现象。(17) 欧洲征服美洲后幸运地处于这一进程的中心地位,并能灵活地抓住大部分机会。但欧洲并非现代化所需的所有科技和思想观念的唯一原创者。正如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所说,欧洲从中国、伊斯兰世界和印度那里吸收了许多后来成就其崛起的科学技术和商业创新,霍布森把这一进程叫做“东向全球化”。(18) 以这种方式展开叙述不但有助于弱化“欧洲例外论”的论调,而且可以拉近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距离。另外,它还可以把西方统治(美洲以外的地区)的时间从五百年压缩到二百年左右。欧洲直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在技术、财富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决定性地超越其他欧亚文明中心。“先进论”的解释只是暗示欧洲的扩张并非进入某种社会真空,而是慢慢将自己的国际社会风格强加到由各具当地文化特色的原有地区性国际社会组成的系统。(19)
尽管“统合论”和“先进论”对欧洲崛起及其先期进入亚洲的举动提出了差异较大的解释,但双方在对19世纪的看法上差异要小一些。19世纪的欧洲和西方在经历了内部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后变得非常强大,很具影响力。“统合论”并未失效,而只是在对从中心到边缘的单向流动问题的看法上和“先进论”更加一致罢了。西方已强大到足以将自身“文明标准”提升到“普世标准”的程度,并强迫非西方遵守西方的规矩和习惯。这一态势给非西方带来两个问题:西方权力增大不仅使西方的单向文化帝国主义越发难以抗拒,而且由于西方也在经历深刻的政治变革,其鼓吹的文化在本质上也是急剧变化的。19世纪是近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成型的一个关键时期,但基本上被“先进论”解释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忽略掉了。(20)
要更深刻地透视西方的这些变化,就需要转向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卡尔·普兰尼(Karl Polanyi)这类学者。(21) 他们把这场从18世纪晚期持续到19世纪且被普兰尼称之为从农业到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作为分析的重点。从这个角度看,产业主义和金融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从西方核心内部创造了一种新型国家,而且创造了一种新型社会秩序(资本主义)。这种新型的现代社会将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导入了公民社会,并打开了似乎是永无穷尽的技术革命之门。(22) 它创造了一种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形态,并前所未有地拉大了现代与非现代、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23)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等人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秩序状态,一种是“自然国”或者叫“限制参与制度(limited access orders)”(指较为传统的形式,政治与经济不分,只有少数精英阶层才能参与政经活动),另一种是“开放参与制度(open access orders)”(指历经困难但已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公民有更多机会参与公司和政党的政经活动)。诺思等人和盖尔纳同样都认为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困难和危险的,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奇迹,因为通往“开放参与制度”之路往往会颠覆自然国,带来的不是转型而是暴力和混乱。(24) 西方在19世纪向外投射的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尽管“公民社会帝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非国家行为体掌握市场扩张的动向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结构,但它还是唤起了英国学派的某些担心,特别是由成千上万个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全球公民社会(或者叫“世界社会”)如何能在国际社会各处稳健运营的同时,仍基本立足于西方并秉持西方的价值观?(25) 这一看法和现代社会学的看法颇为一致,其关注的是现代化的兴起以及功能日益分化的社会形态的发展。(26) 它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过去五百年间,事实上存在两个同等重要且都具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个是系统规模的变革,发生时间约为公元1500年;另一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发生在19世纪。
按照这一看法,19世纪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居于领导地位的西方诸国彻底重塑了其内部社会结构,并在这一进程中重塑了西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开放参与制度区迅速变得比世界其他地区富裕和强大得多,并以此造就了大家熟悉的权力差距。另一个或许更为重大的差距则体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类型之间,即体现在开放参与制度和自然国制度之间。在18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里,开放参与制度逐步从专制主义的自然国形态进化到民族主义形态,然后经由人民主权阶段最终进化到成熟的民主开放参与制度。(27) 这一颇受争议的进程进行得很不顺利,一共经历了四场世界性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它们大都爆发在核心内部的开放参与制度国与其他自然国之间。这些战争持续扩大了开放参与式制度区的范围,并使自由现代化最终战胜了各类独裁和集权统治形式(28)。按贾斯廷·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的说法,冷战就是共产主义国家(即诺思所定义的“自然国”)通过接管私人领域和关闭边境等手段来实现从公民社会帝国中的隐退。(29)
随着开放参与制度在一些主要国家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主要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从直接控制领土等颇具自然国特色的帝国主义状态转变到具有“公民社会帝国”风范的参与状态。开放参与制度区透过国家领土边界,形成了一个跨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私人性质的非国家行为体可以与正统的国家行为体并行运作,也可以在国家间政治领域内或者经由国家间政治来运作。(30) 由于主要的殖民大国都是发达的开放参与制度国,所以随着它们国内结构不断进化,它们逐渐与老式的帝国主义格格不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英法两国日益衰落,进一步推动了它们与老式帝国主义的分裂过程。同时,这两场战争还摧毁了欧洲自命不凡的“文明”,因为欧洲人把此前只用于对付非欧洲人的种族主义、殖民行径和暴力野蛮都统统运用到其他欧洲人身上了。(31) 因此,主要大国始于19世纪的“开放参与制度”变革开始朝着“去殖民化”的方向发展,1945年后正式掀起了“去殖民地化运动”。去殖民地化运动暴露并加剧了以西方为核心的开放参与制度区与第三世界特别是自然国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许多自然国觉得和苏东集团站在一起更舒服些。到20世纪下半叶,开放参与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1989年冷战的结束都标志着在经济领域内的自由主义战胜了作为挑战者的自然国家。然而,尽管核心区域越来越按跨国的开放参与制度来进行组织(即“和平地带”),但多数边缘地区都保持着自然国状态,因此两者之间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冒着过于简约的风险,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一进程看成一种转化,即从单纯在西方核心内部发生的、崛起中的开放参与制度国与自然国之间的斗争,转化成为既包括西方核心区域内开放参与制度国与边缘自然国的斗争,也包括边缘国之间的相互斗争。
这一世界性历史转变对于国际社会扩张的统合论解释来说具有何种意义?它最起码解释了“文明标准”问题为何大都发生在19世纪(尽管有过这方面的先例,如欧洲文明遭遇美洲石器时代文明的时候)。当时,两者不仅在权力和财富方面的差距在增大,而且开放参与制度国和自然国之间的差距也在增大。自然国为实现内部稳定必须保持封闭,而开放参与制度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必然要求一定程度的渗透和自由化,两者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便会动摇并且也的确动摇了自然国的地位。其结果便是亚历山德罗维奇(C.H.Alexandrowicz)等人所观察到的发展趋势,即到18世纪晚期,欧洲和非欧洲地区之间原本基于自然法的平等关系逐渐崩溃,最终演变成一种更不平等的“文明标准”状态。到19世纪,作为变革的一部分,欧洲人开始摆脱自然法,转而采取实在法,在这一进程中构建起一个基于主权和相互认同的纯粹西方法律体系。这使过去一直被当成全面主权国的非欧洲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转眼间变成了通过申请才能加入欧洲国际社会的可能候选国。欧洲与非欧洲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被重新定义,欧洲人现在自视为“文明”的上等人,而把其他人视为“野蛮人”或“野人”。(32)
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规模差异,其组成也很关键。随着西方核心从自然国转型为开放参与制度国,其投射到国际社会的制度类型也开始发生变化。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记录了民族主义和市场崛起的这一进程。(33) 要实现“去殖民化”,第三世界必须接受西方的政治形式作为其独立和进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正如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所说,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国际社会或者是开放性的(因为尽管其源于欧洲,但其他各方在达到特定条件和标准后也可加入),或者是帝国式的(主要指它表面上提倡多元化但本质上要求广泛的西化)。(34) 毫不奇怪的是,针对西方推销的某些制度,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第三世界的不同国家会做出显著不同的反应。尽管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这些反应很简便,但我们还是选择用开放参与制度和自然国之间的差异来进行解释,因为这样解释要好一些。统合的进程大体是在西方权力巅峰时以单向的方式进行的,但其效果却是良莠不齐。那些和自然国适配的制度(主要是威斯特伐利亚制度,包括主权制度、不干涉制度、领土制度、外交制度、国际法的某些制度等,但也包括19世纪的主要制度如民族主义制度等)很容易被多数非西方国家积极采纳。自然国采用这些制度时感到很舒服,因为这些制度主要是自然国所推出的,同时也是为自然国服务的,不会威胁到其国内事务。这就解释了为何这些制度不仅被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所接受,同时也被其国民所接受。例如,民族主义和主权制度尽管源于欧洲且具强制性特征,但在世界多数地区都已生根发芽。
与上述制度相比,开放参与制度国的自由主义制度则显得更具有渗透性和跨国性,特别是20世纪才兴起的民主与人权制度。这些制度反映了成熟开放参与制度国所秉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对自然国的内部结构和文化传统必将构成威胁。这就给了自然国的权力精英们以适当借口,使他们可以把文化差异当做一种政治资源,并用它来抵制西方的压力。对更具自由主义特征的制度(如市场制度、民主制度、人权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国际法的某些方面)和更具威斯特伐利亚特征的制度(如主权制度、领土制度、不干涉制度和外交制度)两者之间的矛盾,西方的开放参与制度国往往借助民族主义来弥合两者间的差异并显得游刃有余。但是从自然国到开放参与制度国的转型之路充满了困难和风险,因此自然国的精英阶层对混合制度进行抵制,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姑且不论文化问题如何,开放参与性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介入既有可能导致向开放参与制度的成功转型,也同样有可能造成混乱和国家的崩溃。正如詹姆斯·梅奥尔所说,无论存在何种规范性的论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仍不具备支持人权和民主的条件。(35)
这里最有意思的或许是自然国与市场(进一步说就是进步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市场和进步毫无疑问是开放参与制度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市场,它对于19-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发生在自然国和西方开放参与制度国之间的长期斗争来说至关重要。非民主的自然国试图在抗拒市场的同时选择进步的理念。然而,到了1990年,有一点变得很清楚,那就是在拒绝市场的情况下,无论是发展还是权力都无法持久。正因为如此,开放参与制度在后来虽然算不上是被普遍接受,却也被广泛认可。开放参与制度国接受市场通常是出于观念上的原因。而其他各方接受市场原则是出于算计和工具性目的。在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政治与经济分立的局面已越来越面临国家管制的威胁。中国的伟大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自然国接受市场的实验,但其中充满了悬念:市场最终是会颠覆自然国,还是会走向与其文化相符的某种形态的开放参与制度?
总而言之,统合论的观点认为文化和国际社会这两者都具有可塑性。它们有变革能力,也的确会变革,因为跨文化互动作为国际社会的常态是呈多方向流动的。统合论认为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文化差异要少于先进论所说的差异,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欧洲国际社会的出现并非一个原生进程,而是和欧亚大陆、北美地区的其他文明长期文化互动的结果。欧洲接受了许多外来事物,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其次,19世纪以来,西方价值观和制度迅速向外传播,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导致西方国际社会的许多老式自然国制度被非西方国家广泛而深入地采纳。
这一历史记录要好过先进论所呈现出的那种渺茫希望。根据先进论,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精英有可能成为对抗分裂性多元文化的堡垒,其观点更倾向于认同亚当·沃特森(Adam Watson)提出的较为乐观的新文化统合论。(36) 主要差异或许只是在政治上的而非文化上的,是开放参与制度和自然国之间的差异。日本和韩国的先例就已经证明,且中国和印度的现例也即将证明:非西方文化即使接受了某些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在开放参与制度环境中,它们依然可以保持自己的文明特色。的确,其他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如此深远,西方对其他文化的影响也同样如此深远,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接受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的看法:“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复存在。(37) 统合论认为,随着交往密度的加大,文化政治互动和共同进化也会加速。虽然人们并不认可这一趋势应当或者必然导致文化同质或政治同质现象,但在某些方面的确会出现相像的情形。统合论强调了国际社会进化与其政治和文化基础进化这两者之间的同步性。因此,在统合论看来,国际社会出现文化/文明危机的可能性就要小一些。先进论和统合论在理解当代国际社会的本质及成因方面的确存在重大分歧。一方面,由于涉及历史准据问题,故这一重大分歧本身就很重要;另一方面,即使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歧也同等重要,因为先进论解释其所隐含的帝国主义态度使非西方国家蒙羞,所以遭到抵制;相比之下,统合论解释则在亲和力以及随和性方面更具潜力。
所有这些都表明:长期融合进程与短期西方霸权相结合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全球性社会遗产。西方让世界其他地区完全接受其社会政治模式的做法在过去未获得过成功,在其权力式微的今日同样也不会成功。相反,各文化间的认同加深,权力也被扩散到整个体系,因此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文明冲突”几乎不可能出现。文化同质和政治同质一样,既不太可能,也让人难以接受,但这绝不表示不会出现一丝雷同。当然,某些代表开放参与制度、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国际社会制度(如民主、人权等)已在精英阶层备受争议,另一些制度(如市场制度)则被精英阶层广泛接受。在冷战结束前,市场制度与其竞争对手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之优劣一直是超级大国间的核心争论议题。但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国脱离计划经济,市场成了全球性制度。这主要是指多数国家都遵循市场规则,且有强大的政府组织对其提供支持。虽然许多国家和民族因信仰而支持市场制度,但仍有许多国家是出于算计的考量而接受并遵循市场制度的,有些甚至是被迫接受市场制度的。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两国以不可逆转的方式开放市场这一事实对共有文化圈的延伸来说仍具重大意义,或许可视此为开放参与制度从目前较为团结一致的核心向边缘主要行为体延伸的关键一步。
除此之外,另有几个制度在许多国家也得到了重大认同。如主权、不干涉、外交、国际法、大国治理、民族主义、自决(并非所有版本)、人民主权、民族平等与进步等制度在国家精英层面都被深刻内化,处于无可厚非的准则地位。某些特例或应用案例也许会引发争议(如对大国治理的痛恨,或出于文化民族主义原因对某些自决要求的抵制等)。但总体而言,多元共存的国家社会得到了诸国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各族群和跨国行为体的广泛支持。多数解放运动的目标都是主权。多数族群也都认可民族主义、领土制度、主权制度及进步观念。多数跨国行为体需要并渴望得到稳定的法律环境。即使西方的权力开始衰败,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多数多元制度仍会续存,对环境监护的有限但不断加大的承诺也同样会续存。某些得到广泛和热烈支持的、主要的国际社会制度构成了共有政治与文化的重要形式。国际社会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所经历的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困难,也并非先进论者或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者所担心的那种文化上的困难。相反,主要困难来自诺思等人所提出的一个更加政治化的课题,即如何构建一个同时包括开放参与制度国和自然国的国际社会?这一思路有效地解释了哪些国际社会制度已在全世界生根发芽,哪些还没有。稳定的国际社会绝不能基于一些既造就失败国家又促使开放参与制度成功转型、对各国的生存和完整构成威胁的制度。
在掌握这一背景后,理解本文导言部分所提出问题(如权力分散为何导致更地区化的国际社会和这一发展趋势为何受到欢迎等)就要简单许多。
三、更为地区化的国际社会?
一个没有超级大国只有大国的世界为何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地区化国际秩序?这一发展趋势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任何支持地区化的论点都要首先确立该地区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同时,它必须说明地区化为何会在全球化持续产生强大“去领土化效果”的今日仍占据上风。
本文在导言部分曾提到权力的不均衡分布状况有所改善,而地区化秩序的物质基础在这一变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短期看,美国自二战以来所取得的非常态统治地位一直受到欧日复兴和新经济大国崛起的双重削弱。从长期看,现代化通过国际体系得到了越来越广泛传播,西方在19世纪压倒世界其他地区的那种巨大优势在持续衰减。权力基础的不断分散不仅造就了新的大国,而且使任何国家都越来越难以获得超级大国地位所需的相对实力。权力分散不仅影响相对实力,也影响绝对实力。越南、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等例子表明:即使是超级大国也不再能轻而易举地占领负隅顽抗的小国;朝鲜、巴基斯坦或不久之后的伊朗案例则表明:哪怕是非常弱小的国家也可获得最小程度的核威慑。世界正在回归到西方集权之前的那种更自然、更均衡的权力分布状态。
地区化秩序的社会基础是强势反霸权主义,这是后殖民地时代国际社会新出现的特征。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曾经表示,他对权力过分集中确实很担心,担心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对权力的反抗。现在美国一些现实主义学者也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美国自视为仁慈的领导国,但在他国眼里却被普遍当成威胁,其外交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和中东政策)深受国内政治的左右。上面这两种看法简直大相径庭。(38) 相比之下,几位英国学派作家在对待霸权问题上则采取了更具社会性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当代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基于主权平等原则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民族和国家平等原则,但它仍充斥着西方统治世界的帝国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霸权与等级恶俗以及地位不平等现象。随着世界向单极方向转变,美国成了西方继续统治国际社会这一霸权主义行径的主要代表和典型。并没有什么“建立在合理普遍共识基础之上的霸权原则”(39) 可以缩小国际社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差距。伊恩·克拉克(Ian Clark)赞同华尔兹的看法,认为权力集中于某个行为体会破坏权力均衡的理念,而后者正是国际社会合法性的传统源泉和存在条件。(40) 中国和印度等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将增强对美欧霸权余势的抵制,甚至在中东等并无新兴大国出现的地区,反霸舆论的力量也越发彰显。
这主要表现为对建立更多极的国际体系的普遍要求。只有欧盟的某些地区(最典型的是英国和东欧)和日本对维持美国霸权真正有热情。此外,在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很有可能部分退出全球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进程。“华盛顿共识”已经死亡,它展现给世人的是其在管理急剧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方面的政治无能。这与其说是美国权力的严重亏欠(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成分),倒不如说是全球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霸权稳定论经证明是有缺陷的,同时却没有哪种充分的共识可以充当全球集体治理的必要基础。经济危机使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这段期间内曾一度明显的趋势越发清晰:苏联的解体并未带来一个符合西方霸权标准的世界。虽然几乎所有各方都承认某种形态的资本主义是唯一的出路,但对这一课题的认识存在多种版本,即便就民主或西式人权也未达成任何共识。此外,尽管各国在民族平等议题上存在着强烈共识,但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关系以及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姑且不论是不同宗教所带来的额外差异)等议题上难以达成任何共识。由此,从许多方面来看,对于现在国际体系适合的秩序是,以具备政治和文化舒适度的区域为基础而推进地区化。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文献中一直存在着对良性地区化国际秩序本质的猜测,其假设前提大体都认为世界是围绕美国、欧盟和东亚三个核心地区进行组织的。(41) 最重要的是地区化的做法已经成熟。地区化可被视为全球化的某种应对手段,它既可充当全球化失败时的退路,又是在全球化世界里获取更多影响力的战略。欧盟和北美自贸区只是该进程的一些最典型的例子。围绕经济和政治合作而成立的其他集团组织还包括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独联体、南亚区域合作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西非经济共同体等。当然,并非所有组织都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和影响力,但这的确显示了地区化势头有多强。在当前经济危机和美国领导权衰落的情形下,这一势头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综合上述,现有思路并不能提供一个清晰的模板来描述地区化世界秩序的具体眉目。上面的例子表明,地区化的世界可能会相当支离破碎,地区的数目也可能超过十个。但也有可能会像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和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所说的那样出现三大集团。但即使是“三大集团”的前景也并不十分明朗。南美是沿北美自贸区的路线和美国结合呢,还是以巴西为核心组建自己的地区集团?西方是分裂成美、欧两个核心区呢,还是以跨大西洋合作为基础构建一个更大的核心?亚洲是将自己定义为狭义的东亚地区呢,还是会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亚?日本是将自己定义为亚洲国家呢,还是自视为西方的一员?按宗恩(Yul Sohn)的说法,日本为使该地区更适合自己的口味,对亚洲采取了较为广泛的定义,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民主国家也纳入其中。(42) 由此看来,即使是“三大集团”的前景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要把日本、俄国和印度摆在哪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中东地区既无核心大国,也无共有制度将其团结成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地区,这该怎么办?这都是些有趣但重要的问题。即便如此,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也无法阻止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里,走向更为地区化国际秩序的总体趋势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能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在任何情形下都属于比较棘手的地区。相对于推动地区化国际秩序的动力机制而言,哪个大国最终和哪个地区联合或者它们是否会自行成立自己的地区性集团等这些问题并不重要。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地区化国际秩序会运行良好。对这种秩序的担心主要源于20世纪的经验:在20世纪里,各帝国主义列强曾为争夺势力范围或征服世界而激烈角逐。下列几个原因会使争夺全球霸权的危险不再那么突出。首先,西方处于相对衰落阶段,其他地区从前景上看也都基本处于守势。大家都在努力维护自身政治和文化特征,同时顶着西方压力寻找各自的现代化之路,没有哪家明显想争夺全球领导人的地位。其次,任何潜在全球霸主都要受到广泛而强烈的反霸主义的抵制,同时在获取必要物质优势方面也困难重重。再次,在意识形态上或种族主义方面的巨大差异尚不足以引发20世纪的那种冲突。最后,所有大国都恐惧战争和经济崩溃,感到对维护世界贸易负有责任,因为没有人想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独裁的帝国年代。
此外,统合论观点还认为,即使在更加地区化的国际秩序中也存在着足够的共有价值,可以确保在合理程度上保持全球共存与合作。当然,朝这个方向发展究竟是祸是福,各国对此存在不同看法。西方等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会因普世主义的弱化而扼腕长叹,他们担心会冒出各种形态的狭隘主义,有些可能会相当丑恶。无论地区化的国际秩序有多少优点,但它毕竟标志着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议程在普世性上的倒退。虽然尚不明确,但丧失霸权领导地位或许表示体系的总体管理能力确实出现了弱化。当眼下依赖美国领导权的故习被打破时,在这方面便会呈现出变革的可能性,对此人们绝不应当小觑。在经济层面,地区仍将担当规模经济中继站的角色,届时,全球贸易和各方在大科学及环境管理等功能性事务上的合作都将保持活跃状态。即使在冷战最紧张的阶段,美苏之间能仍就核试验、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等涉及共同生存的话题展开讨论,这一点恐怕并非一点指导意义没有。
终结一个越来越不成功、越来越不受欢迎和越来越昂贵的霸权令许多西方人感到欣慰,同样,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会由于摆脱西方的控制而高兴万分。许多人认为在蔓延的全球经济、薄弱的国际社会和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以来因身份不同而互不团结的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且这些矛盾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对这些人来说,从全球化的过度野心中稍退一步或许是颇受欢迎的选项。或许,过早尝试全球治理所产生的管理性问题远远超出了当前人类社会与政治能力的承受范围。相比之下,各地区自行管理、不那么野心勃勃的世界秩序或许更能保持稳定,其牵扯的摩擦和失败也会较少一些。人们也许会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在重新尝试全球化之前,搞一段时期的地区性资本主义政经组织实验是可取的。
关键问题是,以这种方式地区化的世界能否达到必要的全球治理水准?能否解决气候变化、犯罪、贸易、恐怖主义、移民和军控等一系列共同问题?如上所述,信心取决于一系列重要制度在国际社会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中的认可程度。这些共有制度构成了维护各地区性国际社会之间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全球领导权弱化和霸权消失所导致的管理能力欠缺在某种程度上将通过管理事项的减少而得到平衡。在一个没有核心霸权的世界里,西方对其他地区的干涉会少一些,其结果是由此类干涉所导致的全球性问题(如基地组织问题等)也会相应少一些。如果各地区无论好坏都能自行管理自身事务,那么由霸权干预所导致的紧张状态就会缓和一些。对“何种程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才是可取的”这一问题或许存在着更温和的看法。当前条件下的地区化世界和20世纪30年代或冷战时期的地区化世界有所不同。按亚历山大·温特(Axexander Wendt)的说法,它将是一个由朋友和对手组成的世界,而非一个由对手和敌人组成的世界。
没有超级大国的国际体系,其主要危险是一个或多个大国将重新争夺超级大国的位置,但这种情形在当前条件下似乎不太可能。另一个危险是将发生更多争夺边界和势力范围的对抗。由于权力分散,这似乎也不太可能引发重大冲突,因为那样做风险太高,且帝国主义的帽子又确实令人厌恶。也许,地区化国际秩序的主要风险是那些过去独立运转的小国和小民族将沦为当地强大宗主国的附庸国,从而无法向外界寻求救灾援助之外的帮助和支持。许多人主张正面看待地区化国际秩序,而这一论调最明显的逻辑缺陷在于:普遍针对超级大国的反霸权主义也将同样适用于地区性大国。许多人担心本地区的霸权主义行径将比西方霸权更丑恶。例如,俄国毫不迟疑地动用武力和强制措施来对付其弱小邻国;印度的弱小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大力抵制印度的霸权;历史记忆仍然不容许中日两国同时担任东亚领袖,到目前为止还一直在阻挠它们走向某种形式的联合执政;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不受拉美邻国的欢迎;南非在本地区的主导权一直遭到邻国的憎恨,等等。甚至在并不存在明显主导性大国的中东地区,只要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或伊拉克采取谋求领导权的举动,便立刻遭到周边国家的抵制。
毫无疑问,地区化的世界在这方面将展现一幅相当多变的图画。在某些地区(最明显的是欧盟和北美地区)已经有强大的政府间组织和制度可以缓解人们对霸权的担心。其他地区(如南美和东南亚地区)则有良好的制度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然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如西非和南部非洲、南亚以及中东),当地的制度可能过于脆弱,根本无法缓解各方对霸权的担忧。非洲和中东的某些地区有可能出现冲突:那里没有地区性大国维持秩序,争端纷起,且地区性集团个个厉兵秣马,嗷嗷待战。这听起来很不妙,但实际上并不会比这些地区以往经历的情形更糟糕。如果少一些外来干预的话,政治外溢和反弹也会相应少一些。在制度脆弱的地区,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权力分布和强国的态度;在权力分散的地区(如中东),能够期待的最好结果或许莫过于管理下的权力均衡;而在权力集中的地区(如苏联、南亚和东亚),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居领导地位的大国的政策。在这方面,中国的和平发展政策堪称典范。中国政府意识到其崛起会引发他国的反霸权主义反应,因此,除和日本的关系有些苦涩外,中国一直在努力扮演好邻居的角色。由于中国、印度和巴西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反霸传统,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它们会管理好各自辖区内的事务。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国际社会演化史的深度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自由派世界主义者,将不得不放弃世界必须按它们的形象进行重塑的观点。地区化的世界在西方人的眼里并非处处都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眼里或许也是如此。地区化世界要求对“共存逻辑”和“容忍差异”这些观点采取更包容的态度。我们目前的状况和19—20世纪文明冲突论盛行时的状况有所不同。权力的扩散使“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共存模式不仅变成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共有政治实践和文化是我们目前在全球各地或多或少都共同享有的历史遗产,其坚实基础将弥合诸多差异,并最终带来和平共存的美好前景。
刘伟华,外交学院博士
[收稿日期:2010-08-22]
[修回日期:2010-10-12]
注释:
① Barry Buzan,“A Leader without Follower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after Bush,”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5,No.5,2008,pp.554-570.
② 对这些概念的详细定义,请参见Barry Buzan,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Cambridge:Polity,1984,pp.46-76。
③ Charles A. Kupchan,“After Pax Americana: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2,1998,pp.40-79 ; Barry Buzan,“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6 ,No.1,2010,pp.22-23.
④ 详见Barry Buzan,“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6 ,No.1,2010,本节的陈述大部分引自篇文章。
⑤ 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London:Routledge,2007,pp.299-309,319-325; Adam Watson,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Routledge,1997; Gerri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Clarendon,1984,pp.7- 21; lan Clark,The Hierarchy of States: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Andrew Hurrell,On Global Order:Power,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35-36,63-65,71,111-114; Tim Dunne,“Societ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3,2003,pp.303-320.
⑥ 互动能力是指体系中运输、交往和组织能力的数量,譬如信息、货物、人员以何种速度、何种成本被运至多远的地方等,详见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80-84。
⑦ John 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8; 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48; Jerry H.Bentley,Old World Encounters: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Donald F.Lach,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Vols.l-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1970,1993.
⑧ Martin Wight,Systems of State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p.34.
⑨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52.
⑩ Nuri Yurdusev,“The Middle East Encounter with the Expansion of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in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eds.,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ddle East,Basingstoke:Palgrave,2009,pp.70-79.
(11) Jared Diamond,Guns,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W.W.Norton,1997,pp.67-81;William H.McNeill,Plagues and Peoples,London:Penguin,1976,pp.185-200.
(12) 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p.364-365.
(13)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The English School and World History,”in Alex J.Bellamy,ed.,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Cr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45-63.
(14) Michael Pearson,The Indian Ocean,London:Routledge,2003.
(15) C.H.Alexandrowicz,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in the East Indies:16[th],17[th]; and 18[th] Centur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 C.H.Alexandrowicz,The European-African Connection:A Study in Treaty Making,Lieden:A.E.Sijthoff,1973; Lauren Benton,Law and Colonial Cultures:Legal Regimes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6) C.H.Alexandrowicz,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in the East Indies:16[th],17[th],and 18[th] Centuries,p.224.
(17) David Christian,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p.351 ; John 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8) John Hobson,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pp.31-49.
(19)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 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London:Routledge,pp.265-276.
(20) Justin Rosenberg,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London:Verso,1994,p.162.
(21) 详见Ernest Gellner,Plough,Sword and Book: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London:Paladin,1988;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Beacon Press,1957.此外,还可参阅现代化理论方面的文献,例如Walt 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要了解对欧洲19世纪自强的不同解释,请参阅Victoria Tin-bor Hui,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p.231-233.另外,还可参阅Fred Halliday,“The Middle East and Con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in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eds.,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ddle East,Basingstoke:Palgrave,2009,pp.19-20.
(22) Douglass C.North,John Joseph Wallis and Barry R.Weingast,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3) Ernest Gellner,Plough,Sword and Book: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pp.62-69,pp.145-171.
(24) 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25) Andrew Hurrell,On Glob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11-114; lan Clark,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World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83; David Armstrong,“Glob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Stat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No.4 ,1998,pp.461-478.
(26)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见Barry Buzan and Mathias Albert,“Differentiation: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thcoming,2010.
(27)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pp.251-255.
(28) 要从不同角度更深入地了解这方面的扩张,详见Daniel H.Deudney,Bounding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6-264.
(29) Justin Rosenberg,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p.134.
(30)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pp.362-367.
(31)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61.
(32) Alexandrowicz,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Nations in the East Indies:16[th] ,17[th],and 18[th] Centuries,p.156; Paul Keal,“Just Backward Children: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Non-European Peoples,”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9,No.2,1995,pp.191-206; Paul Keal,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Tim Dunne,“Colonial Encount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ading Wight,Writing Australia,”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1,No.3,1997,pp.309-323; 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pp.49-98.
(33) James Mayall,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34) Jack Donnelly,“Human Rights:a 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4,No.1,1998,pp.1-11.
(35) James Mayall,World Politics:Progress and Its Limits,Cambridge:Polity,2000.
(36) Ronald Dore,“Unity and Diversity in Contemporary World Culture,”in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eds.,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pp.407-424; Adam Watso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pp.307-308.
(37) Fred Halliday,“The Middle East and Con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in Barry Buzan and Ana Gonzalez-Pelaez,eds.,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Middle East,pp.11-13.
(38) 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pp.42-43; Davis B.Bobrow,“Visions of (In)Security and American Strategic Style,”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2,No.1,2001,pp.6-8; Andrew J.Bacevich,American Empire: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Diplomac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88,p.90; Clyde P.Prestowitz,Rogue Nation: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New York:Basic Books,2003;Kenneth N.Waltz,“The New World Order,” Millennium,Vol.22,No.2,1993,p.189; Kenneth N.Waltz,“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2000,p.13,p.27.
(39) I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54.
(40) Ian Clark,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p.227-243.
(41) Charles Kupchan,“After Pax Americana:Benign Power,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 ,No.2,1998,pp.40-79 ; Eric Helleiner,“Regionaliz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astern Asia Policy Papers No.3,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1994.p.21.
(42) Yul Sohn,“Contest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East Asia,”Journal of World Politics,Vol.29,No.2,2008,pp.157-186.
标签:中国崛起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