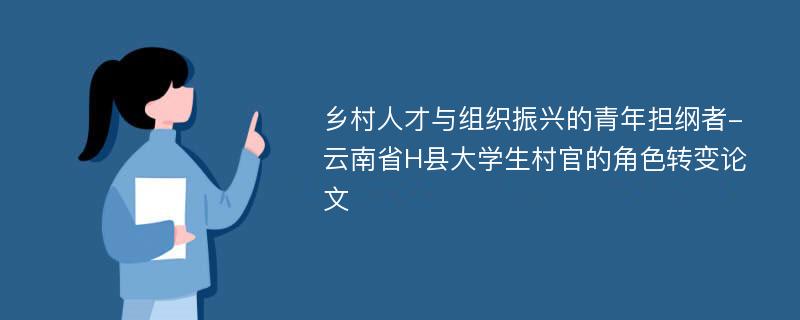
乡村人才与组织振兴的青年担纲者
——云南省H县大学生村官的角色转变
黄志辉 陈九如
摘要: 2015年前后,大学生村官制度与乡村振兴及扶贫战略实现了一种政策交汇,在这次交汇中,大学生村官的教育文化水准与基础信息技术正好与近年来乡村治理需求相吻合。新的扶贫项目及乡村发展项目提供了一种转变机遇,使得大学生村官群体成为一支实现乡村人才与组织振兴目标的重要青年动力支队。由此,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战略本身成为了近几年大学生村官实现在地化治理的重要契机。大学生村官在2015年前后发生的角色转变,呈现出两种不一样的实践形态乃至精神世界,该群体已经并将继续在乡村人才与组织振兴的实践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人才振兴;组织振兴;项目制;大学生村官;有效治理
一、研究问题与相关文献
乡村振兴是近年来党和国家推动的重大战略,这一战略针对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展开了全面振兴部署,其中“人才振兴”“组织振兴”要为其他层面的振兴战略提供领导力、制度建设、实践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保证。有效的乡村治理首先要求较高的文化技术领导力与有效的行政人才队伍。具体来说,基层行政力量能否顺利衔接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以及自下而上的技术治理与信息反馈,成为乡村振兴中对人才与组织振兴这两大板块内容的具体体现。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只有建立一支懂技术、有文化、能深入基层、能衔接地方政府的乡村治理队伍,才能为实现乡村人才与组织振兴提供治理保障。
但问题是,谁来担纲乡村人才与组织建设中的技术治理任务?谁来担当实现上下贯通的基层行政角色?虽然近年来,在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两大战略的引导下,乡村外出务工青年已有部分回流之势,但是诸多返乡青年也呈现出文化水准不一、返乡目的不同、行政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历一个再适应、再培养的过程,才能从返乡青年或在地青年群体中汲取乡村人才与组织振兴的人力资源。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已有的乡村建设经验中寻找制度资源。
其次,由于各企业的情形不一,准则不够完备,只能对企业工作提出基本原则和规范。如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既可采取平均年限法,也可用工作量法;会计政策变更,更能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这种变更会计界一般接受。在这种灵活性下,企业有可能选择不当的会计政策及处理方法,达到实现企业自身效用和价值的最大化。如我国推出的“八项”计提的运用就是由上市公司会计人员根据职业判断自行确定,带有很大的选择性,给会计造假提供了机会。
大学生村官制度在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两项战略实施之前,就已经在全国的乡村范围内普遍推行。以往培养的以及在任的大学生村官可以为乡村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提供库存性的人力资源。自2005年始,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表《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2013年是村官人数的最高峰,全国在职的大学生村官多达22.1万人,数量上可覆盖全国30%的行政村。此后,中央调整了在职村官数量,至2017年底,尚有6.6万大学生村官在岗。虽然在任数量相对减少,但是村官学历逐渐提高,例如,大学生村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成员占比从2013年底的76%增加到了2017年底的93.4%。总之,经过十四年的发展,这个人才库存目前已累积达到上百万人。
大学生村官是具有活力与希望的青年群体,他们的教育文化水准与基础信息技术正好与近年来乡村发展需求吻合,能够推动人才振兴与组织振兴。此外,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这两项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化作细分的政策与项目下沉到基层,同时更需要基层干部的配合实施与充分反馈,完成任务下达、指标分配、信息收集、报表制作与标准化反馈等工作。因此,农村治理的实践与社会治理效果的呈现,需要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重治理轨道中顺畅运行,其具体要求就是项目制度的展开与文件往来体系的建立,而青年大学生们能够担纲此任。综合来看,在新时期的“三农”治理背景下,国家对村干部群体要求的文化水准及沟通能力明显加大。作为国家基层治理与富民政策的最基层执行者,村干部群体内部如何协调分工应对国家整体振兴工程的大考,是近期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关键。显然,大学生村官在村干部群体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战略与大学生制度的实施过程在近几年的实践过程中围绕人才需求与行政组织的建设,实现了一次政策交汇。因此本文关心的是:大学生村官的教育身份、文化能力是否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相关切实作用?十几年的实践过程中是否发生了角色转变?面对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大学生村官群体在新的项目制度或文件治理过程中扮演怎样的新角色?新的制度背景下大学生村官是否能够顺利地接近、体验基层社会并形成自身的实践经验?
4.福娃迎迎是人和藏羚羊的结合体,藏羚羊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保护藏羚羊是绿色奥运的展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羊是十二生肖中的一员,象征美好、吉祥,例如“三羊开泰”,人们借羊的形象来表达美好的愿望,甚至有很多部落都用羊作为他们的图腾动物,说明羊在古代有很高的地位。迎迎的头饰融入了青藏高原和新疆等西部地区的装饰风格,这样的结合也证明了中国对西部的重视。
基层项目需要管理,文件数据需要总结汇报,大学生村官也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产生。与项目制一样,大学生村官制也是这一政治治理大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子面相。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设计就是对这些农村科层治理、项目治理、文件治理等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的回应。当下学界对其角色定位已有广泛的讨论。例如,马德峰将大学生村官的定位理解为四个部分:服务提供者、倡导者、关系协调者与资源筹措者,并强调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是在制度和政策中被建构的,作为一种“他塑”的结果。⑥ 马德峰:《大学生“村官”基层角色定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3(1)。 郑明怀则认为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正在不断弱化,成为了村干部和村民眼中的“好人”,在执行国家政策时采取变通,尽量做到两头讨好。⑦ 郑明怀:《大学生村官角色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9)。 郭明的研究认为大学生村官在国家与农村之间扮演了三个角色:“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村务工作‘秘书人员’”与“无根的农民治理群体”。在他看来,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群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间的人,其三重角色也代表了三重悖论,并导致了这个群体的职业困境。① 郭明:《游走在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之间:杜镇“大学生村官”的个案》,《青年研究》,2012(2)。 程毅在上海市金山区的调查也显示,18%的大学生村官在入职半年后还存在和村民的交流问题。② 程毅:《大学生村官现状调查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设计》,《华东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但地方文化还算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还是大学生村官作为陌生管理者与农村熟人社会之间的矛盾。在政策出台早期,很多村官都处于闲散状态,很难融入到村庄里。郑庆杰在山东的调查则发现村干部也有类似心理,不一样的是,村干部认为大学生村官是来争夺本地村干部权力的,虽然一起工作,却不把大学生村官视作自己人。③ 郑庆杰:《飘移之间: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建构与认同》,《青年研究》,2010(5)。 所以,吕程平的大学生村官研究发现,大学生要实现自我升华,必须突破村内村外的多种壁垒。④ 吕程平:《支持力量、技术选择与创业周期:大学生村官创业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7(6)。 但随着国家治理技术的理性化与科层化,大学生村官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如陈忠所认为的,中国基层政治生态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基层自治存在很多不规范的问题。而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有助于联结知识与社会,促成基层社会的整合,并能培养一批熟悉基层的基层干部。⑤ 陈忠:《大学生村官与中国政治生态:意义、问题与趋势》,《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现代国家的“数字化管理”是实现高效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乡镇干部来说,填报数据事关重大,上级对他们的考核主要就基于这些数字。尤其是自上而下的战略被分化成一个个“项目”之后,“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的技术就至关重要。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税改后,国家就开始使用“项目制”来分发财政资金,虽然地方可以对到手的资金进行一些自主利用,但国家仍然借助对项目的考核进行控制,以促进数据和项目成果达标,这就促使“规范性运作”成了地方干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以来,相关研究者也关注到了国家在乡村的治理角色、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变,这为我们观察大学生村官实践的制度变迁问题提供了分析依据。渠敬东、周飞舟、应星等学者回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变化:从全能型国家向科层制转变,并给予地方一定自主权——这一政治大转型过程中,乡村行政科层化得到快速发展,“项目制”的出现就是行政制度转变的结果。②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09(6)。 折晓叶对项目制的分层机制分析发现,项目制虽然是集权控制下的产物,但使得基层拥有了更强的活力。落实在乡村一级就让村干部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而“跑项目”,并依托自己的知识对获得的项目资金进行灵活运用。③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1(4)。 “项目制”是一种将行政体制与市场体制结合的机制,其核心理念是理性化的目标管理和过程控制。④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5)。 但这种治理方式也产生了使基层社会解体的后果:项目制需要的是理性化的思维和技术控制,而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实践往往遵循的是习惯逻辑。在错误的逻辑指引下,不少村庄走上了一条周雪光所指出的“通往集体债务之路”。⑤ 周雪光、程宇:《通往集体债务之路:政府组织、社会制度与乡村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行政评论》,2012(1)。 在乡村社会中,找到使用习惯逻辑的治理者来推动乡村振兴项目并不难,但要找到大量同时兼具习惯逻辑与技术手段的规模性人才,却实属不易。
社会科学领域中长期积累的实证研究成果,为上述问题的回应提供了诸多经验参考。较早的有关于乡村士绅、经纪人等相关的研究,可以作为类比参照。例如,费孝通先生在其中国绅士研究中,指出古代皇权之所以不下县,就是因为有乡村绅士作为乡土社会的代理人,实现与基层衙门的对接,从而构筑一种比较灵活的“双轨政治”。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第334-363页。 因此,有学者梳理费先生的理论后指出:“传统中国政治治理的‘皇权-民权’结构,皇权的‘无为主义’与民权的‘自治’方式是共构社会秩序的政治框架”。② 黄志辉:《重温先声:费孝通的政治经济学与类型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第84-119页。 共治的前提是中心权力与基层民权缺一不可,如果代理人无法自下而上地反馈民意,就会阻塞轨道运行。③ 谭同学:《桥村有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55-207页。 在《乡土重建》一书中,费先生指出绅权是皇权与民权的中介,这个“中介”不可失效,否则基层行政容易僵化。因此,要活化基层治理,就必须活化这些作为绅士的非正式“村干部”。大学生村官虽然与乡绅群体不同,但他们在双规政治中的角色却很接近。费先生的研究发现无疑能够为本文提供借鉴。
性格内向的李桂明天性聪明,爱好广泛,可就是有个爱赌博的坏习惯。就因为这个,张秋曾多次批评他,甚至还停止过他的工作,李桂明挺恨张秋的,据此,可算作他有作案动机。
二、H县大学生村官的早期实践感:在“前技术时代”虚度年华?
H县位于我国西南山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区经济条件长期较差,居民以农民为主,主要种植烟叶、花椒、花生,兼及畜牧。2018年7—8月,笔者在H县展开田野调查,主要调查对象就是H县的在职大学生村官。期间进村详细访谈了该县4个乡镇的十几名大学生村官以及分管大学生村官的县委组织部干部。这些大学生村官入职时间集中在2013—2017年。其中2015年以前入职的村官大部分都已经转为公务员,2015年以后入职的还处于服务期,部分人要在2018年9月的考试中决定服务期满后的去向。
个人理财精品在线课程具有移动学习、碎片化的特点。教学评价模式的设计应该在参考个人理财师的知识结构和职业资格考试要求,设计出适宜网络运行环境,需求特征明显、操作便捷的要求,结合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特点进行设计。首先,建立在线课程互动空间,实现师生之间的在线讨论、个人学习记录及过程的在线追踪、推送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将“教、学、评”三个环节融会贯通。其次,教师可将个人理财精品在线课程的教学设计、教学反思上传在线课程互动空间,供所有师生参照,以利于教学设计的进一步完善。这样有利于教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同时,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绩也得到提升。[4]
宇航员在宇宙空间中穿的衣服和在地面上差不多,比如T恤和短裤。他们不像在地面时那样经常换衣服——毕竟,在空间站里没有洗衣机。
Signif. codes: 0 ‘***’ 0.001 ‘**’ 0.01 ‘*’ 0.05 ‘.’ 0.1 ‘ ’ 1
早期入职的村官在回忆前几年的经历时,与目前在职村官有着很不一样的实践感。例如,刚从村官岗位离开不到两年的福贵,现今已是该县一个中心镇的干部。笔者在与福贵深谈时,发现他办公室的7名公务人员中有4个都有过大学生村官经历,其中包括了这个办公室的领导。福贵和其他几位有村官经历的公务员感受相同:三年村官工作就是煎熬!如他所说:“我们村官交流就感觉是消磨时间,等待就业,现在在镇上工作也是,没有成就感。如果你说的是干一番事业,在这个系统没戏。任职前想的是进村里好发展,但到村上了解了就知道现实是不一样的。”面对这种让自己不太适应的工作,福贵一直力争逃脱,他每年都参加公务员考试,虽然作为大学生村官可以享受相关政策,但是他连续三年都名落孙山,一直熬到了三年期满。
福贵的领导以前也是一位资历较深的女性大学生村官,她也有类似的表述:“可以说我们一开始是抱着美好憧憬去做的,但最后是很失望,没有得到什么,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村官出身的公务员要在基层消磨8年。男的还好,女的我觉得有点浪费青春。30岁还什么都没有。”目前她已经30岁,职务是镇政府办公室主任。毕业八年,她觉得自己还处于一个没有科层干部级别的位置上,心有不甘。办公室里另外一位几年前转为公务员的女性村官也有类似的想法,回忆早几年的村官经历时,觉得自己在虚度年华。
H县最北山区达通镇贾王村村委会副书记阿飞,也曾经是一名大学生村官。2013年上岗,任期满后又被乡政府指派在村里做扶贫工作。贾王村所在乡镇达通镇是H县最贫困的乡之一,而贾王村又是乡里最穷的村,贫困率过半。回想起自己的村官生活,阿飞认为扶贫攻坚战略实施前后的村官工作节奏截然不同:“那时一方面是村里工作少,另一方面自己又没有经验和关系,都是有事情才来,比较轻松。开始搞建档立卡之后就不行了,当天的活有时候都干不完。”这里阿飞所说的“建档立卡”,就是为贫困户建立一套繁杂的档案体系,一般单户档案有二三十套材料。但从制作材料的过程来看,就是在电脑上按照规范将几个数字反反复复地填充再打印出来,可以说在一般大学生看来,除了费时间之外,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是这只是他者的判断,一方面,乡村社会中难以找到懂电脑和数据的人才;另一方面,一开始大学生村官们也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卷入一个重要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大学生村官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这些在他们看来乏味的工作,使得他们成为了国家技术治理在乡村的担纲者,并借着这个机会融入了村集体。
但村官们自己回忆往事时的表述却并非如此:村官们进村时往往都怀揣着一颗上进的心,大学刚毕业回到家乡,谁不想在这一片小天地中干出一番事业呢?只是工作的冗杂让他们失去了斗志。从访谈和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初期并没有得到太好的成效。对于H县的大学生村官来说,虽然他们大多是本地人(极个别的有籍贯为邻县的),语言相同,又对本地文化相对熟悉,但要想融入到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中,仍是件难事。
传统乡村中的村庄干部可称之为原生型村干部,至少在原则上他们是在地产生的,需要对村民负责,而他们能履行自己的职务也是由于自己作为熟人社会的一员,以及对村内事务的管理经验,这就是所谓的“习惯理性”。比较起来,这些特征都是大学生村官往往不具备的,他们更具备“技术理性”。以H县的情况为例,十位村官大多都是在县城或乡镇接受的素质教育,高中阶段都在县一中读书,至于大学更是各奔东西了。在他们受教育的生命历程中,对乡村基层的认识都微乎其微。正如贾王村大学生村官阿飞所说的,“我还算好的,就在自己老家当村官,开始的时候跟人打交道就说我家是六组的,他们的态度就好多了。像别人没有基础的多难啊。”同样,这一点在在县城内柳溪社区做村官的陈缘那里感受最为强烈。陈缘的户口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云南的了解在工作前仅限于在云南财经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以及来自H县的男朋友。身处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工作又需要群众基础,对她来说不可不谓是一种挑战了。在2013年至2015年日常工作的开展中,由于陈缘处于社区文化的边缘位置,很难接手处理社区内的核心治理业务,“让我处理电脑信息技术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一开始就直接让我接触地方上的老百姓对我来说是难题”。
对于早期的村官们来说,颇为烦心的还有来自县里和乡镇的任务,这些任务并非科层行政的常态化任务,虽然他们是驻村干部,但是上级政府如果举办活动往往会调用他们去帮忙。例如,陈缘由于身处县城,就经常被县政府叫去帮忙做会务工作。而福贵的经历更是如此,他的工作一半是在村委会进行,另外一半则是在镇政府帮忙。按照相关规定,调动大学生村官需要向县委组织部申请,但除去县里举办的大型活动外,大部分日常工作调用都没有下达正式文件。正如许多早期研究指出的那样,很多村官都是挂名在村,实际在乡镇工作。
虽说我国已经实施了很多的发展策略,包括: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并未完全覆盖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在保障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我国金融机构应当积极探索全新的融资模式,不断吸引各项资本的参加,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强化PPP模式的应用,联合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部门应当强化各类形式合作模式的鼓励。
当国家的治理越发细化,对基层的治理要求就越发系统,大学生村官的存在也就相对更加重要。正如前述研究所指出的,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受到国家政策变化、基层治理环境、相关参照群体的评价等方面因素的形塑。但以往的相关研究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第一,十几年来的大学生村官制度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是均质的吗?其效果与执行方式没有发生任何变迁吗?第二,乡村振兴、扶贫攻坚战略究竟如何具体地与大学生村官制度发生了交汇?本研究意图在新时期各种乡村项目治理的背景下,通过对一个县域内的实地研究以及对在职大学生村官的大量访谈,探讨上述问题。同时追问:在当代乡村新的发展战略、尤其是“项目制”背景下,大学生村官们在地方社会的角色适应、具体调整过程以及面临怎样的治理问题或治理障碍。文中县名、乡镇及人名均做匿名处理。
总之,一方面,文化上的区隔使得早期H县大学生村官常常难融入村民,另一方面,当地村干部面对这些来分享自己权力的外来者往往抱有戒心。乡村“习惯理性”的缺失,使得早期大学生村官像村庄大门口的陌生人,无法实现身份的顺利过渡。此外,即使少数村官能克服乡村文化陌生性的问题,上级政府的频繁调用也让村官们难以与村民维持稳定的关系,早期村官缺乏一个能让他们稳定扎根的契机。这些问题共同阻碍了早期大学生村官制度的良性运转。虽然国家出台大学生村官政策时的主要目的是建设新农村,培养一批有基层经验的后备干部,推动大学生村官嵌入基层社会,但这一目的在2015年之前显然没有全面实现,倒是新的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战略,推动大学生实现了身份定位与角色转型,并在近几年的乡村人才与组织建设中有突出表现。
三、技术治理的契机:乡村振兴机遇下的角色转变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国家的乡村治理过程开始进一步趋于技术化与细化,从大型治理模式向适当下放事权的技术性治理发展,作为治理对象的乡村也在中央越来越重视农村工作的背景下发生着变化。乡村事务逐渐迈向行政化,并需要与乡镇乃至县级政府实现文件、数据、政策实施等方面的正式对接。自2015年底打响的“脱贫攻坚战”,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节点。当H县的大学生村官遇到脱贫任务时,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角色从此变得更加复杂了。
早期大学生村官的实践过程,还不像最近几年这样被整合进了乡村扶贫与振兴战略的实践运行中去,也不那么迫切需要电脑技术和信息处理能力,各种具体经验尚处于摸索的阶段。县组织部的一位委员指出,在扶贫细分任务下发之前,许多大学生村官就是去村里享福的,自己有车,每天晚上都会自己回家,经常请假。“他们说自己工作很难进行,不能融入群众,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什么都不干,闲吃干饭,白费了国家给的那么好的政策。”在这位组织部委员眼中,早期大学生村官的形象不太好,很多大学生村官只是将这项政策视为通往正式“编制”的捷径,他们在得到正式工作机会后却不努力工作了。
与费先生的乡绅研究类似,杜赞奇在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中提出了“经纪模式”④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36-37页。 ,该理论经常被乡村治理研究者所重视。所谓“经纪”,是指虽然身处传统官僚体制之外,但却帮助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的群体。按照杜赞奇的表述,经纪群体很似乡土社会与庙堂之间的中介人,他们并非全然是国家的基层代理人,但却与国家意志息息相关。杜赞奇细分出“盈利型经纪人”和“保护型经纪人”,前者是工具理性主义者,以经纪的身份换取利益;后者更加嵌入社会,是乡土社会的道德、利益代表。但是,当下的村干部很难被这样简单地进行二分,现实中村干部的实践角色,更像村庄秩序的“守夜人”与村政中的“撞钟者”。① 吴毅:《“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开放时代》,2001(12)。 这种多重面向的基层治理者,一方面不会故意怠慢国家交付的任务,但也不会全力以赴,尤其是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另一方面,村干部在很多业务的办理上有困难,让村民也不再关注村委会选举。这种村政的懈怠进一步让乡村与乡镇互动中的非制度性因素增加,甚至导致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在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不是一种科层对接关系,而是普遍地通过特殊手段来进行联系。当下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正式、普遍而宏大的社会发展项目,显然不可以完全依靠一种非正式的特殊关系来全面推动。
抓住春耕秋收集中揭膜关键时期,组织督查小组对各乡镇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进行督查,指派专人跟踪检查废旧农膜回收企业,清理整治包片区域内主干道、公路沿线、城乡结合部、田间地头堆放和树梢飘挂的废旧农膜,督促回收企业切实履行包片回收协议。每年春秋两季农资打假专项活动中,联合农业执法大队、工商、质监等相关部门,对秦州区农资市场上销售的农膜专门进行执法检查,严禁厚度小于0.008 mm、耐候期小于12个月的农用地膜在市场上销售,从市场源头上杜绝了劣质、不合格农膜的使用问题。
2015年扶贫攻坚战开展以后,各类贫困户档案和资料的统计任务落在了村委会。具体来说,就落在了大学生村官身上,毕竟H县大部分村委会成员文化水平较低,年龄又大,大多不会操作电脑。笔者在贾王村曾见到这样一幕:县委领导临时来村里调研扶贫工作,得知消息后,众人连忙让阿飞用电脑制作“扶贫队员公示板”里的资料并打印出来,在场有四五人,却都只能围着阿飞转,给他念材料。忙完之后,阿飞向笔者抱怨:“没办法,他们都不太会用电脑(软件),这些事都是我做。”类似的项目检查、调研活动,使得大学生村官成为了相关场域中的中心角色。正如阿飞所言,扶贫工作的到来让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有了不小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他这样的“老村官”更是明显,毕竟他经历过2015年以前的那种闲散生活。当忙得不可开交时,自然会怀念2015年之前闲散的状态;但静下来的时候,许多村官又认为这样锻炼有意义,能够体现村官的存在价值。
与上述现象类似的案例在H县较为普遍。例如,白菇村条件与贾王村差不多,这里的村官楚南比阿飞年轻些,却承受着相同的压力,在反反复复地填了一年表格后,他对贫困户的熟悉程度上可以比肩本地村干部了。楚南清楚地记得全村一百多户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可以细到收入多少、种几亩地、种什么。楚南在这里也是独挑大梁,虽然有年轻的扶贫工作队队员共事,可是主要任务还是由他来做。在扶贫这件事上,无论下派的扶贫队员还是村委会干部,都认为楚南这样的村官是村委会的重要一员。一方面,村官们往往是为数不多懂技术的村委会成员,对大学生村官有隔阂的村干部不得不把工作交给这些年轻人;另一方面,正是在高强度又接近基层的工作中,大学生村官得以快速了解村庄情况,接触各类社会关系,从而促成了从外来大学生向真正的“村官”的转变。
龙井村的村官元芳是村官群体中少见的“城里人”,她从小生活在丽江市区,在昆明读完大学后又在泰国曼谷工作,2015年才回来。她所服务的龙井村虽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但在初任村官的元芳看来还是非常陌生的:“来工作前从来没想过农村会是这样,穷人原来这么穷。”在龙井村,元芳的任务主要就是一件事:党建。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的各项制度落实情况也是上级党委对村党委检查的重点。元芳需要参加各种党小组、党支部以及村党委的例行会议与各种学习,并在会前准备材料,会上做记录,会后整理各种会议信息并在全省信息系统中进行上报。看起来元芳的工作只是“书记员”形式的,可中央的规定是一回事,落实到村里就是另一回事了,农民党员在一个月要开好几次会议和养家糊口之间往往选择了后者,很多党会和党课实际上都没有开,这就需要元芳去“补”材料。元芳并不是党员,却负责了全村的党务工作,她自称为“党外的党务工作者”。在这项工作展开的过程中,元芳获得了村委会和村民的信任,并在秋天作为“扶贫模范”登上了H县新闻。
再如,天平村的朝燕是这一类借助工作嵌入乡村的典型:她是唯一一位担任扶贫队队长的村官。她对自己担任这一职务是抗拒的,希望能让她只做扶贫队队员,但组织上拒绝了她的要求。她自认为组织的任命莫名其妙,但这恐怕和她在村里参与灾后重建的突出表现有关——当时她就在负责登记灾民的相关信息,每天都要工作到一两点。本来就是扶贫工作队的队长,再加上重建工作中每天都在和村民打交道,朝燕赢得了村民的尊敬。朝燕在村中的地位不亚于村支书,在招待下来调研的副镇长时,朝燕和支书、主任坐在一起招待副镇长和乡镇干部。
显然,新时期的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战略重新激活了大学生村官制度,大学生村官们在制度交汇实践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了定位。有学者指出,“只有在流动着的事件与过程之中,才能更准确地完成对变动中国家与社会及官民关系的考察”。① 吴毅:《小镇喧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7-20页。 村官的角色转变也是这个道理,在国家治理方式由全能型转向技术型的过程中,大学生村官所经历的事件不断形塑着他们的角色。乡村振兴、扶贫攻坚战及其带来的一系列事件都使得技术治理得以更深地进入村庄,作为技术担纲者的大学生村官,既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他们不仅逐渐成为了新时期乡村行政过程中的人才,也促进了组织行政的科层化、常态化与高效运作。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当下的大学生村官们在乡村人才振兴与组织振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转型中的困境与方向
在技术治理的推动下,村官在工作上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但他们在村庄场域中依然超脱不了行政身份的两面性问题:大学生村官虽是政府派出人士,存在于村委会编制之外,但没有任何权力。当村官与村干部发生分歧或是提出有创见性的想法时,没有合法身份就成了村官的困境。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大部分村官都不能参加村委会竞选,只能尝试参加村党委竞选。例如阿飞就是通过本村村民而不是外来大学生身份在村委会换届中成为了村委会副主任。但这只是特殊情况,大部分村官在他们的村官任期内,还面临着身份的困境:既是县里派来的“村官”,却又缺乏相关法律对身份的规定。此外,龙尾村的大学生村官宋歌也常遇到这种情况,她所在的村子是华坪县芒果种植最集中的村,没有什么扶贫压力,她主要是做党建工作。但如她所言,在一些村里的发展问题上,她也会向村里提出意见,但无人理睬,这会慢慢磨灭她的斗志。与当地村主任产生意见上的分歧是常有的事,在不断磨合过程中宋歌找到了一些策略,“那能怎么办?只能听主任的,我又没什么权力,但是,反正错了他还得按我说的办”。
能否获得确定身份的问题在各地大学生村官身上都有普遍体现,但吊诡的是,在国家与最基层乡村的科层联系上,大学生却担纲了枢纽的角色。作为技术治理和处理信息数据的担纲者,大学生村官带着知识与技术来到相对封闭的乡村,在政策的调整、与农民的交往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让技术型的基层官员身份在农村的地位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时至今日,大学生村官已不再是一些学者所观察到的在国家与乡镇农村之间的徘徊者、身份飘忽不定的游荡者,也没有成为费孝通、杜赞奇那里维护本地利益的村民代表者,他们更像是带着知识与技术被国家科层机器分配到基层的执行者,项目制下分级运作机制的担纲者,与形形色色的文牍、文件、政策指令、三农数据为伴,这些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将重构新的乡村治理权威。
更为重要的是,村官制度的生计几乎与乡村振兴战略同步展开。从2017年开始,云南省停止了专门的大学生村官招募,转而由新招的公务员赴农村担任大学生村官。公务员村官由于身份确定,处理相关问题时更加果断且面临更少障碍。来自政府的确定性身份以及相对稳定的岗位,让村民不敢随意为难。确实,在编的公务员有着大学生村官没有的优势:公务员是“官”,而大学生村官还是“民”,而且公务员进村后往往会成为上级任命的村委会副书记,在村里站得住脚。
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为了保证乡村治理的稳定,基层治理人才队伍的选择应该在组织与民意上实现双向吻合。① 吴毅:《小镇喧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7-20页。 大学生村官也有类似的属性:虽然不由村民选出,而是组织直接指派,但是指派之后要促成村官与老百姓之间的顺畅衔接。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战略的正式性运作,带来了乡村治理变革过程的两个面向。一面是项目制与技术治理下的变革,隐藏于文山会海和表格数据中的是技术理性,原有的村干部再也不能以个体经验担负承上启下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村官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在他们身后的是越来越多的专职文书与公务员身份的专职村干部。这个技术官僚群体将逐渐打开中国千年来最为稳定的基层社会的大门。另一面则是技术治理与科层化的触角不断下探,在农村扎根。面对越来越冗杂而细分的事务,如村官所言,村委会越来越像乡镇政府联结的行政机构。昔日位于双轨政治下端的本地村干部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到技术化管理体之中,只是做“撞钟者”与“守夜人”恐怕难以为继,而需要努力成为勤勉而理性的治理者。
五、结语
总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个发生在基层社会的微观过程,并深度分析过往百万大学生村官将在未来乡村振兴中发挥怎样切实的功用。基于实地研究,本文至少有以下几点研究发现。首先,从现实层面看,2015年前后是大学生村官制度的重要实践分界点,这个分界点也是大学生村官身份与心态转变的关键节点。促成该分界点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乡村振兴、扶贫攻坚等大型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大学生村官在乡村发展项目下沉与文件上下乡村的过程中找到了自身的技术定位,这可谓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意外结果。第二,青年大学生们不仅作为“人才”振兴了乡村精英队伍,而且是乡村群众、村庄两委以及基层政府之间的重要衔接者,从而至少在人才、组织两个层面自下而上地“反哺”了国家战略。大学生村官们就像费孝通先生笔下“双轨政治”下的扳道工,不断地尽自己所能保证两条轨道畅通无阻,使科层技术治理的逻辑全面进入乡土世界,促使双轨合一。第三,大学生村官立足技术理性,不仅逐渐获得了乡村治理者的技术性角色,而且因此迈向乡村社会的纵深,获得了更多的习惯理性。技术理性与习惯理性的双重获得,意味着大学生村官们正在逐渐摆脱原有的“内外壁垒”,打破了以往研究者所谓的“职业悖论”。笔者相信,过去十几年培养的超百万基层青年村官人才,将继续为乡村人才振兴与组织振兴发挥光热,为乡村注入活力。针对这一人才储备,未来要继续发挥大学生村官的青年力量,还应激发大学生人才群体的专业技能,在乡村实地运用其专业知识,提高大学生村官们的工作积极性,在产业、生态、文化等层面上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The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e Role Changes of College Students Village Officials in H County Yunnan Province
Huang Zhi-hui Chen Jiu-ru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2015, the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 system interacted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Th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tandards of the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and the bas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incided with the rural governance needs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an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provide a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y, making the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become an important young supportive group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ural tal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talization. As a resul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tself become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college student officials to achieve localized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The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s have undergone a major role change around 2015, showing different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mental states. This group has played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tal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Talent Revitalization; Organization Revitalization; Project System; College Student Village Official; Effective Governance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精英阶层’与现阶段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研究”(16BMZ011)。
作者简介: 黄志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人类学;陈九如,中央民族大学创新实验班2016级孝通班本科生。(北京,100081)
(责任编辑:祝玉红)
标签:人才振兴论文; 组织振兴论文; 项目制论文; 大学生村官论文; 有效治理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