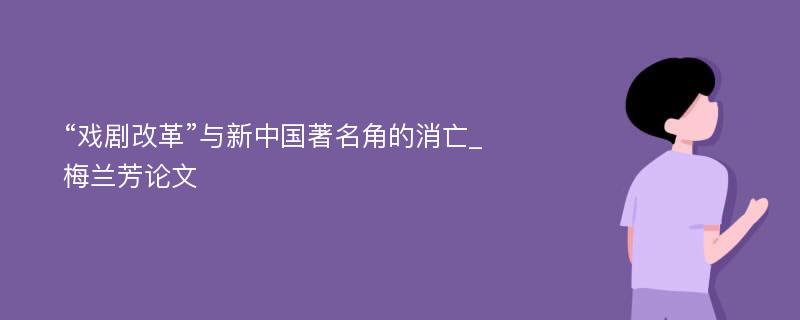
新中国“戏改”与名角的消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角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制:由私家班社走向示范性国营剧团
中国传统戏曲长期以来以自发、零散的形态生存于民间,班社是其基本的组织形式。至近代,随着社会转型,班社由松散的临时组合开始向职业化、商业化组织演变,并逐渐形成了“名角挑班”这一组织模式。“名角挑班”是以某个知名演员为号召组建班社,依行当分工招募配角演员(包括琴师、龙套等),按照名角的艺术特色排演剧目,并制定相应的宣传营销策略。在这一组织模式中,名角拥有极大的话语权,演什么、怎么演等问题,基本都由他定夺。由于名角地位的确立,以名角为代表的、风格迥异的表演流派得以形成和发展。可以说,一个名角不仅关系到一场演出、一个剧目、一个班社,甚至关乎一个流派、一种艺术风格的兴衰。“名角挑班”之所以能够有效建立和有效运作,还在于它的市场号召力,它本身具备充分的可供发掘的商业价值:市场竞争不仅使个别演员脱颖而出,成为名角,而且名角自组班社、在激烈的竞争中巩固其地位,又激励了更多的名角脱颖而出,促进戏曲在竞争机制中走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当然,由于“名角挑班”这一组织机制遵循的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受利益驱使而牺牲艺术、忽视社会责任的现象亦在所难免,其社会功能的发挥自然受到极大的局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整个戏剧界“戏改”的发动,情形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实,早在1948年11月13日,解放区《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旗帜鲜明地表示出要对旧戏进行改革。新中国刚宣布建立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成立,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旧剧改革运动全面展开。1951年,政务院“五五指示”出台,为“戏改”提供了总方针①。
“戏改”的首要任务是“改制”,即戏班所有制性质的改变,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所有制改变为其重心。新政权不再任由数量惊人的戏曲资源流散于民间,而是进行统一收编,将私营性质的戏曲班社改编为国营剧团(或私营公助,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阶段,绝大部分民间剧团都已转为国营),令其为新的国家意志服务,成为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分子。1950年,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新中华评剧工作团在北京相继成立,成为首都地区戏曲团体改制的先行者。在上海,国营化亦紧锣密鼓地推进:1950年4月,华东地区第一个国营戏曲团体——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宣告成立,该团以越剧名角袁雪芬的“雪声剧团”为基础,陆续吸收了范瑞娟、傅全香、张桂凤、陆锦花、陈少春等戏曲名人,可谓名家荟萃,袁雪芬出任团长;与此同时,国营华东京剧实验剧团也组建成立,李玉茹、金素雯、陈正薇、王金璐等沪上名角纷纷加入。此后,京剧团与越剧团并入华东戏曲研究院,由海派京剧泰斗周信芳担任院长,该院的工作方针为:“立足江南,面向全国,建立一个艺术创造、经营管理上有示范作用的正规化的艺术团体。”②在艺术创造和经营管理上起示范作用,不仅是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工作方针,也是当时大型国营剧团普遍遵循的转制后的演出原则,1951年4月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的《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与1951年计划要点》及1952年12月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剧团工作指示》等文件都一再强调这一点。在此,“示范性”既界定了新型国营剧团与旧时班社的区别,又规约了身在其中的名角行为。
剧团国营化后,新的演出机制造成一系列改变,致使名角地位首先受到冲击。国营剧团为文化事业单位属性,同其他国家事业单位一样,有一套繁冗的科层组织,上演剧目需要剧团的团委会(包括剧团支部)及文化主管机构(文化部设有戏改局专门负责戏曲改革工作,各地方也相应设立戏改处或类似的管理部门)的层层审核,不仅程序烦琐,而且对剧目内容也严格加以掌控,不能有效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剧目被以不同的方式清除出舞台,即便是名角的看家戏也难以幸免。由评剧名角小白玉霜领衔的“再雯社”因率先演出革命现代戏成为当时北京评剧界的一面旗帜。恰好文化部戏改局要在评剧、京剧界各以一个剧团为改制试点,“再雯社”被选中。在戏改局的统一调度下,“再雯社”同另一位评剧名角喜彩莲的剧团合并,组成新中华评剧工作团。最初,团长席宝昆还顾及两个名角的戏路特长,决定上演《珍珠衫》——该戏是评剧的主要剧目,颇具市场号召力,小白玉霜亦以该戏成名。此次,小白玉霜和喜彩莲联袂演出,分别出任二旦和大旦,两人都有相当多的发挥余地,但演出受到戏改局的批评,因该戏又名《循环报》,有报应、宿命色彩。戏改局指示该剧团:不要只照顾名演员的戏份,而要重点考虑剧目的思想意义,要发挥剧团的示范功能,并向剧团派驻了政治辅导员③。此后,上演剧目问题便由该团演出股的行政人员直接安排,不再征求两个主要演员的意见。至于文化部门和戏改局干部以人民性、阶级性等为由随意改戏、禁戏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连《四郎探母》这样一出几乎所有名角都演出过的剧目,也因涉嫌民族问题、宣扬汉奸立场、鼓励投降等莫须有的“罪名”处于不禁而禁的状态;而程砚秋欲将程派经典剧目《锁麟囊》重现舞台的愿望,也只能付之东流。
“名角挑班”选择剧目,以发挥演员特长为准则,国营剧团的剧目选择则重在所谓的社会意义。身在国营剧团的名角一旦丧失剧目选择的主动权,其个人艺术发展也便遭到严重的掣肘。1950年底,浙江省越剧实验剧团成立,作为越剧的发源地,这一国营剧团对于浙江全省越剧的示范性地位毋庸置疑。该团设立一队和二队两个演出单位,前者演出传统的女子越剧,后者则进行新式男女合演实验。素有“越剧皇后”美誉的名角姚水娟被分配到二队排演她并不擅长的现代戏。姚水娟不仅成名早,而且是越剧改革的先驱。她率先聘请专职编剧编写演出剧本戏,在越剧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姚水娟并不活跃,有段时间甚至完全赋闲家居,后虽被吸收到浙江省越剧实验团,但一直未曾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了配合当时刚刚颁布的《婚姻法》宣传,浙江省越剧实验团决定移植批判包办婚姻的沪剧《罗汉钱》(该戏和评剧《小女婿》都曾在1952年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戏曲会演中获奖,很快成为各剧种争相移植的样板式剧目)。姚水娟扮演剧中以丑角形象出现的媒婆五婶,这只是一个戏份不多的配角。此后,该团改编评剧《小女婿》,戏中媒婆陈快腿一角一时无人肯演,姚水娟主动请缨,不过,此时的剧团书记曹素清的一番话颇引人思量:“姚水娟同志这种敢挑重担的精神值得学习。但是你是越剧名家,也是我团的主要演员,在《罗汉钱》里你演媒婆也是为解决剧团困难,虽然很称职,但是社会上也有不同的反映,说我们不尊重知识分子,让你演丑角,是变相压制人才。”④曹素清之言透露出几点信息:国营剧团名家所饰演的角色,带有完成任务的成分,并非各施所能、人尽其才;对于名角不能人尽其才,其时已有舆论批评,却无实际改观。
新中国为了配合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化国家行政管理职能,“是各种组织机构以国家的名义,向整个社会行使强制性的管理权力”,个人与这种管理权力的关系并非自由选择,“只有被动的服从”⑤。在这个意义上,单位构成了国家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这一组织,便意味着被体制化了,个体或隐或显地会遭到形形色色的禁锢。对于这一点,戏剧名角未必会有透彻的领悟,但他们隐隐感觉到其中的压力,因而相当一部分名角对国营剧团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持犹疑、观望态度,如马连良、张君秋、言慧珠、童芷苓等,当几经权衡终于决定迈进国营剧团的大门时,他们中的某些人竟然会在上班的第一天“几乎手足无措”⑥,而由于“不适应国家剧团严格的纪律”以及“工作生活习惯”⑦等原因离开剧团的,亦不乏其人。
在新中国初步建立的组织体制之下,单位具有“多功能”性质,它既向单位成员提供各种资源,又代表国家对其成员从工作到生活多方面进行管理,对于加入国营剧团的名角来说,后者尤为凸显,其后果之一便是被搁置、日益远离舞台。言慧珠便是一个典型。作为梅兰芳的得意弟子,言慧珠的舞台魅力无须赘述,但不够积极的政治态度阻碍了她的艺术脚步。1956年5月1日至1957年5月的一年间,供职于上海京剧院的言慧珠只得到十三场演出机会(同一时期,北京的张君秋每年平均演出二百场),无奈的她愤愤言道:自己正在角落里发霉!⑧言慧珠极具艺术天赋,她移植自朝鲜的剧目《春香传》上演后颇受观众青睐,却终究珠落尘沙。针对这一现象,田汉曾在1956年第11期的《戏剧报》发表《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一文,呼吁有关部门合理规划,尽可能给演员更多的登台机会,但收效甚微。1957年5月,在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吴祖光再次就此问题进言道:“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现在一切依靠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⑨在庞大的组织框架下,个体不断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禁锢,而被隔离于舞台的名角,艺术生命日益萎缩。
二、改人:从“旧艺人”到“人民文艺工作者”
1951年,田汉撰文提议废止“旧艺人”这一称呼,改称“戏曲工作者”⑩。经过“改人”(即改变旧艺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接受社会主义革命文艺思想),试图改变艺人的精神面貌,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艺术标准。旧时身陷社会底层的艺人获得戏曲工作者这一新的社会身份定位,而被吸收到国家单位组织之中的名角也成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少数人更是被赋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由名角到人民文艺工作者、人民艺术家,并非简单的称呼改变,更标示其社会形象的深刻蜕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中艺人的地位卑微,但名角的光环却异常耀眼。1913年秋,梅兰芳应丹桂第一舞台之聘与王凤卿一同到沪演出,《申报》连续六十余天对此事给予追踪报道。梅兰芳登台演出的新闻、广告、评论一度成为报刊与民众共同的热门话题。此后,梅兰芳出国演出,从出发情形到国外演出概况,从国外演剧的成功再到归国后的荣耀,更是牢牢吸引了公众的视线。1923年《申报》曾有文章描述“伶王”梅兰芳所到之处引起的轰动场面:“梅兰芳一到上海,居住的旅社门前,聘他的舞台阶下,人头济济,都想一瞻他的风采,究竟比天上安琪儿胜过几分?梅兰芳不来上海便罢,梅兰芳既来上海,上海人不去看他的戏,差不多枉生一世。所以当去包脚布,也要去看他一回。梅兰芳一到上海,上海人有儿子的,就发生教儿子将来也要唱戏,做第二个梅兰芳的心思。”(11)可见,戏迷的拥戴、票友的追捧,越发凸显了名角高高在上、俯视群小的优势地位。梅兰芳的弟子言慧珠也同样受到追捧,被推上“平剧皇后”(12)的地位。
在论述20世纪以来所兴起的明星文化时,王晓华指出明星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众的崇拜对象,在于他们是世俗神话的制造者,为芸芸众生超越凡俗的现世生活提供了一种想象性的渠道,因此明星便具备了某种“神性”(13),得以凌驾于大众之上。但是,在新中国全新文化语境中,这种凌驾显然是不适宜的,新型意识形态要求必须祛除名角身上的所谓“神性”,使他们融入大众,成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梅兰芳的发言可谓是诚惶诚恐:“我在戏剧界工作了四十几年了,没有什么大的贡献,真是惭愧得很……这次在会中听到各位先生的高论,更感觉到我们所演的戏剧的内容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14)梅兰芳所言并非仅指改革戏剧内容,而是更内在地关涉名角姿态的改变——由被大众顶礼膜拜到接受人民的检验和修正。作为伶界魁首,梅兰芳充当着名角改变的风向标。1951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的文章《庆祝建国两周年,做人民的演员》,诚恳表述其与大众融为一体的意愿。1952年10月25日,常香玉的《永远记住这一天》刊发于《文艺报》,文章主要讲述了常香玉出席毛泽东主席招待会时的情形,特别强调了她的激动心情:“我们对国家和人民才不过做了这么一点工作,但党和政府却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光荣和鼓励……”谦卑的语气中充满期待,期望更大程度上得到人民的认可。
身份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名角个性的削弱。上世纪40年代的言慧珠是在舞台上魅力四射的平剧皇后,在舞台之外亦“最懂得引人注目的技巧”。抗日战争结束后,梅兰芳重新登台,言慧珠绝不放过观摩大师表演的机会,却也时时借机彰显自己的名角风范,标示其独特的自我,每次入场她都是“扬着头,迈着轻松的步子,由后而前。高跟鞋响着清脆的韵律,好像告诉所有的看客:我来了,也好像在告诉人们言慧珠在此……”(15)她所期望的正是众星捧月的轰动效应,是凡俗大众难以企及的“神性”光环。然而,言慧珠难以割舍的名角意识和自我意识,终究在新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从戏里到杂外,从艺人到人民艺术家。在小白玉霜评传中,作者张慧这样描述她们去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的情形:“排队步行,一律八角帽,男的灰色中山装,女的列宁服……如果不是乐队的锣鼓乐器,看不出是唱戏的。”(16)“看不出是唱戏的”,似乎是淡淡的一笔,却寓示着这一群体从外形到精神面貌的脱胎换骨,也透露出八角帽、中山装、列宁服遮蔽下的旧日名角那种个体魅力的异变。
旧日的名角之所以被崇拜,恰在于他们在大众心目中是人间之“神”,他们的戏份充满了魅感力。河南洛阳曾流传过一段相声,描述新中国成立前常香玉演出的盛况。据说常香玉演出时有五种票:坐票、站票、挂票、趴票、飞票。坐票是指坐在中间的观众,站票即指站在四周观看的观众。此外,戏院内有许多立柱,有的观众因拥挤而不得不紧贴立柱站着,动弹不得,叫挂票;戏院外面的围墙和席棚之间有空隙,买不到票的观众便趴在围墙上顺着空隙观看,是谓趴票;飞票则是指那些无地方落脚、到处流动的看客。虽然未必尽属真实,这一描述却揭示了一个普遍现象,人们蜂拥去看常香玉的演出,出于自我选择,其目标指向则是常香玉的个人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自我选择被另外一种方式替代。1954年1月20日《戏剧报》刊登了常香玉的文章《一个演员最光荣和最幸福的日子》,同时配发了她在朝鲜某机场慰问志愿军演出的照片:常香玉穿着朴素的便装站在话筒前,对面则是整整齐齐、席地而坐的志愿军战士。志愿军以祖国、人民的名义出现在她面前,接受她的服务,并赋予她以光荣感和幸福感。此时,常香玉面对的不再是拥挤而混乱的场面,不再是戏迷的狂热崇拜,而是精心组织的集体行为,理性、克制的观看仪式。抗美援朝之时,举国掀起支援前线的热潮,常香玉率领剧团辗转巡演,以演出收入购置了一架飞机捐献给前线,该机后被命名为“香玉号”,她本人被授予“爱国艺人”称号,1952年的全国戏曲汇演中,常香玉同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等人一道获得荣誉大奖。此时的常香玉仍然被万众瞩目,但这种瞩目并非基于个体魅力和戏曲技艺,而是掺入更多的意识形态理念和政治热情。实际上,当时对文化名人宣传的舆论导向更多地凸显其社会意义。与此相对,电影界曾评选出二十二位明星,并于各大影院悬挂其照片作宣传,这一举动很快遭致了《人民日报》的批评:“做着千姿百态的演员群相……能对广大观众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应当极力去提高影片的思想内容,而不是去宣扬演员的个人形象。”(17)显然,对名角个体进行祛魅化,是当时新社会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尽管这些明星依然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但此时的他们已经不再凸显建立在个人魅力基础上的名角意识,而是更多地被作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表征符号。
《我的父亲梅兰芳》收录梅兰芳1955年1—5月的记事,可从一个侧面见出一位人民艺术家已经逐渐远离舞台的日常生活,现部分摘录如下:
2月3日:下午到国务院听总理做报告,主要关于我国被邀请参加联合国理事会问题。
2月19日:京剧院转文化部电话,拟请梅兰芳为地质会议全体会员晚会演出一场,日期约在三月初。
3月8日:中央卫生部电话,苏联卫生部长来华,要看梅兰芳的戏,可否演出?中直党委办公室电话,要求在下个季度演出一两场。
3月19日:中国教育工会北京市委员会来函——知道您拍摄工作很忙,为了热爱您的健康我们向会员解释,希望您拍摄完了暑假能够为教师演出一两场,以满足教师对您伟大艺术的热望。
3月20日晚:应邀到地质部赴宴……(18)记事中出现的报告、赴宴之类的活动纯属政治任务或应酬,真正的演出已减了不少,而且无论中直党委直截了当的“要求”、文化部委婉的“拟请”,还是中国教育工会貌似恳切的“热爱”,都隐含着政治话语的青睐,他们或代表机构组织,或打着人民的旗帜,规训这位昔日的伶界大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资源,为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服务,本真意义上的梅兰芳、作为名角的梅兰芳已然被湮没。
三、改戏:艺术权威性被消解
根据1951年《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于戏曲本身的改革在思想内容与舞台表现形式两个层面展开,在内容层面“必须革除有重要毒害的思想内容”,而在表演方法上则应“删除各种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成分”,可以说,“戏改”就是一场由上而下的“清污”(19)运动,其目的在于塑造起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戏曲形象,创立人民的新戏曲。
人民的新戏曲,首先要求内容上反映新时代、反映日新月异的新生活。对于戏曲与时代、与人民的脱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便在给《逼上梁山》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对戏曲舞台被“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20)的现象表达了不满;1948年11月,《人民日报》亦在其社论中以“对人民有利或有害”(21)为标尺评判戏曲内容,一旦戏曲被判定为有害或者害多而利少,面临的命运不是被禁演就是被大幅度修改,或者干脆被打入冷宫、不禁而禁,其中不乏各派名角的保留剧目,有些名角甚至因此而无戏可演。不可否认,“戏改”的确删除了传统戏曲诸多的杂芜之处,也出现过《贵妃醉酒》等成功的改戏案例,但政治意图的强势扩张带给戏曲更多的是扭曲和无奈,于是《玉堂春》中的苏三也翻新了唱词:“苏三离了洪洞县,急急忙忙去生产”……历史审视者看到的是滑稽和荒唐,而历史亲历者怀有的只能是难言的苦痛。新中国成立后的程砚秋享有保留私人剧团的“特权”,与梅兰芳一同作为戏曲界代表参加文代会和政协会议,入党,出任戏曲研究院领导,算得上风光,只是舞台上却少见他的身影,除了一部并不成功的《英台抗婚》,也未见有新戏推出。其时的程砚秋将精力主要投入于中国地方戏曲的考察,尤其是地方戏曲音乐,足迹遍布中南、西南、西北等地,还详细制定过一份《关于地方戏曲的调查计划》,一代名角似乎有向戏曲研究者转型的迹象。程砚秋之淡出舞台,有其自身因素——原本就身材高大,年过四十开始发福,舞台形象遭遇挑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仍然在于无戏可演。程派戏中既有侧重唱功的《武家坡》、《贺后骂殿》、《玉堂春》、《汾河湾》等青衣戏,也有《游龙戏凤》、《虹霓关》、《弓砚缘》等侧重于念白和武功的花旦、刀马旦戏,《荒山泪》、《春闺梦》、《锁麟囊》等戏更是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但在程砚秋供职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很多戏都不在上演计划之内。改编《英台抗婚》时,程砚秋受到当时红遍全国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启发,推翻最初展示梁、祝爱情悲剧的构想,突出英台的反抗,以配合当时形势,尤其是配合《婚姻法》的宣传,借此向“人民戏曲”靠拢,可谓用心良苦,但剧本呈交后便杳无下文。对于文化主管部门的盲目干涉和改戏,程砚秋表示过相当的不满,甚至称“戏改处”为“戏宰处”。
程砚秋并非那个时代的特例,与其遭遇类似的还有周信芳。上海解放后,周信芳曾在上海市军管处、市政府任职,担任过戏改处处长、文艺处处长,但他不止一次地将自己工作的华东戏曲研究院称为“养老院”。周信芳当时月工资两千元,是特高收入,但拿高薪却不演戏,这对于享誉四方的麒麟童绝非享受,他曾言道:“卖艺卖艺,无艺不卖,不卖无艺。”(22)“不卖无艺”,一语道出这位名角对艺术前景的忧虑。正是基于这种忧虑,周信芳开始积极创编新戏,如《义责王魁》、《文天祥》、《海瑞上书》、《杨立贝》,并竭力于剧中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求获得审核通过,并遵命排演了《澶渊之盟》。审视这些剧作,或者主题外露,或者情节堆砌,完全不见麒派风韵;只有《义责王魁》尚属可取,其他都为应景之作、昙花一现。
当时的人民文艺工作者,不仅在剧作内容改编上谨小慎微,在表演形式上也如履薄冰。1951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少波的文章《清除病态、丑恶、歪曲的舞台形象》。马少波时任文化部戏改局书记。该文章无疑是在以一级党组织领导人的身份行使戏曲表演领域里的领导权,于是跷功、喷火等技艺被迫退出舞台,云手、卧鱼、鹞子翻身、踢腿、蹉步等也因缺乏确定的意旨被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在强势的意识形态话语驱使下,戏曲的技能、技艺层面受到极大的压制,不得不将重心挪移至意义层面,而这恰恰不是这些旧日名角所擅长的,于是筱翠花、水上漂等身怀绝技的名角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沦为边缘性存在,他们所承载的艺术符号,也无奈地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小白玉霜曾经在《老妈开唠》中运用过“嗙调”,该曲调活泼欢快,很适合表现男女之间的情感,但这一腔调遭到了马少波的批评。当得到排演《小女婿》一戏的任务时,小白玉霜试图再次运用这一腔调传达男女定情的信息,却又顾虑重重。原本挥洒自如、神采飞扬的名角在舞台上变得迟疑、缩手缩脚。
在舞台形式改革中,名角的艺术创造空间不仅遭受政治意识的侵蚀,还面临盲目西化思潮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的国营剧团大量采用苏联戏剧模式,音乐、舞美、服装、化妆等部门齐全,看似先进、完备的配置对戏曲本身却未必是幸事。
譬如舞台布景。传统戏曲一桌二椅,别无他物,反而给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无限空间。但随着斯坦尼体系正宗地位的确立,写实布景日渐成为舞台的主导倾向,戏曲亦被裹挟到这一潮流中。50年代北京排《雪花飘》时,不仅舞台布景是写实的,还制作了逼真的雪花作为主要道具。面对如此设置,主演裘盛荣大惑不解——所有细节都堆积到舞台上,还要他干什么?裘盛荣的疑惑显示出中国戏曲美学同西方话剧思维的深刻差异,布景只是诸多矛盾中的一例。
还有伴奏问题。在“戏改”中,新式乐队取代“场面”,演员亦无所适从。一个曾经获得过嘉奖的楚剧演员便说过:现在我们是外行,从前是场面听我的,现在我是要听乐队指挥的(23)。再有,之前艺人与琴师是直接、固定的搭配,双方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默契,不仅相得益彰,更直接促动了新腔的创造。评剧乐队原本使用河北梆子的体制、以实心的枣木梆子打节拍,但河北梆子用假嗓、唱腔高亢,以实心梆子伴奏很恰当,而评剧则是用真嗓,唱腔与乐队不协调是一大弊端。当年,喜彩莲与小白玉霜两大名角在上海打擂台,为了不逊色于如日中天的小白玉霜,她苦思乐队的改良之法,后从叫卖食物的梆子声中得到启示,在合作者李小舫的帮助下改用空心的榆木梆子伴奏——这种梆子声音柔和、调门低,与评剧的唱腔很相配,由此评剧伴奏大为改观。越剧界的袁雪芬在演出南薇编导的《香妃》时,为塑造宁死不屈的香妃形象,同琴师周宝才一起创造了“尺调腔”,这种善于表现悲愤与反抗情绪的新腔,一经唱出便被广泛传播,至今仍然是越剧的基本腔调。之后,范瑞娟、袁雪芬合作成立“雪声剧团”,在加工《梁祝哀史》这部老戏时,范瑞娟借鉴京剧反二黄创造了越剧的“弦下调”,当中亦包含了琴师的功绩。
戏曲以“歌舞演故事”,唱、念、做、打四功中唱居首,说明其在戏曲中的关键地位。唱腔,不仅是演员个人的行为,还是与琴师水乳交融的结果。在流派的划分中,唱腔也是根本性因素。位列四小旦的张君秋拜师于梅兰芳,并受到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的指点,可谓博采众家之长,但张君秋真正自成一家当从《望江亭》开始。剧中张君秋的“四平调”既是京剧又有新意,观众既熟悉又陌生,结尾的甩腔令人叹服,十六句的“南梆子”一气呵成,被公认为张派的奠基之作。在这次创新中,琴师何顺信借鉴京剧生行伴奏常用的“唱简拉繁”(24)法(如为杨宝森操琴的杨宝忠,其京胡取法西洋的小提琴,擅演音符繁密、快速的曲调),用繁密的京胡将张君秋的唱腔包裹起来,使其唱腔中特有的蜻蜓点水式风格更为突出,而张君秋本人亦常说他的成功,得益于何顺信的功夫。但所有这些,随着大乐队的通行不复存在。
其实,戏曲改革并非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小白玉霜等名角早已自觉探索过多年,他们自身亦是凭借不懈的革新成为“角儿”,奠定了其在戏剧界的权威地位。但是由新政权发起的、政治意图鲜明的“戏改”运动,却在诸多层面上剥夺了艺人的话语权,无论梅兰芳“移步不换形”的委婉表述,还是程砚秋“戏宰”的慷慨直陈,都表达了一种失去主导权的无奈,也奏响了名角消亡的哀歌。
注释:
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
②上海市文史研究室编《京剧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0页。
③张慧、曹其敏:《清新隽雅——喜彩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④⑦沈祖安主编《书剑传芳录——吴剑芳艺术人生》(内部资料),藏于浙江图书馆,2010年印制,第126页,第150页。
⑤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⑥朱继彭:《坤伶皇座——童芷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⑧(15)章诒和:《伶人往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第44页。
⑨吴祖光:《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⑩田汉:《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载《戏曲报》第3卷第12期(1951年)。
(11)俞慕古:《上海人与梅兰芳》,载《申报》1923年12月2日。
(12)参见1946年8月20日《申报》选举“平剧皇后”。
(13)王晓华:《明星崇拜现象与信仰的一种转向》,载《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5期。
(14)梅兰芳:《我们所演的戏剧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1页。
(16)张慧:《芳菲永驻——小白玉霜》,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17)《悬挂演员大照片起什么作用》,载《人民日报》1964年10月30日。
(18)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续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
(19)马少波:《清除病态、丑恶、歪曲的舞台形象》,载《人民日报》1951年9月27日。
(20)《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页。
(21)《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载《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3日社论。
(22)翁思再主编《矛盾的周信芳》,《京剧丛谈百年录》,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6页。
(23)田汉:《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田汉全集》第1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24)安志强:《张君秋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