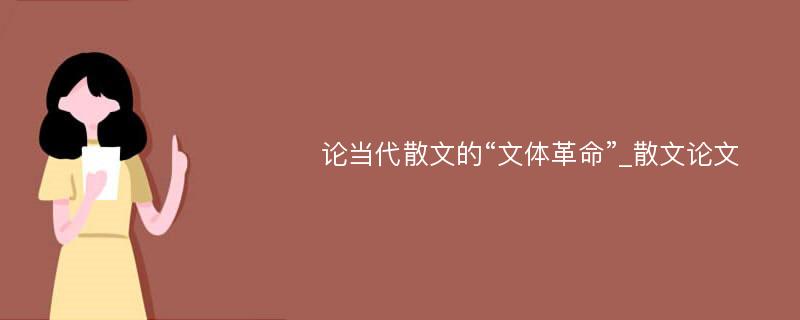
论当代散文的“文体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时期散文艺术变革潮涌概观
不可遏止的散文变革潮涌,起始于80年代中期,繁盛并持续高涨于90年代。这一散文变革潮涌,在主要由老一辈散文家完成并对当代散文模式的多向度破除和旧根基清理的基础上,得益于新时期小说、诗歌等文体变革发展的夺人先声及自身内部锐利理论反省的多元推动,还有在更高的时代基点上对五四散文传统的延续承接,对域外现代文学潮流、作家影响接受的视界开放和为我“拿来”。它以作者队伍的空前壮大,“散文热”的持续升温,一大批青年散文作家的不断涌现,散文变革向度的多元展开(尤其是文化反思的深入、主体人格强健厚实的追求,感觉、情绪和意识流的凸现),散文文体意识的自觉强化为标志,“后发制人”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
显然,如果说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散文,主要表现从政治反思进而深入到文化,并基本达成了与“五四”散文传统的承续连接,那么,80年代中期以后的散文变革潮涌,在基本思想内涵和价值意向上,则表现出文化反思的进一步深入:人生主题热、主体人格重建意向的凸现等;而在散文艺术的发展上,则突出表现为散文自身文体意识和变革意识的全觉醒,表现为一场“散文文体革命”的方兴未艾。
散文变革潮涌的先声和征兆,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几位女性散文作者对独特感觉的体味和表达。1984年底,唐敏的《怀念黄昏》、苏叶的《总是难忘》等作品,以清新婉致、略带伤感、融抒情与叙事为一体的体验性笔调,展现出一个清新纯美、充溢人性温情的女性心灵世界。王英琦从追随旧散文模式的“叙事—议论—抒情”格局中逐渐摆脱出来,以袒露心胸、放言无忌的粗糙“大白话”,客观上对以往散文清醒理性、明白无误的语体形成了冲击力。叶梦的《羞女山》,凸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把社会、历史层面的反封建和文化反思的主题,深入到女性意识的心灵深处而加以完成,使同类主题的表现有了迥乎往常的突破。以唐敏、苏叶、叶梦、斯好、张抗抗、筱敏等为代表,一个阵容强大、以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感性创造力的丰富为特色的女性散文群呈集团军态势独领风骚于散文文坛,这也是散文变革潮涌的重要组成。此间,伴随着时代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生,中西文化冲突、思维方式变革、“新方法论”热潮的崛起,一批实际上为文化、科学、艺术随笔的“亚散文”,也因其思想的新颖、深刻,而格外引人瞩目。
曹明华首创了散文中的“青春独白体”方式,这种“曹明华体”散文的个体情绪性的强化、“发散式思维方式”导致的散文结构的随意自如的开放性,对当代散文传统构成了强劲的冲击与巨大的断裂。曹明华的崛起,也带动了此后一大批“新生代”散文作者群体的涌现:王开林、骆爽、老愚、程士庆等男性作家,戴露、胡晓梦、元元、黄一鸾、于君、冯秋子、桑桑等女性作者,一时灿若星辰。
以刘烨园、赵玫、周佩红、张立勤等为代表的、具有自觉散文革新意识,向着感觉、情绪、意识流领域全面开放,被人称为“新散文”或“朦胧散文”的一支散文变革流向,也是极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他们有扎实的文学创作经历和比较自觉的理论思考,切合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潮流而发现了一个现代人丰富、复杂、无定型的内心世界。他们大多是知青一代作家,有着痛切的个人经历、细致的情感体验和深刻的人生感喟,但见之于散文,却是以意识流动的方式,朦胧诗化的语言,倾诉独白与理性控制的张弛有度而表现出来的。
以余秋雨、周涛、张承志等为代表的散文革新流向,代表了当代散文文化反思主题的最新高度与主体人格重建的深远指向。余秋雨对传统文化负累“含泪告别”的理性批判精神,对边缘性的“贬官文化”的阐扬,对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批判性重构;周涛、张承志的边缘文化意识和人格重建理想;张承志、史铁生对“理想主义”、“家园意识”、终极关怀与自我救赎的热情执着,都堪称达到了时代文化精神的最前锋。在艺术上,他们的散文体现出来的“大品”意识、“大散文”气度,更是作为对多年散文平庸、柔弱、琐屑之积弊的超越而无愧为散文变革中最成熟厚重的成果。
一批本来驰骋于诗歌、小说创作或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领域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学者教授的入盟散文创作队伍,其人数之多、作品数量之丰、质量之精,无疑是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坛一个独特的重要现象。这一支散文创作“新军”的入盟,与原有的庞大散文队伍相聚合,构成了散文变革潮涌的开放式格局。散文在他们的笔下变得丰富多彩、深蕴厚实而潇洒灵动。他们以开阔的视野、凝重的思想厚度、深刻的人生体悟和不拘一格的行文气势,为散文变革潮涌增添了厚实坚固的力量。
与大批学者、评论家、教授的入盟散文创作相应,是“随笔热”的勃兴。当然,对“随笔”这一基本从属于散文这一大的文类概念,其本身却跟散文一样缺少严格界定也很难严格界定的文体样式,我们宜作客观冷静的分析。“随笔”(essay)的命名来自1580年法国散文家蒙田。按M·H·艾拉姆斯的看法,“蒙田的命名里意味着一种‘尝试’,旨在表明他在论述和同议题的正规及学术性论著对比之下所表现出的探索性与非正规性”(注: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因此,随笔作为散文的一种形式,具有体式上自由随意、率意而谈的特点,思想内涵上则往往追求容量大、信息密度厚、哲理意味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随笔热”中,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等老学者、老作家,历尽沧桑,读遍诗书,老当益壮,笔耕不辍。他们的文章文笔老到,已渐臻“无技巧”的浑融之境:邵燕祥、李国文、韩少功、吴亮、朱大可等的“学者随笔”,也观古照今、纵横议论而挥洒自如,或针贬时弊,寓意深沉,或游戏智慧,给人以纯思想的超妙感受。“学者随笔”的兴盛,丰富充实了新时期散文大家庭。承续了西方以蒙田、培根、兰姆等为代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以林语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随笔传统。
此外,苇岸、曹晓东、洪磊等人的散文还透露了向“后现代主义小说”等先锋文学领域借鉴、转化的文体革命意向。或是“现象学还原”的观感方式,或是扑朔迷离的叙述游戏……
这表明了一种不可遏止的散文“文体革命”的意向: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体,乃至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文体。代表一时代之文学实绩的标准,或代表一个作家对文学的贡献,总得看它或他为时代贡献出怎样的独特文学文体。
从根本上说,文体应理解为特定时代特定作家之特定的艺术地把握生活的方式。它不仅仅是语言形式、文本结构和语言表达诸方面的内容。也包括作家主体的人格与精神。别林斯基在论述文体时曾指出:“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注:《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34页。)
因此,正如古人云:“文起八代之衰”。文学中的文体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或形式的问题。它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是主体精神新觉醒新发展的标志,是主体与新的对象交互作用、结合,以实现“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语)的产物。
在新时期文学中,散文文体意识的觉醒,比之于小说和诗歌乃至话剧,都明显地慢了几个节拍。这里散文的不幸与可悲——但换一个角度说,姗姗来迟的散文“革命”恰恰因为足以放眼并汲取兄弟文学体裁“文体革命”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而占据更为有利的时代制高点。从新时期散文本身的发展来说,主要滥觞于老年和中年散文家的对“说真话”、写“真情实感”的强调,以及对“形散神不散”这一流传甚广、几乎成为中国当代散文之“先验神话”的散文定义的争论和诘难,都历史性地完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清理散文文体旧的理论基地的工作,具有文体意识上功不可没的拨乱反正的意义。
二、艺术思维的新变与拓展
文体应理解为特定时代作家之特定的艺术地把握生活的方式。因此,文体的变革,实质上是一个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思维的变革问题。正是因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变异,作家主体才得以与审美对象形成新的“对象化”方式,在主客体之间建立起新的有机的联系。
当代散文“文体革命”表现在创作艺术思维的新变与拓展上,有如下两个方面:
1.抒情的放逐:从热抒情到冷抒情和零度抒情
“抒情”历来被认为是散文文体的“正宗”和根本。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片面强调抒情,也容易作茧自缚,使散文的路子越来越窄。
事实上,情感并非人的真实生活的全部,人也并非无时无刻不处于抒情的状态。而文学(或者说散文)中的抒情,似乎总得选取高强度的情感。如果缺少,那恐怕只得“为文造情”了,故而免不了对平常情感状态的集中和夸饰。久而久之,抒情成为一种空洞的姿态和丝毫不能让人动真情的老调重弹,成为一种虚假的渲泄和再现。人生更真实、普泛的其他生存状态,被单向度的夸饰性抒情排斥了。从这个角度说,建国以来到“文革”期间散文路子愈走愈窄的重要症结就是太重抒情,感情越抒越浮泛、机械、单调而夸饰,离人生之真情性愈来愈远,有的甚至成为毫无个性之真情实感的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时至80年代中晚期,这一类题材平庸、思想苍白、感情浮泛的散文仍流行于文坛,这无疑阻碍了新时期散文的发展。
故而,当代散文“文体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放逐”抒情。打破“事(人)——情——理”的呆板的艺术思维模式。
一种是由单向度的、单一型的“物——情——理”抒情模式。而向着以情绪为主调(有时是以“独白”的方式)、以艺术感觉为基础,叙述与抒情在文内揉为一体,难分彼此的复合型抒情方式转化。在《心中的大自然》中,贯穿始终的是女性心灵特有的良善、细腻、热爱自然的感觉和体验,含而不露的真情在体验性和感觉化了的叙述文字中引而不发、张力内蓄。抒情不再游离于“物”、游离于叙述和描写;一批“青春独白体”散文虽然因其“青春”,实难以逃脱“抒情”,但因通篇以独白式的意识流动为结构框架,作者面对自己的探询和驳诘,使得一种内省式的复杂语态代替了音调、夸饰性的抒情语态。情绪的循环往复,自我追问的内迫紧张,语言节奏的潇洒随意,行云流水,都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抒情”(如果还叫抒情的话)方式。
其二,是由夸饰性的高强度的热抒情,向着不动声色极力节制情感泛滥的冷抒情过渡。更有甚者,在某些探索性散文中,作为抒情主体符号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竟至于消失了。从容不迫、恢宏大度的全知视角使一种与传统散文观相悖甚远的“零度抒情”方式成为某种可能。在张承志、周涛的散文中,有理性的高扬和学者型的思想,沉郁苍凉,极为有效地抑制了感情的虚浮与泛滥;楼肇明惯用不动声色的反讽性笔调,以一个清醒看客的不无悲悯的眼光,调侃、戏谑,解构批判习以为常的平庸和俗世。在放逐感情向度上走得更远的是苇岸、钟鸣、曹晓冬等新生代散文家。苇岸让“大地上的事情”还原和自我呈现,完全剥除消解了主体强加于客体的种种臆想和象征情感内涵,客观事件独立自足的物性,让每一个文化人都足以震惊;钟鸣则沉湎于史料和知识的勾沉和游戏性串接,仿佛是一个智慧的老人,有条不紊、顺手拈来地说古道今,隐隐的、让人费神的影射和譬喻,让人玩味再三,沉吟不已;曹晓冬在一个类似于弥诺斯迷宫的臆想国里,灵魂出世,飘飘梦游。“梦游”过程本身的迷离恍惚、似真似幻已足够吸引你,更无暇让人去抒情写意。
2.象征的离异:重建主客体关系
要抒情,必得寻找抒情对象,“寻找客观对应物”(艾略特语)。主体一意寻找对象而状物写意,托物言志,这是“抒情散文”的一个重要构思模式,此亦即建国以来散文创作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事(人)——情——理”思维及结构的模式。这种“象征式”思维模式,其实隐含着一种不乏粗暴、武断的思维方式——主体膨胀。高高凌驾于自然万物,主观武断地任意将自然对象纳入自己的象征体系,使万物绝对因“我”而存在、完全剥夺了万物客观自足的物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无疑是一次认识方式上的重要革命。“现象学”主张把所有主观的、额外的、先验的理性判断和价值规范都“悬搁”起来,力图为科学寻到一种没有任何先人之见和超验之物的纯粹的本原客体。这一理论对法国“新小说”的影响有目共睹。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后现代派小说”、“新写实小说”及“第三代诗歌”都有较明显的“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的表现向度。在散文中,这一倾向则明显慢了一个节拍,阵势也不如在小说诗歌中来得浩大,但这一倾向代表了散文艺术思维新变的一个重要向度。
这种追求向度,在唐敏最早的《怀念黄昏》、《心中的大自然》、《花的九重塔》等作品中已有所体现。在这些作品中,“大自然”虽仍然是通过一个“我”的“心”去“看”到的,但这里的“看”,与其说多了一分敬畏和体悟的成份,更毋宁说是类似于海德格尔主张的“倾听”(注:海德格尔主张对“存在”的“倾听”状态。他说,“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去‘倾听’,‘倾听’使我们超逾所有传统习见的樊篱,进入更为开阔的领域”(《诗·语言·思》))。黄昏、鹰、老虎虹、“七叶一枝花”……在作者清新温婉的体验性笔致中,仿佛各具自己的生命力和不乏神秘的灵性。象征的蕴含仍有,但却极为含蓄、朦胧,绝不实指,作者更不提示。显然,在唐敏的笔下,大自然成为需要我们平等地、甚至“心中恐惧而敬畏”(《花的九重塔》)地感受,去体悟和“倾听”的自然神性,而不是可以随意拉扯来比附类推,“万物皆备于我”的隐喻象征客体。
苇岸的散文因为这种自觉追求及在文本中的成功实践,而在当前散文中自成一家,格外引人注目。苇岸在其散文艺术世界中展示了一种久被我们所忽略甚至麻木纯化而遗忘了的大自然景观,这种沉静、神秘、充溢灵性的内在呈现,不禁使我们麻木了的审美知觉倍感“陌生”和“震惊”。正如他在《美丽的嘉荫》中写道:“踏上嘉荫的土地,我便被它的天空和云震动了。这里仿佛是一个尚未启用的世界,我所置身的空间纯粹、明澈、悠远,事物以初始的原色朗朗呈现。”
显然,苇岸试图建立(或者说是恢复)一种新的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正如他在《放蜂人》中写道:
放蜂人在自然的核心,他与自然一体的宁静神情,表现他便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与自然最古老的一种关系。只是如他恐惧的那样,这种关系,在今天的人类手里,正渐渐逝去。
在这里,“放蜂人”的恐惧和担忧,不正是苇岸自己的夫子自道吗?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注:《庄子外篇·知北游》。)面对自然的坦荡无言、博大宽宏和深邃神秘,似乎唯有静观、悟道与“倾听”才是充分明智的举措。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不无“浮躁”的社会转型年代,苇岸的恐惧和担忧,应是不无道理的。这类新潮散文独具重建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深远意向,其形而上意义是耐人寻味的。
三、“向内转”:感觉、情绪和意识流动
从某个角度说,建国以后散文走的是一条高度理性化的路子,无论是自我人格萎缩、“大我”压倒“小我”的“时代主题”的绝对先行,还是“形散神不散”发展到极致的“事——情——理”结构模式,抑或准确表达,近乎“科学文体”的语体风格。在大部分散文中,作为散文主体的人的丰富复杂的人生情感状态,诸如微妙的感觉、无定型的情绪和意识流等,都被放逐抽空了。我们很难从中真正体味到作者的真实人格和复杂深刻的人本心理世界。即使到了新时期,也因“解冻”之初,人们更为关心的是“说什么”和“写什么”的问题,因此,较好地解决这一“说什么”问题的关于“讲真话”的讨论,也没能触及“怎么说”(即文体和表达)的更具散文文体论意味的重要课题。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深化,是一个“向内转”的过程,即逐步确立人在文学中的主体性地位,从对社会现实表面的描摹反映转向对人本深处之心态、精神、意识的表现。自然,这种表现带来了语体风格、文本结构、表现方式等一系列文学文体要素的变化,导致新时期文学“文体革命”的持续进行。比之于小说与诗歌,散文的“向内转”姗姗来迟,直至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向内转”趋势才愈益清晰。
首先,是长期禁锢的感觉得到了全方位的开放。
感觉是人的一种重要情感状态。按西方感觉学大师马赫的话说,感觉甚至是“第一性的存在”(注:马赫《感觉的分析》。)。落实到文学创作的层面,它无疑是艺术思维的起点和基础。艺术感觉是否敏锐独特,是区分作家才能禀性之高下的重要标准。恰如别林斯基说:“(作家)他的本能,朦胧的、不自觉的感觉,那是常常构成天才本性的全部力量的。”(注:《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420页。)而对于散文创作来说,感觉尤其显得重要。这是由于散文一般系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常不脱于“我”的自知视角,它一般不像小说那样叙事虚构(某些走得较远的实验性新潮散文除外),也不像诗歌那样以假定性的艺术思维方式想象抒情。
新时期后期散文变革潮流向感觉的开放,最初以唐敏、苏叶等人的一系列散文首开先河。《怀念黄昏》、《女孩子的花》、《心中的大自然》、《总是难忘》等作品,均以清新温婉的笔致,拓开了一个奇妙的充溢女性感觉的艺术天地。而后,以一大批女性散文作家为突出代表,赵玫、周佩红、黑孩、张立勤、黄一鸾、于君、胡晓梦等串起了一条开放的感觉之河。
赵玫在对散文进行理论反思的文章《我的当代散文观》(注:《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里,一连用了十八个“能不能”来多方面悬似散文写作的新的可能与出路,而首当其冲的第一个“能不能”就是感觉问题:“能不能把那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感觉堆砌起来?”她的散文,则几乎是一个心中滴血,“有着彻骨的疼痛感觉”的女性之焦灼、痛楚的娓娓叙说,大量密集的细腻感觉,伴随意识的流动奔涌而来,给人以触及生理的强劲的心灵冲击。黑孩更以写出个人化的独特感觉而著称。尤其在视觉与通感方面,她已将一般情况下形容词之间“一对一”的转换,扩展到了动词的种种延伸义和转换义的“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复合型感觉转换之中,从而体现出人的感官的全面解放和开放。比如:“我看见有一股湿漉漉的情绪开始穿过极微弱的一线月光扑向我”(《醉寨》)。“我感觉一股冰冷的气息涌遍我的全身,我知道这是河水不知为什么神秘地流到我的心里来了”(同上)。“熟悉的笑声有滋有味地穿过了我的肠子……”(《我家乡的秋子》。黑孩的独特的“感觉才能”(汪曾祺评价),竟把许多抽象的心理状态通过视觉、通感等方式,转化为具体形象可感可触的生理感觉状态。
感觉在一些男性散文作家中,又表现为有异于“女性感觉”的形态。显然,男性感觉与女性感觉是有差异的。“男性更倾向于对外部世界的感觉,而女性更倾向于对内心世界的感觉。男性擅长于粗线条的整体感觉,而女性的拿手好戏是对某一局部和细节的细致入微的感觉”,“男性容易理性化,女性则很难摆脱情感性”(注:曹文轩《思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刘烨园散文以密集的理性思考取胜,但也不乏精细的感觉,而他的感觉是指向外部理性世界的。在《自己的夜晚》中,他写自己在一个夜晚里凝神暇思,进行着“精神上来去总是孤独”的漫游。漫游是从精细的感觉开始的:“地气,像夜色一般潮湿。这时,它和绿色植物被的生命气息混融在一起,凉凉地弥漫开来。周围的山野暗得清晰……”在这里,精细的感觉,承载起现实与幻觉的互融状态,打开了外部世界进入内心世界的大门。
楼肇明同样以理性思考见长,他较早将理性思考的触须探入现代人的惶惑、荒诞、异化等生存境况,但他的散文如果缺少了种种密集呈现于其散文语言中的独特感觉,思想的展开和表达将是突兀苍白的。
感觉在变革散文潮流的不断丰富和开拓意义甚大。就散文艺术本身而言,它拓开了一个新的感觉艺术的世界,并以此为契机,诱发了散文文体(语体、结构)诸方面的深刻变革。
情绪的大面积喧哗与意识的无定型流动,是散文变革潮涌的一个重要现象,鲜明地表征了散文“向内转”的总体趋向。许多散文,完全打破叙事、议论、抒情的严格界限,而让远离理性域的意绪的奔涌、情绪的喧哗、意识的流动等心理内容占据散文的前台。常表现为以原发性的自由联想结构散文,呈现为无拘无束的流动型结构、时间、空间的大幅度游移跳跃,大量的内心独白和极少的过度性连接性叙述语言等特点。
张承志的小说,曾在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潮涌中独树一帜。及至转入80年代中期以后,张承志浓郁悲烈的情绪氛围和抒情风格一以贯之,同样独领风骚。骚动不宁的永恒“精神长旅”之追求,起伏跌宕的思绪、苍凉雄浑的诗化风格,都使张承志的散文成为他的“一种放任的精神流浪”(注:张月志《放浪于幻路》。),灵魂的自考自问自叙状。如他的《北庄的雪景》,作品已不再追求头尾完整的叙事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流贯其中的“感觉结构”:大雪迷,一派大静,只有他们乘坐的车在宁静中行驶,一幅幅“惨烈”而“寂静”的雪景,如蒙太奇般闪现、转换。
张立勤常常跟着情绪与感觉顺势成文,着力于情绪与感觉的飘忽跳荡和闪烁不定的拼贴,从而“拼贴出一种虚晃晃的意蕴”。周佩红“充分地感受,充分地体验”(《偶然进入的空间》)现实生活。她用自己源于生活和人生的感受、体验的真切、情绪的奔涌、意识的流动,构成灵动飘忽的散文整体。
由此可见,源自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意识流手法,已经在变革散文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作家利用它来表现主体的心理活动的范围和过程,在这一过程里,人的感觉、经验情绪与意识的或半意识的思想、回忆、期望、感情和琐碎的联想都融合交杂在一起,这就极大地扩展了散文的艺术表现领域。当然,新时期小说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也很类似。而散文中对“意识流”手法的借用,也有一个“东方化”的过程。很明显,比之于詹姆斯·乔伊斯、维吉妮亚·沃尔夫等的“正宗”意识流手法对潜意识、非理性意识活动的全面表现,变革散文中则更多地表现与现实关系较为密切的显意识领域,我们甚至不难从中读出作者理性控制的强大力量,感觉出作者绝对清醒的主体创作状态。
不确定的情绪的飘忽与喧哗,在更为年轻的“新生代”散文作者中表现得最为集中突出,甚至从曹明华开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一定文体独立性的“青春独白体”的散文体式。这种“青春独白体”,有点像戏剧里的人物,进行“一种默默地或大声地自言自语”,“单独地站在戏台上,将他的想法大声地说出来”。显然,这种“能便利地直接传达给观众关于某一人物的动机、意图、心理状态”(注: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第333页“独马(Soliloquy)”条。),带有一定的泻泄、倾诉和释放味道的“独白”,更为切合年轻作者们的青春心态。于是它不再四平八稳、有条不紊地叙述或描写,甚至也无暇像赵玫、周佩红她们那样细细地咀嚼、感受心灵的创作和痛苦,而是一变而为一种抒情的浩叹和絮絮的倾诉,听任情绪的一泻无余。在这种以情绪占据本文前台的散文中,具体可感实在的现实生活退居幕后,外部世界往往只是因为触动引发了情绪而有其存在的意义,唯有情绪的波动起伏和流向是作品的进展状态和结构本身。
散文面向感觉的开放,向人本心理深处的掘进,情绪、意识流动状态的强化等趋向,不但拓开了新的表现领域,更有着极为重要的文体革新意义,这一“向内转”趋向已经引发了散文文体众多因素乃至整个系统的全方位的革命性变异。
首先是语体的变异。新时期散文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仍延续了当代散文的语体风格:说明性叙述语言,即追求说明、叙述的清晰准确,句子结构的完整、规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确如某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以其只持有平面性表层结构和说明性叙述语言向科学文体(论文、说明文、史传等)认同,并因此获得了科学文体的一般风格:简单、明了但又往往是枯燥的准确”。这种几十年一贯的有些呆板的“正体”,在散文变革潮涌中面临瓦解。“向内转”带来的语言表达的内心化和感觉化、情绪化,使散文语言灵动活跃起来。或者是如“朦胧散文”及许多“女性散文”那样,出于内心的复杂、隐晦,感受的细腻、深致,而呈现出含蓄、朦胧、飘忽诗化的言语状态;或者是如“新生代”的“青春独白体”散文那样,以轻倩别致的抒情性口语,随思而言,脱口而出,节奏轻快自然,语调婉转潇洒,呈现为空间性的话语视角,快节奏的独白性倾诉和多向度的情绪流辐射。
再者,在散文的言语组织、语段转换及整体结构方式等方面,“向内转”的散文往往因为心灵性的占据主导地位而显得随意、开放,表现为散漫性、非逻辑性和非完整性。许多语段或意象在外在形式上根本连接不起来,而靠流贯于其中的意绪来串接。而由于追求与心灵更为对应接近的言语形式,因此往往通篇都由流利灵动、相对完整独立的散句构成。有时甚至一句话或一个词就是一个自然段。此外,打破惯常语法规则,非常规的词语组合、词性转换、褒贬颠倒的修辞方式,都绝不鲜见。在结构上,这些散文大多以主体人为中心、以心灵世界为基点,以人的情感流动和情绪的渲泄为隐约线索,心理时间取代了线性物理时间,因而经常表现为无所谓开头,无所谓结尾的首尾全开放式的特点,往往开头即波澜乍起、先声夺人,结束则戛然而止,余韵悠悠。
当代散文的“文体革命”意向当然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事实上,上述所论及的只是最为集中突出且较易为散文理论所接受的几个方面。“变革散文”所表现出来的另外一些较为冷僻,且与旧散文观念冲突相悖得最为激烈的意向,诸如“虚构”与“想象”成为散文的主导构思创作方式,“隐含作者”与叙述者“我”的分离,散文作者主体人格的隐遁,“叙述”在散文中的日益显得重要乃至叙述游戏的成为可能……等等,因为它们还有待更为坚实的作品的发表和时间的检验,在此只得暂付阙如,等待并寻找更适当的时机再作评述。
标签: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文体论文; 革命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意识流论文; 张承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