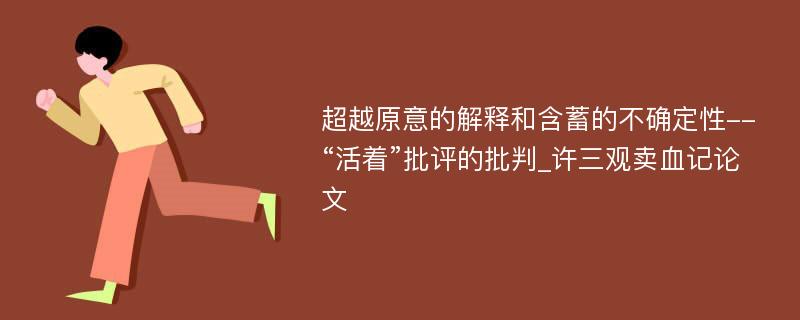
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意蕴论文,原意论文,不确定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3-0090-05
正题:原意阐释
根据题目的设定,作者的原意阐释为正题。正题是本文逻辑理路的起点,且先入正题。
余华是一位不回避对自己的小说作本意阐释的作家,在作品解读方面,他有着异乎寻常的领悟天赋与理性言说的才能。他对他的主要作品差不多都作过解释,有的三语两语,有的专文解说,甚者则一而再、再而三的论及。从情感的力度和阐释的深度来看,他最倾情的小说无疑是《活着》。他对《活着》的本意阐释不是最多,明显少于《许三观卖血记》,但却是最到位最深思熟虑的,所言所论均落到实处。相比较而言,对《许三观卖血记》的阐释常往虚里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福贵和许三观是余华的至爱,在两者之间,他从不作优劣高下之分的价值判断。感受体会余华的阐释文本,是不难触摸到不同的情感温度的。
且先看余华的原意阐释:
《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注:余华:《活着·前言》,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页。)
这一表述可视为《活着》的原意阐释的标准文本。活着就是承受苦难并且与苦难共生共存: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注: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224页。)面对所有的苦难,每个人都应该高兴愉快地去尝试克服、度过它。(注: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224页。)
活着是对生命的尊重:福贵是属于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了。他不需要有其它的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他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是我见到的这个世界上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注: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136页。)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理由发出“活着”的声音,最有理由说他“活着”的一个人。
概而言之,《活着》的原意阐释的思想核心最终可以落实到一句话上,那就是“活着就在活着本身”。尽管余华说《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绝望的不存在”、“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尽管他一再表白《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它讲述了作者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事物,一部作品完成之后,作者也成了读者,这时,“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注: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136页。)可批评家们认准的还是“活着就在活着本身”这一解释。应该看到,余华的原意阐释是不包含这些内容的,这些表白是他在原意阐释之外所作的补充说明。
反题:超越原意阐释的否定性批评
相对于“原意阐释之阐释”,超越原意阐释的否定性批评晚起,到目前为止,以张梦阳和夏中义、富华的批评为代表。
反题1 张梦阳在论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的一篇文章中立论:从阿Q到许三观,贯穿着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和思维方式。”在这个理论语境中,他分析了当代众多小说,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是其中作为重点深论的两部长篇小说。他先将《活着》与《阿Q正传》比较,认为《活着》集中笔力雕刻福贵 ,在表现人物精神上“实现了突破”。福贵继承并凸现了阿Q的乐天精神,说明我们中 国人这几十年以至几千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是怎样乐天地忍受着种种苦难,坚忍地“活着”的。正是本根于这种精神,阿Q才没有发疯或自杀,福贵也没有跟随他所有的亲人 一道去死。《活着》称得上是一部“洋溢着象征”的真正的小说,福贵乐天地“活着” 的精神是一种“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与阿Q相比“差距甚大”。其中症结在于:鲁迅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主要采取批判的态度,深刻揭示了它负面的消极作用,让人引以为鉴,克服自身类似的弱点。余华对福贵乐天地“活着”的精神主要采取赞颂的态度,对其负面的消极因素缺乏深掘。
这一比较是《活着》与文学大师的经典之作之比,点到为止,但高下优劣立见。接着又让《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相比,从《许三观卖血记》的创获中反照《活着》之不足。《许三观卖血记》是《活着》的深化,是余华朝前迈进的一大步。作家通过许三观这个典型形象,从与阿Q既同又异的另一个更为具象、更为残酷的视角批判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与精神机制。所谓“求诸内”就是拒斥对外界现实的追求与创造,一味向内心退缩,制造种种虚设的理由求得心理的平衡。《许三观卖血记》比《活着》深刻之处,“正在于对许三观‘求诸内’负面消极性进行了异常深刻的批判,却又没有采取贬斥、嘲笑的态度,令人从许三观的失败和固执中感受到他是位既可悲又可爱的人。”(注:张梦阳:《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第45-46页。)因此,许三观的典型意义明显高于福贵。
张梦阳从《许三观卖血记》中读出了作者对中国人“求诸内”的活法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严酷的批判”这一宏大意义,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我读来读去,就是读不出“严酷的批判”。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反题2 到目前为止,余华研究中让我拍案叫绝、感叹再三的宏论,是夏中义、富华的长篇专论《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注:夏中义、富华:《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9期。)此作将余华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此作“系统地追溯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旨在从价值论角度对余华长达十余年的文学生涯给出一个经得起玩味的评估。”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划出一道沟堑,具体以《在细雨中呼喊》与《活着》标出界线。《在细雨中呼喊》虽刊于1991年,“但其价值取向仍属20世纪80年代”。其母题演化的轨迹是从“苦难中的温 情”到“温情地受难”。从1987年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在细雨中呼喊》,余华小 说极力叙写“人性之恶”与“人世之厄”,表现“现实境遇层面的生存之难”与“生命 体验层面的存在之苦”。但到《活着》等作品则大变,“纷纷转为乡土的牧歌”。从《 在细雨中呼喊》表现的“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的“温情地受难”,看字面只 是对那母题基因的词序的先后置换,但其纸背却正策动着一场价值哗变。
《活着》领“价值哗变”之先风,自然要先论《活着》。谈《活着》,实际就是谈福贵。夏中义、富华认为,这部礼赞福贵“活着”的小说,福贵显然已成为作家眼中的“特殊人物”,亦即福贵肯定已不是日常意义上的文学典型,而绝对已提升为某种足以呈示古老中国生存智慧的文化偶像了。
不仅福贵,还有许三观,他们都沿袭着遗传的“犬儒”立场“温情地受难”,化苦为乐,苦中作乐,于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就无形中成了“乡土中国的生存启示录”或本土“圣经”。
夏中义、富华对《活着》及《许三观卖血记》的另一种理解,尖锐凌厉,见地精辟,让人叹服,尽管以上所论偶有事实与理性被想象力与情绪暂时所控的迹象,但大体上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当他们的论述继续推进达到极致处时,想象力与情绪就占了主导地位,其结论让人瞠目结舌:“余华所以尊福贵为偶象,是企盼自己乃至中国人皆能像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即增强全民忍受苦难的生命韧性,“以期诱导当今中国人也能‘温情地受难’”。夏中义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学者,他为文坦诚激越,以思想先锋深刻、学识敏捷扎实行走学界。他和张梦阳对《活着》的否定性批评,代表了余华小说研究的另一种声音,比常规视界的研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其基本看法应无可非议。他们都是在学理层面进行批评,态度真诚而严肃,而且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深思灼见作为支撑,绝非哗众取宠的卖弄与不负责任的鼓噪。我充分尊重他们极有创见的研究,但并不说明我没有疑问。在我看来,三位学者超越作者原意阐释的批评有三个理论支点,这三个支点既构成了他们主体阐释的“先结构”,又成为其批评的逻辑构架。
他们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是鲁迅小说。不论他们承认与否,他们理想的小说文本是鲁迅小说,尤其是以《阿Q正传》、《狂人日记》、《祝福》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更是他们用来衡量别的小说的一个标尺。用这个标准衡量《活着》,当然会量出它与《阿Q正传》的巨大差距,析出它及它的作者“企盼”并“诱导”当今中国人像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消极地承受人性之恶、人生之苦。任何一部作品,无论它怎样优秀,都经不起这样的推论。张梦阳直接拿《阿Q正传》与《活着》比较,夏中义、 富华携带的比较文本也是《阿Q正传》及鲁迅的本意阐释。我以为,《活着》非《阿Q正传》,它们不是一路的小说,各有各的意蕴和潜指。余华也非鲁迅,这两篇小说表现了他们不同的写作立场和本意设置。两条不会相交的平行线,硬是要以一个去规定另一个,只会人为地造成批评的失范。以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写法来衡量、规约写作路数乃至写作立场与此相异的另一个作家或另一部作品,乃批评之大忌。
夏中义、富华的第二个理论支点是针对余华的原意阐释。作者的原意阐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作者的写作本意或作品的基本意义,沿着作者的原意阐释,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但是,作者的原意阐释即使是正确的,也不是唯一的绝对,它只能是众多解释中的一种。我相信,绝大多数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熟悉此理论,并乐意接受这一理论。但一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又不知不觉地将作者的原意阐释视为作品内含与外显意义的全部,视作者为阐释的权威者、唯一的合法者。夏中义、富华对《活着》的否定性批评,是以《阿Q正传》及鲁迅对其所作的本意解释为标准的,从否定余华的原意阐释开始,然后再推及作品。论其质,抓的还是作者的原意阐释。我在想,如果余华对《活着》不作本意解释,或者他也能像鲁迅那样对《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小说作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解释,我们又该怎样评价它呢?
三位学者的第三个理论支点是西方现代的人生观,它隐含在否定性批评之中,实际上起着主控作用。西人言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不在自身,而在身外,这一生命取向已凝定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于是,寻求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的成为西方学者解释世界和人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怎样才能使生命变得有意义呢?美国学者艾温·辛格对西人的人生态度、人生理想作了综述:有意味的生命——不止是幸福或有意义——应该追求一种目的,我们选择这个目的,是因为它超越个人福祉的目标。我们的理想起初可能源于自私的利益,但最终是造福于他人的。当我们为这样的理想而创造而奋斗时,我们就获得了并且也感觉到了人生在世的意味。综观人类追求人生意味的种种不同方式,最为常见的还是“意义的生长”,尤其当这意义包含着跨个人理想的价值创造的时候。任何生命的意味,总是在于它影响其他生命的功能,越是有益于大多数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意味就越大。因为到那时候,“人生就进到一个新的完满阶段,它超越了任何个人的渺小性。”(注:艾温·辛格:《我们的迷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144页。)生命的意义、目的不在自身而在身外的跨个人理想的价值创造,用西人的这种人生观及生命哲学来衡量福贵们,自然会对福贵们的“活法”作出否定性的价值判断 。要求福贵们抗争命运,追求跨个人理想的价值创造,从道理上来说该无疑义,从国民 性建设上来说也实属必要,但以此作为对福贵“活着”的价值判断,显然是超出了文化 语境和时代情境的单向思考的结果。
最大的不确定性等于最多的可能的确定性
文学文本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意蕴简单且没有生长性的封闭结构是自足的结构,而意蕴丰富且具有生长性的结构始终处于开放状态。由于内潜丰富、意义多指向,文本意义变得不确定。文本只要存在两个以上的解,其内含就是不确定的,表现为不确定性。越是内在张力与生长性越强的优秀作品,其不确定性就越大。我对此的结论是:不确定性是作品内含丰富的表现;最大的不确定性等于最多的可能的确定性。
把《活着》放到20世纪文学中进行观照,还真不敢狂言它不行。《活着》是一部朴实纯净的小说,像土地一样朴实,像山溪一样纯净,具有一切好小说都有的流畅。它写的是乡土农民,表现的则是一种高尚的人道同情。相比较而言,《许三观卖血记》就没有这么纯净,许三观身上有戏谑的喜剧成份,漫画式的叙写常常不经意地邀粗俗同行。我知道我这一不慎重的比较可能要被不少学者和作家看低,因为他们认定《许三观卖血记》比《活着》好。我只能忠实于我的感觉,这没办法。恕我再直言,我以为《活着》是写给那些如今年龄在45岁以上,并且家庭或个人曾不同程度地遭遇过如同福贵一样苦难的人看的,这些人体验过人生的大悲大劫、大苦大难,能于《活着》的简单平实之中读出别样的况味。
《活着》单纯,单纯到只有一句话的长度:农民福贵为“活着”而“活着”。阔少爷福贵赌博输光祖产祖业,从此一蹶不起,厄运频频。先是父亲气急攻心从粪缸上掉下摔死,母亲病死,接着是儿子有庆被医院抽血抽死,女儿风霞产后大出血而死,妻子家珍病死,女婿二喜做工遇难致死,外孙苦根吃豆子被撑死。一个个亲人相继先他而去,到晚年,孤苦的福贵与一头通人性的老牛相依为命。
故事就这么单纯平实,但它又与丰富相通。余华是一位在写作中追求单纯的作家,在他看来,单纯简洁是最高的艺术原则。他甚至认为:一位艺术家最大的美德是两种,“一种是单纯,一种是丰富。假如有人同时具备了这两种,他肯定就是大师了。”(注: 余华、潘凯雄:《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3期,第7页。)撇开作 者的原意阐释赋予的“先有”、“先见”而直入文本,从《活着》中读出的则是不确定 的意蕴。
《活着》意蕴的不确定性得益于意蕴的“含在”而不是“确指”,以及与此相匹配的“本原状态的叙写”,即“客观事实的叙述”、“纯粹客观的叙述”。关于这一点,我注意到了郜元宝先生的论述。他说:我们很难断定余华对自己笔下的苦难人生究竟有怎样的想法和感觉,事实上,余华越是将人间的苦难铺陈得淋漓尽致,他寄寓其中的苦难意识就越是超于某种令人费解的缄默与暧昧。余华小说刻意延迟、回避甚至排除主体对苦难人生与人生的苦难作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渗透,好像站在“非人间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叙述人间的苦难。直观地看,这种叙写方式是一种“不介入的方式”,抽去了叙述过程中知性主体和道德主体的方式,把“无以名状的情感涵容在平面化的叙述中”,让苦难以苦难的本原状态呈现出来。余华把他的情感凝固在不事张扬、无需传达、不可转译的某种“前诠释”的原始状态,还置到某种身在其中的“在世”、“在……之中”的生存原状,融入“活着”这种最直接最朴素的生存感受,让一切都在存在平面上超于混沌化。(注: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严格地说,《活着》的“本原状态的叙写”——“客观事实的叙述”并不十分纯粹, 一是作品携带着作者浅度的人道同情,这一点是不难感受到的。二是福贵历经人生劫难而大彻大悟之后发出的不谐音,由宿命转而自慰,这种“精神胜利法”在透悟人生真谛之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福贵是活着不知活着为什么的人,所以才活出混沌的境界。活着的目的太明确,就必然要在生命中注入理想、智慧和向身外拓展的驱力,但这些是不属于福贵的。福贵凭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承受着并抵抗着悲剧命运的频频袭击,于苦难极限处善待生命。在这个意义上,余华说《活着》是一部高尚的小说。如果没有这一段“不谐音”,该多好。这自然是我的一厢情愿,当不得真。
《活着》基本上是本原状态叙写,这种叙写营构的意蕴(意义)无明确指向而又多指向,“怎么看都行”。作者的原意阐释自然是其中之一解,而且我认定它是最基本的意义之所在。张梦阳、夏中义等人的超越原意阐释的否定性批评,深刻地揭示了《活着》意 义的另一面,不论你对他们的否定性批评认可到何种程度,但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那 就是他们是以否定的方式抵达它的意义的。余华和张梦阳、夏中义等人对《活着》作出 的这两种阐释,从相对的两面揭示了传统的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村农民 的人生态度:与命运抗争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消极忍耐的病态的人生态度。这两种人生 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又与传统的国民性相通。
毫无疑问,《活着》蕴含的思想、意义绝对不限于这些。一是因为《活着》没有走向绝对性的确指,二是因为福贵不是典型人物。福贵因为不是典型人物,就少了典型的局限性而比典型具有更多的可塑性和生长性。典型是“类”的称名,是个别性与普通性、个别现象与广阔的社会背景统一确定后的特指。典型形象的内涵即使再丰富,但它的位置与范围是确定的。典型的能指和所指明确,具有强烈的指向,其指向的基本意义一旦落实,就不易改变。19世纪以前的文学首功在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并由此发展出关于典 型及典型塑造的理论。20世纪文学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不再以塑造典型人物为文学的 最高任务。19世纪以前的文学主要以典型形象名,而20世纪的文学,特别是西方的现代 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及相当数量的拉美文学,却是以作品名,人物在此中丧失了 思想、性格、精神,成为物质世界的符号。既然这样,就不能以典型作为最高标准来要 求福贵。《活着》写的是一个极其卑微的农民是怎样化解苦难而乐观的“活着”。他是 悲剧年代里像他那一类卑微苦命的传统农民如何“活着”的一个标本,他身上虽然体现 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人生态度,但他不代表“当代中国人”。他只是他,在那个年 代,他只能以苦难的方式“活着”。他不这样“活着”,又能怎样呢?
标签:许三观卖血记论文; 余华论文; 活着论文; 人生的意义论文; 文学论文; 在细雨中呼喊论文; 我能否相信自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