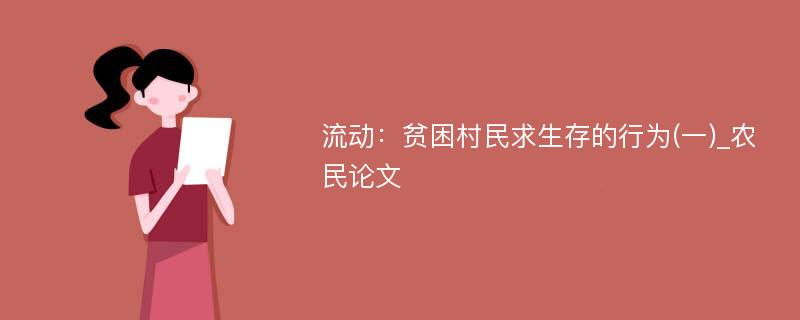
流动:贫困村民寻求生存的行为〔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民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随着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中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但由于流出者以往所赖以生存或生活的村庄与家庭不同,因而其“何以流出”与“得以流出”的因素也就存在着差异。地处中国西北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贫困村民在人与自然的长期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存行为模式,即:天旱了(遭灾了),救济+打工(外出)=吃饭;天不旱(不遭灾),干农活+打工(外出)=吃饭+零用(即有零花钱)。〔2〕 他们的外出流动正是由“混一口饭吃”与“挣点零花钱”这种低限度的生存需求为原动力的。我们在甘肃省陇县北村〔3〕进行的入户访谈证明了这一点。
一、受时代影响的流动状况
1、人口流动简史。在1949年以前,北村农民因生活所迫, 有外出零星讨饭的,但因交通不便,所去之地基本上在邻近各县;到1953年,陇海铁路通车,始有少量人到远处谋生;在1959年~1961年间,因出现饥荒,部分农民逃荒到了新疆、陕西、黑龙江等地,也有用毛毡、衣服等去陕西换粮食的,但由于当时政策不允许,各乡又都有拘留所,流动者随时都有被遣返的可能,因而人数不多;1962年农村实行“三自一包”的政策,村民去陕西做生意或换粮者很多;1964年,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消市场,村民出外做生意或换粮者锐减;1971年~1979年,省城兰州各大工厂招工,村里部分年青人应招而去,但人数并不多。自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该村人口流动的数目才逐渐增多。特别是从1981年开始,流动人口的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地域也不断扩大。与农民自发流出相并行的则是农民合同工的出现。有组织的农民合同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出现了,但数量一直不多,每年只有零星几个。其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在铁路与煤矿。在六七十年代公社化时期,谁能出去做合同工,是由大队、生产队决定的,这些人大部分已转正并留在当地。大规模有组织的农民合同工的出现始于1983年,是由县、乡政府统筹安排的。
2、人口流动现状。1994年,北村全村480户人家中有65.83 %的农户家中有村外流动或村内行业转移(从事非农业)人口,其流动人口总数达408人(包括在村内兼营非农业的115名转移者)。这408 名流动者就其年龄结构而言,18~25岁者最多,占35.29%,其中, 年龄最小者16岁,最大者61岁;就其性别构成而言,男性占74.51 %,女性占25.49%,男性多于女性;就其文化程度构成而言,初中文化程度者最多, 占38.72%;就其流向而言,在乡内流动的占65.20%,在乡外县内流动的占14.46%,在县外省内流动的占7.35%,在省外流动的占12.99%。其中,乡内主要集中在乡镇企业、乡村集市等;县内主要集中在本县县城;省内主要集中在省城兰州及酒泉、玉门、金昌等地;省外则分布在新疆、杭州、北京、陕西、内蒙古、广州等地,其中尤以新疆、杭州、北京三地为多。就流出者的流出方式而言,由政府组织的流出与农民自找门路的流出均存在,但由县、乡政府(特别是劳务输出机构)组织出去者比农民自找门路出去者要少,其中前者占流出者的35.21%, 后者则占64.79%。就流出者所在单位的行业而言,主要集中在工业、商饮 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业中。其中,在工业行业中的占41.18%, 在商饮服务业中的占31.13%,在建筑业中的占15.20%,在运输业中的占8.33%,在其他非农行业中的占4.17%。
从北村人口流动的历史不难看出,村民们的流动总是伴随着饥饿与生活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来人口流动数量的多少却与社会政策变迁是相互联系的。如1962年实行“三自一包”、开放市场时,流动人口数量增多;1964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流动人口就锐减。1979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80年代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广大农民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之间的流动提供了有利机会。另外,以前农民遇到灾年,国家均拨大量的救济款,救济面较大,农民也就靠救济过日子;但现在提倡生产自救,国家的救济款明显减少,且“救济粮款的发放对象是各村所掌握的民政特困户和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特困户”,“一般困难户所缺口粮,通过积极组织群众亲邻相帮、劳务输出等形式自救解决”,〔4〕这也导致部分农民以打工或干临时工来补贴生活的不足。
二、无心苦恋的自然环境
1、气候干旱多灾,农业收成无保障。 北村地处陇县降水量最少的北部半干旱区,年降水量仅有420~450毫米,而且冬春初夏相对少雨,降水量多在7~9月(占全年降水的55%),造成了农、林、牧业需水与供水之间的盈缺矛盾。同时,由于植被差,土壤蒸发量大,致使自然降水的利用率很低,常有干旱发生。干旱以春旱频率最大(占历年的50%),平均两年一遇。个别年份甚至出现春夏连旱,伏秋连旱,一年四季大旱。虽然马河引水工程解决了该村的人畜饮水问题,但无力灌溉农田。村中既无河流通过,又无湖泊;地下水水质差也不利于灌溉。因此,一遇天旱,粮食便大幅度减产,农民便要买粮或靠救济粮维持生存。1994年,北村遇到旱灾,与1993年未遇旱灾时相比,其粮食作物单产减产20%(玉米)~32.09%(糜子),土豆、油料、 中药材等也大幅度减产。不仅如此,北村还位于陇县冰雹三大入境线之一的通安驿—武山线上,易遭雹灾。1994年8月25日22时左右,北村遭受雹灾。冰雹直径10.20毫米,持续时间达35分钟。农作物5~8成受损,受灾面积达400亩。 其中,糜子200亩、谷子100亩、荞麦50亩、高梁50亩。
2、土地相对贫瘠,人地关系紧张。北村的耕地土壤属黄绵土, 虽宜种植多种农作物,但因受干热气候的影响,养分及水分的含量均低,土壤有机质矿化率却高,难于积蓄,特别是有机质的全氮含量较自然土壤低,属低产土壤。加之北村的耕地山地多而川地少,在6620亩耕地中,有82.87%的耕地是贫瘠的山地。由于地贫产量低, 在历史上人们便形成了广种薄收,以多种几亩地来弥补产量低的不足。但由于水土流失严重,加之北村地理位置特殊(位于陇海线上且在乡政府所在地),修铁路公路、建乡镇企业等均要占地,这使北村耕地面积的绝对数不断减少。而与此同时,由于婚嫁、生育等原因,该村的人口急剧增加,由此便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局面。耕地的减少使农民向村集体要地的希望降低,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家庭。而人口流出既能解决流出者本人的吃饭问题,又能缓解家人对土地的需求,村里也并不因该户有人员流出而收回流出者的地,这就等于增加了该户的耕地,农民自然选择了这一两全齐美的方式。在我们所调查的35户农户中,人均耕地2.27亩,低于该村人均耕地3.19亩的水平。人员流出后,这些农家的人均耕地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总之,干旱多灾加上贫瘠的土地,使北村农民不仅在受灾年份地里的粮食收获无保障(有可能连籽种都收不回来),而且在正常年景下的粮食产量也不太高(一般小麦亩产94.95公斤)。 这使“靠天吃饭”的思想在北村村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在这种共识下,村民们由于年龄、文化及观念的不同,其生存观念也有所不同。大多数老人安于现状,眷恋着土地,坚信“镰枷一响三富汉”(即只要种地,就会有吃的、烧的、填(炕)的,就会富起来)。他们请来了雪山太子,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尽管这种做法在1949年以后中断了,但80年代以后,人们又将它重新请了出来)。大多数年轻人则对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失望情绪。他们虽不愿像父辈、祖辈那样“靠天吃饭”,但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无可奈何。一旦有机会,他们便欲乘风离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上天不给这个缘,何必苦相恋”〔5 〕。而大多数中年人却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们既不像父辈、祖辈那样非农不做,对故土须庾难离;但也不像子辈那样不愿务农而一心离去。他们是既工亦农,既离又不离,表现出了做工与务农的双重性与归离时间的双重季节性。
三、难以满足的低限度需求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北村农民的生存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主食结构变化,粮食不够吃。在北村,农户粮食不够吃, 是指小麦不够吃。在我们调查的35户农户中,除因流动而不在家生产、吃饭者外,人均生产小麦155.61公斤,人均消费247.7公斤,两者逆差92.1 公斤;若将外出者也算在内,那么人均产小麦仅有134.7公斤, 而人均消费则要增至262.3公斤,两者逆差127.30公斤, 这还不算用小麦交的公购粮。但若以消费小麦为主,并辅之以杂粮的话,那么,在正常年景下,北村农民的粮食是够吃的。如在上述35户中,除流动在外不在家吃饭者外,人均产粮402.78公斤,人均消费247.70公斤,两者顺差155.09公斤。若包括外出打工者在内,人均产量则减为348.8公斤,而与人均262.3公斤的消费而言,两者顺差也为86.5公斤。但这种细粮与杂粮相混的饮食结构在北村已不占主导地位,人们已经或正在把小麦、大米够不够吃作为衡量粮食够吃与否的标准了。
2、农业收入低下,农户入不敷出。在北村, 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这里的农业收入指种植业收入)入不敷出,不能够解决家庭日常支出所需的全部资金。在被访的35户农户中,农业收入仅占其家庭总收入的22.49%。1993年,35户农户户均农业收入为1403.6元, 而农户户均日常开支为3103.37元,两者逆差1700.77元。这还不包括人情及学生的学杂费,如果加上这两项,两者的差距会更大。农户为了弥补这种差距,就不得不在当地从事其他行业或向异地寻求补贴。从另一个角度讲,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在地里辛苦一年也挣不到几个钱,这也促使人们不愿意在地里多投入,而愿弃地另谋出路。在被访的21户农户中(35户中其余14户因信息不明而未计入),1993年将278 亩承包地里的农作物,如小麦、玉米、土豆、谷子、胡麻、油菜等按当年市场价格折算后,共得农业收入32760元,平均每亩117.84元。但若除去每亩16.56元的化肥、农药投入,1.5元的土地承包费,0.40元的农林特产税,农民 每亩实得收入99.38元。这还不算各种籽种、人力、畜力及各种按人分 摊的费用。这就是说,农民在正常年景下,一年从一亩地中得到的收入最多不超过百元。
四、易于流动的地理位置
北村地处乡政府所在地,乡村集贸市场为该村的上街、下街两社区所环绕,陇海铁路也自村中穿行而过。这样的地理位置为北村村民的就业转移与流动创造了便利条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信息灵、行动快。北村是乡政府所在地,乡政府所张贴的打工启事、广告等,北村的村民可比其他村的村民先看到或听到。这就为其把握时机,选择较好的就业机会提供了便利条件。(2)在乡镇企业就业容易。 北村地处乡政府,该乡的乡镇企业大多离北村较近,有的甚至占的就是北村的地,这就为北村的部分劳力进入乡镇企业创造了条件。1994年,云田乡有9个乡镇企业,这9个企业共吸收北村的劳动力94人。(3 )易于参加集市贸易。乡村集贸市场就在家门口,为北村农民的兼业或转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北村,赶集已经是人们经济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每逢集市,村里的所有工作都陷于停顿,大多数人家都有人在集市上参加贸易或服务。集市交易的商品除了自产的农副土特产、药材外,尚有许多从外乡、外县批发而来的商品。云田集市每月9集, 每人每集可见利20元。除了经济收入外,对北村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他们的非农意识与商品意识。(4 )交通便利,易于流动。陇海铁路穿过该村,连接邻乡、邻县与县城。通往县城的文峰—苟家蕖公路也已初具规模。便利的交通为北村的村民们走南闯北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村中也有人靠偷铁路过活,且已成为村中富户。老年人怕子女在家中闲赋走上此道,便敦促子女外出作活流动,以免无事生非。
五、文化传统与社会选择的双重限制
流出者是流出地所能提供的劳力资源与流入地劳力市场的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北村流动人口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上的特点证明了这一点。
1、从流动者的性别上看,北村的流动人口男多女少, 其原因在于:(1)流入地普遍要求外地流入的女性未婚, 而在北村这一流出地又认为流出的女性最好是未婚女性(甚至未订婚的女性),已婚妇女除跟自己的丈夫一起外出流动外,自己不宜单独出去,并把由已婚妇女单独出去挣钱而丈夫留下守家看作是怪事情,这就限制了部分已婚女性的外出。(2)年轻女性在订婚后,即便是本人愿意出去挣钱, 男女双方的家长(特别是男方的家长)也不愿意让出去。女方家怕的是姑娘出去后眼界开阔了会看不上小伙子,让大人丢人,对不起亲戚朋友;也怕人家说女儿学坏了,大人没把小孩教育好;况且多数人家在订婚时已收了彩礼,如果悔婚,就得将彩礼退回去。男方家则怕鸡飞蛋打,落得个人财两空。这就又限制了部分年轻女性的流出。但该村村民对已订婚的男子却无任何限制。(3 )流入地用人单位对女性文化程度的要求大多比男性高(多数是初中以上),而在流出地北村中,能上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却比男性少,这使部分女性失去流动的机会。(4 )即便各种条件都适合,但女性的家长大多倾向于组织输出,这就又在流动渠道上限制了女性的流动。
2、就流动者的年龄构成而言,18~25岁的人流出者较多, 是因为他们父母的年龄大多在38~45岁之间,家庭中父母是农田地里或家务劳动的主力军,而他们自己则只是这两种劳动中的帮忙者。与此不同的是,同为青壮年的26~35岁年龄段的村民却在流动上较为困难。这部分人大多已结婚,需承担较重的农活,他们或因家中无父母,只有妻子儿女,无人帮助干农活;或因父母已在46~55岁以上,不能从事太多的地里活。这种状况也导致了这两个年龄段上的流出者在流动时间上的差异,前者呈长年性,而后者的流出往往呈季节性。在这两个年龄段上的流动者,就乡内流动的人而言,女性大多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或已婚者,少数末婚者则是文化程度很低或是认为家里比外面舒服,不愿去吃苦的人;而男性则多是农活的主要承担者。
3、就文化程度而言,文化程度较高者流出较多。这是因为:(1)流入地的用人单位大多对流动者的文化程度有一定要求,特别是女性,一般均要求在初中以上。(2)没文化的年青人出去, 年青人自己害怕(不认识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出门连厕所也不认识),老人们也不放心,怕儿女被人骗走。
六、简短的结论
在北村,导致农民流动的根本原因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威胁着村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村民们的就地转移与外出流动成为可能;适宜流动的社会环境为村民们离土或离乡的流动行为提供了政策保证。与此相关的研究〔6〕证明, 人口流动缓解了北村由于地贫而造成的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解决了部分农户吃粮困难的问题,但对村集体的发展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应该说“山也还是那个山,水也还是那个水”。这一方面是因为流出者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用来关心村里的公益事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只关心一家一户的生存,而对他人的生活漠不关心。有迹象表明,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意欲改变其面貌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青人正在大量减少。同时,末婚青年女性与男性壮年劳力的流出,使已婚女性与老人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加重了女性生产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影响了土地的精耕细作与农业科技的推广。
注释:
〔1〕本文资料均来源于笔者1994年12月~1995年1月参与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的《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项目甘肃部分的调查。参加该村调查的人员还有魏晓蓉、张彦珍、徐梅香、石兆俊。
〔2〕本观点最早形成于1995年5月为该项目提交的分报告中。
〔3〕陇县北村是位于甘肃省中部地区的一个贫困村,陇县北村是 我们为其取的学术名。
〔4〕《陇西县云田乡人民政府文件》云政1994年11号。
〔5〕摘自访谈中一青年的日记。
〔6〕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