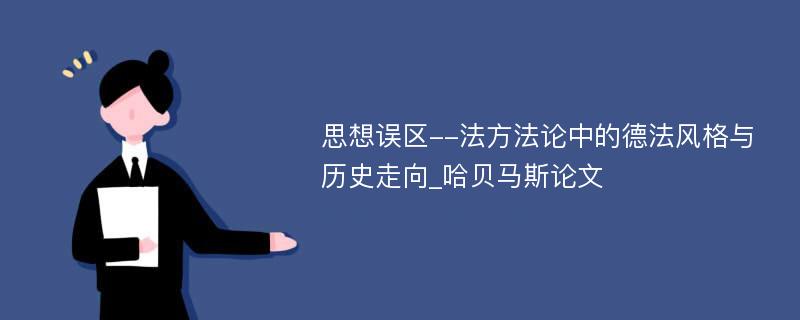
思想的歧途——法学方法论中的德、法风格及历史主义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历史主义论文,歧途论文,法学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
——心都子
方法的突破,已不仅仅是技巧问题,它毋宁说是思想的更新。
——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的研讨,长久以来是欧洲法理学的重要课题。然而同处欧陆的德、法两国,其思想方法与学术风格自有种种微妙差异。本文以两国学人拉伦茨、哈贝马斯和福柯及其著作为例,以书见人、以人见书,揣摩、领会作者对于着手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展开论述的方法,进而找出其间的差异,比较法学方法论中的德、法风格。此外,当下法学理论者对于考据、训诂之风兴趣日浓,历史主义倾向显得甚为明显。然理论家治史与史学家治史,其立场、方法、目的皆有相当的不同。逐一述之,串缀成篇,是为有关法学方法的一点心得。
一、方法的贡献
在德国,法学方法论的问题早已超出了方法的领域。按拉伦茨(Karl Larenz)的话来说,法学方法论所涉及的问题,“或许比刚开始所想像的要广泛得多”。(注:[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页。)的确如此。法哲学研究中需要的方法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又究竟需要些什么样的方法?这种种方法反过来会对审判实践和理论思考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拉伦茨,这个典型的德国人,从法哲学史开始,到法学体系(包括“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的最终构建为止,整整花了七章的篇幅来逐一阐述他的方法。
和其他的德国法学家一样,要阐明方法论的问题,首先(或者说习惯性地)需远远“绕道”19世纪,去看看历史上有关法学方法的种种论辩。利益法学派和评价法学派的长期争论必须被超越,新的评价标准在广泛考察各家之长的基础上终被确定下来:无论如何,法学研究的方法最终是指向“正当的个案裁判”的。然而,要获得一个“正当的个案裁判”,要经过的层层关卡实在太多。拉氏由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方法论之旅”:从最基本的法学术语、概念,到法条的构造与分类,到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以及法官在判案过程中对法律的解释,解释的赓续(法的续造)等等。法学方法以法学家为起点,一一流淌、渗透在立法者、执法者和法官身上,最终到达它的目的地:个案审判。
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实证法或实用法,目的是为使法律适用更加精确、可靠、逻辑自洽。而对于法学方法论的衍说,德国人采用的依旧是一以贯之的法哲学的路子,即为形成法律方法的规则提供哲学基础和体系化的缜密说明。可以说,拉氏的法学方法论正处于实证法和法哲学的中间地带;或者说,《法学方法论》也正是实证法和法哲学这两者相互关联、交叠使用的一个范本。
在阐明其方法论的同时,拉氏也引入了不少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类型学、语义学、诠释学的方法。如此一来,这个经由术语、概念、规则、原理层层叠加构建起来的方法体系就变成了一座极富欧洲特色的“迷宫式的”花园了。拉伦茨在著述其《方法论》时采用的这种极其严谨的、系统化、条分缕析的“方法”,本身也为我们的法哲学思考和写作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这,大概要算拉氏在法学方法论领域所作出的双重贡献罢!
德式风格向来如此。一部沉重不堪的“大书”,机智敏锐、博大精深,自始至终贯穿着谨严缜密的理性,令人望之生畏又肃然起敬。
不过,在我看来,拉氏的法学方法论除了给读者提供一个无比精细又包罗万象的方法体系以外;更多的,怕是意在帮助读者形成一定的法律观。这样的一种法律观,一以贯之地秉承了德国法学哲理化的形而上风格;又因其关注的对象始终集中于实证法、法律应用领域而打上了强烈的实践性的烙印。从规范出发,在通向事实和最终判决的途中,拉氏的《法学方法论》建起了一座跨越天堑的德国式的桥梁。
二、理性与批判:如何重建生活世界?
相比起中规中矩的拉氏,哈贝马斯无疑要显得活跃得多。这位当今德国思想界的大师级人物,不光在法学界声名显赫,他的理论还涵盖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和伦理学等等领域。体现在德国学人身上统一的重思辨、重体系风格,继以严格的古典哲学训练,再加之复杂的学科知识背景,方能造就一个哈贝马斯。由于牵涉到太多的人物和五花八门的思潮,读哈贝马斯,几乎可以说是在与西方近三百年思想史进行对话。
1992年出版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是哈贝马斯在法哲学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部法学专著。哈贝马斯分析现代法律的前提是其描述为“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社会条件。勿庸置疑,在这位始终坚持批判精神的研究者看来,现代社会是有罪的;或者说,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
是的,重建生活世界。——这一信念贯穿了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法律、关于民主与法治理想国的商讨,以及哈氏的整个法哲学、政治哲学理论。他著名的“交往合理化”理论就是经由这个根子生发出来的。
在一个现代社会当中,随着不可避免的专业化和理智化的过程,物质领域被分割,信仰和忠诚被驱逐,旧有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统一的世界于是真正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在这样一个现代性困境当中,欲要重建欧洲的自由政治,哈贝马斯认为:
在完全世俗化的政治中,法治国若没有激进民主的话是难以形成、难以维持的。(注:[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页。)
质言之,民主为法治国的构建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基础,它使得今天这样一个普遍丧失了宗教信仰的生活世界多少变得合理一些。而最终,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程度,“取决于内在于交往行动的、以商谈形式释放出来的合理性潜力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并熔化生活世界。”(注:[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页。)对于越来越原子化、疏离化,并且道德负荷大大减轻的个人来说,要建立起一个巨大组织,必须依赖于相互承认、彼此期待的交往行动。而这样的交往行动,在政治领域中,正是以商谈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一系列讨价还价的商谈过程,交往行动的主体使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建立在一种共识的基础之上;因此,最后作数的仅仅是那些有可能被参与各方所共同接受的理由。无论怎样,行动之协调和互动网络之形成是借助于理解过程而进行的,主体间共享的信念构成了社会整合的媒介。归根结底,社会的整合是靠信念支撑的。
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讨价还价的商谈过程,民主原则也被逐步地建立和培养起来;并且,借助法律形式被巩固下来。反过来言之,民主原则进一步赋予了商谈(立法)过程以形成合法性的力量;或者说,民主原则是商谈原则和法律形式相互交叠的结果,……在商谈过程中,法律规范和形成合法之法的机制,也就是民主原则,是同源地建构起来的。
所谓法治国的观念,按哈贝马斯的定义,也就是说“要求国家的制裁权力、组织权力和行政权力本身必须通过法律的渠道。”(注:[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65页。)而法律本身的合法性与立法过程的合法性实际上是一回事,这样的合法性,在当下完全世俗化了的现代社会中,只能体现为一种民主原则。
法律获得充分的规范意义,既不是通过其形式本身,也不是通过先天既与的道德内容,而是通过立法的程序,正是这种程序产生了合法性。现代法的基础是一种以公民角色为核心、并最终来自交往行动的团结。
哈贝马斯大兴土木地建设他的民主与法治理想国,靠的其实就是两套工具:理性与批判。好的社会,被认为就是根据理性法的规划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欧洲是幸运的,它的政治制度和生活世界正是建立在由古典而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理性原则之上的——尽管,这其间不乏各种各样的批判和置疑。
三、思想的歧途
在欧洲,较之德国传统,法国盛行着另外一种思想风格——学识渊博、力求创新,具有神秘色彩,还有一点危险的意味。这种思想风格几乎被战后法国开发成为思想界的“主要出口产品”。(注:[法]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爱欲生死》,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而福柯(Foucault),他的一系列作品——《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更是这些“出口产品”中的“极品”。
思想的旅途荆棘丛生,众多学者正苦苦进行着方法上的突围。福柯,这位在学术界拥有“无人可以匹敌地位”的思想家,以其惊世骇俗的作品和同样惊世骇俗的生活在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和刑法学、社会学等各方面,为我们设立了一连串的新的路标。
福柯思想方法上的怪异,很大程度来自他生活方式的怪异。这位学术界的“双面神”终身推崇并痴迷于他的“极限体验”。所谓“极限体验”,即是把自己的心智和身体推向断裂点,借助放荡不羁、奇想联翩的行为方式来突破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快感和痛苦,甚至是生与死之间的界限,由此获得通向“未来思想”的道路。
一个人,如果既不遵从理性又不采取有目的的行动,似乎就是在准备好放纵自己。在理性的范围之外探索,既无规则也无标准,既无结构也无秩序,而且必须直面虚无。这样的思想探险,似乎勉强可以称为“无思想的思想”。或者,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讲,是“一种被粉碎了的思考”。这可能是一种无法模仿的天才的思维方式;但它同时也会释放“疯狂的恶念”和“难以抗拒的作恶冲动”,甚至会导致某些捉摸不定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后果。毕竟,天才是只能仰视、不可模仿的。比如福柯最崇拜的个人英雄萨德侯爵(Sad),他的生平故事已被改编成电影《鹅毛笔》。片中,因出版具有强烈施虐倾向性色情小说而被送进疯人院的萨德将整个与他作对的外部世界看成一个大“疯人院”,并继续以他的极端举动对现世进行了控诉和报复。
福柯也足够疯狂了,然而,更加疯狂的是用极度冷静的理性来观察、解剖这种疯狂,并将此种疯狂呈现于世,造成广泛影响。在癫痫、妄想、受虐、强迫症等诸如此类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临床实验中,福柯同时充当了一个病人和医生的角色。这一系列实验的研究报告最后变成了一部综述性著作,即《精神病与性》。福柯本人也曾对此自我解嘲地说,“当时,我已癫狂得足以去研究理性,也有了足够的理性去研究癫狂。”(注:[法]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爱欲生死》,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当然,这种疯狂的心理阴暗和经过严格训练的理性思维的交合,还不仅仅停留在精神病学研究领域,它已经蔓延、渗透在福柯的兴趣广泛的、杂博的哲学、政治学、法学、思想史论著当中。
伟大的天才总有着伟大的病。福柯的病,也就是福柯的神(daimon,“守护神”,在基督教神学家眼中也是“恶魔”之意),把他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的整个一生、包括他的所有作品因此都充溢着“一种不断地撕裂生命的痉挛”。他在学术研究中采用的独特的术语转换激起了层层令人不安的怪异气氛。——这气氛足以使四平八稳、沉闷庸常的学术界为之战栗又兀自兴奋不已。不错,福柯确是一个善于隐匿自己的极端精明者,他“通晓人类本性的全部长处和弱点,并将它们适当地安排到一项(艺术)方案里,直至所有这些长处和弱点都以艺术和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连弱点都显得赏心悦目。”(注:[法]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爱欲生死》,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福柯的理论,他的种种“颠覆方法的方法”,其实给我们很多方法论上的思考空间。罗伯——格里耶就曾说,学术“不是用来消遣的。它是一种探寻”,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发现的想像之旅。毕竟,世界终究是不可知的,自我是所有奥秘中的最神秘者。在思想的浩瀚海洋上,航行是把人交给了捉摸不定的命运,每一次登船都可能一去不复返。“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让自己如同一叶被抛弃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中的轻舟,四处漂泊流浪,摆脱任何方法的监禁,他便获得了自由。而一旦想到方法、一旦开始某种方法上的探求,他就会沦为方法的囚徒,注定受方法之累。四周到处都是路,却又永远只能徘徊于歧途。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福柯的这种“反方法”高明到近于有几分狡诈。他是利用“颠覆一切既有的方法”来掩藏他的方法和技巧。无论如何,在今天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学术界,一个打破所有方法、不受任何方法限制的学者,就像一个航海时根本不需要使用罗盘的船长一样令人仰慕。
若是拆除了方法的楼梯,我们又靠什么来登上思想的高处?——直觉和悟性。必须竖起耳朵,俯身聆听这个世界的喃喃低语,努力领悟那其间未成形的意向。直觉和悟性,再经过严格训练的不断锤打,最终可以转换为一个学者最可宝贵的“气质”(ethos)。而这种气质一经形成,也就意味着学者的方法已然获得。对于我们读者来说,理解一个学者作品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他的“气质”。(注:[法]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爱欲生死》,高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阿尔托曾经说,“事实远远胜过一切虚构,你所需要的,仅仅是知道怎样解释它的天分。”只要具备了这个天分,自然便会找到解释世界的方法。
真实的生活只能通过每个人来体现,而绝不应以戒律、禁条或法律的形式加以限定。同样的,真实的思想亦自有其表达,不需要借助什么特别的方法来构造。换言之,思想已然指示出了方法。方法是一种路径,也仅仅是路径;若找不到目的地,则每一条路皆是歧途。
四、书写历史的方法
在学术研究以及其他更多方面,我们常可看到某种欧洲人特有的趣味,即他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研究对象理想化或审美化(哪怕是暴力,也会生出暴力美学)。然,一种理论无论带有多少理想化色彩,它都必须寻求一个历史的真实作为支点。梅特兰的简要评论更是语出惊人,他说,政治科学“要么是历史,要么是废话”。(注:转引自[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页。)不知此话是否同样适用于法学研究?!
若把法哲学家看作画家,则法律史如同画布。没有画布,再好的画家也无从下笔。但是,从法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记录和书写过往的人物和事件,并不是为了发表一部历史著作;而是在进行对历史的研究。理论家和史学家对于历史资料的处理,其立场、方法和目的都有相当的不同。有学者曾经提出“史学家是反理论的”,但理论家似乎从来不反历史。(注:相关观点请参见杜赞奇:“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载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史家治史,常“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他所涉及的场景,成为一名“再体验”历史的“参与者”,所以他们的历史多半是经验的;而理论家则更多地将自己设想成历史的“评判者”,对于人事,重在论其是非成败。一句话,对于史料,史学家是描述性的,而理论家是分析性的。(注:关于史学家治史与理论家论史的种种不同,近代思想史家王尔敏先生曾在一篇《叙录》中谈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他讲,同样是研习思想史,“思想家在批判与辨析概念之是非、正误、真伪,以至精确的定义。而史学家的研究,则多注重它们的性质,时代意义,以至影响的范围。”参见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齐美尔(Simmel)就曾经很好地表达过理论家的这种倾向,他说:
对我们来说审美性观察和解释的本质存在于这一事实,即在独一无二的事物中发现典型,在偶然中发现规律,在外表和转变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对任何现象来说,都不能逃过这种向重要的和永久的东西的化约。(注:转引自黄宗智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说到底,历史在理论家那里,只是一个供观察和解释的标本;理论家们研究历史,其最终的兴趣,并不在历史本身,而是在于从中“发现规律”。所以理论家笔下的历史,往往呈现出“以小说开头,以论文结尾”的样式。在这方面,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堪称历史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的范本。在这部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完整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对于作者来说,他所置身的那一段革命年代给他的辨别能力提供了“一种手段”,使他得以“庖丁的眼力”看到了构成那个时代链条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如此,事实的叙述已不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事实只是我们头脑中的全部思想和观念所依据的牢固而连续的基础,它为我们展开对历史的观察与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很多启发。托克维尔通过对整部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写,得出了如下结论:革命的发生,自有其合理性;但革命本身,远不足以解决社会的问题。革命之后,旧制度依然存在。事实上,对于这样一个结论,并非只有法国的大革命可以证明。理论家似乎从不满足于“就史论史”,他们总是希图从各种历史事件中去发现那些潜藏在历史深处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以便能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就我的阅读经验来说,孔飞力先生的《叫魂》、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阅读中国系列”丛书(注:“阅读中国系列”是一套由权威美国汉学家执笔的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包括《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先哲的民主》等。)都堪称这样的典范。
另外,当理论家在书写历史、尤其是在书写思想史的时候,对于“思想的形形色色的使用”应该备加留心。通常我们会以思想来划分群体,其实不同群体持不同思想主张,除了其对社会的认识和政治(法律)理念不同以外,往往还和其切身利益、处境息息相关。某人、某一群体思想言论的发表、流布,或与权力的得到或失去相关,或是用来帮助维系社会精英地位,或在寻求上升管道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在此过程中,我以为理论家除了探讨思想本身的意蕴,还应留心这一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功能。不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而是深入探查思想者的内心世界和他们所处的外部世界,让思想者本人、让他们的种种思想及主张变得“可以理解”。(注: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该文发表于2003年3月蒋经国基金会于普林斯顿召开的“中国社会文化的新视野”研讨会。)
最后,不论理论家如何处理历史材料,他们首先要尊重历史本身。因为我们对于发生过的那一段历史,说到底,是知道“答案”的。相较于当时身处其间的行动者而言,我们自然具备了“后见之明”。如果按照最后的结局对历史作“持果索因”式的描述,则这样的书写难免会陷于“目的论”的陷阱。因之,理论家虽非史学家,但涉及历史时,首要的工作仍是要尽其所能地发掘、清理出历史的原貌。那么,该如何进入历史呢?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供了如下建议:第一,进入资料的社会,不带特定的意图。不服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外来的或者既定的观念。第二,不限定特定对象和特定主题。第三,尽可能扩展阅读文献的范围,阅读的时候也不能借助于二手材料,或者断章取义地阅读;要从头到尾地阅读,并且要阅读两遍以上。第四,要以时代先后为顺序阅读。(注:参见[日]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载《学术思想评论》11辑。)
通常,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寻找事实、选择事实,进而组合这些事实,我们会发现历史自然地织成了一张密织的网,它们完整地、和谐地指向某一观点。而这样的观点,并非作者刻意强求,而是水到渠成地显现了。
实际上,历史就是通过真实事例来教授的一部哲学。
标签:哈贝马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法论文; 福柯论文; 法律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