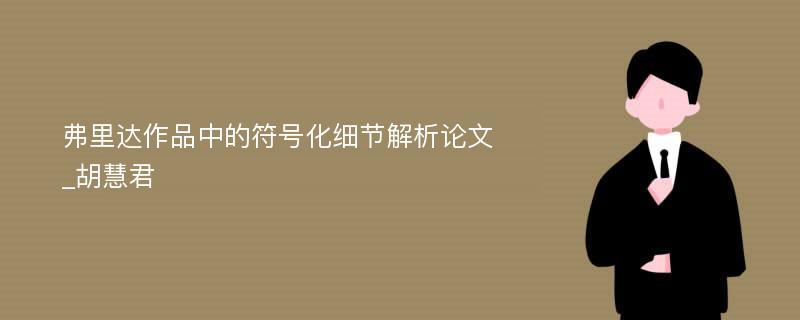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 淮北 235000)
一、面具脸:武装的隐藏,痛苦下的坚韧
在弗里达大部分自画像的作品中,在脸部的描绘上做了符号化的表达,大多作品呈现的都是沉重冷峻表情,这彰显弗里达看待生活的态度,在经历了多次命运的排挤后,依然是以沉重冷峻的脸来应对苦难,或是表达自己对命运的无助和习常。而除了标志化的脸部表情外,面具的出现不占少数,是弗里达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也逐渐成为观者眼中代表弗里达作品和其思想表述的标志符号之一。
在《奶妈与我》(1937)、《哺乳》(1937)、《戴着死亡面具的女孩》(1938)、《面具》(1945)等作品中均有面具的元素呈现。在1938年创作的《戴着死亡面具的女孩》这一作品中,背景天色灰暗,墨西哥的荒郊旷野,在环境的视觉呈现上首先给予观者恐怖不安。小女孩光着脚独自一人站在这环境底下,戴着骷髅头骨的面具,手里拿着小黄花,在墨西哥文化里,这样的黄花是摆放在逝人坟前的。小女孩的脚边放着一个惊悚的、狰狞的面具,那是墨西哥前哥伦布时期的传统面具,只是弗里达由此改变成她想要表达的模样。整幅作品只有小女孩一个生命体,能体现小女孩在这恐怖环境中的孤独和被遗弃的感觉。而从小女孩两腿的比例来看,右腿明显短于左腿,这明显是弗里达把自己化身为画中小女孩的证据,在面具下观者无法确认小女孩是否具有弗里达标志性面容以证明这小女孩表达的就是弗里达本人,但从两腿长度比例能看出是弗里达小时候得小儿麻痹症的症状。灰暗的天色、孤漠的荒野、狰狞的面具等,弗里达想用画作表现幼时抱病在身,内心的震恐、孤独、无助。在1945年的作品《面具》中,弗里达戴着一具哭泣的面具凝视着观者,弗里达把面具眼睛位置掏空了出来,自己透过面具的双孔观看外面世界,将自己隐藏在面具以下,让观者感到不安。
在《奶妈与我》(1937)这一作品中,面具这一元素同样呈现在画作里。画面中弗里达在吮吸着一个戴着面具的印第安女人的乳汁,印第安女人被面具遮挡着,无法看到面具下的表情,但无私地把自己的乳汁奉献给画中的弗里达,这是一个典型伟大的母亲形象。弗里达通过面具遮挡女子的脸部,表达天下母亲的无私,和自己无法成为母亲的遗憾和悲伤。作品中的婴儿弗里达和面具女子,在弗里达的身份认知里其实存有互文关系,一是出生不久后因妹妹克里斯蒂娜的出生,母亲无暇也无心思照看自己,把自己托给了奶妈照顾,是对奶妈的一种感激和对母亲的埋怨及自我的沮丧。
在弗里达的自画像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方式和现实有着极具的反差,画作中的弗里达没有了现实生活中长期饱受病痛折磨和心灵的煎熬,把现实生活中痛苦的自己用面具隐藏了起来,甚至是武装了起来,在画面中反而呈现一种坚韧、顽强,让人否定因身体疾病而出现的柔弱形象。生活中难以反抗的命运使她无法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她透过镜子开始观察自己,开始创作自画像,在镜子中认识自己,也希望通过绘画这种自由的方式,幻象和刻画一个全新或是现实中不可能出现、完美的自己。
画中努力建立一个现实中无法到达的理想自我,并总是用面具和面具化这种成为符号化的面孔来凝视观者。这种表达既是对现实的冷漠凝重态度,也是对理想自我形象的表达和自我武装的保护。
二、项链:民族特征,精神隐喻
项链在弗里达的大部分画作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符号,不仅是因为生活中的弗里达喜欢佩戴具有墨西哥文明色彩的传统项链,弗里达也通过画作中的项链来表达自我情绪。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弗里达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和忠诚在众多作品中都有明显表现,早期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大家作品影响较大,并为之效仿,直到和里维拉结婚后,里维拉的影响和指点,使得弗里达自身风格开始慢慢的形成和定型,也同样因为里维拉,维拉喜欢民族的东西,因为传统的文化及物饰能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认可度,因此弗里达对墨西哥民族的热爱度越来越高。在作品《光阴似箭》(1929)中,弗里达佩戴上了具有墨西哥民族特征的项链配饰,画中弗里达佩戴了石头状的项链。墨西哥的项链与欧洲式项链不同,并没有欧洲式项链的高贵精致,墨西哥的饰品更多的是展现朴素、豪放,这与以往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第安文明的影响有关系,也与墨西哥外来文化纳入度和传统文明传承有着直接关系。墨西哥项链大多以石头为主,不能以奢华著称,但着实予以了弗里达想要表达的粗犷和对民族的热爱,《光阴似箭》中弗里达配搭雀深绿色的石头项链,弗里达身上的饰品不多,绿石项链最为突出,画面中用闹钟和窗外的飞机来表达时光的流逝,弗里达穿着一身白服,高饱满的色块背景,标志性的一字浓眉,端严的注视前方。作品主题与项链没有很直接的联系,弗里达想通过带有墨西哥民族特征的饰品展现对民族的热情和忠诚,也无形中给她代入了更丰富的民族血液。
随之项链成为了弗里达作品中一直陪伴她的标志化工具,除了表达对民族文化的喜爱和热衷外,后期也成为她精神隐喻的一个符号化道具,这当然与她不忠贞的丈夫里维拉有着直接的关系。弗里达一直忍受着里维拉的风流,里维拉和弗里达说过他与外面的女子只是肉体上的关系,并没有动真感情,直至里维拉和弗里达的妹妹发生了关系,弗里达从此陷入绝望,心境的变化也在弗里达的作品中表现出转变和新元素的呈现,而项链也成为表现她心境变化的一个工具。在无法忍受里维拉的背叛后,弗里达把项链从之前的民族特色象征改换成了束缚自己、伤害自己的工具。在《和宠物们的自画像》(1940)和另一幅《自画像》(1940)中,项链都变成了荆棘,缠绕在弗里达的脖子上,划出几道裂口很深的血痕,最初的项链是本土民族风格的象征,在这里开始变成约束、伤害弗里达的工具。用荆棘替代项链作为装饰物并伤害自己,源于生活中里维拉不断的背叛和婚姻的终结所带来的心灵折磨。在《和猴子的自画像》(1940)中,束缚脖子的从荆棘变成了头丝带,长长的头丝带在脖子上饶了一圈又一圈,并衔接在黑猴身上,丝带虽没有荆棘那样直接的侵害性,但绕着脖子同样是一种束缚,从松到慢慢勒紧,直至窒息,同样代表着伤害。可以看出无论是荆棘还是丝带,弗里达都想要表达里维拉的背叛给予她有多深的创伤。
三、动物:情绪表达的辅佐工具
弗里达的作品大多以表达自身经历或是情绪为主,作品中出现的其他元素类如上文提到的面具、项链等,都是以民族特色或是表意形式出现。而墨西哥特色的动物逐渐出现在弗里达1937年往后的作品中,和上述的符号元素的作用一样,动物的出现是用以表达弗里达内心世界。此时的弗里达正经历婚礼破裂的心理折磨,动物以某种形态参与进画作中,与弗里达互动相辅,成为表达弗里达内心痛苦孤寂的辅佐物,也成为了符号化的元素。
在作品《张富兰与我》(1937)中,弗里达把自己描绘成更具男性气质的形象,现实中她唇上淡淡的唇毛,在作品中得以刻意加深,而面部轮廓也描绘得更偏男性化,既保留了女性的本体气质,也带出了男士的特征。而身边的黑色猴子,是里维拉送给弗里达的礼物,取名张富兰,在里维拉离开后,这只黑猴便成为了弗里达生活的伴侣。在墨西哥引以为傲的玛雅文明中,猴子具有性的欲望之表达。既有弗里达用猴子的陪伴来表达自我孤寂希望得以填充之意,也有自我欲望或曰性欲想得以满足的内涵。而画中猴子与弗里达同连一条粉色丝带,相互连接,能看出她与猴子亲密的关系。
除了猴子外,金刚鹦鹉、墨西哥犬等动物也出现在了弗里达的作品中。在作品《墨西哥犬与我》中,弗里达穿着民族特色的服饰,倚坐在空旷的空间里,背景一睹水泥墙,而墨西哥犬则只占了很小的一个比例。狗作为忠诚的象征,千百年来一直是人类生活中最亲近的宠物之一,而墨西哥犬作为家庭犬,它忠诚无形中也与里维拉形成了对比,有嘲讽之意,也有更多可悲在里头。画中的墨西哥犬身形被画者有意缩小,四肢瘦小,像一只玩具小狗,耳朵却比较大,和身体不成比例。这种看似身材不搭的比例,和现实中的弗里达与里维拉正好相反,里维拉比弗里达年龄大20岁有余,体重也是瘦小的弗里达的上倍,人们称他们是大象和鸽子。现实中瘦小的弗里达在这幅画中被身材瘦小的墨西哥犬衬托得高大,是一个保护者的身份和姿态。
论文作者:胡慧君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11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10/26
标签:弗里论文; 墨西哥论文; 面具论文; 项链论文; 作品论文; 民族论文; 自画像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11月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