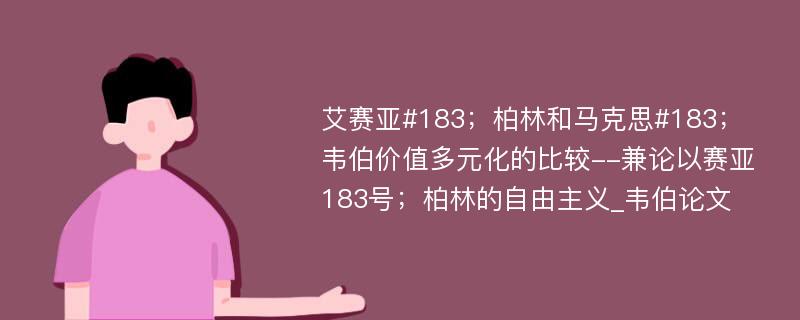
以赛亚#183;伯林与马克斯#183;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之比较——兼论以赛亚#183;伯林的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韦伯论文,伯林论文,自由主义论文,马克斯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084-08
无须争辩的是,以赛亚·伯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其究竟意指什么却不是直接明了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或者说,自由主义就是指有关(有明确界限的)一系列传统的称谓,这些传统除了分享一系列本质规定性的核心特征之外,还具有一种家族的相似性。值得指出的是,作为一个西方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有时自由主义所涵盖的范围包含了那些不仅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种种立场。例如在欧洲,自由主义者通常是指接受自由市场并对国家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人。“社会主义”,更早的时候是“法西斯主义”,一直是欧洲自由主义的首要反义词。而在美国则相反,“自由主义”成为支持国家进行管理和再分配的“进步主义”的态度和政策的象征。此外,“自由主义”还意味着在诸如婚姻、性别关系、家庭、教育、宗教等不同社会领域中的那种反等级的、平等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的反义词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在美国,自由主义既支持自由市场,也尊重既定的社会惯例。人们也能够辨别这些在日常的政治演讲中所使用的“民间的”或“世俗的”自由主义,与那些在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是律师和政治理论家的专业演讲中所使用的自由主义含义(他们称之为“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后者的用法赋予了自由主义一套理念,这套理念既包括约翰·洛克、伊曼努尔·康德、邦雅曼·贡斯当、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约翰·罗尔斯这样的一个血统和世系,也强调他们所提出和辩护那些主张,那就是:宪法中心主义、法治、对集中权力的限制、自由通信和自由结社、基本权利的强调和宽容的习惯。这种用法与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各种形式截然不同。在政治理论家中,这种自由主义有时又被进一步地区别于自由放任主义,有时又叫做“市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后者是包括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弥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罗伯特·诺齐克等人在内的这样的不同世系的一套理念。
让我们从承认以赛亚·伯林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开始谈起。从其众所周知的身世和智识经历来看,以赛亚·伯林终其一生都是个彻底的反共产主义者。在国内政治圈中,他还是个富有社会民主主义同情心的“左翼”人士,绝不赞成市场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也是美国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支持者,因此,他是一个美国,而非欧洲的世俗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
然而一个令人好奇的事实是他很少提及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很少论及,没有写过有关约翰·洛克或伊曼努尔·康德或邦雅曼·贡斯当或亚历西斯·托克维尔等人的文章。当然,伯林也写过一篇有关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几篇关于俄国人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文章。他尊重他们挑战那些标准的、主流的自由主义假定的方式。他所喜欢的穆勒是一个叛教的功利主义者:他是一个“默默离开了同道的信徒”,“敏锐地意识到真理的多面性和生活不可化约的复杂性”,“较之他的功利主义先驱们和自由主义同道们,他关于人的概念要更为深刻,他对历史和生活的视野要更为宽广和复杂”①。他所欣赏赫尔岑的是其对“诸如进步、自由、平等、民族统一、历史权利、人类的团结等伟大的、堂而皇之的历史目标”的“深刻不信任”,“在这些原则和口号的名义下,人类曾经,且无疑会被再度受到欺凌和杀戮,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谴责和毁灭”②。
他也没有与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接洽过:没有与约翰·杜威、雷蒙德·阿隆、罗伯特·波比、卡尔·波普尔、约翰·罗尔斯或罗纳德·德沃金等人进行过争论或对他们加以论述。这部分是因为他把他们的自由主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因为他对其同辈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尤其是波普尔和阿隆并不欣赏,对罗尔斯也没有什么兴趣),部分是因为,也是更为有趣的,他发现自由主义思想家令人厌烦。正如他曾经对我所评论的那样:“读到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几近相同的观点我就感到厌烦。我感兴趣的是阅读(自由的)敌人,因为他们能穿透(自由主义的)防御(体系)。”③
伯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政治理论家的意义上),但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他更喜欢通过其对自由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的阅读来为自由主义进行辩护。更确切地说,他力图为其思考道德和政治问题的方式,即他所谓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辩护,并将之作为支持自由主义的基础,或自由主义的一个前提。为此他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通过生动地展示他所选择的那些思想家的观点——大部分都是上述的(自由的)“敌人”——来作为他们的解释者和对话者。于是马基雅弗利、维科、赫尔德、哈曼、迈斯特和索雷尔等人都被列入名单,并以此来例证不可通约的生活方式的冲突、理智的文化植根性、对于想象的同情的需求、彻底的唯理论的局限和危险、集体主义神话和象征的力量等等。有时你会怀疑这个解释者、对话者已成为一个唠叨的腹语者,他试图用其杂乱的声音去说服他的听众和读者: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多元的价值,它们同等真实、同等终极,尤其是同等客观;因此,它们不可能被安排在一种永恒不变的等级秩序之下,或者是用某种绝对的标准来评判”④。显然,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让自满的自由主义者感到不安,他们假定标准的传统辩护将足以确保自由主义的理智基础并相信自由主义在历史过程中必将取得最终胜利。这些假定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能够被调解、人类理性是普遍可理解和适用的,据此假定所发现的政治原则都是合理的,终有一天,开明人士和民族能够达成一致。在推翻这些假定之后,他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指出对自由主义最好的也是最后的辩护在于拒绝相信这些假定。他的建议大胆而又自相矛盾:通过质疑自由主义者从启蒙运动推论出的假定,从而解除他们的武装并用他们的敌人的武器重新武装起来。
请允许我用些时间来详述一下这个自相矛盾的辩护,它实际上是某种“理性的狡猾”的推理,其中,理性的辩护者就是灾难的预言者,而它的敌人却能使我们免遭于此。伯林的观点是,正是启蒙运动——曾是当之无愧的唯一类型的进步的主要现代根源——支持了一元论——“这种信仰而不是其他……要为在伟大的历史理想的神坛上屠杀个人负责”。也正是反启蒙运动——其主要特征在多方面奏响了“现代好战的反理性的法西斯主义”的先声,并助长了反理智的激进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的非理性主义”潮流——形成了价值多元主义,这种价值多元主义使得容忍成为一种“固有价值”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自由和人权的观念”⑤。正是这些坚持乐观主义和普世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者,他们相信在一个单一和谐的统一体中所有的人类价值能相互协调,这将导致“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存在的危险幻想——为了实现一个能够让人类“永远公正、幸福、富于创造性和和谐”的前景,“可以付出任何代价”⑥。正是那些对浅薄的乐观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嗤之以鼻的神学反动派、同上主义者,往往也是非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想家,他们“对西方思想的中心论传统的深刻而彻底的反抗”和对生活和思想中的“道德多样性”的极其敏感性将为现代自由主义文化打下基础⑦。
关于价值多元主义是否,如果有的话,又是如何与自由主义相关联的问题,伯林的解释者和批评者已做了很多论述。承认前者的真理性需要接受或赞成另一个吗?有人指出,很多自由主义者是一元论者,而许多非自由主义者却是价值多元论者。有些人,比如约翰·格雷和约翰·凯克斯,他们在支持价值多元主义的同时又反对自由主义;而另一些人,像乔治·克劳德和威廉·盖尔斯顿,他们试图通过形成一个自由主义的令人信服的案例,并以此来作为价值多元主义观念所隐含的政治学原则的最好政治表达⑧(克劳德)和通过论证“价值多元主义为个人自由和政府控制提供了具体的理论和实践支持”⑨(盖尔斯顿),在伯林尝试的基础上去构建自由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二者的联系。
而本文要做的就是通过将伯林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多元论进行比较研究(与伯林不同,马克斯·韦伯做出完全不同的假设,并得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力图探明伯林版本的价值多元主义是否具有支持自由主义的鲜明特征(如果有的话,那么它们是什么)。然后,我们继续去追问,在今天作为辩护自由主义的基础,哪个版本更能令人信服。作如此比较的其中一个,可能也是有趣的原因,是韦伯在其两篇短文《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中所提出的韦伯版本的价值多元主义,与伯林版本的价值多元主义一样有说服力,至少已经同样为世人所知,一样有影响。第二个原因当然是韦伯终其一生全神贯注于如何解释现代独特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尤其是他所谓的“合理性”问题,在其各自的意义上,在西方与东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国)是截然相反的。
伯林在其著名的论断中指出,马基雅弗利的原创性在于他已经意识到,对君主而言有两种道德观和两套美德——提倡仁慈、宽恕、自我牺牲、谦卑和其他超脱尘世的基督教道德和提倡现世的抱负、勇气、自信和自发地对敌人进行报复等罗马共和国的原始美德——“不仅仅在实践中,而且在原则上是不可兼容的”。马基雅弗利并没有明确谴责基督教道德,他只是指出,这种道德,至少在统治者中(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国民中)是与他认为的人类理所当然和明智地去谋求的那些社会目标不相容的。人能拯救自己的灵魂,或建立或拥护或服务于一个伟大而光荣的社会国家。马基雅弗利的价值并非基督教的,但它们也是道德价值。于是,马基雅弗利“在后来着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问号”,这源自于他的这样一种认识,“同样终极、同样神圣的各种目标可能彼此抵触,整个价值体系可能相忤,且没有合理仲裁的可能……这是正常人类境遇中的一部分”⑩。
至于韦伯,他在《以学术为业》一文中就认为,“对于生活的终极可能性的看法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它们之间的斗争绝不可能有最终结果”。当然科学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有趣的是,韦伯以一种类似于伯林描述马基雅弗利的方式来例证他的观点。韦伯问到,对于摩西在山上的道德训词,诸如“莫要抵抗恶行”、或(有人打了你的右脸)“再给他左脸”之类,谁能站出来“科学地加以反驳”呢?但是以现世的眼光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是在鼓吹一种无尊严的道德;人们不得不在这种道德所赞扬的尊严,和说法完全不同的人之尊严——“抵抗罪恶,不然你要承担让它横行无阻的责任”,这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根据我们的终极立场,一方是上帝,另一方是恶魔,个人必须去决定,哪一方是上帝,哪一方是恶魔。生活中的所有领域莫不如此(11)。同样,在《以政治为业》中韦伯也提到,在信奉终极目标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也存在“极其深刻的对立”(12)。
除此之外,伯林和韦伯还在其它一些方面不谋而合(虽然知道这点,但伯林从来没有对此做过论述或探究)(13)。两个思想家都指出急需要做的事情是回答托尔斯泰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和我们该如何生活?”他们都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一些观点中寻找到支持。他们均指出价值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冲突,虽然没有予以清楚地说明,但我们可以试着对此加以区分。他们都声称冲突的价值可以是终极的因而也就不可化约:至少在一些,也许是很多情况下,不可能将它们还原为彼此或归入某个包罗万象的价值之下,诸如“功利”或所有的福利或幸福。他们都承认这些价值是不可通约的,因而不可能按照某种尺度或根据某种共同的度量标准将它们进行排列。他们都提出这些价值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不可调和。冲突的价值可能互不兼容是因为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去追求和实践它们,因而必须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权衡”或为了某一个而牺牲另一个(但要注意的是,描述这样的选择的两种比喻性的方式之间有重大差别,一个是商业化的,另一个则是宗教式的。试比较:为追求嗜好所做的选择与要成为僧侣或修女所做的决定(14))。有时,价值的互不兼容不仅仅是在个人层面,而且也是社会性的,因为只是偏好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体制和结构排除了其它方式的可行性,就像市场关系与传统的等级制度会发生冲突一样。这种冲突也可能是相互对立的,就像从上面马基雅弗利和韦伯中的例子一样,一方会极为严肃地否定和谴责另一方。托马斯·内格尔举出了其它一些例子:“享乐主义相对禁欲主义、自我控制相对自发性、世俗性相对精神性、个人主义相对社群主义、直言不讳相对机敏老练。”(15)他们都承认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各种特征是现代性的内在本质。最后,他们都将承认这点看作是个人成熟的标志。伯林写道:“那种确保我们的价值在某个客观的天堂中永恒与安全的要求,也许只是对确定性的幼稚的渴望”,允许这种冲动来“决定一个人的实践,却是一种同样根深蒂固且更加危险的道德和这种不成熟的表现”(16)。同样韦伯也写道,不承认价值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就是一个“政治稚童”(17)。
然而,伯林和韦伯关于价值多元主义的理解在三个重要方面产生分歧。第一个分歧的标志就是伯林经常重申的主张,即多元化的价值是客观的。为此他又援引了生活这个例证:生活赐予了我们多元的价值,这些价值同等真实、同等终极,尤其是同等客观,因而,生活不可能被安排在一种永恒不变的等级秩序之下,或者是用某种绝对的标准来判断(18)。用现代哲学家的术语来说,这就相当于道德现实主义。但是伯林版本的价值多元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就像德沃金所评论的那样,它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多元主义”,所以它们是现实的而非偶发的相互冲突的价值。“种种真实的价值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不仅仅是会就什么是真理的问题而起冲突,而且在关于这些问题的真理之中就存在冲突”(19)。正如内格尔所评论的,伯林一定相信:“这些价值是通过历史传统而被发现和理解,但它们不只是特定群体或个人的态度。”而且,当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不存在“凭空捏造的观点”,也不存在一种“更具优势的评价立场”,由此我们能够在价值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对这一评价性信念持同情态度的内格尔写道,这些不是那种意在描述一个完整世界的企图的一部分,只有我们历史的或科学的信念才是如此。或许存在着一些真正的非主观性的价值,为生活的可能性或对社会系统的选择仅仅提供了局部的规范性秩序。我认为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某些方面,真正的价值会产生相互不一致的秩序,导致个人之间的冲突,那些个人依据这些冲突的价值来使他们的选择正当化,并安排规划他们的生活(20)。遗憾的是,伯林从来没有阐明他所声称的价值是客观的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无论答案是什么,显而易见的是,伯林是认可一种能判断真伪的评价性信念的可知论观点,并认为其中一些是真实的。此外,他也相信,当人们在终极价值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的“生活和思想被基本的道德范畴和概念所决定,这些范畴和概念无论经过多大的时空延展,都是他们的存在和思想以及他们自身认同感的一部分,也是人之为人的因素的一部分”(21)。
马克斯·韦伯不是哲学家,而是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深邃的思想家,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影响(22),了解这点对我们的讨论非常重要。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指的是“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是互不相容的。这暗示了一种作为投射人类关于世界的态度的评价性信念的不可知论观点,而非发现和理解道德事实。至于尼采,他是否是一个道德现实主义者或道德反现实主义者,在尼采文学的评论和批评中已经讨论了很多,这些讨论主要缘自弄清他所恪守的价值观的必要性。不管怎样,他的确是写下了如下这些句子:
只有在相信非实体的存在情况下道德判断和宗教判断才是一致的(23)。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道德判断与宗教判断有一个共同点,即不相信实体的存在。道德只是对一定现象的阐释,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误释(24)。只存在唯一的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唯一的一个“认知”角度(25)。
因此,尼采在这里是要提出一种“负罪理论”,而非对道德和宗教判断进行一种可知论的解释。此外,与伯林不同,尼采对“基本的道德范畴和概念”的理念提出了质疑。对尼采来说,道德与宗教一样:都是人类产生的幻想。道德事实,像上帝一样,是具有巨大实际效果的幻想。至于韦伯,他却将价值承诺描述成信仰一个神并冒犯另外一个神,且“诸神之间的争斗永不消停”(26)。虽然在这儿我无法回答韦伯究竟接受了多少尼采的观点,但我相信韦伯版本的价值多元主义中所隐含的这些足以表明其与伯林的价值多元主义多么的不同。
由上述第一个方面的分歧必然会推导出伯林与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的第二个方面的不同。我认为应将伯林处理有关问题的那种普遍的、泛人类的方法称为“泛人文主义”。如上文所述,伯林把“基本道德范畴和概念”看作是构成使人成其为人的因素的一部分。人类要成为人类就要具有可辨认的道德动机。因而就存在一个可辨认的人类价值的限定范围,他称之为“不同文化或不同人们之间的绝大多数价值体系的共同基础”(27)。这样,“客观目标”或“终极价值”或许会互不兼容,但“它们的多样性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对人类本性来说,不管其多么复杂、多么善变,只要还可以称之为人,其中必含有某种‘类’的特征”(28)。价值观和态度的多样性是有限的,某个社会自己创造了一些价值或态度,而另一个社会却创造了另一些价值和态度,其他社会的成员,(根据他们自己的价值系统)可能赞美、也可能批判这些价值和态度,但如果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总是可以理解它们的,亦即可以视为对这些人而言也是可以理解的生活目标(29)。他的意思是说彼此的可理解性的纯粹事实表明可以扩展那些相异的,有时甚至冲突的价值的限制范围:这个范围会随着对过去以及其它文化的理解的增长而扩大,但依然有限的。
克劳德提出了一种使这套思想更为清晰的解释方法。我们人类所共享的或许只是一些相同而普遍的“为数不多”的价值,但我们可以以一种发散式的“厚的”方式对它们加以解释。或许伯林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与其它文化的价值产生共鸣,因为它们只是对我们所共享的更为普遍的价值的更具体的解释——也就是说,即使在最相异的活动中,我们也可以识别出我们自己的最基本的目的。例如,阿兹特克人的活人献祭,无论是多么的错误,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对繁衍和重生的普遍关心的特殊表达(30)。盖尔斯顿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建议: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这个核心立基于对有关体面的社会生活的积极感受和人类境况中重大邪恶的消极理解。在这共同的“薄的”道德领域之外是“厚的”道德,它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历史和经验的多样性(31)。这里涉及了一个有关理解其他文化的深层次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自法兰兹·鲍亚士以来的人类学历史中已经讨论了很多,我们可以称之为“投射问题”:如何避免将陌生情况也看作是自己熟悉的一个实例的种族中心主义的陷阱——或者更精确地说,如何知道这样做的时候是错误的(32)。伯林虽没认真论述这个问题,但他的观点却强调道德的多样性和被公认的道德范围的界限。遗憾的是,他的著作并没有给我们指明多样性的程度如何,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界限在哪。
如何能区分道德的“薄”与“厚”呢?为了坚持一个“薄”的价值,应为其可能变“厚”的化身设定什么样的界限?然而,似乎清晰的是,伯林在后来的著述和访谈中,在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倾向于强调不同社会间的共性而非差异,也对于西方社会中的价值冲突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出相对乐观。在我看来,在其“相比于通常的看法,在更多国家中有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间里承认更多的共同价值”的考察报告中,人们甚至可以看出某种程度的人类学家柯利弗德·格尔兹所谓的“地方主义”(33)。事实上,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在西方社会,道德多样性已经被大大夸大了。至于“世界的其他部分”,他不很确信的评论道,“他们的一些价值可能与西方的一些价值完全对立,但是不是所有,无论如何也不是。现在的世界是个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冲突可能会叠加,也会日趋增多”(34)。
此处,韦伯的观点再次与伯林完全不同。我们先来看看尼采的观点。完全不把“基本的道德范畴和概念”看作是构成人之为人的因素的一部分的尼采,是这样一个关于道德,也即迄今为止所有盛行的道德、道德判断和评估的批评家。他把道德看作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了人类卓越性的发展,也即,‘这类人的最高权力和辉煌的可能性’”(35)。可以这么说,道德是阻碍人的充分发展的一种手段。正如布赖恩·莱特所说的,把尼采看似不相干的批评性评论——关于利他主义、幸福、怜悯、平等、康德式的对人的尊重和功利主义,等等统一起来的,是他认为,盛行这些规范的文化将是一个根除实现人类卓越性条件的文化。在尼采看来,后者的要求是关注自身、苦难、某种禁欲主义的冷漠、等级感和差异感等等(36)。我们期待有关韦伯与尼采的这些思想的确切关系的结论性研究。蒙森似乎是可信地指明,“韦伯在尼采的理性排他主义和他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之间做了某种折衷”(37)。但也有有力的证据表明,韦伯虽赞同尼采式道德批评的主要内容,但对尼采的蔑视大众、推理式的道德谱系学或把基督教的“悲惨伦理”描述为奴隶道德等这些,韦伯并不接受。此外,韦伯还将道德自身看作是其中独一无二的价值领域,并认为不同的价值领域处于彼此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此外,韦伯不但对将不同文明和文化统一起来的“道德内核”的研究感兴趣,更对是什么使得西方不同于“世界其它部分”,尤其是东方的研究感兴趣。他的比较宗教社会学,采用某些统一的分类,如禁欲主义(另一个受尼采哲学影响的理论),对于考察世界观和伦理教义的深层次文化差异有很大帮助。据我所知,他虽没有详述过可理解性的限度问题,但他在实践中一定探索过其外部的界限,其目的是为了确定什么不是全人类,而是西方所特有的。确定无疑的是,在一战前后的不同历史阶段,他一直在著述和思考什么是古老的欧洲社会秩序崩溃的标志。然而他对西方的看法的确与伯林相去甚远。在他所引用的一个,即“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价值”,“这些不同制度的神和价值之间的相互争斗”的例子时,他再次写到:“不同的神在无休止地相互争斗。”(38)
这直接导致第三个方面,在这方面,韦伯和伯林在他们价值多元主义观点上,也即在他们的政治观念中,尤其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如何对竞争性的价值立场予以政治表达的各自看法中产生分歧。据我所知,关于这一点伯林从未做过论述,但他对正常的政治生活的描述似乎是相当传统和乐观的。他的童年时代实际上是在20世纪早期的俄国革命,也即葛兰西所谓的“非正常时代”中度过的,但后来他在英国找到了一个天堂,成为一个我所指的意义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一个彻底而始终如一的反共产主义者。他喜欢从远处去观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也相信宪法中心主义、法治、通过政治论争来限制集中的权力、通信自由与结社自由、基本权利的强调和宽容的习惯以及对他所谓的“狂热”的范围进行限制的必要性等等。使他思想趋于成熟的环境是冷战,以及他视之为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主要生存威胁的苏联共产主义。相比之下,韦伯对自由主义前景则持一种更为严酷和黯淡的看法。沃尔夫冈·蒙森将他描述为“陷入绝望的自由主义者”(39)。用蒙森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史诗般的悲观主义”源自他所看到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生活各层级的巨大而有力的官僚政治,以及“似乎是不可抗拒的程序化、理性化和科层化趋势”。在他看来,其结果就是工具性关系将遍及社会生活,个体的创造性和个人价值的作用将日益下降,直至退缩到纯粹的私人领域。事实上,他是在怀疑:“在资本主义研创造的这些条件之下,一个自由主义类型的自由社会是否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40)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专制社会的自由化之间他看不到任何联系。因此,在他那个时代,他看到的只是自由主义的黑暗前景:
在美国的“仁慈的封建主义”、德国的“福利供给”、俄罗斯“工厂制度”里,奴役的铁笼已经随处可见;我们唯有等到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减下来,以及租金取得对利润的胜利,连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地区和市场都被耗尽了,我们最终才能促使大众接受这种情境并置身其中(41)。
面对这一由追求最大化利润和竞争性市场的物质利益所推动的不可阻挡的趋势,韦伯看到了抵制它的唯一希望在于他所谓的“大众动员式的领袖民主”形式中的领袖魅力的幸存或复活。在这样的政府体制中,大众动员式的领袖有资格对行政管理机器,乃至政党组织——政党机器进行绝对的控制:只要他还掌权,他就能够以代表其追随者利益的名义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而不管他们自己的信念是什么。他认为这样的一种体制将最大限度地提高有效性和政治活力,能使负责任的卡理斯玛型领袖的统治尽可能的强有力,同时也能有效控制竞争对手的所作所为,从而保证政治和社会最大限度的流动性,因此,能在政治层面上为个体创造性的发挥提供最大限度的机会(42)。正如蒙森所指出的,这实际上是要放弃“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石,尤其是一个自由民主秩序的传统观念”(43)。
韦伯关于政治的特有本性的观点的确与伯林大为不同,实际上它是传统的自由民主观。政治,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家之间,对于韦伯而言,都是恶魔力量和暴力的范围,此间为了达到某人的目的而诉诸危险的手段有时就是不可避免的。韦伯,就像雷蒙德·阿隆所评价的,“无时无处不沉迷于斗争的幻想”(44)。因此,上文所提到的他关于法国与德国文化之间斗争的惊人思想只是诸神之间无休止征战一个实例而已。阿隆正确地指出了,韦伯的政治观点的基础是“一种部分是达尔文式的、部分是尼采式的形而上的斗争哲学,这种哲学倾向于去减少和平和战争之间的对立、民族间的经济对抗和国家间权力斗争的程度”(45)。就像尼采一样,韦伯也认为政治仅仅是从伟大人物的创造性活动中获得意义。这些树立价值标准的具有超凡魅力的伟大人物,他们有责任,尤其是在一个日渐衰退为例行公事的世界里面,去为他们自己赢得一批追随者和促成自己的目标,如果必要的话,不要害怕运用权力,甚至不要害怕与道德法则发生冲突,通过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的法律规则之围墙来保证一个开放的社会免于单一性和衰退的威胁(46)。简言之,他认为法治能够排除,乃至减少“人对人的控制”的传统自由主义理念是一种错觉,从而将伯林的传统自由主义美景看作不过是一个“脆弱的理想”而已。
与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观点进行比较,能够为我们理解伯林的主张,也即价值多元主义构成对自由主义的最有效辩护,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我的看法,也是我在讨论中所提出的,就是伯林的立场相当复杂,他所谓的价值多元主义主要形成于一套前提预设,它们使得价值多元主义能支持伯林所试图捍卫的自由主义。他坚持主张,(消极)自由对于其他价值而言的那种绝对的(在没有例外的意义上)、高于一切的、普遍适用的优先权。他相信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人类本性,因而对那种文化相对主义极为反对。他实际上是要强调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许多,甚至大多数价值冲突的可处理性。我可以断言,在这些承诺与他的认知主义和道德现实主义之间、在他的泛人类的道德核心观念与他的作为一个领域的政治的相对和平的想象之间,能够让自由的合作行为建立在共同的原则和追求共同理想的基础之上。为了支撑这个断言,我力求呈现马克斯·韦伯显著不同的价值多元主义想象和自由主义前景,以及形成它们的完全不同的假定。
注释:
①Isaiah Berlin,John Smart Mill and the Ends of Life,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32.
②Isaiah Berlin,Herzen and His Memoirs,in 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Hogarth,p.196.
③Isaiah Berlin in Conversation with Steven Lukes,Salmagundi,No.120,Fall 1998,p.90.
④Isaiah Berlin,Alleged Relativism in Ejghteenth-Century Eropean Thought,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John Murray,1990,p.79.
⑤Isaiah Berlin,Nationalism:Past Neglect and Present Power,in Against the Current,p.333.
⑥Isaiah Berlin,The Pursuit of the Ideals,in The Crooked Timber,p.15.
⑦Isaiah Berlin,The Apotheosis of the Romantic Will:The Revolt against the Myth of an Ideal World,in The Crooked Timber,p.208.
⑧George Crowder,Value Pluralism and Liberalism,in George Crowder and Henry Hardy(eds.),The One and the Many:Reading Isaiah Berlin,New York:Prometheus Books,2007,p.226.
⑨William Galston,Must Value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Belief Collide? in ibid.,p.153.
⑩Isaiah Berlin,The Originality of Machiavelli,in Against the Current,pp.69,50,55,74-75.
(11)Max Weber,Science as a Vacation,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ited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p.152,148.
(12)Max Weber,Politics as a Vacation,in ibid.,p.120.实际上,这将混淆两个区别:一个是赞成一种绝对的基督教伦理(比如《山上宝训》)和准备诉诸危险的非基督教的手段之间的区别;另一个是关于道德判断的道义论与结果论理解之间的区别。
(13)他说:“对于韦伯的著作我读的不多,这是我最大的缺憾之一,本来我可以弥补,可我从没做过。没有更多的阅读韦伯我让我为之不停地叹息。”(Isaiah Berlin in Conversation with Steven Lukes,p.96.)
(14)Steven Lukes,On comparing the Incomparable:Trade-offs and Sacrifices,in Liberals and Cannibals:The Implications of Diversit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3.
(15)Thomas Nagel,Pluralism and Coherence,in Ronald Dworkin,Mark lilla and Robert B.Silvers(eds.),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1,p.107.
(16)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London and New York,1969,p.172.
(17)Max Weber,Politics as a Vacation,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ited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123.
(18)Isaiah Berlin,Alleged Relativism,in Ejghteenth-Century Eropean Thought 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John Murray,1990,p.79.
(19)Donald Dworkin,Do liberal Values Conflict? in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p.77.
(20)Thomas Nagel,Pluralism and Coherence,in Ronald Dworkin,Mark lilla and Robert B.Silvers(eds.),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1,pp.105,109.
(21)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London and New York,1969,pp.171-172.
(22)正如沃尔夫冈·蒙森所评论的:“如果不参考尼采,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韦伯本人关于终极价值的立场。”(Wolfgang Mommsen,The Age of Bureaucracy:Perspective o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ax Weber,Oxford:Blackwell,1974,p.103.)参看Eugène Fleischmann,De Weber à Nietzsche,Archives Europèennes de Sociologie,Vol.5,1964,pp.190ff.
(23)Fredrich Nietzsche,Twilight of the Idols,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d.Walter Kaufman,New York:Viking,1954,Ⅶ:Ⅰ.
(24)Fredrich Nietzsche,Improving Humannity,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d.Walter Kaufman,New York:Viking,1954,Ⅶ:Ⅰ.
(25)Fredrich Nietzsche,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ed.Keith Ansell-Person,Trans.Carol Dieth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4,p.92.
(26)Max Weber,Science as a Vacation,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ited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152.
(27)Isaiah Berlin,Letter in Reply to Henry Hardy,in The One and the Many,p.299.
(28)Isaiah Berlin,Alleged Relativism,in Eighteenth-Century Eropean Thought 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John Murray,1990,p.80.
(29)Isaiah Berlin,Alleged Relativism,in Eighteenth-Century Eropean Thought 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John Murray,1990,p.79.
(30)Crowder and Hardy,Appendix to The One and the Many,p.300.另外一个例子,他们引用韦斯特马克来表明人类的牺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寿保险的方法。(p.301).
(31)William Galston,Must Value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Belief Collide? in George Crowder and Henry Hardy(eds.),The One and the Many:Reading Isaiah Berlin,New York:Prometheus Books,2007,p.257.
(32)Steven Lukes,Moral Relativism,London,Profile Books,2008,pp.63-69 and John W.Cook,Moral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3)Clifford Geertz,Anti-anti Relativism,in Available Light: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46.
(34)Isaiah Berlin in Conversation with Steven Lukes,Salmagundi,No.120,Fall 1998,pp.119-120.
(35)引自Brian Leiter,Nietzsche on Mora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114.
(36)Brian Leiter,Nietzsche on Moral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29.
(37)Wolfgang Mommsen,The Age of Bureaucracy,Oxford:Blackwell,1974,p.106.
(38)Max Weber,Science as a Vacation,in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edited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8,p.148.
(39)这是《官僚政治》第五章的标题。
(40)Wolfgang Mommsen,The Age of Bureaucracy,Oxford:Blackwell,1974,p.99.
(41)Max Weber,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third edition,Tubingen,1968,p.64.引自Mommsen,loc.cit.p.100.
(42)Wolfgang Mommsen,The Age of Bureaucracy,Oxford:Blackwell,1974,p.113.
(43)Wolfgang Mommsen,The Age of Bureaucracy,Oxford:Blackwell,1974,p.114.关于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最先出现于蒙森著作的译本《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20,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0)。蒙森的著作,在1959年首次被译为德文,并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我们可以在纪念韦伯诞辰100周年的海德尔堡会议的辩论中,尤其雷蒙德·阿隆题为“马克斯·韦伯与权力政治”的文稿以及后继的回应中找到关于这些争论的部分内容。这些会议记录的英文版本是《马克斯·韦伯与当今的社会学》(Max Weber and Sociology Today,ed.Otto Stammer,Oxford:Blackwell,1971,pp.83-132.)。
(44)Aron,Max Weber and Power-politics,in Max Weber and Sociology Today,ed.Otto Stammer,Oxford:Blackwell,1971,p.95.
(45)Aron,Max Weber and Power-politics,in Max Weber and Sociology Today,ed.Otto Stammer,Oxford:Blackwell,1971,p.93.
(46)Mommsen,Discussion on Max Weber and Power-politics,in Max Weber and Sociology Today,ed.Otto Stammer,Oxford:Blackwell,1971,pp.115-116.
标签:韦伯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尼采哲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马克斯论文; 政治论文; 以赛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以赛亚·伯林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