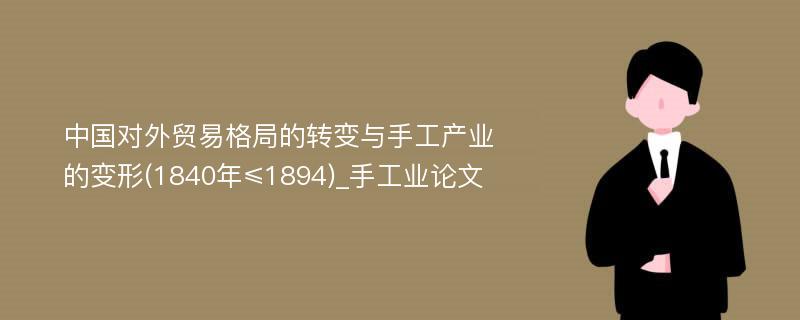
中国外贸格局的转换与手工行业的变形(1840-189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手工论文,外贸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79(2004)05-0015-09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汹涌输入中国,挤压和攘夺手工业的市场,造成传统手工业的严重破坏和迅速衰败,似乎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揆诸史实,一些历史记载的确容易使人们形成这种印象,但这只是问题的—个方面。看不到这个方面,是闭目塞听,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缺乏敏感的认识;然而,大量历史资料表明事物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如果看不到这一面,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就会被人为地简单化。本文拟从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中外贸易格局转换与传统手工行业变形的角度,对这一课题重新检视,既注意西方机制工业品大举入侵的一面,又不忽视中国手工业顽强抵抗的一面,以求得出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一、中外贸易格局的转换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也已经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震荡,不过,与鸦片战争后相比,无论在影响的范围、冲击的频率还是震荡的强度上,尚无法同日而语。随着1840- 1842年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和城下之盟《江宁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主义凭借政治强权,楔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轨道,古老中国逐渐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之中。作为传统社会中最为敏感的社会生产部门,中国的手工行业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与日俱增的影响,从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间,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商品输出。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外国机制工业品品种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价值也越来越高,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商品提供者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发生了全面的冲突。在中国销售的“洋货”,除了鸦片、棉纱、棉布和毛织品等大宗外,还有肥皂、化妆品、火柴、胶制品、樟脑、蜡烛、酸、碱类制品、煤油等“化学工业制造品”和家具、钟表、镜子、钮扣、洋扇、洋伞、灯具、乐器、衣箱、衣帽等“家用品”,又有金属原材料、工具、机械配件、建筑材料等五金洋货,种类之多,不胜枚举。
品种繁多的洋货,大都经由通商口岸,逐渐向中国内地城乡渗透。鸦片战争结束不久的50年代,广州售卖洋货的商店就已经营“红毛洋灯”、“红毛洋针”等外国工业制品。上海在1850年后也出现了一批洋货商店,经营的洋货几乎无所不包。[1](P19)天津虽然开埠较晚,但至迟在70年代前也已经出现了“洋货街”。1870年刊行的《续天津县志》就曾辑入一首题名《洋货街》的打油诗:“洋货街头百货集,穿衣大镜当门立,入门一揖众粲然,真成我与我周旋。”[2](卷19,“艺文”)
在新开口岸及内地城镇,洋货的露面也日渐频繁。1881年,武汉三镇开设的洋货商店已有10家,经营品种包括外国玩具、工具、铅笔、图画、装饰品、伞、利器、珠宝、肥皂,等等。[3]连一些农村乡镇也感受到了进口洋货的影响。浙江南浔镇上营建的楼房,已有不少“仿洋式者,其中器具,即一灯一镜,悉用舶来品,各出新奇,藉以争胜。”[4](P79)直隶《玉田县志》也有记载:“洋舶互市……我之需于彼者,至不可胜数,饮食日用日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5](P168)说日用洋货已达十分之五,恐有夸大之嫌,不过,在这些进口洋货品种中,中国本来亦有相应的手工业生产,则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情况与鸦片战争之前的状况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差异。鸦片战前,除了铸币用的银、铜和果腹用的粮食之外,中国对于海外舶来的洋货并无多少需求,而外国对于中国出产的手工业品,却需求甚殷。从当时中外贸易的内容来看,中国的出口以茶叶、丝绸、瓷器等手工业产品为主,进口则主要是粮食、农畜、金属、矿物等原材料。棉毛织品,数量有限;钟表等物,只作贡品,对中国城乡手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有益无害。鸦片战后,这种贸易格局逐渐被颠倒过来,从而奠定了中国出口农产品和原料,进口机制消费品的对外贸易的基本结构。在这一时期的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仅占8%左右,消费资料则占到90%以上,其中直接消费资料又占到 80%上下。[6](P72-73)显而易见,这对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极大的影响。
二、手工行业的变形
鸦片战争后甲午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生产大体上表现出以下几种不同形态:
(一)因“洋货”输入而首当其冲的手工行业,开始遭受强劲冲击。
在这方面,可以传统棉纺业、棉织业为代表。
在国际贸易中,西方国家的棉纺织品曾经与中国的手织布长期较量。鸦片战争后不久,通商口岸城市就出现了洋布、洋纱排挤土布、土纱的现象,随后又开始由通商口岸城市向临近地区扩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输入中国的外国商品数量激增,其中棉纺织品的增长尤为迅猛,日甚一日地向中国的广袤内地渗透。
洋纱、洋布之间,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别。洋纱在中国销行增长的势头,远远超过了洋布。1840年,输入中国的洋纱为1.82万担,两年后即上升为3.37万担;到甲午战争爆发前,输入中国的洋纱已经超越百万担大关,达到116.17万担。半个多世纪里增长了将近63倍,进展不可谓不速。相对于洋纱来说,洋布进口的增长似乎缓慢得多。1840年时为52.09万匹,5年后一度达到300多万匹,通商口岸地区立即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洋行商人对中国市场不明就里,盲目输入,以致存货山积,随即不得不大幅度贬价求售。直到 1894年,海关贸易册上显示的洋布进口约为1379.59万匹, 54年间增长了25倍,不到洋纱进口增长的40%。
在进口洋纱、洋布价值的比较上,亦是如此。海关关册的统计显示,从1867年到1894年,洋布进口值由1200海关两上升为3100海关两,约增长1.58倍;而洋纱进口则由146万海关两上升为2140海关两,增长了13倍以上。
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洋纱与洋布相比,具有更为雄厚的竞争力量。在此期间,进口洋布的价格下降了26%,而进口洋纱的价格则下降了63%。[7](P1646)中国老百姓之所以舍土纱而用洋纱,正是由于他们敏感地把握住了市场价格的变动。不过,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洋纱比洋布进口较能适应中国的传统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至迟在19世纪助年代的中外文献里,采用洋纱代替土纱进行手工织布的记载已经频繁出现,各地方志中也有许多洋纱进口促进当地手工织布业兴起的有趣描述。从特定的角度看,洋纱进口给中国传统手工织布业提供了某种自存乃至求得发展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进口洋纱在价格上的大幅下降和数量上的迅速增长,阴了洋布进口的增长。
这一时期的洋纱进口,大多销行于华南沿海一带非植棉区,即那些在鸦片战前已经出现“棉纺分离”的地区。华南八港进口的洋纱在全国进口量中的比重,1867-1871年占97.9%,1884-1888年占63.6%,到1893-1894年仍然高居第一位占44.8%。(注:据历年《海关关册》统计计算。按:华南八港为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在广东、福建一带,植棉事业早已衰落,当地农家纺纱所用棉花,先是来自江南和华北,其后改用自印度进口的原棉。这里农家棉纺织生产结合的环节本来就比较脆弱,鸦片战后中外商品交流扩大,当地进一步大面积地以洋纱取代洋棉,自然也就不会发生太大的阻力。当1894年时,广东、福建地区的农家手工织布已经基本上采用洋纱,手工纺纱“有如风流云散”,以至于“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8](P157)。
当地人民之所以舍土纱而用洋纱,一是由于洋纱便宜,以1887年广州的市场价格为例,1包重300斤的印度棉纱售价约57海关两,而同等重量的手工纺纱售价则高达87海关两,差距之大,实在无法在市场上竞争[9];二是由于这里地处通商口岸,长期受到外洋风习熏染,人们消费心理对洋布有所偏好,正如当地方志记载;“洋纱幼细而匀,所织成之布,自比土布可爱,而其染色更娇艳夺目,非土布所能望其项背。”[8](P157)经过50余年的苦心经营,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行愈推愈广,逐步由沿海城市向内地城镇扩散,进入90年代上半期,华中九港进口的洋纱已经占到全国年进口量的 27.38%,四川、湖南等省份也已经有了洋纱的销行。1890年,四川购办洋纱7万担,“均于重庆销售”[10](“宜昌口”, P51-52);1895年,川省洋纱进口增至11万担,“通都大邑,销数日多”[10](“重庆口”,P10)。1891-1892年间,湖南长沙、道州、常德、永州、宝庆、衡州等11个城市,经由汉口运进的洋纱年均2.4万担。[11]19世纪60年代,洋纱在中国土布生产中的使用率尚只占0.56%,到90年代中期已经上升为 18.94%。(注:有研究估算,1860年中国手工织布业用纱总量约为6285530关担,当年洋纱输入35380关担,约占0.56%;1894年中国手工织布业用纱总量约为6123870关担,当年洋纱输入1159600关担,约占18.94%。加上国内机制纱产量342170关担,再减去非织布用纱,匡算约占中国棉织业耗用棉纱总量的23.42%。(参见徐新吾主编:《江面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25页。)与此同时,洋布在中国年用布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从60年代后期的3.20%上升为90年代中期的13.39%。(注:按折合标准土布计算,估计1860年全国棉布应有消费量约为61956万匹,其中进口品学兼优布1988.4万匹,约占3.20%;1894年全国棉布应有消费量约为68475万匹,其中进口洋布9169.7万匹,区占13.39%。(参见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不难看出,鸦片战后甲午战前洋纱洋布输入的增长,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对传统棉纺织手工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洋纱出而纺事渐疏,洋布兴而织工并歇”[12] (P224),这在有些地区确实已经成为严酷的社会现实。
然而,尽管中国传统棉纺织手工业在越来越激烈的中外商品竞争中每况愈下,但对其遭受冲击的程度与速度,仍应有一个符合实际的清醒估计。1883年的《英国驻华各口领事报告》说:“棉纱线消费的巨大增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不仅上海邻近地区如此,全中国也都如此。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英国棉线出售,每一个商店的货架上都可看到英国的棉线。”[12](P208)另一方面,1867年的《海关关册》声称:“洋布在中国的朋已经日益广泛。”[13](P41)以上记载似乎说明中国的土纱土布无力抵抗洋纱洋布的侵袭,业已土崩瓦解,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中国传统棉纺织生产已经被破坏殆尽的印象。其实,上述材料即使所言非虚,也不过只是一时一地情况的反映,且不无夸大和片面之处,远非事情真相的全部。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事物还存在着更加值得注意的另外一面。
与英国领事报告所说每个村庄、每家店铺都有洋纱出售的情况相反,上海的地方志记载:“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沪上未有纱厂,纱线均手车所纺。”[14](P28)苏州的地方志也说:“光绪二十年前,沪上未有纱厂,苏地盘门外苏纶纱厂亦未兴筑。织布纱线,均手车所纺。”[15](P15)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上海及附近地区实际上仍然是手纺纱唱主角。
其他地区的情况同样如此。1894年的江苏省南通县,“乡人尚未行用机纱,……其时布商收布,凡见掺用洋纱者,必剔除不收。”[16](P111)僻处内地的广西贵县,“清光绪中叶以前,布料多为土货,县属比户纺织,砧声四起,一丝一缕,多由自给。于时以服用自织布为贵,布质密致耐用,平民一袭之衣,可御数载。”[17](P127)据前引数据,此时洋纱在中国销用棉纱量中只占不到25%,主要集中在闽、广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在其他大多数地方还受到人们的冷遇,远远未在中国棉纺织生产中扮演主要角色。
至于洋布取代土布,如前所述,成绩又远逊于洋纱之取代土纱。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洋布进口量尚未超过全年销用棉布量的13.39%,因此,那种“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衣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8] (P20)的论断,实在令人难以苟同。当是时,大多数地区的真实情况更可能是“以服厂自织布为贵”。土布厚实耐穿,颇受普通劳动者青睐,“穿洋布的主要是城镇商人和富裕阶级,穷苦的城市贫民和乡下居民都穿土布”。[7](P1354)
说到底,这一时期洋纱洋布之所以在中国未能畅行无阻,根本原因在于其遭受到中国农民家庭手工生产的顽强抵抗。中国农民“自己种棉花,或以自己田里的生产物交换棉花,自己做成简单的织布机,梳棉纺纱,全部自己动手。除了家庭成员的帮助以外,不要其他帮助,就把棉花织成布”;只要以“较棉花略高的价格把布匹卖出,就能把简单再生产维持下去。”[7](P1337)虽然“曼彻斯特的制造家们看到(中国)农舍这种简单的织布机及其附件也许会发笑”,“但是这种织机能够完成这一工作,而这个民族不倦的勤劳则代替了蒸汽力”,甚至“胜过了蒸汽力。”[7](P1335)
(二)因“外贸大畅”而繁荣起来的手工行业,获得较大发展空间。
缫丝业和丝织业可以作为这一类型手工行业的代表。
中国是丝绸的祖国。在历史上,中国长期扮演着世界上蚕桑丝绸技术和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应者的角色。由于蚕桑丝绸生产所需要的特殊条件和独特技艺,欧美农业中的蚕桑事业发展相对迟缓。近代缫丝工业直到19世纪上半期开始在欧洲起步,但是一直受到蚕桑业发展迟滞的制约,五六十年代更由于欧洲蚕瘟病的流行,生丝原料更加仰赖东亚的中国和日渐崛起的日本。[19]丝织业则是欧洲纺织业中工厂化生产最为落后的部门。从19世纪中叶左右,才开始出现动力织绸机,普及相当缓慢,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手工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传统丝织手工业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因此,鸦片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外国棉纺织品汹涌而来,开始挤占中国手工棉纺织品市场的同时,中国的丝绸产品不仅依然源源输出国外,更由于国门的打开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而呈现出“益呈蓬勃”[20]的景象。鸦片战争前的1830-1837年间,中国每年平均从广州输出生丝9058担。战后,生丝出口迅速窜升,1845年为2万担,1874年为6.84万担,到1894年增为8.32万担,价值2728万海关两,减去其中的厂丝2.25万担、1205万海关两,土丝出口为6.07万担、1523万海关两,较之1840年前,增长了5.74倍。(注:鸦片战争前的数字,参见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1910,p.413.鸦片战争的数字,参见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附录(21),《1859-1948年全国桑蚕丝出口品种数量表》;附录(22),《1859-1948年全国桑蚕丝出口品种价值表》。)生丝输出在中国出口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843 -1845年约为17%-28%,1852-1858年上升为31%- 45%。[21](P45)60年代以后,丝绸出口一直在中国出口总值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1860年为60.10%,1869年为32.41%,1879年为39.60%,1889年为37.55%,1894年为33.29%。(注:根据历年《海关关册》计算。)
进一步分析生丝在国内外市场销售量和值的消长,更能显示对外贸易对中国缫丝手工业的促进。鸦片战争前夕,生丝内外销总量约为6.4万担、总值约为1067万海关两,到 1894年,增长为16.02万担、5166.14万海关两。其中,生丝内销的量和值1840年前夕为5.5万担、864.83万海关两,分别占到当年中国生丝总产量和总产值的85.94%和81.05%;到1894年,内销生丝的量和值上升为7.7万担、2438.13万海关两,但在当年生丝总产量和总产值中的比重却下降为48.06%和47.19%。与此相反,生丝出口的量和值1840年前夕为0.9万担、202.17万海关两,分别占中国生丝总产量和总产值的14.06%和18.95%;到1894年,生丝出口的量和值增加至8.32万担、2728.01万海关两,在当年中国生丝总产量和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经上升到51.94%和52.81%。(注:根据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1840年前与1894年生丝内外销量值比较表》计算。不难看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生丝的内外销比例已经发生逆转,生丝产量的增长明显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刺激。不仅如此,内销生丝1894年比1840年前增加了2.2万担,但绸缎的内销量折合生丝只不过增加了0.43万担,绸缎出口量折合生丝则增加了1.77万担[22](“全国土丝产量表”,P55),反映出内销生丝的增加也主要是用于生产外销绸缎。种种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中国缫丝业的发展,基本上都是由于对外贸易扩大的缘故。
柞蚕丝绸生产的发展,同样反映了这一事实,中国柞蚕丝绸生产的历史,追溯起来十分久远,但是一直未有多大起色,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较快地发展起来。全国柞蚕丝产量,1840年估计不过4000公担上下,到1871年已经增长为 8265公担,到1894年又翻了一番,达到18895公担,其中直接用于出口的9822公担,超过一半,而内销柞蚕丝中也有相当数量是织成绸缎后再行出口。[22](“1871-1937年全国柞蚕丝生产量和值估算表”,P662-667)可见柞蚕丝绸生产的地位日渐重要,主要也是来自外销的增长,由于柞蚕丝绸为中国特产,在世界市场上并无竞争对手,“世界野蚕丝的需要,几乎全部仰给予我国”[23](第11章(戊),P222),其增长的幅度和发展的速度,似乎犹较桑蚕丝绸为大。
在传统丝织手工业方面,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鼎盛。其中的某些年份,由于生丝出口增长减少了内销供应,危及某些地区丝织手工业者的生计,曾引发过行会手工业者捣毁近代丝厂的暴动。广东省南海县本为丝织手工业繁盛之区,“江浦、九江、西樵一带,机工不下万余人”。[24](P960)1881年,江浙地区蚕丝歉收,又有豪商胡雪岩囤积居奇,导致上海的生丝出口量锐减,欧美商人纷纷转向广东求购。广东土丝大量输出,内销不足,“至市上无丝可买,机工为之停歇”。[25] (P45)当地“锦纶堂”的丝织手工业行会组织,遂迁怒于专营出口的蒸汽缫丝厂,“倡言机器害其本业,不如聚众前往拆毁。一唱百和,当场纠集机工二三千人,……涌往学堂乡,将该村陈植榘、陈植恕开设之裕昌厚丝厂之缫丝机器尽行捣毁。”[24](P960)随后,丝织机工又打算捣毁同乡的继昌隆及其他几家丝厂,酿成了乡民、机工各有伤亡的流血事件。
发生于珠江三角洲的这次事件为人们所习知,然而充其量只是一时一地的局部现象,并不足以说明中国丝织手工业已经陷入困境。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丝织手工业尚处于不断发展、日益繁荣的状态。正如苏州丝织业云锦公所的文献所载:“丝织业历史悠久,出品精良,海通以还,外销大畅,益呈蓬勃。有清一代,苏垣东半城几全为丝织业者所聚居,万户机杼,彻夜不辍,产量之丰,无与伦比,四方客商,麇集于此,骎骎乎居全国丝织业之重心,而地方经济之荣枯,亦几视丝织业之兴衰以为断。”[20]
根据《海关关册》的统计,鸦片战后到甲午战前,中国丝织品出口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1860年,丝织品出口值为 212.38万海关两,1989年上升为449.9万海关两,到1894年达841.55万海关两,35年间增长近3倍。在中国出口商品总值中,丝织品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1860年占5.34%,1879年沾22%,1894年又提高到6.57%。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间,中国丝织品的出口量,折合生丝由0.44万担增至2.21万担,增长了4倍多。同期,丝织品的内销量折合生丝只从5.06万担增至5.49万担,只增长子8.50%。丝织品内销与外销的比例,也已由1840年前的1:0.086上升为1:0.402,增长了3.67倍。[22](P110-111)凡此种种均表明,尽管这一时期丝织品的内销还大于外销一倍以上,但中国丝织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国际市场的开拓上的。
中国的丝绸生产长期以来具有“谋国外之发展”的内在需求,近代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正与诸如丝绸这一类行业谋求扩大海外贸易的需要相适应,诚如时人所说:“绸货销路为最多,销地为最广,……吾人所造之绸货,惟有恃国外各市场为挹注之地。”[26]中国丝绸业的巨大生产能量与发展潜力,决非国内市场所能包容,能否不断开拓和长久维持一个广阔的国际市场,决定着中国丝绸手工业的盛衰荣枯。但是,这样一来,国际市场的需要也就左右了中国丝绸业的发展,使之一步步地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面貌进行自我改造。随着欧美丝织业工厂化生产的不断进步,对生丝原料的品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与中国农家土法缫丝以及生丝交易上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中国的近代缫丝工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到1894年,珠江三角洲已有蒸汽丝厂75家,长江三角洲有丝厂12家,无论在工厂数、雇工数及资本总额等方面,都在当时中国近代工业中首屈一指。
近代机器缫丝工业是作为传统缫丝手工业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它一发展起来,就开始挤占了手缫丝的出口份额。 1883年,广东已有出口厂丝1254关担的记载,约占广东生丝出口总量的13.12%。两年后,厂丝出口量增加为3437关担,占粤省生丝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2.45%。此后,厂丝出口一路攀升,到1894-1895年度已达18179关担,占广东生丝出口总量的89.38%;而土丝外销则不断下泻,只有2159关担,只占粤省生丝出口的十分之一,(注: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1892-1901),“广州口”数据计算。)同年,由上海输出的厂丝也首次在《海关关册》上列载,为4344关担,价值232.43万海关两。[22](附录(23))不过,截至1894年,全国厂丝出口仍然只占中国生丝外销总量的26.94%,在中国桑蚕丝总产量中,更是只占区区14.06%。
与缫丝业的变化相比,这一时期中国丝织业的生产方式则依旧循着传统轨道发展,尚未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其间,外国商人和洋务大臣曾经几度设想举办机器织绸工厂,企图以此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进一步打开欧美销路,却终于未能成功。
(三)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少的手工业,仍沿传统轨道运行。
这种类型的手工行业,可以四川井盐业为代表。
四川井盐的开采,历史悠久。由于井盐生产的特殊需要,到18世纪时已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工场手工业,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四川井盐业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到19世纪中期,已经能够开采千米左右的深井浓卤,并且广泛使用了高压天然气。此时的四川井盐产区,井深普遍达到200丈以上到300丈,而明代的井深一般只有六七十丈,清代前期也不过百丈左右。盐井深度的增加,对于井盐业生产力的提高关系甚大。首先,“井浅者咸轻,井深者咸重”,[27](“井厂”1)井盐深度与卤水咸度是成正比的。其次,“井深出大火”,增加并深有利于利用天然气煎盐。清道光初年,并盐业中利用天然气煎盐者尚少,“时烧盐者率以柴炭,引并火者十之一耳。至咸丰七八年而盛,同治初年而大盛。”[28]至此,以天然气煎盐而日甚一日,“取火为烧料者占十分之九,炭灶占十分之一”。[29](P86)掘井深度的增加和天然气的采用,使得四川井盐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数倍,一个盐工平均日产食盐,已经由明末清初的20-40斤增加至100斤左右,遂使井盐产量大幅度提升,加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影响,淮盐的运销受阻,川盐取代了淮盐在湖南、湖北的销区,亦给井盐生产以强有力的刺激,年产销总额达到8亿多斤。
四川井盐生产的扩大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促使井盐业资本积累的加速。19世纪90年代时,每口井盐的平均年利润,高产黄卤井为5590元,黑卤井为13837元,甚至有高达5万元以上的。(注:据自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表”算。)于是,出现了一批“富甲全川”的盐业巨头,拥有资本额从数十万两到百余万两白银不等。商业资本向手工业生产转移的情况也进一步发展起来。咸丰年间,陕西商人控制了犍乐盐场生产“济楚盐”的十大井灶中的6个。[30]同治以后,更是“川省各场井灶,秦人(陕西商人)十居七八”。[31](“征榷九”)雇佣劳动也在四川井盐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发展,犍乐盐场的“吴景让堂”雇工“总数在千名以上”;[32]“王三畏堂”雇工人数亦有1200多名。[33]富乐盐场的“李四有堂”雇用的各类劳动者竟多达2千余人。出卖自身劳动力者通过“人市坝”与劳动力购买者进行两相情愿的交易,两者之间仅有雇佣关系,并无人身依附。[34]佣工自食其力,“日取酬值,可以食五日”。(注:同治二年《嘉定的府告逾石碑》,原碑存五通桥盐场。)
四川井盐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十分细密,“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灶、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35](P37),等等。工人专司其业,“为烧匠者,好为煎烧;为简匠者,好为转水”。[36] (P354)70年代时,一个日推卤水20余担的盐井,“雇工40余名,水牛15条,月产盐八千斤到一万斤”。[37](P521)若是一口日产百担卤水的井盐,从汲卤到煎烧共有工种37个,需要雇佣工人近百名。[38]
总之,时至19世纪后期,四川井盐业的独立发展,已经具备了工场手工业发展成熟的全部要素,向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过渡,似乎应该是它的内在要求和历史趋向。我们好像看到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就要从这里产生出来,但是遗憾得很,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近代机器生产仍然一直没有在四川井盐业中露面。
(四)新从国外传入的手工业,因应海外行情变化而勃兴。
草辫业是其中一个典型。
“草帽辫业,非中国古法,其传入中国也,当在道光咸丰之交。或云烟台英国洋行之指导,或云法国传教士之口授,然自来为农家妇女之职业。”又有一说,认为同治年间,福建省有外人传授制法,用于当时福建水师制作草帽,“是为吾国草帽辫业之嚆矢”。[39](P1003)尽管关于草帽业创于何时、起子何地、传自何国的说法不一,一时也难以考辩精详,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并非中国古来所固有,而是近代以后由外国人介绍到中国来的新兴手工行业。
世界上草帽辫的制作,以西欧诸国为早,随之传往美国。到19世纪中叶,欧洲的草帽辫生产,以意大利、德国、瑞士三国为最盛。60年代前后,草帽辫业传来东方,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其始初兴于山东沿海一带,随后经外国传教士组织大批农家妇女从事编织,逐渐推广于全省各地。外国人将草帽辫编织技术介绍到中国来,是看中了这里充足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同时民间妇女也具备从事生产的手工技能,麦草来源又极为丰富;而草帽辫业传来中国之时,正值中国农村经济凋敝,传统棉纺织手工业受到冲击,迫切需要利用任何一种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之时,新兴的、具有国际市场需求的草帽辫业自然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草帽辫的编织方法简单,技术易于操作,又无需很多投资,这些也使得许多急于谋生者不致望洋兴叹。于是,草帽辫手工业在中国迅速兴起,不断蔓延,“产地甚广,南起闽、浙,北至豫、冀、鲁、晋,无不产之”。[39](“制造业”(下),P1003)
草辫业生产虽然仍采取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形式,却是完全的商品生产,而且是外向型、即面向国际市场需要的商品生产。在草帽辫生产发达的地区,常由包买商组织生产,散处乡间的村民从包买商处领取原料,按照包买商提供的产品规格和要求进行生产,编织成辫后领取工资。也有一些出产草帽辫的地区,农民家庭每于秋收之后从事编结草帽辫的手工劳动,成品则由串乡走村的商贩挨户收买,再转卖于设在城镇的草帽辫庄或草帽辫行。草帽辫庄行将收购来的草帽辫整理打包,运往通商口岸城市,经外国洋行之手输出国外。海关关册上反映的草帽辫出口,始于同治八九年间,由于品质强韧而价格低廉,颇受欧美市场欢迎,出口量一路上升。1874年,中国输出草帽辫16616担,1884年增加为 78166担,到1894年已经达到120609担,20年间增长了6.26倍。一时之间,草帽辫后来居上,超越许多中国传统手工行业,成为仅次于丝、茶的重要出口商品,“为吾国出口货之大宗”。[40]郑观应因此说:“就我夺回利益言之,大宗有二:日丝茶;……次则北直之草帽辫。”[7](P1454)
草辫业的兴起和发展,对于改变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促进自然经济向以市场需要为目标的商品经济转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一部分农民从传统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其产品最终流入国际市场,具有着非同以往的特点。在某些地区,草帽辫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从烟台开埠起,草帽辫业就开始成为“山东省北部和中部大部分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41](P246)。龙口、登州、莱州一带农民“几无户不兼操斯业”。[12](P698)据说从事草帽辫业生产,农家妇女每天约可赚取50文,“可以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较为舒服”。[41](P923)这里也许有点过甚其词,但对农家生计不无小补则是显而易见的。草帽辫业的生产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利用了农闲时的空隙时间,给贫乏的农村经济带来某种扶危济困之助,草帽辫的出口又能换取相当数量的外汇,多少可以平衡一些日益严重的外贸赤字,所以当时有人著文称赞:山东、直隶等地农村的这一手工业生产,“乃我国财政上之一大助力”[42]。
在草帽辫业生产繁盛地区的农村集镇,草帽辫贸易蔚为大观。上海、天津、烟台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商人都来此地购买,或者通过“辫庄”、“辫行”向农家预定。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专业性的草帽辫市场,山东掖县的沙河镇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处。沙河镇的居民和四乡农民,以草帽辫生产为“唯一营生”[43](P60),不仅每年自己生产草帽辫4万包,价值5百余万元,还成为附近一带草帽辫贸易的集散中心。[44]镇上设有“辫庄”五六十家,每年集散草帽辫1.5万担,“该县商人,如张、杜、丘、徐诸姓,皆以此起家”[12](P699)。适应着草帽辫生产和外贸的需要,出现了一批专业的草帽辫行庄商人。他们在内地村镇收购草帽辫,然后运往通商口岸卖给洋行出口,虽然与外国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并非洋行雇员,亦非附属于洋行的买办商人。中国商人开办的草帽辫行庄,多属经纪性质,为洋行与草帽辫集散市场中国卖家之间的中介商。[45]草辫出口公司则多由外国商人开设,有时也会雇佣买办为助手或品质检查员。[46]通过这些华人中介者,外国资本家得以利用大量中国农村的廉价劳力赚取利润,而小农生产者也在日益货币化的市场经济中,更加依赖副业的现金收入,以帮补生计。
草帽辫手工业的勃兴还刺激了一些城市经济的繁荣。烟台开口通商以后,商业逐渐发达,主要原因在于土产出口的增长,而土产之中,又以经营草帽辫、花边、发网者资本雄厚,决定着烟台城市经济的盛衰。尤其是草帽辫,为早期烟台港输出贸易的代表性商品。1887年,草帽辫的出口值占烟台出口货物总值的38.1%,1894年更上升为占82%。在胶济路通车,青岛港崛起之前,烟台港一直是中国草帽辫最大的输出港口。经由烟台输出的草帽辫,1874年为13176担, 1884年为34796担,1894年为60238担,分别占当年全国草帽辫输出总量的79.30%、44.52%和49.94%。(注:据王传荣:《近代山东草帽辫业发展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9、84、85页《烟台、青岛全国草辫出口对照表》计算。)到青岛取而代之成为中国最大的草帽辫输出港口以后,烟台港也就一蹶不振,城市经济“几有江河日下之忧”,亦从一个侧面表明草帽辫手工业的影响力之巨。
然而,完全为了国际市场的需要而兴起的草帽辫业,它的盛衰也就完全由国际市场的行情所决定,也就必然更多地受制于外国资本主义。在草帽辫生产和贸易中,实际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外国洋行。这些洋行亨受着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保护,通过控制草帽辫的市场价格而操纵着草帽辫行业的生杀大权。外国商人以极低价格购取中国农民手工生产的草帽辫出口,每担不过白银十六七两,而在国外制成草帽后再运回中国销售,则每打售价就值白银十余两。一进一出,殊堪惊人。中国的廉价劳力和丰富资源助成了外人财富的膨胀,但外国商人并无意于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而是使草帽辫业的生产始终维持在农民家庭的手工劳动的低级水平,因为对于外国资本来说,采取这种形式的手工劳动最便于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
另一方面,草帽辫出口贸易的发展也没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少经济福利,“编制者并无厚利之可言,每日所获不及银圆二角”(《商务官报》戊申23期,P25)。草帽辫的生产者和贩卖商都要受到外国洋行的盘剥,洋行常常百般刁难,压低收买。他们经常采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国外市场若实际需要 5万担草帽辫,订货时则往往订10万担,到期收齐后,则故意挑剔,多方吹求,即使合乎质量要求也以种种理由退货,结果自然是从事草帽辫生产的农民和经营草帽辫贸易的商人受到损失。中国商人资本薄弱,只求尽快将货物脱手,一旦受到洋商刁难,既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另找买主也有许多实际困难,不得不任人宰割,忍痛以低价出卖。
诸如草帽辫业、花边业、发网业等近代中国适应国际贸易需要而开发出来的新兴手工业,其经济利源几乎全为外国资本所垄断,从而作为外国资本的一种进益源流,溢出了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渠道。这些完全视国际市场需要为转移的新兴手工业,既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左右,又受外国商人恶意的控制,实际上很难获得持续正常的发展,旋兴旋灭是它们难以摆脱的宿命。
(五)无力抗拒洋货竞争的手工行业,很快遭受灭顶之灾。
在这一时期就不敌洋货竞争,很快遭受灭顶之灾的,是传统的土针、土钢手工业生产。中国的土法制针,是用钢丝凿孔磨尖,耗时费工,成本高昂,以致售价甚高,而进口的机制洋针,质量精美,价格低廉,且不断降价。1860年,进口洋针每千根售价0.51海关两,到1894年降至0.14海关两,不到原来的1/3,销至内地,一文钱可以买到洋针2根,于是土针的原有市场很快就被洋针挤占殆尽。1868年,洋针的进口量为517898千根,到1894年增加到2421724千根,增长了3.68倍,中国原有的制针手工业随之迅速凋敝。苏州原来盛产“苏针”,质坚不脆,遐迩闻名,但是与洋针相比,成本高,售价贵,清朝中叶已有的十多家制针作坊,在洋针倾销下停闭相寻,到20世纪初仅剩一二家仍难以维持(民国《吴县志》,卷51,P23)。滇西鹤庆的手工制针,原本极负盛名,在“洋针未入口之前,鹤制为各属所需,嗣以洋针物美价廉,浅见者遂自弃其所制而用之,利权遂为外溢。”[47](P157)山西晋城县的太阳镇,本以制造土针为业,出品号称“太阳针”,行销各省,远至中亚。洋针倾销后,勉力挣扎到印年代,终因成本较高,价格不能降到90根售价50文以下,无法与洋针竞争,逐渐归于淘汰。安徽省宿松县明清时“专制成衣匠及妇女刺绣需用之针,从前所出亦广,近因洋针销售日多,制针营业日渐衰落,业此者逐寥寥焉。”(《宿松县志》,卷17,P47,民国10年刊行)广东的佛山,从前也是手工制针业的一个中心,鸦片战争前曾经盛极一时,已经出现了商人资本支配下的家庭劳动形式,19世纪50年代时还维持着土针作坊二三十家,从业人员数千人,其后在大量进口洋针的排挤下急剧败落,到20世纪初,只剩下寥寥数家作坊苟延残喘(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P15),土针生产实际上已经微不足道。
中国的土钢生产,历史极为久远,发展到明清时期,形成了安徽芜湖、湖南湘潭、邵阳等土钢生产中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土钢手工业面临着国外钢材进口的强劲冲击。最初,人们以为洋钢质量不如土钢,不愿使用,有些地方还禁止洋钢入境[48](P247),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洋钢质优价廉、规格划一、便于再加工等优势日渐显露,土钢实在无法与之竞争。所以,尽管“中国商人很感到它(洋钢)的品质可疑,但是贫穷阶级制造工具时就很需要这种钢”[12](P19)。洋钢的输入量与年俱增,1860年时只有27万担,1880年增至80.7万担,20年里增长了2倍。在第一个十年里,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及附近地区的土钢市场已经全为洋钢所夺占,此后,洋钢进一步深入内地,土钢受其挤压,地盘越发缩小。安徽芜湖出产的“芜钢”,明万历年间即已驰名,产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武器等,如刀剑、剪刀、犁头之类,颇为时人所称道。清乾隆、嘉庆年间,为“芜钢”极盛期,“居市廛冶钢业者数十家”。(嘉庆《芜湖县志》卷1,P18,嘉庆十二年刊行)19世纪 60年代,芜湖冶钢作坊尚有14家,自光绪初年芜湖辟为通商口岸后,洋钢进口激增,土钢作坊大都歇业,1884年只剩下最后1家,到90年代末,连这硕果仅存的最后一家土钢作坊也归于消灭,曾经盛极一时的“芜钢”终于成为历史陈迹。(民国《芜湖县志》,卷35,P6,民国八年刊行)湖南的土钢手工业生产也未能苟延残喘多久,19世纪五六十年代,湘潭有苏钢作坊40多家,邵阳有条钢作坊20多家,由于进口洋钢的竞争,当地土钢作坊因销路断绝而接踵倒闭,到19世纪末,邵阳土钢作坊只剩8家,湘潭则只剩3家,不久即双双均告绝迹。[49](P117、P349-350)在进口洋钢的打击下,中国历史悠久的冶钢手工业终于败落殆尽,“通商以后,洋商以机炉炼出之钢输入,此业遂辍”(民国《芜湖县志》,卷8,P23,民国八年刊行)。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的50余年间,由于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在进口机制工业品的猛烈冲击或逐步蚕食之下,传统手工行业已经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表现出种种复杂情状。从经济学上看,商品之间出现竞争的前提是彼此在效用上的相似性,即商品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商品之间的效用替代率越高,相互竞争就越激烈。例如洋针、洋钢、洋纱等进口商品,在效用上几乎可以完全替代土针、土钢、土纱,且价格较低而质量较优,因此这些中国手工行业自然面临着剧烈竞争;而煤油只能在照明的效用上替代植物油,并不具备植物油的其他效用,相对而言替代率就要低一些,竞争也要缓和一些;还有一些中国固有的手工行业,一时之间尚无进口洋货来替代和排挤,因而暂时尚未面临竞争的局面;更有一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而又为国际市场所需要的手工产品,如生丝、绸缎等,则由于对外贸易的刺激而兴盛起来。
还要看到,外国机制工业品的输入和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有一个不断累积和逐步扩散的过程,而与小农经济结合得异常紧密的中国手工业生产又造成了巨大的成本节约和时间节省,对机制工业品的进攻进行着最顽强的抵抗。于是,在鸦片战后甲午战前这一特定时期内,尽管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基盘已经遭到不断侵袭和削弱,尽管城乡手工业者已经“痛感无生活安定如前之逸乐矣”,但除了个别行业一经与国外机制工业品接触就一败涂地之外,大多数手工行业尚得以勉强维持不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