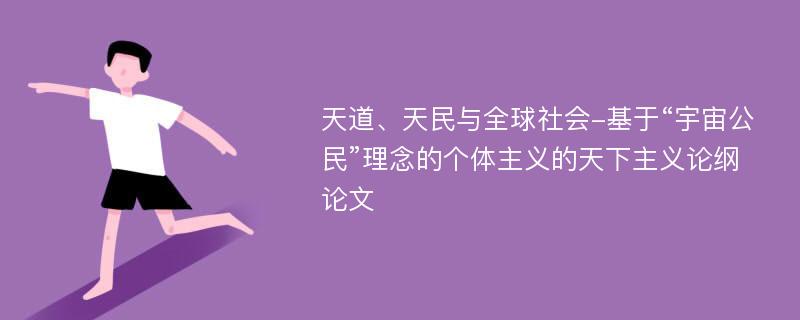
天道、天民与全球社会
——基于“宇宙公民”理念的个体主义的天下主义论纲
李洪卫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 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之争,发展演变为两种类型的学说:一是以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型为标志的天下主义,一是以心性通达天地构成个体自主和因为感通而达致人类社群这样一个二元一体的以个体自主为本的天下主义。个体之所以能成就本体性的自由平等,皆因它秉承天道下贯的属性,这是思孟以来儒家心学思想的命脉。孟子以“天民”即宇宙公民概念确认一种个体存在,它是在道德维度而不是等级层面确认个人身份价值的概念,它的现实载体以“士”为表征,最高则达到“同天”之境界。这个理念由此确认个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尊严和自由、平等,超越中国传统社会之身份和伦理构成的文化观念,以此构造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道德性基础。“天民”概念可以使我们基于人格的平等建构所有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尊严,同时依据个体才具的差异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不同机制和状态。同时,宇宙公民的道德感通属性,能够在人类天下主义的轨道上推进两点:第一,凭依“良知”观念趋向于与世界其他宗教文明的沟通;第二,以士君子群体的扩展为全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发展构架社会基础。
关键词: 天下主义;天道;宇宙公民;尊严;良知
一、天下主义的当代论争
在儒学重新大行其道的今天,关于天、天下、天道、天道秩序和天下主义的论述连篇累牍,不一而足,大家都在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取径或迥然有异,目标也不尽相同甚或相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盛洪先生首揭天下主义这个命题,后来者接踵而至,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种是反民族主义或反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就是首先由盛洪展开的向度。赵汀阳的《天下体系》意旨大体也是指向这里的,但是最后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整体主义的叙述,他后来试图在“共在”和“关系理念”的基础上展开,但是迄今似乎没有更详尽的叙述。第二种是政治儒学家们基于中国历史文化观展开的天下主义,诸如姚中秋的《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和干春松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等。其实,这个维度与其说是天下主义,毋宁说是王道仁政和礼教,其指标在于强调诸如董仲舒的天、君、民三元关系的对立统一辩证,此于姚中秋最为显著,蒋庆则是这一思想最重要的当代发明者。干春松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文本中加入了宋明儒家的“万物一体”的论述,持论稍有回旋[1](P51-52)。第三种是以个体为根基的天下主义的叙述。笔者在《良知与正义:中国自然法的构建》中强调孟子的天民思想:
就氧化还原反应而言,首先,要熟悉常见元素的化合价,能根据化合价正确书写化学式(分子式),或根据化学式判断元素的化合价。其次,要了解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这当然也包括《化学·选修4》中的H2C2O4溶液与KMnO4酸性溶液作用,Na2S2O3溶液与稀硫酸作用等在近几年高考试题中已经频繁亮相的一些重要的氧化还原反应(前者出现在2015年高考全国Ⅱ卷第13题中,后者出现在2017年高考全国Ⅰ卷第12题中)。再次,要熟练掌握常见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和相关计算。
修天爵,行仁道,就是人类立足于道德修养而成为天民、宇宙的成员,不再只是某个城邦、家族、邦国的分子而附属于世俗的爵位等级。成为天民,也可以成为一国之民,但是,作为国民,乃至一国之君,也不一定就能成为宇宙的公民,宇宙公民的顶点,是达仁,即尽心、知性、知天,以阳明所言,就是人性的完全展开。命运本来是外在于天的,现在由自己把握了,同天了,人同天齐,还有比天更高的吗?他已超越了任何地域、民族、种族的藩篱,这正是人类平等的前提,也是人类平等的根本。[2]
同时,从这个角度出发,基于个体良知和公共良知可以在民族国家和世界秩序层面实现政治或人类共同体的更理想的构造(1) 参见李洪卫:《良知与公共理性的道德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 。而黄玉顺教授则以个体身体作为从个体延伸至国家和世界的前提:
明确“以身为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身”这个概念的内涵转换,正意味着时代的转换:在前现代的话语中,“身”只是“家”的附庸;而在现代性的话语中,“身”成为了“家”的基础。例如极具平民性、现代性的王艮就在其《明哲保身论》中申言“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这是因为“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答问补遗》)。“吾身是矩”意味着个体自我乃是家、国、天下的尺度,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表达。[3]
欧阳橘红把玩具汽车和洋娃娃,默默地递给雷钢和雷红,明知叫他们不会答应,就没把小钢,小红几个字叫出口了,但她内心里,在痛苦地嘶喊着,小钢,小红,仿佛声声都沾着血丝,带着痛苦。她弯下腰,一手将雷钢和雷红揽进怀里,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天下主义的价值观中第一种和第二种都不讨论个体的地位,具有特殊主义的内在倾向,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类型,基于从上而下的“治理”和社会伦理属性建构所谓的“天下体系”,没有关于个体价值以及基于此价值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论述。而第一种类型,如赵汀阳试图将“世界”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天下概念期望一个世界成为政治主体的世界体系,一个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order of existence)。”[4](P2)这从机理上似乎很难成立,如果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它就不是一个政治单位,这和政治的含义有悖,若他从人际关系入手试图既克服儒家缺乏处理“陌生人关系”的问题,又能够解决不同文明之间的争斗,必须要走向对个体的定位,尤其是对于陌生人关系来说更是如此。但是,这在他目前构建的理论中也是付之阙如的。第二种类型即基于社会等级和人文礼教的“天下体系”则具有许纪霖教授批评的问题:中国的天下主义与其他轴心文明一样,皆是以某个天赋民族为中心,然后完成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化,向周边和更大的领域扩张,从而建立起天下的普遍性[5](P8)。姚中秋谈到的周人的天下即是如此:“周人按照文明程度,把自己所了解的世界划分为五种类型,从而形成了‘五服制’。不论哪种服制理论,大体上都是按照文明程度对天下进行的结构划分。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图景。”姚中秋并指出,这里的“服”有臣服和服事两层含义,“五服首先是臣服于周王的五等程度,这种臣服程度也必然与诸侯、周王间的亲疏关系有关”;“周人构造天下,处理不同人群、文明关系的上述基本原则,用现代词语来描述,或可称之为‘天下主义’”[6](P619-621)。从这种天下主义的视角来看,天下不过就是一个所知世界的等级制度,只是有一个所谓的文明程度的高低,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软实力”的问题,当然也同时是“硬实力”的支撑问题。从它的积极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战国时期孟子等所赞颂的王道,但是,这个制度本身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并不是如今天政治儒学家所描绘的那么美好。这个天下政治依托于中心自身政治的合理性,其自身的合理性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君主的人格和治理水平。所以,君主的治理能力成为这种天下的基础要件。在姚中秋同时也包括赵汀阳的天下观中,政治就是“治理”。赵汀阳认为:“所谓政治,就是治乱,就是建立合法的社会/生活秩序。”[7](P21)赵汀阳认为,西方政治理论从其“丛林法则”的出发点开始,建立权利理论、国家主权理论以及民主法治理论,基本还是成立的,但是当世界发展到全球规模,这个理论就不适用了:“世界作为共同政治事业的逻辑是建设一个完整政治存在的逻辑,它不再设立对立面,不再需要敌人,按照天下理论的说法,就是‘天下无外’。这个天下逻辑显然与排斥异己的逻辑是接不上的,更是排斥异己的逻辑推不出来的。于是,西方政治哲学所设想的政治制度在世界问题上失去了解释能力,它被证明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完全传递性。”[7](P22)赵汀阳从“天下无外”的维度认为,依据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理论不能解决当代世界的整体性问题,尤其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文明冲突,但是,他只是看到了世界政治的部分画面,尤其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冲突与紧张,而无视世界政治的基础层面,即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市民社会)的逐渐发展,后者恰恰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中形成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概念保护下的渐次发展。我们今天也许需要从“个体—家庭—社区—民族国家—区域社会—全球社会”的连续统的维度来思考所谓的“天下问题”。抛开了个体这个基石,其实就抛弃了世界或天下主义的“普遍性”,因为在这里个体性与人类性具有同一性,并没有一个抽象的人类性或既成的世界共同体存在,我们正是在面对个体生存状景之下的人类思考,而不是纯粹基于民族国家之间斗争的思考,如果简化这个连续统,而强调一个可能的法律秩序,那么它应该是“个体-民族国家-全球社会”这样一个共同体,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两两之间和连续性之间的多重关系事实:第一,我们如果抛弃了个体生存的基本权益讨论世界或天下,那就失去了政治思考的目的性;第二,如果考察个体生存的权益和幸福,首先不能脱离个体生存的空间,就今天而言,个体作为政治存在的根基是国家而不是国际社会,如果没有这个考量,所谓天下或世界都是空中楼阁。譬如当下国际社会的移民问题、难民危机问题构成当代“天下”中的困境,但是,它可能既是人类政治共同体缺失的问题,同时更是民族国家自身政治治理质量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首先不是“天下”或“世界政府”存在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首先是个体的权利在国家体系中的合理保障问题,是一个国家政治是否能够保障公民基本生存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之下的世界性流动才构成全球社会的各种语境和问题。当然,这里不是说,国际社会之间毫无关联,而是当我们考察现实世界的个体境遇的时候,需要第一位考察的是这个个体存在的国家社会的政治治理体系是否合理、健全、正当等;第三,还需要将个体置于全球社会的交往中审视所谓世界或天下指向的合理性问题,即今天的人类个体是同时作为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的双重向度来生存和发展的;第四,作为当下之“天下”(世界)政治主体的民族国家以及作为天下之社会主体的文明或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交织着个体在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方式。显然,无论如何,在不同向度的考察中,个体的维度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第一位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 天道与天民
(一)天道的复合内涵
中国古代“天道”不是“天”,而是天的运行及其法则,其中包含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双重性内涵。中国古人论天和天下秩序相联系,它最初是从天下之治理和转移、从宇宙的秩序和法则展开的。《书·皋陶谟》:“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孔颖达疏:
典礼德刑皆从天出,天次叙人伦,使有常性,故人君为政,当敕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叙爵命,使有礼法,故人君为政,当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礼,当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当承天意为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讨治有罪,使之绝恶,当承天意为五等之刑,使五者轻重用法哉!典礼德刑,无非天意,人君居天官,听治政事,当须勉之哉
孔颖达疏大体反映了《皋陶谟》的内涵,即古人认为,是上天制定颁行了人伦社会的纲常秩序和法律秩序,若此,与后世天道含义比照,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即是天道含义近似的最早版本,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先天规则秩序、天命、天命之德性等后世天道观念中的常规内容。后世的天、道或天道合一呈现了世界之先天规则秩序、社会秩序和德性内在的一体性内涵,宋儒张载同时展示了这两个方面:“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9](P19);“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义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动静合一存乎神,阴阳合一存乎道,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9](20-21)。后世儒家用“天秩”、“天序”等术语者不是很多见,张载此说算是一例。西周以后天秩、天叙也不多见,天道之用词逐渐为常用,表明在某个历史阶段中思想的抽象化之发展。梁启超摘录《诗经》用语诸如“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然后说:“这个时代的天道观念,已经很抽象,不像基督教所谓全知全能的上帝了。天命是有的,不过不具体而已。把天叙、天秩、天命、天讨那种超自然观念,变为于穆不已、无声无臭的自然法则,在周初已经成熟,至孔子而大进步,离开了拟人的观念,而为自然的观念。”[10](P201-202)梁启超认为这个自然不是排斥人道的自然,而是排除了上帝规定性的自然,换句比较容易理解的话说,它从超验的上帝统驭的观念分开走向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两个方向。这个转向中大概最值得关注的是天德、德之纯、纯德等作为思想变化之桥梁的作用,但是限于篇幅,我们此处不做专门讨论(2) 后文约略提及,另作专文研讨“德”的问题。 。
劳思光认为,从商周之际考察,中国人对人格天的崇拜还是限于那些既是国家大事,但又是人间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以政权转移问题为最主要的关注焦点:“就中国古代观念而论,言‘天’言‘帝’,固皆表示对‘人格天’之信仰。但中国人似只以人力所不能决定之问题,归于天意。因此,古代中国思想中,‘人格天’并非事事干预之主宰,而只在某些人力所不能控制之问题,表现其主宰力”;“据此再推一步,即可知何以《诗》、《书》之‘人格天’,主要作用在于决定政权之兴废。盖政权兴废之间,原有许多因素为人力所不能掌握者”; “此外,关于《诗》、《书》资料中之‘人格天’与‘形上天’之关系,尚有应加以说明者,即由于古代中国无创世观念,故‘人格天’虽为最高主宰,却仍受某种形式约束。此种约束,即是一理序观念。就《诗》、《书》中之资料言之,‘天’或‘帝’照例支持有德者,惩罚失德者,而‘德’之所以为‘德’,并未解释为‘天’本身所立之标准。万事自有其理而不必是由天生出,反之,‘人格天’之作用仍以此理为根。故‘人格天’不表一无限权威意志,其主宰力之运用仍受理之约束。此义理推而言之,可说是‘人格天’低于‘形上天’之思想。此种思想颇能表现希伯来观念之中‘神’与古代中国之‘天’或‘帝’间之差异”[11](P69-70)。 劳思光认为,中国初民的人格天意识即便有也是有限的,而且主要集中于政权转移的层面,并以“德”所有为中介,其中“理”是作为一个内在的普遍法则发挥着无形的作用,这二者都和民心、民意有一定的关联。劳思光认为仅从政权转移的角度说,战国后期的孟子把这个问题做了彻底的解决。他认为,孔子以重建周文为目的,以尊周、存周为志,故平生未言及政权转移的问题,而孟子处在周室衰微,旧政权已经无可为计,遂有代周之念,故有新的理论。而孟子政权理论的核心都是从得民心、失民心的维度展开的,畅言得天下有道,民心为政权转移之根据,遂以民心释天命和天意[11](P131-133)。天意、民心的关联是天道秩序的一个向度,这即是前后具有一定连续性的天民合一维度(3) 但是,遗憾的是,在劳思光先生指出孟子这一重要发现的时候,却无视孟子天道思想在其思想中的核心位置,他反对宋儒的习惯说法,认为孟子只是以民心解释天意:“孟子之思想,以心性论为中心;落至政治生活上,乃形成其政治思想。宇宙论问题及形上学问题,皆非孟子留意所在。故谈及‘天’时,最重视有关政治问题一面之说法,但其理论立场则是以‘民心’释‘天意’,故并非提高‘天’对政治生活之重要性,实是削减‘天’观念之分量。”(劳思光,第149页)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劳思光完全看错了孟子,没有看到孟子思想的核心之处,孟子不是削减天的观念,在他那里,天本身就不是观念而是人的生命之本质,是人性,人性展开是天,同时是天道,这是与《中庸》相通和相同的。 。
有机农业植物保护工作水平持续提升,需要保证植物具备较强的土壤能力,更多的是需要不断提升土壤本身的肥力和活性。通过积极开展有机农业土壤配肥工作,将能更为充分有效的保护有机农业植物。首先,需要树立起统筹规划的理念,针对其中的各项内容进行充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增强土壤肥力的持久性。不断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同时还需要从土壤特性出发,适当性的调节土壤,切实提升土壤的供肥能力。其次,在添加有机农业植物有机肥的过程中,需要能从土壤实际肥力状况出发,开展充分有效的处理工作,强化施肥效果。采用选择性和混合性不同的施肥方式,将能够有效增强土壤养分供应的平衡性。
陈来教授曾经对比古代希腊的正义观指出中国古代或早期的三个政治哲学的主题:天民合一、天德合一、天礼合一。他认为从《尚书》的天民合一和天德合一到《左传》的天礼合一是一个向前演进的历程,而所谓天礼合一即是将天自然化,而将人类社会之礼仪规范与自然之天的运行相比拟的过程。陈教授引《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见赵简子论“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一篇议论后指出:
子大叔此篇礼论中的“天”,与《尚书》中具有宗教意义的主宰之天不同,是与‘地’相对的自然之天,这是春秋时代天的宗教意义逐渐减弱、人文思想不断兴起的一种表现。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子大叔的这一套礼论,包含了自然法思想的意义,按照这种看法,人世社会的秩序与原则‘礼’来自更广大的自然(天地),合乎自然界的本性和秩序,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所制定的‘礼’是模仿、依照天地及五行六气的结构属性而形成的。[12]
陈教授认为,此文所展示的天之经、地之义或天地之经直接展现了中国人所谓天经地义之“天道”的意味。他认为:“在前孔子的时代,这种把道德置于政治中心的立场是借助‘天’的权威加以实现的,而天的权威又是被‘德’所规定了的。”[12]天的超越性和威权性已经足见,而天礼合一之天不是《尚书》中的宗教之天而是自然之天,礼节的遵循是自然之天的合乎规则性的展示。这就是陈教授展开的谱系,即从天民合一到天德合一再到天礼合一的顺序。所谓天民合一即从《泰誓》的“保民”思想到《酒诰》《皋陶谟》等的“民本”思想;而天德合一则是《周书》中诸如“皇天不亲,惟德是辅”等天德宰制和敬天德的主体意识,然后到周秦之际的天礼合一的提出。从上述引文可见,先秦天道秩序的法则包含有自然秩序与道德内在统一性、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统一性两个维度或复合表达。
《皋陶谟》之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四者都彰明天的规范性、秩序性和规定性,从“天讨”角度还有人格性,能赏善罚恶,但是里面都隐隐约约透出一点儿道德内在于个体的讯息。梁启超认为,这到孔子已经成为“自然”观念,这个所谓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说这种天道运行的“信念”变成一种日常观念,同时“天”不再是“外在的”和“超验的”,而是“经验的”,这个经验的其实就是一种自然信念,但是排除了有一个主宰的人格之天的意味,且已具有个体内在性的蕴含。其实这在孔子那里已经是一种个人的“经验性”的信念,“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即表达出这样一种信念。天道尤其是道德价值的内在性已经展示出来,当然到孟子这种认识才得以显豁。宋儒张载所提出的“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总体上延续了古人的观念,但是,他通过性与天道的合一实现了天道运行的自然原则和天道内在的道德原则的统一。今人劳思光“‘人格天’不表一无限权威意志,其主宰力之运用仍受理之约束”,意在说明天道的规定性不完全在帝或天那里,还有一个纯粹的“自然秩序”,这和陈来先生所强调的天民、天德、天礼之间的三重合一是有共同之处的。子大叔所谓“天礼”即天经地义之礼是要说明“礼序”的先验性,既非人格性又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这正是传统社会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也具有某种“天德”的蕴含或暗示。上述引文表明古代中国论天道皆依从双重路径:一个路径是自然秩序,里面也包含着社会秩序和法则;一个路径是社会秩序,同时又需要追溯到自然秩序的规定性,凸显自然规定性与社会规定性的统一。但是,从上述引文以及今人之论述都不难看出,德或天德内蕴是连接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支点。实际上,天德之内在彰显路径的展开,即从天民合一到天德合一再到天道内在,是中国古代天道观演进中的重要分支。如果说“天礼合一”类似于自然法或自然秩序,那么依据于天德内在与天道下贯的思孟路径更类似于古希腊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概念。天道内在之天的意义,即所谓自然之天不是大自然而是含有内在衍生秩序本性的天道,这个天道内蕴于人性之中,以个体道德的方式显示,此即子思、孟子个体主义的天道价值观。
青海贵南县中学教师云丹的父亲患肺癌晚期住在曼巴扎仓,活佛说他的父亲可能来日不多。于是他特地赶过来最后照顾一下父亲。
(二)天道、天民及天民的天下
宗教冲突是当代世界人类整合面对的主要困境之一,是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近来中国哲学界对阳明“万物一体”思想的政治延伸给予了较大关注。吴震指出,明德亲民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而这喻指“一体之仁”。“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这个观点可谓是儒家的天下主义伦理学。“一体之仁”可以引领重建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联系,即重建文明世界的整体性、一体性,进而促进人类文化发展以及世界文明对话朝着“一体之仁”的方向前行,以实现个人的道德理想人格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23]。董平认为,“博爱”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美德,中国文化对它不仅是不陌生的,而且原本是深刻地内在于中国文化之中的,是作为一种本原性价值而居于其价值体系结构之核心的。董平借此来重新彰显“博爱”作为德性之爱的普遍价值[24]。这里不展开讨论儒家差等之爱与博爱之间的争议,但这个问题无疑还有可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万物一体”便是最彻底的博爱,具有超越儒家自身基于家庭的差等之爱的空间。仅就阳明思想而言,它具有个体主义和社群主义双重维度,而这个社群不仅是社区共同体的社群,而且可以指向人类社群。阳明的“万物一体”的源头其实在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明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及象山的“宇宙不限隔于人,人自限隔于宇宙”,阳明则将其大加张扬,并加以具体明确地表述。阳明所论的确是天下主义的根基性原则:
在孟子那里,人的本质是性或人性,性是先天和内在的,命也可以认为是先天的,但是不能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因为命是看天的,是外在的,非由己所能决定,而性内在于己,属于人的本质属性的东西,是应该向往追求致力于此的。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14](P113)仁、义、礼、智、圣是五种价值,圣为最高,而天道则是内在又超越的。说它超越,因为它是天道;说它内在,是尽心则知性知天,是可以达到的,因其是内在于人本身的。就孟子来说,它的特殊性在于,现实世界中享有人爵的人不一定享有天道,因为他不一定觉,“觉”是天民的职责,天民在孟子是有觉,即觉悟但又没有世俗爵位的人。孟子所称“天民”之处甚多,最经典的一段是: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14](P04)
第二,良知感通与破除宗教文明的壁垒。
当下国人讨论天下或天下主义有二,一是无民族观念之谓天下,二是所谓王天下之天下。但无民族观念就是人类意义上的天下吗?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姚中秋在《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中认为,周人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表明,周人相信,天下是普遍的,涵盖所有人。即使现在不是普遍的,上天也注定了天下将是普遍的。因为,天是普照的,而人为天地所生,生活于天之下的人们,必将形成一个完整的天下”[6](P621),将这句话作为周人之天下主义的意识萌发。实际上我们充其量只能说这是王者的天下。孟子基于他的天民思想而有一个普通人或士君子的天下,即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4](P44)孟子是在和景春交流何谓“大丈夫”时作此回答的。孟子厌弃那些为功利经营而奔走天下的人,认为那不是大丈夫,那个天下也不是天下,因为那只是诸侯的各种或多或少的“地盘”。孟子且于作答时痛斥“妾妇之道”,妾妇之道是以顺为正,正是指正义或合理,顺乃顺从,不是正义。天下和正义和大丈夫有什么关系?大丈夫的天下是什么天下?这正是儒家心学一系思考的独特之处。
“天下之广居”应含三义。一指的是“仁”。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14](P54)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14](P25)“仁”乃人生最安稳和广大的住处,即生命之道德。由此引出“广居”的第二义宇宙,即天。天的最高贵之处也是仁,故与第一义相通,而未必重复,因为这既是道德的,又是连接着俗世的,是天地相通的世界:“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14](P91)广居的第三义即我们世俗所说的人间的天下,即整个人类社会,也即不同民族在其特定历史场域之下形成的认知范围内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细绎孟子思想,其核心则惟在第一义和第二义。孟子厌弃当时大多数人不涵养道德而又企图获得世俗地位和名声,在他看来,世俗的地位应该是用来以道德本位教化社会大众和博民济众的,但人们却将其作为人生终极目的,而把道德善行变成一时的手段,目的一旦达到就弃如敝屣,这就背弃了天道原则。
冯友兰先生称孟子的“天民”为“宇宙公民”,认为一个儒者要观照现实世界,但更要以天道原则为根基作更超越的观照,有更超越的追求:“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而且作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一定要自觉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则他的行为就不会有超道德的价值。”[15](P8)他在讨论孟子一节中专门论述道:“照孟子和儒家中孟子这一派讲来,宇宙在实质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原则也就是宇宙的形上学原则,人性就是这些原则的例证。孟子及其学派讲到天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个道德宇宙。理解了这个道德的宇宙,就是孟子所说的‘知天’。一个人如果能知天,他就不仅是社会的公民,而且是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15](P67)冯友兰先生在讨论孟子的天民时,交替使用天民或宇宙公民两个概念,其意义是一样的(5) 他在英文版《中国哲学简史》中用“citizen of the universe”或“citizen of Heaven”来表示。 。宇宙公民的天下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没有人群、族群、阶级、阶层或宗教等的规定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是一个道德概念,它以道德为标准和判据。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王天下是做天下之王尊,但孟子却认为这不在君子之乐的范围。显然,君子之乐是德性高尚之乐,无论他是穷居荒野的村夫野老,还是市井之人乃至达官显贵,并无分别。由此孟子确立的是一个生存于世间的个体的平等但又至高无上的人格尊严,由此而来的天下即黄宗羲所谓“天下人之天下”。
三、尊严、感通与士君子扩展的全球社会
(一)道德尊严与现实等差的并置
吴经熊先生曾指出,对孟子来说,“有二种不同的尊贵,即人为的尊贵和天然的尊贵。人为的尊贵,公卿大夫、政府名流属之,它是短暂的,亦非固有的;而天然的尊贵,在乎能行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因此它是一切人之所以为人者均可分享,所以它是永恒的和固有的。此外,授予公卿大夫和政府显要名位的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达臻人类幸福所采用的方法”,“因此,在人类这一面,人民是最后的主权者,统治权源出于此,同时人民的幸福是施政首应考虑的”[16](P239)。确立人的尊严的意义何在?人因尊严而形成平等之人格以及共同的法律秩序,这是我们这个世俗世界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世界层面实施交往的前提条件,是近代以来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和制度架构的前提,没有这个共识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市场体系和法治社会不可能真正建构,也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预期并构成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条件。
取用水国控监测点建设包括地表水流量自动监测站,管道流量自动监测站,地表水、地下水水位自动监测站建设。项目确定的标准配置包括遥测终端机、传感器、通信设备、供电设备、避雷设备和安装辅材等。所配备的设备应该是市场上成熟可靠的产品,用于水资源监测的设备应该具有国家质量监督局颁发的产品生产许可证和指定认证机构颁发的使用许可证,计量设备还应该通过计量认证。
从“政治哲学”这个视角观之,平等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概念,也是最与时俱进、最核心的需要反复阐释的理念。在政治哲学的框架下,“正义”是一个总括的概念和价值,它基本上范围了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和所有思考方向。在它之下,人们讨论了很多价值或观念:平等、自由、国家、人权、民主、契约等等,但是在我们的考察中,这些不同层次的政治哲学概念,乃至包括“正义”概念,都与“平等”或“不平等”观念之间形成互相解释,甚至都以后者的确定性为前提,无论是突出人的平等还是不平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柏拉图因为社会存在的必要分工和人的先验不等而构造了他的“理想国”,斯多亚学派则依据人的先验平等(理性内在)确定人的平等价值,从而构成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的社会转换,自然法和万民法才有其基本基础。康德的道德自由和理智世界奠定的是人的绝对的平等而不是经验世界的自由,在道德自由和个体平等的前提下形成感性世界中的相互性义务并由此推定人的权利。从19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功利主义和经济学“理性人”的设定占据了人文和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准此,罗尔斯才重新以理性人假设重建人的平等观,并成为20世纪后半叶政治哲学探讨的重心。由上足见,无论在人类发展哪一阶段,关于人类平等问题都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性的退化更让人感觉到这个问题之根本性。我们一度把自由与平等相对立,将公平和效率作反射。其实在先验论证中,自由和平等是同一的,在经验层面上则会有较多的层次性差异,譬如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等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但平等恰是这些不同层次自由探讨的共同的设准,一方面这是人类尊严的根本要求,同时这也是现代社会成立、法治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公平和效率问题也同样如是,人类平等的绝对性根源于宇宙的道德属性,而人的后天(也有某些先天成分)才能的差异则形成劳动分工与资源分配上的诸多等别,这既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冲突,也是一种现实人类的必然性。基于人格平等建构所有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尊严,同时依据个体才具的差异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不同机制和状态,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是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均需要满足的条件。同时,我们这里可能需要对所谓平等尤其是基于平等的社会公平多说几句:公平基础上才有根本性的效率,这就是罗尔斯强调的机会公平问题,虽然他是从功利主义角度论证的,其目的当然是让已经信奉人类功利主义原则的所有人信服他所不得不做的新契约论证明。即便是推崇自生自发秩序的哈耶克,也更多是从避免理性设计或政治结构对人的基本自由产生限制的层面出发的,这个自由是人人都有的,这就是平等,而所谓的博弈首先是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进行的。因此,平等是所有问题开始的条件,也是自由的条件。我们承认现实社会中的差异和不等,但不能将其论证为先天的,人在人格上的平等是第一位的,然后推论出机会的均等,然后才是社会的现实分工的不等。如果要让人们自觉地接受社会分工带来的差异和不等,必须有一个人格尊严的平等性要求,以及这种差异和不等必须是基于一种公平原则而来,这样,这个社会才能有一个道德和法律的共同允可的基础。
中国哲学尤其是从阳明以后,十分重视人的平等关系,而孟子则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石,即人人分享先天道德的根基,人人皆能根据“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展开自己的天德良知本体,进而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现实世界都是一样的,尤其是才能上可以是而且必然是不同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德是人逻辑上的性,才是生物学的性,才是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界分德与才的二元结构是试图说明人有双重存在属性[17](P541)。在德性层面,人人分享天道的平等和尊严;而在现实层面上,由于人的生物性的差异,天命则会存在性别、种族和职业的分殊。一个理性健全的社会制度结构要同时满足这二者的二元次序,但以确认人的尊严为前提。中国所谓传统的天下社会并未能满足这个条件,人的尊严的个体性被掩埋在国家实体的普遍性中,这个天下主义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所以从所谓“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分别得不出人是不平等的结论,而从儒家自身看,恰恰应该说,从德具上,人是平等的;从才具上,人是不同的。德是宇宙的根本,是生命的本体,应以人类平等的要求来建构社会制度,以市场来调节才具的差异,但又要以德的要求来约束它。如果说我们这里和政治儒学家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人不是先天不平等的,而是先天平等的,才也是先天的,但在逻辑上相对于性而言是第二位的。我们必须依据德来确立人的先天平等原则,然后根据才的不同并通过劳动分工发挥各自的才能,同时根据德之尊严的要求,让人不在劳动分工中受到歧视,这就需实现个体性原则的展开。
牟宗三认为,古代中国就是一个文化观念,即伦理观念,也就是天下观念。个体存在是一个伦理的存在,而没有成为政治存在,这是前提性的问题。在传统中国之政治治理方式下,理念上都是德或以德为目的的,但是在现实中则不是或根本得不到。“在中国,五伦就是自然律,这与权利义务的订定以及对于权力安排的订定根本不同”[19](P43)。中国古代政治的哲学表述就是:“凡是运用表现都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这二者皆在免去对立:它或者把对象收进自己的主体里面来,或者把自己投到对象里面去,成为彻上彻下的绝对。”[19](P45)彼此成为隶属关系犹如中国的家庭和国家皆如此。这种隶属关系将“打天下”与“坐天下”形成一个惯性和理念,政道就是要从根本观念上予以纠正:“政道:此即安排政权之道。”[19](P46)把打天下的非理性转为理性,把“总体的持有”即“天下人的天下”抽象的、形式的确定,这种确定的客观化就是形成一种制度使之成为永固的形式化的存在,也就是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固定,政权成为永远,治权才是流动的、变化的。“这一步构造的底子是靠着人民有其政治上的独立的个性,而此独立的个性之出现是靠着人民有其政治上的自觉,自觉其为政治上的存在”[19](P46)。将在政治上无所事事只是一个被动的存在的个人转为人民与皇帝成为“敌体”,即独立的和对立的存在者。如果政权只是武力得之,人民没有政治上的独立个性,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所以,古代中国只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不是一个国家单位,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二)伦理化的天下观与个体主体性精神的确立
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早熟,只有合理的自由,没有主体的自由,但是不等于这种自由不会发育出来而成永久的停滞。他区分了普遍性原则与个体性原则。实体意志即古代中国尽伦尽制而成就合理的自由,也就是国家在伦理层面的发展达致极盛,因此,也不能说个体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个体在其中也是自觉的伦理服从的,但这种自由却又不是自觉的,而是未经反省的,因此缺乏真正主体的意义:“他不有真实的存在,在‘统一体’中不能有其真实的责任与义务。即依此义说为‘偶然’,精神在此落了空。”[18](P62-63)牟宗三受到康德、黑格尔极其深刻而且是有益的影响,即强调人的精神的自觉。牟宗三认为人的精神的自觉是人能够独立于这个世界的前提。在中国古代“天下国家”中,只有普遍性的原则,实际上只是宗法一体性原则,而不是个体性原则,个体精神汩没在整体性中。如果使人自觉到这种个体性,自我精神便是人的解放的根本要素,而这种个体性精神从实质上说就是自由意志。他因此对中国古代“天下”这个“大实体”做出了精神性的批判:“中国只有普遍性原则,而无个体性原则。普遍精神,若没有通过个体之自觉而现为主体自由,则主体精神与绝对精神间之‘对反’不能彰著。此而不能,则‘大实体’所代表之‘统一’亦不能有机地谐和起来,即不能通过各个体之独立性而重新组织起来。此而不能,则国家、法律所代表之客观精神亦不能真实地表现出来。在周文之‘分位之等’上、尊尊之义道上,吾人已说有客观精神之表现。但须知此客观精神是在宗法形态下表现,此即黑氏所说:‘主体的自由不是在其自身寻求它的尊严,而是在那个绝对实体中寻求它的尊严。’后来的忠君爱国,亦是此意。依此,大实体所代表的‘统一’弄成硬固而僵化、虚浮而挂空,法律亦成为某种固定而抽象的东西:此即黑氏所说的‘散文式的帝国’,一种‘平庸的理解之形式’的帝国。”(6) 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63页。牟宗三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对中国传统帝国统治的评价,认为所谓“大实体”即皇帝自己作为主体的实体。黑格尔认为家庭精神是中国国家精神背后的哲学,他说;“在这种发展阶段上,我们丝毫看不到任何‘主观性’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任何个人意志的反省,以及这种反省和那强大的‘实体’(所谓的实体就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倾向于消灭个人)因素的对抗。人们从来也没能意识到自己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同这种‘实体’结合成一体,从而知道自己在这种‘实体’内部是自由的。中国人从来没能做到这一点。”潘高峰译《黑格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25页。 牟宗三对古老帝国的抨击是基于个人自由和平等的批判,精神的解放是回归个人的自主精神,而这个精神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存在的,这就是存在于个体身心之中的天道。天道觉醒其实就是个人的自觉,获得这种自觉,个人的解放得以实现,个人现实的具有独立性的平等也由此开启。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言:“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性情、学问、境地造就不同人生体验,那么对同一事物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由于原画失踪,只能从目前搜集到的不完整的诗歌入手,对《青松红杏图》的主旨一探究竟。 先谈题画诗,可分为以下几种:
这个道理非常深刻,但当下尤其是政治儒学家及与其同调者们似乎又开始倒退起来,把一个抽象的“天下”观念重新坐实搁置到当代中国头上,而没有经过一个民族国家概念转折的天下观念是非常成问题的,特别是这种观念又将传统的伦常法与近代契约法律混淆起来,这是非常遗憾的。这种混淆涉及伦理之天下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内涵的认知问题,二者是根本不同的。所谓“伦常法”不是法,只是伦理道德关系,最多是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自然法”。严格来说,中国儒家传统之“天下”不是一个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只是一个模拟家庭伦理的设定,不具有真实性。而近代以来由西方发始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的基础是个体以及个体权利和义务的界定,它们都具有法律规定性的安排与保障。我们即便从超越民族国家的角度看现代“世界性政治建构”,也应该有一个非伦理的设计,而不是一个伦理性构造。伦理构造既不能解决政治实体之间的贯通问题,也不能解决个体在新的政治实体中的真实存在问题。这个真实存在首先应当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存在,因为政治实体的扩展从相互关系看,是陌生人之间的“相互性”(reciprocity)问题,而不是伦理层面上的亲情或家庭关切问题。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一个政治实体扩展的法律机制的完善,即首先保证个体在民族国家之中的权利保障,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对边界的穿透和民族单位的政治实体的超越。但是,这也不是说中国儒家的相关观念完全无处可施,从孟子、阳明的良知概到儒家的“精英意识”,对建构新的全球社会来说还是有其用武之地的。
(三)公民、良知感通的天下与士君子的全球社会
今天人们讨论所谓真正的天下主义,实际上还停留在概念层面。第一种是结构主义的整体化,但是强调要有一个类似的“大家长”,但是这个大家长除了美国二战以后的霸权稳定机制外还没有一个合理的国际机制安排。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国际政治体系,不是松散的而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目前似乎还不可能,只能依靠历史演进的逻辑慢慢推展,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在做这个推展方面的设计。另一种是中国传统类型的无远弗届,其实是一种传统中心模式,以文化修饰之,是伦理和礼教复合的伦理主义天下观。这种伦理主义的天下观,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下,在民族国家对立和宗教文明之间紧张的态势中,不可能发挥更大功能,但是其中的一些观念如良知、士君子等的涵育、培养,则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后文会论及。上述二者核心都是王天下主义,对于传统中国的所谓伦理天下主义模式有双重依赖:一个是圣明的君主,一个是合理的理性的官僚体系建构。而两者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君主与士大夫都必须是无私和忘我的,所以其理想主义殊可钦佩。但是,在现实性上却存在严重的疏漏和缺环,以至于很难落实。
从对治当代世界的宗教紧张乃至于冲突言,良知可以构成不同宗教的交集与共同的支点,笔者在《良知与全球秩序》中曾指出:
第一,理性的世界公民的训练在国家公民建设中。
或认为,现代社会以主体性之倡导而导致个人主义的盛行与泛滥,进而倡导主体间性:或曰主体性相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而主体间性则对应于社会关系,我想这二者是相互的。在社会维度,既有主体性的诉求,同时也有主体间的结构性即相互主体性的要求,他们以“相互性”为原则,而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则要思考民族国家的“主体间性”之结构,这个国家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结构目标则是超国家的。现在对于超国家机制的建设核心,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个体性之指向与民族性之内向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导致倡导民族性的集体本位与倡导个体性的个体本位之间形成某种张力。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作为人类分子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个体之中的普遍性即人类性,这里的人类性并非指人类的整体,而是指人类的人性,即个体性的本质指向人性本身,这是全世界之人类之共性,是与超国家的世界普遍性追寻相一致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今天以现实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各个人类个体都是以民族成员身份出现的,以国家公民身份存在,因此这种个体性的人性同时受约于既有的民族性特性与国家体系规范,二者之间既具有相互的依存性,也存在着某种矛盾。我们这里试图申诉的仅仅是个体人性的普遍性与超国家的世界普遍性趋向具有内在的一致之处,它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冲动,无论我们对这种冲动的认识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需要正视它。
孙向晨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中曾指出,霍布斯意识到了国家整体意识问题,但在他那里似乎难以解决或协调。“在霍布斯的论述中,个体对于国家的认同和贡献都是非常薄弱的,甚至只能通过一种交换,即国家保护个体,个体奉献国家来加以解说,这成了霍布斯的难题”;“在霍布斯所论述的‘契约’关系之外,卢梭认识到了国家的整体意志问题,也就是‘公意’问题”,试图凸显政治民族的整体性。孙向晨进而认为,“个体本位和民族认同共同铸就了现代国家,表现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于是‘民族’的概念把前现代基于等级观念的人在新的个体文化环境中重新凝聚起来”,“在均质化的个体中建立了族群在文化上的差别认同,对内则建立起均质化的文化,这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展开创造了条件。人类整体的均质化文化或者说‘大同文化’一直是乌托邦思想家的梦想,但在现实中真正行之有效的却是差异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个体本位和民族意识认同之间的内部张力是民族国家失败的因素之一,但是现实世界依然是以民族主义为基本建构原则的,这样世界性的大同文化便成为乌托邦[20]。上述论述既展现了人类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继续推进的困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些希冀,即个体的均质化的扩散,它是民族主义的解毒剂。当然,这也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它具有建设和破坏双重性质。那么,如何既推进个体意识的泛化向世界公民方向转化,又削弱其消极的破坏性,就成为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这就是理性公民在国家层面的建构问题。
所谓心者,非仅一团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者也,此所谓良知也。然而无声无臭,无方无体,此所谓“道心惟微”也。以此验之,则天地日月四时鬼神莫非一体之实理,不待有所彼此之比拟者。古人之言合德合明、如天如神、至善之诚者,皆自下学而言,犹有二也。若其本体,惟吾而已,更何处有天地万象。此大人之学所以与天地万物一体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尽处,不足谓之学。[26](P1608-1609)
孟子的“天民”从他的意思理解就是“士”,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士,而是按照孔子说法“得仁”的士。说他仍然是士,一方面因为这个天民并无任何爵位、等级或官职;另方面,这个“天民”无官职却有“志”并有“觉”,其能全尽天理,同时其道可行于天下则行之,不可行则隐之。这个天下不是诸侯国,而是人类社会,此天下是普通人的天下。
健全形式多样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建立健全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的监督机制,把国防动员军民融合发展落实情况,作为党管武装述职和每年向人大、政协报告工作的必要内容,并对述职和工作报告作出客观评价,为提拔使用干部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结合双拥模范城评比、文明创建等活动,定期对各级、各单位、各系统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在表彰评先、税收补助等方面实施奖惩激励,提升全社会参与军民融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
论及孟子的天道、天民思想需要溯及两位前辈学者,一位是著名的法学家吴经熊先生(4) 吴经熊先生较早地讨论孟子思想与自然法问题,他有一篇专论《孟子的人性论与自然法》,载氏著《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一位是哲学史家葛荣晋先生。这里着重引征葛荣晋先生的观点略作论证。葛荣晋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孟子的天人合一说。他认为,先秦的天人合一有五种模式:一是绝对的天人合一,二是天人相通,三是天人感应,四是天人合德,五是天人合道[13](P636)。所谓绝对的“天人合一”是殷代以前上帝观念统御的阶段,天命归于上帝。所谓“天人相通”是孟子的观念,葛荣晋先生指出其有两重含义:一是人天并非对立,而是息息相通的整体;二是天乃人伦道德的本源,人伦道德原于天,所以天道和人道是合二为一的[13](P638)。天人相通的根据有二:其一,以心性释天。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仁义忠信为天爵;尽心,知性而知天,天性与心性是合二为一的,宋明儒家继承并弘扬了孟子的思想。其二,从政权转移的角度看,权力并非君王私相授受,而是天授与民受。特别是民受与不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民心决定天意,这是孟子对天命论的一种修正[13](P639-640)。葛荣晋先生与前述劳思光的看法比较一致,与现代新儒家的牟宗三、徐复观等先生的看法也基本相同。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无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25](P79)
所谓理性的国家公民建设,按照康德的意见,就是法律共同体和道德共同体的并建。我们这里特别强调一个法律共同体的建构,康德所构想的一个法律共同体的三个先验原则是:(1)作为一个人的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2)作为一个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3)作为一个公民的每个共和国成员的独立[21](P74)。罗尔斯将公共理性确定为公民之间的关系结构,他将“相互性”(reciprocity)作为公民关系的基本前提,这是他在《万民法》中关于公共理性的核心概念。罗尔斯的“相互性”是对康德理论的现实化,但是他们还没有展开的一个是说理的论证,这一点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开。哈贝马斯强调理性的公开运用,即强调一种理性的说理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实现。哈贝马斯说:“如果我们从程序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实践理性概念,我们就会认为,有效的正是那些在话语条件下获得主体间自愿承认的原则。接下来,就是更进一步的经验问题:在世界观多元化的现代社会背景下,有效的基本原则何时才能确保政治稳定。”[22](P80)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一种个体公共性的普遍要求,立足于实现个体在政治结构中基于个体权利与义务都能有效保障的方式,这是对个体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结构的共同要求。但是对于没有世界政府的人类社会来说,我们如何建构一个政治结构,这首先是一个程序主义的问题,因此,仅从这一点说,哈贝马斯的立论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即基于公民理性在国家层面乃至世界层面的“理性自觉”,商谈说理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人类建构未来共同体的路径要求之一。但是这一点首先要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得到积极有效的训练,这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公民训练。理性的世界公民建构其实首先是国家公民的建设,是国家公民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二重建设,它为培育良好的人类共同体创造了个体的道德和法律条件,并对可能破坏理性的那些因素(无论它是暴力强权还是宗教狂热)都有一定的阻滞防范作用,它是作为人类走向整合的、理性的、建设性的因子而存在和发展的。
良知作为仁体成为个体生命的根据,同时又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据,这个政治生活一方面是儒家的“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同时又是与现代人权概念相一致的。这个一致性在于“良知”也提供了个体生命在天地间的终极性意义和完全独立性的价值根据,即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宇宙公民,这个意义是终极性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可以开始讨论一个独立的个体因其内在的良知的呈现而形成的自由状态,也才可以讨论良知之承担而造就的个体行动的自由与自主,因其独立性而承担的责任、义务以及由此生发的权利等等,更不用说良知自在地显现的个体的道德正义(7) 黄玉顺教授最近也注意到阳明学的个体自由可能性的问题,参见李海超 黄玉顺:《阳明心学的真精神:个体自由可能性的敞开》,江淮论坛,2017年第6期,以及一篇会议讲稿等。 。同时,良知的万物一体还给出了一个“儒家社群主义”的证明,当然它是整合的不是小共同体的,既有类于斯多亚学派,又不同于他们。斯多亚学派的理性、逻各斯仍然不具有道德情感的意义和价值,而阳明的良知一体论则将小到一个家庭,大到至大无外的宇宙,都一体整合起来,是所有层面的社会共同体都可以凭依的道德基础和道德根据,它实际上同时建构了儒家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一个综合体系,这是在西方思想中难以达到的思想和精神体验的高度。这里所说的“自由”即源于良知成为本体的可能及其现实,良知作为宇宙本体和个人本体的共在,确定了每一个生命的独立的尊严和价值,这即是个体生命之真正平等的源泉。
2.重构商业模式,重新定义生产者与顾客之间的关系。大数据在营销领域中主要是处理与人有关的数据。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人的需求,人的行为,必须思考商家、产品和人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产销模式是“先产后销”,是以生产者为主导的供应链,顾客只是最末端的接受者;大数据引领的C2B商业模式是“先销后产”,是以顾客为主导的供应链,生产者根据顾客的需求实行个性化定制服务。大数据确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全方位的市场营销新模式,产品从刚开始生产就已经决定了将来的归属。
我们设想一种理想的天下主义基于三点:第一,普遍意义的个体性概念的成立,即人类之普遍的个体之成立及其认同,同时,这个个体是理性的公民,是接受国家法律和人类道德价值的个体,这是人类共同体的基点,由此培养之并逐步扩展之,而其培养的源头是国家公民的培养,从国家公民的理性化推展到世界公民的可能性;第二,依据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家之“万物一体”之共同体论消弭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建构以良知为根基的社会价值;第三,在人类法律共同体之可能性成立之前,以儒家之士君子为社会肌体建构的重心之一,在国家和全球市民社会两个层面建设“士君子”社会。
良知既是天道的贯通,又是主体自身的挺立与彰显,具有超验与经验的双重特征。良知恰恰由于依赖于自我把握而不借助于教士、神父,而能使主体意志获得完全的表达。
良知的可经验性又在于它基于每一个人在日常中都能感知的个体身心的道德灵感,正直、悲悯、助人等等一切善良之行止都是良知的发用,只要保养、发挥、扩充就有高扬的可能,这正是非宗教徒所能接受的一种德性的生活,这正是中国儒家之修养不离日用常行的特点。良知的超越性与内在性、本体感悟与日常发用的统一恰恰可以构成全球伦理之不同宗教之间、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公约。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劝善的宗教都发源于人类的良知之心,既然它是一切宗教与德行生活的根源,当然它也就可以构成全球伦理的共同的基础。[27]
增值税会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确定当期应交增值税及利润表中的增值税费用,在核算应交增值税的会计科目设置上,笔者在《规定》的基础结合申报缴纳实务稍作修改,以期更加简化、逻辑关系更清晰,下文仅对修改部分进行说明。增设损益类科目“增值税费用”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增值税,核算时对企业的购销业务与相关增值税计算抵扣视为不同的业务,分别予以确认计量。首先,按照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确认资产、收入、成本、费用等会计要素,并按“含税法”计量;其次,按资产负债观收益计量理念确认计量增值税费用。
从个体与人类共同体的一体性来看,良知的万物一体之仁是宇宙众生共在的根基,是个体作为宇宙公民、家庭成员及社会成员或国家公民的共同的本然基础,它是我们人类共在共享的哲学根源,从此出发才能建构一个有根基但是又不狭隘的世界政治哲学。
2.2 NAFLD组与对照组CD4+CD25+T细胞结果比较 NAFLD患者外周血CD4+CD25+T细胞百分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第三,士君子与公共性“全球社会”的培育
个体精神的确立不等于个体在现实世界中与他人毫无联系或根本对立,这是两个问题。今天无论是讨论天下主义还是国家政治架构,都需要在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平衡上有合理的把握。但是,显然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生活于不同文化和历史中的人群,其解读和认知存在严重分歧。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中国国家建设,还是人类共同体的建构,都离不开一个所谓精英群体的形成和带动,这是我们和当代政治儒学家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但是其中仍然有一个重要的分歧,即我们强调的是“士君子”,而他们偏重的是“士大夫”,前者是平民而后者是官僚精英。但是,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说,平民和精英的交集是德性君子及其涵养。政治儒学的方向是使君子努力参与“为政”,构成钱穆所说的古代“士人政治”的范型,士大夫既是社会的管理者又是社会的教士,既发挥道德教养的“化”的功能,又发挥政治管控的“治”的功效。
如果我们还能接受钱穆以及当代政治儒学所谓的“教化”是一种“化”的话,那么对赵汀阳的所谓“化”我们就很难理解了。赵汀阳认为“无外”就能化外,而且认为这是中国先秦诸子共有的思想特质和方法论:“它决定了中国思想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思想,简单地说,它注定了中国思想中不承认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the transcendent),也就是那种无论如何也‘化’不进来的存在。”这导致中国没有宗教和异教徒等等。又说:“西方思想框架是人(主体)在‘看’世界,在这个知识论框架中,凡是主观性所‘化’不进来的东西就是绝对外在的超越存在(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主观性不能为之立法的东西),这种绝对逃逸在外而绝对异质的东西只有两种:上帝和他人。于是,上帝非指定为万物之源,而他人特别是异教徒就被认定为死敌(如果一个他人与我同心同德则只是个自己人,不算是他人)。承认超越存在的理论后果就是在宗教以及与人为敌的政治理论。这是西方思想的底牌。”从个人主义、异教徒到丛林假设,都与承认超越者有关。中国不承认绝对外在的存在,因此等于是另一种思维方式,是另一个天地:“可以说,西方思想可以思考冲突,但只有中国思想才能够思考和谐。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在逻辑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论和方法论,在逻辑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思想,这些完全不同的思想对于未来世界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建设性依据。”[7](P14-15)赵汀阳将超越性存在作为现代民族主义之间冲突对立的根源,显然失之偏颇,因为无论就世界历史还是古代中国而言,不同民族、宗教和宗族之间的冲突,既有诸神的对抗,也有权力争夺的斗争以及利益争夺。中国不承认绝对外在的超越存在,但是承认绝对的实际的现实的“主宰性”的事实存在。西方的外在超越决定了一个个体的真实性、独立性和为精神性掌控的努力,中国的现实性无外决定了它的世俗性价值的存在和一个现实的实际的最高统治对于每一个个体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作为“天下”中“臣民”存在的属性。没有这个现实的无外的最高统治者,我们的无外就失去了“归一性”和“实在性”,天道、天理的存在最终和一些世俗价值及其最高现实关联者——皇帝或天子——联系到一起,这是我们中国的无外和大一统之间的内在关系。
摘 要:高校教育资源体系生态化构建战略主要是按照生态化管理的要求,保证高校教育资源体系能够以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为根本目的,促进生态能源资源体系的科学构建。其与传统的高校教育资源体系的构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注重生态化的高校教育资源开发,通过科学、系统、合理的分析,实现高校教育资源的开发、整合以及利用,从而以保护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的再生性为根本目的,构建生态化高校教育资源体系。
其实,西方更是“无外”,因为都无外于“上帝”之下,而中国传统则无外于“皇帝”之下。西方思想恰恰依赖这个外在存在超越了现实王权的束缚,这是它的积极意义。在中国传统中,真正在部分意义上意欲超越现实王权的只有两种尝试性努力:一种是董仲舒式的天道超越,但在董仲舒这里却成为一次不成功的实验,因为这个天道没有真正成为超越主宰和所有个体之信仰,所以并不能构成一种针对全社会的具有普遍性的制约力量。另一种是所谓儒家的道统式超越。道统虽然在现实世界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它涵养了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和士人精神,这种精神在世俗社会或市民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按照托克维尔的三原则,美国民主有三个支柱:法律体系、乡镇自治和宗教,即基督教精神。后来贝拉等人又循此考察美国精神的脉络及其可能的兴衰,而成就《心灵的习性》,总体表现了美国立国精神的基本方面:即在道德共同体(宗教类型的)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建构,这个道德共同体的发轫,即贝拉等人对新英格兰奠基人温思罗普作为清教徒和绅士的描述,他们在1630年弃船登岸之际,在船上发布了一篇“基督仁爱之楷模”的布道书:吾辈务须互悦互爱,为他人设身处地,有愉同欢,有哀同举,同劳作,共患难,视他人如手足,待全民如一体。贝拉等认为,这些清教徒对物质繁荣并不感兴趣,即便成功也把它当做上帝的恩典,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道德和精神的社会共同体[28](P41-42)。贝拉等人在讨论公民生活时指出:“凡是我们谈话接触到的人,几乎都同意吉姆的看法,认为美好的生活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一是个人事业的成功,二是为社会服务得到快乐。他们还认为,这二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这位加利福尼亚银行家在总结自己满意地度过的生活时说:我工作一直很卖力,从未辜负过我的雇主,也从未辜负过我的社区。”[28](P294-295)上述引文说明两个问题:首先,人类共同体的政治生活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这个基础依赖所有人对公共生活的共同接受与认可;其次这种生活需要一部分人的杰出带动,这就是上述温思罗普等人的典范作用。这也就是中国儒家士君子的样式,虽然他们处于不同文化或文明体系中,但是这些共性说明人类对于公共生活的道德意识是普遍的,儒家士君子也是热心于公共生活的典范,虽然他们需要以忠孝节义的模式出现,但是这种根基是共有的,所谓“忧患意识”或“先忧后乐”的精神等等,不胜枚举。但是,恰如梁漱溟早就指出的,西方人相对于中国人的长处或国人没有过的生活是公共生活,梁漱溟希望重建伦理性的生活模式,同时他又列举了四条西人所长而中国人所短的特质: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制精神[29](P67)。将中西结合起来的方式就是将道德的意识和公共生活的观念整合起来,这种精神的拓展就是从个体出发可以直达人类共同体的精神意识,它可以被理解为士君子精神:从宇宙公民的个体性与人类普遍性的二元一体出发,构建一个全球市民社会,逐步扩展不同文明中的士君子群体,成为全球社会之公共生活的带动者、协同者、鼓舞者。这是我们今天在国家建构和世界建构中可以展开的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工作。
正畸治疗主要通过各种矫正装置来调整面部骨骼、牙齿及颌面部的神经及肌肉之间的协调性,以达到口颌系统的平衡稳定[4]。正畸治疗前,医生需对患者面部外观、口内牙列等进行评估后,再选择合适的支抗进行固定矫治。而固定作用直接影响矫治的成功率,因此,稳定的支抗是口腔正畸治疗的关键,优良的设计是矫治成功的基础[5]。
世界性的上层建筑何以构成?至今可能还没有答案,我们能做的是构建国家文明体系和推动全球市民社会发展。杜威说:“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参与一种有共同利益的事,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方向,这样的人在空间上大量地扩大范围,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活动的全部意义。”[30](P97)杜威所说的民主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文明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是从文明教养诸如儒家“反求诸己”和现代权利文明的论理文化之统一(8) 近年,陈嘉映教授、童世骏教授等一再倡扬“说理文化”,这是现代文明的理想的存在方式,也是国人在公民意识和论证层面上所普遍缺失的,它是西方论证文化和辩护文化的自然延伸,需要我们汲取和发展之。另参见拙作:《论经学、新子学与哲学的当代并立——从当代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建设相互关系的视角考察》,《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 。文明必须是个体权利的文明、法治的文明和礼乐的文明有机结合起来的整体性的文明,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文明。构建全球市民社会和文明的国家法治体系,即是规则建构的推展,即建筑在个体意识基础上公民意识和理性人类认同的发展,是文化修身的推展,是文化的而非等级的礼乐文明即人类普遍的教养文明的扩展,是以良知为根基的弥合文明冲突的共同价值的推展。我们或可在上述推展的基础上,再以联合的方式促进世界的一体化,如此,或可实现新的意义上的天下主义。
参考文献:
[1] 干春松.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李洪卫.良知与正义:中国自然法的构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3] 黄玉顺.“以身为本”与“大同主义”——“家国天下”话语反思与“天下主义”观念批判[J].探索与争鸣,2016,(1).
[4] 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
[5] 许纪霖.新天下主义与中国的内外秩序[A].许纪霖,刘擎主编.新天下主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6] 姚中秋.华夏治理秩序史·天下[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
[7]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8] 十三经注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11]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 陈来.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三个主题[J].天津社会科学,2007,(2).
[13] 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 朱熹.孟子章句集注[A].四书五经:上册[C].北京:中国书店,1984.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6] 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17] 冯友兰.贞元六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8] 牟宗三.历史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9]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0] 孙向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J].探索与争鸣,2014,(9).
[21] Kant.Kant Political Writings[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3.
[22] [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3] 吴震.论王阳明 “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J].哲学研究,2017,(1).
[24] 董平.“差等之爱”与“博爱”[J].哲学研究,2015,(3).
[25] 王阳明全集:(上)[M].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6] 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M].吴光,等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27] 李洪卫.良知与全球秩序的构建[J].河北学刊,2006,(4).
[28] [美]贝拉,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M].翟宏彪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2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A].梁漱溟全集:第三卷[C].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30] [美]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The Way of Heaven Citizen of Heaven and Global Society—— One Compendium of Individulisitic Cosmopolitanism Based on Ideas of Citizen of the Universe
LI Hong- wei
( School of Marxism ,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Tianjin 300401, China )
Abstract: The deba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 cosmopolitanism doctrine has developed into two types of doctrines. One is the doctrine marked by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itual system; the other is the doctrine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autonomy formed by the human nature being inconsistent with the universe. The reason why individuals can achieve noumenal freedom and equality is the human nature through which the way of the universe passes. The concept of citizen of the universe, which confirmed one’ s identical value with the universe. This concept thus affirms the dignity, freedom and equality of individuals in human society, transcends the cultural concep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identity and ethics, and construct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al sense of citizens of heaven can advance two points on human identity: firstly, the concept of“ conscience” may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communicating among different religious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second, the expansion of“ gentleman groups” serves as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universal development of global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cosmopolitanism; Law of Heaven; citizen of theuniverse; dignity; conscience
中图分类号: B222;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 2019) 05-0027-015
收稿日期: 2018-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国家观的近代转变研究”(18BZZ027);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支持项目
作者简介: 李洪卫,男,哲学博士,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