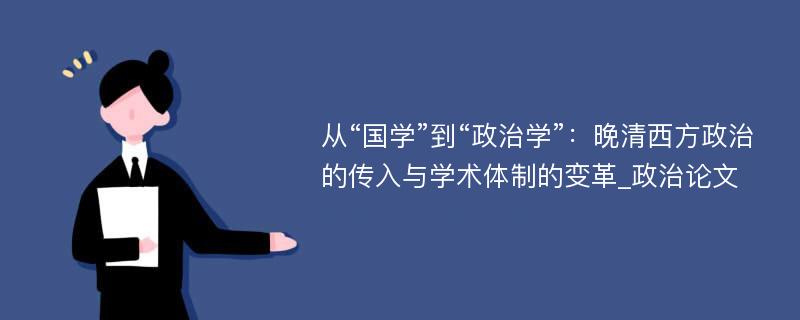
从“国家学”到“政治学”:清末西方政治学的引入与学术体系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清末论文,体系论文,学术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12~0055~07 虽然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经历了几次较大的变动,但学者对其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史实和一般脉络还缺乏充分的研究,无论是历史学研究领域还是政治学研究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①因此,从源头上重新梳理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历程,无论是对于历史学的研究还是对于政治学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伯伦知理与“国家学”体系的初步形成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关注国家的学问,“政治学是各种各样的国家以及社会为了弄清直接面对着的于自身所处时代的诸课题,并把提示出的解决方法和策略作为自己的任务的科学”,“政治学的作用是以同社会对话为开始,并以同社会对话为结束的”②。但是,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最初阶段,社会知识群体是否对政治学也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说,当时的政治学研究者是否对政治学也有这样清晰的学科价值定位? 梁启超曾把翻译西书的重要性提升到实现中国自强之路第一步的高度,“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③。而事实上,梁启超的确是西方政治学著述在中国译介传播的先行者。1899年4月10日,《清议报》第11期开始刊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著,这可以看作是具有学科意义的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但是,目前学界关于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起点的界定,大多都采用王一程先生的说法,即“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④,但这一说法并非确凿有据。在目前国内学界出版使用的大部分政治学教材中,也基本采用了“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这一说法,但均未指出这一论断的出处。⑤与此同时笔者关注到智效民先生的一个说法:“赵先生还说:既然要开政治学课,就需要政治学教材。中国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的讲演录(翻译本),出版时间大约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⑥。引文中所说的“赵先生”即是我国政治学界的泰斗,北京大学的赵宝煦先生。此外笔者还发现,赵宝煦先生曾在自己的回忆性文章中这样叙述过:“1898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到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⑦事实上,也只有智效民先生明确指出了这种说法的确切来源,因而笔者大胆推测,上述学者所引用“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的说法,可能来自于赵宝煦先生的个人回忆,或者说极有可能是部分学者与赵宝煦先生交流后采信了赵先生的说法,因而有了目前学界的这一基本界定。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笔者已有的考证,尚未发现1898年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译著,也没有发现相关的抄本和讲演录,因而笔者依旧把西方政治学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界定为目前可以考证清楚的基本史实⑧,即:从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开始,西方政治学通过日本作为中介载体逐步传入中国。 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学术体系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分析国家沿革的历史,从政教分离的视角阐释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第二,提出“神道政治”的概念,对亚里士多德国体、政体的分类标准进行补充;第三,强调国家“有机体”学说,对卢梭的政治理论加以批驳。需要指出的是,伯伦知理所构建的“国家学”学术体系模式,在后来影响了众多东方国家的政治学学者,这其中也包括日本学者高田早苗。⑨ 伯伦知理关于国家理论的论述,首先是从宗教与政权分离的角度展开的:“以学理释国家之意义,实自希腊人始也。昔时东方诸国之惑于宗教者多矣……迷溺宗教,牢不可破”⑩。“该教(指基督教——引者注)之兴也,原非藉王公之力,其主权又非受之于国家,不过托渺不可知之所谓天神者,以立宗旨。故自罗马国中有此教,而政教遂分为两途”(11)。伯伦知理关于国体、政体类型划分的理论来源则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国体,有名异而实相类者,有名同而实相反者,今一据希腊人之原则,唯就主宰官,以判别其国体而已”。“今欲审说政体之名实异同,不可不先敷衍且弥缝亚利斯土路(即亚里士多德——引者注)之分别论”(12)。于是,伯伦知理将国体、政体分别划分为三类:“古代希腊人别政体为三种,学者至今皆依据焉……曰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合众政治。又别其变体,曰暴主政治、权门政治、乱民政治”。“盖主权者,能自制私欲,以谋公利,则目其政治曰正体,反之曰变体”。(13)值得注意的是,“政体”与“正体”并不是同一种说法的不同表述,而是存在一种包含关系,即“政体”包含“正体”与“变体”这两种类型,而与“政体”相对应的则是“国体”。当然,或许是由于译者的疏漏,该书中存在将“政体”与“正体”混用的现象。 伯伦知理并没有全然接受亚里士多德对于国体、政体的划分理论,而是提出了“神道政治”的概念:“虽然古来别政体为三种者,未可谓至矣尽矣。盖三种外,更加神道政治一种,则始备矣……神道政治,以天神若人鬼为国之真主。故其根本既与自余政体不同”(14)。虽然有学人认为神道政治并没有脱离亚里士多德对于国体、政体的划分体系,但伯伦知理仍旧认为神道政治是一种特殊的“异样”政体,可以与其他三种政体产生不同的结合方式。需要指出的是,伯伦知理对于神道政治这种特殊政体形式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方今国民,苟以文明自许者,莫不以神道政治为诈术诡道,凡政略含此臭味者,一切排斥,以为鄙陋有害”(15)。那么,世界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当时各国实际采用的政体到底是何种类型呢?伯伦知理直接抛出了自己的结论:现存的政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多行于欧洲的代议君主制,另一类则是多行于美洲的代议共和制。 上文笔者主要论述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沿革理论与国体、政体分类理论,但伯伦知理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学发展最为重要的贡献却是其提出了“有机体”学说,这是伯伦知理针对卢梭学说的创造性发明。或者我们可以认为,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学术意义便是其作为卢梭学说的“反对者”:“以国民为社会,以国家为民人聚成一体,此说由来尚矣,而德国政学家独以新意驳之曰:国家有生气之组织体也。徒涂抹五彩,不得谓之画;徒堆积碎石,不得谓之石偶;徒聚纤维与血球,不得谓之人类。必也彼是相依相待,以成一体者也。故国家者,非徒聚民人之谓也。非徒有制度府库之谓也。国家者,盖有机体也”(16)。 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影响深远,直到抗战时期仍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而这一理论对梁启超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梁启超在其各类文章甚至是“未来小说”中多次提出“有机体”这一命题,以彰显自己独特的政治认知:“凡人群皆有机体,所以随时发达成长。西人自治制度皆日日进化,非如中国一成不变也”(17)。“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事,况于数十年后乎”(18)。 在日本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伯伦知理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高田早苗就继承了“国家学”的学术体系。事实上,这种继承关系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强调国家对于各类政治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把政治学的关注点集中在“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之上:“盖国家云者,于确定土地上,以治者、被治者之关系而团结人类之谓也”(19)。但是,从政治学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出版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包括其“有机体”学说的影响力就每况愈下。 因此,在以伯伦知理为代表的“国家学”学术体系内,“政治学”与“国家学”实际上具有相同的含义。而在这一阶段,“政治学”或是说“国家学”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国家本身,例如国家的沿革与定义、国体与政体的划分、宪法与政府权力的制限等等。而对于公民社会、政治团体这些我们今日熟知的政治学研究内容,“国家学”体系却没有涉及。相较于小野塚喜平次在《政治学大纲》中对于政治学研究体系的划分,笔者将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这一阶段称之为“国家学”体系时期,而小野塚喜平次则是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另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笔者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政治学”体系时期。 二、小野塚喜平次与“政治学”体系的系统构建 从“国家学”学术体系向“政治学”学术体系转型的最主要的代表作,便是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清末时期,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出版版本与次数都相对较多(20),其中商务印书馆刊印的《政治学》、《北洋法政学报》刊载的《政治学大纲》等译本传播较广。事实上,《政治学大纲》是参酌《政治学》的基本内容修改而成的,因而两者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只是略有表述的差异而已。在下文的论述中,笔者将主要以出版时间相对较晚、论述较为成熟的《政治学大纲》为例,研究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学术体系的系统构建。 《政治学大纲》一书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研究政治学的学科概念、体系划分等问题;第二部分属于国家理论阐释部分,主要涉及国体政体的定义、分类等问题;第三部分则主要针对国家的内政、外交等政策展开论述,既提及了国家机关的运行,又研究了实际的政治现象(国民行为)。应该说,这三部分主题明确、界限清晰、体例完整,因而《政治学大纲》是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研究基本问题的重要著作。 小野塚喜平次在开篇便回答了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基础性、前提性同时也是根本性的问题,即:何为政治学,政治学的定义与范围是什么,政治学与其他诸学科的关系为何。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商务印书馆刊印的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一书的序言中,该书汉译本的作者郑篪认为,“政治学于世界诸学科内成立最后,吾儒则以为道德之支流也,西国政家则以为术而非学也”(21),这可以看作是晚清学人对于西方政治学概念的差异化理解。 小野塚喜平次认为存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的递进关系,即:宇宙——常识——精密智识——学。(22)基于这样的知识体系关系,小野塚喜平次提出了“广义政治学”这一概念,“关于政治社会之学”即是广义的“政治学”。为了论述“广义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小野塚喜平次明确指出了政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边界、区别与联系,并特意区分了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实际上“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彻底分离的互动关系,并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政”、“法”分离。因而小野塚喜平次没有纠缠于“政”、“法”之间的界限问题,而是对二者的内涵与互动关系进行了解释:“或谓政治之范围,较大于法律,盖法者以国家之法,行于国家认许之下者也。故其法规之设定施行,亦不过政治政策之一手段而已,从此点观之,研究此学问,固已含于研究国家政治之学中”(23)。“法者,有分科独立之性,何则,盖法者虽为政治之手段,然已为法以上,其自身有惰性,于政治为反动,故亦得从政治分科,而为独立之一体也。若政治虽因其政策终局之见解,亦不能脱出法规之范围”(24)。 前文已述,在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学术体系内,“国家学”等同于“政治学”,而小野塚喜平次则利用“广义政治学”与“狭义政治学”的概念对“政治学”的定义进行了区分,“广义政治学者,合关于国家之种种学而成者也;狭义之政治学者,以国家事实之说明,及其政策基础之学也”(25)——正是这种区分,将“国家学”与“政治学”的关系再次进行了明确。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明确区分,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政治学”学术体系的初步构建阶段。当然,这也是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学术体系取代伯伦知理“国家学”学术体系的重要体现:“人类社会之现象,其关于国家者,即政治学也。日本所谓政治学、国家学诸名词,悉属广义;而广义政治学,与国家学同一解者。致有精理,盖关于国家现象之学,即为政治学。二者有密切之关,在欧洲则政治学与社会学亦相同。……自研究日精,而法律、经济等学,分枝别类,各成一科,而政治乃渐成狭义。夫学问日进一日,则范围即日小一日。政治之学,苟其以相关各学,兼容并色,则研究愈难精密,此所以今之所称政治学。”(26) 不仅如此,小野塚喜平次还对政治学研究的学派,或者说是政治学研究的路径进行了分类。而实际上,这种划分也说明,这一时期学者对于政治学的研究,已经从“国家学”的体系中挣脱出来,进入了英美“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已经从对国家理论的探讨,进入了对社会现实、政治现象、国民行为的研究。“政治学中,往往尊纯理为形上,鄙应用为形下,此一谬也。又有谓纯理近于空谈,应用乃有实效,此又一谬也。……二者关系甚密,皆不可偏废者也。……政治一学,纯理、应用当同价值”(27)。而这种转变,可以说具有了早期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初步特征,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进行了转换——实现了从“纯理”到“应用”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小野塚喜平次在此时已然认识到当时政治学研究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政治学的研究并不一定客观公正。第二,政治环境会左右政治学的研究结论。第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术语尚未系统形成。他指出:“研究学问,不外乎以一己之经验,主张学说;然而事有万变,岂能悉当,况乎他种学问,皆以我身立于客观之地位,而下公平之判断”(28)。“夫学问有研究之法,即有门径可得。政治学以何为研究之普通方法,迄未能定。术语者一科之专语,凡学皆有之。政治学所用术语,如立宪共和,种种名词,尚未明了确切”(29)。 对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清晰划分是“国家学”学术体系向“政治学”学术体系转变的重要标志,而另一个转变特征即是小野塚喜平次强调对政治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小野塚喜平次明确提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政治现象,“政治现象,即政治学之目的物也”(30)。在政治现象的研究中,小野塚喜平次认为需要重点关注国民,“国民于政治上可分为二,曰舆论,曰政党”(31)。将舆论与政党系统地纳入政治学的研究体系,是小野塚喜平次对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重要贡献。而在“国家学”学术体系的视角下,对于舆论与政党从未有过系统性的学术研究。 除了对舆论与政党的关注外,小野塚喜平次还对国家的内治政策进行了特别的论述,并主要研究了社会劳工问题与外交政策问题。小野塚喜平次认为,内治政策虽然要讲求众民自由的原则,但更应注意这些政策的制定应该存在“合理的差别”(32)。值得注意的是,小野塚喜平次在对社会劳工问题进行阐释时,引入了大量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其对社会主义并不持赞成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破坏少数之有财产者,使悉归于平等”,是“牺牲优势者之地位”来达到“劣者为同等”(33)的目的;同时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体系中,“人人依赖国家,不能自由行动”(34)。 与此同时,小野塚喜平次还特别强调利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学,强调从政治现象、政治行为背后发掘深层的政治学因素,这些尝试与西方在20世纪上半叶所提倡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很多相同之处。“政治学研究之资料,即社会上之事实也,有统计学取社会事实而荟萃之,则便利孰甚。例如计某国某种犯罪之数,则可知其政教风俗;计某国财政上以某事经费与某事经费,比较其额之多少,即可知其政策之轻重之点”(35)。再比如小野塚喜平次在对两党制进行研究时,并不是仅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去阐释,而是更多从政治现象本身来探讨两党制在政治活动中的实际表现,并由这种实际的政治行为得出一定的政治学论断:“保守与进步,乃对待之称,论其大体,则进步必喜改革,保守则否,而实际上亦复时有转移。当少数执政之时,进步党欲移少数于多数,保守党则欲维持此少数,故反有进步之意。及多数持政之时,保守党欲移多于少数,进步党则欲维持此多数,而反有保守之心。一彼一此,其心同也”(36)。“政党内阁之国,必为二个之大政党;非政党内阁之国,必为多数之小政党”(37)。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小野塚喜平次将政治学的研究从简单的理论阐释转向了对社会政策、政治现象和国民行为的关注与探讨,这种做法具有了早期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初步特征。至此,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也从“广义政治学”的研究视野渐变为“狭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从对政治学理论的阐释渐变为对政治现象的关注,最终实现了从“国家学”的学术体系到“政治学”的学术体系的转变。 三、从“国家学”到“政治学”的学术体系转型 19世纪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形成的重要时期,查尔斯·E·默瑞阿姆曾在《政治学的新方位》(New Aspects of Politics)一书中对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作出了以下四个阶段的划分:“到1850年为止基于先验的、演绎的方法之上的政治学的时代;从1850年到1900年为止基于历史的、比较的方法之上的政治学的时代;从1900年以后到1920年代以观察、调查、测定为志向的政治学的时代;自此之后开始的政治的心理学研究的时代。”(38) 事实上,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引入过程中,其研究重点、理论框架与学术体系的形成与转变也符合默瑞阿姆的划分。而这种转变在清末时期最好的体现,就是伯伦知理“国家学”学术体系与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学术体系的转换。但是,“国家学”体系与“政治学”体系并不是两种截然对立、界限明晰的学术体系,并不是一种体系与另一种体系的简单替代关系。在“国家学”体系阶段,就有学人对“政治学”学科的体系进行过清晰阐述:“(政治学——引者注)学说包甚广,宜分类研究。……如伯伦知理,分国家学为国家学泛论,国法学,及政略学三种;又有分政治学为国内政治学,及国外政治学二种者。而国内政治学中,又分宪法及行政二科,国外政治学即万国公法是也”(39)。再比如,“政治学者,有研究国家之关系与研究国家与国家之关系之别。研究国家之关系者,称之曰国内政治学,又曰国法学。研究国家与国家之关系者,称之曰国外政治学,又曰国际法。然二者外,又有为两学派之普通者,即国家之性质、国家之起原、国家之意义、国家存在之形态是也。研究此普通之部分,曰普通政治学”(40)。因此,从伯伦知理“国家学”学术体系到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学术体系的转换,实质上是一个逐渐清晰的渐变过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清末各类政治学译著中,除了“国家学”、“政治学”这种学术表述外,“国法学”一词也频繁出现。那么,“国家学”与“国法学”究竟与“政治学”是何关系,三者是否具有同一含义,是否有一定的包含关系?还是说,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根据已有的材料,狭义的“国家学”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国法学”,即主要研究国内政治的学问,在这一范畴内,“国家学”即“国法学”。而广义的“国家学”又可以等同于“政治学”,在“国家学”体系阶段(例如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中)可以相互替换。但“国法学”却不等同于“政治学”,两者并不具有替代性。例如,“所谓国法学者,定国家体制及运用之法律之学也。说明国家学为何,虽属国家学之事,然说明国法学,不可不知国家之概要”(41),这里的“国家学”和“国法学”就没有替代关系。再比如,“故国家学者,即集合人民之心思财力以经营公共事业之大团体,而定此团体之编制以明其发达之法式,谓之国法”(42),这就对“国家学”和“国法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解释。 上述引文中所使用的均是广义的“国家学”含义,它的体系内涵比“国法学”要广,但还有另一个例子:“国法学乃学问中一种法学学问,即国家之统治组织及统治作用之法学也”(43);“法学者,俟社会外部的组织后,规定人与人相互行为之社会现象学也。……如法学、政治学,则有社会有形之秩序也。法学一种,国法学附焉。国法学一种,法学、司法学、行政学亦附焉”(44)。上文引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笕克彦《国法学》一书,而在此时“国法学”已经不再纳入狭义的“国家学”体系之中,而是直接并入法学的研究领域。 因此,从上述文献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国家学”与“政治学”既存在混用的关系,又存在区分的现象。而这种复杂学术分类的背后,实际上是德国政治学与英美政治学之间的冲突与转换。高田早苗就直接指出了这一实质:“德国所谓国家学(Staats wissenschaft),英国所谓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皆统括国家之性质组织作用等学问之总称也,而兹之所谓国家学原理(或又称为普通政治学)者,则仅为其总论耳”(45)。而实际上,虽然高田早苗用“国家学原理”来命名其著作,但他同样也用“政治学”一词来进行理论阐释。可见,“国家学”与“政治学”在理论内涵与学术体系上,既有重叠、替代的关系,也存在区别、对比的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20世纪初的日本政治学界,也存在笔者所说的两种学术体系的转变。“仍如所认为的那样,假如这前后两种政治学均在我们早稻田大学里得以应用实施,可以想象的是美国的政治学风应用在我们大学部里的是使实际研究得以盛行,而德国的政治学风应用在我们的研究里则鼓吹的是深邃幽悠的研究态度”(46)。 我们必须指出,除了伯伦知理的政治学学术体系属于德意志的“国家学”体系外,包括那特硁(47)、高田早苗、杨廷栋(48)在内的其他政治学研究者的著述,也属于这一体系。甚至包括小野塚喜平次本人,在其《政治学大纲》的理论阐释中,仍然可以找到德意志“国家学”的影子。但是,日本政治学学者腊山政道却认为,小野塚喜平次依旧努力尝试把“政治学从对其束缚的国家学里独立出来”(49)。如果说德意志“国家学”的学术体系是以国家为研究视角的话,那么小野塚喜平次则是以“政策”与“治理”为新的研究维度。我们也可以说,小野塚喜平次把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从“国家”下移至“社会”、“团体”甚至是“个人”。 行为主义是“能够而且应该对政治行为进行科学的研究,特别是通过使用定量方法,旨在创立完全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政治科学”(50)。如果以成熟的行为主义研究定义来讨论小野塚喜平次的学术体系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认为小野塚喜平次的研究不属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范式。目前学界多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成熟于二战后,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行为主义”更是“科学”研究政治学的代名词。但事实上,强调政治学研究重视政治现象,提倡政治学研究利用量化方法的这种政治学研究思想的出现,要远远早于上世纪40年代。或者说,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二战前就出现了具有早期行为主义研究基本特征的政治学研究。而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与所关注的视角,就应属此列:“在东京大学正在不断探究德意志流的国家学以及有国法学色彩的政治学的时候……政治学(指早稻田大学的政治学——引者注)就已经从法学和国家学里独立了出来,不是观念的,而是实证主义的对政治进行研究的传统已经被逐步地建立了起来。……根据这些人士接连不断的努力,实证主义的科学政治学以及政治科学的柱石被最终奠定。”(51) 此外,相较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中译本多是“忠实”地“抄袭”日译本的情况,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在近代中国的译本则多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增补,呈现出了不同译本的作者对《政治学大纲》的“再加工”。需要指出的是,伯伦知理《国家论》在清末的流行程度远不及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也被各类书局重译、再版(52)。但是,关于“国家学”学术体系与“政治学”学术体系的渐变与转换,却并没有停留在伯伦知理与小野塚喜平次的年代。 四、结语 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最初建构的学术体系是以“国家”、“宪法”为基础的,是围绕与国家相关的诸多问题形成的“国家学”学术框架,而在这一框架下,国体、政体等问题又是其中最为核心与关键的组成部分。伯伦知理便是这一学术体系构建的代表性人物。应该说,这种体系建构与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学的理解是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政治学学术体系的引导下,从国家视角研究政治学是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形式。 小野塚喜平次所著的《政治学大纲》一书,将政治学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了公民社会层面,其不再仅仅追求理论层面对于政治学的探讨,而是追问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学因素。除此而外,小野塚喜平次对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强调从广义与狭义这两个角度对西方政治学进行定义与划分,并厘清其他相关学科与政治学学科的界限与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野塚喜平次奠定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的学术基础。 事实上,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与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学大纲》代表了两种不同范式的西方政治学学术体系——前者是“国家学”的学术体系,而后者则是“政治学”的学术体系。在“国家学”的学术体系中,政治学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国家本身,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学术体系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延续。而在“政治学”的学术体系中,小野塚喜平次强调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提倡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手段对政治学进行研究,这其实也代表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至此,在清末的最后十多年间,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不仅完成了传播的工作,还承担了学术体系转型的任务,从德国政治学的传统转向美国政治学的前沿是这种学术体系转型的最终目的。但实际上,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引入的最大使命并不仅限于此,它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政治走向和社会思潮的启迪要远甚于它在学术层面的影响。 注释: ①截至2015年9月,国内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孙青:《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孙宏云:《学术连锁:高田早苗与欧美政治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之传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王昆:《晚清政治学学科发展研究:1899~1905年》,《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其中,尤以孙宏云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②(49)(51)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161页、第163页。 ③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④王一程:《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及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⑤例如在王邦佐编写的《新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明军编写的《政治科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许耀桐编写的《政治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和沈文莉编写的《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政治学教材中,均采用这一说法或类似表述。 ⑥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⑦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⑧孙宏云先生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杨廷栋撰写的《政治学教科书》首次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内容(见孙宏云:《杨廷栋:译介西方政治学的先驱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6日,第B03版)。而笔者所见该书的最早版本为作新社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十月二十日版,既晚于赵宝煦先生所说的1898年,也晚于笔者所提出的1899年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著。因而,笔者仍旧把1899年4月《清议报》刊载伯伦知理《国家论》译著作为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系统传播的起点。(关于《国家论》一书更为细致的考证,除了法国学者巴斯蒂女士的相关论著外,另可见王昆:《梁启超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1期) ⑨高田早苗对于日本政治学的发展来说意义巨大,是具有奠基作用的学术人物。虽然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影响了高田早苗的学术态度,但高田早苗并非完全承袭“国家学”的学术体系。 ⑩(11)(16)伯伦知理:《国家学纲领》,广智书局,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第1、3、7页。 (12)(13)(14)(15)伯伦知理:《国家学》,东京善邻译书馆,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第50、46、47、49页。 (17)(18)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4页。 (19)(45)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版,第8、1页。 (20)中山大学孙宏云先生经过考证,发现清末时期流行的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的译本大致有七类。详见孙宏云:《小野塚喜平次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1)(22)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三日,序言、第6页。 (23)(24)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丙午社,光绪三十三年,第15、16页。 (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北洋法政学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第16、14、21、25、30、27、157、193、195、196、12、175、176页。 (38)Charles E.Merriam,New Aspects of Polit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1,p.49.转引自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39)高田早苗:《政治学研究之方法》,《译书汇编》第6期,1901年8月8日。 (40)戢翼翚、王慕陶:《政治学》,《政艺通报》第7期,1902年6月6日。 (41)(42)有贺长雄:《国法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版,第1、2页。 (43)(44)笕克彦:《国法学》,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三年仲春,第1、4页。 (46)《早稻田学报》1915年1月号,第11页。转引自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2页。 (47)目前国内学界对于那特硁的研究甚少,那特硁几乎成为一个被忽视的历史人物。但从其学术价值与实际影响力看,则非常有研究的必要。参见孙宏云:《那特硁的〈政治学〉及其在晚清的译介》,《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 (48)由于杨廷栋所译的《政治学》、《政治学教科书》、《新编国家学》等著述的内容基本一致,而其又与伯伦知理等人的著述无太大差异,因而在前文的论述中,笔者并没有介绍其著述的相关内容。 (50)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思想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52)例如民国元年刊出的署名“张锡光”的《政治学》亦是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的汉译本。此后民国二年、民国三年等时期,亦有许多小野塚喜平次《政治学大纲》的译本重印、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