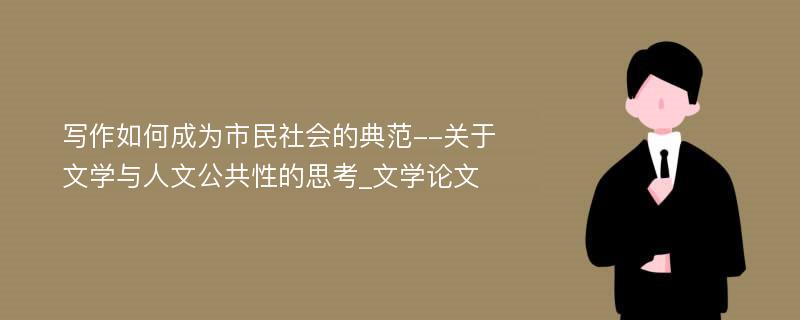
写作如何成为公民社会的典范——关于文学及人文学术的公共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范论文,公民论文,人文论文,学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在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获悉自己成为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这一消息的时候,他正在纽约访问,并正在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记者安赫利卡·阿维列拉女士问道:“几分钟前,你曾建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多读点诗。那么,你建议墨西哥总统做什么呢?”帕斯毫不犹豫地答道:“也是读诗。”这是一个诗人对政治家的建议。在旁人听来也许会觉得有些好笑。这是一个乖僻的、书生气的建议吗?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吗?政治家真的需要读诗吗?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读诗又有何益?
实际上,对于国家政治而言,诗即使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有害于城邦的谎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华美但却无关紧要的装饰品,除非那些政治家们打算用这些华彩言辞来诱骗公众。诗,既不能使经济增长,也不能使国民所得有所增加,又无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甚至,也从没有过谁依靠一首诗来征服敌国或消弭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对于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来说,诗,并非政务的急需。而政治首脑应该有更多重大的有意义的事情等着他去做:国家行政事务、国际外交、社会发展计划,等等。另一方面,对于日常生活而言,诗歌更可以说是一件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不用说是政治家,就是对任何一位平民而言,读诗也决不会比一场球赛,甚至是一条股市行情来得更为重要。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一定要求人们在诗歌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上面浪费宝贵的时间呢?作为诗人的帕斯应该很清楚这一点。然而,帕斯却似乎丝毫不以为忤。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几年之后去世了的话,我想,他大概还会固执地向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首脑提出同样的建议。我不知道布什是否接受了帕斯的建议,在打完了海湾战争之后也去读上几行诗。这并不重要。事实上,诗人帕斯是在这里向所有的人发出呼吁,希望诗歌(以及文学,乃至整个人文性的写作)能够进入他们的阅读空间。
在帕斯看来,文学至少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事情,不仅如此,它甚至是一个社会保证其健康的文化精神的必不可少的事物。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由那些有情感、有心灵的人所组成的共同体而不只是一堆经济、政治事务的话,那么,就会同意帕斯的说法。然而问题在于,不是写作行为本身直接介入了公共事务。写作对现实的影响,乃是在写作行为已然完成之后。而写作本身并没有多少公共性可言。
写作,尤其是文学性的写作,首先是一件发生在私领域内的事情。许多类型的文化活动,比如,文艺表演、文化教育,以及诸如演说之类的政治性的言论活动,具有较强的公共性。这一类文化活动往往需要在公开场合展开,并需要与公众之间有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它直接介入公共领域,并对公共事务产生重大影响。而写作则不同。一般而言,写作不具有在公共领域里公开展示的功能。当人们面对一个书写文本(比如,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等)的时候,所见到的是一个已然完成的作品。写作是写作者在孤独状态下完成的动作。
与写作行为的孤独性相一致,书写作品的文本内部也是一个相对孤独的空间。一个作品一旦完成,即有着相对稳定的形态,而且要求作品有一种内在的自足和自我完善的特性。文学作品遵循其美学上的完满性,学术作品则遵循其逻辑上的完满性。这种相对独立、自足的完满性,并不会轻易随外部环境和舆论力量而变化。
还有一重孤独性来自阅读方面。文学的阅读空间也是相对孤独的和自足的。尽管文学会被拿到公共场合下,为众人所分享,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文学还会表现为公众情绪的原动力和催化剂,比如,在政治运动中,诗歌会在广场上朗诵,并激发起众多听众的情绪。但这都是文学的非常状态。在现代传播的语境下,作为印刷符号的文学文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单个作家的个人的话语。在通常的阅读状态下,读者与作者,是两个孤独的个体之间的互相打量、注视、倾听和理解。
在文本的私密领域内,文本拥有其自足性,但它并非一个自闭的空间。通过传播和公众的阅读行为,文学的话语空间向公共领域敞开。文学在其内部空间,模拟公民社会的状态。在文学的空间里有激情,有忧伤,有美好的事物,也有人间邪恶(被批判的邪恶)。帕斯在访谈中继续说道:“不只是政治家们应该读诗,社会学家和所谓的政治科学(这里存在着一个术语上的矛盾,因为我认为政治的艺术性比科学的艺术性更强)专家们也需要了解诗歌,因为他们总是谈论结构、经济实力、思想的力量和社会阶级的重要性,却很少谈论人的内心。而人是比经济形式和精神形式更复杂的存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要恋爱,要死亡,有恐惧,有仇恨,有朋友。这整个有感情的世界都出现在文学中,并以综合的方式出现在诗歌中。”① 从帕斯的表达中可以看出,他将文学写作看作是对社会的精神空间的一种虚拟,而且是那些其他文化形态不可替代的部分的综合呈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文本空间里相互交往、对话、冲突,通过阅读文学,人们在陌生的事物和人群之间寻找理解。人们习得甄别合理的不合理的事物的能力,并最终在阅读终结的时刻,反思现实世界的缺陷。如果可能的话,并加以改良。
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舆论,也不提供舆情参照,但文学可以反应单一个体对舆情的情绪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又是一种特殊的舆情。但从文学的生产方式上看,与公共舆情有着根本的差别。文学首先是一个个体的创造活动。首先是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体的自我充实和自我完善为基础的。公民有权选择介入或者是疏离公共事务。作为一名有较强文化能力和话语权力的公民,作家和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言论影响力显然要大于普通公民,因而,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相对要多一些。但这并非文学写作的根本。作家往往会选择远离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性,来建立自己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必要的距离,摆脱现实利害关系的制约,以保证作家对现实公共事务的独立评判和批判立场。人文学术也有同样的特征。倘若文学自身尚未获得自主的意识,其现实“介入”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一种舆论,成为某一社会阶层(有权势的或无权势的)的代言工具。
1950年代至1980年代,当代中国文学却是一种至少看上去“公共性”极强的文化门类。大批的革命文学作品的普及率,绝不亚于今天的畅销读物。而诸如关于《红楼梦》、《水浒传》的评论,则几乎是全民性的运动。在这几十年里,文学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起着顶部装饰的作用,将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芒反射出七彩的颜色,美化了公众生活领域的灰暗。文学家则在公共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公众的教导者和拯救者的角色。但这并非因为文学家有着特别的人格魅力而堪称道德典范,相反,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们在基本的人格尊严和艺术品格上,乏善可陈,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甚至还不如普通民众更有道德感。公众对文学的相对较为强烈的热情,也不意味着国民有着普遍强烈的文学需求和高水准的文学鉴赏力。文学享有这种过分崇高的地位,有赖于背后的政治强力的支撑。文学话语不过是政治话语的柔化版,在社会运动最热烈的场面里,借助政治强力的文学的高亢声音,看上去像是一种狐假虎威的表演。
在今天看来,文学的这种“公共性”首先来自公共生活的一体化,文学不过是这种一体化的公共生活中的较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形态之一。依照某种权力的指令,文学家像外科医生一样,致力于公众的思想改造和灵魂重塑的手术。这样,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当代文学是那般的高贵和强大。然而,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大和意识形态禁锢的松动,当代文学的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就暴露无遗。
长期被误解的“文学公共性”的虚假性一旦被揭穿,文学就不得不面对自身在“公共领域”及“公共事务”中退场的命运。建立在作协机构、报刊出版、学院文学教育等文学制度之上的垄断性生产关系面I临挑战。在大众文化时代盛大的文化筵席上,文学不得不屈居一隅,在次要席位上分得一些残羹剩饭。虽然在主流的文化格局的等级秩序中,文学依然高居文化金字塔的顶端,但显然已不再居于公共言论舞台的中央。文学家的角色在公众视野里备受冷落,文学的声音也变得可有可无。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文学充其量只能自救了,拯救社会或拯救公众的宏大理想,变得不切实际。文学尚未真正建立自身内部的价值,要想在社会公共领域引导价值,如果失去了外部强力的支撑,就只能被公共文化所抛弃。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呼吁自身的独立性,试图挽回自己的尊严。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自律性的试验,是文学恢复自身主体性的尝试。1980年代,一个写作者如果不能在公开出版的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话,就没有可能获得作家的头衔,没有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说,公众没有可能知道他们,自然也就没有可能认可他们。先锋诗歌则是例外。1980年代的前卫诗人一直是以民间诗刊的方式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聚集同仁诗人。诗歌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民间传统。这一传统被称之为“第二诗界”。“第二诗界”的规则与主流文学界的规则正好背道而驰。不能赢得民间诗刊认可的诗人,在诗歌界恰恰没有地位。与此相反的路向是汪国真。汪的诗歌尽管还不属于“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但已经具备了诗歌娱乐化的雏形,他通过迎合公众趣味和媒体造势,达到了宣传上的成功。
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遗产,即是试图建立文学自身在价值上和美学上的内在完整性。事实上,这一传统始于“文革”后期。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来自民间青年知识分子的隐秘化的文学书写(如“今天派”诸诗人的写作)依然绵绵不绝,而且,在今天被视作198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源头。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派”的文学书写,并非依靠积极和公开地“介入”当下的公共生活来赢得其公共性,相反,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为公众所知晓,它是以对一体化的公共生活的疏离和回避,来赢得自身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派”诗歌或“文革”期间的地下写作缺乏对公共性的关注。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今天派”中的北岛、江河、杨炼等人的诗歌,乃是日后所谓“新时期文学”对公共领域的文学“介入”的典范。而那些持较为纯粹的唯美主义立场的诗人和作家,甚至会对北岛他们的诗歌过于强烈的“介入”色彩持批评性的态度。
毫无疑问,我们很容易在文学史上找到作家介入公共事务的范例,比如,雨果、左拉、萨特、索尔仁尼琴等作家,以他们的写作,直接干预了现实事件的进程。他们也因之被视作社会的伟大“良心”。这一类的写作触及到现实的公共生活中的某些部分,而且往往是那些较为显著和影响重大的部分。但另一类写作者,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的作家,却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极度淡漠,他们在私密的空间里完成了对一个内在的精神空间的探索和批判性的摹写。但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对自己时代的生存经验的揭示和批判而言,普鲁斯特、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在深度和强度上,都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极限。
一般而言,在个人的审美领域与公共交往领域之间,有一种“不可通约性”。个人性经验一旦进入话语领域,就会遇到很多麻烦。文学家需要面对的首先是个人,是个人的内心。他常常以逃离公共生活领域、疏离公共事务,来获得对公共性的独特的关注。萨义德在谈到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时,做了如下描述:“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这需要稳健的现实主义、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复杂的奋斗,在一己的问题和公共领域中发表、发言的要求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就是这个使得它成为一种恒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② 这种状态,既是知识分子的,也是文学家的和艺术家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陈寅恪的意义。当几乎所有的学者和作家都在忙于为现实涂脂抹粉的时候,陈寅恪选择了寓居岭南,与世隔绝,专心为古代的一位身份卑微的风尘女子立传。
文学以及人文学术的写作所建立起来的“书写理性”,它与公民社会的政治理性相类似。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并有权选择自由表达的方式和对象。虚构性写作、纪实性写作、学术性写作和批判性写作,凡此种种基本的写作类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公民社会意见表达的诸种方式。个体的独立性要求和内在的精神律令,是建构其公民主体的基本保证,正如文学和学术遵循其自身的美学的和逻辑的规律。
另一方面,每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又是无限敞开的。文本与读者之间,构成了一个奇妙的交流装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交流并非简单的单向灌输和控制。读者有权随时抛开手上的任何作品,如果他对它不满意的话。他甚至可以因为愤怒而撕毁手中的书,这也是正当的行为。从这种理想的文学阅读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的公民社会交往伦理的雏形。通过阅读关系,作者与读者共同建立起一个微型的有关美学和价值的“精神共同体”。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由是开始形成。
重返独立的文学精神空间,这不仅意味着作家需要捍卫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同时也意味着作家的文学书写需要营造一个独立的和自我完善的话语空间。前者是文学独立性的精神驱动力,后者是文学独立性的生存空间。从这一点出发,文学的公共性问题的进一步的要求,则是公民对于阅读、书写等精神生活的需求和空间的建立。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即是建立在这一系列独立的个体精神空间单元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及其阅读)乃是公民社会的行动典范和价值典范。
注释
① 奥克塔维奥·帕斯:《太阳石》,朱景冬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
②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