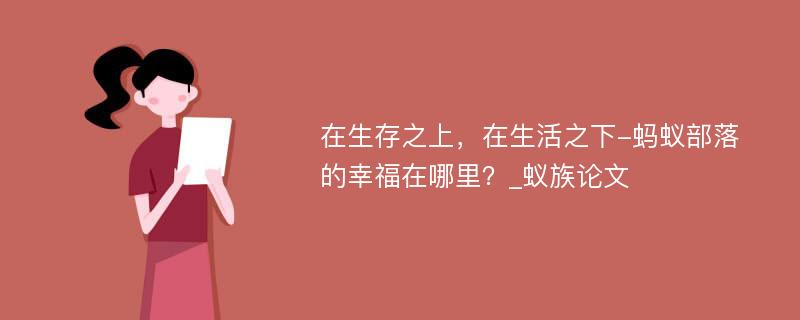
生存之上,生活之下——“蚁族”的幸福在哪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幸福论文,蚁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起初,《蚁族》的火爆,让廉思有些不习惯。
这本书他是自费出的。此前,这个80后学者曾受北京市政府委托,率队对北京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地的青年聚居现象,进行过长达2年的深入调研。向出版社自荐的情形还清晰地记得。
“首印8000册。”
“太少了,我这本书肯定能火。”廉思争取。
人家还是淡淡的,“每个到我们出版社的人都这么说……”
刚开始真还挺平静,但年底一部叫《蜗居》的电视剧播出了,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开始了,“梦想还有没有执著的必要?道德是不是很可笑的坚持?做海萍还是做海藻?要小贝还是要宋思明?”
同样有梦却居无定所、有知识却两手空空的蚁族,也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成为2009年底最热的词。热到什么程度?近百家媒体,不仅国内还有国外的,包括日本共同社、法国路透社、俄罗斯塔斯社……纷纷架起摄像机,来到唐家岭,不停地拍摄。中央高层也开始关注蚁族群体。
草根阶层、大学毕业生、聚居村、第四大弱势群体、卑微姿态、期许情怀……蚁族,取代振臂一呼、风云变色的人间王者,成为“时代”关注的对象。
他们高擎火把而来,却成为古希腊悲剧里为命运所捉弄的神。
主体是22岁到29岁的80后,聚居在北京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城乡结合部,普遍月收入为1000至2000元。七八个人一间房、七八十人一间厕所,每月房租300元(就这300元,不少人还交不起,躲着房东)。那里有坑洼不平的路面、横行抢道的黑车、疲倦的年轻人坐着拥挤的公车,从城里归来,回到村里小小的寓所。
“北京竟有这样的地方!竟有一群同龄人这样生活着!”
这是廉思第一次带队去唐家岭,大伙儿唏嘘的感慨。“当公共汽车的门关上时,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错过了这辆车,就错过了这个世界。”这是调研员张冉的一次晚归经历。
“失落的世界”,荒凉如斯。
调查证实,竟有数以10万计的青年在聚居村栖身——这还仅是北京一地的数据。随着《蚁族》一书的出版,不断有数据反馈回来,几乎在所有的省会城市,包括一些二线城市如焦作,都有这样的聚居村。生活之窘迫,堪比农民工、下岗职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迥异于前两者:均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0%来自于211重点院校,90%来自于普通院校、民办高校。这一点,发人深思、令人惊觉。
这就是传说中能借“知识改变命运”的一群人?
“一个重视知识的国家,掌握知识的人却过得不好:国家还没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有知识的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时代的后面……这是为什么?”坐在我对面的廉思抛出第一个重磅级问题。
与其说是问我,不如说是对时代的苦苦追问。
2.
“蚁族”陈华或许也在问。当他经过一条大学的河边,看到漂亮的女孩子站成一排、陆续被小汽车接走时。
他没有愤怒,只是轻轻叹口气,提醒自己更努力。这只“蚂蚁”身上凝聚了人生教科书上教导的要素,勤奋、乐观,永不言弃。你会惊讶命运为什么还要给那么多一波三折。
陈华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考研失败,开始了求职的旅程。他坚持不啃老,啃馒头,最多时啃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拿到offer,在北京一家文化发展公司做推销培训,底薪只有800元,不解决户口,不提供三险一金。
“有点饥不择食了。”陈华笑。
饥饿还在后面。两三个月之后,因为成绩平平,这工作丢了。陈华又开始在某商学院做起了营销,对这第二份工作,他也很珍惜,把展开“易拉宝”、在街头做推广的经历,都视作有趣的经历。可他最终还是失去了它。
生存至上,生活至下。为了生活,陈华去街头发过传单、帮婚庆公司舞过狮子,实在不能变劳动力为人民币的日子,就去图书城看书,站着看那些关于求职和营销方面的书,指望着“今天看,明天就能用上了。”最困窘的时候,连28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这时,屋里种的一盆蒜苗就成了最大的安慰,起码有了它,一顿下饭菜就不愁了……
调查者杜韵竹笔下的“蚂蚁”陈华,是个动人的形象,当他拿起笛子、闭目吹起《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简直是幅唯美的图景,笛声里传递了不该属于他的寂寞忧伤。
邓锟是我想记述的第二只“蚂蚁”。《蚁族》一书里的《聚居村村民序》就是他写的。廉思介绍,“邓锟是个有思想的人。”
生于1984年的邓锟是山西人,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北上的原因很浪漫,为了爱情。在人脉全无的异乡,他开始了一切全靠自己打拼的日子:在某医院的医疗器械中心上过班,也被传销组织欺骗过;考过研,最终失败了;谈过恋爱,最终也失败了。《蚁族》一书的出版,也未改变他的命运,几天前邓锟还给廉思打来电话,老师,我现在在卖数码相框,您要吗?
白天的邓锟,是沉静的、忙碌的、微笑着的……一天清晨,好友狄群“揭穿”了真相:“昨晚你哭了?”
“没有啊。”
“怎么枕头上湿了一大块?”
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情,不是哭泣,是哭了自己还不知道。
出去接受采访,邓锟常常遭遇好心的“建议”:为什么不回家?他不作答。怎么答?说学“生物工程”的回去后更惨吗?当地一个官员很雷人地问过,“这专业是不是养小动物的?”说父母不同意他回家吗?蚁爸蚁妈眼中,娃留在北京就是北京人了!说比起家乡,他宁可相信北京的一线光明?这都市多少允许你凭借个人努力找到工作,而地方上的“门阀政治”和“豪强垄断”,更让人无法呼吸……
陈华与邓锟代表了广大蚁族的共同困境:不乏知识与文凭,也愿靠双手改变自己家族命运,却与幸福缘悭一面。为什么?
3.
“纯粹胡扯!知识改变不了命运。我被骗了!”
“4年前,我用一袋钱换了一堆书,4年后,我这一堆书换不回一袋钱,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互联网上不少蚁族质疑的声音。
“它反映的是目前高等教育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廉思分析,“通过4年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是断裂的,有时一个专业设置,并未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就匆匆上马。怎么能不耽误人。”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如一高校设立一个新专业,学生家长咨询,老师,这个专业是干嘛的呀?招生老师答,我不知道。出来以后是不是分去某某部委?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招收的是200人而不是150人或250人?还是不知道。
那为什么设立这样的专业?很简单,学校有师资、有宿舍、又能赚钱,那就招人呗!这样培育出来的学生,你怎能保证不是次品、废品、保证他们在人才市场上受欢迎?
其次,大学里传授的内容,也值得商榷。很多大学教给学生的不是技能,而是偏研究型的,但市场哪里要得了那么多研究者?在廉思团队设计的问卷有一个选项,“你认为高等教育给你带来了什么?——知识的丰富?英语水平的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很多人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一纸文凭。”
“我们去德国考察,在宝马、奔驰,一个经过专业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其受社会尊重的程度和工资水平,并不亚于大学毕业生。所以,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对扩招也有建议的,不是说扩招不可以,但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职业教育与精英教育齐头并进,这样我国才能成为真正成为一个资源大国。”廉思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曾经为大学定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梁任公也为学术、学问正名。放眼世界各国,教育于国民福祉之影响,举足轻重,GDP增长,只能称雄一世的,而培养有创造力、有担当的年轻人,却可泽被百年。难怪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先生措辞深切:“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大的变动,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
另一方面,追究外部原因之外,新一代“知识青年”,不妨从自身找找出路。
2009年12月16日,《南方周末》登出头版文章,探讨杨元元的人生之路,标题触目惊心、似曾相识——《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这个自杀的女研究生,几成“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代名词。但引起笔者格外留意的是同年12月14日,著名人生发展咨询专家徐小平,于博客上写下的文章——《盲目考研杀了杨元元》。文中说,“考研要有明确的职业目标,要和人生现状相结合,不能盲目,更不能为了户口、身份、社会地位这些本身就不真实的价值目标。对于杨元元这样家庭极其贫穷的大学生毕业生而言,救穷如救火,当务之急是把十年寒窗学来的知识投入到增加收入的活动中去……”而不是陷入学位帽越来越高、生活质量越来越低的恶性循环。
机制的改变,非一日所能达成。相比那些希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呼声,这样犀利,清醒而自觉的提醒,对广大青年人来说,现实意义、可操作性更强。
广大蚁族中,也有看清时势、破茧为蝶的人。如郑章军,这个来自内蒙古普通工人家庭的青年,不愧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他的有些想法,是真正的in,比如有了钱绝不买房,干什么?投资实业,开个小饭馆,让内蒙古的亲人能在北京扎根;他不太认同那些醉生梦死、躲在屋里打游戏的蚁族,“有钱不是判断人的惟一标准,但有没有上进心就很重要了……”
目前的郑章军月收入已达5000元,在一家国企任软件工程师,打算过几年自己再开家公司,计划着早一点搬离聚居村……
从心底里我为这样的蚁族鼓掌。“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你打不败他。”郑章军给后来者竖起一个遥远却可以抵达的目标,是蚁族没有被打败的证明。
4.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关于人生,王国维先生有三境界说。对于蚁族的解读,也不能逗留于“高等教育”“知识经济”的层面止步不前。
坐在我对面的廉思抛出了第二个重磅级问题:“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谷建芬有一首著名的歌,是这样唱的,‘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未来已经成为了今天,今天为什么不是想像中的未来?”
因为“他们的幸福感,被相对剥离了。”
与出生于大城市的同龄人不同,来自农村、县城,父母均为普通工人、农民的蚁族,世袭了基因与命运。当他们来到大城市,才惊觉自己每一步都被人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而房价的狂飙、找工作的艰难、资源的不平等流动,加剧了这种差距。于是,整整一个青年的群落,比一个时代“慢半截”。
“当韩寒在鸟巢开卡丁车的时候,当胡斌在杭州玩漂移的时候,这样一群80后在默默地坚持。你不能说他们牢骚满腹,但也不能说他们无动于衷。”事实上,一些蚁族的言语,已露出情绪的端倪:
“生活扑面而来,梦想流离失所。”
“不是我物质,是生活逼我物质,没有房子,我们连遗传权都没有了。”
……
调查数据显示,蚁族的焦虑感、挫折感均高于普通人的正常值,亲情亦然。如2009年春节,廉思问过留北京的蚁族:“为什么不回家?”蚁族答:“买不到票。”这是借口,真实的原因是——过年给父母的孝顺钱,给弟弟妹妹的压岁钱,太沉重了,蚁族负担不起。他们也想挑起生活的重担,但就能力而言,真的“尚未成年”。
遑论蚁族,廉思认识的一位月入过万的白领,最近也搬到唐家岭,成为“新蚁族”。“不省房租怎么办?我1个月挣1万,花1000,才攒9000,一年才攒十万,什么时候才买得起北京一卫生间?”从这个角度上看,“每个人都是蚁族。”一样面临捕食和被捕食的命运,是食物链上苦苦挣扎的一环。一个完善的社会,是致力于为下层的人民铺设一条通道、让他们有向上的希望的社会。希望可以微渺,但只要它在那儿,广大的人们就不至于绝望。
如何改变蚁族的生存境况?廉思提出短、中、长期三项建议,包括环境治理、职业培训、落实民主权利、兴建文体设施、控制招生规模、改革廉租房政策等。“当然,最根本的是充分发展二三线城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具有巨大的虹吸作用。二三线城市如果发展好了,不用号召,青年人自然就会欣然前往。”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像蝼蚁一样生存,并不影响蚁族蝴蝶一样的美丽。调研问卷里有一个选项,“你为什么留在大城市?”蚁族的选择依次是,“一、为了梦想;二是为了父母,我可以过得很苦,但不能让爸爸妈妈苦,我现在苦是为了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第三个是为了孩子,我可以苦,但子孙后代不能苦,不能奋斗了18年才和城市里的80后一起喝咖啡。四是为了爱人,女朋友。五是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多、学习机会多。”没几个是为了自己的,绝大多数是为了别人。
这是80后从“迷惘一代”成长为“鸟巢一代”的深层次原因。
也是中华未来更强大、更美好的动力与源泉!
5.
但冰川依然存在。于同一代人之间横亘。
在一所重点大学,一个学生向前来做讲座的廉思开炮了:“你说的这些人里,有多少是我们学校的?他们的生活,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是社会的精英,是国家的栋梁,我们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这样的“独善其身”,让廉思怒了,他当场给予反驳:“你自以为是社会的精英,你知道精英是怎么形成的吗?精英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作‘蓝血贵族’,这些贵族相信自己的血是蓝色的,也坚信只有自己才配去流血,打仗的时候不让穷人上阵,自己保家卫国。你享受的权利越多,你承受的责任也就越大,心为平民,行是精英,这才是真正的精英!”
经济学家林毅夫有一句话,廉思很认同,“世界上有一个是饥饿的,我是饥饿的;当世界上有一个人是贫穷的,我是贫穷的!”有这种关注苍生的意识,才叫精英!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蚁族的辐射作用,实际上已经开始显现。
最先受辐射的是调研员。人大、北大一共有100多名同学参与了调研和拍摄,对蚁族的观感,也经历了大起大伏,由“不相信”“鄙视”“同情”到最后的“佩服”。居然还有人说,“羡慕!”“你羡慕什么呀?”廉思乐。“师兄,那帮人的精神力量才真叫强大。我们每天在学校浑浑噩噩,去那儿了才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生活!”
同样被牵动的还有千万中国家庭。很多蚁爸蚁妈看过书后含泪给廉思打来了电话,有的甚至要给他钱:“我们支持你做下一本书。谢谢你,你让我们知道了孩子在北京过得怎么样。”
作为旁观者,国外的媒体站在比我们更高的纬度上打量蚁族,他们似乎看到“这群沉默,隐忍而又谙熟互联网的年轻人,对未来不可小视的影响。”“反对日本入常”的联合大签名行动、“联合抵制家乐福”事件,都初步展现了这种影响的威力。它能创造也能破坏我们所依存的世界,能缔结也能摧毁我们所寄望的天堂。
剑指何方?
我想起1998年,才子李方在名篇《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写下对清华学子的期许和希望:“清华人,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士兵。当然,清华人更多的会成为成功的学者和工程师。”
推而广之,今日之蚁族,何尝不能承载未来中华之希望。“上者为各行业的翘楚,中者为稳健的中产,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子民。”
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果其如此,诚为吾国吾民之福音。
(原标题为:蚂蚁的幸福关乎大气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