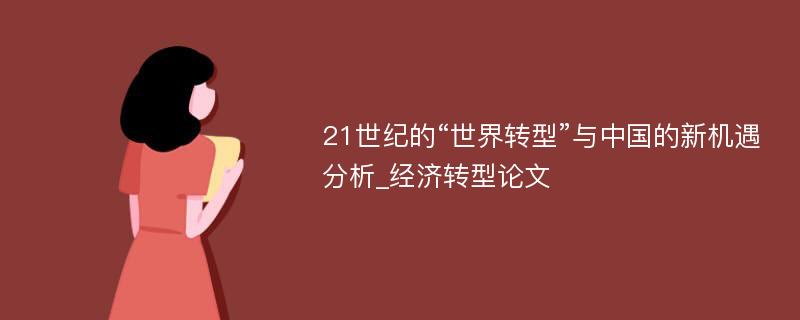
试评析21世纪“世界转型”与中国的新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机遇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一个世代都有用以表述其基本特征的关键词。如果说,人们用以表述15、16世纪世界变局及其基本特征的关键词是“地理大发现”、17及18世纪的关键词是“工业革命”、19世纪的关键词是“殖民化运动高潮”、20世纪的关键词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话,则最能准确反映21世纪世界变局和基本特征的关键词将是“世界转型”。21世纪世界转型的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外交、安全及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各层面,既包括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模式以及人们的国际观转型,也包括发展领域的生产、消费和社会管理模式、能源资源使用模式等转型,以及包括军事安全模式、人们有关战争与政治、战争与和平的观念等转型,并将从各方面深刻影响各国战略环境及其战略抉择。与21世纪世界转型进程相一致,中国也将在各方面转型。实际上,中国的转型不但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也是世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必须适应世界转型大趋势,制订相应的国家大战略,趋利避害,以求在世界转型进程中顺势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千秋功业。
一、21世纪是世界大转型的世纪
进入21世纪以来,转型(Transformation)一词在世界上已经越来越流行。2008年以来,“转型”尤其成为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和观念变化以及认识世界格局、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变化的关键词。最具典型性的例证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11月发表题为《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的国际大趋势预测报告,以“世界转型”(A Transformed World)为其关键词和“灵魂”,并以之贯穿报告始终,报告正文尤其反复使用了“转型”这一术语。①无独有偶的是,英国国防部2010年1月12日发表的战略报告《全球战略趋势——2040》(Global Strategic Trends—Out to 2040),也以“转型”为关键词,并称从现在起一直到2040年,将是世界“转型时代”(a time of transition)。②
21世纪世界转型的起点是世界经济格局及西方与非西方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非西方而不利于西方的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自15、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一直垄断性地掌握着全球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主导权以及国际话语权,控制着国际体系,把西方经济、政治模式甚至思想观念强加于非西方世界。历时数百年的全球化进程从根本上说就是世界的“西方化”进程,亦即所谓“西方的冲击”。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霸权,或是法国、英国的霸权,抑或是美国的霸权,都反映了西方对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非西方国家在此进程中受尽奴役、剥削,成为西方的附属物和牺牲品。在此过程中,全球出现了西方与非西方的政治、经济“大分裂”,西方上升为世界“中心区”,而非西方则沦落为从属于西方的所谓“外缘区”、“半外缘区”,甚至沦落为“外缘以外地区”。③
西方之所以垄断世界事务达500年之久,其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其对非西方世界享有极不对称的经济实力优势,亦即享有世界经济“中心区”地位。但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的世界“中心区”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其经济总量的上升势头被打断,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非西方中的“新兴国家”出现“群体性崛起”效应,这是把冷战结束视为“历史的终结”的西方政治家所始料未及的。根据世界经济增长趋势估算,从现在起到2025年前后的大约15年左右,将是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非西方国家力量及其国际影响开始赶上、甚至超过西方世界的转型时期。这种有利于非西方力量增长的趋势主要从三个维度表现出来。
一是从大国力量对比看,因中、印、巴、俄、墨以及印尼等非西方大国加速崛起,西方大国长期享有的实力优势正在迅速消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报告估计,到2025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将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中、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④高盛公司最新研究成果甚至提出2030年前,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到2032年,非西方的中、俄、印、巴四国(即“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西方七大国之和。⑤
二是从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力量对比看,冷战结束前后,西方占世界经济比重约为3/4,现已降至2/3左右。如,1999年,能反映西方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经合组织(OECD)各国GDP之和为24.8万亿美元,约占当时全球同比的5/6,⑥但到了2007年,OECD各国GDP之和为30万亿美元,全球同比已缩减了大约1/2,⑦非西方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则相应上升。人口总量方面,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比值变化将更大。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报告预测,到2025年前后,西方人口所占世界比重将从目前的18%降到16%。⑧兼之西方各国经济总量之和在全球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届时非西方的综合力量将呈现与西方平分秋色之势。
三是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看,亚太经济总量将超过美、欧两大传统经济中心。过去500年国际秩序长期由跨大西洋的美欧主导,其原因是以大西洋为依托的美欧长期享有综合经济优势。如,1900年,欧洲与北美占有世界制造业总值的85%以上。⑨整个20世纪,大西洋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份额一直在3/4左右波动,从未低于60%。然而,由于世界经济中心加速从“西方向东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一情况正在改变。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2009年欧盟各国GDP总量约为16万亿美元,而东亚仅中、日、韩及东盟与港、台地区等亚太核心区的GDP总量即已达13万亿美元,与前者相差不大。⑩如考虑到印度及大洋洲国家近年日益认同并融入东亚,则算上这些新融入国家的“扩大版东亚”(11)地区,其经济总量已可与欧洲并驾齐驱。由于中、印、东盟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欧洲各国,今后10-15年间,东亚经济规模将大大超过欧洲。届时美国的大西洋国家属性将弱化、太平洋国家属性将增强,并将最终完成从大西洋国家或两洋国家向太平洋国家的转型;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等也可能蜕去“泛欧”属性,完成从“泛欧”国家向亚太国家的“变脸”、“变身”,大西洋历时数百年的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将让位于太平洋。
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虽然总体上使世界各国,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均无一幸免,但非西方崛起这一趋势并未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变化。国际政治强调相对实力对比,由于美、欧、日所受打击更大、复苏更困难,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差距实际上在拉大而不是缩小。因而,非西方国家总体实力赶上西方国家的势头很可能因这次金融危机而加快,西方国家长期垄断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不合理性及其实力弱点也因这次金融危机而进一步暴露。
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转型必然要触动国际体系的根基,促使国际体系发生相应变化,这可以说是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铁律”。由于这一轮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颠覆了西方与非西方这两大集团——其组合奠基于种族、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国际观等根本方面的不同——历时500年之久的力量格局和相互关系模式,由此引起的国际体系调整必然会被认为是质的转型而不限于量的积累。
目前的国际体系继之于雅尔塔体系,始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主要反映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而当时欧美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仍占有压倒性优势。当前国际体系较之此前出现的维也纳体系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有一定的进步,但总体上依然以西方政治思维为指导思想,未完全摆脱权力政治、零和博弈、弱肉强食、大国主宰等思维的影响,依然是西方昔日实力优势及其国际政治观的派生物。
在机制上,当前国际体系具体表现为联合国体系、八国集团、世界银行、IMF、WTO、新成立的G20以及各类区域性组织等机构并存,分别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和地区问题上发挥作用。但是,这些机构或者功能不全、或者未能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趋势的新变化、或者根本上就是西方强权政治的残余,因而需要进行调整、改革和系统整合。如,联合国体系虽较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零和原则”、较之维也纳体系的“正统原则”以及较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战败国和弱小国家无情压迫的“惩罚”、“分赃”和“弱肉强食”原则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大国主宰”方面并无根本性变化。安理会“五常”中,美、英、法等欧美大国居三席,其中英、法人口总量已退居世界排名20名之后,经济实力也大幅下降,已不成其为世界大国,这显然不符合世界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俄罗斯较之前苏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从人种看,占世界人口1/6的白种人国家占据了安理会“五常”中的四席,而占世界人口5/6的有色人种只占其中一席,这也显然不正常、不合理,难以永久持续下去。
又如,世界银行、IMF在二战后初成立时,一度对世界经济复兴及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被认为是经济领域的“联合国”。但是,这两个机构一直由西方全面掌控,其“西方性”较之战后初期的联合国更甚。IMF总裁及世界银行行长一直法定由欧美国家代表执掌,美欧尤其通过其垄断性股权掌控这两个机构的运作,进而控制世界金融、经贸、投资以至影响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冷战后因非西方国家崛起、区域化如火如荼、全球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变化等因素影响,这两个机构的全球影响力不断缩小,美欧对这两大机构的全面控制也越来越不合时宜。这两大机构的改革、改造势在必行,目前并已出现一定进展。
八国集团原是美国为联合西方对苏联进行冷战而结成的西方大国集团,并不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广泛利益诉求,却喜欢“管理”全球事务,且管而不当,显然也需要转化其机制与职能。有人分析说,八国集团只代表不到世界人口1/5的西方国家,排除了中国等新兴大国,因而不具备全球代表性,正在走向衰亡。诞生于2008年大危机之际的“G20”虽然反映了更大的历史性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国际潮流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但也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它能否成长壮大,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今后10-20年,随着以“金砖四国”、“钻石五国”、“新钻十一国”等为主导的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普遍发展、崛起,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转型,国际体系转型的步伐也会加快。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八国集团及世界银行和IMF等不再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那样到处指手画脚,“G20”集团诞生并活跃,中国及印度等新兴国家在世行及IMF等机制中的投票权和影响力增大,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东盟+N”、海合会、非统、拉美一体化进程等区域组织和区域化进程的活跃,或许是国际体系大转型的序曲。
除此之外,21世纪的世界转型还将涉及世界高位政治、低位政治、生产与消费、文化与生活、经济与安全以及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各种事务、各个层面、各大领域。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历时数百年、无限制追求利润、高消费、高浪费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这将引起生产与消费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以及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和国际观转型。
早在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就提出了“发展极限论”,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增长终结论”。(12)今天,世界现实证明“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具有洞烛先机之能,也证明人类在追求发展的无限性与能源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其与地球和人类心理文化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存在严重悖论。
一方面,人类——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都有权追求更多的幸福、更高的生活标准,因而要求生产和消费更多的高质量产品;另一方面,世界资源有限,全世界包括能源、各种矿产品以及土地、淡水、粮食等各种资源在内,大多数已趋于供应极限,不少资源的供应量已经超过或者接近于“峰值”。在石油生产领域,一些传统主要产油国的原油产量已陆续过了“峰值”,产量日减,例如依赖北海油田的英国和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美国;另一些正在接近“峰值”,例如世界一、二号产油大国沙特、俄罗斯等。但世界石油消费却有增无减,在汽车等产品日益风行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报告估算,照目前趋势,未来20年内,世界石油供应将越过“峰值”期,越来越供不应求,直至枯竭。世界必须转变以石油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尤其要积极研究、开发石油以外的新能源,包括开发生物燃料、风能、光能、氢气和清洁煤等。(13)
除石油等能源供应不足问题外,由于世界人口总量继续保持增势,非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有向西方消费标准靠拢趋势,世界粮食供应、水资源、土地资源等日趋紧张。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报告估算,今后20年世界将新增人口12亿,2030年世界粮食供应需求将增加50%。这无疑是世界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及能源供应紧张进一步加剧的主要原因。(14)
不仅如此,世界如继续目前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地球环境将更加恶化,温室气体排放将进一步增多,地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将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并难以修复。凡此种种,要求世界各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都要携手合作,在发展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能源、地球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作痛苦而理性的选择,转变持续数百年,以高消费、高浪费为特征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和出路。
对于未来世界转型,英国国防部战略报告《全球战略趋势——2040》有一段精辟归纳。该报告提出,2010-2040年将是“世界转型时代”,其特点包括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世界“不稳定”、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人口快速增长;资源紧缺;意识形态混乱;全球实力中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等。面对这些世纪性挑战,任何单个的国家、组织或个人都无力单独应对,惟有“集体反应”才能解决问题。(15)
二、21世纪也是中国转型的世纪
近代以来,世界先后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型。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15、16世纪,其突出标志是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地理空间扩大,全球“链接”为一个政治、经济统一体。但那次转型对中国几乎不发生影响,中国照旧偏安于东方一隅,偏安于封建帝国的全盛时期。第二次世界大转型发生于17、18世纪,其突出标志是蒸汽机和煤、钢的大量生产、应用及铁路、轮船投入使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此时的中国仍在小农经济的牧歌中沉睡,虽然中国当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但科技和工业能力、尤其是军事科技和军队装备已大大落后于西方。(16)第三次大转型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突出标志是石油、电力、电器、内燃机、汽车、飞机等广泛应用。在此过程中,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惊醒,有意搭车,发展近代工业技术,搞“西学为用”,但为时已晚。此后外患接踵而至,中国相继在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中败绩,被迫不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四次转型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突出标志是核能、计算机技术、航空航天、新材料、生化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应用。中国自改革开放开始,赶上了这次转型的末班车,带动中国经济、科技进入一个飞跃式发展时期,但稍稍嫌晚。
与前几次转型不同,21世纪的世界转型是在中国加速崛起、综合国力和科技能力及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的条件下发生的。中国不是被动地适应世界转型,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也是促成世界转型的基本力量。西方和非西方力量对比变化、亚太崛起、国际体系转型、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管理方式、发展模式及思维观念的转型,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就与中国迅速崛起及中国国际威望和影响力空前提高密切相关。
在一般情况下,世界转型通常有利于后起大国,比如,蒸汽机的应用便利了后起的英国在工业和军事领域应用新技术,使之迅速超过西、葡、荷等老牌国家;内燃机和电力的应用便利了后发的德国,使其在工业、交通、科技及军事科技领域迅速超过英法;而航空航天技术、交通通讯技术、核能、计算机、生化、新材料等新科技的应用则便利了美国迅速超过所有的世界大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直至成为“唯一”超级大国。
综合看,这次世界转型对中国是机遇大于挑战。即使在挑战领域,只要中国应对得当,也有机会化挑战为机遇。
首先,在经济层面,2009年中国GDP总量为340507亿元人民币,按年末人民币汇率6.8282折算,合约近5万亿美元,已大大超过德国,紧紧咬住日本,进入“坐三望二”位置。(17)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研究报告《转型的世界:2025年全球大趋势》有关2025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8)的预测结论是相对保守的。虽然2008年末发端于美国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不小,但对美、欧、日等影响更大。从相对力量对比看,这场金融危机是加快而不是延滞中国“赶超”西方大国的历史进程,这从2009年中国经济仍保持9.1%的高增长率可以得到反映。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越过一道重要的国际政治“分水岭”。(19)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的时间也很可能切合高盛公司及林毅夫的预测时间表而提前。(20)无论如何,只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中国就能对世界转型进程、议程和转型方向产生积极影响,也能主动、积极地适应世界转型。
其次,不仅中国力量在增长,包括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力量也普遍在增长,而西方相对力量则在下降。各种全球性问题一方面增大了世界各国面临的压力,也凸显西方管理模式及其国际政治思维、国际观的不足。世界需要新思想、新观念、新模式,这就为拥有数千年文明史、曾在古代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有诸多优秀政治、文化和战略传统的中国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合作,共同推动西方及世界各种力量合作,调整历时数百年的西方国际体系及其指导思想、推动并引导国际体系转型提供了活动空间。世界银行和IMF股权、投票权的调整;G20日益活跃,有在国际舞台上取代G8之势;亚非及拉美各种区域性组织的发展,均典型反映了中国及非西方国家崛起正在引起国际秩序重组、转型。
第三,在资源、能源、科技领域,世界转型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有机遇。以2009年为例,中国消费煤炭30.2亿吨、原油3.8亿吨、天然气887亿立方米、电力36973亿千瓦时、钢材6.9亿吨、水泥16.3亿吨,同时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则已与美国比肩。(21)为支持如此庞大的产能和消费力,中国2009年进口了62778万吨铁矿砂、20379万吨原油、3696万吨成品油、4255万吨大豆、2806万立方米原木、1368万吨纸浆以及其它大量原材料。(22)而目前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0%左右。理论上,按目前增长模式,即使中国人均GDP增至美国同比的50%,也意味着中国的煤炭、石油、钢铁、水泥、电力及粮食、淡水消费量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再增长5倍,原材料进口量也再增长5倍,这是不允许的、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中国和世界所做不到的。因此,即使世界不转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必须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转型符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中国应以欣喜和欢迎姿态适应新一轮世界转型。
第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中国经济已初步具备较强的“自增长能力”,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中国这种经济“自增长能力”首先奠基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是一个10亿级人口的超级人口大国,正是这种超级人口规模使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经济“自循环能力”,从而为中国经济“自增长能力”提供独一无二的基础。中国30多个省就相当于30多个中等以上的“国家”或者说30多个相对独立的供需市场,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规则,贸易互补、增值规则,资源共享规则等在国际市场上起作用的原理,在中国一国之内可以自行实现,甚至可以实现得更好、更合理。这是前几轮世界转型过程中的领军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甚至苏联、美国都难以比拟的。与中国相比,美、苏也不过是人口亿级规模国家,差了一个数量级,它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做不到可持续的经济“自增长”。中国经济具备“自增长能力”的另一个条件是中国经济、科技、教育、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社会管理水平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足以与巨大的人口规模相结合,推动“经济自增长”。建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巨大的人间经济奇迹。2009年一年,中国生产了5亿多吨粮食、6亿多吨钢铁、近30亿吨煤,新增发电能力8970万千瓦、新建铁路投产里程5557公里、新建公路12万公里、汽车产销均超过千万辆。(23)这种巨大的产能,使中国具备了继续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工程建设能力。而印度虽然是与中国并列的10亿级人口大国,但不具备中国这样巨大的产能和经济科技水平、工业基础,因而不具备类似中国目前所具有的经济“自增长能力”。要而言之,一方面由于巨大人口规模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低成本优势尚有潜力,另一方面由于内需市场急速扩大,在实现现代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需求上已能“自给”,中国因而具备“经济自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这种经济“自增长能力”使中国在具有国际市场、国际合作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如虎添翼;而在相对独立于国际市场、甚至孤立的条件下,也将能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这一点已由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的事实所初步证实。这就使中国在新一轮世界转型过程中,享有一定的战略主动权,而不必像英美战略家在其战略研究报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对世界转型抱持一种过于“悲观”、消沉和无可奈其何的心态。
不容否认,世界转型也确实对中国提出了巨大的世纪性、战略性挑战,其内容同样涉及资源供应、环境安全、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模式、人口、移民、军事安全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定位、身份及国际行为范式等方方面面,其中有些是尚未完全解决的老挑战的延续,有些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型挑战。
比如,在人口方面,因历时数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构成和增减模式变化很大。未来10-20年,中国不但人口增速减缓,将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提早到来、人口构成男女比例失调等问题。“人口红利”期渐渐逝去,将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及劳动力低成本优势。(24)在世界人口流动浪潮中,中国因内部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和多样性,各地区发展差异大,一方面对外输出移民的态势将继续,另一方面有可能成为接纳其它国家移民的移民输入国。后者尤其是打破近代历史记录的新现象。近年以各种途径旅华居留的外国人增多,如广东有非洲人聚居、温州有阿拉伯人聚居、北京有韩国人聚居、东北有大量朝鲜人和俄罗斯人流入、滇桂有越南人偷渡移居等现象,就反映了这种趋势。今后随着中国沿边大开发加快,中国沿边地区又较陆邻周边国家发达、富裕,中国沿边、尤其是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可能成为周边一些落后国家居民移居的目的地。对中国而言,这将是在世界转型浪潮中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又如,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国际影响增大,“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会继续上扬,同时“中国责任论”也会水涨船高。中国在世界转型过程中如何定位自己的身份、地位,如何积极适应、参与甚至主导国际体系转型,就需要未雨绸缪。
再如,军事科技的发展、尤其是空-天技术的发展、高速铁路的普及、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战争等,将导致战争形态、军事安全范式与人们有关地缘政治、海陆空权竞争关系,以及有关战争与和平关系等方面的观念转型,从而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安全构成新挑战。尤其要指出的是,最新空-天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有关战争思维的时空观。美国推出的“猎鹰”计划(FALCON)旨在谋求建立一支具有从美国本土出击、1-2小时打遍全球的“环球快速精确打击”能力的空-天力量。美空军已在2010年5月试飞成功X-51A新型空-天飞行器,其飞行速度超过6倍音速,而其远景规划是达到20倍音速。(25)美国这一计划如果成功,有可能借速度优势改变“核战争没有胜利者”的核逻辑,使一些国家的核威慑能力失效,其直接后果是可能重新增大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甚至使世界重新“回归”世界大战时代。凡此种种,要求我们调整、甚至跳出传统的军事战略思维,实现军事安全观和军事战略、军备建设路径、方向及重点的全面转型。
三、中国如何适应世界转型?
历史一再表明,在转型时代,能够适应世界转型要求的民族、国家,就能以转型为契机,调整产业、科技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和思维方式、观念,以及调整国际观,等等,带动国家飞跃式前进,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之林。反之,那些不能适应世界转型要求的民族、国家,则可能坐以待毙,被世界潮流抛弃,甚至遭遇亡国灭种的命运。以中国目前之发展阶段及改革开放30多年所积累的实力、经验和国际威望,中国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搭乘世界转型的顺风车,在世界转型中抓住机遇,调整产业及政治、经济、科技体制和发展模式以及社会管理模式,也调整中国的发展观、政治观、国际观,使中国成为世界转型每个领域的真正赢家,在世界转型中实现百年强国梦。
首先,在观念上,要认清世界转型是大势所趋,具有不可抗性,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从如何适应世界转型大趋势,保障中国实现战略崛起的战略视角观察、把握世界转型趋势,包括其内涵、方向、路径及其方方面面的影响、后果,等等,预筹应对之策。在这方面,美欧大国、尤其是美英等目前无疑已抢先了一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战略报告、英国国防部出台《全球战略趋势——2040》战略报告,皆以研究“世界转型”及其应对之策为主旨,就是其重视、超前研究世界转型问题的突出标志。在政策层面,奥巴马政府较其前任更重视环境问题,推进新能源技术,推动美国经济“再工业化”,在国际上搞战略收缩、“换肩”,加强与新兴大国协调、尝试推动“G2”、迫使欧洲在IMF等国际机构中向新兴大国“放权让利”,以及军事建设重点转向空-天力量和网络战能力建设,等等,明显是在为适应世界转型趋势提前布局。英国等一向战略布局超前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动作。相比之下,中国在应对世界转型问题上明显慢了半拍。虽然中国一些媒体、网络、企业甚至学者也不时使用“转型”这一术语,但多止于包装甚至是文字游戏,并未深入堂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政治成就,这可能形成思维惯性,导致对世界转型趋势失去敏锐的感知力和洞察力,甚至导致观念和战略上的固步自封和顽固的经验主义及其保守性。这是面对世界转型变局时,中国尤其要努力加以克服的战略思维瓶颈。
其次,要适应世界转型趋势,及时和尽快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以达到既要实现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战略目标,又能有效限制能源、资源消耗的过快增长和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这样一个超巨规模大国,一直保持9.8%以上的年均增长率,这是史无前例的。尽管仍有不同意见,国内外经济界主流意见认为中国有潜力继续维持一代人之久的高速增长。例如,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研究认为中国今后二三十年仍将保持8%-10%的长期高增长。(26)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2008-2020年间中国仍可能保持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27)《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也认为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起点低,仍有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发展空间”。(28)
然而,中国如果不转变增长模式,即使用今后一代人时间仍然保持过去30年的高增长率,也会穷尽资源和发展潜力,耗尽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国际社会不会接受,就是中国自身也难以承受。因此,适应世界转型需要,转变高消费、高浪费、高投入、高污染型的粗放增长方式是当务之急。而要达此要求,一方面要转变增长观念,进一步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同时更要采取积极措施,科技先行,尽量采用节能、环保新技术。比如,2009年中国全年能耗为31亿吨标准煤,与第一能耗大国美国相距不远。(29)有专家估计,中国很有可能在2010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耗大国。并且,如果中国能耗增长速度保持本世纪以来年增8.9%的增速,则2020年中国能耗将达8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能源消耗的一半以上。(30)但中国能源使用效率却远低于美国,更低于德日英等其它发达国家。目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7%,能耗却占世界总量的17.7%。(31)有研究数据表明,目前中国能源总效率仅为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1/4,大致相当于它们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32)如果中国采用新的能源生产、应用和去污技术,增加水电、风电、核电、太阳能、地热能等低污染、高效率能源的使用比重,达到美欧日等OECD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则中国以今天的能耗总量,足可以保障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代人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过去30年的增长率,实现经济总量再翻番甚至超过美国,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老大”。能源方面如此,其它资源消耗,如水资源、土地资源、各种矿产资源使用效率方面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第三,及时调整国际观和国际政治观,以更积极的合作姿态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转型,同时理性应对国际上时起时落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不同声音,以及理性应对国内某些阶层、某些利益集团和“媒体英雄”、“网络英雄”们非理性、甚至带有狭隘性、狂热性和利益集团背景的国际战略诉求或者说战略杂音,稳妥应对世界转型时期的各种新型国际国内挑战。中国经济独一无二的“自增长能力”是中国增加战略自信心和战略主动权的源泉,而不是中国走向自我孤立、自我封闭、脱离世界体系或狂热挑战世界秩序的本钱,中国仍要继续坚持“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合作路线。
近几年内,各种类型的“中国威胁论”,如中国“资源威胁论”、“经济威胁论”、“环境威胁论”、“军事威胁论”、“中国发展模式威胁论”等,仍将是中国发展崛起过程中的主要国际杂音。3-5年后或者5-1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甚至逼近美国,中国军事实力增长、尤其是综合实力增长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实、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而拥有强大实力的中国确实并未采取任何咄咄逼人、超出保护合理国家利益限度的所谓“进攻性”对外政策时,“中国威胁论”有可能因中国的“真正强大”而淡出,“中国责任论”可能替代“中国威胁论”,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国际社会一时盛行的主要杂音,届时中国将需要更多地应对“中国责任论”。简而论之,“中国威胁论”有可能随着中国真正实现战略崛起而自行消亡,即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中国责任论”将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及亚太崛起进一步加快、尤其是中国“超日赶美”步伐进一步加快,将进一步上扬。(33)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国际社会就出现了要求中国“履行责任”,领导世界解决危机的声音。(34)今后如出现新的世界性危机,尤其是经济、金融、安全危机和周边危机,要求中国采取切实“领导”责任的声音将会更多、更高,中国将很难回避。而在前者向后者过渡期间,可能还会出现所谓“中国傲慢论”。(35)如何在“韬光养晦”和“中国责任”之间寻求平衡将是中国国际战略面临的长期课题。
面对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变化,中国要有新的思路。中国不能学二战后的美国、尤其不能学冷战后的美国,“自告奋勇”地以“领导”世界、亦即称霸世界为己任。世界太大、太多样,不需要这样的“领导”,做这样的“领导”也必然得不偿失。但中国也不能学19世纪末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却坚持孤守一隅,搞孤立主义那一套。对当前国际体系,中国仍应坚持参与其中、促其不断自我改造、弃旧图新,并争取逐步增大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G2”、“中美国”(Chimerica)、“中印度”(Chindia)、“中德国”(Chermany)等概念的出台,(36)以及中国在世行、IMF、G20、APEC、“BRICs”、上合、“东盟+N”、“六方会谈”、全球气候峰会、甚至在G8会议上话语权的增大,都不是中国主动索取来的。在未经过重大战乱和国际突发事件的情形下,中国的国际地位、权势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在“桃李不言”中增长,这是国际关系史所罕见的。照此速度,无需中国采取特别激烈的行动,中国在一代人内就有可能自动跃升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真正的主导型国家。这是真正的和平崛起,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战略成本最低的崛起,其唯一代价是需要中国有战略耐心以及坚持“咬住发展不放松”。
第四,在世界转型大潮中,中国的军事安全战略、军备建设路线和战争观、战略观也要及时转型。纵观战争史,“重”、“大”、“多”一直是军队建设的关键词。军队要取胜,要求重装备多、军队规模大、人数多。因此,古希腊、古罗马军队不惜成本多建重装步兵、重装骑兵,中国秦汉则强调强弓硬弩,长矛“丈八”。近代德、英进行“无畏舰”竞赛,搞巨舰大炮主义,也是突出“重”和“大”。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把军队建设的“重”、“大”、“多”原则发展到顶峰。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军队建设的“重”、“大”、“多”原则,美苏在冷战高峰时期各自拥有把地球毁灭无数次的核能力,它们的战舰、坦克、飞机越造越大、越造越多。但是,空-天力量和网络力量的发展将从本质上改变军队建设的“重”、“大”、“多”原则,军队制胜更多地依靠技术先进和战略思想超前而不是依靠“重”、“大”、“多”进行二战式的死打硬拼。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批评美国军备建设囿于传统,不能适应21世纪的军事变革,是在“浪费资产”,要求美军停止研发“朱姆沃尔特级”(Zumwalt-class)驱逐舰、中止陆军“未来作战系统”研发计划中8种战车的研发与生产,就反映了美军在进行战略转型。(37)美国战略界更有人明确提出美军建军思路要从“少而大”转向“多而小”(“Many and small”beats“Few and large”),要求奥巴马政府即使不中止、也要延期生产或延期交付航空母舰以及其他大型舰艇、先进战斗机、坦克等“所有传统武器系统”。(38)还有人直接要求缩小“前沿陆上基地”规模、减少航空母舰数量,因为二者“越来越难以抵御攻击”。(39)而2013-2015年间,由于“企业号”退役、“福特号”延时完工(因美军航母替换周期由4年延长为5年)而一时不能“补役”,美军航母总数确实将由目前的11艘减为10艘。(40)与之相一致,俄英法等国停止研发重型坦克、英国新航母建造计划暂停等,也是其军事战略转型的重要迹象。
世界军事战略转型的另一个表现是传统地缘政治观和陆海权观的变化。传统上,地缘政治竞争表现为陆海权竞争“二分论”特点。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提出,数千年来的地缘政治史就是一部“陆上人”和“海上人”之间“反复斗争”的军事斗争史。(41)早期飞机的出现并未打破陆海“二分论”,当时的飞机不过是陆权的延伸,“是陆上强国可以用来对付海上强国的一种武器”。(42)直到冷战结束,虽然人们已经开始讨论“币权”、“制天权”、“制网权”,但陆海“二分论”仍然是战略界进行地缘政治分析的金科玉律,也是军事准备的基本指导原则。但是,在21世纪,空-天技术的新发展、5-10倍音速甚至更高速环球飞行器的出现,增加了空-天力量的优势。空-天力量加上网络力量以及建设环球高速铁路网的可能前景,将打破传统的陆海“二分论”,推动21世纪战争形态和军事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型。在21世纪,谁掌握了空-天力量优势和网络力量优势,谁就如15、16世纪掌握舰炮技术、20世纪上半叶掌握航母技术和装甲兵团大纵深作战战术、二战后掌握核能力一样,拥有战略主动权和战争制胜法宝。
鉴此,军事战略转型一定要破除传统的“重”、“大”、“多”迷思和陆海“二分论”迷思,使我们的战略思维走出“中途岛时代”、超越朝战、越战经验,瞄准高新技术研发、瞄准空-天力量建设和网络力量等高新军事领域。
注释:
①参见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②Ministry of Defence,“Global Strategic Trends:Out to 2040”,Fourth Edition,pp.2,10,http://www.mod.uk/NR/rdonlyres/D701.(上网时间:2010年6月21日)
③罗荣渠:“开拓世界史的新视野”,引自[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代译序”,第3页。
④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p.7-28,http://www.dni.gov/nic_2025_project.html.(上网时间:2008年12月26日)
⑤Alan Beattie,“Changing face of power:stars shine bright but fail to transform the world”,Financial Times,January 18,2010.
⑥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ors”,June,2000,p.263.
⑦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ors”,January,2009,p.283.
⑧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19,http://www.dni.gov/nic_2025_project.html.(上网时间:2008年12月26日)
⑨[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⑩“2009 List by the CIA World Factbook”,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GDP_(nominal).(上网时间:2010年5月31日)
(11)本文“扩大版东亚”概念缘出于麦迪逊著《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在该书中,麦迪孙的“东亚”概念打破传统的七大洲划分法,不仅包括原有东亚概念中的东北亚、东南亚,也包括印度半岛及大洋洲国家。参见[英]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0-154页。
(12)[美]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著,李涛、王智勇译:《增长的极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12月,pp.XII-XIII.
(13)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p.42-43,http://www.dni.gov/nic_2025_project.html.(上网时间:2010年5月26日)
(14)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译:《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09年9月,第4页。
(15)Ministry of Defence,“Global Strategic Trends—Out to 2040”,Fourth Edition,p.10,http://www.mod.uk/NR/rdonlyres/DT01.(上网时间:2010年6月21日)
(16)[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第10页。
(17)刘铮:“中国经济去年增速上调为9.1%”,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3日。
(18)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pp.28-29,http://www.dni.gov/nic_2025_project.html.(上网时间:2010年5月26日)
(19)Peter Mandelson,“We want China to lea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12,2010.
(20)关于中国GDP总量何时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的预测,经合组织经济情报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统括部研究员小峰隆夫分别预测为2020年;原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预测为2030年;高盛公司预测为2041年。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高盛公司又把中国超美的时间表大大提前。英国国防部报告《全球战略趋势——2040》综合高盛报告观点,提出2025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到2040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2倍,或相当于美欧之和。参见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8,p.36;林毅夫:“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未来发展展望”,载《外交评论》,2007年6月,第9页;[日]小峰隆夫:“世界经济长期预测”,载《越洋聚焦——日本论坛》,2007年11月号,第17期,第29页;高盛公司报告:“BRICS——通往2050年之路”;Ministry of Defence,“Global Strategic Trends—Out to 2040”,Fourth Edition,p.52,http://www.mod.uk/NR/rdonlyres/D701.(上网时间:2010年5月26日)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2010年2月26日。
(22)中国海关统计:“2009年1-12月中国主要进口商品量值”,载《国际贸易》,2010年,第2期,第71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2010年2月26日。
(24)Ministry of Defence,“Global Strategic Trends-Out to 2040”,Fourth Edition,pp.52,84,http://www.mod.uk/NR/rdonlyres/D701.(上网时间:2010年6月21日)
(25)Caitlin Harrington,“USAF successfully test X-51A WaveRider”,Jane's Defence Weekly,June 2,2010,p.5.
(26)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上升中的中国国力”,载《新华文摘》,2010年,第4期,第47-49页。
(27)樊纲:“中国经济需要下一个30年高增长”,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17期,第45页。
(28)Gideon Rachman,“Rising China is a real contender”,Financial Times,March 16,2010.
(2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2010年2月26日。
(30)周婷:“我国能源要转向高效绿色低碳”,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2日。
(31)周婷:“我国能源要转向高效绿色低碳”,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2日。
(32)李孟刚:“能源安全需要新思考”,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2期,第29页。
(33)Peter Mandelson,“We want China to lead”,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February 12,2010.
(34)David Pilling,“China will not be the world's deputy sheriff”,Financial Times,January 28,2010.
(35)Katrin Bennhold,“West unready and uneasy as China boldly emerg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uary 27,2010.
(36)Martin Wolf,“China and Germany unite to weaken the world economy”,Financial Times,March 17,2010.
(37)Daniel Wxsserbly,“Gates calls for defence spending overhaul”,Jane's Defence Weekly,May 19,2010,p.5; Andrew F.Krepinevich,jr.,"The Pentagon's Wasting Assets",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9,p.31.
(38)John Arquilla,“The new rules of war”,Foreign Policy,March/April 2010,pp.63-67.
(39)Andrew F.Krepinevich,jr.,“The Pentagon's Wasting Assets”,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9,p.31.
(40)Sam LaGrone,“Ship shape”,Jane's Defence Weekly,May 19,2010,p.31.
(41)[英]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等译:《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42)[英]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4页。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中国崛起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