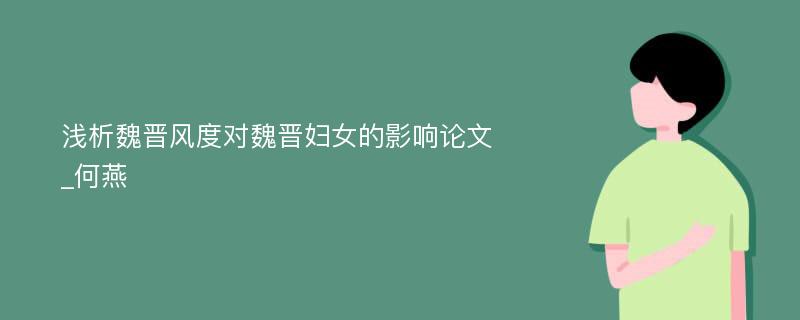
摘要:《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很多活泼生动的魏晋女性,这些女性受到当时士人和世风的影响,她们的身上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色彩和精神风度。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风度;妇女;世风
魏晋时期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束缚逐渐减少。这一时期的妇女行为言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因此处于这个历史时期的妇女有机会彰显她们的个性。
一、社会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代,战乱和分裂造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的混乱,思想的崩溃,在战争和灾难中人们生命意识得到了觉醒。恶劣的社会坏境和政治环境,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们纷纷远离政治,他们不营物务,崇尚隐逸,只以清谈为务。名士们注重清谈与善于品鉴,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身边的女性。
当时的门阀士族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巩固家族势力,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这些世家大族对家庭教育的重视表现在他们对家庭成员文学修养的重视和培养上。《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当时的门阀士族为了培养家庭成员的文学才能,经常举办一些家族辩论和文学集会。如《言语》第七十一条所记载的: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这段文字记载的就是当时的谢家士族,谢安家族的文学聚会。这次文学聚会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家庭文学集会,当时作为女子的谢道韫并没有因为女性的身份不能参与,反而在此次文学集会中她可以畅所欲言,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由此可见,当时出生在世家大族的女性和男子一样,是有条件,也有机会参与到家庭的文学集会当中的。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家庭成员的魏晋妇女也自然的接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学熏陶。
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崩乐坏,君臣父子的传统礼教在这个时代已经显得很苍白,同样的压在女性身上的纲常伦理也有所弱化。干宝《晋纪总论》中对当时社会以及魏晋妇女的生活状况有详细的记载:
其妇女,壮节织纤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木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泆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及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母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妇女,勇敢地挣脱礼教的枷锁,“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敢于大胆地追求情爱;而当时社会对女性这样一种突破礼教大防的态度也极为宽容。女性的个性追求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恋爱求偶的态度上,她们也不再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忠实于自己的情感大胆地追求真情。由此可见,当时的魏晋妇女已经突破了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人意志、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这一时期的妇女,她们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彰显。处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魏晋妇女的身上就学得了魏晋士人的那一套思想和做派,表现出魏晋时代的一种精神风度。
二、魏晋妇女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总的来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清谈、品鉴和任诞。这三个方面体现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即表现为魏晋风度。魏晋时期的妇女她们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加之受到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她们的身上也表现出清谈,品鉴和任诞的个性特征。
这些魏晋妇女不但能书善画,而且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品鉴人物和玄学清谈方面也表现出突出的才能,受到当时男性的尊重和赞赏。谢无量在其《中国妇女文学史》中说:“晋世妇人嗜尚,颇与其时风气相协,自汉季标榜节概,士秉礼教,以人伦风鉴,晋世妇人亦有化之者。又好书画美艺,习持名理清谈,皆当时男子所以相夸者也。”魏晋女性,特别是上层阶级的妇女,对音乐、绘画和书法有很高造诣者甚多。在清谈和品鉴人物方面,她们也具有突出的才能,谢道韫和山涛之妇就是女性中善清谈和品鉴人物的典型例子。
(一)清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不断更迭的政权,频繁的战争使得人们颠沛流离,苦不堪言,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下降,转而消极避世。不再醉心于功名利禄的魏晋士人,开始将精神寄托于玄学清谈。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名士群集,互相品题,臧否人物、发表见解以引起执政者的重视。但到了魏晋时期,名士们为了避祸不敢再议论政治,而是专心于高深莫测、言及玄远的玄学。
在谈玄的过程中讲论者所表现出来的风度、仪容之美以及丰富的学识成为名士们自觉的追求。作为名士的妻子或者女儿,生活在他们身边,无疑也会受到清谈之风潜移默化的影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校注》中说,“晋人崇尚玄风,任情作达,丈夫则糟粕六艺,妇女亦雅尚清言。”反映了当时士人谈玄任诞的同时,女性也尚清谈雅言。加之,由于她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因此她们普遍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对当时盛行的玄学也有独到见解。《晋书》中有一段关于谢道韫为小叔解围事迹的记载:
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幛自遮,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
这段记载充分地展现了谢道韫在清谈方面的才能。这里的宾客即是指与王献之清谈的“辩手”,词理将屈是指他的议论将要被人驳倒,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谢道韫站了出来,她重申了献之之前的议题,参加辩论,结果是“客不能屈”,扭转了辩论的局势。下文又说到王凝之被害后,谢道韫寡居会稽,与当地太守清谈的事迹:
太守刘柳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修整带造于别榻。道韫风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柳退而叹曰:“实顷所未见,瞻察言气,使人心形俱服。”
从这则事迹可以看到当时的谢道韫在谈玄说理方面的名气甚高,以至于当地颇有名气的太守刘柳都邀请她一同清谈讲义。谢道韫身上散发着风韵高迈清雅的气质,在谈玄的过程中,慷慨流涟,词理无滞,表现出她从容叙致的姿态以及在谈玄方面的突出才能。以至于刘柳退而叹曰,“实顷所未见”“使人心形俱服。”
受当时谈玄风气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妇女也表现出机敏善辩的个性特点。如《贤媛》第六条中记载了丑女阮氏用从容的言谈挽救了自己婚姻的事迹。
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
许允的新婚妻子是阮卫尉的女儿,因相貌丑陋,新婚当夜许允便以妇有四德来质难她。不料妻子大方自信地说“新妇所乏唯容尔”,接着她也不甘示弱地问自己的丈夫,“士有百行,君有几?”当丈夫回答“皆备”的时候,她又一针见血地指责丈夫只爱色不爱德,一时之间竟让丈夫无言以对,面露惭色。许允妻表现出来的机敏和善辩,是当时上层社会的魏晋妇女,受到了当时论辩风气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名媛》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谢道韫和许允妻一样能玄学清谈、机敏善辩的女性,如班婕妤讽赵飞燕、诸葛诞女讥讽丈夫等,都反映了能言善辩个性特点。
(二)品鉴
“魏晋时期盛行的人物品鉴之风起源于汉末察举制度的乡党评议即评价一个人的品德优劣与否以此作为其能否受到统治者青睐的标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玄学风气的影响,魏晋人物品题的侧重点就从政治的转向了审美的,并且逐渐成为大势所趋,成为魏晋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说新语》中有《识鉴》、《赏誉》、《品藻》等篇专门的记载人物品题。品鉴的主要目的是对人物的洞察远见和精妙鉴赏,并且判别其才性优劣,分为不同的等级。虽然这个时期的人物品鉴与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但它可以直接影响人的名誉、地位、声望等,所以当时的人十分注重人物品鉴。
在品鉴成风的世风盛行下,魏晋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一份子,她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品鉴的大队伍中。并且上至贵族女性下至较低等级的女性,都具有了一双慧眼。如《汰侈》第二条记载的: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石崇家里的用度十分奢华,连厕所都布置得富丽堂皇。面对着那么奢侈的设置以及美人在旁边的侍候,很多人都羞于去厕所,但是王敦丝毫不客气,按部就班的上了厕所,并且“神色傲然”,从他的从容自若、不卑不亢的表现中,厕所婢们便看出了他的“作为”。从之后的历史来看,她们所言非虚。
此外,山涛妻韩氏也具有十分过人的识鉴才能。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贤媛》第十一条有载: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 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 妻曰:" 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 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 二人何如?" 妻曰:" 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 公曰:" 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山涛与嵇康、阮籍“契若金兰”,韩氏便效仿僖负羁之妻观察二人,并得出“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的结论,正与二人言山涛以度量见胜相符。韩氏慧眼卓识的才能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能够反映当时魏晋妇女具有识鉴才能的还有王浑之妻钟氏。王浑与钟氏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生的容貌姣好,品德贤淑,作为哥哥的王济想要为妹妹寻一个夫婿。王济物色好人选后,让母亲钟氏来看。
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
钟氏一眼就将王济(武子)所选的兵儿认出来了,钟氏觉得他虽然出类拔萃,但却很难申其才用,并依据这个人的骨骼形貌判断他“必不寿”的命运。后来果然如钟氏所言,“兵儿数年果亡”。这则故事虽有可能是钟氏因门第之见不肯接受兵儿的借口,但钟氏对兵儿的预断和兵儿后面数年果亡的结局也可见钟氏在识鉴人物上所具有的高超远见。
谢道韫不仅在玄学清谈方面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在品鉴识人方面也有独到的眼光和犀利的评点。如她直言其弟谢玄“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以及当她嫁到王家之后,看到王凝之时,竟发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这样鄙薄丈夫的言论。从这两则小故事来看,谢道韫在识鉴人方面是具有深刻的洞察和远见的,能够准确地判断人的才性优劣。嫁给王凝之后,发现丈夫资质平庸,谢道韫更是大薄丈夫王凝之。历史上的王凝之才华的确不是十分出众,和其他兄弟相比也只能算是平庸者。可见当时被称为“咏絮之才”的才女谢道韫的在识鉴人物上的慧眼卓识。
在品鉴成风的世风盛行下,魏晋妇女也加入了品鉴的潮流之中,她们在赏鉴识人方面也不乏高超的远见和精妙的见解。无论是贵族女性还是较低等级的女性,她们都具备并且善于赏鉴识人的慧眼。
(三)任诞
任诞是魏晋士人表现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精神,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用了54则故事对魏晋士人“任诞”的外在表现进行了记叙与描写。朱碧莲在《世说新语译注》中给“任诞”下了一个定义:“任性放达,魏晋士人不满于旧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之自由和精神之解放。”从这个定义来看,“任诞”精神是一种主张人性自由、反对礼法禁锢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在魏晋士人的身上就外在表现为嗜酒成性、蔑视礼法和任性而为。他们追求身心的自由和解放,追求人性的自然和人格的率真。士人们反抗传统礼教的束缚,主张率性而为,在社会上便形成了一种任诞的风气。魏晋妇女受这种任诞风气的影响,她们的身上也表现出一种有悖于传统礼教的精神面貌。她们表现出来的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从本质上来说,与魏晋士人的任诞精神是一致的。
魏晋妇女的任诞精神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就表现为思想的通达和行为的开放,她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志的表达,这可以在她们对待自我婚姻的态度上看出来。如《晋书·王浑妻钟氏》:
既适浑,生济。浑尝共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故不翅如此。”
参军,谓浑中弟沦也。王浑出自太原王氏,是当时的名士和重臣;钟琰出自颍川钟氏,是魏太傅钟繇的曾孙女。王、钟都是当时一流的大士族,钟氏开这样的玩笑,不仅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反而作为一种风流放达的风度而传颂。
这时期的魏晋妇女似乎并不十分注重传统所谓“妇道”,在当时,离婚、再婚的情况相当多。因此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说,“晋之妇教,最为衰弊”儒家礼教中,要求女性必备四德,《贤媛》第六条刘孝标附注曰:“《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卿,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东汉班昭在她的《女诫·妇行第四》中对四德有更为详细、具体的说明: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辨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其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从这则材料来看,儒家传统礼教对女性的要求集中在贞洁、柔顺、寡言、女红等方面,若妇女能达到这几个标准,即是“贤”了。而《贤媛》一门记录的大多数女性和以上儒家规定的标准是背道而驰的。《贤媛》篇中的女性表现出机敏善辩个性特征,与传统儒家的推崇的女性品质大相径庭。如《贤媛》第九条载:王广进入洞房后,就对妻子说:“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这句话一方面是贬低妻子,另一方面当着妻子的面称岳父的字,也是对岳父的不尊敬。妻子则反唇相讥:“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 ”妻子认为丈夫本来比不上他的父亲,因而并没有资格要将自己和自己的父亲相提并论。王广的妻子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着丈夫的面称公公的字,并把自己的父亲称为英杰,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维护了父亲的尊严。
与《女戒》中“不必辨口利辞也”的妇言要求相悖,有的妻子甚至向娘家人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不满。如《贤媛》第二十六条载:谢道韫嫁给了王凝之,回到谢家后,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谢安安慰她说:“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逸少是王羲之的字。谢道韫回答说:“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谢道韫分别列举了谢家有才能的人,谢家可谓人才济济。谢道韫与王凝之的婚姻虽是门当户对,但她觉得在众兄弟之中个个出类拔萃,但没有想到天底下有丈夫这样的人,言下之意是说丈夫资质平庸并没有突出的才能。
从以上的一些例子来看,魏晋妇女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思想和行为上不再恪守传统的理法,她们面对丈夫时也不再守着以夫为尊的礼教原则,甚至敢于鄙薄丈夫,说出一些离经叛道的话来。她们的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是对传统礼教的反叛,是当时的任诞精神在她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在这样的世风下,当时以葛洪为代表的的一些封建卫道者就指责这些妇女不守妇道。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还有一段文字专“疾”西晋妇女交游之“谬”:
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裟。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炜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
从葛洪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妇女已经不愿幽居闺房门户之内了,她们有着强烈的周旋之好、交游之愿,常常结伴而行,举火而游,以至炜晔盈路,嘻笑盈耳,佛寺和城邑是她们游戏周流之所。她们不仅敢在各种公开的社交场合抛头露面,而且大胆地与男士交际。无怪乎正统而古板的抱朴之士要骂她们“背理叛教”了。
魏晋妇女的任诞不同于魏晋士人的裸形纵酒,她们的任诞主要表现在她们不再局限和服从于传统妇道对她们的要求和规范上。她们的行事做派都表现出她们独特鲜明的个性,她们敢于发表自己的言论,不再以传统妇道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
总结
受历史文化制度的制约,历史上的女性从来都是弱势群体,常常被作为附属品的形式出现,但这一时期的魏晋妇女却与前代以及后来的妇女不同。在家世文化和世风等因素的影响下,她们呈现出了独特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一种风神和魅力,是魏晋风度在她们身上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魏晋风度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个性和风采。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5]朱碧莲.世说新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论文作者:何燕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时代》2019年19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3/18
标签:魏晋论文; 妇女论文; 自己的论文; 礼教论文; 女性论文; 士人论文; 丈夫论文; 《文化时代》2019年19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