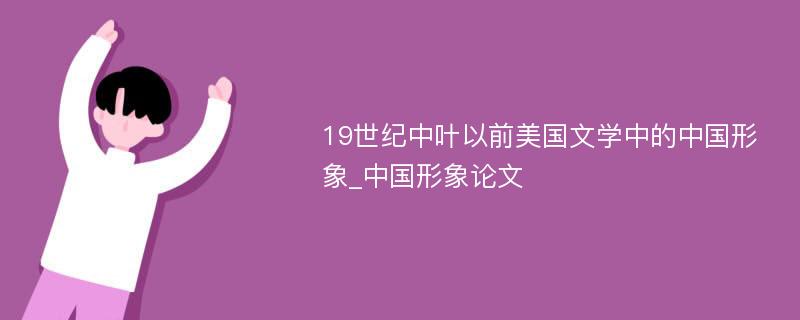
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形象论文,世纪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美国建国初期到19世纪中叶,中美关系以经贸为主。及至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前后,美国虽然已开始积极展开对华外交活动,但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仍侧重于商业贸易。从人员交往来看,这期间来华的美国人中除最早的一批新教传教士外,主要为商人和外交官。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但由于华人是在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后才开始大量涌入美国,由此逐渐引起美国朝野重视,而成为“美国公共问题”之一①,这之前,在赴美移民中,华人只占极少数,因此,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作家既鲜有机会亲历中国,也未有可能去真正接触或关注美国本土的华人移民。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印象多是来自于运至北美的中国商品和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等观察中国后所写的实录报导以及译自欧洲的关于中国的各种作品。虽然对中国客观现实的些许了解很可能使他们提及中国的作品包含某些相关事实,但其笔下的中国更突出反映的是作家本人所在社会和时代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及其自身的文化立场与写作目的。本文即选取19世纪中叶之前曾提到中国或以中国为背景、题材的几种文学文本,以此来解读具有不同创作动因和审美导向的美国作家为读者建构的繁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及其所内涵的实质,并尽可能地发掘出影响这些文本之形象塑造及误读的各种不同的因素。
一、弗瑞诺与德怀特诗歌中的中国形象
在早期中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的东航之行,它不仅掀起了商人们对华贸易的热潮,也为当时美国本土的作家们提供了创作素材和灵感。其中,对此作出最直接反应的作家要算素有“美国革命诗人”之称的菲利普·弗瑞诺(Philip Freneau,1752-1832)了。
菲利普·弗瑞诺在一首题为《第一艘驶华商船颂》(“On the First American Ship That Explored the Rout to the East-Indies”)的诗中热情洋溢地颂扬了“中国皇后”号出航的意义及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收益。该诗向读者传达出了几个不同层面的讯息。首先,与“中国皇后”号的船务负责人山茂召一样,诗人也是开拓中美贸易的积极拥护者,但他的支持除了出于发展本国经济与贸易的考虑外,更多的是基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又与诗人所处的时代和他自身的经历与创作观密不可分。弗瑞诺是在美国独立革命爆发后开始其诗歌创作生涯的。在理性思潮的感染下,他竭力提倡文学创作的社会性,即诗人应将其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并运用自身的知识和文学才能来弘扬美国人的历史和思想责任感。而对于当时的北美人而言,历史赋予他们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摆脱英国的殖民桎梏,争取民族独立。作为一位充溢着爱国热忱的诗人,弗瑞诺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社会诗,还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战争。弗瑞诺痛恨英国的殖民统治和一切专制政体,他因此在很多诗作中都对英国政府及殖民地保皇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鞭挞②,《第一艘驶华商船颂》就包含有这样的诗句。例如弗瑞诺在诗中明确指出,美国商船的东航可以使美国人进一步摆脱“充满嫉恨的英王”的限制,不必由“外国人为我们的船只指明航向”,由此,美国人将“径自绕过风暴难测的岬角,/在咆哮的海风中傲然东航”。可见,诗人将“中国皇后”号的出航首先视为是能彰显国家独立精神和民族傲骨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正如弗瑞诺所预料的,与中国开展贸易的美国商船确实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中美贸易使美国敲开了通达远东的大门。
作为一位极力维护本国权益的诗人,弗瑞诺的爱国情怀无疑是令人钦佩的,但使他颇为自豪的不仅仅是美国人的独立和开拓精神,还有美国在通航贸易中表现出来的无餍的贪欲和咄咄逼人的霸气等这些他引以为荣的民族“德行”,正像他在诗中所夸耀和希冀的,“贸易给我们带来的将是/迎合不同口味和需要的各色商品,/这样,印度的织机就可随处购得,/爪哇的香料树将被我们剥得精光”,因而,“伟大的商船,快快前行吧——/每一阵海风都将带给你繁荣和财富,/直到,东方的宝石装满了船,/你才又驶回那故乡的海岸”。不难看出,该诗传达给读者的最为彰明显著的讯息是诗人对东方丰饶物产的渴求和对富庶繁荣的东方社会的仰羡。曾在建国初期的美国享有很高声誉的诸如茶叶和瓷器等产品将一个积极美好的东方形象直观地呈现在了诗人面前,他因此由衷地欢呼道,“这令人神往的远航的终点,/就是不久将至的中国海岸”③。由此可见,作为东方代名词的中国在诗人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他来说,“中国皇后”号的出航不啻为美国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个举措。
客观地讲,弗瑞诺采用传统英诗韵律写成的这首小诗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并无很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修辞技巧。在诗人的整个创作中,该诗亦显得极不起眼,但恰恰由于它有应景性质,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及此种想象后面的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化心理动机便在诗行之间凸显出来,而这个“集体想象”中的中国首先所指涉的是一种古老而富庶的文明,这一具有乌托邦特征的中国形象不仅为美国的创业者们构筑美国精神、建设理想家园提供了某些灵感和参照,也为建国初期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独立进程树立了一个坐标。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态度并不只单纯地体现为羡慕和尊崇,而是从一开始就承袭了欧洲中国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18世纪中期以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主导性评价无疑是肯定和积极的,但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在很多文本和资料中也都可以看到,甚至在对中国颇为偏爱的首批耶稣会士的笔下,中国也是“光明与黑暗并存的”④,只不过由于当时的欧洲文化并不需要一个过于庞杂、班驳不清的中国形象,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贬斥就没能成为西方中国观的主流,而是作为一股潜流隐伏在对中国的一片赞扬声之中。毋庸置疑的是,早期美国人出于自身时代与文化的需要,在承袭欧洲中国观的过程中,首先会对占主导地位的肯定性中国形象格外关注,但与此同时,否定中国的潜流也不可避免地渗入进了他们的意识之中,如曾视中国为德行之邦的富兰克林就认为中国人“顽固坚持旧习俗”,甚至将中国描述为农业乐园的杰斐逊也曾试图从中国文字中推断中国落后的原因⑤。这种对中国的批评与排斥态度尽管在当时盛赞中国的潮流中并不十分突出,但也绝不可忽视。特别是随着北美对欧洲人否定中国的作品的译介,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和船员有机会去亲历中国,他们的实录报导连同前者一起强化了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美好形象的质疑和贬斥,而文学作品此时又成为了表达这另一种中国观的最形象、最直接的文字平台。
曾担任过耶鲁大学校长的美国教育家兼神学家提莫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1752-1817)曾创作过一首题为《异教徒的胜利》(“The Triumph of Infidelity”)的诗歌,他在诗中所讽刺的对象显然是“异教”中国:
在那个充斥着欺诈和谎言的国度里,
走了样的自然罩了一件伪装用的外衣,
萎缩晦气的躯体嘲笑着关注它的目光,
干枯的灵魂抗拒着思想的力量,
蠢笨的官员,幼稚的皇帝,
受着严格管束的矮子哲学家,
崇拜着不太愚昧的佛的愚昧的信徒们,
似乎一无所知的可怜虫们,
灵魂比身体还要暴露的僧人们,
所有这些人不仅外形野蛮,内心更加野蛮,
面对欧罗巴剽悍的子孙们,(异教)女神畏缩不前,
虽然她依然拖着一双沉重的铁鞋,驾着她那破旧的帆船,
而就在这船上,她曾讲述过无数精彩绝伦的故事,故事中,
有历经四万年漫长历史的帝国的沉浮起落,
有生时鼻梁上就架着一道彩虹的Tohi,
有老子的长生之道——那就是灵丹妙药人参的神秘魔力。⑥
德怀特是弗瑞诺的同时代人,但他对中国的描述与其文学同行笔下繁荣、富庶、光亮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他诗中的中国阴晦虚伪、愚昧枯萎,宛如一个行动迟缓、全无生气的耄耋老人。虽然中国曾有过伟大的神话、帝国的荣光和诱人的巫术,但当面对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时,“中央帝国”的古老、富饶、文明已成了不值一提的昔日神话,中国变为了贫困、邪恶、无知、停滞的代名词。从皇帝到官员,从僧侣到信徒,从哲学家到普通民众,所有生活在这个“充斥着欺诈和谎言的国度里”的人们无不是以“干枯的灵魂来抗拒思想的力量”。诗人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毫无掩饰的鄙视,无疑是对包括维柯、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等在内的欧洲文化精英们在西方进步神话背景下编制的“中国停滞论”的积极呼应,但他自身的宗教背景也部分地解释了其否定中国的个人动机和立场。德怀特出生在一个宗教气息极其浓郁的家庭里,他的曾外祖父就是美国历史上“大觉醒运动”的倡导者、赫赫有名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德怀特本人也是非常虔诚的加尔文教教徒,曾担任专职牧师。之后他虽因就任耶鲁大学校长离开了教职,但却从未放弃对宗教的热情。就是在耶鲁期间,他完成了其神学领域研究的代表作《被解释和捍卫的神学》⑦。作为一位信仰坚定的加尔文教教徒,德怀特当然对该教义所宣扬的“上帝的绝对权威”和“预定论”深信不疑,他认为,只有自己及本教教民才是上帝的真正选民,而那些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们则因没能得到上帝的垂青与恩惠而只能在地狱中挣扎。在他眼中,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异教”国度,其之所以停滞不前除了因为她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国度充斥着崇拜佛祖的“愚昧的信徒”和“灵魂比身体还要暴露的僧人们”。可见,德怀特对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是极端排斥的,而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颇显狭隘的宗教观及其所导致的近乎咄咄逼人的自信和优越感。
弗瑞诺和德怀特都是美国建国初期有一定影响和声望的诗人,虽然两位作家的生平简历显示他们均未与中国有过任何直接的接触,但二人在各自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中国,这说明中国这个异域形象确实为当时美国本土作家提供了素材和灵感。然而,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形象表现为截然不同的一正一反,可见,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由于中西方力量关系的变化,西方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已开始出现转型。此外,两位诗人不同的写作立场和目的也可以表明他们为何为读者呈现出了相互矛盾的两种中国形象。这两种形象与其说诠释了中国,不如说诠释了作家在被社会、时代和文化心理等因素所囿限的条件下所表达出来的关于自身潜在意识结构的主观真实。
二、美国早期游记作品对中国的想象
除诗歌外,在美国早期文学中,另一类利用中国题材以达到“为我所用”目的的文类是游记文学。严格地说,游记文学分为纪实性和虚构性两种,前者由亲历过中国的人所作,他们将自己在旅游目的地的所见、所闻、所感真实地记录下来。后者则往往由作家杜撰出一个旅行者,由这个假想的主人公来观察评价异地异国。当然,即使是纪实性的游记作品,作者也会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掺入虚构和想象的成分,而虚构性的游记则更为那些意欲肆意发挥想象力从而彰显文学灵感与个性的“身在坐椅上的旅行家们”,提供了一片充满异地风情的创作领域。
曼德维尔的《东方闻见录》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篇》及第三篇《感想录》可以说是欧洲东方游记史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纯文学性作品了。前者以借假乱真的手法将关于东方的诱人镜像吹嘘得眼花缭乱,把中国描述为一个神奇的人间乐土⑧。而后者则是笛福本人借鲁滨逊之口,以中国作陪衬来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倾向、国家主义思想;表达对重商政策和殖民扩张的推崇;以及表达对尖刻讽刺的文学风格的偏好⑨等。可见,由于欧洲社会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种种变化,也由于作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种种需求,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想象既有神秘传奇、赞美敬佩的,也有批评否定、嘲讽指责的,但不论是何种态度、何种见解,中国形象在游记文学中所反映出来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虚构,用以代表不同于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的东西”⑩。
可以说,美国早期文学史上出现的东方游记作品直接师承了欧洲的传统。根据学者奥尔德里奇(Alfred Owen Aldridge)的考证,在1825年以前,欧洲人所写的此类故事已被大量译介到了北美大陆。在此影响下,美国人自己也创作了不少包括纪实性和虚构性在内的游记作品(11)。纪实游记如“中国皇后”号船务负责人山茂召根据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所写的航海和旅游日志,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曾于1794至1795年代表荷兰出使大清帝国,后加入美国国籍的万·布拉姆(Van Braam Houckgeest)的《1794至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行记》(Voyage of the Embassy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4-1795)以及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被称为“美国的马可·波罗”的小罗伯特·沃恩(Robert Waln Jr.)创作的大部头作品《中国》(China; Comprehending a view of the origin,antiquity history,religion,morals,government,laws,population,literature,drama,festivals,games,women,beggars,manners,customs of that empire)。而以中国为题材或背景的纯文学性游记则既有散见于报刊杂志上的想象故事,也有独立出版的游记小说。这类虚构性游记虽然在美国早期文学史中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但当我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美国想象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构筑与利用时,此种作品自然就成为了相关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创作就是富兰克林的《中国来信》(A Letter from China) 和一位来自巴尔的摩的署名为沙伦的作者所写的《詹姆士·沙伦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James Sharan Compiled from the Journal,Written during His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Globe)。这两个故事展现给读者的都是旅行者在中国的经历和观感,但由于创作者、叙述者及主人公关系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又是显而易见的。
在富兰克林的中国故事中,叙述者是由作者杜撰出来的一位来自葡萄牙里斯本的绅士,他偶遇一个曾参加过库克船长组织的前往远东地区进行海上冒险活动的英国水手。当库克的船抵达澳门时,这位英国水手不幸落难,只得独自留下来等待救援。后来,他乘上一艘驶往北美的葡萄牙商船,但在途中,这艘商船被海盗所劫持,为了保住性命,船上的水手们不得不加入了海盗团伙。最后,中国官船虏获了这个团伙,并将真正的强盗绳之以法,而葡萄牙商船上的船员们连同被救的英国水手只需在中国监狱里服刑数日即可被释放。富兰克林的故事就由此围绕着主人公,即这个英国水手在中国监狱里的经历而展开。不过,《中国来信》并不是一个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富兰克林只是在此作品中通过游记形式再现出了他道听途说来的关于中国社会的种种传闻,如中国的监牢生活充实而舒适,中国人爱吃狗肉,中国政府对偷盗、抢劫、破坏民宅等行为惩罚严厉,却对泛滥成灾的诈骗现象置之不理等等。作为观察者的英国水手还发现中国妇女的脚并不比欧洲妇女的小,而且在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中也有教堂和牧师,但他们不常去教堂,这是因为去那儿需付钱给为他们做祷告的牧师们,所以,在家中自己敬佛对中国信徒来说就是一个既省钱又实惠的表达信仰的办法。富兰克林的这些描述无疑说明了他对中国现实和文化的一知半解,但作为一位聪明的作家,他却能采用一种巧妙的叙述方式和结构来弥补自己在掌握有关中国信息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充分和不确定性。他安排曾在中国作过短暂停留的那个英国水手充当故事中的旅行者兼主人公,由这位水手将自己的中国之行讲述给里斯本的一位老绅士,而这位绅士又以书信的形式把他听来的故事转述给老友富兰克林,于是,后者就成为这个故事的记录者。事实上,经有关学者的考证,富兰克林与葡萄牙老绅士的通信往来纯粹是子虚乌有的杜撰,这些所谓“中国来信”与信中讲述的英国水手的冒险经历分明就是他头脑中的虚构故事(12)。但是富兰克林的聪明之处,就体现在他能采取这种由不同身份的人物分别充当故事的创作者、主人公及叙述者的叙事方法,来为自己通过道听途说采撷而来的中国信息增添几分现实感和可信性。
美国早期文学中提及中国的另一个饶有趣味的游记作品,是1808年出版的《詹姆士·沙伦历险记》,作者署名即为詹姆士·沙伦。由于这个名字从未在美国文学史册中出现过,因此,除了可以从这本书现存的版本中看到它的出版地为巴尔的摩外,其它关于作者真实身份与生平简历等相关情况我们就无从知晓了。但单从这部作品的题目来看,不难推断出,作者叙述故事的视角和方式与富兰克林为其《中国来信》所设计的结构截然不同。沙伦显然使自己具有了创作者、叙述者、主人公三位一体的身份,这种身份可以令读者在阅读作品时能处处感觉到作者的在场,但由于作者的经历很可能是他本人杜撰出来的,因此,他在掌握旅行目的地的相关情况和信息方面所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极易在叙述中显现出来。如作者谈到,他是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法罗斯岛登上了一艘驶往中国广东的商船的,但他既未提及这艘船的名字和国籍,又没有介绍船长是谁,而这条航线在19世纪初以前的中西航海史上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至于沙伦乘船从广州北行驶往澳门的路线更与实际地理状况大相径庭。之后当他有机会深入到中国内地时,他又访问了不少中国城镇。但除北京、南京外,其它出现在故事中的中国地名的真实性及沙伦在这些地方的经历就实在令人怀疑了,如他提到了一个名叫Nangan的中国城市,他看到那儿的妇女从不裹脚,她们身体强壮,勤劳能干。他还发现,溺婴现象虽然在中国较为普遍,中国政府却会委派专人来照料那些被人救上来的弃婴,能活下来的婴儿就由政府抚养长大。可见,同富兰克林的中国故事一样,沙伦的游记中也包含有许多有关中国的虚妄之说(13)。
应该看到,富兰克林和沙伦在各自的游记中所讲述的并不全是不实之说,在他们传达出的中国讯息中,也有一些是有所依据的。如在《中国来信》中富兰克林提到了豆腐的制作过程和曾引起不少欧洲作家兴致的中国风帆车的动力原理,其中的描述就与实际情况相差无几。能对此种信息掌握得如此准确,当然与富兰克林对中国文化的留意和平时阅读有关书籍和文献的习惯密不可分。据考证,他在英国期间曾听说了到过中国的著名冒险家詹姆士·库克的航海经历,后又在巴黎得到了一本由好友本杰明·沃恩寄送的当时尚未正式出版的库克的《太平洋之旅》,他如获至宝,并竭力向美国船员推荐这本书,由此可以推测,库克的这部纪实游记很可能就是富兰克林创作《中国来信》的重要灵感和素材来源(14)。同样,沙伦在叙述自己的“中国之旅”时,想必也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如当他在故事中讲述自己如何爬上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建筑中国长城时,他对长城的高度、宽度及历史功用都作了相当精确的描写。显然,沙伦不可能编造出如此客观真实的文字,他应该是参照了他人对长城的介绍(15)。总之,富兰克林和沙伦的游记作品尽管在叙述视角和结构安排上有所差异,但两位作者都是在参阅前人有关中国的记述文字的基础上,或也有可能在与到过中国的人有过接触后,揉加了一些自己主观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从而创作出了时常会令读者感觉真假难辨的中国故事。
前文提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欧洲业已抬头的“中国停滞论”对美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也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的潜流,但这股潜流还处于有限的影响范围内,很多未亲历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仍抱有一种带有隔膜感的肯定之情。富兰克林和沙伦显然就对中国持有这样一种温和的接纳态度,富兰克林在《中国来信》中将中国监狱描写成了一个温暖、舒适的避难所,他笔下的那个英国水手在此处不仅受到了公正的待遇,日子过得还很充实,甚至似乎找到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沙伦在其游记中也不时流露出对中国的欣赏和理解。如前文所提及的,他发现溺婴现象虽然在中国较为普遍,但政府却会委派专人来照料和收养被抢救过来的弃婴。可见,这两位作者对中国不仅少有恶感,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还被涂抹上了一层体现着宽厚、仁慈、公正等理想德行的乌托邦色彩。但如果我们因此推断他们是在真诚地为梦中的中国高唱一首赞歌,那未免太过武断。事实上,富兰克林和沙伦笔下旅行者的中国印象虽然没有笛福塑造的主人公鲁滨逊的评价那么糟糕,但也绝不是曼德维尔所构筑的那种神奇斑斓、眼花缭乱的中国形象的翻版。客观地说,中国这个已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逐渐引起美国人关注的异域国度只是为富兰克林进行文学练笔或为像沙伦那样默默无闻的小作家实现其文学野心提供了适当的创作素材和背景。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中国观实质上并未建立在非常鲜明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但另一方面,不论文学创作者如何肆意地想象中国,也不论他们将中国纳入何种视域,这些并没有去过中国的神游者们在借助历史、想象、虚构来穿越中国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我们真真切切地描画了一个与“自我”截然不同的“他者”形象,而这一形象与那些曾踏上过中国土地的旅行家们的中国印象一起构成了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
三、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利用
虽然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中美贸易的开展和来华美商对中国的实录报导为美国建国初期的本土作家提供了不少灵感和素材来源,但他们的创作与同一时期欧洲涉及中国题材的纯文学作品相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不免有些相形见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文学本身的发展在当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20年代仍未有太大改观。不过,在其后三四十年间,由于受到新时代上进精神的感染,同时在英国和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启迪下,渴望表现自己新经历和新追求的美国人经过不懈的尝试,终于开创出了一条属于美国自己的文学之路,由此真正独立的美国文学伴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蔓延和高涨,在19世纪上半期逐渐炼铸成形(16)。
美国浪漫主义文学首先当然是诸多美国本土因素和条件熔铸为一炉的产物,但19世纪30年代以前波及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对独立的美国纯文学创作的奖掖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以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为主要特征。为了着重表现个人主观世界对事物的内心反应、感受或追求个人解放,浪漫主义作家常常在作品中描述异乎寻常的情节、自然环境和人物,有的甚至沉溺于遥远、玄妙世界的探索(17)。对他们而言,能给予这种陌生神秘之感的最奇异的地方莫过于在时空意义上可望而不可及的东方国度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曾一度流行的“东方故事”就突出地反映了欧洲作家对东方的想象。在此类作品所涉及的引人遐想的遥远国度中,中国无疑是可供作者利用和把玩的最具异国情调的“他者”之一。仅就英国文学而言,18世纪的作家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和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都曾借用中国人的口气,以书信体的形式对英国的人情风俗和司法制度加以批评(18);而中国历史传奇的瑰丽和神秘,更为19世纪上半期的重要诗人柯律瑞治在其被称为“英国文学最伟大的诗作”《忽必烈汗》中营造一种浪漫主义梦幻般的意境,带来了汩汩涌动的灵感之泉(19)。
受到欧洲“东方故事”的影响,美国文坛自19世纪初也开始出现类似体裁和风格的纯文学创作。这其中既有以东方为背景或题材来讽喻自身或谈论道德的虚构小说,也有将东方神秘化、传奇化以烘托浪漫奇异气氛的想象故事。进入19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浪漫主义作家开始逐步摆脱欧洲传统束缚,彰显自身创作个性。不过,在他们笔下,弥散着异域情调的东方仍未丧失其楚楚动人的魅力。如擅长运用超自然因素渲染气氛的作家霍桑,在《红字》、《福谷传奇》及《玉石雕像》等作品中,就曾使用“东方公主”、“东方特征”等字眼来表现多情善良的女主人公们所具有的神秘性感之美。虽然霍桑所指涉的东方从地理概念上讲意义并不很清晰,但从他留下来的读书笔记中,我们不难发现:包括中东的穆斯林地区、南亚的印度以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等在内的不少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曾进入过他的阅读视野,其中,他可能接触过的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文本,有查尔斯·古兹拉夫的《中国简史:古代与近代——兼对中外贸易交往的回顾》(1834年纽约版)、马嘎尔尼的《英使谒见中国皇帝纪实》(1799年伦敦版)和约翰·怀特的《中国海之旅》(1823年波士顿版)等历史文献资料和纪实游记作品(20)。可见,霍桑对中国并不十分陌生,但他毕竟从未亲历过任何一个东方国家,因此,根据自身的阅读经验,将包括中国在内的遥远东方视为一个远离日常平庸和拘束、充满生动质感和神秘风韵的超凡脱俗的理想空间,就成为了像霍桑这样喜爱通过营造虚幻意境来阐述人心真理、讥弹社会不公的典型浪漫主义作家处理异域想象的最常见的方案。
19世纪上半期,美国文坛上另一位对异域东方流露出迷恋和敬羡之情的作家,是稍晚于霍桑的浪漫主义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与霍桑不同的是,惠特曼笔下的东方不再是阴柔和感性的代名词,而成为了人类智慧和灵性的象征。如在《到印度去》(“Passage to India”)一诗中,诗人提出要重返印度,他写道:“啊,灵魂啊,首先歌唱的,永远歌唱的,和你一起呼唤的却是/‘过去’!‘过去’!‘过去’!”可见,诗人呼吁“到印度去”的内在宗旨是要以东方形象所表征的古代精神文明来抗衡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由此来表达自己“梦破犹惜梦”的迫切之感(21)。
在惠特曼的东方之梦中,中国显然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因为他在其最为人称道的诗集《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中提及中国之处就至少有10次之多(22)。如在《遐思于时刻》(“This Moment Yearning and Thoughtful”)一诗中,诗人坦诚自己对“遥远的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充满了好奇,并将生活在这些异域之邦的人们视为“同胞和相爱者”(23)。在《向全世界致敬》(“Salut ou Monde”)中,他仰望喜马拉雅山、俯视中国海以及长江、黄河、黑龙江和珠江,显然“中国”已成为天地宇宙的一部分(24)。据采访过惠特曼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卡彭特的记述,惠特曼曾将中国人与德国人相比,认为中国具有德国人的朴素、真实和热情,“此外还有德国人所缺乏的某种机敏文雅的品德”(25)。不难看出,惠特曼的中国印象并没有受到西方当时业已抬头的否定中国的潮流影响,相反,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的信仰使其坚定地认为自由与平等思想不仅适用于美国人,而且世界各国各族都应地位平等,尽享民主自由之福。因此在诗人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中,没有国界、肤色、种族之分。他预见到“由水陆形成的庞大的地球在授受一切,欧、亚、非三洲相接,构成新的世界,各国国土和地貌手持节日花环,宛如新郎与新娘执手相爱一般”(26)。
如果说以霍桑为代表的,以低沉、孤抑为创作基调的浪漫主义作家,在表现和利用东方形象时,还未能脱离欧洲传统的“东方概念”束缚的话,那么力图以美国的方式表现美国生活的诗人惠特曼,在唱出自我之歌的同时,则以不同于欧洲的声音肯定了不同民族、国家、种族共同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跨越时空隧道、用灵魂聆听东方古代先知和神祇谆谆教导的可能性。在惠特曼聆听到的智慧之音中,中国圣贤孔子的声音可能不是最清晰可辨的,但从他保存过的一些关于中国的报刊剪辑文章的内容来看,他对孔子并非全然无知。惠特曼的一位传记作家就谈到,诗人在其所著的《只言片语》(Notes and Fragmants)中曾两次提及孔子。此外,在诗人的葬礼上,他的一位朋友还诵读了孔子著作的片段以志哀戚之情(27)。当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惠特曼果真阅读过中国儒家经典,但从他指涉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度的字里行间中,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这位在19世纪美国诗坛上特立独行的歌者不同寻常的“东方情”和“中国情”。可以说,惠特曼是在超前的民主意识和近乎乌托邦式的崇高理想的基础上,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纳入其诗歌创作视野的。在他笔下,无论是古代中国的悠久文化还是现实中国的客观存在,都仅仅是世界多样性和一体性的一个表征。因此,他自然不会将关注的焦点定格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细节内容上,而也只是从“为我所用”的原则出发,将中国或东方视为可以为其诗歌主旨服务的素材之一。
惠特曼可以说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诗歌理念和精神追求曾受到不少同代人的冷嘲和白眼,但幸运的是,堪称美国独立文学铸造者和一代宗师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却向他投去了赞佩和赏识的目光。爱默生在美国文学文化史中的主要贡献是倡导超验主义,推崇个性解放。他之所以极为肯定惠特曼的创作,无疑是因为后者以诗歌形式积极贯彻了超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主张,而另一方面爱默生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解读也可能直接或间接催发了惠特曼对东方古代先知的向往之情。在爱默生的眼中,中国古代哲学关于自然一体性的观念和人本主义精神以及和谐、安静、精神化的特点,不仅对“西方的机械主义和异化可以起到某种平衡作用”,也能为遵循西方哲学“主动、活跃、物质化”特征的美国人提供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角(28)。正是带着这样的视角,爱默生一而再地摘引儒家思想中关于道德、人性、修身、治学等方面的语录。同时,也正是在此种视角的制约下,他对自己不能认同的、体现儒家崇古思想和忠、孝、节、义等封建观念的信条说教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对于建立在这些思想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他更是表现出难以抑制的厌恶和反感。爱默生曾在日记中不断地抨击中国,他最为有名的一句评论是“中国是她自己的纪念碑”,因为中国的历史单调重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古老呆板,“中华帝国享有的完全是木乃伊的声名”(29)。
爱默生对现实中国的否定与他对孔子的景仰似乎构成了其中国观颇显矛盾的两个方面。但事实上,他的这两种态度恰恰体现出了其间必然的一致性。首先,爱默生是从自身文化立场和思想实质出发,来借鉴中国儒家思想中的部分内容以构建美国独立的文化精神的,而其超验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既强调冲破束缚、又重视道德自律的理想的个人主义理念和信仰,儒家的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信条因此可以为这种个人主义提供灵感和佐证。而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爱默生为了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才接触儒家学说的,可以想见,他自己既无兴趣也无必要去深入探究儒家思想与现实中国的社会制度与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便可能导致了他未能对孔孟学说作辩证全面的考察,当然更看不到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某些正面影响。对爱默生来说,借鉴异域思想文化精华的最实用易行的方法就是直接摒弃掉他确实无法认同的内容,而不必对其进行学术意义上的分析。为表达对个人主义信仰的追求和对专制落后政治的痛恨,他又简便地将他实际上并未去真正了解过的中国社会,视为一个反面典型和闭关锁国、思想狭隘的同义词。因此,对爱默生来说,虽然孔子是睿智圣明的代名词,而中国却成为象征其所强烈反对的一种话语符号,进入19世纪以来这一符号也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关于中国的“集体想象”。
四、结语
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人中国观形成的基础是传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和来自欧洲和本土的关于中国的文字叙述。经由这些渠道所传达出的信息连同西方文化心理潜意识中的中国形象一起构成了作家们认知中国的“知识场”和“文化场”。当然,凡涉及到知识或文化的问题总是具有因袭力和传承性的,而另一方面,“社会集体想象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的某些‘先入之见’在适当的现实外力作用下又会发生变异,产生出与传统集体想象既联系、又有别的另一种社会集体想象来,新的想象物又会影响同时代或下一代的作家”(30)。18世纪末至19世纪最初几十年正是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认识从肯定向否定过渡的阶段。在对中国的传统集体想象和尚未最后成形的新判断的双重影响下,19世纪中叶以前的美国作家在不同体裁的文本中表达了颇不稳定、甚至相互矛盾的中国观:他们或羡慕,或批判,或尊敬,或仇视,或包容,或排斥,其相关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也由此显得斑驳不清。
当然,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并不只是对其所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的简单复制,因为文学文本中的异国形象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31),即每个作家在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囿限的同时,也必然要以文本为手段和平台来呈述个人视阈中的艺术真实和精神立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由于独立后的美国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均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文学创作领域也随之出现了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作家中有的仍固执地坚持师法欧洲文学的传统,有的却以一种乐观的情绪积极应和着新的时代精神,还有的则因意识到了上升时期的美国社会已潜伏着危机,而力图以自己独特的美学探索和哲学思考来反对日益明显的物欲横流,总之,在“集体想象”、文化立场、创作来源与动因、主旨题材、情感诉求和审美导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作家们笔下的中国形象有时表现得风情万种,有时睿智优雅,当然也不乏面目可憎的时候。而不论他们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有关中国的客观现实,这些从未亲历过中国的作家们其实都是在透雾观花,隔水望月。当然雾里和水中的影象必定将会变形、扭曲乃至虚幻不清,因为真实的花与月毕竟不是他们最终的兴致所在。
作为被新经历和新思潮充盈着的美国本土的新一代作家,他们的历史职责是用艺术的手法再现现实,揭示人生真理,表达生命欲念和理想追求。因此,对这些作家而言,中国形象仅仅是作为素材或背景来服务于他们个人观念和情感的表达的。而要想达到上述目的,他们只需依赖于自身明确的写作目的以及对其所处社会关于异域文化的集体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了解和利用。当然,在此基础上,作家们相关的阅读经验和与到过中国的人所可能有过的接触经历也会有助于他们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更趋近于客观真实。但作家们并不一定要必须背负起去查究和反映历史实与虚的时代使命,因而,对于作家们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无论是美好或恶劣的中国形象,我们中国读者大可不必为之得意或愤慨,而应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前提下对美国文化视野内中国形象生成、变形以及意义重构的轨迹去进行学理层面的考证、分析和判断。
注释:
①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1页。
②常耀信:《美国文学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③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pp.101-102.
④史景迁:《16世纪后期至今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罗溥洛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包伟民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2页。
⑤韩德:《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⑥Timothy Dwight,The Major Poems of Timothy Dwight,William J.Mctaggart& William K.Bottorff ed.,Gainesville,Florida:Scholars Facsimiles & Reprints,1969,pp.344-345.该诗由笔者自译,但在袁柯编著的《中国神话大词典》中笔者并未找到诗中提到的“Tohi”。
⑦James D Hart ed,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217-218.
⑧姚京明:《平托〈远游记〉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3期。
⑨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114页。
⑩张隆溪:《非我的神话》,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彭晓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11)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69-272.
(12)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p.78.
(13)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39-241.
(14)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pp.78-79.
(15)Alfred Owen Aldridge,The Dragon and the Eagle: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41-242.
(16)常耀信:《美国文学史》,第116页。
(17)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18)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210-211页。
(19)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第229页。
(20)Luther S.Luedtke,Nathaniel Hawthorne and the Romance of the Orient,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p.230-231.
(21)常耀信:《美国文学史》,第337页。
(22)杨金才:《文化对话与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2期。
(23)Walt Whitman,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Justin Kaplan ed.,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1982,p.280.
(24)Walt Whitman,Complete Poetry and Collected Prose,Justin Kaplan ed.,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Inc.,1982,p.287.
(25)李野光:《惠特曼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26)常耀信:《美国文学史》,第338页。
(27)常耀信:《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学中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
(28)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77-78页。
(29)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第145-146页。
(30)孟华:《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31)孟华:《形象学研究要注重总体性与综合性》,《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