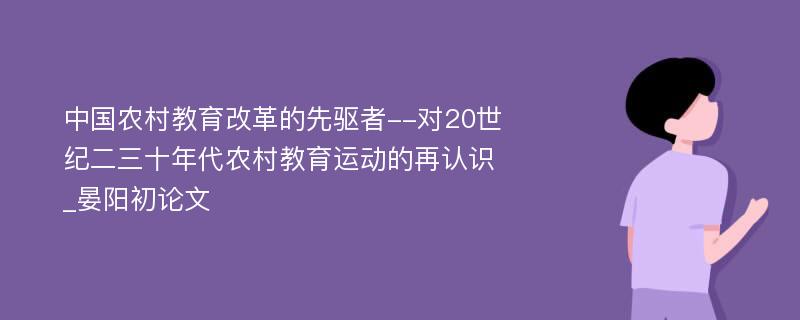
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年代论文,先声论文,教育改革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5-0124-08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但积淀在中国人头脑中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思想并没有随“大清帝国”的覆没而烟消云散。袁世凯的“洪宪帝国”、张勋的“辫子军”复辟、封建军阀的割据……无不在向世人说明:仅推翻一个封建帝国是不能立即把中国人民带进民主自由的国度的,更无法使中华民族很快走上繁荣富强之路。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晏阳初曾作过这样的反思:“在民族自身没有力量之前,一切的一切都是废话。涨红了脸,吹破了胰子泡以后,沉下心来反求诸己,觉得非在自己身上想办法,非靠自己力量谋更生不可。这就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乡村建设便是这觉悟的产儿。”[1](p.175)中国早期的思想精英们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革面”与“革心”要统一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与复兴,必须开启民智,振兴教育,弘扬民主与科学。继新文化运动以后,平民主义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教育实验、教育独立等诸多思潮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酝酿与发展不仅随中国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及各种因素的变革而推移演变,而且还受国际教育大气候的影响,成为国际“新教育运动”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乡村教育思潮是这股浪潮中的一朵激越而亮丽的浪花。本文拟对以黄炎培、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思想及实验进行比较性的研究和再认识,以期获得可供解决今天中国农村和农民教育问题的一些有益启示。
一、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相同的目的
黄炎培被认为是20世纪初最早看到乡村教育重要性的第一人。1921年,他在《农村教育牟言》一文中指出:“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虽然,全国国民之生活,属于城市为多呼?抑属于乡村为多呼?吾敢十之八九属于乡村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思想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生活之教育。”[2](p.93)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80%~90%,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差,文化素质低,是影响中国走向富强的主要障碍,因而,要使中国走向民主与科学,实现强国之梦,必须重视乡村教育,实施“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之工程。对此,陶行知深有同感,他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3](p.69),“中国以农立国,十之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4](p.494)。
在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的倡导下,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放下架子,走出书斋,奔赴农村,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实验,从事着伟大的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工作。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演化成20世纪初规模空前的乡村教育运动。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成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社团作为组织机构,如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陶行知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1)、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和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1929)等;其二,创办大量试验区,如黄炎培的江苏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1926)、陶行知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7)、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试验(1929)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试验区(1931)等,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到1935年,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乡村教育、乡村改进和乡村建设的实验区已达193处之多;其三,形成特色各异的乡村教育理念,如黄炎培把职业教育作为改进乡村的根本途径,陶行知把乡村学校和教师当作改造乡村的核心和灵魂,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以达“除文盲、做新民”之目的,梁漱溟则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整个建设的和谐与统一。尽管他们的试验方法和教育理念互不相同,但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和追求,即通过乡村教育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之目的,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之大业。正如陶行知所说:“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的幸福!办的好,能叫人民上天堂;办的不好,能叫人民下地狱。我们的教育同志应有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3](p.80)他曾立下宏愿:“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叫中国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新生命。”[3](p.80)
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手段
中国农村的贫穷、愚昧、落后,使人们都认识到乡村教育的重要性。由于从事乡村改造和建设的有识之士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因而,他们在提出改造乡村的方法和手段上也有着迥异的特色。
黄炎培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特科班,经济实业思想较早在头脑中扎下根基,同时,他还深受蔡元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1914年,他以上海《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遍走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教育考察,目睹了教育与生活、教育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切为他的“职业教育救国论”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尤其是1915年他参加了旅美实业团任随行记者,看到美国职业教育的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亟需改革。顺应农民心理是黄炎培乡村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主张用职业教育振兴中国农村,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吾们认为‘利之所在,民尽趋之。’只须把有利的事实给人家看,不怕人家不照办。”[2](p.210)
陶行知抱着强烈的教育救国思想,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改造中国的教育之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曾留学美国的他,深受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乡村教育思想中亦有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他的改造乡村的理论结构是:以乡村学校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以乡村教师作为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以乡村自治作为改造乡村组织的保证。由于他把乡村改造的重任寄托在学校和教师身上,认为培养足够的校长和教师,才是改造乡村、实现理想的关键,因而,他致力于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以便能让那些带着理想、激情、知识的青年教师奔赴各个乡村,去完成那“普罗米修斯”般的神圣职责——建造中国乡村的“乌托邦”。
晏阳初因把毕生精力和心血献身于中国及国际的平民教育事业而荣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伟人”[1](p.340)的称号。他自幼就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博爱和平、舍身救人、造福人类”的教训在他心灵上留下了烙印,同时也深受中国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的熏陶,其乡村教育理论的思路是:通过“平民教育加乡村改造”,实现“除文盲、做新民”之目的。他从实际的农村调查出发,认为中国农村问题虽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有四个病根:愚、贫、弱、私,他主张用“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加以攻克,并采用“三大方式”(学校式、生活式、家庭式)进行推动。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一大重要特色就是“三发”原则:发现、发明、发扬——开发农民的智慧。他说:“我要说世界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世界最宝贵的矿藏是‘脑矿’,最大的‘脑矿’在中国,中国农民蕴藏着无穷伟力。我们搞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就是在开发‘脑矿’,开发民力。”[1](p.325)
梁漱溟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自小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功底。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5](p.174)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基本理念与结构。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入侵,传统文化自身失其调和,破坏了伦理本位的礼俗秩序,从而导致农村混乱。“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5](p.164),救治的“药方”要靠乡村建设,建起新的乡村文化礼俗,恢复伦理本位的社会秩序。他认为,具体途径有二:其一,利用中国传统制度中的“乡规民约”形式,赋予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自发产生、自愿维持、共同遵守的信条,从而达到改造和稳定乡村之目的,实现家庭化、家族化、伦理化的和谐社会。“在中国必须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换句话说,就是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本精神。”[6](p.665)其二,建立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我们中国现在所急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团体组织,就是要在团体组织里去变,而求得团体组织之道。”[6](p.665)创立不同类型的乡村学校就是建立团体组织的重要措施。
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社会阅历、意识形态观等,他们在医治中国乡村“疾病”时所开的处方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于社会实践,都有一颗“救民于水火”的诚挚的心!
三、“大乡村教育观”——共同的教育理念
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乡村改造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乡村教育家都从教育着手,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从事乡村的改造工作,并且他们并不是把目光仅仅局限在教育上,而是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改造。
黄炎培把孔子的“富、庶、教”思想演变为“富教兼施”,且进一步走向“富、政、教合一”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救国之本在实业,实业之本在道德,教育者除脑力运用之外,而复以道德为依归,所谓职业者,如是而已。”[7](p.635)他认为乡村是一个整体,应该进行整体改进。1925年前后,黄炎培提出“划区施教”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其目的就是在农村以区域为中心,而不是以学校为中心,施教者兼顾该区的经济、卫生、交通、治安等问题,把它们和教育放在一起统筹解决。“方今教育上最大问题,无过于学校与社会隔绝。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从此更进行扩大教育的范围,沟通生活界线种种方法,而理想的教育,或者因之而实现。”[2](p.218)
与黄炎培“划区施教”不同的是陶行知的“以学校为中心,以乡村教师为灵魂”的整体乡村改造模式。他根据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把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思想,演变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这里,陶行知不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是把整个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大化。他认为,乡村教育的生路“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3](p.79)。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理想主义的“大教育观”!
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更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试验区的工作,是以整个农村生活为对象的,它把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四种教育连锁扣合起来,成为整个的农村建设。”[3](p.80)实施“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三大方式”则发挥着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其开发中国农民“脑矿”的教育理念与仅把乡村教育看成识字教育的观念相比,更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晏阳初的乡村改造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政治、经济、教育、卫生、自卫、礼俗建设的整体进步,达到复兴国家、振兴民族之目的。晏阳初重视社会教育的作用,采取多重教育的形式,是我们今天从事社会综合治理时所应多加借鉴的。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被破坏而激起的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我们民族和社会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他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云一种建国运动。”[5](p.161)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为寻求民族自救之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其乡村建设的内容是通过建立“乡村组织”(乡长、乡农学校、乡公所、乡民会议)以实现“新乡政”,解决农村教育及政治、经济建设三大问题。具体途径是用乡农学校实现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生产劳动及知识教育等,以推进社会,组织农村,达到“政教合一”之目的。
上述四位教育家关于乡村整体改造的具体设想及阶级性质各不相同,晏阳初和梁漱溟因其政治倾向性问题,他们的乡村整体改造计划最终为国民党所利用,对其负面作用,我们应明确立场。但就教育理念而言,笔者认为,他们的“大乡村教育观”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教育所应具有的先进理念和特色:一是教育地域的扩大,学校、课堂、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炕头等都可作教育的场所;二是受教、从教人员的增加,男女老少、农民、教师、官员等既是受教对象,亦都可作施教人员;三是教育内容的拓宽,读书、识字、乡政、自卫、农、工、商、贸等都是教育的内容;四是教育方式的灵活,课堂教学、课后活动、乡规、民约、劳动、陶冶、示范等多重方式灵活运用。可以说,中国20世纪初的乡村教育思想已初具现代终身教育的理念。
四、“改良”与“革命”——先觉者的困惑与反思
乡村教育运动经历了十几年风风雨雨,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内政局的动荡不堪而走向沉寂,但代表着那个时代“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们,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的拯救及农村出路的探索。热潮平静下来之后,他们已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总结这段乡村教育运动的得与失。
“以出家的精神做乡村工作”[8](p.446)的梁漱溟,抛弃优越的都市生活来到乡村,欲以满腔热血和激情“解救众生”,结果却遭到农民的冷遇,甚至反对,心中难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该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们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做不下去”。他也意识到自己未能代表时代的要求、乡村的要求,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5](p.575)。
晏阳初以实现孙中山“必须唤醒民众”的遗愿为己任,认为从事“人的改造”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希望从根本上提高民族整体素质。几十年乡村工作的实践使他感触颇深:“一个强加于人民的计划,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会满足不了其真正的需要而宣告失败。”[1](p.356)“积几十年经验,我们深深认识到,要使自己乡村的改造事业取得成功,非要和农民打成一片不可,非要向农民学习不可。”[1](p.325)20世纪80年代,晏阳初两度重游60年前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定县翟城村,看到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叹道:“定县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它使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与希望。我很赞赏老百姓讲的两句话:是毛泽东领导我们翻了身,是邓小平带领我们走上富裕路。”[1](p.412)也许直到此时,他才对“改良”与“革命”的真正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黄炎培一心想在动乱的时局中走出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现实性使他根本没有机会走通这条路。他曾十分感慨地说:“良以我们没有政权,赤手空拳地改良社会,除掉根据一点热诚所发出的情感,还有什么武器可以利用。……不过照此干法,时间总需长些,区域总需小些。如果有了政权,一切当然痛快干去。”[9](p.293)1982年,黄炎培在回顾这段岁月时自叹道:“现在看来,我的这些做法只能说是改良主义的尝试。”[10](p.88)
陶行知的村治主张充满民主进步色彩,有的还近似空想主义。1928年,在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曾提出这样三条规则:(1)每个实验社会,对内对外应有完全主张;(2)每个实验社会,应严守中立;(3)每个实验社会的实验期暂定一百年,但不得延长[11](p.120)。然而这仅是他的一厢情愿。且不说这些主张能否得到政府的同意,就连他从事乡村教育实验的晓庄师范也遭到封闭,自己落得亡命天涯的结局。他后来反思道:“我承认大众文化的普及,是要等到整个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但是大众的政治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要靠大众继续不断的努力才实现。”[12](p.161)
20年代至30年代的教育家怀着强烈的爱国心,以牧师布道般的精神从事着乡村工作实验,但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汪洋大海中,想通过几个试验区改造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其可能性之小,是不难想像的。这种尝试就如19世纪欧文想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建立起一座社会主义的孤岛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向以代言人自居,从‘代圣贤立言’到代人民立言,从文以载道到文化启蒙,永远摆脱不了思想优势的自恋心态。知识分子总是在考虑如何引导人类按自己预设的道路前进,总是在想自己与大众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做才能显出不同,却没有人去思考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有什么共同之处。”[13](p.45)20年代至30年代的乡村教育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已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并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救世主”的心态,当然他们“在黑暗中以爝火荧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科学发明是通过试验取得的,社会改造也有待于试验来推广”[14](p.109)。
五、借鉴与启示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80%人口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5](p.1078)目前,我国正在从事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其重点和难点仍在农村。江泽民同志在1999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强调指出:“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我国12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广大农村人口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和现代化的大问题。”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解决农村及其教育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通过对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及乡村教育家思想与实践的再认识,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些启示和借鉴。
(一)理论、实践与激情的融合,造就出一代伟大的教育家
中国20年代至30年代可谓是教育家群星璀璨的时代,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教育家群体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出有这样几种因素促成他们成为一代伟大的教育家:其一,有着自己特色的教育理念;其二,亲身从事教育实验(践);其三,具有强烈的献身乡村教育事业的激情。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都以“出家入佛”的精神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毛泽东亦对这种“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1](p.400)他们忧国忧民,悲天悯人,都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爱默生说,“无热诚即无伟大”,正是这种对人民的无限热诚及对教育的无私奉献,造就了一代伟大的教育家。
当代中国教育界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或著书立说,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教育理论体系;或投身教育改革实践,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或默默耕耘讲坛几十载,教书育人,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生……但他们或许少有机会集理论、实践、激情于一身。正如吴康宁先生所言:“凡是真正有作为的教育思想家所提出的教育取向,无不伴有实现这些取向的相应的技术路径,无不具有这些教育家所亲身经历的亲自设计、亲自指挥的教育实践,或教育实验的支撑。”[16](p.53)21世纪的中国农村也正在迫切地呼唤着一大批既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又富有激情的教育家,能把自己的理论与激情奉献于中国的农村教育实践,去完成那20世纪初乡村教育家们未竟的伟大事业。
(二)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
20世纪初,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内受封建军阀的凌辱欺压,天灾兵祸,民不聊生,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一大批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不断地追寻、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为代表的众多知识分子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也是历史的必然。梁漱溟曾说:“我们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是人为的,真不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与其说乡村建设运动倡导于我,不如说是历史的决定。我亦是被历史决定的,所以我亦料不到我自己啊。”[5](p.34)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外无独立的国家主权,内无民族自由平等,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完全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无‘国’可救”。这不仅是乡村教育家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说得好:“面对极端反动腐朽的统治,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或不认识马克思主义,从爱国主义出发,囿于自己的经历,以目代纲地各自提出实业、科学、教育救国,虽然救不了国,多数还是出于不甘自弃的好心。要是把他们放在改造社会的总纲之下,忠诚地从事实业、科学、教育等事业,在任何时候对社会都是有益的。我们社会里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14](p.108)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苛求:让梁漱溟拿起枪来,让晏阳初去参加游击队。因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只能改变武器使用的方向,而决不会轻易放下武器。鲁迅的文艺救国如此,李四光的科学救国如此,陶行知的教育救国也如此。”[17](p.252)
教育的社会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一功能能否正常且正确地发挥,必须依托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确立。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单纯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并不能使中国迅速走上富强之路,“辛亥革命”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也都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978年,他刚一复出就自荐抓教育,他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18](p.274)这位睿智的老人站在历史长远发展的高度,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都在不断地强调依靠教育和科技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他的论断为提出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构筑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993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提出,“必须坚持把教育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96年,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把“科教兴国”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如果说,20世纪初的“教育救国”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救国云云只是一种奢望的话,那么,今天的“科教兴国”则是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必然需要。从“教育救国”演进到“科教兴国”,是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强国复兴道路的必然历史进程,是“中国教育的社会价值观从主观到客观,由梦想到现实的艰难转换过程”[19](p.80)。“科教兴国”方略必将给中国的农村及乡村教育带来新的景象。
(三)从“乡村改造”到“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无法摆脱社会政治经济制约的,乡村教育运动要想摆脱当时社会客观现实的束缚也是不可能的。我国20年代至30年代的乡村教育家也已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从事乡村改造时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不同的政治派别、社会团体或国际支持,但在一个时局动荡不堪的年代里,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和社会力量都无法给教育一个稳定而长久的支持。正如黄炎培所感叹的那样,若有了政权,便可痛快干下去。但有了政权的支撑,是否就能一切按照预先设定的理想蓝图“痛快干下去”?建国后的农村“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已给我们作出了历史性的回答。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家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诸多积极而可贵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和实践财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梁漱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离不开教育,运动的本身就是一项教育工程。“所谓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自一面言之,其义实即如何企及现代文明之问题。”[20](p.401)他曾一语道破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的问题。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不仅流溢于我们的肌肤,更渗透于我们的血管和骨髓,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换来的必是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那样,“割了辫子,便也自称是革命者了”。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否定或肯定都是不科学的,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如果我们缺乏正确对待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必将导致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无法发挥其应用的作用,进而直接影响现代性本身的落实,制约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农村地域辽阔,文化差异悬殊,特色各异,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如何继承并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使之朝着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方向发展,是中国农村教育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村的改革和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是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发端。1987年,国家教委决定在河北建立农村贫困地区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自1989年以来,全国已确立116个国家教育改革实验县。可以说,今天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是昔日“乡村改造运动”的历史演进,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家在乡村改造中所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与20世纪初的“乡村改造”相比,今天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有着强有力而稳定的政治经济支持。但历史事实已无数次地证明,仅仅依靠行政杠杆根本撬不动中国农村这块巨石。要使中国农村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恢复起农村社会原有的自组织能力,激发起农民身上自有的活力与激情。
标签:晏阳初论文; 梁漱溟论文; 黄炎培论文; 陶行知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农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