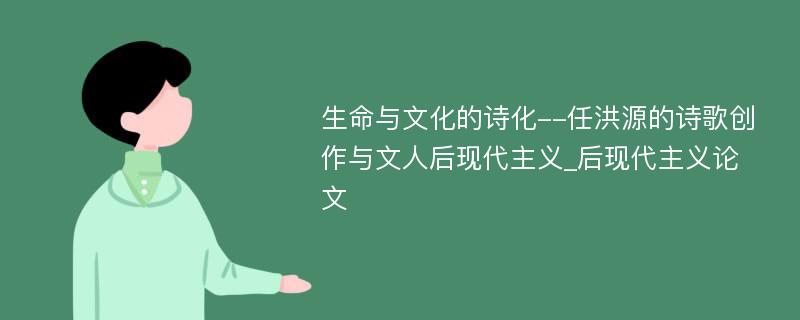
生命与文化的诗性转换——任洪渊的诗歌创作与文人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的诗论文,文人论文,生命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说,我们的世界正进入一个既多元化又一体化、既虚无化又感觉化的“去中心”(decentration)的真正世俗化时代。人们习惯用“后现代社会”(而不是“后工业社会”)来指称这种文化与生活既割裂脱节又水乳交融的矛盾状况,指称这种与已有的一切文化规范(现代的和前现代的)既巍然对峙又浑然包容的“反文化”的文化。在中国,这种与世界共通的后现代境遇,使现代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又多了一份“有中国特色的”不能承受之“重”,一种双重尴尬和焦虑:他们的双脚被捆缚在前现代化社会贫困的物质底座上,身体感受着现代的欲望与诱惑、荒诞与挣扎,头脑意识着被后现代文明消解重组的恐惧和痛苦,唯有心中对终极家园的浅唱低吟和浪漫呼唤,使他们与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养尊处优的现代主义同仁兼导师庶几近之。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而又忧虑的图景。
也许,一切正如流行套话所说,只在观念的改变。任洪渊教授的诗与诗学合集《女娲的语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让我们看到这种后现代转换的可能,及其积极的一面。他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对汉民族的神话、历史、语言以及文化智慧、生命体验等元素的解构和重构,让我们从喧嚣的后现代声浪中(浮躁、庞杂在所难免,因后现代从不作“庄严宝相、唯我独尊”态),依稀听到一种清晰稳健的足音。
我们把这种状况称之为“文人后现代”(文人后现代主义),以与前述的文人现代主义和后文将提及的“大众后现代”相区别。以此作为一种过渡性后现代现象的描述,但愿不至于引起误解。
中国的后现代批评家,曾用“后社会主义”、“后新时期”、“后文革后”〔1〕等概念,为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命名。 这些概念大都敏锐地把握了后现代主义试图超越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实质,有人干脆用“政治后现代”来概括、形容实际生活与艺术创作中这一越来越明显的倾向。任洪渊的后现代性,首先表现在他进一步超越了解构政治的政治情结,把以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和深度模式为核心的传统历史观,进行边缘化与平面化消解,以此作为从文化的重负下拯救生命的起点。作为一位中年学者和文人诗人,他痛切地意识到“历史是中国人生命沉陷的险区”,〔2〕以对历史的反叛和重构,表现出与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大众诗人)无视历史不同的后现代取向。创作于80年代中后期的长诗《女祸11象》和组诗《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不是我们从众多文人诗歌中习见的那种对民族神话与辉煌历史谱系的渺小的复写和改写,而是以卑微个体猛烈撞击历史、拆解历史的极具原创性力度与纯度的生命重写。借诗人自己的话说,是“作为一种文化去与以前和以后的全部文化抗衡”。〔3〕这与台湾现代派诗人洛夫,以一曲现代《长恨歌》颠覆白居易流传千古的帝王爱情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后者只是偶一为之,并且像众多现代主义者一样,最终皈依了传统。这使我们想到任洪渊谈及洛夫的“时间之伤”即“历史之伤”时的一段话:“历史,对于远离大陆的岛,可能是一种思乡的婉转的诗意;而对于大陆,则是一种再也承受不起的直接的重压。就是黄河,它那‘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激情冲决力,也已经消失在和它一样长的历史中”。〔4〕
既然历史曾给诗人如许的重压,既然诗人以“女祸的语言”命名他的诗论与诗歌集,我们不妨从神话历史观的内核切入“文人后现代”的中心话题,探讨文化与生命诗性转换的一面,并探寻诗人的文人性与后现代性在语言观和生命观的表现。
女祸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颉刚语)中,是一个“箭垛式”的神话人物,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制定婚俗,以至治洪水杀猛兽,在神话时代,她是一位以化身变形来创世的女性创世者(许慎《说文》称她为“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近年在陕西临潼发现蛙图腾彩陶图案,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女祸在新石器母系氏族时代的图腾原型)。〔5〕诗人彰显女祸这个已在“种族记忆”中“靠边站”的边缘形象, 意在重构她作为创世者、进化者和反抗者的原初性、个体性及精神性的一面。诗人再次把女祸作为“箭垛”,来放他的“文人后现代”之“矢”,不过他的“的”是让文人们不能释怀的文化与生命悲剧关系的沉重母题(也包括“文化使命感”问题)。
《女祸11象》包括上下两篇。在上篇的六象中,诗人首先展示了女祸作为世界的第一体验者和命名者,从“人首蛇身”这种象征状态(半人半兽是诸多民族的原始梦魇)的艰难诞生。“但是我拖着庞大兽身的头/是不自由的/爬行的肢体拖着我的思想/也贴着地面爬行”, 经过“一日七十化”的痛苦蜕变(实际上是千百万年进化历程的浓缩),人终于“让野兽的躯体死去”,并“与世界一同开始”。这是人从兽、文化从生命裂变生成的伟大起点。但这种裂变注定是不彻底的,本能与文化(人身与人首)的纠结和冲突与生俱来,于是,人有了“孤独”、“苦闷”、“焦渴”。为战胜绝望这种“致死的疾病”,女娲(亦即人)唯有不断地创造,命名,解答,“我用补了的天解答/ 我用黄土抟成的千万种生命形态解答/我用野兽的躯体上长出的人首/和人首下死去的野兽的躯体解答/我用我平分而成的他和她解答”, 目的在赋予无望的生存以希望和意义。这是人类磨砺生命和提炼文化的自然上升之路,人作为类和个体似乎都无法逃避。后现代主义者首先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们不象老子那样认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不像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自然主义者,在“回归自然”以至“回到母腹”的旗帜下呆得过久。后现代主义者的这份“平常心”,使他们在对待现代物质文明的态度方面,与现代主义者一味反“物化”、反“异化”的近乎神经质的纯粹否定大相径庭,他们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并享用了它。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是随波逐流的文化认同者,相反,“反文化”一直是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和生命源泉。只是后现代人没有弗洛伊德主义者的那份自信,他们同时意识到文化与生命及本能关系中宿命的一层。这正如诗人在《找回女祸的语言》中所说,“生命从反文化始,却一定以成为一种文化形式终。人不能不是一种文化形式——上升为文化的生命和转化为生命的文化。”这种生命与文化的混合,使后现代人的反文化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生命形态。《女娲11象》的下篇五象,呈现的正是人类生存的这样一种境况。诗人意识到,当文化定于一尊,凝聚为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巨大力量给人以庇护或威慑,个体生命的萎缩就成了一大问题。在这里,诗人把女娲神话作为神话母体加以泛化、重组,以断片化和零散化取代上篇的连续性,着重表现女娲和女娲的后裔们(刑天、后羿、嫦娥等)对禁锢生命的各种文化规范(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等等)的反抗,以及个体作为“永远抛出的人”,从语言形态、精神信仰到生存模式的渐次剥离。“无头的呼喊张开肚脐的嘴/ 命名,叫响万物”,刑天以“断头的身躯高高矗立”,算是象征性地完成了一次身对头,生命对文化的奇特征服。最末一象《无象之象:神,佛,人》对人的后现代境遇揭示得最为彻底,剥离了神和佛的人只能面对自己:“到底不能把头身躯四肢钉死成,十/为了天堂的地狱/为了复活的死亡/一生,向着自身回到开始/向外塌陷的空间/向前倒流的时间/退潮涨破黑色的,O/点,坟”。这种生存的O度状态, 是后现代人反文化的极致。相比之下,古典诗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空体验和孤独失落,现代诗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的执著于终极关怀的文化使命感和文化幻灭感,就显得既沉重又缺乏勇气了(刘毅然的小说《青春游戏》中“我觉得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里,我认为我自己是谁我就是谁”的后现代戏拟,正好与此形成有趣对照)。
面对神话和渗透着神话精神的历史观,后现代文人不惜花费偌大功夫去解构重构,恐怕不是“六经注我”的癖好使然,这里面其实大有文章。
19世纪末神话研究在西方成为显学以来,在科学的名义下,为神权与王权服务的传统神话观渐被剔除;以同样的名义,现代神话学的原理,也逐渐从人类学渗透到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神话的意义和功用,再次被神话般地无限夸大了,被当作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超时空的“原型”。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意象”等绝对理念式的概念,赢得满堂喝彩之余,甚至主张以神话拯救现代人类。〔6〕这种把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态的原始初民的逻辑,强加于高度社会化和个人化的现代人的思路,对现代主义诗学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到艾略特的《荒原》,现代诗完成了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的大循环。《荒原》是西方圣杯传说等神话原型的现代再版,艾略特对此供认不讳并引以为自豪,他强调诗人须“感觉到远古和现在同时并存”〔7〕的宿命历史观,被中国不少现代主义诗人奉为金科玉律。 从朦胧诗中客观派一支“呼唤史诗”和“远古梦想”的“文化诗”,到“新诗潮”中的整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中国远未发育的神话乃至传说成为诗人们文化寻根和重振传统的主要内容,甚至连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之类,也给诗人以原型的灵感和智慧的快乐。个人与世界被纳入各种森然可畏的黑格尔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系图式之中。现代诗人们对必然的认识,让我们感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沉重和无望。
然而,任洪渊对女娲神话的解读和解构,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他以深谙历史又反叛历史的文人式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神话的模拟和最后书写,以平面化的混合与包容,消解了文化与生命的二元对立,及必然性与决定论的深度模式的神话(包括拆解现象与本质、意识与潜意识等传统的或现代的深度模式),从而最终瓦解了神话与历史的神性依据和必然逻辑。诗人所要找回的“女娲的语言”,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玄想玄念,也不是某种神圣使命或终级关怀的“新的宗教”,而是一种比现象学还原更彻底、更纯净的原生存在状态,是剥离一切“整体化原则”的必然律和外在时空限制的“纯粹生命体验”。诗人断言:“空间化的时间和时间化的空间,空间的O度和时间的O度,可能是被无限的空间和无穷的时间抛弃的人,所能为自己建立的唯一的一个永恒的自由的家园”。〔8〕时间和空间由你开始由你结束,天国与地狱、此岸与彼岸、 毁灭与创造、沉沦与超越,都由此身历尽,都在今生走完,一生就是整个宇宙和全部历史,是创世,也是终古。这实际上已从外求的历史观,进入全新的内在化的时空观和生命观。个体化的诗性存在,已成为一种消除生命与文化的分界的生命状态或文化状态,这是生命与文化的诗性转换与融合。
后现代主义与以往的“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本质上是反理论(体系)、反独断论(主义)的,它主要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捍卫生活的个性权力的文化生命本能,用费耶阿本德的话说是“怎么都行”,用田壮壮、刘毅然们的话(电影《摇滚青年》)说是“怎么痛快怎么来”,它的生活化与世俗化,它的宽容性与个人性(有时也表现为“无我性”,这同样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在“大众后现代”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内在性,使它对外在环境的要求不至于过分苛刻,因此它并非工业或后工业社会的特产和专利。据此,弗·杰姆逊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化”的后现代理论。这牵涉到后现代文化的多元性与本土性问题。不少学者对汉斯·伯顿斯“从多种后现代主义走向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归“多”为“一”的观点〔9〕颇多非议。其实, 重要的不是阻止“多”走向“一”而是防止“多”走向坏的“一”。这是后现代文人以多元性和本土性相号召的真正用意之所在,它与捍卫生活的个性权力是并行不悖的。中国的“文人后现代”,其价值和功用也不外乎此。
这种多元性与本土性,使后现代主义共通的激进解构和反叛,带上了几分宽容,几分冷静。在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同时,中国的文人后现代主义对生命观和语言观的重构,表现出建设性和积极稳健的文化整合倾向,这使它更能投合中国人喜渐变重过渡的中庸心理,从而具有现实可行性。这里我们以《女娲的语言》中的其他几个组诗为例略加说明。
先说生命观。《东方智慧》和《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走的仍是让文人们铭心刻骨的“历史—文化”的轻车熟路,只是与传统的或现代的咏史诗和怀古诗已南辕北辙。诗不再是历史现象与文化灵魂的简单反映或表现,因其生命底蕴已成为“支撑历史的根基”。〔10〕具体而言,《东方智慧》避开当时流行的“寻根”与“掘根”的文化决定论视角,从本土文化潜在的精神内核——传统诗艺与“诗的意象结构”(如李商隐的夕阳、陶潜的菊、李贺的红雨……),切入人的诗性存在,以体悟洞见作为文化的“东方智慧”的生命本质,它那澄彻明净的“无时空体验”及其内在化的“生命时间”的内蕴和奥秘。《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是继司马迁之后对历史和“生命的历史形式”的再一次“创世”般的书写(“第二”乃相对女娲创世而言),是对传统的“宏大叙述”以及经典阐释与权威话语的挑战和反讽。诗人把《史记》中的历史边缘人物(聂政、孙膑、项羽、虞姬、褒姒等)推到历史的前台,以民间性和体验性重塑被主流社会损害和被主流话语侵蚀的个性化的生命形象,表达“生命因为残缺而完整”的反主流生命观。诗人“发现”与“重写”历史的目的,不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是试图为被文化抑制的生命及其历史形式提供某种释放的可能,以尝试从“文化—历史”和“知识—权力”等不乏惯性倾向和暴力遗迹的话语网络中突围。用诗史作比譬,诗人在宋诗的沉重外表下,蕴含唐诗自由不羁的灵魂。这是中国式文人后现代主义的沉重处(文人性)与轻松处(后现代性)。
“女娲的语言”的最后落脚点自然是语言,尤其是诗集中写作最晚的组诗《汉字,2000》,更是直接以“汉字”为标识,并成为针对母语本身的极富创意与魅力的母语文本,较充分地展示了后现代文人诗人语言观中的生命感的本土性。诗人意识到“诗是生命和语言最初和最后汇合的唯一存在”,并试图“让语言随生命还原”〔11〕。因此,诗人有意识地把古老的汉字和汉语置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把面向2000年与21世纪的当代汉语诗和汉语文学的困惑与焦虑、潜能与生机,和后现代的语言革命连为一体。这是整合了1917年白话对文言的现代语言革命及此后文言与白话、欧化与口语的长期对立的“后白话”对白话的革命。〔12〕诗人以一种质地坚固、形式纯粹、富于光泽与韧性、断裂与张力的诗化新语体,开掘汉字原始的语言力量与命名力量,挖掘着汉语在人文性、形象性、修辞性以及自由的语序、词性、时态等方面的巨大潜能(突出的诗篇如《石头的字红移成绯色的天空》、《太阳缩小种一粒莲子在水中开放火焰》、《词语击落词语第一次命名的新月》等)。诗人以独特的体验和声音,加入了世纪之交汉语“后白话”的“众声喧哗”与“多元对话”(应该指出,诗界与小说界的这种“后白话”的对话或独白,有些仅停留在语言层面,有些则从生命观、世界观到语言观均已后现代化,任洪渊属于后者)。同时,面对语言与“历史—文化”的纠结和相互渗透,面对语言对生命的“澄明与遮蔽”,诗人把“第二次找回女祸的语言——汉语言的自由和自由的汉语言”(《找回女娲的语言》结束语)作为自己更高的乃至最后的理想,这是破除“历史—文化”的必然性神话之后,生命对语言的又一次不无沉重的挑战。后现代文人承受着较后现代大众远为复杂的精神负荷和内心冲突(不过已剔除了现代主义者的偏执而“游戏规则”化)。过渡阶段前后的巨大落差与反差,需要他们用个人性和本土性去填补去平衡。他们对“女娲的语言”的最后执著,表明他们作为女娲的后裔和作为文人对历史与文化所自愿担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整合”角色。后现代的大众则走得更远。大众诗人们也曾倡导“诗到语言为止”(韩东语),但目的只是以此与语言之外的一切尤其是“历史—文化”一刀两段划清界限,他们对诗歌的口语化(现实感)、叙述化(反抒情)、寓言化(反意义)的提倡,导致诗歌的散文化和向极端行动艺术的滑行。文人后现代主义对诗在形式上的非诗化和精神上的神性化(从海德格尔到海子)的回避,反映出它与大众后现代主义和文人现代主义之间的距离和自身的独特追求。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心态、一种真正的“敞开”状态,是一种直面存在、自我担当的勇气和胸襟,是宽容与调侃、狂欢与沉醉、行动与抗争甚至游戏与妥协的矛盾混合。它是在解构必然性的基础上重构自我与自由的行动哲学和行动艺术。在中国,后现代主义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困扰。一是与现代主义崛起之初处境相似的真伪之辩。人们从环境出发的习惯思路使他们忽视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性及其于“义理”之外现实的具体存在。实际上,我们从余华、苏童、池莉、王朔、刘毅然以至王蒙的小说,从任洪渊、严力、韩东、廖亦武、于坚的诗歌,从高行健、王培公、牟森、孟京辉等的戏剧,从谭盾、崔健、窦唯、何勇甚至李春波的音乐,从徐冰、方力钧、吕胜中、王广义等的绘画,从张艺谋、田壮壮、陈凯歌、张元导演的电影,从申小龙、尹吉男、张颐武、陈晓明、孙津等的学术批评与研究……,都不难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文人的和大众的)在中国富于本土性和多元性的喧哗与骚动。后现代主义受到的另一个困扰是现代主义者有意无意的误解,将精神生活和人文价值神圣化的现代主义文人们,往往把后现代漫画化、低俗化、物质化,从而曲解了后现代文化宽容与多元的精神品格。
注释:
〔1〕参见《文艺争鸣》1992.6、《读书》1993.2、 《天津文学》1993.3、《作家》1993.8张颐武、孙津、陈晓明等的有关文章。
〔2〕〔4〕任洪渊《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悲剧》,见《诗魔之歌》,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182页。
〔3〕〔8〕〔11〕任洪渊《找回女娲的语言》,见《女娲的语言》,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93年版第11页、15页、20页。
〔5〕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355页;张自修《骊山女娲风俗及其渊源》,见《陕西民俗学研究资料》第一辑,1982。
〔6〕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见《心理学与文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
〔7〕托·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9〕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 见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同〔9〕第583页。
〔12〕有关后白话,可参见张颐武《在边缘处追索》,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9—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