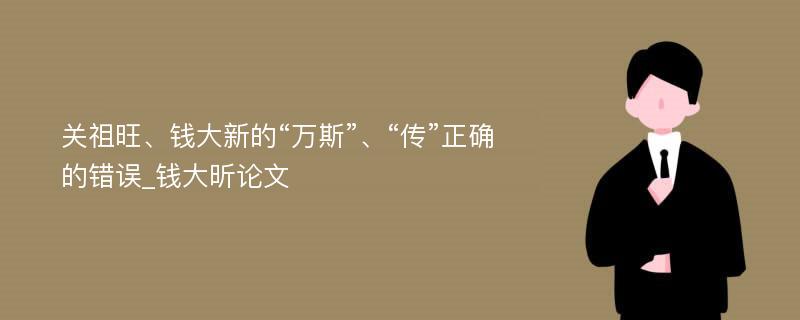
全祖望、钱大昕所著万斯同“传”纠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著论文,全祖望论文,钱大昕论文,纠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全祖望和钱大昕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各自所著的万斯同《传》,影响很大,然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全祖望所作《万贞文先生传》,对万氏在京修史时间及其修史的佚事,颇有失误。钱大昕的《万先生斯同传》,除对万氏卒年重复方苞之误外,文中所述万氏主立中史表的言论和建文帝自焚的书法问题,其实都是把王鸿绪《史例议》中的观点,误嫁于万斯同。由此可知,治史之难,治史必须慎之又慎。
关键词 万斯同 全祖望 钱大昕 传
我在与陈训慈先生合著《万斯同年谱》一书过程中,发现全祖望和钱大昕所撰万斯同的传记,多有失误。近年来又发现我们合撰之万《谱》错误之处亦不少,①因叹治史之难。愿以纠前贤之误,以勉自己,并祈海内外史家,纠本文及万《谱》之缪,是则为我写本文所期望的。
有关万斯同的墓志铭、行状、传记、主要有黄百家、刘坊、杨无咎、方苞、李塨、全祖望和钱大昕所著七种,为研究万氏的生平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其中后面三人,都著名于世,所以影响最大。方苞是著名文学家,缺少史家严谨精神,加上记忆力不好,其回忆之作往往有误,柴德赓先生的《万斯同之生卒年》一文已有辨正②。全祖望生活在雍乾之世,钱大昕生活在乾嘉之世,时离万斯同的逝世已有一段距离,他们或由于传闻失实,或由于文献失考,在他们各自撰写的万《传》中,也产生了若干错误,而以后者更甚。
全祖望所著名《万贞文先生传》,收于《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其收于《续甬上耆旧诗》卷七十八的,名《贞文先生万斯同》)。他的失误,主要有二处:
一,在京修史时间之误。他说:
先生自以故国世臣,不欲出仕,而有志于故国之史,故出而秉史局之笔者七年。
然而万斯同自康熙十八年(1679)至京修史,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京逝世,除其中二次南归故里约一年时间外,在京修史共二十二年,怎能说“秉笔七年”呢③?
二,修史事迹之误。他说:
故督师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馆于督师《传》少为宽假,先生历数其罪以告之。有运饷官以弃饷走道死,其孙以贿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
生于道光、咸丰、同治间的全祖望同乡陈康祺,在其所著《郎谮纪闻初笔》卷十二《万季野父子之狷介》中,受全氏的影响,而更予以发挥,他说:
故督师之姻人,方居要津,请先生少宽假,先生噤不答。有运饷官遇贼,走死山谷,其孙怀白金请附《忠主传》后,先生曰:“将陈寿我乎?”斥去之。后先生兄子言,与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故国相家子弟多以贿入,求减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其父子狷介如此。
其实,全祖望在《传》中所述的这件事,是万言的事,他把叔侄两人事混淆起来了。陈康祺或许看过全祖望的《传》,而又风闻万言撰《崇祯长编》而得罪权贵,因此以讹传讹,以讹增讹。万斯同卒后,他的另一们侄子,万斯大之子万经,在雍正时纂修《宁波府志》,在卷二十五的《儒林·万斯同》和卷二十六《文苑·万言》两《传》中,都没有提到全祖望所说的这件事。首先辨正此事的是全祖望的弟子蒋学镛,他根据刘坊的《万季野行状》,全祖望的《传》和万经《宁波府志》中的有关资料而作《万斯同传》,他删去了全祖望《传》中的这一段,而把这一内容移到《万言传》,在他所著《鄞志稿》卷十五《文苑下·万言》中说:
召修明史,独成《崇祯长编》一书,杨武陵(即督师杨嗣昌,湖南武陵人,崇祯十二年特旨任督师剿农民军)孙行贿于阁臣明珠,乞督师《传》少宽假,又有运饷官以弃饷走死,命附入死事之列,并力拒之,以此得罪当轴。后以教习期满知五河县,大吏承阁臣旨,文致之,论死。其子承勋遍贷诸有力者,得以赎免。
经过蒋学镛订正,此后宁波的地方志,都把此事归于万言,这样,导源于全祖望《传》的错误,终于得到纠正。
钱大昕所著名《万先生斯同传》,载于《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其取材多来源于方苞的《万季野墓表》和全祖望的《传》,而他自己所增加的部分则全误:
一,万斯同卒年之误。他说:
康熙壬午四月卒,年六十。
万斯同卒于康熙壬午四十一年四月,这是对的,然而,年六十则错了,柴德赓在《万斯同之生卒年》中已纠正了钱大昕之误,他还指出其错误所造成的影响:“自竹汀有季野卒年六十之语,后之作者,多循此误,如阮元《国史儒林·文苑传》、钱林《文献征存录》、李元度《先正事略》下至《清史稿》,皆云季野卒年六十。大师一言,不幸为众所奉行,每至如此。”④
二,万斯同论史表之误。他说:
马、班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机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入《记》、《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
这一段话,往往被视为万斯同主立史表的观点,但这段话在万氏所有著作中都找不到,却在王鸿绪《史例议》中找到了。王鸿绪说:
《史通》之论表也曰:“……而重列之《表》,成其烦费,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然有其人入《纪》,入《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纪》,未入《传》而牵连以《表》之者,是《表》所以通《纪》、《传》之穷也,庸可废乎⑤?
由此可知,钱大昕基本上采用王鸿绪《史例议》的内容。万斯同善于作表,上述这段话与万斯同提倡史表并不矛盾,但把这些内容引入万《传》,说是万斯同说的,那就失实了。
三,万斯同建文书法之误。关于建文书法有两种:一为“建文自焚”说,即燕兵入南京后,建文帝阖宫自焚而死;一为“建文逊国”说,即燕兵入南京后,建文帝离京出逃。钱大昕在万《传》中,说万斯同力主“建文自焚”,并说:“由是建文之书法遂定”。然而,他所引用的万氏的话,也基本上摘自王鸿绪的《史例议》,今把两人的原句摘录对比于下:
钱大昕
1,建文一朝无《实录》野史因有逊国出亡之说,后人多信之,先生直断之曰:“紫荆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
2,《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岂肯以皇后尸诳其主,而成祖亦竟不之察耶?况成祖清宫,中涓嫔御平日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拷,苟无已死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
3,若曰“逊”、曰“让”,则登极二、三年间,窜周王于蛮方,执齐王于京师,囚代王于大同,幽岷王于云南,专行削夺之谋,曾无宽假之诏。及至欲执戮燕王,以致称兵犯阙,为其逼迫自殒。厥躬即曰“出亡,”亦是势穷力尽,何“逊”何“让”之有?
王鸿绪
1,为逊国之说者曰:“……”,夫鬼门是何地?既无所考,……况紫荆城无水关,如何可出?
2,《成祖实录》称,建文阖宫自焚,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涓嫔御为建文所属意者,逐一毒拷,苟无自焚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之令耶?
3,且建文登极二、三年,削夺亲藩,曾无宽假,以致燕王称兵犯阙,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⑥?
看来,钱大昕不过把王鸿绪《史例议》中这三段话予以量增饰,不少地方简直原句照抄,从而把王鸿绪的建文书法,变成了万斯同的建文书法。
不过,是不是由于万斯同正如钱林所说的以布衣而“隐操总裁之柄”⑦,王鸿绪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作《史例议》呢?如果是,则是王鸿绪的书法,即万其同的书法,或许钱大昕正是这样考虑的。其实不然。《史例议》第十八条有“后熊文端公为监修,虽加删订,然造峻甚速”句。熊文端公即熊赐履,卒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文端”为其卒后谥号,而万斯同卒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这样《史例议》自然作于万斯同逝世以后了,王鸿绪不可能征求过万斯同的意见。不仅如此,《史例议》多次批驳由于明太祖曾奉韩林儿名号,“便当表林儿为君,明祖为臣”的书法,并责问:“则九江王(英布)之杀义帝(楚怀王),德庆候(廖永忠)之沈林儿,千古有同罪矣,明太祖其心服乎?”⑧他的观点,显然与万斯同《明乐府》第一首《沉瓜步》指摘廖永忠“弑主甘为贼”⑨的观点恰恰相反。更有甚者,他在《史例议》中还说:“然则今之为史者,远乏前贤之著述,近无耆旧之可征,加以才学浅陋,论断寡识,欲比拟古人万万不能。”⑩万斯同生前,他礼聘万氏到其馆邸,委以修史大权,一旦逝世,尸骨未寒,却大肆攻击他无才、无识,既掠人之美,又置人于学术上死地。但我们且不管他“心所阴蓄,不觉流于笔端”(11),《史例议》根本不可能出于万斯同之意,则可以肯定无疑了。所以钱大昕《传》中的建文书法,是王鸿绪本人的书法,与万斯同毫不相干。
然而,是不是万斯同本人也主张“建文自焚”的呢?也不是。万斯同在其《明乐府》第八首《火烧头》一诗的诗序中明确说:“燕王称兵犯阙,既入京,宫中火起,帝已潜身逸去。”诗中还有这样一段:
金川门开兵才入,乾清宫闭火已烧。
火烧头,真还假?
当年火裹尸若真,异日逊荒胡为者?
乃知天心终有存,难亡天下不亡身。
头白归来帝城死,眼看仇人已易孙。
君不见,
高皇寄食萧寺里,前为沙门后天子。
又不见,
嗣王行遁滇江滨,前为天子后沙门(12)。
明确宣称建文帝已假扮和尚逃亡了。《明乐府》第九首《下西洋》中也说:
人言让帝遁西极,此举意在穷其迹。
被褐已辞黄屋尊,泛舟宁作沧波客。
何妨尺地使容身,应念高皇共本根。
徒使狂涛填壮士,几曾穷岛遇王孙?
宿师海外馀十载,让帝行踪竟安在(13)?
显然万斯同是力主“逊国”说的。清咸丰同治间,万斯同同里人徐时栋,发觉了《明乐府》与钱大昕《传》中所说的矛盾,为了解“读者之惑,”他解释说:“盖先生(万斯同)少年以逊荒为真,既师梨洲,梨洲力辟之,先生亦遂变其初说。”(14)徐时栋错了,其错有二,我们翻开《黄宗羲全集》,其中没有一句提到黄氏是主张建文自焚的,此其一;说万斯同师事黄宗羲后才变其初衷的,这是他不了解《明乐府》写作时间所致。全祖望早已指出:“此(《明乐府》)乃先生少年时馆李杲堂(即李文胤)家作也。”(15)考万其同馆于李文胤家在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他三十七岁时(16),这一年,李文胤为他的诗集作《序》,其中说:“季野近与余约,拟取三百年朝延大事与士大夫风节有关名教及他轶事足传,每题以乐府一章。”(17)可知那一年《明乐府》尚未作,而黄宗羲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却在康熙七年(1668),比作:《明乐府》起码早六年。师梨洲在前,作《火烧头》在后,怎能说师梨洲后而变更其建文书法的初说呢?
现存天一阁的万斯同《明史稿》(18)在《郑和》传中说:“当是时,帝以兵戈取天下,心疑建文帝行遁海外,将踪迹之。”可知在他生平后期,万斯同和仍力主“建文逊国”说的。
1937年,孟森在《万季野先生明史稿辨诬》一文中已辨正了所谓万斯同力主“建文自焚”说之误,并指出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中关于万氏主张“自焚”说来源于王鸿绪《史例议》(19),但在钱大昕盛名之下,孟森的纠误并未为人所重视,甚至逐渐为人所遗忘。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在历史人物卒后,其生平事迹,几经岁月的流迁,被淡化,模糊而趋向湮没。故历史文献学,是史学的重要内容;强调信史,是史学的可贵精神;历史考证,是史学的必要方法。全祖望、钱大昕都是有清一代的史学大家,治史以缜密著称于世,全祖望提倡治史要“核其实”(20),钱大昕更是乾嘉历史考据学派贡献最大的史家。然而,他们尚且都不免失误,可知治史之难,治史之必须慎之又慎。
本文来稿日期:1994年5月25日
注释:
①陈训慈先生治史极其严谨,我看到他在已发表的《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旁,以蝇头小字,密密修改,这种自己纠自己之谬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我发现万《谱》之错误近十处,可补之处也有十余处。梁启超曾说:“明史长处,季野实尸其功;明史短处,季野不任其咎”,我也可以说:“万《谱》长处,训慈先生实尸其功:万《谱》短处,训慈先生不任其咎。”但愿在以后再版之机,我亦能纠自己之谬。
②柴德赓:《史学丛考》,中华书局1982年6月第一版,第244页。
③陈训慈、方祖猷:《万斯同年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7页和217页。
④《史学丛考》第245页。
⑤⑧⑩刘承干:《明史例案》卷二《王横云史例议上》。
⑥《明史例案》卷三《王横云史例议下》。
⑦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下《斯同》。
⑨《万季野先生明乐府·沉瓜步》。
(11)魏源:《古微堂集·书明史稿二》。
(12)《万季野先生明乐府·火烧头》。
(13)《万季野先生明乐府·下西洋》。
(14)(15)《万季野先生明乐府》卷首徐时栋《新刻万季野先生明乐府序》。(16)《万斯同年谱》第114页。
(16)《万斯同年谱》第114页。
(17)李文胤:《杲堂文续钞》卷一《万季野诗集序》。
(18)参阅方祖猷:《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清史研究》93.2。
(19)孟森:《万季野先生明史稿辨诬》,《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基墓纪念刊》,1936年宁波华升铅石刷局印,第八页。
(20)全祖望:《鲒奇亭集》卷三十五《辨大夫种非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