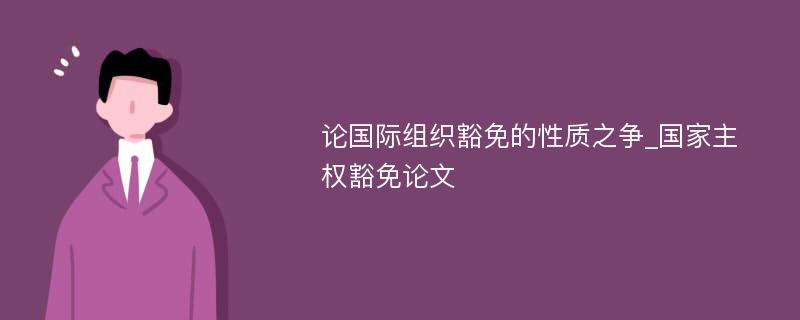
论国际组织豁免权的性质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豁免权论文,国际组织论文,之争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2)10-0151-06
长期以来,政府间国际组织(以下简称“国际组织”)享有特权与豁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组织的文件中,多边条约中,东道国协议,国内法以及国际习惯中,并且在各国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普遍承认。但是,随着国际法的新发展,国际社会出现了关于国际组织豁免权性质的理论之争。
一、产生原因
一般来讲,国际组织豁免于国内的各种司法程序,包括司法、行政和执行程序。传统上,“豁免于各种司法程序被认为是一种绝对豁免标准”①。在实践中,一般都认为只有给予国际组织绝对豁免或者接近绝对豁免才能保证(有关国家)的司法审查不会妨碍这些组织执行其职能。因为“与国家不同的是,由国际组织的职能形成的豁免权不能区分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因为后者同样可能属于国际组织的职能。”②因此,国内法院很少挑战国际组织的豁免权,他们多半倾向于“职能必要”等同于绝对豁免,一般不对国际组织行使管辖权。
二战后,国际组织数目和种类不断增加,国际组织活动也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与国际组织活动有关的争议也逐步增加。围绕着国际组织在内国的诉讼地位,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其实质主要表现在:国际组织在内国法院享有的是绝对豁免还是相对豁免,如何认识有关文件中的“弃权”条款,如何解决国际组织豁免权与人权保护的冲突等。在当今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对国际组织豁免权的质疑,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受到了国家主权豁免的发展影响。晚近时期,国家主权豁免权已经由绝对豁免转向相对豁免,这不仅体现在多数国家已经倾向于接受限制豁免,并且还体现在相关的国际条约中。2004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就确定了豁免规则,同时列举了多种例外。借鉴国家主权豁免的立法与实践,有学者提出应区分国际组织的行为,对其商业行为不应给予豁免。第二,保护人权的需要。现代国际人权法的发展要求国际组织应当实行“善治”,要承担超过其组织文件和内部管理程序的义务,要受一般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包括人权法的约束。因此,“在讨论国际组织管辖豁免时首先要考虑国际人权保护③”,对于国际组织造成的损害人权的行为,国际组织不应当享有豁免,而应给予救济。
二、限制豁免理论对国际组织豁免权的影响
在国际法上,限制豁免已经成为国家主权豁免的趋势。国家行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对国家的主权行为给予豁免,对非主权行为不给予豁免。但是对于国际组织而言,是否也像国家豁免一样,从绝对豁免走向了限制豁免,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有争议的问题。
(一)理论上的争议
在限制豁免理论对国际组织豁免权的影响上,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与做法,严格来讲,可以分成两大类观点,一类是通过对国家主权豁免内容的类比适用,对国际组织的商业行为不给予豁免;另一类则是通过对职能必要的限制解释来限制国际组织豁免权的适用范围。
第一类观点以美国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应将限制豁免的理论应用到国际组织豁免中,对国际组织的商业行为不给予豁免。他们通过探讨美国《国际组织豁免法》和《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关系,主张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内容对国际组织的豁免具有溯及力,因此应将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内容并入到《国际组织豁免法》的适用中,对国际组织的商业行为不给予豁免④。
二战后,为了履行有关国际公约与东道国协定的规定,一些国家专门制定了相应的国内法,明确规定国际组织在其内国法上的法律地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立法包括1945年的美国《国际组织豁免法》(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mmunities Act以下简称“IOIA”)。该法明确规定了美国为会员国的国际组织在美国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享有相应的特权与豁免。但是该法并未明确这种豁免的本质及范围。此外,该法中还规定国际组织“将享有同外国政府一样的管辖豁免和司法程序豁免,除非该组织在任何程序中或任何合同条条款中明示放弃豁免。”这就成为日后争议的缘由之一。
1976年美国通过了《外国主权豁免法》(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y Act,以下简称“FSIA”),该法案采用限制豁免的理论,在第1605条规定了一国可以接受管辖的情形,也就是说国家商业行为是例外,是不给予豁免的。所谓的商业行为,在第1603条第(d)款界定为“一个经常的商业行为过程或一个具体的商业交易或行为”,判断商业行为的标准是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目的。
就IOIA和FSIA关系而言,美国理论界和司法部门都在思考,IOIA中规定参照外国国家享有的豁免权,那么是仅仅参考立法时外国国家享有的主权豁免情况呢,还是要考虑外国国家主权豁免的变化与修改。如果参考1945年立法时的国家主权豁免的发展情况,则应认为绝对豁免,如果还要参考以后的发展情况,及1976年立法具有溯及力的话,则应认为是限制豁免。有学者认为尽管从FSIA的立法意图看还存在一定疑问,但是从立法相关的参考文件看,“当FSIA对外国豁免的态度发生变化时,对国际组织的豁免的程度也相应变化。因此,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最初享有的绝对豁免就不再适用了,而是由限制豁免原则取代。”⑤因此,这些学者们主张应当适用美国FSIA,对国际组织的商业行为不给予豁免⑥。之所以借用主权豁免理论,是因为职能必要保障了国际组织在实现其目的和宗旨时能独立于有关成员国的司法审查之外,但是给予国际组织超越其法定职能之外的绝对豁免就太宽泛了,因此,希望借助于FSIA达到一定的平衡。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FSIA不适用于国际组织,并且FSIA中也明确规定了国际协议例外条款,同时,该法案中关于商业行为的界定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从实践的操作来看,界定国际组织的商业行为存在一定难度。
另外一种做法以意大利法院为代表,通过对绝对豁免条款的保留,通过运用职能必要来解释国际组织的豁免权,“将绝对豁免转变成限制豁免”⑦。这种限制豁免近似职能豁免,即将主权行为等同于职能行为,对职能行为给予豁免,对非职能行为不给予豁免。针对国际组织为被告的案件,有些会选择通过对条约中的豁免条款进行限制解释,即通过限制司法权的范围来限制豁免,实际上采用了国家豁免中的限制豁免标准,尽管通常被认为适用的是绝对豁免。但是,严格来讲,这并不能称为限制豁免,因为所有的豁免都以条约为根据,对于条约所限制的,当然也是成员国自愿接受的,这不能等同于国家主权豁免中的限制豁免。
还有个别国家则是直接采用限制豁免的习惯标准,即在缺乏明示规则时则将国内主权豁免适用于国际组织,即根据一般国际法,对照国家豁免的原则,国际组织应当仅享有限制豁免。如E GmbH v.European Patent Organization⑧案中,奥地利最高法院将European Patent Organization的职能豁免视为原则上绝对在其职能限制的框架内。
(二)美国的司法实践
与理论上的探讨不同,美国国内法院在国际组织豁免问题上非常谨慎。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是给予国际组织绝对的豁免。
在Tuck v.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on⑨案中,涉及国际组织商业行为是否给予豁免。在该案中,原告就其与被告有关法律服务的协议起诉。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决,理由是被告对此类诉讼享有豁免权,并且法院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被告享有豁免权。法院认为其无权对照FISA的内容,来判定IOIA给予国际组织的是绝对豁免还是相对豁免。虽然原告主张被告在哥伦比亚特区内从事了商业性的租赁行为,这就等同于FISA中所说的“商业行为”。但是,法院认为,这种行为和被告缺乏联系,因此即使是根据不宽泛的限制豁免标准,法院也认为被告具有管辖豁免。因此,法院认为没有必要来决定是否应适用绝对豁免标准。
1980年的Broadbent v.Organizations of American States⑩案第一个解释了IOIA中国际组织豁免的范围。在该案中,原告是被告OAS的前员工,他们主张被告应对其错误的终止雇佣协议的行为给予损害赔偿。原告认为被告OAS不能就其商业行为享有豁免。被告OAS认为FISA中的限制豁免条款不适用于国际组织,因此被告OAS享有绝对豁免。法院回避了应适用哪一种豁免标准的问题,而是判决,即使根据FSIA中限制豁免的做法,被告OAS也应享有豁免,理由是雇佣行为并不是FSIA中所指的商业行为。法院从职能必要出发,认为国际组织在从事其职能行为时要免受国内政治的干预,如果涉及雇佣争议将卷入国际组织内部管理,这就会损害国际组织平稳运行。
Rendell-Speranze v.Nassim(11)案中第一次涉及了国际组织应当根据IOIA还是FSIA享受绝对豁免还是相对豁免的问题。该案也是一起关于雇佣合同的争议,在该案中,原告起诉其主管以及雇主——国际金融公司,要求就所声称的侮辱和殴打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法院在本案中要解决适用哪一种豁免标准。法院不认为这是一个内部行政管理事项因此享有豁免,相反,法院认为所指称的行为属于FISA第1605(a)(5)所指的事项,对私人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不能给予豁免。按照FSIA,IFC不能享有豁免,因此法院认为IOIA中“同样豁免”要并入FSIA在外国主权豁免上的变化。但是该案不久被Atkinson v.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2)案推翻。
美国法院在国际组织豁免权的问题上小心谨慎,通过两步分析法来判定国际组织是否享有豁免。首先是根据IOIA确定豁免的最低标准,即法院需要确定是否永久性的采用IOIA1945年制定时外国国家主权豁免规则,还是要并入以后的发展。对此,法院倾向于国际组织具有绝对豁免权。第二步分析是确定国际组织是否放弃了其根据IOIA享有的豁免权,这包括在特定案件中或合同中的特定放弃,也包括在基础文件或者总部协议中的一般放弃。即使已经放弃,法院也倾向于将弃权条款做狭义解释,仅适用于外部事项,对于诸如雇佣合同等事项都解释为内部事项从而排除弃权条款的适用,保证了国际组织职能的实现。
三、人权保护对职能必要的限制
不可否认,国际组织在人权保护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也不排除国际组织豁免权的存在会对人权保护产生影响。在实践中,如果个人在内国法院起诉国际组织,由于国际组织享有豁免权,这就意味着受害人在内国法院无法得到正当的法律救济,当事人权利无法得到救济。正如学者指出的,这种给予国际组织绝对豁免的做法,事实上使得当事人个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救济,违反了国际法和国内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否定了受害人对于政府提起诉讼的权利,侵犯了当事人寻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等(13)。
当事人有权得到正当救济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正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3条所规定的: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甲)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乙)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第2条规定,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所需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其他公约和国内立法中也有类似条款。国际组织尽管不是这些公约的缔约国,但是对于那些公约缔约国而言,在实践中,如果因为给予国际组织豁免而不能对当事人提供有效救济的话,被认为是违反了人权保护的义务。
在Mendaro v.World Bank案中,Susana Mendaro,在美国联邦法院根据美国1964年民事权利法案起诉其前雇主世界银行,一审法院以银行协议条款并未放弃国际组织豁免法所赋予的豁免权为由驳回其起诉。上诉法院维持原判,认为在法院协议中的弃权条款仅适用于世界银行的外部行为和合同,但是不适用于与雇员之间的内部行政管理事项。Atkinson v.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案虽然确认了国际组织的绝对豁免权,但也饱受诟病,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国内法院抛弃了绝对主权豁免,国际法中个人权利日益得到承认,根据国际法国家组织承担国际义务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对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国际组织要按照民主原则并要直接承担责任的公共例外原则,个人在对公共结构的争端中有权得到公众程序待遇这样的大背景下,该案的判决显然和国际法的发展与实践不相符(14)。
在Waite and Kennedy v.Germany(15)和Beer and Regan v.Germany(16)案中,原告方来是自英国、爱尔兰、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司的员工,在德国起诉要求按照德国劳动法,承认其是欧洲航天局的雇员地位。但德国法院根据公约的规定,以欧洲航天局享有豁免权为由驳回起诉。原告不服,又将案件提交到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审议了作为成员国的欧洲航天局授予豁免权是否不当的问题。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德国做法并没有违反公约第6(1)款,因为这是为了保证国际组织能不受个别国家干扰而适当的履行其职能。但欧洲人权法院也指出,如果各国建立国际组织以谋求或加强在某些领域的合作,而且将若干权限归属于这些组织并给予豁免权,可能会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产生影响。
四、对国际组织豁免权的再思考
(一)国际组织豁免权的理论基础
要将国家主权豁免类比适用于国际组织豁免,将限制豁免理论运用于国际组织豁免的实践中,首先要从国际组织豁免权的理论基础出发,分析这种类比的合理性。
职能必要理论是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基础,这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方便国际组织不受干扰地履行其职能,国际社会赋予了国际组织以法律人格,给予其特权与豁免,表现在《联合国宪章》第104条和第105条的规定(17)。《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则具体阐述了联合国人格和豁免,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18),又对国际组织享有的特权和豁免问题进行了较为明确和系统的界定,这两个条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成为以后国际组织制定相关公约的范本。在许多国际组织的基础文件或者有关特权与豁免的多边条约中,也都规定国际组织豁免于各种司法程序。“长期以来,国际社会都接受,国际组织需要东道国和成员国给予一定法律和实践独立性来保证其实现组织目标。”(19)在豁免问题上,当时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基本上是一个未知领域,考虑到当时限制豁免的理论尚未被国际社会接受,因此可以推论出国际组织享有的是绝对豁免。
无论是在其理论基础还是在立法与实践上,国际组织的豁免权,都与国家豁免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能将国家豁免等同于国际组织的豁免权。国家的豁免权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权平等,根据平等者间无管辖权这条古老的国际法原则,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已经成为一项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原则。但是对于国际组织而言,国际组织并不具有主权,因此不能援引主权平等原则来讨论国际组织的豁免权,它们豁免的基础是不同的(20),那些“立法者、法院和评论人试图将限制豁免原则适用于国际组织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21)。
(二)豁免的标准
国际上广泛接受职能必要是给予豁免权的基础,根据该理论,国际组织享有的豁免限于实现组织目标和宗旨的需要。因此给予国际组织何种豁免就取决于对职能必要理论的解释。
实践中,许多国际组织,包括那些其组织文件中规定其有可能在国内法院被诉的国际组织都坚持只有绝对豁免或者接近绝对豁免才能保证司法审查不妨碍他们实现其组织目标。在当今的国际实践中,职能必要被运用得非常弹性,并不完全是以行为的性质作为给予豁免的依据,也就是说并不区分一项行为是职能性的还是非职能性的行为,而是考虑该行为是否是该组织的运行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如果该组织在其职务之外行事,其仍然能依据职能必要理论享有豁免,因为若不给予豁免的话就可能影响其履行职能。这就意味着,法院必须在国际组织运作和其他法律原则与例外之间寻找到平衡。
即使在个别案件中,国内法院不给予该国际组织以豁免,也会适用国际组织的规则,而不是国内法,以免影响国际组织发挥职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荷兰法院1976年的Cf.Eckhardt v.EUROCONTROL案,比利时法院1986年的Devos v.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 and Bulgium案。
(三)豁免的放弃
实践中,一些国际组织在其章程,或者东道国协议或者某些合同中明示对某些事项放弃了豁免(22)。从国际法理论上讲就该条款下的内容,该国际组织不享有豁免。但是如何看待这些弃权条款,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国际组织豁免权的态度。
一般来讲,内国法院对国际组织的弃权条款都很谨慎,一般都做狭义解释。在1967年Lutcher S.A.Celulose e Papel v.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案中,美国法院拒绝进行狭义解释,并未给予涉案的中美洲发展银行以豁免。但是,该案后来被Mendaro v.World Bank案推翻。法院指出,国际法上国际组织为了实行其组织职能有权在成员国享有豁免已经得到了广泛承认,任何国际组织放弃豁免权的基本合理的出发点,法院认为都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其组织目标,正如银行放弃条款的目的是“让银行履行其职能”。法院认为允许债权人、债券持有人和其他类似人提起诉讼是为了银行债券市场化的必要性,而银行雇员对银行提起的劳工诉讼将置银行在其有业务的140多个国家的毁灭性的干扰下,并且任何国家的任何法院试图裁判国际民事服务人员的申诉将卷入那些国际组织的内部行政事项,对于职员规则和规定的不同解释将大大影响组织的有效履行其职能的能力。因此,法院认为对于国际组织的内部事项不能援引弃权条款。
在Ezcurra de Mann v.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案中,阿根廷一审法院认为其没有管辖权,因为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享有豁免权,只有其明示放弃后才能管辖,至于银行章程中的放弃条款“在银行设立了分支机构的国家境内,或在银行任命了一名代理人专门接受诉讼传票或通知,可向有充分司法权力的主管法院对银行提起诉讼”,上诉法院认为这不构成放弃豁免权,而是银行“可以或不能接受这种传票或通知”,并且一审法院中判决的指定一名代理并不足够建立管辖权,这名代理是被授权接收传票或者通知,而不是接受。在African Reinsurance Corporation v.Abate Fantaye案中,东道国协议允许一般事项可以起诉该组织,但是尼日利亚法院认为根据其国内法不构成明示的弃权。有时,法院也用类比的方法给予国际组织豁免。在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efrigeration v.Elaim案中,东道国协议中仅给予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efrigeration执行豁免,并未提到管辖豁免。但是法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以该组织为被告的雇佣诉讼,因为可以从该组织的员工享有的基于条约的管辖豁免中推论出该组织也享有管辖豁免。
(四)完善国际组织内部争议机制
国际组织豁免权的存在事实上阻止了当事人在内国法院起诉,从保护人权的角度看,应当存在一定的救济机制来保护个人的权利。在实践中,多数国际组织内部都设立了争端解决机制,如行政法庭或雇员管理咨询联合机构等来解决争议。这些机构处理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劳工纠纷,到个人损害,甚至性骚扰等案件,尽管从实践的运作看,无论是机构的独立性,还是工作程序、决定公开性等都无法完全满足法律上的正当程序条款的要求,但是可以通过成立独立的仲裁机构,或者在这些机构进行改革,增强纠纷解决机制的独立性、透明度,加强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同时有学者(20)提出的将职能豁免作为有效抗辩的依据,而不是法律上绝对不受理案件的依据也具有一定合理性,这样就能给予原告在法庭上充分申诉的机会。
与国家相比,虽然国际组织涉及豁免权的案例不多,但是考虑到国际组织的数目和作用在增强,因此对于国际组织豁免权的重新考量就具有时代意义。尽管无论是从国际组织豁免权的法律基础看,还是从各国国内法院的实践看,一般都认为国际组织享有的是类似于绝对豁免的豁免权。但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对国际组织豁免权有所限制,无论是立法的方式还是司法的方式,有必要将国际组织豁免限制在职能必要的范围内,既不影响国际组织的有效运作,干扰其正常的内部管理,也能促进国际组织承担更多的责任。
注释:
①August Reinisch: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efore National Cou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57.
②沃尔夫冈·格拉夫·魏智通主编:《国际法》,吴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页。
③Michael Singer,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Human Rights and Functional Necessity Concerns,36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3,Fall,1995,p162.
④Stecen Herz,〈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U.S.Courts:Reconsidering the Anachronism of Absolute Immunity〉,31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2008,p532.
⑤Kevin M.Whiteley,Hold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countable Under the 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Civil Actions Against the United Nations for Non-Commercial Torts,7 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619,p638.
⑥Stecen Herz,〈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U.S.Courts:Reconsidering the Anachronism of Absolute Immunity〉,31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2008,p532.
⑦August Reinisch: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efore National Cour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89.
⑧Austrian Supreme Court,11 June 1992.
⑨668 F.2d 547(D.C.Cir.,November 13,1981 ).也可参考Decis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mmunities Act-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restrictive immunity-commercial activity,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76,July,1982,p623-624.
⑩156 F.3d1335( D.C.Cir.1980).
(11)932 F.Supp.19(D.D.C.1996)
(12)F.3d 1335(D.C.Cir 1998).
(13)Greta L.Rios and Edward ZPZ.Flaherty,16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433,Winter,2010,p5-p8.
(14)Stecen Herz,〈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U.S.Courts:Reconsidering the Anachronism of Absolute Immunity〉,31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2008.
(15)转引自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Sixth edition,白桂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4页。
(16)Application No.28934/945,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Feb.18.
(17)《联合国宪章》第104条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执行其职务及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联合国宪章》第105条第一项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第105条第2项中规定“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和本组织之职员,亦应同样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18)《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第4节,《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第3节都规定:“专门机构,其财产和资产,不论位置何处,亦不论由何人执管,对于各种方式的法律程序,应享有豁免。”
(19)Kunz,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41 Am.Int'l L.(1947),p836.
(20)Rosalyn Higgins,Problems and Process:International Law and How We Use It,1994,p93.
(21)Michael Singer,Jurisdictional I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Human Rights and Functional Necessity Concerns,36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3,Fall,1995,p62.
(22)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中都规定了特权与豁免,典型的条款如:当该公司作为一个商业实体履行自己的职能时,“只有在银行或公司设有办事处,指定可收受传票或诉讼通知书的代理机构,或业已在该地发行或担保证券的会员国境内有权受理的法院,才能受理对银行或公司提出的诉讼。但成员国或者代表成员的或其索求权源于成员国的个人,不得提出诉讼。银行或公司的资产和财产,不论在何处为何人所保管,在对银行或者公司的终审判决作出之前,均免受任何形式的扣押、查封和执行”。美洲发展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章程,亚洲发展银行等也有类似的内容。
(23)Lutcher是一家巴西公司,也是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借款人,起诉银行不得向其竞争对手发放贷款。Lutcher主张,如果银行给竞争者贷款的话,Lutcher可能就无法偿还贷款,这样银行就违反了其勤勉行事的义务。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则抗辩无论是根据《国际组织法》还是其组织章程,其享有管辖豁免。法院驳回了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主张,指出银行已经在其成立文件中放弃了豁免。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主张法院应当对弃权条款做狭义解释,仅应在涉及加强组织的效率的案件中适用,例如由债券持有人,债权人以及受益人的担保人提起的诉讼。但法院以四点理由驳回。
(24)Greta L.Rios and Edward P.Flaherty,Legal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Challenges and Refor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form or Immunity? Immunity is the Problem,16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winter,2010,p452.
标签:国家主权豁免论文; 豁免权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组织职能论文; 国际法论文; 银行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国家主权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