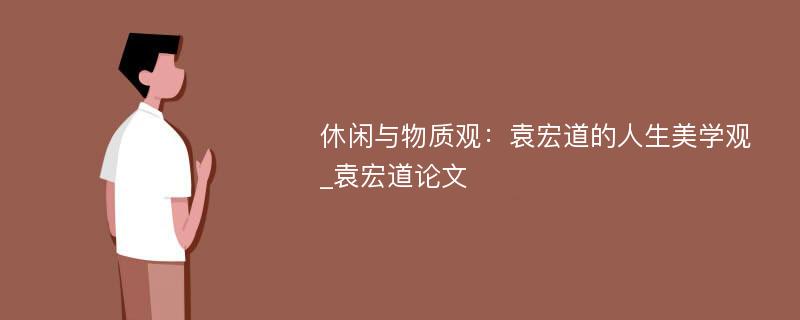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闲适论文,人生观论文,袁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4)02-0117-06
一、“闲适人生”的精神溯源
袁宏道的一生,仅有43载春秋。他少年聪慧,擅长诗文,24岁(1592)中进士,27岁(1595)谒选为吴县(今苏州)知县。他自27岁始,到他43岁病逝,三度出任朝廷命官,三度辞官,做官的累积年限不超过7年。他三度做官,都做得很好。袁宏道在吴县为官一年余,即令吴县大治,展示了难得的治理才能,时任首辅申时行称赞他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深得民心拥戴,辞官将离吴县时,吴县百姓闻知他因庶祖母詹姑病危辞官,“吴民闻其去,骇叫狂走,凡有神佛处皆悬幡点灯建醮,乞减吴民百万人之算,为詹姑延十年寿。以留仁明父母。其得人心如此”[1]。但他的人生志趣,实在不在于做官。他说:“世间第一等便宜事,真无过闲适者。白、苏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2]这是他在《识伯修遗墨后》一文中所说的话,可视作是他倡导闲适人生的口号。撰此文时,1604年,袁宗道已去世四年,袁宏道在公安柳浪乡居亦四年。
“闲适”的精神宗师,当上推到庄子。庄子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逍遥无为”“无所可用”,这就是闲适精神的要义。但庄子并没有用“闲适”一词,白居易大概是后世文人中首倡“闲适”者。他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闲适诗”即其中一类。他说:
仆数月来检讨囊袠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芙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3]。
白居易在这里对“闲适诗”的定义,实际上也是对“闲适”本身的定义。“退公独处”“移病闲居”,是就“闲适”的境况而言——“闲”;“知足保和,吟玩情性”,是指出了“闲适”的精神意态——“适”。若要达成“闲适”,就境遇而言,须是“闲”;就精神而言,须是“适”。白氏还指出了“闲适”的审美风格:“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同上)“思淡而词迂”,即指“闲适”是以吟赏玩味为主旨的,因此,用思轻淡,词调舒缓。
白居易主张闲适,自谓是以古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为导向。他说:“仆虽不肖,当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终始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4]白氏以美刺干政的“讽喻诗”为“兼济之志”,以吟玩情性的“闲适诗”为“独善之意”,他将“闲适”的“个人”取向揭示得非常清楚。他写《与元九书》正值被贬官江州(今九江),做闲官“司马”,实属“寂兮寥兮,奉身而退”的“穷时”。他以“知足保和,吟玩情性”为“适”,自然是“独善之意”。苏东坡引白居易为先朝同道,他为官一生,屡遭贬放,晚年被贬黄州,作诗推崇白居易说:“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在诗末他还自述说:“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轼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5]
袁宏道倡导闲适人生,以白居易、苏东坡为旗帜。袁宏道与白、苏略有差异的是,他不是在被贬处闲的境遇,即“穷”中,而是在初获授官的新官任上,即“达”时求闲适。袁宏道1595年,即中进士后四年,才得选授吴江(今苏州)县令一职。然而,正是这位勤政亲民的袁宏道县令,一方面励精图治,政绩斐然,把官做得上下都认可,另一方面却不断写辞职书,上任不到两年,连续上书七封请辞书,上峰无奈,只好准辞。他在任上,反复修书亲友,倾述为官的苦衷。在1595年的书信《龚惟长先生》中,袁宏道说:
“无官一身轻”,斯语诚然。甥自领吴令来,如披千重铁甲,不知县官之束缚人,何以如此。不离烦恼而证解脱,此乃古先生诳语。甥宦味真觉无十分之一,人生几日耳,而以没来由之苦,易吾无穷之乐哉!计欲来岁乞休,割断藕丝,作世间大自在人,无论知县不作,即教官亦不愿作矣。实境实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语相诳。直是烦苦无聊,觉乌纱可厌恶之甚,不得不从此一途耳。不知尊何以救我?[6]
正是在这为官的“如披千重铁甲”的大束缚中,袁宏道生起追求闲适、做“大自在人”的志意。
在1595年致徐汉明的信中,袁宏道把“学道之人”分为四种(玩世者,出世者,谐世者,适世者),他最认同向往的是“适世者”。他说:
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荘周、列御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几千裁,数人而已,已矣,不可复得矣。出世者,达磨、马祖、临济、德山之属皆是。其人一瞻一视,皆具锋刃,以狼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虽孤寂,志亦可取。谐世者,司寇以后一派措大,立定脚跟,讲道德仁义者是也。学问亦切近人情,但粘带处多,不能迥脱蹊径之外,所以用世有余,超乘不足。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除此之外,有种浮泛不切,依凭古人之式樣,取润贤圣之余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为此乃孔门之优孟,衣冠之盗贼,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7]。
“玩世者”即庄子所代表的道家高人,袁宏道以为是现世不可再有的了;“出世者”即禅宗祖师达磨所代表的佛禅宗师,“以狼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是袁宏道难以认同的;“谐世者”即孔子(司寇)所代表的儒家,袁宏道认为“用世有余,超乘不足”。“适世者”,无德无能,无为无志,“甚奇,然亦甚可恨”,“最天下不紧要人”,而袁宏道却最赞赏认同这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白、苏为“闲适”的旗帜,袁宏道心目中的闲适人,却并非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白、苏之辈志士仁人为原型,而是“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的“最天下不紧要人”。“做不紧要人”是身为官情所缚的袁宏道意想中的“大自在人”——闲适者。
还是1595年,身为吴江县令的文人袁宏道,在致舅父龚惟长的另一封信中,提出了“人生五乐”。他说:
年闲散甚,惹一场忙在后。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电光泡影,后岁知几何时?而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名虽作官,实当官耳。尊家道隆崇,百无一阙,岁月如花,乐何可言。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竞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古来圣贤,公孙朝穆、谢安、孙玚辈,皆信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与东邻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异哉?[8]
袁宏道所谓“人生真乐五种”,一为声色玩赏之乐,二为宾客欢宴之乐,三为高朋雅聚之乐,四为风流冶游之乐,五为乐极而穷之乐。这五种“真乐”,前四种均是以富贵打底,穷奢极欲之乐,而其乐的终究便是“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袁宏道以这个“乐极而穷”为人生真乐五种之最,实有大寓意的。大概而言,其寓意有二:其一,富贵之乐,并非可靠之乐,依仗富贵而乐,总不免穷极而终;其二,人生真乐之至,恰是穷极之际,“恬不知耻”“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做“最世间不紧要人”。袁宏道论的“五乐论”,是含有深刻的反讽和自嘲意味的,不可作字面理解。1595年的袁宏道,一方面是深感官场缚执而解脱不得,一方面又确有一腔新政利民的抱负欲展。他向亲友申明要做“最世间不紧要人”,实在因为他正在做、而且也愿意做“世间紧要人”。他的苦恼无奈是,“紧要人”做得不自在,而自在的“不紧要人”又做不了。在1596年的《李子髯》一信中,袁宏道提出“作诗”为“人生之寄”的观点。他说:
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可怜,可怜!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9]。
其实,袁宏道提出人生真乐五种之说,荒诞反讽之外,何尝又不是于现实缚执中对人生大解脱的“寄兴”呢?后世学者以此五说批评袁宏道贪图声色享乐,实在冤枉了袁宏道。
二、为官与归隐的两难
1597年,袁宏道获解官之后,携友人往江浙一带游赏,“走吴、越,访故人陶周望诸公,同览西湖、天目之胜,观五泄瀑布,登黄山、齐云,恋恋烟岚,如饥渴之于饮食。时心闲意逸,人境皆绝”[10]。这期间的袁宏道,的确度过了他一生中短暂(约一年)的“最不紧要人”的闲适生活。
袁宏道本是极敏感多情于色相之人。在解官前,以县令之身视察当地灾情时,他游览灵岩,写出的是这样令人欷歔的文字:
石上有西施履迹,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动。碧繶缃钩,宛然石发中,虽复铁石作肝,能不魂销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嗟乎,山河绵邈,粉黛若新。椒华沉彩,竟虚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谁作双鸾之雾?既已化为灰尘白杨青草矣。百世之后,幽人逸士犹伤心寂寞之香趺,断肠虚无之画屧,矧夫看花长洲之苑,拥翠白玉之床者,其情景当何如哉?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11]
但是,在解官后的“心闲意逸”之际,袁宏道的游记所表现的确是“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的意绪。举《雨后游六桥记》为例:
寒食雨后,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12]。
这是很典型的被后世称为袁宏道“性灵小品”的文章。文字简略而又极为细致,写景状物、叙事抒情,真是“思淡词迂”:感觉主导了思绪,声色落于文字,不是浓墨重彩的触目惊心,而是云淡风轻的生趣悦人。这篇短小的游记比之于唐宋柳宗元、苏东坡诸大家的游记,你会感觉它只是一幅简笔小景,尺幅局促而无远景可观。但是,袁宏道笔下文字,却又是这样独特的“简笔”:字字贴切,而又字字空灵,看似无心涂写的笔触,却又笔笔触景追心。袁中道称袁宏道此间文字“人境皆绝”,所言极是。只是须要解说的是,这“人境皆绝”,也就是人境合一、心物不二的生动气象。
然而,即使在这“心闲意逸”的“闲适人生”中,袁宏道的感触体悟也并非一味地驻留于花香月媚。他游会稽(今绍兴),写《兰亭记》,为王羲之《兰亭序》引发如此感慨:
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故或登高临水,悲陵古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电之易逝。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羲之《兰亭记》,于死生之际,感叹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昭明《文选》独遗此篇,而后世学语之流,遂致疑于“丝竹管弦”“天朗气清”之语,此等俱无关文理,不知于文何病?昭明,文人之腐者,观其以《闲情赋》为白璧微瑕,其陋可知[13]。
“虽当快心适志之时,常若有一段隐忧埋伏胸中,世间功名富贵举不足以消其牢骚不平之气。”这样的说法,写于袁宏道“快心适志”之时,自然不是泛泛而论,他埋伏在胸中的“隐忧”和难以消解的“牢骚不平之气”,实际上总不免以他的“闲适”的作派和诗文表现出来。
1598年,解官一年多的袁宏道,在家兄袁宗道的劝导下,赴北京候补,授顺天府教授职,至1600年,官升至礼部仪制主事。然而,这时的袁宏道似乎更有闲情逸趣于花鸟虫鱼和种种天地色相。只不过,他的《瓶史引》道出了其胸中的“隐忧”和“牢骚不平之气”。该文说: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让人,而人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嗟夫,此隐者之事,决烈丈夫之所为,余生平企羡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隐见之间,世间可趋可争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而邸居湫隘,迁徙无常,不得已乃以胆瓶贮花,随时插换。京师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为余案头物,无扦剔浇顿之苦,而有味赏之乐,取者不贪,遇者不争,是可述也。噫,此暂时快心事也,无狃以为常,而忘山水之大乐,石公记之[14]。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袁宏道指出幽人韵士屏绝声色,钟情山水花竹,实为“不得不”,其意图不过是为了“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山水花竹非世人争逐乐受之物,占据它们无争夺之忧,不会惹祸。在《瓶史》中,他纤毫毕致地描绘瓶中养花插花的技巧、程序,体贴万分地描绘瓶花的姿容风韵,影映的是他如此独特的境遇:“幸而身居隐见之间,世间可趋可争者既不到,余遂欲欹笠高岩,濯缨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这样的“闲适”,若以为“独善”,自然是有很深刻的“不得不”的委屈迁就的①。
袁宏道在诗文中倡导、讴歌闲适,要求大解脱、做最不要紧人。然而,真从官情世道中解脱出来,做了“闲适人”,时间久长了,他又不禁眷恋市井,怀念世众。他1601年初居柳浪不久,给友人陶周望的信称“山居颇自在”,“闲适之时,间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无复遁处”,而且体会到过往“只以精猛为工课”之误,学道之要是以“冷淡人情”的“任运”为工课[15]。然而,不过六年,1606年再致信陶周望却说:
山居久不见异人,思旧游如岁。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语;雪齿娟眉,能为人语,而不能解人意。盘桓未久,厌离已生。唯良友朋,愈久愈密。李龙湖以友为性命,真不虚也[16]。
与这封信相呼应的是他1604年的组诗《甲辰初度》之一:“闲花闲石伴疎慵,镜扫湖光屋几重。劝我为官知未稳,便令遗世亦难从。乐天可学无杨柳,元亮差同有菊松。一盏春芽融雪水,坐听游衲数青峰。”[17]袁宏道是二度称病辞官之后,在柳浪山居,但隐居久了,他体会到的是人情冷暖、市井繁寂,非可以山风水月、花木鸟鱼替代。对于他,入世为官不妥当,但遗世独立也难持久。正因为不能真正忘怀世故人情,山居的闲适就有“不得不”为之的自我放逐的无奈与苦涩。“一盏春芽融雪水,坐听游衲数青峰。”这看冰雪消融、春芽吐翠的闲适者,比之于那寂寞游走于青峰间的僧人,是加倍的寂寞和“不紧要”的。因为他并不真正安心于这寂寞和“不紧要”。
三、“闲适”的美学遗产
1606年,袁宏道结束柳浪山居,赴北京任吏部郎官。他这次做官约两年,同样勤勉为政,出使陕西主持乡试(典试秦中),也是革故鼎新。但终了,1608年他依然以病请辞。归乡游途中,他撰写《游苏门山百泉记》,说道:“举世皆以为无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谓溺。”但是,他又说“溺”只是以“常情”论为“至怪”,以“通人”看却是“人情”。关于自己,他说:
百泉盖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绿,目夺焉。日晃晃而烁也,雨霏霏而细也,草摇摇而碧也,吾神酣焉。吾于声色非能忘情者,当其与泉相值,吾嗜好忽尽,人间妖韶,不能易吾一盻也。嗜酒者不可与见桑落也,嗜色者不可与见嫱、施也,嗜山水者不可与见神区奥宅也。宋之康节,盖异世而同感者,虽风规稍异,其于弃人间事,以山水为殉,一也。或曰:“投之水不怒,出而更笑,毋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贵者,汩没尘沙,受人间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而更谀,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曰:“子之于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谓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极者也,余庸人也。”[18]
这篇游记,写于1609年,是袁宏道以43岁辞世前的一年。他称自己对于山水闲逸之情“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极”,即“有嗜而不溺”,承认自己实为“庸人”而非“通人”。这其实是他自己一生性情的自白。他的情性本是热爱自由、向往自然的,但是他又不能如李贽一般“捐性命以殉”,家国亲朋,都是他终其一身牵扯不舍的情结。“劝我为官知未稳,便令遗世亦难从”,这是袁宏道人生根本的性情纠结,他的矛盾在于此,他的深刻生趣也在于此。他三度入仕,三度致仕,无去无归,死而后已。1598年以后的袁宏道,呕心沥血要寻求“安于常人”的“平易质实”,极而言之,要寻得庄子式的逍遥。“惟能安人虫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与大小争,斯无往而不逍遥矣。”[19]然而,正如甘于做泥涂之龟的庄子心怀的却是高山真人之志,而袁宏道不仅不能安于人虫之分,甚至于真做“不紧要”的“常人”,也是不得安心的。因此,他之求闲适,实在是因为背面有为天下的大志不甘。就此而言,“闲适人生”确实是“兼济天下”的文人士夫的另一个面目,这面目展现为美学,是对功利人生的补充超越——它以超功利的闲情逸致灌注于人生自由灵动,它本质上是一种由我及物、由物及心的“达”——达至人生于世的自然自在。袁宏道畅舒性灵而求闲适,人生意义就在于此。
袁宏道的“闲适人生”,以其撰写的小品文为体裁,造就了一种亲切、鲜活、即物即我的审美情趣及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既非审美的静观,也非由我及物的移情,而是在我与物相遇的当下,我的生命舒张,感官与物象自然沟通,在身心调适中,我的眼耳手足肌肤与物象一同朗然于天地光景中。我们且看袁宏道《瓶史》写“浴花”一则:
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浴花者得其候,乃为膏雨。澹云薄日,夕阳佳月,花之晓也;狂号连雨,烈焰浓寒,花之夕也。唇檀烘目,媚体藏风,花之喜也。晕酣神敛,烟色迷离,花之愁也。欹枝困槛,如不胜风,花之梦也;嫣然流盻,光华溢目,花之醒也。晓则空亭大厦,昏则曲房奥室,愁则屏气危坐,喜则欢呼调笑,梦则垂簾下帷,醒则分膏理泽,所以悦其性情,时其起居也。浴晓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夕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细微浇注,如微雨解酲,清露润甲。不可以手触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隐士,浴海棠宜韵致客,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妙女,浴榴宜艳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儿,浴莲宜娇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腊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当以轻绡护之。标格既称,神彩自发,花之性命可延,宁独滋其光润也哉?[20]
这则在《瓶史》中标题为“洗沐”的文章,全文更长。在常人看来,如此说道“洗花”,实在神乎其神,小题大作了。然则,袁宏道视花为物,非视之为无情性之植物,而如视人一般,同以“性灵”视之。花既有“性灵”,爱花赏花者,自然当以“性灵”的立场与之相待遇。袁宏道主张“悦其性情,时其起居”,不仅是主张依循花的生物节律伺养之,而且主张尊重花的个性,不同性情的花当由具有相应性情的人来伺养。袁宏道虽然在这里用了指述人的行为情态的“梦”“醒”“愁”“喜”等词语指述花的生活,但意不在将花拟人化,而是主张“性情”本来是天下万物与人类共有的,不能以“性情”待物者,绝不可得物之生趣也。“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21]赏花本为“求雅”,而不懂花的性情,不能以性情待之,反成恶俗。袁宏道由此开拓的审美空间,可以称为一个以“性情”为核心,由我生物,由物悦情的生命空间。
袁宏道的闲适小品,发之于物我并生的性情,落实于市井人生,更酿造出在天地景物风致中看人生、赏玩人情世故的审美意绪。他的西湖纪游诸篇,都是这样的“闲适”小品。比如《西湖二》: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传金吾园中梅,张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22]
西湖纪游,本当以西湖景致为对象,以其变迁风韵为主题。而袁宏道笔墨敷衍出来的,却是风物中的人间性情,褒贬抑扬,不脱山水晨昏之灵气,但更渲染出意味醇厚的人情世态。这样的以景托人、借景写人的文学趣味,虽不可说是袁宏道孤心独发,但却是他将之推广提升到中兴之景。明清之际张岱的游记小品,实深得袁宏道真传。比如张氏的《西湖七月半》,无疑有很重的袁宏道《西湖》组文的印迹。兹录《西湖七月半》上半部分如下: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皷,我冠盛筵,灯火优傒,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喧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23]。
收稿日期:2013-12-01
注释:
①阿英说:“《瓶花斋》一集,表现了中郎对时局最复杂的苦闷,也说明了他自己内心冲突最激烈的过程。此集作时,他正在京师,小人当道,正义难伸,倭议纷纷,时局严重……他目击种种的失败,愤慨达于极点……他拼命的压抑自己愤怒的感情,想发展他的‘嘿’之哲学,把自己对‘时事’的注意力,牵扯到许多琐碎的事情上。”(阿英《袁中郎全集序》),载《袁宏道集笺校》,第1763页)。
标签:袁宏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