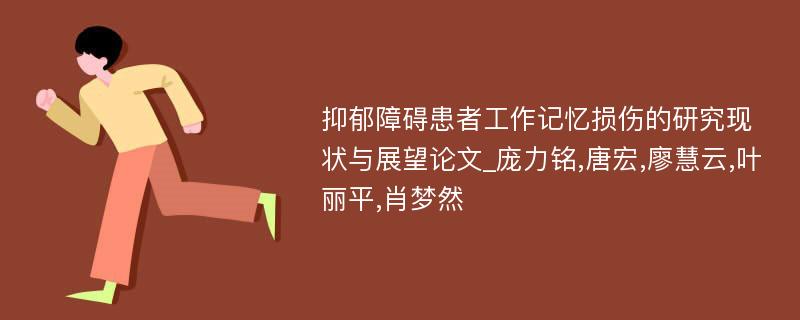
【摘要】抑郁障碍患者除了情绪低落意志消沉,还伴有认知功能损害,而工作记忆是高级认知功能的核心。但是治疗上,医疗工作者往往会忽视后者,导致患者即使“治愈”后,仍残留认知功能的损害。本文就抑郁障碍患者的工作记忆损伤近十年的研究现状作一综述。
【关键词】抑郁障碍;工作记忆;认知功能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9)04-0002-01
抑郁障碍是以情绪或心境低落为主要表现的一组疾病的总称,不仅具有高复发率和高自杀率的特点,而且伴有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尤其体现在注意和记忆受损上。在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往往只关注情绪和意志方面的好转情况,忽略认知功能恢复,因为工作记忆是人类高级认知活动的核心,是学习和工作以及适应生活的基础。当患者“治愈”后由于认知功能受损,其真正回归社会还是会造成一定困难。
1.工作记忆与抑郁障碍的关系
工作记忆是同时对信息进行暂时存储与加工的容量有限的系统,修正后的工作记忆模型包括四个子成分:语音环路、视空间模板、情景缓冲器和中央执行系统[1],该模型强调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之间的联系以及各子系统信息整合的加工过程。总的来说,工作记忆对于人们的学习、推理、创造力等高级认知起重要作用,是人类高级认知活动的核心,它对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以及病情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内有学者认为抑郁障碍患者情绪加工脑区过度激活与认知控制脑区功能降低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恶性循环可能是抑郁障碍产生的原因之一。国外有学者提出对负性信息的加工偏向对抑郁障碍形成与复发起决定作用[2],其中包括记忆负性偏向。抑郁障碍患者容易被负性信息或情绪占用资源,并主要表现为工作记忆能力的损害。认知控制受损模型认为,抑郁障碍患者在限制无关负性信息进入工作记忆上有困难,从工作记忆中移除负性内容用时更长,该模型假设,这些认知控制的缺陷导致人们难以从当前负性信息加工中分离注意。
2.抑郁障碍工作记忆损伤的神经生理机制
大量研究证明抑郁障碍患者的神经解剖环路功能和结构出现异常,尤其是在额叶皮质、杏仁核、海马和扣带回功能上的异常。有结构影像学的研究显示,抑郁障碍患者的前额叶、前扣带回、膝下区域、眼眶叶、尾状核、壳核等部位的缩小。临床研究发现抑郁障碍患者血液中的甲状腺素和促甲状腺激素(TSH)含量降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含量升高。ACTH含量的升高会促进皮质醇释放增多,大量的皮质醇会造成含有大量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海马的受损,从而导致记忆和注意的受损,这些研究说明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损害虽然与情绪低、动机减退等症状密不可分,但情绪低落以及动机减退并不是导致工作记忆等认知功能受损的原因,抑郁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受损与抑郁障碍状可能相互独立。
3.抑郁障碍工作记忆损伤的认知机制
但也有研究认为,抑郁障碍患者工作记忆能力较正常人低,可能是因为消极情绪占用了较多的认知资源,另一方面抑郁障碍患者工作记忆能力较低,以致于其不能较好地对信息进行刷新、转移,进而更加恶化其认知表现。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如Levens等人让抑郁障碍患者完成情绪面孔的2-back任务,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相比,患者组在消极情绪刺激时停留时间更长,在积极情绪刺激时停留时间更短。这说明消极情绪占用抑郁障碍患者更多的注意资源,而注意控制是工作记忆子成分中央执行系统的重要功能,这可能是导致抑郁障碍患者工作记忆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3]。基于抑郁障碍患者在处理消极的自我相关信息时用时更长,Koster等人认为这是由于患者不能自如地控制受损的注意从消极的自我相关信息中脱离[4];Foland-Ross等人的研究发现抑郁障碍患者执行工作记忆任务过程中,将消极词汇移除时,背侧前扣带回、顶叶和双侧脑岛激活增强,这表明患者难以从消极刺激中转移,从而占用更多的工作记忆资源,导致工作记忆受损[5]。
4.展望
根据前人研究可见,国内外关于抑郁障碍与工作记忆的研究大多是及抑郁障碍与工作记忆某个成分或某几种成分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性研究,较少涉及对抑郁障碍患者工作记忆结构的研究,以及工作记忆训练在抑郁障碍患者中的应用型研究;大多涉及抑郁障碍患者于正常人的比较研究,而较少涉及不同程度抑郁障碍患者的工作记忆损伤轨迹。关于抑郁障碍形成与复发的问题,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受损是持续性的,即使完全康复后仍然存在工作记忆能力下降的问题[6]。并且大部分患者反复发作,社会功能减退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抑郁障碍患者只是在抑郁情绪上暂时得到缓解,但其工作记忆等认知功能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参考文献】
[1] Baddeley A. Working Memory: Theories, Models, and Controversies[J]. Psychology, 2012,63(63):1-29.
[2] Gotlib IH, Joormann J. Cognition and Depress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10,6:285-312.
[3] Levens, S.M.,I.H. Gotlib, Updat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imuli in working memory in depression[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2010. 139(4):654-664.
[4] Koster E H W, De Lissnyder E, Derakshan N, et al. Understanding depressive rumination from a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 The impaired disengagement hypothesis[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11, 31(1): 138-145.
[5] Foland-Ross L C, Hamilton J P, Joormann J, 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difficulties disengaging from negative irrelevant material in major depress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4(3): 334-344.
[6] Ardal G, Hammar A.Is impairment in cognitive inhibition in the acute phase of major depression irreversible?Results from a 10-year follow-up study[J]. Psychol Psychother,2011,84 (2): 141-150.
论文作者:庞力铭,唐宏,廖慧云,叶丽平,肖梦然
论文发表刊物:《心理医生》2019年第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3/7
标签:抑郁论文; 障碍论文; 记忆论文; 患者论文; 工作论文; 认知论文; 功能论文; 《心理医生》2019年第4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