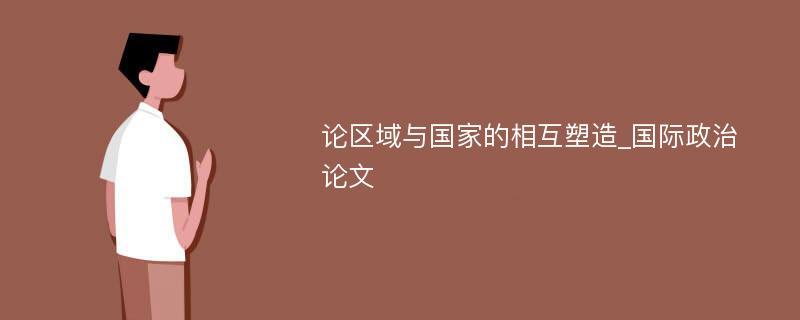
论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国际体系和国家行为体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而地区只是作为一个不变的背景和被动的客体,对国家、国家间关系和全球范畴的互动产生影响;相应的,在人们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解释与理解中,地区因素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显然,对地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传统观念,满足不了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发展变化的需要。要认识日益具有地区特性、受到地区特征与结构制约的那些事态、关系、观念与行为,就必须赋予地区范畴和地区层次分析以更高的地位。
地区是分析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的变量
(一)地区是人们思考国际政治的特定空间和新语境
对于以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体系理论来说,体系特征是发挥作用的因素,而单位(国家)是受这种作用影响的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基于“结构选择”、“制度选择”的因果关系抑或基于“文化选择”的建构关系。③然而,体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超时空的宏观性在达致理论本身“科学性”的同时,也显示出其解释力的局限性,对于一个由不同地区构成的、非同质的复杂多变的世界而言尤其如此。要全面和深刻地把握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地区政治图景、地区层次分析必须进入人们观察与思考的视域。
社会科学中的“地区”概念来自于自然地理学对地球表面的划分。所谓地区首先是指地理区域,“它多少受到自然的地形上的阻隔,带有生态学特性的烙印,如‘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北美,‘南美南方圆锥体’,‘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或‘印度次大陆’”。④然而,对于以人为本的社会科学而言,地区更主要表现为人类生活的一种载体,它不只是按照地理界线(陆地、海洋、山川湖泊等)划出的,更主要是按照不同人类群体的种族、民族、文化、生活习性,特别是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状况等加以划分的。⑤
划分不同地区的合理性来源于不同地区之间差异的客观性。一个地区作为相对连贯的领土次级体系(不同于非领土次级体系,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佩克⑥)和全球体系的其他部分明显不同,人们依据“相似或不同”的认识和判断来理解地区。较早研究地区概念的英国学者布鲁斯·M·拉西特(Bruce M.Russett)提出五种类型的地区,即社会和文化相似的地区、由政治观点和对外政策相似的国家组成的地区、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地区、地理位置靠近的地区。⑦坎托里(Louis J.Cantori)和斯皮格尔(Steven L.Spiegel)则基于内聚力(cohesion)、交往(communications)、权力(power)以及次地区国家关系结构(structure of relations)认定了15个明显有别的政治性地区,并进一步区分了核心区(the core sector)与边缘区(the peripheral sector)。⑧当代国际政治学者曾一度倾向于认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对“地区”概念的界定,即“由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而结合在一起的数量有限的国家”。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对地区研究的兴趣再一次升温,地区概念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提出,以共有的特性、内部互动的类型以及共享的观念来理解地区的存在。⑩
地区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与国际体系、国家或其他行为体的对立和割裂,相反,由于地区体系作为一种中间层次存在并发挥作用,国际社会诸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和多样,国际政治的内涵也因此更为丰富和深刻。相对于全球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而言,地区是一个子系统(subsystem),但不是一个静止和孤立的系统。一方面,地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事实,地区的构成基础并非一定数量、某种程度上相邻国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组存在互动关系的相邻国家。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代表了地区成长的状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内国家的权力和目标。另一方面,地区外政治或全球政治会渗入和影响、甚至是侵扰地区政治。“全球介入地区事务的逻辑是有可能来自全球对抗和关切以及偶然事件。不管是在斗争还是在合作中,全球行为体和地区行为体的视角还是有区别的”。(11)
对地区的分类和对地区特征的界定可谓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把地区当作一种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进行研究。而且,正如人们把国家和全球整体当作理性思考的空间一样,人们也越来越把地区作为思维活动的另一种特定空间来看待,(12)用来创造和建构进行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思考以及相应的知识生产的新的语境。
(二)地区的社会性和地区差异的存在,有助于人们理解地区体系的运转以及地区与国家互动的现状和趋势
地区首先是由地理相近的国家所构成的地域性单位或体系,而且一个地区内的各个国家总是具有一些共性。但地区的存在及其意义,或者说我们将它作为国际政治分析变量的意义,要超越这种给定的、自然的性质,而更多地在于其社会性,在于一个地理上的地区从被动的客体向主动的主体转变的过程,在于有某些力量如认同和观念、制度与规范等将地区与国家以及地区内的各个国家连接在一起,并使之具有特殊的互动关系,同时还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体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与价值。这些特点有些源于内部,包括共有的历史、文化、观念、政治态度和地区意识观等;有些则源于外部,包括对地区未来地位的相似预期和对地区外部事务的共同态度等。
地区的社会性使地区的差异性体现出来——无论是作为空间的存在,还是作为历史的存在。对不同地区的比较所依靠的就是他们的地区的社会性差异,表现为地区与国家、地区内国家间互动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广度和深度。即使是同一地区,随着内部互动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演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表现出状态与强度不同的地区性,而地区内国家的内外政策和行为方式也往往随之发生显著的改变。比如当今的欧洲,在地理上与50年前别无二致,但在非地理的意义上,前后已有天壤之别。随着内部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欧洲已经不再是由一个个彼此竞争或相互对抗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地区国际体系。虽然民族国家依然存在,但每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以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都得到了“地区”的塑造。
地区的社会性和差异性的特征,预示着地区不是凝固不变的。事实上,“地区是政治和社会工程,既然它是由人类行为体设计,用来保护或改变现存结构的,那么这些工程就像民族国家工程一样也可能失败。地区可以从内部和外部被修建他们的力量打乱。既然一个地区在观念和物质上能被建构,那么它也能在观念和物质上被再建构”。(13)地区特征变化的逻辑显示出其作为国际政治分析变量的价值。可以说,理解了地区的社会性和地区差异在空间和历史上的存在,有助于我们回答一个特定的地区是如何运转的,地区与国家的互动以及地区内国家间的互动是如何维系和变化的。
(三)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背景下,地区角色的变化赋予其更大的分析价值
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推动下,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国际事务和国家行为越来越具有地区的属性,受到地区结构与特征的制约。不同特征的地区作为一种变量和中介,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尤其是在塑造地区内国家间关系方面的作用与意义日益凸显。
诚如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所言,冷战这个全球“大盖子”(overlay)一度掩盖了地区多样性。(14)冷战的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一方面消除了超级大国的力量及影响对世界所有地区的严密覆盖,尤其是对各地区内的国家间关系的压制与扭曲,使得各地区被全球政治军事对抗和竞争所割裂的局面基本上消失。地区事务的管理与安排不再完全受大国的控制或者从属于全球政治力量均衡的要求,而是主要以地区内国家的利益以及他们对地区稳定、秩序与更好地应对全球竞争挑战的需要为基础。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也导致了众多单个民族国家难以单独驾驭的地区性问题,地区协调与合作的内在动力陡然增强。诸如跨越国境的民族、宗教问题,极端民族主义的发酵以及地区分裂势力的存在,历史遗留下的领土和领海纷争以及棘手的划界问题,地区和次地区范围内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凸显等,成为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的主要内容。因此,如戴维·莱克(David A.Lake)和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Morgan)所说,从一般意义上讲,“地区致力于应对暴力冲突以及实现秩序和安全,将主要基于地区层面上所设计和实施的一系列安排与行动。……与过去相比,地区已经成为实质上更为重要的冲突与合作的场所”。(15)
在经济领域,地区的存在对于国际事务、尤其是地区内国家间关系的意义更为突出。其一,全球化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密切联系。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特别是一定规模的市场的形成,资本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切显然为地区内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政策协调和地区经济力量的整合带来压力和动力。其二,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经济竞争,它在削弱民族国家的管理能力与自主性的同时,对其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前景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这在客观上需要一种集中的、有某种机制的管理,而所谓的全球治理对于多数国家而言过于庞杂和难以驾驭,地区范围的行动取向则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以地区为平台的协调与合作一方面处于区内各国政府的一定控制之下,同时又保证了相关国家的平等参与和共同受益,各方也就易于接受统一的标准与规章制度,支持必要的地区治理。其三,在地区层面上解决全球性问题,或者说以地区为单位实施全球范围内达成的标准与措施,最有利于推动全球化的发展并应对其带来的挑战。因为只有在特定的地区内才能最直接地感受到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全球性问题,以及全球影响的意义,利益与动机的平衡在地区而非全球层面上最有可能促使国家去寻求政策的响应。与此同时,国家的应对将会首先在地区范围产生直接影响。
可以说,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地区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地区问题的解决以及地区力量的发展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地区这一更加积极的角色变化赋予其特别突出的分析价值,研究地区体系和秩序如何塑造了地区内国家的观念和行为,又如何反过来被国家的力量所塑造,就成为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地区对国家的塑造
(一)地区是一个重要平台,它能够赋予地区内国家一定的地位、权力和国际形象
在当今世界,地区是国际事务发生和国际关系运作的空间和舞台,它能够赋予国家一定地位,是国家权力和目标的发源地,是国家利益和影响之所在,也是国家借以实现对外战略、提升国际形象的重要依托。
地区体系出现之后,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相对地位与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在世界政治中作用不大的中小国家,现在很可能成为地区内的重要角色,获得“超越其‘大小’的发言权和国际影响力”;(16)实力与影响难以覆盖全球的某些大国,现在则可以成为地区内的霸权或能够起主导作用的力量。(17)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18)当今美国式的“帝权”也完全借助于地区和地区力量的支撑。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曾指出,作为地区核心国家,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支持了美国的权力和目标。“在20世纪后半叶,它们的转变给美国帝权体系中的多孔化地区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缓冲器,在美国权力上升太快的时候防止美国骄傲自大;另一方面是支持国,当美国权力看起来衰落的时候,对负担过重的美国给予支持”。(19)
地区能够为不同国家或力量的发展与活动提供更宽广、更灵活的空间,为他们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以及满足自身的需要提供合法性权力。从地区政治的角度来看,冷战时期受超级大国竞争政策的制约,如种族冲突、领土争端、某些国家间利益的不一致等地区内不稳定因素处于潜在的状态,没有对地区的整体秩序形成冲击。冷战体制瓦解后,这些因素转而成为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又主要是地区内的国家拥有解决问题的合法权力与责任,他们因而进入了地区政治事务的主要议程。从地区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地区合作为其在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继续发挥作用取得合法性和更多资源的支持,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利用和控制地区化的进程,而且还可以通过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的方式来修正全球化,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最大限度地确保对市场的有效调控。
地区还是一个国家借以实施发展战略、发挥国际作用和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依托。在联系广泛而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一个国家要顺利实现其发展战略,必须超越国界不断寻求新的支撑点,而与自身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地区就是最好的选择。地区范围内商品、资本、技术、人员和信息等的大规模流动,以及地区市场的形成和拓展,都将为融入其中的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与此同时,地区还将为一个国家在发展的基础上承担更大的地区与国际责任、提升自身形象和声望,并为消解来自地区内外的各种消极反应提供重要的舞台和关键的支撑。
(二)地区利益的存在、地区合作与认同的增进,不断塑造着国家的自身定位和政策选择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存在于一个无政府体系中,一国政策和行为的基础应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个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20)然而,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尽管反映了民族国家的基本需要,但它只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相契合,并不能充分适应当今世界的新变化。
事实上,在全球化与地区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存在于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共同利益同时也符合其国家利益。比如,对于东亚地区来说,发展经济一直十分突出,为发展经济而谋求长期稳定的安全环境也是整个地区的共同利益,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产生的改善社会和生态环境的需要又成为新的地区共同利益。此外,在全球化过程中应付来自地区之外的经济政治挑战和压力也使地区内各种行为体的利益紧密关联起来,形成新的共同利益。(21)同样,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欧盟的不断成长成熟,既是地区整体利益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有力存在,也切实符合并推进了地区内各个国家的自身利益。
地区利益在地区内各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以及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它在推动地区合作的进程中,显然有助于增进地区认同,即“若干地理上接近并相互依存的国家在观念上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认同以及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一部分的意识”。(22)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下列两种情形推动了地区认同的形成:一种是地区范围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加速流动促使地区内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和政策协调不断扩大,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地区各国间的贸易、投资和信贷关系日益紧密,国家逐渐意识到本国利益已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不可分割且日趋紧密,地区内国家的普遍繁荣使国家意识到本地区是本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依托和后盾,因而产生了对地区重要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突然爆发的具有地区蔓延性的危机和灾害等使各国普遍意识到地区各国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本国的命运与地区的命运处于共荣共损的状态,由此产生共同命运感和地区认同。(23)
正如建构主义者所指出的,认同“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24)不过,“国家在互动之前,没有认同,没有利益,没有预期”。(25)互动过程决定了认同和利益。与此同时,国家在形成某种利益攸关的认同后,通常会采取与之相符合的行动,或者有关行动具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地区利益的客观存在,以及在寻求地区共同利益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广泛参与地区事务和日益增进的地区认同,将直接影响地区内国家的自身定位和政策选择。当一个国家将自己视为地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与自身的稳定和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它就不会突出差异和不同,更不要说斗争和对抗;相反,和平稳定、合作共赢、承担责任就成为一种选择。
(三)地区主义日益发展,并通过制度和规范等不断塑造着相关国家的观念与行为
所谓地区主义,“是地理位置相邻、有着较高程度的政治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许多共同特性的三个以上的民族—国家,基于增强各自的利益、管理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应对地区内外的各种共同挑战的需要,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或制度为机制,从地区整体性的角度出发寻求地区事务上的共识和共同安排的一种合作意愿与政策,并在此架构与秩序下处理相互关系的一种多边主义制度形式”。(26)
地区主义从无到有,从兴起到再度兴起,从旧地区主义到新地区主义,呈现出一个日益发展的过程。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不同的地区在地区特性、发展模式与发展程度、国家间关系、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差异很大,他们选择与适应的地区主义也就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点,有如赫特(Bjorn Hettne)和索德伯姆(Fredrik Soderbaum)在理论上所描述的地区性的进化逻辑,即从地区区域(regional space)、地区复合体(regional complex)、地区社会(regional society)、地区共同体(regional community)直到深化和融合为地区国家(region-state)。(27)地区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地区内国家间加强交往、交流、理解、相互接受和彼此信任的过程;它反过来又在不断塑造着地区内国家的观念与行为,尤其是通过制度和规范的力量。
在地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各领域和跨领域的地区性合作组织的建立和相关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机制的创设,能够影响和转变融入其中的国家的利益及行为。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所指出的,“通过提供信息,减少交易成本,作出更为可信的承诺,建立合作的基点,制度在总体上为(国家之间的)互惠行动提供便利”。(28)此外,作为制度和机制的重要载体,区域组织能够成为组织成员国利益和认同构成的基础,“可以激励国家和社会把自己设想为一个地区的一部分”,(29)从而产生出整合地区内和国家间原有的对立和排斥、隔阂与矛盾现象的动力。因此,地区组织和制度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框定”国家行为,而且还能够建构国家的认同及其寻求自身利益的方式。与正式的制度形式相比,规范的适用性更强。“规范是由权利和义务界定的行为标准”。(30)规范的主要功能是规定和限定行动,协调相互之间的期望以及减少不确定性。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规范可能对于那些希望解决共同问题和追求互补互利的目标、而又不愿将自己从属于某一等级体系或严格制度约束的政府来说,既易于接受,又能发挥作用。正如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在研究“东盟与地区秩序”之后所指出的,“通过对不同的国家制定同样的行为要求,规范确实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创造了国家之间相似的行为方式”。(31)
国家对地区体系和秩序的重塑
(一)国家的权力及其相对变化在地区层面的辐射
在地区体系和秩序的背景下探讨国家的作为,离不开对权力的分析。虽然其定义非常多,但就基本含义而言,权力是指一个行为体根据其意愿来影响另一个行为体去做或不去做某事的能力。施加影响的行为体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该行为体拥有一定的实力。而且,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所认为的,测量国家实力的大小是可能的,测量的依据是各国在以下方面的得分: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32)
权力是塑造国际行为的核心变量,而地区是国家权力和目标的重要指向。强大的国家往往会通过战略行动和自身影响力的结合将国家目标投射到国土之外。这样做是为了追求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所称的“与国家所处的环境有关的目标”,即“环境目标”(milieu goals),(33)旨在塑造一种国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超越其国界的环境。作为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在二战中取得了对法西斯的绝对胜利,并在随后的冷战中成为最后的赢家,美国表现出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大综合实力。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众多的军事基地,与一些地区核心国家及其支持国(如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保持长期的紧密联系,而且不遗余力地创设并利用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制度与规范。这一切构成了美国权力向地区辐射的基石。正如彼得·卡赞斯坦所言,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地区组成的世界,整个世界深深嵌入了美国帝权之中,而美国帝权通过整合其领土和非领土权力的行动,对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概言之,“美国帝权现在已犹如车轮的轴心,不同的地区是轴心辐射出去的辐条”。(34)
如果说当今由美国帝权支撑的地区构成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那么,同样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由于国家间相对变化的权力,地区体系和地区秩序乃至某一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都将不断得以重塑。事实上,伴随着一个国家硬实力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它不可避免地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而其所在地区受到的影响与冲击无疑最为直接和明显。如果一国实力增强的同时又有意愿去承担更重要、更积极的角色,用符合地区整体利益的方式来使用它的实力,那么地区的有序、稳定和发展将会更有保障;相反,如果一国硬实力的增长不是伴随着软实力和国际认同的提升,那么这样的增长很可能会被视为“威胁”而不是机会,从而引发或者加剧地区内甚至是更大范围的“安全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家权力相对变化的背景下,一个日益崛起的国家往往成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冲突与对抗、协调与合作,以及制度与规范建构中的关键因素,并由此重塑着地区内国家的互动方式,影响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向。
(二)国家的政策及其调整和变化在地区范围的溢出效应与规制塑造
作为经济学的术语,溢出效应又可称为外部性、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强加了成本(负外部性)或赋予利益(正外部性)的情况。
溢出效应对于理解某个国家的政策与行为在地区层面的含义和后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一方面,地理位置上的相邻或相近,为一国政策和行为在地区范围内的溢出效应大开方便之门。在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之间,不同类型的、积极或消极的社会互动的密度和强度才最高。就国际政治而言,冲突总是容易在邻国间发生,比较完美的秩序也更有可能在邻国间形成。另一方面,地区内各国往往存在更为密切的、广泛的联系网络和相互依赖,体现在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广泛领域,如水资源利用、森林砍伐、土地荒漠化以及人口爆炸等。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地缘的因素以及互动的广度和密度,地区内各国之间难免会遗留下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并在现实中存在暂时的误解与误判。在此背景下,一方的政策与意图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很难不受到他方的关注和猜疑,并由此引发一连串的反应。
如果说溢出效应尚属一国政策与行为的客观后果,是其主要目的以外派生出来的影响;那么,规制塑造则是一国主观意图的直接产物,它是通过制定政策、设计制度、运用规范和承担角色来影响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以此塑造出自己期待的、有利于实现目标的地区和周边环境。在这方面,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卡赞斯坦所指出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采取的行动,对于过去50年里亚洲和欧洲形成的地区制度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政策“对欧洲施行多边主义,而对亚洲施行双边主义。所产生的后果对后来欧洲和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5)值得注意的是,地区内国家不是整齐划一的,存在规模大小、力量强弱之分,因此就有了地区大国(地区霸权)、中等国家和小国的区别。如果说地区强国或霸权国家影响地区事态的能力通常更为显著,那么中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尤其表现为由其构成的次地区组织展现出的强大政策协调能力,进而对于地区体系和秩序的规制塑造作用。
理解一国的政策在地区层面的溢出效应与规制塑造,需要进一步考察其调整与变化的轨迹,而在变化的背后通常包含着复杂学习(Complex Learning)(36)的过程以及观念的转变。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学习、观念转变和政策调整不仅对其自身是有意义的,同时它依靠这种力量又在改变与外部行为体的互动方式,从而不断重塑着地区体系和秩序。
结语
以地区而不是传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作为理解和解释国际政治与国家行为的概念基础,同时又不割裂存在于体系、地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本文构建起一个地区与国家相互进行塑造的分析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可以解释:地区对国家的地位与权力、认同与观念、政策与行为的塑造;与此同时,国家的相对权力及其变化、观念和政策及其转变还对地区体系和制度秩序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地区与融入其中的国家处于相互塑造的过程中。彼此从对方那里吸取不同的元素,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进行重塑和改造。整体而言,地区与国家“谁为主导、谁是配角,谁决定谁”不是既定的、单向的,而是相互塑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区与国家存在基于“过程选择”的互动关系。
作为上述框架的支撑点和组成部分,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都在不同层面上成为分析工具。因为每一种理论都有长处,同时,每一种理论又有解释力的局限。他们可以成为思考与分析的起点,但不太可能以“一家之言”达致对重大问题的完整阐释。卡赞斯坦曾指出,“我不试图测试这些理论哪一种更具解释力,我只是希望能够有选择地从三种理论中汲取营养,以便解释各种不同进程之间的联系”。(37)
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为我们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以及与亚太周边地区变化中的新关系提供了理论视角。中国日益融入其中的地区体系是否有助于推动其观念转变、对外政策与行为的调整?反过来,当代中国外交的调整与变化、中国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是否又在塑造着地区体系和秩序?进一步来看,当代中国外交“转型”的持续推动力是否来自于地区与国家的相互塑造?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相互塑造将是积极的,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塑造将会是消极的?基于地区与国家相互塑造的理论视角,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将有助于我们廓清上述疑问,增强我们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能力。
注释:
①《当代亚太》2010年第2期,第28~41页。
②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Bimonthly)
③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8~9页。
④Bjorn Hettne and Fredrik So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in Shaun Breslin,et al.,eds.,New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2002,p.39.
⑤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⑥参见巴瑞·布赞等:《新安全论》,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⑦Bruce M.Russett,International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A Study in Political Ecology,Chicago:Rand Mcnally & Company,1967.
⑧Louis J.Cantori and Steven L.Spiegel,"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Regions",Polity,Vol.2,No.4,1970,pp.397-425.
⑨Joseph S.Nye,ed.,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Readings,Boston:Little,Brown & Co.,1968,p.5.
⑩Barry Buzanm,"The Asia-Pacific: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McGrew and C.Brook,eds.,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Routledge,1998,pp,70-73.
(11)[美国]布兰德利·沃马克:《地区与世界之间的中国》,载《新远见》2009年第5期,第38页。
(12)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第23页。
(13)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8.
(14)David A.Lake,"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A Systems Approach",in.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p.46.
(15)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 ,"The New Regionalism in Security Affairs",in 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p.5,7.
(16)Bilveer Singh,Singapore:Foreign Policy Imperatives of a Small State,Singapore: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88,p.12.
(17)王学玉:《国际关系研究的地区主义视角》,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3期,第27页。
(18)叶自成:《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第10页。
(19)[美国]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20)[美国]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21)耿协峰:《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第61页。
(22)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第18页。
(23)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第20页。
(24)[美国]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25)Jonath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 ,No.2,1995,p.235.
(26)王学玉:《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8期,第29页。
(27)Bjorn Hettne and Fredrik So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pp.39-44.
(28)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42.
(29)Emanuel Adler,"Seizing the Middle Grounds Constructivism in World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3,1997,p.345.
(30)Stephen D.Krasner,"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186.
(31)[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32)[美国]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
(33)[英国]阿诺德·沃尔弗斯: 《纷争与协作——国际政治论集》,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34)[美国]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46页。
(35)[美国]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46~47页。
(36)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286.
(37)[美国]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第42页;Peter J.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Japan,Asian-Pacific Security,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3,2001/02,pp.177-182.
标签:国际政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