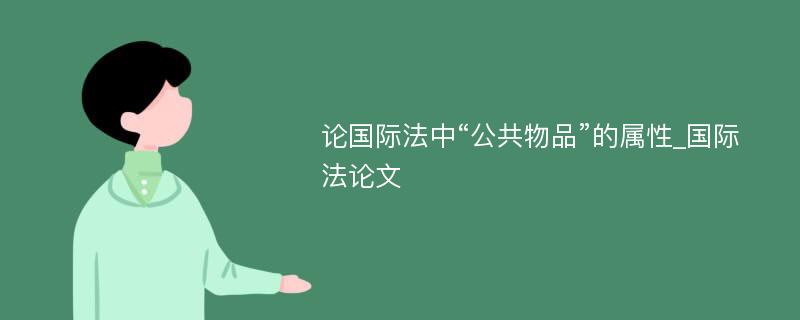
试论国际法的“公共物品”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试论论文,属性论文,物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9)01-0036-03
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最初是西方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同时满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供整个社会享用的物品[1]。如灯塔、公共电视,等等。所谓“非排他性”(nouexcludability)是指,在不付费的情况下,想享用商品的消费者很难或不可能被排除在消费者之外;“非竞争性”(nonrivalrous)是指,消费者的增加,并不需要增加新的产品供给。从消费方面来说,任何人增加对这种商品的消费都不会降低其他人所可能得到的消费水平[2]。根据上述两个特点,可把物品分成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兼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两个特征,如面包、鞋和汽车等。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称作公共物品,如天气预报和消防等。
公共物品学说在理论上有很多应用,并逐渐延伸到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具有社会公共职能的活动,诸如国防、国家行政、外交等都被视为“公共物品”。而根据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这两个基本特点,公共物品理论也可以适用于法学。尤其是国际公法、即通常所说的国际法,其英文“public international law”与“公共物品”即共有“public”一词,足见它们的渊源。事实上,国际法的公共性是很明显的。
一、作为国际社会共同立法的国际法
国际法是调整国际关系、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与国内法所不同的是,国际法是由呈平行结构的国际社会成员共同制定的。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主权国家就一直是国际法的主体。它们之间缔结的大量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1986年3月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赋予政府间国际组织——即IGO以缔约权)。条约——无论是双边条约还是多边条约——的缔结往往需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数年、甚至十数年、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达成。
一战后、尤其是二战后形成和确立的废除秘密协定及条约登记制度以来,各国之间的条约、协定逐年增加。成立于1947年的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迄今已完成了多个国际公约,包括《条约法公约》、《海洋法公约》①等,都是经反复多次才形成最终草案、经联合国大会认可、并召开外交会议讨论通过(表决方式或为多数通过制,或为协商一致通过制)才形成的。
二战结束后,随着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面貌,国际立法格局从过去的以西方为主导转变为由发展中国家推动,从而加强了国际法的民主化趋势。发展中国家追求和平与发展,珍视主权与独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针对这些诉求,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发展权利宣言》等文件的精神体现在众多的条约(公约)之中。
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的共同立法的这一特点还体现在国际社会对国际立法的广泛参与上。除各国政府(包括司法机关等)主导这个过程之外,学术界、各种媒体、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NGO)等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从而使各种力量、各种利益、各种观点都能得到表达。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NGO在国际立法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最近的一些条约,无论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禁止地雷公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还是《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的通过,NGO都积极活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就是在“大赦国际”的直接推动下通过的[3]。1997年,主要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禁雷运动”(IBL)构想和起草的《禁止使用、储存、生产、转让并销毁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即《渥太华公约》)最终获得通过,从而使其变成国际法②。
此外,作为国际法主要渊源的条约尽管数量在不断增长,但仍有许多国际问题未尝涉及,且不少国家没有批准相当多的条约;因此,习惯国际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就成为条约的有力补充,以满足各国在相互交往中的需要。许多习惯国际法规则迄今仍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无害通过、不使用武力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等。
同时,对于作为各国意志集中体现的条约,各国还有多样性的选择:对于已有的条约,他们可选择是否批准,甚至在批准某项条约后还可以退出条约(少数条约不允许退出);在批准或加入条约时,他们可对一些条款予以保留(有些条款不允许保留),从而限制条约对本国的适用;或对条约作出相应的解释③。
也正是由于集中了各国的意志,并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合意”,国际法规则才成为各国间增加相互信任、增进共同利益的粘合剂,成为各国合作的基础,成为维持国际关系稳定发展的保障。这也是国际法具有“公共性”的首要原因。
二、为国际社会所共同适用的国际法
国际法为国际社会所共同适用,尤其是具有强行法(jus cogens)效力的国际法规则,则对一切国家——无论是否接受它们,甚至无论是否为联合国的会员国——都适用,比如“条约必须信守”(pact sunt servanda)、“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这方面,各国都应该是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法上的一些案例,如“尼加拉瓜诉美国”、“梅盖求偿案”、“墨西哥诉美国”、“帕尔马斯岛仲裁案”,等等,美国都是败诉方;还有很多类似的小国、弱国获胜的案例。事实上,弱小国家通常倾向于利用国际法来抗衡强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并使后者处于舆论的被告席上。这充分体现了国际法在适用时的平等性。
同时,作为调节、规范国际关系的共同规则,国际法在适用时充分体现了公共物品的两个特点:非排他性——绝大多数公约(条约)都是开放性的(除双边条约和区域性条约外),其他未加入进来的国家都可以成为其缔约国;非竞争性——国际法的规则对所有缔约方都是平等适用的,任何国家援引条约规定都不会影响其他国家行使同样的权利④。无论是在正常的国家交往中、还是国家间关系发生争端时都如此。甚至经济学中的“免费乘客”(free-riders)概念也可适用于国际法,比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6条⑤中规定的第三国,就是此类免费乘客。而各人权公约中,作为第三方的个人虽未参加公约的缔结,却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也相当于“免费乘客”:根据国际法,国家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其人民,而必须遵守有关的国际标准—这些规定已令数十亿人民从中受益。
习惯国际法是相对于以条约为载体的成文国际法而言的。它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各国不断重复类似的行为,这是量的因素,即物质因素;二是被各国承认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是质的因素,即心理因素,即通常所说的法律确信(opinion juris)。国际法院在“大陆架案”(Continental Shelf case)中所述:“习惯国际法的要素主要应在国家的实际行为和法律确信中寻找,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⑥当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确立后,即使此前没有对该规则作出任何贡献、甚或反对该规则的国家也可从中受益,即成为“免费乘客”。
国际法的规则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另一部分是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定。国际法在多数情况下都得到认真遵守(国家如不遵守国际法,就会引发国际争端)。世界各国政府毫无例外地都承认国际法是对国家有拘束力的法律,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公然宣布不受国际法的拘束[4]。对于少数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国际社会通常有联大发表声明谴责、安理会通过决议实施制裁(甚至使用武力,如1991年海湾战争)、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予以解决。各国也可发表单方声明,在政治上进行谴责,使不法行为国蒙受舆论上的耻辱——即所谓“耻辱激励”(shame mobilization)。
在国家间发生争端时,由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文件明文规定:“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⑦因此,国际社会设计了多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International Disputes Settlement Mechanism,以下简称IDSM)。重要的多边性IDSM,如常设仲裁法院(PCA)、常设国际法院(PCIJ)、国际法院(ICJ)、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国际海洋法庭(ITLOS)、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国际刑事法院(ICC),等等;重要的区域性IDSM如欧洲法院(ECJ)、《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争端解决机制[5]。从而使各国可以有多种选择,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这些IDSM迄今已处理了数以千计的争端,其所作出的裁决绝大多数得到执行。
国际法对于各国国内法的整合、趋同也有着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际规范不仅在国际层面上发挥作用,更以强制性的拘束力进入内国法[6]。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现代国际条约的规定对统一列国执法机关包括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思考方式和方法,作成决定的程序,以及撰写决定和判决都具有直接且重要的影响[6]。从而使国际规则在各国国内得到更好的适用。
不过,并非所有的国际法律规则都必然是公共物品。例如,两国间的双边贸易协定就不是公共物品,因为它排斥别国的参与,从而不能从中受益。而区域性的条约,对于其他国家往往也是不开放的。但重要的是,要承认许多重要的国际规则拥有“公共物品”的关键性要素。
三、属于全人类的国际法
在世界格局新旧交替的当前,人类目前面临众多的困难和挑战,联合国《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即《名人报告》)指出,当前的全球性威胁有:贫穷、传染病和环境退化,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冲突,核武器、放射性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等等⑧。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在处理这些问题、尤其是少数大国在国际关系中崇尚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时,明显滞后、甚至显得软弱无力。以致许多人对国际法的效力、价值产生怀疑。
对于国际法的效力,毋庸置疑,是要弱于国内法,但正如国内法也经常遭到破坏、违反,而并未否定其效力一样,国际法虽也有被违反、破坏的情形,但更多的时候是得到各国的遵守的,至少遵守国际法的国家是远多于不守法的国家的、甚至那些违反国际法的国家也并非总是在违反国际法,而且几乎每个国家都宣称自己是遵守国际法的。各国政府、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和NGO在总体上是在努力维护国际法的效力的,尤其是后者在人权、裁军、环境、人道事务等领域的积极活动,更是将各国政府和广大民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国际法的价值集中体现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文件之中。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条,联合国的宗旨有四项:第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第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第三,促进国际合作。第四,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宪章第2条确立了联合国及其成员在国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它们分别是: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善意履行宪章义务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依本宪章规定而采取的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联合国不应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本原则不妨碍对威胁和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采取的强制行动[4]。
根据此类规定,国际法维护的是诸如“共同利益”、“全人类共同利益”(而非个别国家的利益!)、“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月球协定》等中有集中体现)、“和平”、“安全”、“人权”等价值。这些价值具有普世性,是惠及各国、全人类的,具有充分的公共性,是有利于各国的公共物品。国际法的生命力之所以不竭,就是因为国际法追求的价值取向符合国际潮流。而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际法对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包括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关注越来越多,并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因此,可以断言,国际法作为国际社会共同制定、共同适用的规则,也是国际关系中的显规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各国共同享用的公共物品。
要解决人类现在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就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共同贡献本国的力量,增加国际社会各种“公共物品”的供给。为此,西方有学者主张,以国际法为工具,实现全球治理;其基础就在于国际法是属于全人类的、在于国际法日益深入人心。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诸多行为体参与的互动过程,是一个包含全球的、区域性的、国家的、地区的等多层治理的结构[7]。它呼吁完善国际法规则,呼吁各国共同遵守国际法,呼吁包括NGO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监督国际法的适用,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全球治理构想并没有否定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社会组织原则(the organizing principle)的基础地位,而是通过限制主权的滥用与赋予主权不仅是权利而且是责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的新含义来加强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关系运作原则(the operational principle)的作用[8]。也就是说,主权平等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石,是不能动摇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让少数国家践踏别国主权的情形再次发生。
总之,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利益攸关,休戚与共。只有在国际社会中共同遵守国际法的准则,才能确保国际社会的秩序稳定有序,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全文共7,708字)
收稿日期:2008-08-31
注释:
①1994年7月28日达成的《关于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让步的结果。
②参见叶江、甘锋著:《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当代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59页。《渥太华公约》的缔约国现已超过150个。
③《条约法公约》第31、32、33条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解释权在WTO部理事会和DSB及其他国际司法机关,各成员之法院、立法和行政机关都无权对WTO规则进行解释。
④See Cf.John C.Yoo,Force Rules:UN Reform and Intervention,6 Chi.J.Int'l.L.641,655-59(2006)(arguing that military intervention to eliminate rogue states,terrorist groups,and "human rights disasters" is an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 that is likely to be "undersupplied").
⑤即:一、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对一第三国或其所属一组国家或所有国家给予一项权利,而该第三国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该第三国倘无相反之表示,应推定其表示同意,但条约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二、依第一项行使权利之国家应遵守条约所规定或依条约所确定之条件行使该项权利。
⑥See ICJ,Continental Shelf ease(Libyan Arab Jamahiriya v.Malta),Judgment,3 June 1985,ICJ Reports 1985,pp.29-30,§27.
⑦《联合国宪章》第33条第1款,见前注,第210页。
⑧参见http://www.un.org/chinese/secureworld/ch1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