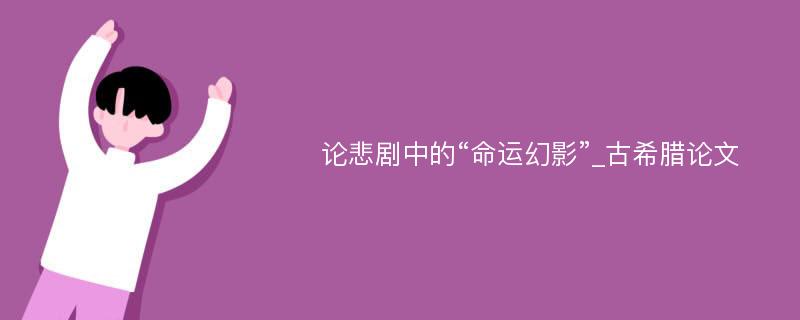
论悲剧的“命运幻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幻象论文,悲剧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悲剧问题一向是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的众多悲剧理论之间的明显差异性表明:悲剧问题仍然是一个美学之谜;不断地对悲剧提出新的理解,也许是美学的一项历史的乃至现实的使命。
在以往的悲剧理论中,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关注。其一是古希腊的宿命论和悲剧的关系问题。西方美学史上占主流的悲剧理论,一直否认宿命论会对悲剧产生任何意义上的积极作用;另一些悲剧理论,虽然非常重视宿命论和悲剧的关系,但没有看到古希腊独特的宿命论在悲剧形式和悲剧艺术观的形成上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个问题是悲剧的艺术形式问题。黑格尔以后的西方悲剧理论,有一种抛开悲剧作品的形式而直接探求悲剧本质的倾向,这样就完全忽略了悲剧的艺术形式所形成的独特的艺术视觉,从而也就无法把握悲剧依此艺术视觉所表现出的特定内容。即便是亚理斯多德和黑格尔对悲剧的艺术形式做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但也没有把这一形式上升到一种艺术视觉,乃至艺术思维的高度。
本文是寻求新的悲剧理论阐释的努力。我们的出发点是宿命论和悲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悲剧做诗学研究(本文中主要指对悲剧作品情节结构的研究),寻找出悲剧独特的艺术视觉和思维方式,进而对悲剧的本质及悲剧性这一美学范畴做出新的阐释。
一 悲剧和宿命论
以命运观念来解释悲剧的努力,在西方悲剧理论发展中,是一种持续不断而又隐蔽着的力量。它之处于隐蔽状态,是因为它一再遭到有力的攻击,而其自身的理论阐释始终没有令人信服地显明出来,反倒只停留在感受和体验的层次上。
反对者们有着正当的理由:悲剧不是宿命论思想的表达,因而必须把命运观念和悲剧划清界限。这里所说的命运观念,在希腊传统中又称为“神谕命运”,属于原始形式的宿命论。宿命论一般被认为是笼罩在人类远祖头顶的绝望阴云,它产生于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无知无识,信奉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人的行动和命运:一切都被决定了,人的自由和力量是无足轻重的。这样一种思想信仰显然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悲剧精神(即表现个人自由独立的意识,以及在此种意识支配下所显示出的人的力量)格格不入;把它和悲剧划清界限,或者把它从悲剧中剔除出去,看来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悲剧诞生外,宿命论和悲剧有着必然的联系,进一步说,没有古希腊的宿命论,就可能没有古希腊悲剧,从而也就不会有悲剧这种特殊的艺术。不过,宿命论和悲剧关系的内涵至今尚未完全显明,因而以往用命运观念来解释悲剧的努力,还仅只具有一种隐秘的根据。
艾略特在《莎士比亚和塞内加的苦修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利于我们解决问题的见解:莎士比亚只是“为了戏剧效果”才“利用”了塞内加的宿命论[①]。即便艾略特的见解对于莎士比亚是正确的,我们也不可草率地认为古希腊的悲剧诗人们也是超然物外地“利用”了宿命论,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宿命论思想起着普遍的重要作用的时代。不过,艾略特的见解仍然具有启发性。
由此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宿命论何以能给悲剧带来戏剧效果?或者说,悲剧“利用”了宿命论中的什么东西使悲剧具有效果?这种“利用”是偶一为之呢,还是一种本质性的“利用”?如果悲剧“利用”了宿命论,那么悲剧为何不是宿命论思想的表达形式?悲剧的目的何在?
亚理斯多德说,悲剧是从酒神颂中发展出来的[②]。在纪念狄奥尼索斯的仪式上,酒神歌队处于其核心地位。作为抒情诗之一的酒神颂之所以能演变成悲剧,是由于史诗因素的介入。史诗因素,尼采又称为“日神性质”,它以外观的形式构成了悲剧的“戏剧幻象”。尼采把悲剧的本质归属于酒神精神是有待探讨的,但他认为悲剧是“酒神认识和酒神作用的日神式的感性化”[③],这一观点是有启发意义的:它指出了悲剧是如何从酒神颂中诞生出来的。“日神式的感性化”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直观的形象,然而悲剧并非雕塑,人物行动所构成的情节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直观的形象也要依附于它才有可能。所以尼采认为,“日神式的感性化”包括两种因素:“直观的形象”和“剧情的结构”[④]。那么,剧情结构是如何进入酒神歌队并使悲剧产生出来的呢?尼采似乎完全忽视了这一问题。
汉密尔顿指出:“在公元前五世纪,德尔斐方式与狄奥尼索斯方式的结合非常完美地体现在当时的戏剧中。”[⑤]所谓“德尔斐方式”,可以等同于尼采的“日神性质”,但这一提法注意到了尼采所忽略的东西。德尔斐,阿波罗神庙所在地,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求神谕之处。神谕最初可能是“凭自然现象向人类启示他们的智慧”的;它往往是隐晦的,但它包含有确定性的力量,这力量来自神,因而常常预言并决定着求神谕者的命运,例如俄底浦斯杀父娶母的神谕,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⑥]。海伦·加德纳说,神谕“在希腊宗教中至关重要并普遍地存在于希腊悲剧中”[⑦]。因而,所谓“德尔斐方式”或“日神式的感性化”,就是神谕在悲剧中的运用。神谕是一种奇特的宿命论形式,歌德称之为“一切可怕事物的据点”;它往往集中在某人会采取某种行动的神秘预见上;这种行动的结果是可怕的,且具有必然性;但行动具体如何实现是不在预言之内的,即它还具有某种神秘的模糊性;此外,行动的结果并不标志为一种正义的惩罚,它没有“伦理的特性”,只有一种“审美的模糊性”[⑧]。苏珊·朗格认为,神谕“这种公开的,不包含细节和主题的行为的确定,为悲剧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开端,因为它限制了诗人对人物的塑造,这些人物的行为必须在命中注定的范围内自然地发生”[⑨]。
我们认为,史诗因素正是由神谕负载着进入悲剧的。在现存的33部古希腊悲剧作品中,绝大多数都采用了神谕及其变种(预言或诅咒)的戏剧化形式。黑格尔曾指出:“在古典艺术里用神谕形成内容,使神谕占重要地位的不是雕刻而是诗,特别是戏剧体诗。”[⑩]悲剧“用神谕形成内容”,说明神谕具有负载内容的形式功能。正是那些来自德尔斐神庙的可怕预言,赋予了悲剧行动以整体框架(即剧情结构);没有这一整体框架,日神式的直观形象将无所依附,人物和对话都将处于游离状态,酒神歌队也将永远停留在纯粹抒情的氛围里,悲剧也就无法诞生出来。所以我们说,悲剧在其诞生处对于宿命论的“利用”,并非仅仅“为了戏剧效果”,也非偶一为之,而是一种本质性的“利用”。神谕决定了希腊悲剧的情节模式,预示了悲剧的发展方向,并在其根源处,使悲剧艺术与其它叙事艺术区分开来。可以说,审美意义上的神谕,包含了悲剧布局的全部奥秘。
从上所述,神谕这种独特的宿命论,为悲剧艺术提供了表现形式。古希腊三位悲剧诗人对于“神谕形式”的普遍运用,一方面形成了古希腊的悲剧艺术观,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希腊悲剧由诞生到成熟以至衰落的艺术形式方面的根源。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一部用预言(神谕之变形)及其实现所构成的悲剧;诗人最成功的作品《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展示的是阿波罗神谕的实现过程。这种运用神谕来布局谋篇、营建悲剧整体构架的做法,在索福克勒斯那里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在三位悲剧诗人中,欧里庇得斯也许是最了解“神谕形式”奥秘的人;他在宗教方面的不虔诚态度,说明他是自觉地把神谕作为构成悲剧作品的形式因素来利用的;他继承了前两位诗人的悲剧艺术观,但是他在开场白(往往是一个神谕)、神力和相同结束语的运用上,把“神谕形式”变成了一种僵化死板的模式,从而扼杀了悲剧布局的活力,这无疑是希腊悲剧艺术衰落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原因。
在古希腊,宿命论思想统治着一切,神谕并非全然是一种审美因素,它包含有确实的宿命论内涵。“在希腊传统中,人们普遍信奉‘神谕’的命运,以致神谕成了公共遵守的法则”[(11)]。希腊悲剧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那么,既然宿命论为悲剧提供了表达方式,反过来,这种表达方式会不会必然要表达宿命论思想呢?
从表面上看,一出悲剧展示一个神谕命运的实现过程,那么它必然要表现这样一种宿命论思想:人的行动是由命运的力量支配的。但是,即使是《俄底浦斯》这样的悲剧,也只是“关于自我判断、自我预见、自我毁灭的伟大剧作”[(12)]。神谕命运的实现固然显示了神(或命运)的力量,但表现这种力量并非悲剧的目的。在悲剧中,宿命论气氛以及神谕所决定的情节结构,就如同一台压榨机,其目的在于,要通过它把葡萄压出汁来,即在绝境中表现出人的力量。即使是索福克勒斯那样虔诚的诗人,也让他的人物具有着“个人自由独立”的意识。纵观古希腊悲剧,不管诗人们写下多少行表现宿命论思想的诗句,他们的着重点始终在于展示人的完整命运,以及人对于自身力量的认识上。正是神谕命运的实现,悲剧人物完整的人生图景得以展示;在此展示中,悲剧庶几让我们窥探到生存的秘密。汉密尔顿说,在古希腊悲剧中,“世上的巨大奥秘——人的生活——通过伟大的艺术力量呈现在人们面前”[(13)]。
黑格尔把“个人自由独立”的意识看作悲剧得以产生的前提;此一前提只有古希腊才具有,照他的看法,这是悲剧唯独产生并繁荣于古希腊的原因。黑格尔认为,“东方的世界观一开始就不利于戏剧艺术的完备发展”,其原因在于东方民族的宿命论思想[(14)]。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然而笼统地认为宿命论不利于悲剧,则是错误的。古希腊奇特的宿命论在其悲剧中是必不可少的:不是作为一种思想信仰,而是作为审美因素。在一切民族的宿命论中,古希腊神谕命运观是极其独特并在其民族的历史生存中起着普遍的作用;它和悲剧的联系表明:悲剧得以产生的条件,除了黑格尔所说“人物意识到个人自由独立的原则”之外,还必须加上一条,即神谕观念的存在。一方面,个人自由独立的意识对于神谕命运的审视,正是悲剧艺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独立意识的存在,很难说明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它还需要相应的艺术手段。
以“神谕形式”为核心的古希腊悲剧艺术观,对近现代悲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西方悲剧的发展在古希腊、近代和现代等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特征、思想倾向和社会历史内涵,但仍然是一个联系着的历史。这种联系是由古今悲剧中最为普遍的基本性质决定的,或者说,这种联系说明有一种最为普遍的原则贯穿于古今悲剧之中。我们认为,悲剧中最为普遍的原则是一种艺术原则,这就是审美意义上的神谕,即“神谕形式”。
“神谕形式”作为一种普遍的艺术原则,在古今悲剧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较为具体的分化可以从悲剧历史发展阶段中所现出的差异中表露出来。现在,我们回到艾略特的那个论断。我们认为,莎士比亚不仅仅是为了“戏剧效果”才利用了宿命论,而是经由塞内加接受了古希腊的悲剧艺术观。但是,在伊丽莎白时代,宿命论已是不合时宜的思想,莎士比亚如何能运用神谕观念构造他的悲剧,仍然是个问题。说莎士比亚是“异教徒”、“在精神上接近古希腊”,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人文主义思想兴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基督教天命观已受到动摇,原始形态的神谕命运观几乎无存身之地。然而,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像一切历史规律一样有其必然性;它要求那些“生不逢时”的诗人接受前代诗人创造的艺术原则,并找到适合于自己时代的表达方式。莎士比亚正是这样为我们奉献出近代悲剧的杰出典范。在他那些最杰出的悲剧中,他运用变化了的神谕构造情节,以图激起类似于古希腊悲剧中的必然性观念,并把它和文艺复兴时代所激发的个人愿望结合起来。唯有歌德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一种超个人能力的愿望是近代才有的,可是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发出来,因此它成为一种命运,而接近于古典的戏剧”[(15)]。《哈姆莱特》中的鬼魂的命令和《麦克白》中女巫的晦涩预言,相当于古希腊悲剧中的神谕;它们是作为审美因素出现的,并不是说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是如此这般发生的。这一“外在机缘”把“个人愿望”提高为一种命运,从而确定了悲剧的情节结构。这样,在神谕命运不被信仰的时代,莎士比亚仍然运用“神谕形式”创造了他的悲剧。在易卜生以来的现代悲剧中,神谕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尽管此时的“神谕形式”不再借神或鬼魂、巫师之口道出,但它仍 旧完整地保持着它在希腊时代所具有的审美本质和功能。如果我们在易卜生的《群鬼》或奥尼尔的《哀悼》中,仍然嗅到生理或心理决定论所形成的宿命论气息,我们不必吃惊,这是“神谕形式”带来的:它要求悲剧中的一切必须在“命中注定”的范围内完成。
二 “神谕形式”和悲剧视觉
由于“神谕形式”的缘故,我们称悲剧意象为“命运幻象”。通常,“命运”这一概念有两层含义。其一,它是外在于人且支配人的一种神秘力量;另外,在古希腊神话中,人格化女神摩伊拉是这种力量的化身;这是原始形式的宿命论的理解,至于后来的斯多噶主义、基督教、黑格尔、谢林、海德格尔等对于“命运”的解释,不在本文涉及的范围。其二,“命运”这一概念标志为一种前定的个人、民族或历史的走向和完成;这种含义和第一种含义有着内在联系,即这种“走向和完成”是由作为现实力量的“命运”支配着的;由于宿命论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消隐,两层含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失去了,“命运”也就纯然成为一种“前定的未来”。按照我们的理解,悲剧的情节结构,就是这样一种“前定的未来”,即“神谕形式”。而“命运幻象”就是一种“对于可见未来的幻象”[(16)],即预示着即将完成和最终确定的人生图景。
大多数悲剧理论,都给悲剧以极高的地位:“诗艺的冠冕”,“文艺的顶峰”,诸如此类。从亚理斯多德,到黑格尔、叔本华、尼采,都对此提出过自己的解释。尽管说法不一,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悲剧在诸艺术种类中之所以具有极高的地位,在于它做着其他艺术所不能做的事,在于它所达到的独一无二的效果。我们认为,悲剧之所以能如此,首先取决于它的形式特征,即审美手段;那种抛开悲剧的形式特征而直接探求悲剧效果的做法,超出了美学领域,因而难免失去根基。悲剧的形式特征主要在于情节结构,或者说“神谕形式”,它决定了悲剧独特的艺术视觉,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思维模式,即“悲剧思维”。这是悲剧形式所具有的最为深刻的审美内涵。
亚理斯多德强调悲剧情节安排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悲剧艺术中的“第一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事”。就此,他提出了关于悲剧行动的“完整性”的概念:悲剧是一个“完整”的行动的摹仿;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17)]。亚理斯多德对于“完整”概念的概括是准确的,但他没有进一步挖掘这一概念在悲剧中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完整性是“神谕形式”的一个特征。“神谕形式”是一种“前定的未来”,所以悲剧行动总是暗含着并指向未来;但这种未来不是开放的,不是时间上的永无尽头,而是封闭的、没有出口的,因为它要求着行动的最终完成,即亚理斯多德所说“无他事继其后”[(18)]。也就是说,悲剧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向未来展开的完整过程,在其终止处,悲剧行动得以终结。但行动的终结并非目的,其目的是使悲剧人物的命运得以实现或完成。因而,悲剧展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幻象,而只有一个完整的、确定了的、终结了的人生,才有理由让人们在其中寻找生存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悲剧的完整性和其他艺术所要求的完整性区别开来:其他艺术只要求形式结构方面的完整,而悲剧的完整性不仅要求形式结构方面的完整,同时也是一种艺术视觉,它决定了悲剧处理人生题材的独特“眼光”,即展示悲剧人物完整的命运幻象。
悲剧要创造完整的命运幻象,这就是悲剧中充满毁灭或死亡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悲剧情节的完整性、悲剧行动的终极性,是通过人物的毁灭或死亡实现的。这样一来,由于和情节结构的关系,悲剧中的毁灭或死亡就具有了审美意义,而非纯然是现实意义的。在现实生活中,照一般人的观念看,死亡的到来,不仅取消了一个人全部的生存可能性,而且也就此取消了生命的意义。而在悲剧中则恰好相反,正如卢卡奇所说,“悲剧的生存,在一切可能的生存中,是最应当属于这个世界的生存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边界总是向死亡延伸。现实的日常生活,决不能达到这个世界;它只是把死亡当作恐怖的、毫无意义的现象来理解,视为某种截断生命之流的力量。……但对于悲剧来说,死亡这个边界是一种始终内在的现实性,与各种悲剧事件紧密相联”[(19)]。死亡是悲剧人物生存的“内在现实性”,这一“现实性”,决定了悲剧生存是作为一个整体凸现出来的,并且赋予了这一生存整体以某种确定的意义。当然,并不是每一部悲剧作品都以死亡或毁灭的方式来实现人物的命运。苏珊·朗格指出,许多现代悲剧“通过与死亡完全一样的绝望,即一种‘灵魂的死亡’来结束一切”[(20)]。无论如何,悲剧人物的命运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凸现出来。
从根本上说,悲剧不是对于一个死亡“事件”的描述,因而不能在本质上把它概括为“对死亡的认识”[(21)]。死亡在悲剧最后一幕中,是作为“审美因素”出现的。死亡作为“审美因素”,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作为审美手段,即悲剧的主要结局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悲剧生存的“内在现实性”,即生存整体中的终极指向,而这一生存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审美的生存而与现实生活有所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只有在死亡之时,悲剧人物个人生活的道路才告完成,生存的意义得以显现,悲剧的命运幻象才得以营造。
乌纳穆诺认为,人必有一死和心灵向往永生的渴望的冲突,构成“人生的悲剧意识”[(22)]。然而,悲剧并不表现“人总有一死”这一必然性,勿宁说它着力表现的是完整的个人命运。在我们看来,悲剧人物从来没产生过那种“永生的渴望”,因为在死亡迅速降临的时候,他意识到他个人的命运即将完成,在那个瞬间,生命的光芒倏然闪现,试图照亮那在其整体命运中仍然晦暗的部分,就此生存的意义得以展现。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他变动不居而最终确定下来的完整的人生图景,而不是什么“永生的渴望”,更不仅仅是死亡本身。
在悲剧世界,并不因为存在着大量的死亡“事件”,就说明悲剧表现了人生的无意义。如果人生无意义,悲剧不能赋予它意义;如果人生有意义,悲剧也不能在最后一幕通过死亡而取消它。在悲剧中,死亡把生存作为一个整体凸现出来,恰恰说明这是一个有意蕴的整体;这种意蕴是生存本身所具有的,只是它需要在一个整体中才能充分得以显明。这说明悲剧正是要探究人生的意义,而它的艺术视觉决定了这一探究是在完整的命运幻象中进行的。所以,我们认为,那种认为悲剧只是把我们带进“死荫的幽谷”,并让我们认识到死亡的必然性和人生的无意义,甚至教导我们放弃生命的看法,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这是脱离开悲剧的形式特征及艺术视觉而片面地把悲剧中的死亡理解为一种普遍“事件”而造成的。
悲剧常常唤起一种必然性的观念,也称“命运感”。我们认为,必然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悲剧情节的发展上,因而可以把它归结为“神谕形式”的一个特征。在古希腊,神谕命运被信仰,因而它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但它进入悲剧后,则造成了悲剧的情节模式,即“神谕形式”,因而又是一种审美的力量。神谕命运作为一种审美力量,决定了悲剧的情节结构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构,这一必然性仅仅表现在,它决意要使飘忽不定的人生固定下来,形成命运幻象。因而,悲剧中的必然性,首先不是命运的必然性,不是心理必然性,也不是自然或社会规律的必然性,而是审美的必然性。当然悲剧中可以表现自然或社会生活中具有必然性的事物,但这一切必须通过审美的必然性,即具有必然性的情节结构表现出来。从古至今,创造必然性的“事物”,不仅是悲剧诗人,而且是一切诗人和艺术家的渴望,因为“必然的事物”异常伟大。悲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要求必然性的情节结构,这就使得悲剧人物的命运总是给我们一种前定的必然如此的印象,即“命运感”。
悲剧情节的完整性,是通过必然性得以实现的;没有这种必然性,悲剧的完整性就难以保证。“神谕形式”是“前定的未来”,也就是说,悲剧一开始就预先指向了这个未来。或者说,悲剧的结尾“必须把全部行为概括为一开头就已暗示出来的一种可见的、实现的命运”[(23)]。这就是为什么一出悲剧总是给我们一种离弦之箭直飞箭靶的那种必然如此的感觉,而其他叙事艺术并不总是给我们以这样的感觉。在悲剧结构中,必然性往往集中体现在“悬念”这种戏剧形式里。悬念就是把前定的东西预先通过暗示的方式透露出来,它指示着悲剧情节发展的方向,并暗含着这一发展的最终完成。悬念造成悲剧情境,情境引发出一系列动作,最终达到悲剧行动的完成。
对于悲剧中的必然性,人们总是迷惑不解,他们常常以为必然性背后一定有某种实体性的力量,正是它支配着悲剧行动的进程,造成人物的毁灭,并引起我们的必然性观念。这种力量一般被称为“终极力量”。其实,悲剧中的必然性,并不表明在它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支配一切的力量。必然性是悲剧的目的所要求的,是通过“神谕形式”体现出来的。所谓“终极力量”的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对它的探讨,也将徒劳无功。不过,用“终极力量”来解释悲剧有其深刻的理由:其一,悲剧人物无辜受难有违人们的道德情感,所以需要给出超越于道德感之上的解释;其二,悲剧人物命运的神秘,需要做出合乎理性的解释。当人们在道德情感上坚强起来的时候,当人们认识到理性的限度的时候,有关“终极力量”的问题会在悲剧的探讨中自行消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悲剧的情节结构表明了这样一种艺术视觉:选取具有必然性的生存整体来显示生存的意义。一般来说,悲剧的生存是一种审美的生存,因而与现实生存有着区别。但是,悲剧世界并不是与现实世界毫不相关的,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由于两者的区别,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主题、思想观点和人物形象从悲剧中截取出来,并且只根据它们所包含的现实生存内容来评价它们;由于两者的联系,我们又不能无视悲剧的艺术形式,这一形式确立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视觉,并以此显示出悲剧表现现实生存的独特眼光和所选取的特定内容。所以,悲剧的形式是至关重要的,抛开这一形式,无法了解悲剧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种类的根基所在,也无法把握悲剧是以何种方式与现实生存保持至深的联系,从而也就无法认识到悲剧的独特内涵。
三 悲剧的“宿命”
悲剧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完整的命运幻象,这一幻象以直观想象的形式显明生存的意义。那么,在悲剧独特的艺术视觉中,这一“意义”显示出何种倾向性呢?我们用“神秘”一词来概括悲剧的这种“意义倾向”。
布莱德雷说:“如果悲剧不是痛苦的神秘,那它就不成其为悲剧了。”[(24)]用“终极力量”(无论是“盲目的命运”,“永恒正义”,还是“道德秩序”)来解释悲剧中的“神秘”,虽然简单易行,却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知道,一切必然的事物,在我们尚不理解它们的时候,都是神秘的。季节的永恒更替等自然现象,对于我们来说是神秘莫测的,但科学给我们提供了解释。如果把人之生存看作一个“生老病死”的自然过程,科学也同样可以给出解释,无“神秘”可言。但是人在社会历史情境中的生存,具有着理性科学所不能阐明的“意义”,这一“意义”常常是隐晦不明的,可以称之为“神秘”,它集中地保存在人类的直观想象中。而由于悲剧艺术视觉的特征,它把生存表现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整体的生存,因此它比其它艺术更集中地保存了这种“神秘”。在悲剧中,“神秘”不纯然是那些黑暗意象所构成的气氛,它和必然性的悲剧行动密切相关,但它主要指悲剧人物整体生存中所包含的意义。“神秘”,就是一个“谜”,而“谜”并不要求在别处得到解答,它本身就包含着意义,甚至就是这种意义。对于悲剧来说,这一“谜”或“意义”,并不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疑问或陈述,因为悲剧是直观想象,它把这一“谜”或“意义”保存在自身之中。所以说,悲剧乃是一个“谜”的形象,即“谜”的幻象。因而只有面对这一幻象,这一整幅的命运图景,我们才能对悲剧人物生存的意义有所领悟。但是悲剧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对于生存之谜的解答,它不为我们提供任何关于生存的教条。因为个人生存的“神秘”对于人类来说,是一如既往的、永恒的;对此,我们并不比古希腊人知道得更多。如果说悲剧“揭示了关于人生的重要真理”,那么这一真理可以表述为:生存之谜就是生存之谜。这一真理,体现在悲剧人物去生存、去完成和实现自己命运的“神秘”图景里。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期望通过谶纬、占星、相术等把握个人的命运。这种宿命论虽然判定了理性的局限性,但它对我们领会生存之谜不仅没有助益,反倒加重了人类头顶上的迷雾。悲剧最初借助宿命论诞生出来,却成为突破宿命论迷雾的第一道曙光。纵观悲剧的历史,关注个人的命运及其在历史境遇中的生存,是悲剧一以贯之的东西。但是面对永恒的生存之谜,悲剧不像哲学那样给出理性的解答,也不像宗教那样施以超越和拯救,而是把生存之谜作为生存之谜保存在命运幻象里。那么,悲剧是不是采取了一种悲观绝望的态度呢?或者说,悲剧如何能把生存之谜表现为一个“谜”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明了“悲剧的本质”、“悲剧性”以及我们所说的“悲剧思维”这一系列概念的关键所在。
我们认为,悲剧是通过“疑问”把生存之谜表现为一个“谜”的幻象;而悲剧的历史,是一个永远“疑问”着的历史。
“可是永恒的神秘,是不向血肉的凡耳宣示的。”当鬼魂对哈姆莱特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我们立刻意识到,那个展示哈姆莱特命运的丹麦王宫,最终将成为一座真正的迷宫。这部作品,既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剧,也不是一般所理解的关于复仇的情节剧,或者什么“性格悲剧”,而是展示哈姆莱特生存之谜的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哈姆莱特最初接受复仇的使命之后,替父报仇、“重整乾坤”就成为他生存的意义。但是,这一生存使命中,包含有诸多暧昧不清的成分,哈姆莱特在行动上的犹豫不决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装疯卖傻,是因为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种使命的沉重和暧昧,超出了他的力量负荷和认识限度,以致使他难以保持住平日的举止和风度。哈姆莱特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是所有内心怀有秘密而孤立于众人之外的人的那种痛苦。不仅如此,哈姆莱特内心的秘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对于他本人,同样也是一个秘密。而这一“秘密”,却是他一切行为的依据和意义所在。因而这部悲剧表现的是这样一种痛苦:生存行为缺乏确凿的依据和意义的巨大痛苦。他怀疑那鬼魂是个恶魔,这使他渴望复仇和完成自己使命的心,变得“像铁匠的砧石那样漆黑一团”。当他开始忧虑他的使命的正当性的时候,他的疯癫几乎是真实的而不是沉着老练的诡计。这部伟大的悲剧几乎没有冲突,总领全剧的是哈姆莱特对他使命中那种晦暗不明部分的“疑问”,由此而引发的对于普遍的生存意义的沉思默想是该剧精华所在。尽管哈姆莱特最终完成了他的使命,然而“一切”并没有因此而真相大白。这个“追寻真理的愿望毫无限制的人”在其临终的时候,仍然表露出他的无知以及生存可能具有着无法理解的意义:“此外仅余沉默而已”。雅斯贝尔斯说:“哈姆莱特的命运是个未解之谜。”[(25)]这部悲剧正是对于这一命运之“谜”的展示。只是由于哈姆莱特坚韧不拔的“疑问”和探寻,我们得以一瞥那丹麦阴暗迷宫的轮廓。
每部悲剧都有着一个不可解决的疑团。这个疑团把悲剧人物带进窘迫的境地,并激发他毫无节制地探寻下去。这种毁灭性的探寻,像划过夜空的彗星,标画出悲剧人物命运的轨迹。随后,黑暗依然如故。仿佛真如卡夫卡所说:“他们从黑暗中来,也将遁失于黑暗。”然而在悲剧的“黑暗”世界中,仍然包含着“光明”,这就是“悲剧之核”——“疑问”。真正的“疑问”,指向着值得一问的东西;“疑问”是进入其中的道路;它只是进入其中而有所领悟,因而不需要回答。而且,所有值得一问再问的东西,都不能有某种确切的唯一的解答,所以“疑问”的意义被包含在“疑问”自身之中。悲剧的“疑问”是对生存意义的“疑问”,通过此一“疑问”,悲剧才能把生存之谜表现为一个“谜”的形象。朱光潜说,“悲剧满足于作为一个问题展示在人面前的那些痛苦的形象”;“换言之,悲剧不急于作出判断,却沉醉于审美观照中”[(26)]。许多人强调,“悲剧最关心的是苦难”,“是苦难使悲剧成为悲剧”。然而,如果在俄底浦斯所承受的巨大苦难中没有“疑问”,那么苦难仅仅是苦难而已,俄底浦斯的命运不过就是逆来顺受的命运。悲剧固然不能没有苦难,但苦难的深度,是“疑问”挖掘出来的,“疑问”所及的深度就是悲剧的深度。对于苦难的承受,只显示了人的忍耐力;在“疑问”中承受苦难,或者在承受苦难时保持着“疑问”,才真正显示出由“个人自由独立意识”所生发出的人的力量。所以,从根本上说,是“疑问”使悲剧成为悲剧,而不是苦难。没有“疑问”,任何一种悲惨的命运都不会具有悲剧性;只有通过“疑问”,混沌的个人命运才能上升到悲剧的高度。所以我们认为,命运幻象是以“疑问”为核心的幻象,“疑问”乃悲剧的本质所在。
那么,悲剧的态度是否就是哲学上的怀疑主义的态度呢?尽管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易卜生等悲剧诗人,都曾被冠之以“怀疑主义”的名号,但悲剧中的“疑问”所包含的意向,与怀疑主义认识论上的怀疑及其伦理学中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怀疑主义认为,任何可靠的知识都不可能,因而事物是不可认识的。悲剧并不以这种认识作为其探求生存意义的原则。悲剧承认“神秘事物的存在”,而一切神秘事物中最为“神秘”的莫过于人之生存。悲剧正是在“疑问”中对生存有所领悟,并把此种领悟依然保存在“疑问”里。这是悲剧形象地探求生存意义的独特方式:它不表现为概念的陈述,而凸现为直观形象。按照通常的理解,“疑问”必须得到回答,才算圆满;其实,“疑问”本身就已经有所领悟,“疑问”所到之处也就是领悟所及之处。这种在“疑问”中对生存的本质性领悟,我们称之为“悲剧思维”。这种思维,决非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思维”,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形象思维”。它是把个人命运作为一个整体来磨砺和接受的力量,是在仍然晦暗的整体生存中“疑问”地把握一个人行为根据的极为奇特的艺术思维。这一艺术思维,体现在以“疑问”为核心的命运幻象里,而不在别处。所以我们说,悲剧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艺术,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形式特征所形成的艺术视觉,还表现在它的内容倾向即“悲剧思维”上。
我们认为,悲剧快感的最终根源,就在于悲剧的“疑问”中包含有对于生存意义的本质性领悟。对于这一问题,尼采提出了著名的“形而上慰藉”的理论。他说:“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27)]尼采接受了叔本华关于现象和本体的划分,而为了克服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肯定生命,他把叔本华痛苦着的“生命意志”改变为“强力意志”,即一种不断毁灭和生成着的洋溢着欢乐的永恒生命。但尼采却接受了叔本华对于现象世界的看法,认为它除了痛苦别无所有,并把这一点作为他悲剧理论的前提。在他看来,悲剧的意义或者慰藉,不能在现象中寻找,而在于“那似乎隐藏在个体化原理背后的全能的意志,那在一切现象之彼岸的历万劫而长存的永恒生命”[(28)]。
但是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现象的世界,在这个现象世界的生活也是我们唯一的生活;它并非只是痛苦,而是苦难和美丽交相辉映;它并非没有意义,而是一切意义的来源和最终的去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对于这一意义的探求,并把对于这一意义的领悟保存在直观想象里。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艺术是一种形而上活动,因为广义的形而上学就是对人生世界的意义的探求。但是,艺术的这种探求并不表明它要在人生世界之外寻求一个“解释”或“评价”,然后再把它“塞入”人生世界。艺术既然对现实世界的意义有所揭示,它当然要把它所揭示出的意义归还给现实世界。需要强调的是,艺术赋予生活以意义,只是事情的结果而非根源。艺术之所以具有此种“馈赠”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它以直观想象的方式揭示了生存的意义,还在于我们个人生命的短促,经验的匮乏,以及理性认识的局限,尤其是人类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人类命运的变迁,使我们渴望通过艺术了解人类生存的丰富内涵和一以贯之的本质,从而对现实生活有着更为深邃的领悟。
狭义的形而上学或哲学,不是以直观想象而是以逻辑手段达到它的目的。艺术是活生生的、永恒的图景,“它的鲜明性与抽象事物反复无常的真理无关”[(29)]。尤奈斯库曾指出,一种哲学总要反对另一种旧的哲学,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也必将取代以往的旧的科学理论,“但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却是互相支撑的”,因而“正是艺术证明了可能存在某种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30)]。然而在诸种艺术中,悲剧则显示出一种较为一致的“形而上学”倾向,它标志出悲剧的“形而上慰藉”的特定内涵。我们认为,悲剧属于现象和时间的世界,我们不能像尼采那样到现象背后,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到永恒的“理念”领域去寻找“慰藉”。悲剧是对于生存意义的探求,它不满足于任何一种结论,所以它把生存之谜表现为一个“谜”的形象,“谜”的形象通过“疑问”得以实现。“疑问”,并不表明悲剧处于某种懵懂状态,而是包含着对于生存的本质性领悟。因而也可以说,悲剧的“疑问”是一个“展开了”的“疑问”,但仍然是一“疑问”。雅斯贝尔斯指出:“悲剧知识是不完整的,只有在这种一再提出问题的持续体验中庶几可以发现完满。”[(31)]悲剧正是藉此“疑问”的“持续体验”而得以超越自身;此超越表明,人类在精神方面的探求是一种“在途中”的疑问性体验;而“疑问”,是精神探求的最高形式。所以,悲剧之所以能给我们一种“形而上的慰藉”,在于悲剧在其“疑问”幻象中显示了人类对生存意义永远探求的精神,以及这种探求行为孤立无援的伟大。这正是悲剧能给予我们审美快感的最终根源,也是我们所理解的“悲剧性”这一美学范畴的核心内涵。
每部悲剧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对于人的命运的困惑,以及在困惑中的自我认识所导致的毁灭。这是任何时代的乐观主义都不能容忍的。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就毁于苏格拉底的理性乐观主义。尼采的这一发现,被大多数现代悲剧研究者所认可。从西方悲剧奇异的历史发展来看,无论是理性乐观主义,基督教乐观主义,还是现代科学的乐观主义,一旦变成一种强制的乐观主义,就将扼杀悲剧。在乐观主义那里,没有什么生存之谜的问题,一切皆可穷达,一切都是透明的;问题当然会有,但无一不可以完满解决。但悲剧显示的恰恰是不可解决的事情。歌德说:“解决不了或没有解决的窘境给我们带来悲剧的因素。”[(32)]尤奈斯库也说:“只有不可解决的事物才具有深刻的悲剧性。”[(33)]一切不可解决的事物都与人的命运相关联,除此之外没有“不可解决”的事物;而人生存的意义也就在这种不可解决的“窘境”中昭示出来。陷入悲剧“窘境”的人是这样一个人:像卡桑德拉一样,他了解他所处的窘境,他预感到他的命运,他以“疑问”的方式将行动和命运连接在一起;他知道这里面有一个解不开的“谜”,这一“谜”昭示着他行动的意义;就像雷电撕开乌云,他要解开这个“谜”;然而他能力有限,他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力量,而这一力量将导致他的毁灭,但他必须依持此种力量完成自己;只有完成自己,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奉献出来,他才能在最终毁灭的电闪雷鸣中感到某种欣慰:那个“谜”已经展开。然而,电光过后,乌云四合,我们又被黑暗笼罩,并在此黑暗中领悟着他生存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悲剧主人公,甚至包括麦克白,都是“悲剧英雄”。而悲剧则因为展示了人对自身命运的毁灭性“疑问”幻象,而成为人类向其自身献祭的精神祭坛。悲剧人物的这种“英雄气概”,与那种肤浅的乐观主义无关。
悲剧中的“窘境”只是生存之谜的表象,并非悲观主义的绝望。悲剧和乐观主义不相容,但它也并非其反面——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否定一切价值,并以绝望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叔本华把悲剧归入他的哲学,因而使悲剧成为悲观主义的,正如黑格尔把悲剧纳入其哲学并使它成为理性乐观主义的一样。如果悲剧真的以表现痛苦、不幸、毁灭为目的,那么它不是处于悲观主义的中心,也至少是徘徊在其领地的边缘。然而悲剧尽管显示了“人生可怕的一面”,但这不是悲剧的目的。悲剧是“疑问”。虽然它不给出明确的结论,但“疑问”始终意味着有所“疑问”,而这是出于“生存是有意义的”这种内在信念。这不仅是悲剧能撼人心魄的原因,而且它还构成了悲剧的形而上学基础。在悲剧中,倘若没有这一形而上基础,“我们除了痛苦、悲哀、厄运、灾难和失败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34)]。
许多现代西方学者认为,经过古希腊、伊丽莎白和法国古典主义三个繁荣时代之后,悲剧已经“死亡”。这一说法虽然完全否定了现代悲剧,但仍然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悲剧艺术在历史上是以间断性的“奇峰异岭”的形式出现的。造成这一奇特现象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不过,我们不想在这里探讨这一复杂问题,而只想顺便指出:悲剧是一种“稀有植物”,它产生并繁盛于某些特殊的时代,这是因为它的生长需要特殊的土壤、雨水和阳光;它的独特性要求它所繁荣于其中的时代,在其精神方面有着一个健康的胃口;它以命运幻象表现生存之谜,并通过“疑问”把对生存的领悟保存在一个“谜”里,这也许是它不能繁茂于所有时代的原因。
有看法认为,悲剧衰亡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小说或电影。海伦·加德纳说:“假使我们放弃悲剧一定要采取戏剧形式的这种观念,那么,可以确凿无疑地视为悲剧的小说仍寥寥无几。”[(35)]这就是说,悲剧的形式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电影或电视剧也只是戏剧形式的进一步演化。我们认为,悲剧性是标志着悲剧本质的概念,它来源于悲剧,但作为一美学范畴,又不仅是就悲剧而言的。一部小说可以是悲剧性的,也可以不是;一首诗可以成为悲剧性的抒情,也可以成为别的什么;只有悲剧永远是悲剧性的,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有悲剧永远是悲剧性的”,这并非一个毫无意义的陈述。它表明悲剧有着区别于其他艺术种类的形式特征和由此形成的艺术视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悲剧思维”。悲剧独特的艺术视觉和思维方式表明,悲剧艺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在整体性的生存中“疑问”地把握生存的意义,乃是悲剧的历史宿命。
注释:
①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② (17) (18) 亚里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25、25页。
③ ④ (27) (28) 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3、72、28、70页。
⑤ (13) 汉密尔顿:《希腊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7页。
⑥ ⑩ 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4—196页。
⑦ (35) 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99页。
⑧ 克尔凯郭尔:《古老的悲剧主题在现代的反映》,见《悲剧:秋天的神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⑨ (11) (12) (16) (20) (23)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9、406、409、360、414、413页。
(14)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7页。
(15) (32) 歌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第303—304、302页。
(19) 卢卡契:《悲剧的形而上学》,见《悲剧:秋天的神话》,第50页。
(21) 桑塔耶纳:《悲剧的面目》,见《悲剧:秋天的神话》,第33页。
(22) 参阅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24) 布莱德雷:《莎士比亚悲剧的本质》,见《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第50页。
(25) (31) (34)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60、112、73页。
(26)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29) (30) (33) 尤奈斯库:《戏剧经验谈》,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9、632、6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