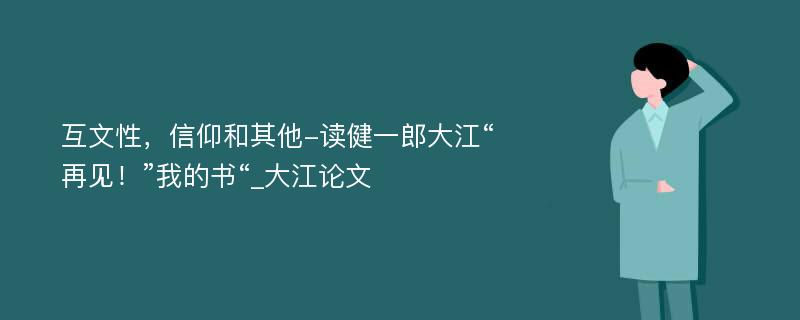
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读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别了论文,我的书论文,及其他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文性可以理解为作品之间的对话,古人、今人与来者的对话。它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一张强权之网或纯语言七宝楼台,反之,它建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因此既有历史的维度,又不乏作者个人的主体特色。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别了!我的书》(2005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法文系,他的小说创作深受欧美文学的影响,往往有互文性的特征。但是大江在自己与外国作家、作品的对话中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独立性。
一
假如《愁容童子》(2002年)是大江与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对话,那么它的续篇《别了!我的书》是作者与英国诗人托·斯·艾略特的对话。后者的故事情节始终与主人公阅读艾略特诗作《小老头》和《四个四重奏》的经历、感受交织在一起。
《别了!我的书》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是一位有成就的大作家,可以被认为是作者大江的化身。互文性是他有意追求的写作特色。他曾经这样说:“早在我刚开始写作那阵子曾有一位前辈鞭策我,‘要写互文性小说’。目前,我要解读出那些正是互文性小说要素的、包括人事在内的所有一切的、微小的、甚至有些奇态的‘征候’,并将其记述下来。”①此前古义(在小说中与“古义人”通用)告诉他儿时的朋友、也是他的“另一个自我”椿繁(也称繁),他要写一部“非同寻常的大厚书”,其整体内容可用“征候”一词概括。繁听到这词后问:“choko?是自传吗?”译者在此加了一条注释,指出日语中“征候”和“长江”是同音异义词,都发音为“choko”(275)。古义没有给予直接的回答。他自己的名字“古义人”在日文中发音为“cogito”,即笛卡儿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中的“我思”。②这时他又思考起来:“刚才所说的“征候”,首先就是sign,叫作表现、标志、征候……然后则是indication,好像也可以理解为行情、证据、疾病的症状等语义……也可以理解为symptom,作为预兆和标志,用于不希望出现的负面事态”(276)。也许小说既带有自传的成分,又是对“负面事态”的预警。叙事者古义要以自己的经历来提醒世人,国际上某些事态是不祥前兆,它们似乎指向“一条无可挽救的、不能返回的、通往毁灭方向的道路”(276)。古义信奉存在主义的“介入”之说,他个人的生活轨迹始终离不开战后日本政治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小说终章的题目就叫“征候”,可见“征候”或“长江”确实在作者构思作品时占有主导地位。该词很可能来自古义一直在读的艾略特的早期诗作《小老头》第17行——“征候现在被人看作奇迹。‘显个征候给我们看看!’”在原文中,“征候”一词用的是“sign”。“显个征候给我们看看!”③是不信耶稣的法利赛人的叫喊,他们要耶稣施神迹以显示自己的神性,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着神迹。”④在小说中,“征候”既是以战争为基础的世界新格局里的乱象,也是一次爆炸事件,它不妨理解为古义和他的同伴们发出的警示。
古义数十年前就在东京附近的北轻井泽买下一块林中空地,并请繁设计、建造了一幢房屋,取名“小老头之家”。古义在获得一项世界文学大奖后,又在“小老头之家”旁另建新宅。繁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建筑系执教,因厌倦于“9·11”以后美国的一系列黩武政策回到日本,同行的有学生弗拉基米尔和清清,他们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中国山东的高密。繁想买下古义的地皮和房屋,作为他和一些年轻朋友在日本的活动基地。为了抢得重组世界秩序的先机,他们在秘密组织“日内瓦”的指挥下准备炸毁东京某一超高层建筑,实施所谓的“大决战”。照一般理解,这是一伙恐怖分子,但是作者非但没有把他们写成异类,反而突出了他们正常、人性的一面。古义几十年来反对日美安全同盟和不义战争,他倾听了繁等人意图制造这一事件的缘由,感到自己的另一个自我(“有着怪异之处的年轻家伙”)把他往那方向推去:“说实在的,关于繁今后要干的事,我不认为自己会采取不同的态度”(184)。古义并不希望这次爆破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他把自己心爱的“小老头之家”贡献了出来,并要以这一爆炸作为“征候”,向有组织的国家恐怖主义发出抗议之声。“小老头之家”是古义人生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彻底毁灭预示了古义绝望中的决心。在三岛由纪夫小说《金阁寺》(1956年)中,年轻和尚沟口有自卑情结,他焚毁永恒之美的象征金阁寺,想以此变卑劣为勇气,化缺德为热能;⑤古义贡献自己的居所纯粹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但是繁想在炸毁房子前去警察局作一番说明,掩盖政治抗议的意图。他的两位技术人员大武和小武提前实施爆破,拍摄了整个过程(小武因此丧身)并留给媒体一份声明,宣布要以此来推广繁发明的“unbuild/进行破坏”的理论与技法,从而使“自由的个人团体”能够对抗“现代世界的巨大暴力构造”(259)。事发后古义的态度暧昧不明。
从古义的自述中读者得悉,他早在19岁时就在大学学生会的书店购得深濑基宽翻译的《艾略特诗选》,这是英日对照版,附有解说,是古义常读之书。⑥诗选中的《小老头》一诗深得古义喜爱,购书十年后他写过题为“‘小老头’之家”的文章,后又以此作为自己别业的名字。在小说第一部第一章,年届七十的古义请中国姑娘清清朗诵《小老头》,清清说,诗歌开首部分素描的老人简直就是古义:“这就是我,无雨月份里一个老头儿,/让那小童念书给我听,企盼着天降甘霖。”清清所言恰是古义心里所想。古义和艾略特一样,年轻时就以“小老头”自况(18-19)。但是,《小老头》的创作受19世纪英国宗教思想家纽曼启发,也有宗教的维度,甚至可以被解读为一首上下求索信仰的诗歌,“风口里一个迟钝的脑瓜”所揭示的是现代城市生活中某种致命的欠缺。
我们再来看一个在艾略特影响下同音异义词的用法。古义因头部受伤住院治疗,出院回家那天,他在书房床上小憩后站起来走向书库,感到一阵眼花,他站立不动,品味着眼花这个词的语义。“迄今为止,古义一直把眼花这个词汇解释为眩晕,大多以目眩或耀眼为主。可古义现在感觉到的则是黑暗。”译者在此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日文“眼花”与“黑暗”发音都是“kurawu”。大江紧接着写道:“在这一片漆黑中,他一动不动地站立着。然后,他只取过一本书,便重又回到床上”(26)。这本书就是浅绿布面的深濑基宽的艾略特译本。在这一场合,“眼花”、“目眩或耀眼”与“黑暗”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一联想也可能由阅读艾略特而生发。在小说第183页,古义引用了《四个四重奏》之二“东库克”第三部分的头两行:
啊黑暗黑暗黑暗。人们全都去往黑暗之中,
那个空空如野的星辰的空间,空旷前往空旷
第一行诗的前半部分借自弥尔顿的《力士参孙》第80行至82行。原诗写的是古犹太人领袖参孙被非利士人剜目,面对正午的黑暗:
啊黑暗,黑暗,黑暗,在眩目的正午
无法挽回的黑暗,没有一丝白昼的希望
全部黑暗的日食!
一般艾略特诗歌的注释本都会引用弥尔顿的这几行诗供读者参考。“眩目”一词原文用的是“blaze”。大江读到这一出处时会想到,“眩目”与“黑暗”在日文中发音相同,真是巧合。小说中有关古义站起来感到眩晕的文字不是单纯的语言游戏,知道力士参孙典故的读者会细品它们微妙的潜台词。古义多次流露出悲哀,他几乎像参孙一样面对巨大的黑暗,但是身体虚弱,难有作为。力大无比的参孙不堪忍受胜利者的羞辱,抱住大厅的柱石,发力摇撼,柱石断裂,房顶崩塌,他与以色列的敌人同归于尽。参孙的勇敢自杀为他赢得犹太民族的敬仰,古义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二
当我们关注作者如何引用艾略特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什么没有被引用。没有出现的诗行对我们讨论这部小说的互文性以及背后的文化差异恐怕同样重要。大江一方面深深为艾略特的诗作所吸引,一方面又对艾略特的某些倾向有所防范、戒惧,因此小说的互文性还体现了作者主动的选择和复杂的意图。紧随前面所引的“黑暗”诗行的是艾略特作为一位基督教徒发出的肯定之声。大江有意与表示宗教信仰的文字保持距离,小心规避了以下两行诗。尊贵显赫的人物都进入黑暗,但是:
我对我的灵魂说,静下来,让黑暗降临在你的身上
这准是上帝的黑暗⑦(the darkness of God)。(第12行至13行)
“黑暗”转化为信仰,不幸转化为幸福的前兆。上帝的“黑暗”指的是一个深远莫测的世界,神圣而又神秘,常人无法凭世俗的经验来想象或理解,因而又是黑暗的。⑧但是这种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的宗教归属感并不属于大江。在“东库克”这一部分第23行至25行,艾略特重复了“我对我的灵魂说”。大江在第184页先引英文,再引日文,在此我们只用中文译文:
我对自己的灵魂说,静下来,不怀希望地等待,
因为希望经常是对错误事物的希望;不怀爱地等待,
因为爱经常是对错误事物的爱;
在古义人看来,不带希望与爱意的等待也适合他的情形,即所谓“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2006年来华访问时所作演讲的题目)。艾略特表达的则是一种宗教的等待,涤荡了杂念的等待,不求个人欲念满足的谦卑、温顺的等待。艾略特随后要重点表达的却被大江有意略去:
还有信仰
但信仰、希望和爱都在等待之中。
不加思想地等待,因为你没准备好怎样思想:
所以黑暗将是光明,静止将是舞蹈。(裘小龙译198)
当艾略特作品里出现谦卑肯定的声音时,大江总会小心地回避。他并没有在艾略特的皈依里发现一种能帮助他在全然不同的语境里取得信念的力量,更何况“上帝”之类的语言已被“十字军斗士”滥用。
这种警觉的回避在书中多处可见。《别了!我的书》是大江与艾略特的对话,全书三部分的篇名和卷首引言都来自艾略特的作品。第一部篇名“宁愿听到老人的愚行”来自“东库克”的第二部分——
我已不愿再听
老人的智慧,而宁愿听到老人的愚行,
他们对不安和狂乱的恐惧,(第43行至45行前半部分)
这几行诗也是第一部分的卷首引语。在小说第181页至182页,大江又一次引述了这些诗句以及第45行的后半部分和第46行:
他们厌恶被缠住的那种恐惧
他们惧怕属于另一人,属于其他人,属于上帝。
艾略特笔下有待克服的心境却被大江用来当成贴切的自我写照。中文“被缠住”在原诗里是用名词“possession”来表达的,意指处于某种完全被支配的状态。因此这些诗句可以理解为老人过分看重独立自主,实际上,要求不受羁绊的愿望已成为一种恐惧,在这恐惧心理的支配下老人不得安宁,迟迟不能做出归主的决断。艾略特要以谦卑的睿智来医治老人的愚行和恐惧,下面是两行未被引用的诗句(原文第47行和48行):
我们惟一能希望获得的睿智
是谦卑的睿智:谦卑是永无止境的。
有了“谦卑”(原文“humility”)就不会惧怕“属于上帝”(“被缠住”),同时信主又使它永无止境。这种恬淡和充实的平静是古义不断愤怒责问的灵魂所不能而且可能也会拒绝达到的境界。古义曾引用《小老头》第33行:“我洞悉这一切,还有什么理应赦免之物吗?”(34)⑨这语气是不妥协的。古义一直到老都无法像艾略特那样得到灵魂的安慰,他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呐喊,无法谦卑起来,这两行诗他当然不愿引用。
小说第三部篇名是“我们必须静静地、静静地开始行动”。在该部卷首和(全书的)结尾,大江两度引“东库克”最后(即第五)部分倒数第8行至第6行:
老人理应成为探险者
现世之所不是问题
我们必须静静地、静静地开始行动
原文是这样的:
Old men ought to be explorers
Here and there does not matter
We must be still and still moving
这里所说的“探险者”并不是指地理意义上的探险者,因此地域无关紧要(“Here and there does not matter”直译为“哪里都没关系”)。艾略特想说的是精神领域的探寻,然后说到辩证的静中有动(“be still and still moving”)。这一诗句并未结束,在原诗中也不见有“开始行动”的意涵,从字面上看只是“移动”而已。那么这移动取什么方向?下面是艾略特给出的答案——它指向一种无所不包的伟大:
Into another intensity
For a further union,a deeper communion
Through the dark cold and the empty desolation,
The wave cry,the wind cry,the vast waters
Of the petrel and the porpoise.In my end is my beginning.
进入另一种强度
为了进一步的结合,更深的沟通
穿过黑暗的阴冷和空荡的荒凉,
波浪呼叫,狂风呼叫,海燕
和海豚的汪洋。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
老人要敢于探索,静中有动地移向“另一种强度”,“为了进一步的结合,更深的沟通”。三个词(“intensity”、“union”和“communion”)层层推进,宗教的意义十分明显,最后一词“communion”更是基督教的常用词,指圣餐仪式或教徒之间的团契。往这一目标进发,还得勇敢穿过“黑暗的阴冷和空荡的荒凉”。“海燕”(petrel)一词有浓郁的宗教暗示,据一种较通俗的说法(见OED,《牛津英语辞典》)由圣彼得的名字演变而来。海燕紧贴海面而飞,仿佛就是圣彼得在耶稣的神助下踏浪而行。圣彼得初次履海,心里不免有点慌张,风浪一大,身体下沉,只得向耶稣求救。耶稣赶紧施以援手,同时责备他的门徒信仰还不够坚定:“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圣经·马太福音》14:28-31)“海燕”被用来凸现转意归主的过程非常贴切,同时又因与“海豚”并列,皈依的含义不是十分直露。这些诗句被作者跳过,说明他有所触动,故意略去。大江引用了最后一句“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但是不带任何得到救赎后新生的感恩和欢欣。也许作者更多想到的是故乡四国关于当地森林的传说。每人都在林中有一棵“自己的树”,树的根部是人们降生以前的灵魂的栖息处,人一出生灵魂就离开树根进入身体,死后灵魂又返回树根(19)。肉体的生活结束以后就是灵魂在树根生活的开始。
老人行动方向无法确定,这是大江的苦恼,也是他的力量。大江无法像艾略特那样最终有所依凭,而且确信世上的一切都将变好,“烈火与玫瑰化为一体”(《四个四重奏》最后一篇“小吉丁”的结尾)。他也曾为绿叶丛中孩子们的欢笑和水面上奇异的闪光(《四个四重奏》首篇“烧毁的诺顿”第一部分)所吸引,但是这些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上帝慈惠的体现,它们反而使古义独自面对大风的怒号和波涛的呼啸时更觉苍凉。没有彼岸,没有平静的幸福感,有待进行的将是一场艰苦的“记忆之战”。⑩虽然半个世纪以来古义的内心时时泛起艾略特的诗行,他又意识到自己另有文化归属,负有不同的使命。古义藏有很多法国作家塞利纳的作品和研究他的著作,那些图书是六隅先生(即大江的恩师渡边一夫)的遗物。他可能更像塞利纳在《长夜漫漫的旅程》(1932年)中所描写的那样,把目光死死投向自己所处时代的茫茫黑夜:“你必须不含丝毫谎言地说出在这个世界上曾见到过的人类的所有的堕落。然后,你就闭上嘴巴进入坟墓之中。作为人这一生的工作,只要做了这些也就足够了”(163)。这种语气不见于艾略特加入英国国教(1927年)后创作的任何作品。
三
大江在引用艾略特时有一种隐隐的抗拒,这并不是意味着他认为艾略特在信仰上误入歧途。古义如此爱读但丁和艾略特,但自己却没有加入基督教会,引起繁的困惑。一天夜深人静,两人把酒畅谈。作者通过繁告诉读者,在古义很亲近的人中间,有的已悄悄皈依了基督教并有了信仰,古义却并不知道,如六隅先生、篁(著名作曲家武满彻)和吾良(著名导演伊丹十三,大江的大舅子),他们其实都是教徒。繁说,没有信仰者就像被洪水卷裹着的人,他们手里抓不住任何有根柢的东西。这种悲惨生活过了一辈子也不愿自杀,真是无法解释。繁是清醒的,认识到自己随波逐流的生活缺乏意义,虽然在从事被他称为“unbuild”的爆破工作,也是三心二意。此前发生的一起所谓“交通事故”其实是他自杀未遂(194-195)。就在繁发表这一通意见的时候,他听到了古义发出哭声:“‘古义,眼下你是在哭泣吗?咱可是听到那哭泣了。即便你是在模仿哭泣,也是过于逼真了,因此让咱吓了一跳!’说完这话后,(繁——引者注)便开始在睡眠中发出粗重的呼吸”(200)。这是从古义的视角来描写的,实际上他是在真正哭泣。繁几天前驾车时神情恍惚,求死未成,回到生界,依然有一种“被突然的虎头蛇尾打垮了的气馁和疲劳”(197)。此刻他语虽沉痛,心里却有点麻木,很快呼呼入睡,而古义可以说彻夜不眠。
上面的引文是小说第二部分的最后一段。从这一细节可见,古义对信仰问题看得很重。正因为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他不能为了灵魂的安妥或个人的解脱匆匆入教,仿佛教会是个满足自己情感需求、使用便捷的避难所。他为世俗的黑暗所包裹,无法像艾略特诗中所言,静候“上帝的黑暗”(也是一片光明)降临,为此他有刻骨铭心之痛。他读艾略特的诗和关于他的传记、研究著作,(11)深深感动,但又因时代、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某种独特的个性,未能完全进入艾略特的世界。他在大量引用艾略特的同时一次次谨慎地在可能涉及积极宗教内涵的诗行前止步,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性是自己求信仰而不得的必然结果。他意识到那些诗行自己如此钟爱,却没有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英国哲学家麦可·泰纳曾经讨论过非基督教人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欣赏基督教音乐的问题(Tanner 127-47),古义感叹自己对艾略特的诗作毕竟还有点“隔”,为这问题的复杂性做了很好的注解。古义是一位细心出色的读者,他知道,《小老头》尽管是艾略特的早期作品,也是对信仰的探索。这里是古义痛苦的自省:
在自己前行的途中,倘若那一天,把下面这节诗果真作为自己的东西而接受的那一天到来——
新年又在等待春天
猛虎基督往这里来。[《小老头》,第19至20行]
如此怀着可怜的期待并流淌着泪水,即使过去了十五年。
新年里猛虎跳了出来。将我们,吞噬。[《小老头》,第48行]
也从不曾有过如此体验,现在,已然成为一个没有信仰的小老头。古义人在想,在自己的心底里,较之于五十来岁——那般带着醉意哭泣、像是在苦苦劝说位于远处的某人——时的自己,现在更觉得凄凉。(109)
含泪期待,但是始终无法顺利抵达;与自己搏斗,与上帝搏斗,拒绝轻松自如地入教。古义身上透出一种绝不马虎通融的精神,一种已经具有宗教意味的真诚。前面提到的泰纳还曾在“时间的考验”一文里比较了艾略特与弗兰克·雷蒙·利维斯朗读《四个四重奏》时的不同风格。他并不欣赏艾略特为自己诗歌所作的录音,指出那是“专为亲罗马的英国国教徒录制的”,而利维斯在剑桥英文系讲堂对该诗的诵读却独具特殊的品质,那是“对宗教信仰可能性的令人激动不安的探索”(泰纳209)。利维斯对艾略特的宗教选择颇多微词,但他本人晚期的批评论著却多炽热(有时是坏脾气)的终极关怀,然而他的虔诚不能轻易纳入教会轨道。古义晚年时“更觉得凄凉”,但是他从未停止探索,从未停止“带着醉意哭泣、像是在苦苦劝说位于远处的某人”,也许他对艾略特的阅读与利维斯有可比之处。艾略特本人曾在比较信仰上的怀疑主义和皮罗(12)主义的差别时肯定了怀疑主义为信仰的动力一说。他认为怀疑主义——“检验证据的习惯和推迟决断的能力”——是“高度文明的特征”,(13)古义几近执拗的认真和怀疑精神实际上已经带有一点基督教文明的色彩。他没有像好友吾良和恩师六隅先生那样投入教会的怀抱,但他深感无所依凭的个人是莫大的缺憾,(14)这就使得小说中有一种中国读者可能十分容易忽略的维度。大江在访华时多次提及鲁迅,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出于对中国的礼貌。鲁迅从来不会感到一个独立的、愤怒的、嘲讽的个人会有什么不足。
小说中来自山东高密的中国姑娘清清感觉敏锐,她在为古义朗读艾略特的过程中发现他并不是基督徒。古义的回答十分简短:
“我没有信仰。”
“那么,你也就不把愿望寄托在死后,是吗?”
“也有人虽然不信仰基督教,可对自己死后的社会发展寄予了愿望。然而就我而言,已不再考虑在自己死后,世界的毁灭和核武器的废除这两者谁更可能”。(223)
这句话道出了古义一生最大的关切:核裁军乃至彻底销毁核武器。半个多世纪来核竞赛使人类一直处于危险的状态,大江坚决反对的立场在日本是极具代表意义的,中国作家和读者一般不会感到这种关怀的紧迫感。不过古义提出“两者谁更可能”,依然是发出警告,表明他并非真正万念俱灰。
四
国际上某些势力热衷于武器和霸权,为消灭地上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使“硫磺与火”从天而降(《旧约·创世记》19:24)。古义为此绝望,并像创世纪中的亚伯拉罕那样产生疑问:世界最高的仲裁公正吗?这也许是他与基督教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因。亚伯拉罕最终向上帝的绝对权威屈服了,古义依然透过一双泪眼独自寻寻觅觅。他“没有信仰”可能还另有道理。那是古义和他的创造者身上带有中国和日本文化特色的隐衷——对某些情况下自杀行为的认可。
大江在他早期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年)就写到过自杀问题。在《别了!我的书》里,叙述者古义依然在为是否应该自杀而烦恼。小说起首说,古义身负重伤,(15)入院治疗后身体虽然慢慢复原,却一直在思考着究竟应该“前往彼界”还是“退回此界”。前者就是指自杀,后者则指配合医生,接受治疗。自杀的原因一则是可以结束因伤而产生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二则是“自己老大无成且率性而为”(5)。最终古义决定忍受痛苦的煎熬,“退回此界”。小说序章的题目“看呀!他们回来了”取自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中的最后一首“小吉丁”的第五部分:
我们与濒死者偕亡。
看呀!他们离去了,我们也要与其同往。
我们与死者同生。
看呀!他们回来了,引领我们与其同归。(9)
古义喜爱《四个四重奏》以及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如作品第132号),因为这些作品都有着对死亡的循环往复的思考。与艾略特截然不同的是,古义脑际时时浮上自杀的念头(这不是艾略特作为一个基督教徒会探讨的问题)和自杀者的形象。弗吉尼亚·吴尔夫曾在日记中记述,年幼时走到一个水洼边,无法跨越过去,这时思考起自己存在的意义来。古义注意到这一细节,并说从那一刻直至投河自尽的近五十年里,吴尔夫度过她“刻苦勤勉的一生”(266)。古义的心头还萦绕着其他自杀者的形象。
在政治上而言,大江与三岛由纪夫代表了日本战后背道而驰的两种思潮。晚期的三岛由纪夫所追求的恰是大江愿意舍生抗拒的,两人目标虽异,追求的方式却可能相仿。小说里特别提到,新出的三岛由纪夫全集里有一封信函讲到古义自杀未果。有记者死皮癞脸地向古义打听这传言是否属实,古义的挚友吾良不得已出面对付记者的追问。吾良搬出了古义不会自杀的理由:“因为,他害怕在但丁的《地狱篇》第十三歌中的自杀者森林里被变成树木!”(198)(16)这细节是古义在与繁夜间长谈时回忆起来的,他们当时在讨论是不是会有下意识的自杀冲动。基督教徒不主张自杀,(17)问题是古义并非教徒。
在《愁容童子》中我们读到这样的内容:古义写文章悼念导演古良之死,他引用了但丁:“吾之灵魂为愤怒所驱,愿以一死摆脱诽谤,将以非妥之自杀,明证吾身之清白”(311)。经笔者查核,这些文字就是《地狱》十三章的第七十至七十二行。(18)说话的人是彼埃尔·德拉·维涅(Pier delle Vigne,约1190-1249),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重臣。他于1249年被控谋反,入狱后被剜目(参孙也遭此酷刑),不久饮恨自尽。但丁没把他打入背叛者所居的地狱最底层,而将他置于自杀者的行列,大概相信他是受人谗害,有意为之申冤。按照当时的基督教神学,自杀是不赦之罪,但丁还是毫不含糊地把他扔入地狱受罚。古义用彼埃尔的语言为古良辩护,仿佛他是以小恶(自杀)求大善(清白),这种价值取向完全背离了基督教反自杀的基本原则。我国古代说到自杀,往往指忠贞节烈的人士引泱自裁,以义灭身。孟子说:“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下)》)。屈原自投汨罗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 (或非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缺少像奥古斯丁那种对卢克莱西亚和加图等自杀案例的批判性分析。(19)古义是这种文化的产物,与基督教严禁自杀的立场难以一致。如果为局势所逼迫,已经献出了自己身体居所的古义会再献出他灵魂的居所吗?这是一个不忍的问题。
写毕于2007年9月18日(20)
注释:
①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276。以下该小说引文页码在正文中用圆括号注释标出。
②见大江健三郎,《愁容童子》326。大江先生常用的一枚闲章上刻着“think,write”两个英文动词。
③“神”版圣经这一句是“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④《新约·马太福音》第12章第38节至39节。耶稣到加利的迦拿,一大臣求耶稣为他儿子治病,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signs and wonders’),你们总是不信”(《新约·约翰福音》4:48)。
⑤《别了!我的书》第57页提到弗拉基米尔在读俄文版的《金阁寺》。
⑥小说中还提到上田保、健谷幸信合译的《艾略特诗集》和西胁顺三郎译的《四个四重奏》。大江在《别了!我的书》中引用艾略特诗句时使用的是这三种译本。
⑦为突出视觉效果,凡未被大江引用的艾略特诗句用黑体标出。下文均同。
⑧艾略特在《小老头》中有类似的表述:“道中之道,说不出一个词,/裹在黑暗中。在一年的青春期/基督老虎来了。”艾略特在这几行诗里引用兰斯洛·安德鲁斯的布道文,但有误。See B.C.Southam,A Guide to the Selected Poems of T.S.Eliot,6th ed.(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96)71.“The word within a word”应该是“The word without a word”。“裹在黑暗里”原文是“swaddled with darkness”。“道”可以解释为上帝、逻各斯。
⑨英文原文是“After such knowledge,what forgiveness?”
⑩古义引用米兰·昆德拉小说中一位人物说的话:“对人世间的权利所进行的战斗,就是对忘却所进行的记忆之战”,参见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163。
(11)小说中提到的林德尔·戈登的艾略特传,牛津学者海伦·嘉德纳和诗人、批评家斯斯蒂·斯彭德研究艾略特的著作都是很有名的。大江对后面两位尤为推崇。
(12)皮罗,公元前4至3世纪希腊怀疑主义哲学家,认为来自理性和感觉的知识皆不可靠,天下没有善恶荣耻,对一切都不应执着。皮罗哲学也含合理的文化相对主义成分,见蒙田长文“雷蒙·瑟朋赞”。
(13)T.S.Eliot,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London:Faber and Faber,1962)29.参看艾略特对丁尼生长诗《悼念》的评论。他指出该诗因其怀疑的品质而可以被称为“宗教的”。T.S.Eliot,Selected Essays (London:Faber and Faber,1951)336.
(14)真正的存在主义者不会因此苦恼。也许强调大江早年受存在主义影响也应该有个限度。
(15)受伤的过程中似有自杀的冲动,见《愁容童子》最后部分。在这本书的起首(第3至4页),古义人在海边喝了点威士忌后踏入海水,想彻底摆脱种种烦恼。笔者从许金龙先生处获悉,在带有自传成分的《大江健三郎述说作家自我》(日文版2007年6月)一书中,自杀的话题一再出现。这部新作已译毕,新世界出版社即出。
(16)见但丁《地狱篇》第13歌。在但丁设想的地狱第七层第二环,居住着那些已变成树的对自己施以暴力者,他们被剥夺返回肉身的资格,永世不得救赎。重新读小说第19页上所说的“自己的树”,可能会体味出新的含义。“自己的树”与自杀者森林里的树木也形成互文关系。
(17)参看吴飞:《自杀与美好生活》(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18)比较田德望译文:“我的心激于愤懑的反抗情绪,想以死来逃避人们的愤怒和轻蔑,致使我对自己这正义的人做出了不正义之事。”参看田德望译:《神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92。
(19)见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一卷。
(20)英国作家乔纳森·雷本在“9.11,我们付出的代价“一文(载2006年9月8日《独立报》)里提醒读者,在纪念“9.11”的时候我们也要记住“9.18”,在2001年的那一天,美国国会通过授权总统使用武装力量法 (英文简称“AUMF”)。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6年9月11日举办的“大江作品研讨会”上特意介绍了这篇文章,相信在场的大江深有同感。
